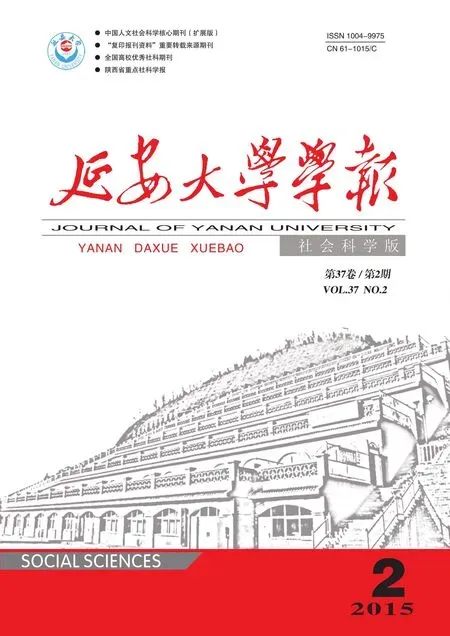义分则和——荀子礼制建构的内在理路及其仁爱基础
张 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义分则和
——荀子礼制建构的内在理路及其仁爱基础
张 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荀子思想的核心绝不是屡遭非议的性恶论,其核心关切乃是群体生存秩序的安排与建制,即“礼制”。基于群体生存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荀子根据“义分”的总原则构建出互摄互涵的“政治—伦理—经济”多维立体的社会基本礼制结构,其终极目的一方面指向个体欲望的合理表达与满足,另一方面指向群体生存秩序的和谐稳定以及群体本身的日益强盛。荀子的礼制建构内蕴着深刻的仁爱基础,正是作为本源情感的仁爱产生了利欲,利欲导致了冲突;同时,亦正是仁爱情感要求依据正义原则来建构制度规范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荀子;礼制;仁爱;义;利益;和
荀子思想的核心绝非历来备受关注与屡遭非议的“性恶论”,其核心关切乃是群体生存秩序的安排与建制,用儒家的言说方式表达即是“礼制”*“礼”在古典文献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涉及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既指日常生活中人们具体的行为规范,如“婚礼”、“丧礼”、“祭礼”等礼仪;又涵摄维持群体生存秩序的基本社会制度,“礼”的这一维度即是“礼制”。当我们使用“礼乐文化”来指称“华夏文明”时,固然蕴涵日常生活中的个体遵守具体的礼仪规范这一维度,但是,这一词汇应当首先在制度文明即“礼制”的层面来理解。。荀子的礼制建构有着清晰地内在理路及其仁爱基础,本文尝试阐明之。
一、礼制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论及群体生存秩序的安排与建制问题,首先要说明的即是“群”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问题。事实上,当我们着眼并陷溺于荀子对人性的讨论中时,悄然忽视了荀子对“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即“人是群体的动物”*这一论断是比照亚里士多德“人是城邦的动物”这一尽人皆知的定义而作,并非荀子真有此言。亚氏在《政治学》中明言:“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至9页。)。这一根本规定优先于荀子的“性恶论”及其他对人性的规定,因为荀子关于人的一切讨论皆是在“人是群体的动物”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可以说,这是荀子讨论任何问题的根本视域所在。
荀子对“人是群体的动物”的论证分为两个层次。首先,荀子认为人必然要生活于群体之中,正所谓“离居不相待则穷”(《富国》)。就个体与动物的区别而言,个体之人的能力远远逊色于大部分动物,即使是最常见的动物如牛、马,个体之人只能是“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王制》)。不必求之于人类学、考古学的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个体之人不生活于群体之中,而是孤立地生活于世,结果只能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惶惶不安、苟延残喘。就个体与个体之间而言,个体之人的欲求是多样的,但其能力却是有限的,正如荀子所谓“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富国》)。因此,与在个体之间合作下的群体生活相比,孤立的个体生活乃是贫乏困顿的、不值得欲求。
其次,荀子认为个体在群体中生活是可能的、可行的,即人“能”生活于群体之中。虽然个体之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是牛、马等皆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如果在群体中生活的人能够实现完美的合作,荀子认为则能“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胜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王制》)。但是,荀子敏锐地意识到,个体虽然“不能无群”,但是,和谐有序的群体生活的维系依赖于利益分配的正当与否。“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分则和。”*王念孙认为:元刻本没有“以”字,文中“曰义”与“曰分”对文,则不应当有“以”字。王先谦认为王念孙的观点是对的,故根据元刻本改正。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兴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3页。(《王制》)如果不能进行“义分”,结局只能是“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住也”。(《王制》)
荀子正是从群体秩序的治乱与否来定义“善”、“恶”。荀子明言:“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性恶》)群体生存秩序的正理平治即是善,反之即是恶。由此我们反观荀子的“性恶论”,则可以明晰:荀子的“性恶论”绝非本质论意义上的“性本恶”,而是结果论意义上的“后果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很明显,如果放纵人的欲望,则群体秩序就会变得“偏险悖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而人的欲望本身并不能谓之“恶”,因为欲望本身的存在并不会导致群体生存失序。徐复观指出:“他(荀子)的性恶的主张,只是从官能欲望这一方面立论,并未涉及官能的能力那一方面。官能欲望本身不可谓恶,不过恶是从官能欲望这里引发出来的;所以荀子说‘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问题全出在‘顺是’两个字上。”[1]209准确地讲,欲望本身的存在之所以不可谓之“恶”,乃在于群体秩序的治乱与欲望本身无关。荀子指出: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正名》)
这一段话对于理解荀子的“性恶论”乃至于整个思想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说荀子的核心关切是群体生存秩序的安排与建制,那么上述引文明确表明:欲望是生来具有、不待可得的,那种禁欲、寡欲的主张是将人异化为“非人”的“异类”;群体生存秩序的治乱与否与欲望之多、寡没有实质性关联,群体生存秩序的安排与建制取决于人生而具有的认知能力,即“治乱在于心之所可”。“所谓‘性恶’不外是说‘人而有欲’,这种利益欲求之所以被判定为‘恶’,并不是因为它违反了道德规范,而是因为它导向‘争’‘乱’‘穷’,这无论对于群体还是对于个体来说都是有害的。这显然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上文谈到的认知能力方面的利害判断。因此,‘义’的对立面并不是‘利’,而是‘害’。”[2]137基于上述立场,荀子认为礼制建构的目的在于“养欲”,而绝不是“寡欲”、“去欲”乃至于“禁欲”。正所谓“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礼论》)。
由上可知,荀子将人安置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来思考,即荀子所谓“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富国》)。杨倞注曰:“不相待,遗弃也。穷,谓为物所困也。此言不群则不可,群而无分亦不可也。”[3]前者着眼于群体生存的必然性,后者致力于群体生存的可能性。就逻辑顺序而言,群体生存的必然性优先于群体生存的可能性,然而,一旦群体生存的必然性得到论证,群体生存的可能性便成为荀子整个礼制建构的核心所在。而笔者之所以用大量篇幅来对荀子“性恶论”进行辨正*关于荀子的人性论笔者有专文作出探讨,参见氏著:《社会秩序之“善”与主体之“德”的融通——荀子人性论新探》,载《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目的是为了阐明礼制建构的终极指向乃是“养欲”,即使得人的欲望得以合理有序地表达与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认为荀子“以功利主义说明社会国家之起源,而与一切礼教制度以理论的根据”[4]。
二、礼制建构的制度安排及其原则
群体生存秩序建构的可能性根据在于“义分则和”,这正是荀子礼制建构的指导思想。对“义分则和”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在《王制》篇中: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胜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
荀子按照由低到高的次序将世间万物排成一个价值链条,通过这一价值链可以发现人之所以异于水火、草木、禽兽等的特质所在——义。但是,此处的“义”绝不是指个体的内在德性,亦不是指个体的行为正义,而是指作为“群分”之原则的“正义”。有意思的是,同处于“轴心时代”后期的作为中西方思想史上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与荀子对“人之为人”以及制度建构的原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为人所熟知的“人是城邦的动物”之外,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5]。荀子认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乃在于:人能够根据正义原则对群体秩序进行制度规范建构,从而保障群体生存的和谐稳定、物质财富的稳步增长以及群体本身的日益强盛。可见,荀子认为正义的制度安排能够能够产生良好的群体生存状态,既有益于个体利益的增加,又有益于群体的和谐与富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借用罗尔斯话语来表达荀子对制度正义的价值诉求,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3。
正义原则是为了解决群体生存秩序的制度建构问题,而制度建构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即是“利益”的分配问题,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6]7。荀子与罗尔斯处在不同的时空下,一个置身于轴心时代的中国,一个生活于当下时代的美国,他们关于社会主要制度的具体建构方式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但是,真正具有启发意义的并不是站在当下的立场去求二者之异,恰恰是寻求二者的共通性,以窥探出人类社会存在的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基本问题。此基本问题即是:古今中外的任何社会,必然需要社会主要制度的基本安排,而建构社会主要制度的核心目的即是通过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广义上的社会利益。
那么,荀子是如何对社会主要制度进行安排的呢?荀子明确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承认社会差等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维齐非齐。’此之谓也。”(《王制》)如果社会基本制度的安排致使利益分配是绝对平均的,其后果只能是:一是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源,即“不一”、“不使”、“不能相事”等等;二是社会运行缺乏内在动力源会致使社会资源极度缺乏,从而导致群体的争乱,即“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正是基于上述立场,荀子批评主张“尚同”、“兼爱”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并针锋相对地言明:物质财富的不足并非天下之公患,社会基本制度安排得当即可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的绝对平均主义才是天下之公患,此乃“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富国》)。因此,荀子认为,群体由偏险悖乱转向正理平治以及富国强兵之道皆在于“明分”,正所谓“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富国》)。荀子明分的总纲领及其目标乃是:“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也。”以分析的视角来看,“贵贱有等”指向政治权力——身份及其义务的规制,“长幼有序”强调社会伦理秩序的安排,“贫富轻重”关涉经济利益的分配。以综合的视角来看,政治、伦理、经济这三者的制度建构乃是互摄互涵、深度关涉的。可见,荀子以“明分”为中心的礼制建构乃是一个“政治—伦理—经济”多维立体结构;并且,从建构顺序而言,政治上的规制优先于伦理上的安排,伦理上的安排优先于经济上的分配。因此,荀子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王制》)通过多维立体的制度建构使得“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不但能够保证群体和谐有序的生存状态,而且能够实现“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王制》)。
礼制的安排固然可以使人各得其“位”,形成稳固的社会结构,但是,荀子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结构的固滞依然会导致群体的争乱。因此,荀子认为,处在每一“职分”上的人应该“称位”,即“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篇》),从而切实有效地做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富国篇》)。难能可贵的是,荀子认为应该实现社会结构内部的“职分”之间的动态互补、良性循环。“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由此可见,荀子不仅主张庶人可以通过自身之努力改变原有的生存现状,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身份与地位;更是认为,如果身在较高“位”者,不能符合自身所处职分之要求,则必须给予其降低社会身份与地位之处分,正所谓“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儒效》)。
古今中外的任何社会,必然需要也必定存在着社会主要制度的基本安排,荀子礼制建构符合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潮流,因此,其所建构的“政治—伦理—经济”多维立体结构在当时便是正当的。然而,以现代性视域审视荀子所建构的礼制,毋庸置疑,其中必然包含很多“不合时宜”的主张,比如其在政治秩序上所建构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荀子所建构的礼制难以穿越时空的牢笼而直接切入当下,这种诉求不仅是迂腐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之所以迂腐,在于其违背儒家制度建构的根本传统——礼有损益*《论语·为政》篇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事实上,儒家虽然注重“礼”,但绝不仅仅停留于对礼仪的简单遵守以及礼制的因循守旧,而是主张“礼有损益”。;之所以有害,在于其违反现代性生活方式下的人类基本价值诉求。真正的问题是,荀子礼制建构所依凭的超越时空的具备普适性的正义原则(礼有损益的原则)极其容易且事实上已经为我们所遗忘。正是基于此,黄玉顺犀利而深刻地指明这是“一个传统的集体失语”[7]3,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正义论’”[7]3。在论及荀子的正义理论时,黄玉顺详细地阐明了中国正义论的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与适宜性原则,其中正当性原则又可以具体划分为公正性准则与公平性准则,适宜性原则又可以具体划分为时宜性准则与地宜性准则。[2]138-141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变动不居的乃是制度及其行为规范,而真正超越时空的乃是制度及其行为规范所赖以建立的普遍性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正义论缺乏规范与制度、规范与原则的区分因而并不是普适的正义论而仅仅是一种“现代社会正义论”。[8]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地域化深度缠绕的今天,不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建构制度规范必须依据于上述普适性原则而行,才能真正实现荀子所期盼的“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王制》)。
三、礼制建构的仁爱基础
荀子通过正义原则建构赖以维持群体秩序的社会基本制度,即根据“义”来建构“礼”。荀子虽然常常“礼义”并举,但对于任何一位儒者来说,主张“仁爱”才是最为根本的。那么,仁爱与正义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事实上,这牵涉到对荀子思想内部“仁爱”、“性恶”、“正义”之间关联的理解,而对“性恶”的阐明构成释读三者关联的关键环节。对此,《礼论》中的一段文字充分暴露出“仁爱”与“性恶”之间的张力,对这段文字的阐明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礼论》中指出: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损益也,故曰无适不易之术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踰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焦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礼论》)
对于这段文字,王国维认为:“然先王之制礼果何本乎?……考荀子之真意,宁以为(礼)生乎人情,故曰:‘称情而立文’。又曰:‘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荀子之礼论至此不得不与其性恶论相矛盾,盖其所谓“称情而立文”者实预想善良之人情故也。”[9]很明显,王国维将“称情而立文”之“情”理解为“善良之人情”。据此“善良之人情”而“立文”显然与荀子的性恶论相悖。徐复观也认为,“从他的这一段话,他把‘知’与‘爱’作必然的联结,则是人心之有知,即等于人心之有爱;因而从这一点也可以主张人之性善。因此,他的性恶说,实含有内部的矛盾。”[1]226的确,在这段文字中荀子一反常态,将其严厉、苛刻的外表卸下,露出含情脉脉的内心,似乎勾勒出一幅人性本善的社会图景;以致使读者百思不得其解,纷纷诘难其思想自相矛盾。前文已经提及,荀子的性恶论并不是本质论意义上的“性本恶”,仅仅是结果论意义上的“后果恶”,而后者指向欲望的过度放纵所导致的群体生存秩序的悖乱。但即使澄清了荀子“性恶论”的本意,这里似乎依然存在着悖谬之处:如果人生而具备仁爱之情,即荀子所谓“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那么,又该如何安置荀子所说的“人生而有欲”的自爱自利之实情呢?
化解这一悖谬的关键即是充分注意荀子这段文字所针对的乃是“三年之丧”。事实上,对丧祭的重视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孟子以及荀子对丧祭都极为重视。《论语》记载: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对此,朱熹注曰:“致,尽其极也。盖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同时引尹氏注曰:“亲丧固所自尽也,于此不用其诚,恶乎用其诚。”[10]可见,处于“亲丧”这一生活情境中的人易于实现情感上的复归,即回归本源情境,从而本真的仁爱情感得以显现,此乃儒家所说的报本反始、返本复初。“报本反始”、“返本复初”强调的是处于日常生活之沉沦状态的生命存在向作为生命之终极根据与来源的本真状态的复归。事实上,“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这句话的论域已经远远超出人类本身,根据荀子对水火、草木、禽兽以及人的规定,这句话涵摄世间一切存在者。因此,这句话并非仅仅指向“人”而言,即并非是说“人”生而有知、知而有爱,而是处于前主体性、前对象化的本源情境中对本源情感——仁爱的本真领会。荀子认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立足于对象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天、地、人、神乃是截然分离、各归其位的;然而,在前对象化的本原情境中,荀子笔下的天、地、人、神乃是“不分彼此”、“共同在世”的。至关重要的是,本源情境中的仁爱情感并不是说“人的情感”,而是先于人并给出人的本源情感。*关于本源情境与本源情感的详细阐明,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至222页。因此,荀子只有在处理丧祭之礼时才会一反常态的言明:“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正是基于本源情境、本源情感,我们才说仁爱是一切的大本大源。“如果说仁爱确实是所有一切事情的大本大源,那么仁爱必定也是善与恶的共同来源。荀子彻底坚持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爱’,由此出发阐明一切问题,包括‘恶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荀子比孟子更彻底。”[2]137基于此,荀子明言“仁者自爱”(《子道》),因此,正是仁爱本身导致了利欲,利欲导致了冲突;同时,亦正是仁爱本身要求依据正义原则来建构制度规范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于此,上述王国维与徐复观所诘难的悖谬便得到圆满的解决。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黄玉顺.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J].社会科学研究,2012(3).
[3]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兴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174.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79.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8]黄玉顺.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J].社会科学战线,2013(8):27-33.
[9]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215.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1.
[责任编辑 高 锐]
2015-02-07
张 新(1991—),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B222.6
A
1004-9975(2015)02-00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