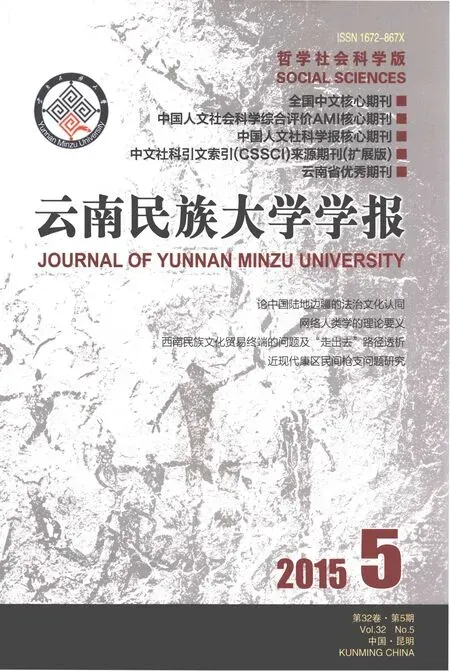网络人类学的理论要义
卜玉梅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由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发展所引发的信息化、数字化,正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全面塑造着人类社会新的面貌和社区形态。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随之兴起,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机构、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也纷纷涌现。由之,人类学家也开始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针对网络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并致力于构建网络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下文将对网络人类学的发展进程、研究范畴和方法论等问题予以述论,以期厘清这一新兴人类学领域的脉络和进展,推动网络人类学作为独立人类学分支的制度化发展。
一、网络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等在《当代人类学》杂志发表文章《欢迎来到网络世界:有关网络文化的人类学笔记》,提出进行“网络文化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研究的设想,以涵纳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与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研究的人类学研究。埃斯科瓦尔认为,这些新技术给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和意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们不仅以文化的建构和再建构为基础,同时也反过来形塑文化。因此,网络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就是要关注这些新技术所建基并反过来形塑其自身的文化建构和重构。①Escobar A,Hess D,Licha I etc.,Welcome to Cyberia: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Current Anthropology,1994,35(3):211-231.埃斯科瓦尔将网络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置于“科学技术研究”的脉络中,将网络文化作为理解和实践技术的背景,凸显网络文化研究对理解现代性本质的意义。在不少学者看来,埃斯科瓦尔这一论文的发表即意味着“网络人类学” (Cyber Anthropology)的雏形开始出现。例如,斯博朗德J.布雷耶以此指出,作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分支之一的“网络人类学”自此产生。②Sprondel J,Breyer T,Wehrle M.CyberAnthropology– Being Human on the Internet,2011.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CyberAnthropology%E2%80%93Being+Human+on+the+Internet&btnG=&hl=zh-CN&as_sdt=0%2C5.菲利普·布德卡也断然认为,网络文化的人类学也即网络人类学。③Budka P,From Cyber to Digital Anthropology to an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Working Paper for the SASA Media Anthropology Network,2011.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From+Cyber+to+Digital+Anthropology+to+an+Anthropology+of+the+Contemporary&btnG=&hl=zh-CN&as_sdt=0%2C5.可以想见,埃斯科瓦尔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网络人类学的概念,但他的理论和研究设想正符合其他一些人类学者的想法。在2002年韩国召开的有关虚拟系统和多媒体的国际会议上,“网络人类学”概念正式被提出,并随之成为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的常规会议议程。在大会上,学者对网络人类学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一个致力于对被视为复杂交互系统的人类想象世界进行心理生理学和心理物理学分析以及语义和符号学分析的概念和新领域。换言之,也就是关于人类处理其所创建的人工世界的方式的研究,涉及技术生成的人工现实与人类身体和精神的互动,或者说这种人工现实对人类所产生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①Thwaites H H,Cyberanthropology of Mo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Technology,Applications&Systems.ACM,2006.不难想到的是,这是一种带有体质或生物人类学取向的界定。实际上,网络人类学概念在名词构造上是对唐娜·哈拉维等所提出的“赛博格人类学” (Cyborg Anthropology)的借鉴。赛博格人类学是关于人类与机器之间互动的民族志研究,考察技术如何成为社会和文化生产的力量。②Downey G L,Dumit J,Williams S.Cyborg Anthropology.Cultural Anthropology,1995,10(2):264-269.网络人类学与之一脉相承,其前缀“cyber”取自20世纪40年代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iener)所使用的“cybernetics”一词,其意指人工有机系统中的沟通和控制。③Wiener N.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MIT press,1965.但是在此基础上,网络人类学的“cyber”已经完全超越了机器本身的意涵,而包含了更丰富和更广阔的人类生活空间。
经过多年的发展,网络人类学已经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发展速度较快,但依然难以进入主流人类学的领地。究其原因,其一在于学者之间对网络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如研究对象的混杂理解。按照人类学分支学科的设定通则,网络人类学即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网络文化。继埃斯科瓦尔之后,网络文化的概念逐渐脱离了最初所囊括的生物技术的意涵,泛指一切由计算机、网络技术带来的,或与计算机和网络相关的当代文化及文化产品,涵盖计算机文化、互联网文化、数码文化等文化形态。也有学者指出,网络人类学是对有组织的网络现实的研究,致力于理解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组织自我的方式所实现的新的社会建构。这些虚拟空间主要是基于思想相似性而构建的虚拟在线社区,而非以种族、宗教和语言联系或地理因素为纽带。网络人类学则关注虚拟空间中的所有人类互动。④参见http://www.cyberanthropology.net/那么,对于这些不同的表述,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呢?格尔茨认为,研究地点并非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落 (部落、城镇、社区等),而是在村落中进行研究。在此种意义上,技术也不是研究对象。我们是在技术中或技术背景中从事研究。⑤Rode,Jennifer A.Reflexivity in Digital Anthropology.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ACM,2011.也因此,用“在线社区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Online Communities)来概括人类学在这一领域的问题意识、方法和视角,⑥Wilson S M,Peterson L C.the Anthropology of Online Communiti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2,31:449-467.或者用“网络空间的和网络空间中的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and in,Cyberspace)的表述以提醒人类学者在技术所得以产生和运作的文化情境中研究技术,⑦Gray C H,Driscoll M,What's Real About Virtual Reality?:Anthropology of,and in,Cyberspace.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1992,8(2):39-49.类似这样的注解实际上顺应了人类学学科的传统和宗旨。而人类学在经历了多种转变之后,将核心视域转向了“文化”,因此,若说网络人类学便是研究网络文化的学科,其实也并无悖逆,只是对于网络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更多的概念化的工作。
其二在于,在不少学者踌躇满志致力于网络人类学分支学科建设的同时,另一种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即并不倡导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例如,针对网络空间所带来的新的社区类型和交往行为,威尔逊和彼得森认为,这些虽然值得人类学者关注,但是,人工构造物与生活世界 (artificial constructs and the life world)一直是民族志研究的中心。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创造全新的分析方法,而是运用现有的人类学专业知识对其予以研究。一句话,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新型人类学,而只是拓展了已有民族志研究的应用领域。⑧Wilson S M,& Peterson L C,the Anthropology of Online Communiti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2,31:449-467.这虽然不无道理,却略显保守。事实上,人类学自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尤其是二次大战以来,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愈来愈宽,研究的专题愈来愈细,因此学科开始分化,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如教育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技术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等。这些分支学科的出现无疑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人类学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增进相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当前,计算机技术的激速发展以及网络文化的日益渗透,也必然会对人类学学科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而网络人类学的产生正迎合和适应了这样的形势。并且,就人类学学科本身的特点而言,拥有特定方法和理念的人类学学科,可以实现跨文化、多层次、多点现象的调查,有助于了解新兴的沟通和社会实践的文化嵌入性质,因此可以说尤为适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说,网络人类学的确立既是时代发展所需,也是学术潮流所趋。
然而,任何分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都涉及核心概念的凝练、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立和相关资料的收集等工作。出于同样的初衷和志向,欧美学界产生了不同的实现路径。美国人类学界倡导网络人类学的研究和分支学科构建,英国人类学界所进行的则是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学科化建设的努力。丹尼尔·米勒与海蒂·盖斯马在伦敦大学学院设立数码人类学的硕士研究方向,开设相关课程,并出版了可作为教材使用的编著《数码人类学》。从《数码人类学》一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来看,数码文化涵盖从社交网站到数字化博物馆、从自由软件到数码游戏等对象。数码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有效地理解数码文化,分析数码科技的使用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①[英]丹尼尔·米勒,希瑟·A.霍斯特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总的来看,虽然网络人类学与数码人类学都是针对新的技术和文化的研究,但是从其所建基的理论脉络和学术传统来看,两者则差异甚为明显。网络人类学继承了美国人类学重视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传统,与美国的人类学分支相关联,而数码人类学则凸显了英国的物质文化研究,也因此与英国人类学关联。②Budka,P.,From Cyber to Digital Anthropology to an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Working Paper for the SASA Media Anthropology Network,2011.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From+Cyber+to+Digital+Anthropology+to+an+Anthropology+of+the+Contemporary&btnG=&hl=zh-CN&as_sdt=0%2C5.本文着重使用网络人类学这一术语,继续相关问题的探讨和论述。
二、网络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作为对计算机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知识形态的回应,一方面,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及其形态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人类学的一项工程,哲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各学科都对之倾注了诸多注意力,网络人类学要如何与之相区别并定位自身,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网络人类学必然要有不同于传统人类学的问题意识、研究范畴等,这同样需要作出明确的框定。
埃斯科瓦尔在提出“网络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设想时,将这类新的研究领域要关注的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现实的社会建构、人的社会化、人与机器的边界、不同社群的属性与体验、对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意义。具体涉及五个层面:(1)新技术的生产与使用。人类学研究可以关注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和专家、虚拟现实设计中心和技术用户等,以及新技术带来的主体性生产的民族志;(2)以计算机为媒介的虚拟社区。人类学研究不仅对于理解这些新的社区来说至关重要,还可以设想由这些新技术而产生的新的社区类型;(3)科学技术的流行文化。考察技术如何在审美和实用意义上融入日常生活,大众知识被重组的方式等;(4)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交往的增长和逐步发展,尤其是从语言、沟通、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的视角,关注由媒介本质引起的沟通和语言实践;(5)信息的政治经济学,探讨历史和全球语境下的社区,关涉信息分类和流动被创造和循环的方式,信息生产模式的统治机制的构建,网络文化兴起后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治关系等议题。③Escobar,A.,Hess,D.,Licha,I.,Sibley,W.,Strathern,M.,& Sutz,J.,Welcome to Cyberia: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Current Anthropology,1994,35(3):211-231.我们知道,自195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就已经开始研究新的现代技术及其对社会尤其是非西方社会的影响。在1970年代,人类学家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并由此出现了科技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产生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④刘珺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1期。受到科学技术人类学思维的影响,网络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在这一框架之下也具有了类似的问题意识,不仅关注技术本身的生产和应用,也关注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当我们以“网络空间的民族志”作为网络人类学的诠释时,应该聚焦于以下核心议题:(1)网络空间的实体的基本特征;(2)这些实体所形成的自我认同;(3)这些实体所构建的微观的、亲密的社会关系 (如与亲密朋友的关系);(4)中观的中介的社会关系 (如社区、地区和公民的关系);(5)其宏观的社会关系 (如国家的、跨国的);(6)网络空间实体生产和再生产并受制于它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些议题将网络空间视为人类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文化空间,而社会互动的这些层面要求民族志学者关注“成为人的新的可能方式”。①Hakken D.Cyborgs@cyberspace?:An Ethnographer Looks to the Future.Psychology Press,1999.目前,不少人类学家对社交网站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社交网站的研究,被认为接近于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亲属关系这类社会关系研究,甚至可与库拉圈的研究进行对比。因为,库拉是文化的象征,是主体间时空的载体,类似于脸谱(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亦是如此。②[英]丹尼尔·米勒,希瑟·A.霍斯特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182页。
涉及到作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的网络生存,网络人类学还需回答,在互联网所构筑的环境中,人类是如何理解它自身和他者的,在嵌入到虚拟环境中时如何建构其生活世界。这需要考察的问题包括:互联网是一个新的虚拟现实,还是旧的规范和习惯的呈现?是否可以称“网络公民”?如果考虑到互联网超越了地方、地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界限这一事实,利益集团如何形成?新的边界和规范秩序如何出现?等等。概括起来也即三个方面:(1)虚拟现实的社会建构:生活世界和互联网的互动;(2)虚拟的人类活动;(3)生物性社会政治:虚拟人类的密切互动。由此,网络人类学的研究议程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1)虚拟生活的规范;(2)网络应用;(3)个体、他人和社会的感知与表达;(4)生活世界与互联网的互动:新的习惯、社会和政治网络的发展。③Sprondel,J,Breyer,T,& Wehrle,M.CyberAnthropology – Being Human on the Internet,2011.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CyberAnthropology%E2%80%93Being+Human+on+the+Internet&btnG= &hl=zh-CN&as_sdt=0%2C5.
总体而言,网络人类学是对一种新的技术文化,一种新的社会交往空间和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环境的全面关注。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整体性研究。这主要涉及技术如何在社会和文化中建构、操作和应用等问题。二是网络虚拟社区研究。虚拟社区不再由地理甚至符号(种族/宗教/语言)的界限来界定,而是一个从网络中产生的社会集合体。它是人类学进入网络文化研究的一个窗口。④李志荣:《网络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课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具体来说,虚拟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及网络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三是网络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网恋文化、网络犯罪、网络社会运动等。
三、网络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
在人类学家推动网络人类学研究系统化的同时,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民族志作品的涌现,也给分支学科的建立增添了不少学术自信。丹尼尔·米勒和唐·斯莱特的著作《互联网:一个民族志方法》,探讨了特立尼达居民如何利用“他们的互联网”及其应用和服务,是对互联网技术及其后果进行的“全面的民族志研究”。⑤Miller,D,& Slater D.the Internet:An Ethnographic Approach.Berg Editorial Office,2000.P.1波什托夫的著作《第二人生时代的到来:虚拟人类的人类学研究》使用民族志方法研究虚拟世界“第二人生”,并将其与经典民族志如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埃文斯-普里查德所创作的努尔人民族志或马林诺夫斯基在太平洋岛屿的民族志研究联系起来。⑥Boellstorff,T,Coming of Age in Second Life:An Anthropologist Explores the Virtually Human.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国内学者刘华芹运用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对“天涯虚拟社区”进行详细考察,描述了社区的发展史、社区的公共决策、社区意识、社区的婚姻等方面。⑦刘华芹:《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在这些研究实践中,都可以发现一组特定的民族志研究程序和范式,包括认识论、分析框架和进入现场的指导原则、参与观察的方法、数据分析、伦理道德等等。应该说,网络人类学最基本的问题是方法论的问题,确切地讲就是如何把人类学特有的思想和方法应用到其应有范畴的研究中。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要求,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完整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人类文化的整体认识,是构建民族志的必要步骤。综观网络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首先,有关“真实性”的认识论讨论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也构成了网络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分支的重要区别。其次,整体论依然可以而且应该得到体现。最后,在网络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法始终是其立足之本。
(一)关于“真实”性
有关网络文化或网络空间的学术研究,一直延续着虚拟和真实的辩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由于互动的匿名性和“不在场”,个体往往缺乏“身份感”和感觉不“真实”。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空脱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靠想象的,而非“真实的”。在安德森等关于民族主义、种族等重要概念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认识,即包括民族在内的所有社区都是想象的,即使是从未谋面的人也能借由他们共同的想象而联结在一起。①[美]安德森·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18世纪印刷媒体的发展促进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增长。而以互联网传播为代表的信息时代,正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升华。②段宇晖:《互联网时代“想象的共同体”的祛魅— —兼论民族主义建构论的困境》,《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在人类学家看来,关于真实性的讨论,对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无裨益,反而会阻碍学术想象力的发展。因为,“在人类学家眼中,一位纽约的会计师,或是一位韩国的游戏玩家,其真实性并不会比当代的东非部族牧师多,也不会比之少。无论是通过亲属规制、宗教规范、网络礼节还是游戏规则,我们都是文化作为中介的产物。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什么是真实性。”③[英]丹尼尔·米勒,希瑟·A.霍斯特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因此,在学术语境下,如果我们继续纠结于真实性问题,盲目崇拜网络时代之前的文化,认为那才是真实,实际上也是在破坏网络人类学研究的根基。
(二)关于整体论
整体论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部分或要素所组成的整体,要考察人类及其创造的文化就要注意这一整体的层次、结构和相互联系,从而更好地揭示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④李泳集:《浅谈人类学的整体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在网络人类学中,我们依然有理由支持人类学的整体论观念。首先,没有人完全生活在网上。个体在有意或无意地嵌入到网络空间的生活中的同时,依然无法脱离现实的生活环境,往返于线上线下由此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在这样一种网络化生存的背景下,我们通常也要将线下语境纳入考察范围。其次,在传统的人类学领域,目前来看没有一个主题不受计算机和网络的影响。从信息流动、医疗服务、身份认同、金融贸易,到语言、政治等等,几乎生活的各个面向,都和计算机和互联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者,民族志始终不应该脱离了对政治经济大环境以及全球体系的考察。这些方面归纳起来也即个人的整体论、民族志的整体论和全球整体论。⑤[英]丹尼尔·米勒,希瑟·A.霍斯特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4页。应该说,人类学的整体探讨、综合研究的思维和民族志撰写方式正是与网络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趋势相一致的。
(三)关于参与观察法
与传统人类学研究不同的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在许多研究中,计算机和网络平台既是研究内容,又是研究工具。计算机技术已经在改变着人类学的数据获取、记录、传输、发布协作过程和方式。但是,“尽管有大量的数据和新形式的可见性通过计算媒体得以体现,许多世界仍蒙着面纱,披着斗篷,而且很难破译”。⑥Coleman E G,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Digital Media.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0,39:1-19.因此,学界的一个共识是,要进行网络文化的人类学研究,长期的田野调查是必要的,参与观察法依然是其立足之本。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长期栖居于所研究的社群里,甚至成为其中一员,以了解这一空间和群体的全貌。与传统田野工作方式不同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退回到传统的扶手椅上的人类学,也即打开电脑,连接上网,便可进入研究的田野,进行参与观察。但是,与传统的面对面访谈和参与观察不同,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基础的观察和互动,更多的是基于文本和图像的传输。从观察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包括对文本、图像或情感符的观察以及对网络虚拟社区中的社会互动的观察。参与则更多的只是参与对话与互动。①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对研究者而言,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同样可以取得身临其境的效果,但是,身体的不在场对人类学家提出了更高的甄别和判断的能力要求。需要指出的是,有许多研究者宣称自己正在网上进行人类学调查,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网上进行问卷调查等。还有,许多人把在网上进行访谈和分析博客文本等同为网络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只有参与观察法才是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核心。当然,与现实中的人类学方法一样,人类学家同样面临进入和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这些学界已经有不少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四、结语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技术社会,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变革,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技术发展推动的。由此,人类学研究转向现代社会,关注除宗教、亲属制度等传统领域以外的科技现象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身就具有题中之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代表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而任何技术均代表文化发明,因为它不仅以文化的建构和重构为基础,也形塑了文化。基于这样的信念,人类学者应该为了解这些过程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而,主流人类学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研究目前依然稀缺。其结果是,我们对许多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理解大都来自于其他学科。实际上,计算机、信息技术不仅带来了现代社会文化结构和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也影响到人类学调查,并有必要构成人类学的专有领域。如前所述,网络人类学的确立既是时代发展所需,也是学术潮流所趋。但目前,网络人类学依然处于探索和发展过程当中。如果说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网络人类学的发展还需要开展很多工作,包括相关核心概念的进一步凝练、学科理论与体系的建立、资料的收集等。鉴于我国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应用的迅速普及,发展网络人类学学科,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在我国学术界,学者刘华芹②刘华芹:《网络人类学:网络空间与人类学的互动》,《广西民族志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杨立雄③杨立雄:《赛博人类学:关于学科的争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2期。等学者在10年前,就对网络人类学予以了引介,朱洁随后阐释了网络人类学的田野考察问题,④朱洁:《网络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思想战线》2008第2期。但总体而言,发展依然迟缓。而要推动网络人类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网络人类学的方法和经验,另一方面,有赖于我们在研究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