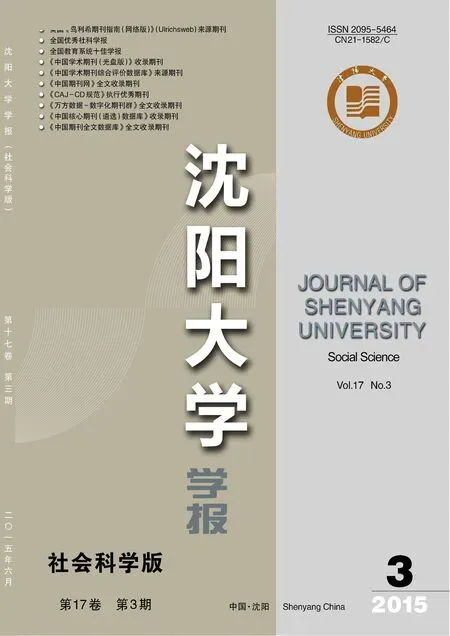翻译风格与再创作——以林少华版的《挪威的森林》为例
崔 岩
(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041)
翻译风格与再创作
——以林少华版的《挪威的森林》为例
崔岩
(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41)
摘要:以林少华译本《挪威的森林》为例,探讨其翻译语言风格,认为其翻译语言优美婉约,沉着冷静中流露着保持原文文学性的执著,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村上春树笔下的主人公形象。通过对林氏翻译语言风格的分析,更好地让文学译者及读者掌握日文作品的翻译技巧,理解翻译作品的再创作。
关键词:翻译风格; 再创作; 林少华; 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

自1989年《挪威的森林》在中国大陆发行以来,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越来越有人气。因此,作为翻译家的林少华也被更多的读者知道,提起村上春树,就一定会谈及林少华。可以说林少华是村上春树在中国的代言人。
一、村上春树的写作风格
在全世界掀起“村上热”的风潮之时,对其作品的评论也不胜枚举。其中,哈佛大学的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的《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MurakamiandtheMusicofWords)则比较系统地对其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论述。国内的日本文学研究者也对其写作风格以及村上作品给日本文学带来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研究。
其写作风格主要体现在创作内容、作品结构、文学体裁和语言特色等方面。其文学作品“更加看重的是朦胧的感觉和格调。经常冠之以柔和的、温柔的、简约的文学外表,内在含义往往蕴藏着较为深刻的精神层面的实质性内容”[1]。从作品的结构上看,“篇幅较为短小, 整体结构松散,不容易看出明显的主题”[2],是一种“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融为一体的结构”[3]128,即“现实”与“虚构”的两条平行轨迹的交错结构。另外,村上作品的魅力之一就是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例如:《挪威的森林》是一部具有日本“私小说”特质的自传体虚幻长篇小说[4]136;《寻羊冒险记》类似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家庭时间》则近似一部喜剧小说。从语言风格上看,其作品句子简洁明快,语言通俗幽默,伴随故事情节的发展,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音乐符号,展示出活力四射的充沛精力。
总之,他用村上“用简洁、富有节奏感和幽默的语句,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架构起虚幻与现实平行并交融的结构,并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夸张的修辞诠释了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3]131。
二、林少华的翻译风格
随着村上春树知名度逐渐的提高,知道林少华的人也越来越多。出名之后的林少华在许多地方都发表了自己对于翻译的观点。从他的观点可以看出,翻译文章的时候应该保留住原著的灵魂,所谓的翻译,就应该“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在纯洁与美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进行“再创作”[5]。林少华翻译的文章不仅十分重视语言的“文字之美”,而且经过反复地锤炼和推敲,将村上作品独特的“孤独之美”“深刻之美”以及“隐喻之美”展现在中国读者眼前[6]。
本文将从如下四个方面来分析林少华翻译语言的特征。
1. 景物翻译的语言特征
以下是1987年在日本首次出版的《挪威的森林》中,第一段落中描写主人公渡边彻到达德国机场时的场景的段落。那个时候,渡边带着怀念的心情看着机场于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人、物、事。
原作: 僕は三十七歳で、そのときボーイング747のシートに座っていた。その巨大な飛行機はぶ厚い雨雲をくぐり抜けて降下し、ハンブルク空港に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だった。十一月の冷ややかな雨が大地を暗く染め、雨合羽を着た整備工たちや、のっぺりとした空港ビルの上に立った旗や、BMWの広告板やそんな何もかもをフランドル派の陰うつな絵の背景のように見せていた。やれやれ、またドイツか、と僕は思った[7]5。
林版: 三十七岁的我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十一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候机楼上呆然垂向地面的旗,以及BMW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弗兰德派抑郁画的背景一般。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8]3。
机场本就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就一定会看到很多悲欢离合的场面。在机场,有见到想念之人的喜悦,也有和亲人分离的悲伤。在这样的场景下,主人公到达了德国,却不能自由地想见谁就见到谁。渡边本以为那个最想见的人已经在记忆深处越来越远,模糊不清,可是当他怀着这样的心情到达机场时,雨下起来了。因为这雨,使机场别离的气氛变得更重。这个部分对景色的描写,抓住了主人公的心情,营造出了悲伤的气氛。特别是他的非常简洁的语言,将那种悲伤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俯身”“涂”这样的动词的使用,给人一种很灵动的感觉,将文章的走向与格调引入恰到好处的境界。另一方面,“俯身”“涂”这样的动词将飞机和雨等拟人化。通过这样的动词,使文章的感情能够流畅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用生动的语言词汇来衬托出沉重的气氛。
2. 人物性格翻译的语言特征
《挪威的森林》是用第一人称叙述描写的小说。每一个地方都表现了主人公渡边的思想。人物性格的描写和翻译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以下便是渡边和直子散步时候的心理描写:
原作:そんな音を聴いていると僕は直子のことが可哀そうになった。彼女の求めているのは僕の腕ではなく誰かの腕なのだ。彼女の求めているのは僕の温もりではなく誰かの温もりなのだ。僕は僕自身であることで、僕はなんだかうしろめたい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った[7]53。
林版: 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8]37。
“虽然这一刻直子挎着渡边的手腕,手插在渡边外套的口袋里,却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直子所需要的并不是自己。”渡边这样想着,心里也充满了失落的情绪。
在这一部分中林少华对词语出神入化地准确使用又一次表现出来。他将“求めている”译为“希求”;“腕”译为“臂”;“温もり”译为“体温”;“誰か”译为“某人”。虽然都是简单的词语,却将主人公伤感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说,使读者能够体会出隐藏在这简单的用词之后的主人公的失落心情。
3. 会话描写翻译的语言特点
原作: 前と同じスチュワーデスがやってきて、僕の隣に腰を下ろし、もう大丈夫かと訊ねた。
「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ちょっと哀しくなっただけだから(It’s all right now, thank you. I only felt lonely, you know.)」と僕は言って微笑んだ。
「Well, I feel same way, same thing, once in a while. I know what you mean.(そういうこと私にもときどきありますよ。よくわかります)」彼女はそう言って首を振り、席から立上がってとても素敵な笑顔を僕に向けってくれた。「I hope you’ll have a nice trip .Auf Wiedersehen!(よい御旅行を。さようなら)」
「Auf Wiedersehen!」と僕も言った[7]6。
林版: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我微笑着说道。
“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摇了下头,起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8]4
这个部分,原作是用日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描写的,但是林少华将英语的部分省略了。笔者认为最好是将日语部分译成中文,将英语的部分按照原文的格式保留下来。理由是如果将英语的部分留下的话,能使读者更容易联想到主人公当时对话的状态。再者,对于空姐说的“Well, I feel same way, same thing, once in a while. I know what you mean”这句话的翻译让人觉得略显生硬。提到空姐,人们在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是温柔、美丽的印象。“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这样翻译过来的说话方式会让人觉得与空姐给人的印象不符。并且这样的说话方式与渡边说话的方式太过相似,会给人一种渡边在自言自语的感觉。下面请看另外一个例子。
原作: 「自分が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るのではなく、やるべきことをやるのが紳士だ」
「あなたは僕がこれまで会った人の中でいちばん変った人ですね」と僕は言った。
「お前は俺がこれまで会った人間の中でいちばんまともな人間だよ」と彼は言った。そして勘定を全部払ってくれた[8]103。
林版: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8]74。
这是渡边和永泽谈论到“绅士”这个话题时的场景。这段话中,最难翻译的就是“変った人”和“まともな人間”。林少华把它们翻译为“特殊”和“地道”。“変”本来的意思是“奇怪”“不同寻常”,把它翻译为“特殊”会让人感觉渡边有点太过于温柔。“まとも”在字典里的意思是“正经”“认真”,确实也有“地道”的意思。但是“地道”这个词普通的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并不怎么用到,在林少华版的《挪威的森林》中却经常被用到,这样就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两个人在日语使用型上的不同。渡辺使用的是“あなた”“僕”以及“です”。而与之对应的永泽使用的是“お前”“俺”和“だ”。这样不同的用词习惯会反映出人物不同的性格。但是,遗憾的是翻译成中文之后就不能表现出这种不同了。
4. 人物的姓名以及特定的事物翻译的语言特征
(1) 人物的姓名。《挪威的森林》中出场的人物主要有“渡边彻”“直子”“木月”“小林绿子”“永泽”以及“玲子”。请见表1。
首先,主人公的全名——“ワタナベ·トオル”在小说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只是在绿子确认他的全名时才出现过一次。原文用片假名书写是为了强调,如果把它的汉字型直接翻译过来,就会削弱原文强调的意思。林少华没有借助中顿点而直接把它翻译成“渡边彻”,没有表达出原文强调的意义。其次一点是,与林少华把“キズキ”翻译成“木月”相比,赖明珠版的直接将其翻译成“kizuki”更好一些[9]。保持原本的片假名状态,而不是具体的汉字名字。如果翻译成“木月”,就会给读者一种与原作不同的感觉。而将“小林緑”翻译为“小林绿子”,虽然也有点与原作不符,但“绿子”这个名字给人很可爱的感觉,可以说很符合绿子开朗的性格。此外,“永沢さん”“レイコさん”这些名字后面都带着“さん”,而“直子”就是直接被称呼为“直子”。在日文原版小说中,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由于汉语中并没有表现这样关系的词语,因此不能完整地翻译过来。

表1 氏名対照表
(2) 音乐和料理。《挪威的森林》中涉及的音乐和料理的词汇可以说有很多,本文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将原作与翻译对照列表分析。请看以下的表2和表3。

表2 音楽

表3 料理
村上春树是一个十分喜欢音乐和料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行家。但是翻译专业用语是件相当难的事情,这从上面的表格就可以看出来。对于音乐的部分,如果没有非常详细的信息,与其用自己的汉语生硬地翻译出来还不如使用原文的英语。如果读者对音乐感兴趣的话,自然会自己去查。林少华虽然去过日本,却是以老师的身份去的。由于没有作为学生的生活经历,他对于作为学生的渡边所吃的料理并不怎么了解。对于料理的翻译和字典上的大致相同,虽然不能说他翻译的有什么错误,但更应该翻译出符合汉语的名称来。
三、结语
读者是小说的动力。对于林少华版的《挪威的森林》,读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有的人喜欢,也有的人不喜欢。但是译本的好坏,并不是由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的。基本要遵循以下三条标准。①作品是从属于社会的特征以及对时代背景的了解的产物。②必须十分了解作家的风格。③如何展现原作中的形象。
林少华的译本毋庸置疑的是一本成功作,优美简洁的用词和恰到好处的节奏以及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将原作中的被压抑的伤感,内心深处的孤独印象彻底地表现出来了。不过尽管如此,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对于音乐和料理等等名称的翻译并没有用专门用语[10]。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应该使用地道的本土翻译为好。例如“三人寄れば文殊の知恵”这个谚语按字面意思翻译是“三个人联合起来就会有文殊菩萨的智慧”,但是由于这个谚语的意思和中国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谚语的意思大体相同,翻译成这句话也更像汉语。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环境。如果无视对语言环境的把握和词语的转意、派生、修辞等问题的分析,只翻译文章的意思,就无法表达出原作品的主旨。林少华正是抓住了这种翻译的方法,成功地摆脱了日语的阴影,得以使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精美作品奉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参考文献:
[1] 朱丽蓉. 村上春树与日本文学[J]. 作家, 2013(18):105-106.
[2] 文钟莲. 幽默的青春序曲——从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看日本语言风格[J]. 作家, 2013(8):111-112.
[3] 申秀逸. 村上春树的作品风格[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128-131.
[4] 杰·鲁宾著. 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M]. 冯涛,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6.
[5] 林璋. 文本的翻译与评说——以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为例[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9(5):109-116.
[6] 陈伯鼎. 林少华的翻译观及其翻译风格初探[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09(1):169-172.
[7] 村上春樹. ノルウェイの森[M]. 東京:講談社, 2007.9.
[8] 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M]. 林少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7.
[9] 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M]. 赖明珠,译. 台湾:时报出版社, 2010.1.
【责任编辑田懋秀】
Translation Style and Recreation: A Case Study ofNorwegianWoodTranslated by Lin Shaohua
Cui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1, China)
Abstract:Taking Norwegian Wood as an example, Lin Shaohua’s translation style was studied. It was considered that, Mr. Lin’s words are elegant, peaceful, and dedicated to the literary factors in the original Japanese versions that he appropriately depicts the hero’s images in Murakami’s novels. The analysis on Mr. Lin’s translation style could be helpful for literature translators and readers to master the translation skills and understand the recreation in translation works.
Key words:translation style; recreation; Lin Shaohua; Haruki Murakami; Norwegian Wood
文章编号:2095-5464(2015)03-0369-04
作者简介:崔岩(1974-),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讲师。
收稿日期:2015-02-01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