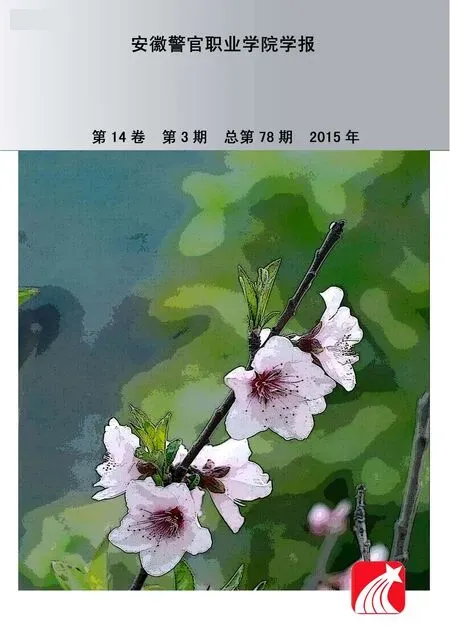简论乌克兰民主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博弈
孙雁南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简论乌克兰民主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博弈
孙雁南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近年来,乌克兰政治危机频发,与其民主政治转型密切相关——快速民主化进程带来治理困难的“弱民主”,历史原因累积又造成两大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的尖锐对立,族裔民族主义隐疾严重侵蚀民主政治的根基。那么,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孪生关系究竟该如何界定,二者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又以何种方式进行互动运作,彼此之间的博弈冲突可否化解?鉴此,从乌克兰国家及民族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其作为多民族国家典型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无疑是求解的有效途径。
乌克兰;民主;民族主义;关系
2004年以尤先科为首的乌克兰政界发动“橙色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去,2013年底由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主导的中止与欧盟签署 “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强化和俄罗斯关系的政策再次引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犄角待战的导火线。此后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在数月之中从政权更迭、总统外逃到克里米亚公投独立、脱乌入俄,乌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企图效法成立“独立国家”、武装冲突升级,再到乌克兰日益“巴尔干化”,国内危机溢出国界。
目前,乌克兰局势走向尚不明朗,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后冷战时期,作为俄罗斯与欧美直接对峙的“缓冲带”和利益争夺区,乌克兰政治失范所导致的社会失序和国家分裂危机,与其外部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脱不了干系,但追溯乌克兰国家(state)实体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可以深刻发现,这个现代国家机体内的裂痕更多来源于对抗性的民族(nationality)关系。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共生共荣本应促进社会民主政治转型,多元融合的意见表达以及政治资源的合理性分配本可滋养“民主(democracy)”这一“人类共善”,但乌克兰境内两大主体性民族——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却由于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心理倾向等各方面的差异而撕扯着这个本就脆弱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尤其是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借民主、自由之名大搞接头政治,宣扬民族自决,强化民族自我意识,实则极易为别有用心的民族分裂者和外部行动者利用,成为威胁本国政治稳定,践踏民主法治,引发社会动乱的火种。
一、乌克兰的弱民主和族裔民族主义隐疾
(一)乌克兰的“弱民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试图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而进退维谷,统一的苏联像被激活的休眠火山一样,地下暗流涌动之时,正是乌克兰这股岩浆喷薄而出,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率先打出“独立”、“主权”的旗号,并在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简称“鲁赫”)的支持下,于1990年7月6日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8月24日正式宣布脱离苏联独立。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几乎凑齐了“西式民主”的各种七巧板,并在独立后的20年间基本搭建出现代民主制度的框架:在法治建设上,1996年乌克兰通过新宪法规定乌克兰的民主国家性质;在政体设计上,选择了西方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同时废除苏联时期的一党制实现多元化政党制度,从1997年到2004年短短几年间,乌克兰出现了近两百个政党,目前国政党数量仍维持在130个左右,属于小党体系[1];选举制度改革经历了单一的多数代表制到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混合制选举制度再确定为比例代表制的发展历程,民选政府的程序相对完整。
然而,乌克兰的民主生态并不像字面反映的那样健康——其宪政根基不稳,在半总统制政体问题上始终徘徊于议会—总统制和总统—议会制之间,不仅没有通过法治途径解决反而不断修宪以迎合领导人意向;乌克兰半总统制的政体并不像德国那样典型,也未能走上芬兰式的转型正轨,而是在各种历史包袱和政治因素博弈下的妥协,由于政党在议会中没有组阁权只有倒阁权,政府不一定由议会多数党组成即没有执政党,总理和内阁成员的任命则交由总统。议会只作为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这种“大总统、小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并未能很好的展现三权分立原则的初衷[2];1997年乌克兰通过的《乌克兰人民代表选举法》本希望通过混合制实现小党的稳定发展和推促两党形成的双赢局面,结果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产生的“独立候选人”这道独特风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却造成国内党派林立,政治意见难以整合;比例代表制难免出现选举偏差,对民意的许诺往往落空,使得代议制民主流于形式。尽管2004年乌最终确定了比例代表制,但其完善仍需假以时日。
观视当下,乌克兰政治上自由放任、钱权交易,经济发展朝私有化大步迈进,社会投机分子向经济寡头靠拢并利用多党制度干政的趋势正一步步蚕食着乌克兰本就不够成熟稳健的民主。2013年11月21日因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止“入欧”进程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和群众性街头运动已引发学界关注,由“欧洲”和“广场”两词根缀合成的一个新词“欧罗迈丹”(Euromaidan)更生动地再现了以乌克兰“街头政治”为代表的民主弊病[3]。可见,尽管乌公民置身于所谓的“民主洪流”之中,披上了选民的外套,群情激昂地进行表决,实际上其政治意见的表达由于缺乏内在体制的支持而被扭曲变形,甚至危及国家存亡。倘若按照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在《论民主》一书中列出的民主过程的标准——有效的参与(effective participation)、投票的平等 (equality in voting)、充分知情(gaining 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对议程的最终控制 (exercising final control over the agenda)和成年人的公民权(inclusive of adult)[4]来审视乌克兰的民主形态,其民主实践沉积了过多的社会历史杂质:政权与帮派交融、民权被对抗绑架、话语权为复仇充斥。有学者尖锐指出,目前的乌克兰社会还徘徊于 “反共—思想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政治寡头化—社会犯罪化—国家弱化”的泥淖中不能自拔。[5]可见乌克兰的“弱民主”完全不符合民主发展的本意,盲目西化,无视经济和国家发展现状,未能从国家发展的正序列考量民主政治的实施,不仅造成民主本身的越位和错序,更使得这个原苏东民主化先驱在现代国家善治的道路上越走越偏。
(二)族裔民族主义“隐疾”
民族主义最初是作为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加以演绎的,在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下,罗马教会的衰落和王权至上的理念催生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民族国家应运而生,民族主义遂与人民对主权、地位的呼唤结合在一起。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她的《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路径》一书里归纳了民族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和对应的三个类型,即16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民族主义,18世纪中叶以法国为代表的公民的(civic)和集体主义性质(collectivistic)相混合的民族主义和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以俄德为典型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tic)的和族裔的(ethnic)民族主义。[6]民族主义在向中、东欧国家传播的过程中较多地被复制和摹写了民族主义的第三种形态,即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族裔”这一概念发端于18世纪末,由德国人类学家约翰·布鲁门巴赫最先提出,它反映了人民对自身归属性特征的认同和信服,而这种归属性往往与人类的眼睛、皮肤颜色等先天特征相联系,更多地关注遗传、血统和自然因素。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族裔”的划分并无多少意义和价值,只有当这些特征成为影响人们社会权利地位的制约性因素时,其功用才被彰显。复旦大学校长姚大力认为,族裔民族主义本身确实也是不应该被全盘否定的,但在社会结构环境业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中,往往事情发生的次序就被颠倒了:人们力图通过民族主义在政治中发挥出来的动力作用,去激发当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转型。[7]“一族一国、一国一族”,就这样成为第三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最响亮的口号。
回顾乌克兰的民族构成和民族演绎历史,我们甚至无法对其国家实体的稳定民族构成予以描述,因为如今的乌克兰(Ukraine)与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仍有明显差距,尽管身负欧洲除俄罗斯外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名,但它似乎更像是一个地理标识或行政区划。历史上独立的乌克兰仅在十月革命以后短暂的存在过,其余时间不论是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还是近现代列强势力扩张之所,区划和民族的分合都错杂交纵。“乌克兰”这一称号最早于12-13世纪在南罗斯公国被使用,含义是“边区”,指的是南罗斯加利西亚沃伦地区,后来这一称谓逐步扩及现在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并开始具有民族意义。

时期 内部民族及外部入侵 国家成分及所属10世纪 东斯拉夫各部—古罗斯部族、瓦良格人 基辅罗斯国家12-14世纪(内部割据)俄罗斯人(东北)、乌克兰人(西南)、白俄罗斯(西北)3支系乌克兰人脱离古罗斯形成单一民族若干罗斯公国,如基辅公国、佩利亚斯拉夫公国、契尔尼夫北方公国等,其中苏滋达尔-弗拉基米尔公国和加利西亚公国-沃伦公国重要13-15世纪(外族侵略)蒙古鞑靼人、日耳曼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11-13世纪占领外喀尔巴纤);蒙古金帐汗国(1240年占领吞并);立陶宛(14世纪初占领基辅周围和沃伦公国大部分);波兰(14世纪初占领加利西亚和沃伦公国西部);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15世纪末统治乌克兰全境)17世纪1653-1654年东乌克兰与俄国签订佩利斯拉夫协定,乌克兰受俄国保护1667年东西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 俄国(东),波兰(西)18世纪 俄国不断扩张,逐步统治乌克兰全境1795年西乌克兰(除加利西亚)并入,俄国基本统治全境;奥地利(1772-1918控制加利西亚)20世纪1917年底乌克兰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短暂真正意义独立国家1918—1920外国武装干涉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盟1933年二战爆发波兰被分割1941年苏德战争苏联失守后于1944年重返乌克兰1991年波兰(占领西乌克兰)苏联加盟国(东乌克兰)西乌克兰与东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合并德国曾占领乌克兰全境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
从上述表格中不难发现,乌克兰最早的民族起源可追随到东斯拉夫三个支系,即俄罗斯人(东北)、乌克兰人(西南)、白俄罗斯(西北),与中国的“大杂居,小聚居”格局不同,乌克兰各民族的片区分化相当明显。“大俄罗斯族”与“小俄罗斯族”(主要指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在地域范围、人口繁衍、宗教文化、民族心理上差异是伴随繁重的外部侵略逐渐形成的。上表标注的两种色调清晰地展现了近现代以来乌克兰在东西方之间的反复,尽管各种势力易手,但是波兰和俄国都曾全境占领乌克兰长达两个世纪。波兰对乌克兰的侵占固然与其自身的强盛有关,但14世纪初乌克兰内部加利西亚和沃伦公国领土上“小俄罗斯族”在文化上对拉丁文的使用、在军事上对抗蒙古鞑靼人入侵反抗等与“大俄罗斯”的迥异表现使得分裂成为一种可能,伴随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东西乌克兰的文化分野更为明显,特别是波兰对乌克兰的农奴制压迫、天主教皈依更从社会政治层面在乌克兰民族身上打下深刻烙印。1654年,乌克兰在面临外患威胁——波兰的残酷统治时由哥萨克领袖鲍格丹·赫梅利尼茨的带领下向逐渐强盛的莫斯科公国求援,“保护”之名引发了俄罗斯与波兰13年的长战,但却开启了乌与沙俄长达263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血缘”关系。
如今,乌克兰的民族构成既包括东部近20%的俄罗斯族,也包括西部70%的乌克兰族。从“族裔”的角度来观察,且不论深层的文化共性等“想象共同体”上的差异,外在长相已可区分——俄罗斯族有着高颧骨、淡黄色皮肤、深色头发、宽大的鼻子等芬兰血统特征,而乌克兰人则流淌着南部罗斯突厥部落的成分,身高普遍比俄罗斯族高1-4厘米,深色眼睛和头发,黝黑的皮肤,头型宽短,额及鼻子均不大。[8]此外,放眼全国,乌克兰境内有着大大小小130多个民族,且从古以来冲突纷争不绝——乌克兰人、犹太人、鞑靼人、俄罗斯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彼此厮杀,侵占领土、扩张文化。时至近代,而当1991年宣告独立之际,乌克兰又江河不拒细流地容纳了这些有着不同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心理倾向的民族。本身,民族“杂烩”版图,不过是各民族对聚居地选择的结果,但当民族发展的不同轨迹与现代国家的政治议程相结合时,尤其是在国家显现危机(包括族际冲突)时,往往其“历史记忆”既成为凝聚与动员族群的必要资源,又是族群(及其变体)寻求并保障其现代权利与诉求的主要证据 (历史正义性)。[9]乌克兰的地域冲突和民族主义隐疾,往往裹挟在多民族国家的外衣之下,却使得构建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和解与包容都无法培育起来。
二、乌克兰民主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博弈
民主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学中特定的 “意识范畴”,都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及体系分支。例如民主与自由联姻谓之自由民主,民主与泛伊斯兰运动结合叫伊斯兰主义民主;民族主义与个体充分交融的可发育为公民性民族主义,与种族血统整合在一起可催生族裔民族主义。如此分类其实并无统计学上的确切依据,只是在具体语境分析中给予我们辩证思考的空间和提醒: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二元对立的简约论,避免纯粹乐观的情绪表达或悲观思想的宣泄。同时,在对两者的独立命题资源充分占有的前提下,不少学者也对其的互动形态——包括促进和冲突进行了分析论证。但是我们认为民主与民族主义的耦合必须有一个政治框架,即现代性国家的构建。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下,任何思潮和意识形态都必须围绕着这个框架来进行分析,如果某种理念的讨论使得现代主权国家走向分裂,那么我们认为它就是弱性的和不具备治理性、上升性的政治说辞。乌克兰的政治图景正深刻地验证着我们对民主和民族主义的理解。
(一)民主愿景激发民族主义意识,民族主义运动推动民主化进程
首先,民主内生地包含和蕴藏着平等,而平等的诉求意味着各族人民不论出身背景、性别种族、社会地位、价值理念都应获得同等权利、享受同样待遇。平等是民族主义发展的强大推进剂,其所到之处都塑造着面貌相同的人们,为共同体奠定了强大的内聚认同基础,从而推动了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从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为争取民主自由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3世纪蒙古鞑靼人入侵乌克兰之际,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就竭力保卫基辅城;哥萨克统领带领乌克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反映出民主运动在发轫之际与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并蒂同生的,“民族”是以血缘、种群为纽带的物质基础,而“民主”则是现代国家演进过程中人民的精神诉求。
其次,民族主义还推动了民主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民族主义为民主主义的作用范围划定了确切的边界,从而使民主的运作拥有了现实的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民族国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光斌认为,民主主义主要是对内而言的,它解决了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人民的同意为国家权力的产生与运作提供了合法性。然而民主概念本身却无法提供这种合法性的依据,只有通过公民、民族等法律概念予以确认。就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迄今为止,民主仍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属性既包括时空和地域的划分,也包括行为主体的筛选。前者的探讨可能框定在某区域性自治组织或疆界明晰的国家及其行政区划之内;而后者正是由阶级阶层、民族种族等具体的政治经济范畴来界定的。民族主义正是通过对共同的历史、语言、种族、地域、风俗习惯等的强调,赋予人们明确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落实在现实中就产生了边界效应。[10]
(二)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可能解构“弱民主”,阻碍良性民主政治发展
多民族的意见表达是否真的有利于民主政治朝着正方向发展?民主又是否真的有利于民族和解,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
毋庸置疑,作为公共之善的民主,在制度上有追寻的意义,但民主本身作为上层建筑只是政体的一种实现形式,其内部必然存在利益主体的博弈冲突,也隐藏着从正宗政体向变态政体演变的可能。①亚里士多德根据统治者的目的和人数,将整体分为正宗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变态政体——僣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尽管冲突性和张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在乌克兰,民族分裂型的社会结构可能更是“罪魁祸首”。上文我们已经分析到,且不论乌克兰境内的少数民族,其两大主体性民族——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恩怨分合已是十多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接受过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思潮的洗礼,尤其是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乌克兰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想大有抬头之势。
这个时期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可从三个维度分析:首先族裔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交叉,在国土疆域内以族群为基础,为维护本民族利益,提高本民族在权利中心的地位而通过各种途径排挤对立的民族,最主要的做法是通过政治议程确立民族主体地位。如西乌克兰与俄罗斯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近期推翻“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斗争中,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便成为生力军。其次,文化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民族分裂的深层原因,文化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核,影响着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心理特质的塑造。东部亲俄的俄罗斯族长期信奉东正教,宗教律令戒严;西部亲欧的乌克兰族则在波兰的占领下信奉天主教,且沐浴文艺复兴的春风,拉丁文的文艺作品丰硕。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从表面到肌理的渗透更为艰难。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亚努科维奇下台后,执掌政权的反对派取消了俄语作为地区官方语言的地位,并禁止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电台频道播放,这种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做法割裂了民主政治的同质性基础。再次,民族分离主义夹杂跨国民族主义。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政治状况时常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民族分离主义以“民族自决论”为口号,强调以民族为基础建立独立国家,而这种分裂力量的背后可能是国际势力的争逐。克里米亚的公投独立显受俄罗斯的影响。
应当指出,民主并不总是意味着秩序和保障,有时民主的实施带来的恰恰是混乱或无序,特别当别有用心的民族主义分子搭上了“民主的便车”。发达的公民社会与基于碎片化的族群和上百个政党而形成的弱公民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在分裂型的社会结构中,自由民主往往由于缺乏宪政、法治的约束、缺乏社会基本的政治共识而被引向歧途,从以熊彼特为代表的选举民主风靡一时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回溯,呼吁强权政治回归的现实,我们看到了无效的民主。在乌克兰,代议制民主中对选举制度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多民族的比例代表制的规定,以民族为界其本意是为了促进多元意见的整合,保障国内的民主政治生态普惠各族。但是现实的政治运作往往相当复杂,乌克兰单一选区独立候选人模式以及弱政党的特殊国情,更容易使议会民主发育不充分而演变为民族势力的竞技场;宪政民主的极度缺失也给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可乘之机,借公民权利之名倾轧民主法治。从高层看,在党内斗争中,“乌克兰民族主义”也常常成为大规模整肃的口实。乌克兰历任的党政一把手,从斯大林时代的埃何、波斯蒂舍夫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谢列斯特,常常不得善终。而从民众角度看,托克维尔曾用“多数人暴政”来概括良性民主的对立面,基辅独立广场的街头抗议虽冠以“民主”之名,实则是议会内各党派角力的外延。
(三)民主与民族的耦合点是国家认同
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在各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其正常运行不仅要有基于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认同,也要有对法律、制度等的政治认同。而现代民主国家的良性发展,也强调民主政治的文化性,如阿尔蒙德倡导的公民文化、英格尔哈特对公民表达权的呼吁,但是理性的公民文化需要一种对主权国家的认同。可见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只有在国家认同这个框架内,才能找到彼此的耦合点。有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新的认同,一种与族属意识、族籍身份相分离的政治认同,它是发生在公共的政治领域。[11]但是,超越了种族、阶层和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的认同是以对国家性(stateness)的认可为前提的。由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打破原有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建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冲击原有社会秩序和利益藩篱,国家认同就更需要切实的公民权益来夯实。而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实现又是建立在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法制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忽视了稳定大局、抛弃了经济发展、漠视了宪政法治,任何形式上的政治安排都是动摇国本,使得稳定、平和的民主政治成为空想。
可以发现,独立以来的乌克兰社会一直存在着国家认同的分歧。这种认同差异在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激烈言行的动员下演化成为国家认同危机,并成为影响乌克兰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国家认同危机不仅阻碍了乌克兰的民主巩固,使得国家发展后劲不足。事实上,不论是基于个体主义的民主还是基于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其价值取向的调和都应当紧紧围绕现代国家的构建,因为真正民主的实现需要共生的民族心态、包容的民族话语。
三、结语
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激昂地呼唤民主“即使我们不能指望温和的历史力量去推动民主,我们也不能成为我们自己所不能控制的黑暗力量的牺牲品。”虽然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已经从制度建设发展到民主巩固的阶段,但快速民主化进程显得简单粗暴,狼吞虎咽的结果往往是消化不良。民族主义的 “隐疾”也使其民主本身的根基不稳。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民主巩固问题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无论是渴求民主本身或民族主义的正向维度,还是警惕少数分子借民主之名以原教旨主义态度去对待民族主义。二者的交互博弈都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在当今世界,总共有3000多个民族,分布于200多个主权国家之中,形成了复杂的民族结构,多民族体系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体模式,惧怕和躲避民族主义并不能改变现状。分析乌克兰民主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干扰并非冷眼旁观,而是给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提供借鉴。
事实上,为确保不同民族、种族或亚文化群体的政治融合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各民主国家都采取了一定的政治安排。然而纵观世界,在黎巴嫩、斯里兰卡和尼日利亚,由于文化分裂的历史性积累,尽管治理者试图采取各种措施和巧妙的安排以实现暂时的稳定,但这并不能许诺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再被点燃,种族冲突不再威胁到民主。尽管如此,我们仍需保持对现代国家发展的足够信心,从民族主义最初对主权在民的政治民主化愿景出发,重审族裔民族主义的那些合法、正当的政治诉求,充分激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生活力。同时,尊重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断探索和优化包括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在内的各种民主形态及其组合形式,使现代国家得以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在善治轨道上稳健前行。
[1]谭扬芳,贾江华.“向东走”还是“向西走”——乌克兰动荡的根源分析[J].红旗文稿,2014(6):36-37.
[2]张弘.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乌克兰案例研究[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4):23-27.
[3]秦晖.乌克兰民主政治的艰难历程[N].经济观察报,2014-03-10(45).
[4]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28.
[5]张树华.乌克兰民主在选择中迷失(2014-05-26)[2015-02-11][EB/OL].http://www.qstheory.cn/international/2014-05/26/c_1110858597.htm.
[6][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M].上海:三联书店,2010:97-103.
[7]姚大力: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及其演变[J].世界民族,2005(01): 15-22.
[8]沈允.苏联东欧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 (60):34-38.
[9][10]杨光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建设[J].行政科学论坛,2014(04):1-9.
[11]张弘.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6):1-9.
Discussion on the Interactive Game of Ukrainian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Sun Yannan
(Management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9)
In recent years,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Ukraine’s political crisis contacts closely with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transition——weak democratic governanc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rapid democratization.Historical reasons accumulation also caused sharp confrontation with the two main ethnic:Russian ethnic and Ukrainians,the shortcomings of ethnic nationalism severely eroded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So how to define the twin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in what way will the two have interactive 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n state,ca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 be solved?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in Ukraine as a typical multi-ethnic n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from its nation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Ukrainian;democracy;nationalism;relationship
D032,D082
A
1671-5101(2015)03-0113-06
(责任编辑:孙雯)
2015-02-23
孙雁南(1990-),女,安徽黄山人,安徽大学管理学院2014级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