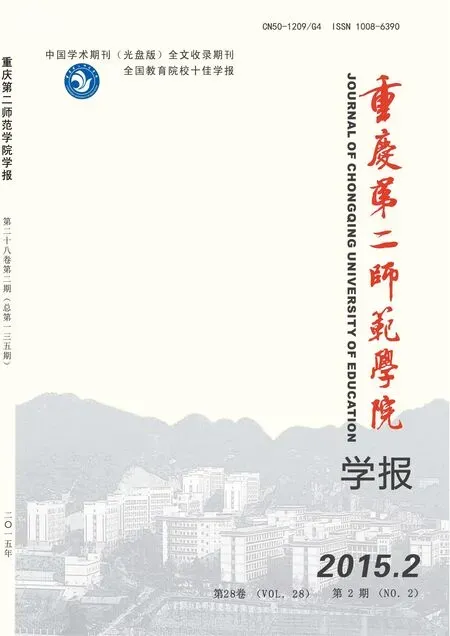数字和字母混合材料加工中的SNARC效应
王强强,侯亚楠,邹骐羽
(东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数字和字母混合材料加工中的SNARC效应
王强强,侯亚楠,邹骐羽
(东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采用快速呈现刺激分类范式,以扑克牌中的7、8、9、J、Q、K为材料考察了具有大小的不同材料间是否也存在SNARC效应。结果发现:(1)被试用左手对小于10的数字反应更快,用右手对大于10的字母反应更快,在数字、字母混合后的材料加工中出现SNARC效应。(2)SNARC效应十分顽固,不易受材料性质的影响,该效应甚至可以发生在不同性质的材料之间。
关键词:SNARC效应;心理数字线;数字;字母
收稿日期:2014-10-25 2014-11-16
作者简介:王强强(1985-),男,宁夏隆德人,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识码:A
文章编号:编号:1008-6390(2015)02-0167-03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111020);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改项目(JG20132209)
一、问题的提出
当要求被试对随机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的数字做奇偶分类并快速按键反应时,被试用左手对小数字反应比右手更快,用右手对大数字反应比左手更快。这一现象不受数字奇偶性质的影响。Dehaene等人于1993首次发现该现象,并将其命名为空间-数字反应编码联合效应(Spatial-Number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effect),即SNARC效应。这一效应的发现说明人们对数字按照其大小从左向右表征在心理数字线上(mental number line),小数字表征在心理数字线的左侧,数字越大,其在数字线上的位置越靠右[1]。
SNARC效应被发现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很多学者采用不同刺激材料对其进行了验证性研究。一时间SNARC效应成为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对SNARC效应的验证性研究整体上可以分为以下方面:第一,不同国籍的学者采用本民族的数字,考察了本民族数字加工中是否存在SNARC效应[2-6]。以潘运、沈德立和王杰的研究为例,他们采用Ponser的实验范式要求被试判断“壹”到“玖”这些数字的奇偶性,探讨了不同提示线索下注意与非注意条件下数字的SNARC效应。结果发现在汉字数字加工中也存在SNARC效应,但是SNARC效应受到注意水平的影响[2]。第二,选用一位数以外的其他阿拉伯数字,考察SNARC效应是否广泛存在于所有的阿拉伯数字加工之中[7-11]。比如高在峰、水仁德、陈晶、陈雯、田瑛和沈模卫对负数SNARC效应研究发现,负数按其绝对值大小表征在心理数字线上,绝对值小的负数表征在心理数字线的左侧,绝对值大的负数表征在数字线的右侧[10]。第三,以非符号形式的数量为材料,考察数量信息加工中的SNARC效应[12-16]。比如吴彦文和杨龙要求被试判断出现的计数单位大于“千”还是小于“千”时发现,计数单位加工中依然存在SNARC效应[16]。第四,采用非数字材料考察这些材料中是否存在SNARC效应,结果发现有顺序的非数字材料中也存在SNARC效应[17-20]。比如王强强、朱小同、康静梅等人要求被试判断呈现字母的颜色时发现,字母加工中存在SNARC效应[19]。
虽然以上研究发现SNARC效应普遍存在于数字、数量和非数字有序材料(比如字母、朝代字)的加工之中,并且他们一致认为在有大小或顺序的材料加工中均会出现SNARC效应。但是在有大小和顺序的混合材料(比如数字和字母混合材料)中是否同样存在SNARC效应呢?这方面至今尚无研究。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SNARC效应。
考虑到扑克牌游戏中表示大小的既有数字(比如7、8、9),也有字母(比如J、Q、K),并且这些数字和字母之间各有其大小和顺序,如K大于J大于7。故本文选用7、8、9、J、Q、K这几个数字和字母并随机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判断呈现数字或字母大于10 还是小于10以考察混合材料加工中是否存在SNARC效应。
二、方法
(一)被试
选取某高校和某中学24(男15,女9)名在校生自愿参加本实验。最大年龄29岁,最小年龄13岁,平均年龄为17.44±4.93岁。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二)材料和仪器
7、8、9、J、Q、K这些数字和字母作为本实验刺激材料,字体宋体,西文字体Times New Roman,颜色黑色,大小为72点阵。将其置于大小为85×85像素的白底图片之上,眼睛距离计算机屏幕47cm处的视角大小为2.5°。仪器为联想笔记本电脑,屏幕大小为14.1寸,分辨率1280×800像素,刷新频率60HZ。
(三)实验设计
2(反应手:左手,右手)×2(材料大小:小于10,大于10)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反应时和错误率。
(四)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用E-prime1.1编写,实验开始后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红色“+”作为注视点,随后会很快被实验选取的任一刺激材料取代,当出现刺激材料后被试要迅速判断出现的刺激材料大于10还是小于10并按相应键做出反应。被试按键反应后呈现1500ms的白色空屏后进入下一试次。3s内未反应记为错误反应并自动进入下一试次(见下图1)。

图1 实验流程图
在按键安排方面本实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要求被试对小于10的刺激用左手按F键反应,对大于10的刺激用右手按J键反应;另一部分正好相反。两部分先后顺序在被试间进行平衡。整个实验中每个刺激重复呈现20次(每个部分呈现10次),正式试验开始前练习12次(每个刺激重复2次),总共144试次,大概需要20分钟。
三、结果分析
剔除三个标准差以外的所有反应时数据,对所剩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本实验中被试最高错误率为12.5%,最低错误率为0,平均错误率很低,为5.5%。故不对错误率统计分析。对反应时数据进行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反应手主效应非常显著,F(1,23)=12.20,P<0.01,η2=0.347,右手反应(460.49ms)明显快于左手(473.29ms);材料大小主效应不显著,F(1,23)=0.01,P>0.05,η2=0.000;反应手和材料大小交互作用非常显著,F(1,23)=9.99,P<0.01,η2=0.303。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左手对小于10的材料反应(465.23ms)比大于10的材料反应(481.36ms)更快,右手对大于10的材料反应(451.98ms)比小于10的材料反应(469.01ms)更快,结果见图2。

图2 左右手对不同大小材料的反应时
四、讨论
已有研究发现SNARC效应普遍存在于符号数字、非符号数字和有序的非数字材料认知加工之中。但是在有大小和顺序信息的不同性质材料之间是否也存在SNARC效应已有研究并未涉及。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理解SNARC效应。因此,本文选用扑克牌中的数字和字母为材料对不同材料间SNARC效应展开了研究。
对研究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被试右手对刺激材料的反应明显快于左手,说明实验中出现了右利手现象。一般情况下,我国绝大多数人为右利手,出现这种结果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有趣的是被试用左手对小于10的刺激材料反应比大于10的刺激材料反应快,用右手对大于10的刺激材料反应比小于10的刺激材料反应快,这说明在数字和字母混合呈现的分类任务中出现了SNARC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是:扑克牌游戏中表示大小的材料由数字(比如本实验用的7、8、9)和字母(比如本实验选用的J、Q、K)共同组成。虽然字母本身不具备大小信息,但是根据游戏规则,在玩扑克牌游戏时都会给这些字母赋予相应的数值来表示其大小。这样使得扑克牌中的字母本质上与数字一样带有相应的大小信息。所以把数字与字母混合后的认知加工中也会出现SNARC效应。
前人采用不同的材料和实验范式研究发现SNARC效应广泛存在于数字、数量和非数字有序材料的认知加工之中。他们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为SNARC效应的普遍性提供了相关证据。本研究超越前人的研究,创造性地选用不同种类的材料考察SNARC效应,发现不同种类材料分类中依然能够出现SNARC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SNARC效应的普遍性提供了新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果说明只要条件具备,SNARC效应甚至可以在不同的材料加工中出现。
五、结语
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数字和字母混合后的不同性质材料之间的认知加工中存在SNARC效应。(2)SNARC效应非常顽固,只要条件具备,很少受材料性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Dehaene,S.,Bossini,S.,& Giraux,P.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parity & number magnitude[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1993,122:371-396.
[2]潘运,沈德立,王杰.不同注意提示线索条件下汉字加工的SNARC效应[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9,7(1):21-26.
[3]刘超,买小琴,傅小兰.不同注意条件下的空间-数字反应编码联合效应[J].心理学报,2004,36(6):671-680.
[4]Calabria M,Rossetti Y. Interference between number processing and line bisection:a methodology[J]. Neuropsychologia,2005(43):779-783.
[5]Nuerk H C. Notational modulation of the SNARC and the MARC(linguistic markedness of response codes)effect[J]. Th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ociety,2004,57(5):835-863.
[6]Nuerk H C,Wood G,Willmes K. The Universal SNARC Effect[J].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05,52(3):187-194.
[7]Brysbaert M. Arabic Number Reading:On the Nature of the Numerical Scale and the Origin of Phonological Recoding[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1995,124(4):434-452.
[8]Reynvoet B,Brysbaert M. Single-digit and two-digit Arabic numerals address the same semantic number line[J]. Cognition,1999(72):191-201.
[9]Tan S,Dixon P. Repetition and the SNARC Effect With One-and Two-Digit Numbers[J]. 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11,65(2):84-97.
[10]高在峰,水仁德,陈晶,等.负数的空间表征机制[J].心理学报,2009,41(2):95-102.
[11]张宇,游旭群.负数的空间表征引起的空间注意转移[J].心理学报,2012,44(3):285-294.
[12]Kirjakovski A,Utsuki N. From SNARC to SQUARC:Universal Mental Quantity Lin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tudies,2012,4(2):217-227.
[13]Ishihara M,Keller P E,Rossetti Y,etal. Horizontal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time:Evidence for the STEARC effect[J]. cortex,2008(44):454-461.
[14]Lidji P,Kolinsky R,Lochy A,etal. Spatial Associations for Musical Stimuli:A Piano in the Head?[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2007,33(5):1189-1207.
[15]胡林成,熊哲宏.刺激模拟量的空间表征:面积和亮度的类SNARC效应[J].心理科学,2011,34(1):58-62.
[16]吴彦文,杨龙.计数单位的空间联合编码效应[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3,11(4):440-443.
[17]Gevers W,Reynvoet B,Fias W.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ordinal sequences is spatially organized[J]. Cognition,2003(87):B87-B95.
[18]Previtali P,de Hevia M D,Girelli L. Placing order in space:the SNARC effect in serial learning[J]. Exp Brain Res,2010(201):599-605.
[19]王强强,朱小同,康静梅,侯亚楠.基于Stroop实验范式的字母顺序信息自动加工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36(5):85-87.
[20]朱小同,祝铭山,王强强.朝代字的空间编码联合效应[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4(7):6-8.
[责任编辑刘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