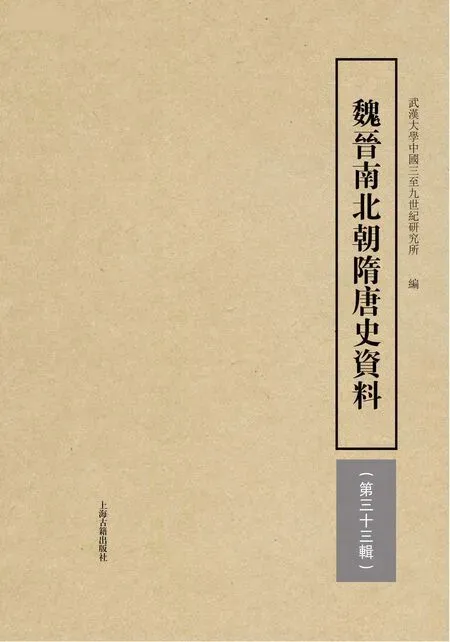《唐故突騎施王子誌銘》再探討
——兼論突騎施黑姓及其與唐朝的關係
吴玉貴
《唐故突騎施王子誌銘》再探討
——兼論突騎施黑姓及其與唐朝的關係
吴玉貴
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西郊發掘了一座唐墓,出土一合墓誌,誌蓋篆書“唐故突騎施王子誌銘”,誌題“大唐故交河公主孫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光緒墓誌銘并序”(以下簡稱《墓誌》)。*西安市文物保護研究所: 《西安西郊唐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8期,第4—18頁。《墓誌》發表後,葛承雍和周偉洲先生先後撰文,進行了介紹和研究。*葛承雍: 《新出土〈唐故突騎施王子誌銘〉考釋》,《文物》2013年第8期,第4—18頁。周偉洲: 《〈唐故突騎施王子誌銘〉補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4年第1期,第110—114頁。以下引葛、周論點俱出二文,不另注。討論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有名的交河公主或金河公主的公案上,*除了以上兩篇論文外,關於這個問題請參見岑仲勉《唐史餘瀋》卷二“交河公主或金河公主”(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第90— 92頁。對突騎施奉德可汗及王子光緒入質唐朝的問題關注不多,尤其是對光緒所處時代的突騎施歷史及突騎施與唐朝的關係未及作具體研究,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大體而言,突騎施汗國的歷史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突騎施首領烏質勒和娑葛統治時期(690—711),第二階段爲突騎施首領蘇禄統治時期(715—738),第三階段是突騎施分裂時期(738—780?),前兩個階段分别由黄姓和黑姓統治,後一階段黄、黑二姓各立可汗,互不統屬。在漢文傳統文獻中,《舊唐書》、《新唐書》等正史都爲突騎施立傳,*《舊唐書》卷一九七《西突厥傳》下附《突騎施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5090—5192頁;《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6066— 6069頁。《通典》、《太平寰宇記》等也有專章記述突騎施歷史,*《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附《突騎施》(北京: 中華書局,1988年),第5462—5464頁;《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七《西突厥》附《突騎施》(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3776—3779頁。相關記載並不算十分稀缺。但具體來説,突騎施蘇禄可汗之前,即突騎施汗國第一、第二階段相關記載較多,突騎施分裂時期的歷史記載非常少,内容分佈失衡。《通典》、《舊唐書》記突騎施事止於開元二十八年(740)吐火仙可汗入唐,基本未涉及突騎施分裂時期的歷史,《新唐書》對分裂時期的記載也僅有寥寥數語,突騎施分裂時期史實零落,綫索隱晦,嚴重影響了對突騎施歷史的整體認識。突騎施王子光緒於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在長安去世,其人其事不見於傳統文獻記載,《墓誌》的出土對認識和研究突騎施分裂時期的歷史和安史之亂爆發後的西域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本文試以突騎施黑姓與唐朝的關係爲主綫,系統梳理蘇禄可汗以後即突騎施汗國分裂時期的歷史綫索,並在此基礎上,將《墓誌》放在光緒入質長安或與入質長安較近的時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希望能爲《墓誌》的研究提供新的觀察角度。
一、 突騎施汗國的分裂與阿史那昕入主突騎施的失敗
蘇禄可汗(715—738年在位)是突騎施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統治者。*玄宗開元三年(715)蘇禄始見於史,但他就任突騎施可汗當在此前。參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一開元三年(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第6714頁。蘇禄在位期間,正處在唐朝、大食、吐蕃諸方勢力匯聚西域的重要歷史時期。蘇禄部下有二十萬衆,“雄西域之地”,*《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附《突騎施傳》,第5192頁。建立了强大的突騎施政權。在突騎施汗國分裂之前,漢文史料中鮮見黄、黑二姓的相關記載。到了蘇禄晚年,由於老病,再加上與唐朝戰爭的失利,對突騎施汗國的控制力下降,諸部離散,黄姓、黑姓開始凸顯。《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騎施傳》:
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最爲强盛。百姓又分爲黄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開元)二十六年夏,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禄,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禄之子咄(吐)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咄火仙”,《通典》卷一九九《突騎施》(第5463頁)、《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七《突騎施》(第3778頁)作“吐火仙”,據改。
“百姓又分爲黄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新唐書》作“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爲‘黄姓’,蘇禄部爲‘黑姓’,更相猜讎”。*《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8頁。進一步解釋了突騎施黄姓和黑姓的具體構成。黄姓、黑姓的出現,可以追溯至突騎施興起初期即黄姓娑葛的父親烏質勒可汗統治時期(690—706)。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在張説主持貢舉期間,曾針對當時西域形勢出過一道策問,稱自從王孝傑長壽元年(692)再開四鎮以來,已過去了十年,“今赤曷既并於黄姓,默啜復覘於庭州,漢掖徒張,胡臂未斷,而内匱積穀,外非足兵。於何出踐更之師,奚使間穹廬之黨,息人靜國,有策存乎?”*張説: 《兵部試沈謀秘算舉人策問三道(之二)》,《全唐文》卷二二二(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第2240頁。《四部叢刊》本《張説之文集》未收這道策問。這是我們見到的較早的關於黄姓的記載。這時正值烏質勒異軍突起,以武力取代了原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統治地位。“今赤曷既并於黄姓”一句,顯然是指烏質勒征服原西突厥屬部而言。張説稱娑葛的父親烏質勒爲黄姓,與《新唐書》所載突騎施“自謂娑葛後者爲‘黄姓’”完全相符。從張説的記載中可以了解到,雖然《新唐書》記載,突騎施部落自稱娑葛的後代爲黄姓,但至少在娑葛的父親烏質勒在世時,突騎施這一支就已經有了“黄姓”的稱謂。“赤曷”的確切含義不詳,《舊唐書》記載“百姓又分爲黄姓、黑姓兩種”,據此判斷,“赤曷”有可能是8世紀初年對後來漢文文獻中所謂“黑姓”的别稱。如果這個假定可以成立,則可説明至少從8世紀初年起,突騎施就已經有了黄、黑二姓的區分,只是“黑姓”的稱謂在漢籍中還没有最終固定。
《舊唐書》先稱“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最爲强盛,又謂突騎施“百姓又分爲黄姓、黑姓兩種”,顯然莫賀達干與都摩度兩部雖然勢力强盛,但本身很可能並不屬於黄姓或黑姓部落。都摩度最初與莫賀達干聯兵殺害黑姓蘇禄可汗,表明在突騎施汗國分裂初期,他們屬於突騎施黑姓的對立方。與莫賀達干反目後,都摩度轉而與突騎施黑姓即蘇禄的後代結成了聯盟,擁立蘇禄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與莫賀達干相互攻擊,將突騎施黑姓作爲自己的支持對象。《舊唐書》明確説都摩度擁立吐火仙可汗是爲了“輯其餘衆”,即招撫離散的突騎施諸部落,可知蘇禄可汗的後裔當時在突騎施部落中有很强的號召力,是都摩度在與莫賀達干的鬥爭中可以依賴的重要政治資源。史書中並没有明確記載莫賀達干所屬的陣營。但這時突騎施百姓分爲黄、黑兩姓,互相猜讎,而莫賀達干又屬於黑姓支持者都摩度的對立面,則他很可能屬於突騎施黄姓即娑葛後代一方。
都摩度與突騎施黑姓的聯合,使突騎施内戰規模進一步擴大。莫賀達干爲了增强與都摩度對抗的實力,轉而投靠了唐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唐朝在西域的軍事力量正式介入突騎施内戰。唐軍的加入,促使突騎施内部黄、黑兩姓間的戰爭,轉化成了以唐朝及其支持的莫賀達干及突騎施黄姓陣營,針對都摩度及突騎施黑姓的戰爭,唐朝也由局外人變成了戰爭的主導方。開元二十七年(739),雙方正式開戰。突騎施黑姓一方由吐火仙可汗、都摩度守碎葉,黑姓可汗爾微特勤守怛邏斯城。唐朝一方也分爲兩路進擊,一路由安西節度使蓋嘉運與莫賀達干率領進攻碎葉城,參戰者有石國和史國的國王;另一路由唐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率領,與拔汗那王一起奔襲怛邏斯城。蓋嘉運攻克碎葉,俘虜了吐火仙可汗;夫蒙靈詧也偷襲成功,斬殺爾微特勤和他的弟弟撥斯,并進入曳建城,俘獲了交河公主及蘇禄可敦、爾微可敦。開元二十八年(740)三月,蓋嘉運將吐火仙可汗一行押送回長安,唐玄宗赦免吐火仙,並任命他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修義王,*《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8頁。《册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下文簡稱《册府》,中華書局,1960年,第11346頁)作“循義王”。莫賀達干及黄姓一方在唐軍的支持下大獲全勝。*這次戰役情況,主要參見《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附《突騎施傳》,第5192頁;《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8頁;《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七年,第6838頁;《册府》卷三五八《將帥部·立功》,第4245— 4246頁。按照常理,蘇禄的兒子吐火仙可汗當然是突騎施黑姓的大可汗,爾微特勤應是小可汗,但是在漢文文獻中,並没有明確指稱吐火仙可汗爲“黑姓”,而對於爾微特勤,則特别記載是“黑姓可汗”。姑存疑。
但是,軍事上的勝利並没有能夠使莫賀達干獲得對西突厥故地的實際統治權,或者説没有得到唐朝對他的統治地位的最終認可。戰爭結束後,蓋嘉運向唐玄宗提議,册立長期居住在唐朝境内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懷道的兒子阿史那昕爲十姓可汗,入主西突厥故地。蓋嘉運的建議得到了玄宗的認可。開元二十八年四月,唐朝正式册立阿史那昕爲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濛池都護,並册封他的妻子涼國夫人李氏爲交河公主,*《新唐書》卷二一五下《西突厥傳》,第6066頁;《唐大詔令集》卷四二《册交河公主文》(北京: 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206—207頁。此“交河公主”與王子光緒的祖母封號相同,但一爲西突厥可汗之妻,一爲突騎施可汗之妻,不應混而爲一。説見上引周偉洲文。準備返回西域,統領包括突騎施在内的西突厥各部。
對於莫賀達干而言,唐朝的安排無疑是一種嚴重的背叛行爲。莫賀達干聲稱:“討平蘇禄,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附《突騎施傳》,第5192頁。於是聯絡烏蘇萬洛等突騎施首領,“扇誘諸蕃背叛”。*《册府》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第11482頁。在莫賀達干的威脅下,唐玄宗不得已改變成命,任命莫賀達干爲突騎施舊部可汗,而阿史那昕則兼統突騎施以外的西突厥諸部,由安西節度使蓋嘉運出面“宣恩招諭”,居間調停,莫賀達干和阿史那昕各統所部,互不相屬,雙方暫時達成妥協。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莫賀達干率妻子及纛官首領歸降唐朝,表示服從唐朝政府的新安排。*有關莫賀達干降而復叛的經過,不同史書的記載差歧很大,本節主要根據《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第6841頁)所引《考異》的考證及《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8—6069頁)、《册府》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第11482頁)的記載。
扶植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是西突厥汗國滅亡(高宗顯慶二年,657)以後,唐朝政府一貫施行的傳統方針。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無論唐朝政局及西域形勢如何變化,扶植西突厥王族的方針,都不曾在根本上有所改變。即便是在7世紀末葉突騎施政權已經成爲西突厥十姓故地的新主人之後,唐朝仍然不斷派遣長期居住在内地的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子孫前往西域,千方百計取代突騎施已有的統治地位。突騎施可汗蘇禄的興起和他對突騎施的長期統治,曾迫使唐朝一度擱置了長期奉行的扶植西突厥王族的政策。但隨着蘇禄的去世和突騎施汗國的分裂,唐玄宗故伎重施,再次選擇了扶植阿史那氏子孫的傳統政策,將已經淡出西域歷史舞臺的西突厥阿史那氏貴族又一次推到了前臺。
其實早在突騎施汗國分裂之前,即唐朝與突騎施戰爭期間(734—740),唐朝政府就已經制定並實施了將西突厥阿史那氏王族派回西域的計劃。開元二十三年(735)深冬,當唐軍開始反攻突騎施之際,唐玄宗在給安西節度使王斛斯的信中,一方面提醒王斛斯,在戰爭過程中要注意與北庭節度使蓋嘉運相互配合,同時又特别指出:“史震襲父可汗,即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失所宜。”*《張九齡集校注》卷一○《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書》(熊飛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第616—617頁。這位承襲了父親的可汗稱號,受命隨唐軍前往西域“招輯”突厥部落的史震,應該就是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後代。*唐代文獻中往往將突厥姓“阿史那”與“史”混稱,如阿史那獻又稱“史獻”,阿史懷道又稱“史懷道”,阿史那昕稱“史昕”等,都是顯例。此“史震”既然“襲父可汗”,來到西域從事“招輯”,顯然他應該是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子孫,而且他的父親還擔任過“可汗”。開元六、七年間(718—719),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獻在突騎施蘇禄可汗的逼迫下從西域回到長安(張説: 《并州論邊事表》,《文苑英華》卷六一四,北京: 中華書局,1990年,第3188頁),稍前在開元二年(714),唐朝也曾爲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加特進(《册府》卷九七四《外臣部·褒異》,第11443頁),我們推測,史震,很可能就是阿史那獻或阿史那懷道的兒子。唐玄宗囑咐王斛斯遇事要與史震“計會”商議,共同妥善處理與“招輯”相關的事宜。可知至少在“招輯”突厥部落的問題上,史震充當了與安西節度使王斛斯同等重要的角色。雖然史震在戰爭期間及戰後究竟起過何種作用未見記載,任用史震與稍後阿史那昕被册立爲西突厥可汗之間到底有什麽關係也並不清楚,但對史震的任命表明,唐朝在與突騎施戰爭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重新起用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子孫。换言之,即便册命阿史那昕果真是在戰後出自安西節度使蓋嘉運的建議,也只是迎合或體現了唐朝政府的既定方針,不應單純理解爲蓋嘉運本人的謀略。
但是,此後的西域局勢並没有朝着唐朝政府預期的方嚮發展,唐朝希望的莫賀達干與阿史那昕相安共存的局面也没有出現。天寶元年(742)十二月,唐玄宗專門派遣軍隊護送阿史那昕前往西域履任,當行至碎葉西南的俱蘭城時,莫賀達干發兵殺害了阿史那昕,交河公主與兒子阿史那忠孝一起逃回唐朝,莫賀達干擁兵自立爲可汗,與唐朝徹底決裂。*《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9頁。唐朝扶植西突厥阿史那氏的計劃徹底失敗。*《新唐書》卷二一五下《西突厥傳》載(第6066頁):“(阿史那)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干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遂亡。”將阿史那昕的敗亡作爲西突厥滅亡的標誌性事件。
二、 突騎施汗國分裂時期黑姓與唐朝的關係
在莫賀達干與唐朝決裂之際,早先擁立突騎施黑姓吐火仙可汗反對唐朝的突騎施大首領都摩度的立場再度戲劇性逆轉,與唐朝握手言和。唐朝原來的盟友莫賀達干成了敵對方,而都摩度與突騎施黑姓則反而成了唐朝依靠並扶植的力量。天寶元年(742)六月,唐朝册立突騎施大纛官都磨度闕頡斤爲三姓葉護,授左羽林軍大將軍,*《新唐書》卷二一五下《西突厥傳》,第6066頁。並且頒賜鐵券。*《册府》卷九七五《外臣部·褒異》,第11457頁。册立詔書稱:
維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六月甲戌朔二十二日乙未,皇帝詔曰: 於戲,王者無外,不隔遐方,必揆忠款,是加寵命。咨爾骨咄禄毗伽都磨度闕頡斤,代襲榮望,名擅驍騎,信義有聞,部衆稱美。往在蕃任,受制兇威。元惡已除,能革心而向化;牙纛既立,克輔主以歸懷。嘉爾誠心,載崇賞秩,是用命爾爲三姓葉護。往欽哉,爾其祗奉典册,懋明忠順,善翊君長,勉樹勳庸。可不慎歟!*《册府》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第11348頁。參見《全唐文》卷三九,第423頁。
“都磨度闕頡斤”,就是“都摩度”其人。“歸懷”,《全唐文》作“懷歸”,文氣較順。“元惡已除,能革心而向化;牙纛既立,克輔主以歸懷”一句,是理解這段史料的關鍵文字。此時莫賀達干甫與唐朝反目,莫賀達干最終兵敗在天寶三載(見下文),“元惡已除,能革心而向化”中的“元惡”,不可能指莫賀達干,而應該是指突騎施蘇禄可汗。意思是説蘇禄可汗死後,都摩度方纔有了洗心革面,向唐朝投誠盡忠的機會。這裏隱去了在突騎施汗國分裂初期,都摩度一度曾擁立吐火仙可汗與唐朝爲敵的事實。“牙纛既立,克輔主以歸懷”,大概意思是指,都摩度在這時擁立了新主,並輔佐新主歸服唐朝。但詔書中没有具體記載都摩度所輔之“主”到底是誰。據《新唐書》記載:“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爲可汗,數通使貢。”*《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9頁。顯然都摩度擁立的新主,就是突騎施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據《册府》記載,天寶二年九月“黑姓可汗骨咄禄毗伽”遣使貢獻方物,*《册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第11411頁。與《新唐書》所説骨咄禄毗伽可汗“數通使貢”也適相符契。應該特别關注的一點是,唐朝册拜都摩度爲三姓葉護在天寶元年六月,莫賀達干殺害阿史那昕在同年十二月。也就是説,在莫賀達干與唐朝公開反目之前半年,唐朝就已經與都摩度即突騎施黑姓結成了同盟。
天寶三載,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發兵擊敗並斬殺莫賀達干。《通鑑》天寶三載下稱:
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六月,甲辰,册拜骨咄禄毗伽爲十姓可汗。*《通鑑》卷二一五,第6860頁。
《通鑑》本節記載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一是據上文討論,早在天寶元年,都摩度已輔立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次年,骨咄禄毗伽可汗還曾向唐朝貢獻方物。《通鑑》記載的天寶三載六月,只能理解爲唐朝政府正式册封骨咄禄毗伽可汗的時間,而不是他始立爲可汗的時間。其次,《通鑑》稱夫蒙靈詧爲“河西節度使”。但根據相關記載,開元二十九年,夫蒙靈詧繼田仁琬之後擔任安西節度使,*據《舊唐書》卷一○三《王忠嗣傳》載,開元二十九年,田仁琬自安西轉任河東節度使(第3198頁)。又,據《新唐書》卷一三五《高仙芝傳》,高仙芝在蓋嘉運和田仁琬任安西節度使時一直未獲重任,後事夫蒙靈詧,“開元末,表爲安西副都護”(第4576頁)。可證在開元二十九年,夫蒙靈詧已接替田仁琬擔任了安西節度使。迄止天寶六載被高仙芝取代,*《通鑑》卷二一六天寶六載十二月,第6887頁。在此期間未見靈詧曾轉任或兼任河西節度使;而且天寶元年至四載期間,河西節度使爲王倕其人,*《新唐書》卷五《玄宗紀》,第143頁;《通鑑》卷二一五天寶五載正月,第6870頁。夫蒙靈詧不可能在天寶三載轉任或兼任河西節度使。《通鑑》之“河西”顯然應是“安西”之誤。
雖然相關文獻中没有記載都摩度與黑姓可汗曾參加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征討莫賀達干的軍事行動,但夫蒙靈詧五月獻俘,唐朝政府在六月就應夫蒙靈詧的請求,正式册立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揆諸情理,突騎施黑姓可汗一方顯然參加了針對莫賀達干的戰爭。從《楊和碑》反映的情況分析,天寶三載册封黑姓可汗,是當時一件非常轟動的大事件:
(前略)公名和,字惟恭,河東人也。(中略)二十七年,有詔四鎮諸軍大出漢南壘,問罪蘇禄,洗兵滇河。旌甲數萬人,城池五十國,公以麾下爲前,四罪之名,*所謂“四罪”,是指遠古時代之共工、驩兜、三苗、鯀,《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四罪而天下咸服。”即此。有百牢之饋,酈生之奇也。後五載,有累姓之後來朝京師,金甲善馬,織文大貝,告於廟之室,旅於大庫之庭。公覽傅、常遺風,烏孫故事,井泉可數,談笑成功。上壯之,賜弓甲一副,廄馬二疋,伏波之美也。*楊炎: 《楊和碑》,《文苑英華》卷九一七,第4829— 4830頁。參見《全唐文》卷四二二,第4307— 4308頁。原題《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
碑主楊和,天寶十四載(755)卒于安西四鎮節度副使任,開元、天寶年間,親歷了西域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碑文所載開元二十七年問罪蘇禄,就是上文提到的安西四鎮唐軍與莫賀達干聯合,進攻突騎施黑姓吐火仙可汗的軍事行動。蘇禄開元二十六年已死,碑文以“蘇禄”代指與唐朝爲敵的突騎施勢力。據上文討論,此役唐軍分南北兩路,北路由安西節度使蓋嘉運率領,自安西直搗碎葉,南路由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率領,從疏勒奔襲怛邏斯城。碑稱“出漢南壘”,則楊和應該參加了夫蒙靈詧攻擊怛邏斯城的行動。“滇河”不詳,碑文“洗兵滇河”與“問罪蘇禄”相牽,應是指怛邏斯附近的某條河流。又,西漢酈食其曾以一介之使下齊七十餘城,碑謂楊和有“酈生之奇”,或者在這次戰役中,楊和曾作爲唐使召降西域諸國或突騎施部落。“傅、常”即西漢傅介子、常惠,二人都是漢代經營西域的名將。碑文將楊和與傅介子、常惠相類比,稱“上壯之,賜弓甲一副,廄馬二疋”,“壯之”云云,與“酈生之奇”的描述也正相符合。
最重要的,是“後五載,有累姓之後來朝京師”記載。按,唐代西域漢文史料未見有“累姓”之記載。碑文“後五載”,前承開元二十七年。開元二十七年之後五年,正當天寶三載。據上文,天寶三載六月,唐朝册封突騎施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完全有理由推定,“累姓”就是“黑姓”之誤,“累”、“黑”形近,因而致訛。從“黑姓之後來朝京師”推斷,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很可能在天寶三載親自來到長安,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他還帶來了“金甲善馬,織文大貝”,而唐朝則因爲他的到來舉行了告廟的儀式。楊和應該是在這一年陪同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來到長安,因而有機會得到唐玄宗的賞識。《楊和墓誌》補充了唐與突騎施戰爭及册封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的重要史料。
對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的册封,標誌着唐朝政府對突騎施黑姓統治地位的正式認可,經過了反覆摇擺之後,突騎施黑姓最終成爲了唐朝扶持和依靠的對象。到了天寶八載(745),唐朝又册封“十姓突騎施移撥可汗骨咄禄毗伽俱支”,*《册府》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第11349頁。雖然相關史料没有具體指明移撥是否是黑姓可汗,但此前在天寶三載,唐朝册封了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此後在天寶十二載,又“别册黑姓種伊羅密施爲骨咄禄毗伽突騎施可汗”。*《册府》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第11350頁。“伊羅密施”又稱“登里伊羅密施”。不僅在移撥前、後册立的兩位可汗都是黑姓可汗,而且兩位可汗的名號都與移撥相近,因此我們認爲,移撥應該也是唐朝册立的突騎施黑姓可汗。黑姓可汗伊羅密施不僅受到唐朝册封,還接受了唐朝頒賜的“特進”官職和鐵券。*《唐大詔令集》卷六四《賜突騎施黑姓可汗鐵券文》,第353頁;同書卷一二九《册突騎施黑姓可汗文》,第696頁。在賜鐵券的詔書中稱,伊羅密施“雖擁在沙漠,常捍煙塵,識進退存亡之端,知古今成敗之數。久率蕃部,歸化朝廷,兼拒兇威,挫其侵軼。精貫白日,義光青史,績用累著,嘉尚良深。”特别表彰他對唐朝的忠誠。稍後在天寶十三載,又有“突騎施黑姓可汗”遣使來朝。*《册府》卷九七五《外臣部·褒異》,第11458頁。這位黑姓可汗,應該就是伊羅密施。安史之亂之後,突騎施黑姓仍然與唐朝保持朝貢關係,肅宗乾元二年(759)八月,“十姓突騎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羅”遣使來朝,肅宗在内殿設宴款待。*《册府》卷一一○《帝王部·宴享》,第1311—1312頁。參見同書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第11414頁;卷九七六《外臣部·褒異》,第11461頁。
綜上所述,玄宗天寶以後,突騎施黑姓雖然記載很少,但通過仔細爬梳,可以整理出大致的綫索,而同一時期對黄姓的記載則幾乎完全闕如。《太平寰宇記》記載:
十三(二)載秋,朝廷又册立黑姓種伊羅密施爲骨咄禄毗伽突騎施可汗,常羈屬安西。自至德已後,突騎施部落轉衰弱,分爲二部: 一爲黄姓,即娑葛之族,一爲黑姓,即蘇禄之族。互相攻擊,各立可汗。旋又篡奪,因遂分散。至乾元元年,復遣朝貢。大曆之後,三姓葛邏禄還盛,移據碎葉川。百姓貧者,或納税于葛禄葉護處。*《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七《西突厥》附《突騎施》,第3778—3779頁。“十三載秋”,《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九《册突騎施黑姓可汗文》在“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通鑑》卷二一六天寶十二載亦繫于九月甲辰。據改“十三”爲“十二”。點校本失校。
《太平寰宇記》的這段史料,又見於《新唐書》和《册府》,前者稱:“至德後,突騎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9頁。後者稱:“自至德年後,部落衰弱,分爲二部,各立可汗。旋又篡奪,因而分散。”*《册府》卷九六七《外臣部·繼襲》,第11372頁。稍加比較可知,三段記載應該出自相同的史源,只是《太平寰宇記》保留的記載更爲詳盡。但即便是從《太平寰宇記》的記載中,除了黄、黑二姓各立可汗相互攻擊外,也無法了解到有關突騎施黄姓的更多的内容。到了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即唐朝勢力最終撤出西域稍前,*吐蕃軍隊最後攻陷唐西州,即唐朝勢力最終退出西域在貞元八年(792),説見陳國燦《八、九世紀間唐朝西州統治權的轉移》,《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0— 620頁。唐朝曾爲“四鎮節度管内黄姓纛官、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頒賜鐵券,詔書中表彰頓啜護波支“嗣守職官,祗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並稱“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于鼎彝,族列於藩籍”。*《陸贄集》卷一○《賜安西管内黄姓纛官鐵券文》(王素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第294—296頁。參見《唐大詔令集》卷六四,第353頁。如果詔書的記載可信的話,則突騎施黄姓頓啜護波支的祖先也一直與唐朝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但從上文梳理的天寶以後有關唐朝與突騎施關係的記載中,並没有見到反映突騎施黄姓與唐朝關係的具體史料;*突騎施被葛邏禄吞併的具體時間不詳,要之,應在代宗大曆(766—779)以後。參見《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9頁;《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七《西突厥》附《突騎施》,第3779頁。而且更重要的是,據《新唐書》記載:“大曆(766—780)後,葛邏禄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禄,斛瑟羅餘部附回鶻。”*《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9頁。所謂“二姓”,就是指突騎施黄、黑二姓,“斛瑟羅餘部”應該是指原西突厥十姓部落。*突騎施汗國開國可汗烏質勒最初隸屬於西突厥斛瑟羅可汗,號莫賀達干,後取代斛瑟羅,成爲西突厥十姓故地的統治者。參見《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傳》附《突騎施傳》,第5190頁;《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騎施傳》,第6066頁。突騎施臣服葛邏禄,恰恰與唐朝册封突騎施黄姓大纛官前後相銜接,我們懷疑突騎施黄姓降附唐朝,或者與葛邏禄部的擴張有關,“乃祖乃父,代服聲教”云云,很可能是詔書中慣常使用的虚飾之語,不能用來説明此前黄姓與唐朝的關係。否則,我們便不能理解,天寶以後漢文史料中爲什麽没有明確提到突騎施黄姓。
除了册封和朝貢活動外,天寶以後,唐朝西域軍隊曾發動過針對突騎施的兩次戰爭。一次見於杜佑的族侄杜環的記載,稱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曾攻打碎葉城,“城壁摧毁,邑居零落”。*《通典》卷一九三《石國》引《經行記》,第5275—5276頁。碎葉城是突騎施活動的中心地區,這次行動的對象肯定是突騎施。一是天寶十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新唐書》卷五《玄宗紀》,第148頁;《册府》卷一三一《帝王部·延賞》,第1571頁;同書卷四三四《將帥部·獻捷》,第5158頁。又,《舊唐書》卷一○九《李嗣業傳》(第3298頁)載,天寶十載,李嗣業從高仙芝平石國,“及破九國胡並背叛突騎施,以跳盪加特進,兼本官”。諸書並未記載高仙芝破突騎施的具體時間,要之,當在天寶十載稍前。由於缺乏相關記載,我們對這兩次戰爭的具體細節幾乎一無所知。學界研究認爲,王正見攻打碎葉和高仙芝擒降突騎施可汗,都是唐朝針對突騎施黄姓的軍事行動。也就是説,雖然缺少直接證據,但根據當時形勢分析,從開元末年到怛邏斯戰役期間,作爲西突厥故地中心的碎葉及附近地區,一直是與唐朝敵對的黄姓突騎施活動的重點地區。*前嶋信次《タラス戦考》,《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民族·戦争》,東京: 誠文堂新光社,1982年,第42—112頁;畢波《怛邏斯之戰和天威健兒赴碎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31頁。特别請參考畢波文。
三、 《唐故突騎施王子誌銘》再探討
《墓誌》正文13行,滿行17字,正文186字。爲了討論方便,以下試根據《西安西郊唐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墓發掘簡報》公佈的圖片,並參考葛承雍、周偉洲先生的録文,將墓誌正文迻録於此:
永泰元年二月日,突騎施質子光緒卒。 」 詔下有司,官給葬備,以永泰二年十月十六」日窆於長安縣承平原,典也。突騎施蓋烏孫」之後,自西漢以來,與中國通爲婚姻之舊。 」皇家撫柔殊俗,亦以交河公主降焉。光緒即」公主之孫、奉德可汗之子。少自絶域,質於京」師,緬慕華風,遂襲冠帶。希由余之識達,宗日」磾之重慎,内侍歷年,敬而無失。故於其終也,」 恩禮加焉。亦所以來遠人、報忠款者也。史官」奉職,乃爲之銘曰: 」生遠國兮慕」皇洲,瞥過隙兮逝不留,望故鄉兮蕪絶万里,」聖澤兮松檟千秋。」*第1行“光緒卒”,因涉下文“詔”字,敬空兩格;第4行“婚姻之舊”,因涉下文“皇”字,敬空一格;第12行“生遠國兮慕”,因涉下文“皇”字而提行。葛承雍録文對敬空、提行以及末行結尾的空白處,全部都補以闕字符“□”,不解有何深意。又,末句“望故鄉兮蕪絶万里,聖澤兮松檟千秋”,“聖澤”上疑原石奪去一字。本文斷句、標點與葛、周二文略有不同,請參看。
關於《墓誌》涉及的交河公主的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周偉洲先生的意見,《墓誌》中記載的交河公主,就是開元十年嫁與突騎施可汗蘇禄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懷道之女,她與後來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昕(阿史那懷道之子)的妻子李氏雖然封號相同,而且是姑嫂關係,但一位是突騎施可汗之妻,一位是西突厥可汗之妻,二者判然有别,不能混爲一談;更不能將《墓誌》中的交河公主,視爲阿史那昕之妻。此外,周偉洲先生還對突騎施部的來源以及光緒葬地承平原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有助於對墓誌的進一步研究。
對於突騎施奉德可汗和王子光緒入質唐朝的問題,周偉洲先生也提出了兩種推測,“一是其父奉德可汗爲唐封之交河公主所生,也很有可能入長安爲質子。在長安,奉德可汗或帶其子光緒,或光緒出生、成長於長安。正如《墓誌》所云,光緒是‘緬慕華風,遂襲冠帶’。另一種可能是,光緒幼年隨突騎施使臣從西域至長安爲質子。”周先生認爲第一種推測的可能性較大,並解釋了傾向於這種推測的原因,稱:
原因是光緒父“奉德可汗”之名,可能是唐朝因其長期爲質子,在開元二十六年蘇禄爲其下莫賀達干所殺後,封其爲“奉德王”(即奉德可汗);爲準備以後將其返回,統領部衆,故而有此敕封。正如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唐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攻佔碎葉,俘突騎施部吐火仙可汗骨啜、弟頡阿波(均蘇禄子)後,唐朝頒《授吐火仙等官爵制》,内云“骨啜可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仍封爲循義王;頡阿波可右武衛員外大將軍”。内吐火仙可汗所封的“循義王”。光緒父“奉德王(可汗)”,都是從唐朝的角度命名的。其次,奉德可汗王子名“光緒”,這也(是?)一個内地漢族的名字;如果其父仍在西域大漠,是決不會爲其子取此名的。
簡而言之,周先生認爲最初入長安爲質的應該是奉德可汗本人,光緒王子幼年隨父入唐,或者是因父爲質而生於長安,後來繼承了父親的質子身份。惟其父子長期在長安爲質,所以纔有漢化的封號或名字。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以爲,周先生提出的第二種推測,即光緒王子本人在少年時期自西域入質長安的可能性較大。以下試簡述理由。
首先,有關“奉德可汗”稱號和“光緒”名字的問題。從歷史事實看,爲突騎施或西域本地首領加封具有明顯政治含義的爵位、封號甚至姓名,是唐代尤其是玄宗朝常見的做法。比如,中宗神龍二年(706),封突騎施首領烏質勒爲懷德郡王;*《通鑑》卷二○八,第6598頁。同年,烏質勒去世後,懷德郡王的稱號由其子娑葛繼承。*《册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第11342頁。景龍三年(709),中宗再册拜娑葛爲欽化可汗,賜名守忠,*《通鑑》卷二○九,第6636頁。《舊唐書》卷七《中宗紀》(第147—148頁)作“歸化可汗”。娑葛的弟弟也被賜名爲守節。*《唐大詔令集》卷一三○蘇頲《命吕休璟等北伐制》,第705頁。開元六年(718),唐玄宗册封突騎施可汗蘇禄爲順國公,*《册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第11343頁。次年,又册拜爲忠順可汗。*《通鑑》卷二一二,第6737頁。對西域諸國的國王也是如此。比如,開元二十七年,册封拔汗那國王爲奉化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寧遠國》,第6250頁。二十八年,册封石國王莫賀咄吐屯爲順義王。*《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九《册莫賀咄吐屯爲順義王文》,第695頁。天寶三載(744),封曹國王哥邏僕羅爲懷德王,*《唐會要》卷九八《曹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79頁。康國王咄曷爲欽化王,*《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康國》,第5311頁。米國王爲恭順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米國》,第6232頁。天寶四載,封安國王屈底波爲歸義王。*《册府》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第11349頁。有些西域土著政權的國名,也被唐朝改换成了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名稱,如開元二十九年,改拔汗那國爲寧遠國;*《册府》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第11724頁。天寶三載,改史國爲來威國等等。*《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第218頁。在天寶三載,唐玄宗甚至將生母竇氏的姓賜給了拔汗那國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寧遠國》,第6250頁。此外,石國王子名遠恩、*《册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第11413頁。拔汗那王名忠節,*《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寧遠國》,第6250頁。也都是非常典型的漢名。這類史例在在皆是,不勝枚舉。所有這些得到唐朝賜封稱號或漢名的突騎施首領、西域國王或其戚屬,都生活在西域本土而不是長安。尤其是早年頒賜給突騎施首領的“欽化可汗”、“忠順可汗”等可汗號,“守忠”、“守節”等漢名,與“奉德可汗”、“光緒”並無二致。這些從唐朝角度命名的漢文稱號或漢名,更多是體現了西域土著政權與唐朝的政治關係狀況,與接受稱號者居住在長安還是大漠並無直接關聯。也就是説,奉德可汗擁有漢化的可汗號,並不足以否定他是居住在西突厥故地的突騎施黑姓可汗;同樣,光緒的漢名也不能證明他生於長安。
其次,從上文的討論可知,在蘇禄可汗死後,即突騎施汗國分裂時期,唐朝與突騎施黑姓一直保持着比較密切的交往,對黑姓可汗的册封至少持續到了天寶十二載,一直到了唐肅宗乾元二年(759),黑姓可汗還與唐朝保持着朝貢關係,這時距離突騎施王子光緒去世(代宗永泰元年,765)只有六年時間。也就是説,從突騎施汗國分裂到質子光緒去世,突騎施黑姓的汗統雖然間有闕載,但基本上傳承有序,而且與唐朝一直保持着傳統的册封關係。唐朝實無必要,也不可能另外册封一位在長安的質子爲突騎施黑姓的“王”(《墓誌》原文作“可汗”),“準備以後將其返回,統領部衆”。
第三,更重要的是,從《墓誌》内容來看,誌文稱光緒“少自絶域,質於京師”,已經明確指出他是從西域來到長安爲質。銘文中所描述的“生遠國兮慕皇洲”,“望故鄉兮蕪絶万里”,也表明光緒王子生自“遠國”,故鄉在“万里”之外的荒蕪絶漠,而不是生在長安,繼承了父親身份的質子。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認爲奉德可汗應該是一位得到唐朝封號的突騎施黑姓可汗,王子光緒是奉德可汗由西域派往長安的質子。
《墓誌》内容非常簡單,只提到了光緒的卒、葬年代,並没有記載奉德可汗擔任可汗的時間,以下試根據《墓誌》提供的年代綫索,結合上文討論的傳統文獻的相關記載,做初步的推論。
光緒王子卒於代宗永泰元年(765),次年入葬。《墓誌》稱他“内侍歷年,敬而無失”,但没有記載究竟何時入長安爲質。今按,交河公主嫁與蘇禄可汗是在開元十年(722),按一般情況來説,迄止永泰元年,奉德可汗應爲42歲左右。由上文可知,吐火仙被俘之後,漢文傳統文獻中保留的,可知姓名或可汗號的突騎施黑姓可汗總共有四位,即天寶元年(742)由都摩度扶植的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天寶八載(749)由唐朝册立的骨咄禄毗伽俱支可汗,天寶十二載(752)册立的伊羅密施可汗和在乾元二年(759)向唐朝進貢的黑姓可汗阿多裴羅。如果排除奉德可汗與上述四位可汗中的某位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如果奉德可汗與此前四位可汗中的某位是同一人的話,唐朝官方記載中應該記録“奉德”這個明顯出自唐朝册封的可汗號,而不是他們在本國的可汗號或本名。則他很有可能就是阿多裴羅之後的一位突騎施黑姓可汗,即在乾元二年或稍後(即乾元二年至永泰元年之間)繼立的第五任突騎施黑姓可汗,他在阿多裴羅之後擔任黑姓可汗,並在繼位後派遣王子光緒入質長安。我們認爲這種推測不僅符合已知的突騎施黑姓可汗序列,而且與《墓誌》稱王子光緒入質後“内侍歷年”的描述也是相符的。
光緒王子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位入質長安的突騎施質子。*葛承雍先生説:“‘光緒’顯然不是突騎施派入京師長安的第一個質子,《册府》卷九七五《外臣部》記載開元二十二年六月‘突騎施遣其大首領何羯達來朝,授鎮副,賜緋袍、銀帶及帛四十匹,留宿衛’。這個何羯達就是一個留宿衛的突騎施質子,其宿衛授官雖然不高,但‘執戟丹墀,策名戎秩’,通過蕃望功效途徑步入升遷仕途。”今按,入唐質子多司宿衛之職,但不一定外族宿衛者必是質子。此何羯達是唐代西域歷史上的一位知名人物,開元二十二年,何羯達與突騎施闕俟斤驅趕羊馬至唐貿易,行至北庭,何羯達向北庭都護劉涣告密,稱闕俟斤謀反,劉涣殺闕俟斤,從而引發了唐朝與突騎施的大規模戰爭,何羯達也因此留在了長安。事見《張九齡集》卷一一《敕突騎施毗伽可汗書》,第635— 640頁。何羯達因告密立功而入唐宿衛,與所謂“質子”毫不相干。《墓誌》記載光緒入質長安後“希由余之識達,宗日磾之重慎,内侍歷年,敬而無失”,死後“官給葬備”,並由史官撰寫墓銘。毫無疑問,光緒入朝後曾在唐朝宫廷内奉職。我們知道,歷官是唐代墓誌書寫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但奇怪的是,墓誌中並没有提到光緒在唐朝宫廷擔任的官職。如果没有其他的特别原因,這種情況表明王子光緒雖然在内廷供職“歷年”,但唐朝並没有授予他具體官職。依唐朝慣例,來到長安宫廷的各國質子照例要由鴻臚寺按照“蕃望大小”奏擬授官(説見下文),很少見到王子光緒這樣奉職歷年而無具體官職的史例。葛承雍先生的論文中約略涉及了這個問題: 他解釋説:
有人猜測“光緒”是王子,認爲他“生前地位較高”。實際上當時京師長安聚集了不少周邊民族的質子“留宿衛,習華禮”,光緒不過是衆質子中的一員,地位不會太高,埋入平民墓地亦屬正常。況且此時突騎施正走向衰落,已不構成對唐朝的威脅。所以新出土墓誌對光緒質子事迹記録簡單,没有明確記載他入侍宿衛,或擔任過其他實職,連唐朝按慣例對質子授予空具名號的虚銜散官也没有,説明他社會身份標志不高,只是安分守己罷了。
《墓誌》中不書光緒職銜,與突騎施是否對唐朝構成威脅,以及光緒本人“社會身份標志不高”,是否“安分守己”等等,應該没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我們認爲,《墓誌》中没有書寫他的官銜,原因很簡單,就是唐朝没有爲他授官;而没有授官的原因,很可能與肅、代之際唐朝對外行政政務近似癱痪的狀況有關。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政局動盪,日常行政尤其是對外事務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亂。唐德宗初即位時,爲了節省行政開支,曾針對四夷使者及地方官員來到朝廷公幹,因政務不暢而長期滯留長安的人員,進行過一次大規模清理,《通鑑》記載: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失職、未敍,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并部曲、畜産動以千計,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敍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通鑑》卷二二五大曆十四年七月,第7264頁。參見《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第322頁;《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第1348—1349頁;《册府》卷五○六《邦計部·俸禄》,第6067頁;《唐會要》卷六六《鴻臚寺》,第1361頁。
“四方奏計”及“言事失職”、“未敍”等諸種情形不論,“四夷使者”,是指來自包括西域及突騎施在内的外來使節。據《唐六典》記載,鴻臚寺典客署掌管“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歸化在蕃者之名數”,“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酋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若疾病,所司遣醫人給以湯藥。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已上官奏聞。其喪事所須,所司量給;欲還蕃者,則給轝遞至境。諸蕃使主、副五品已上給帳、氈、席,六品已下給幕及食料。丞一人判厨事,季終則會之。若還蕃,其賜各有差,給於朝堂,典客佐其受領,教其拜謝之節焉。”*《唐六典》卷一八《鴻臚寺》,第506—507頁。舉凡迎來送往,辨等位,供職事,教禮節,生活所需,病喪處置等等對外交往事務,都屬於鴻臚寺的職責範圍。這些因“事多留滯”而被迫長期滯留在長安客省的四夷使者,顯然是因爲鴻臚寺行政功能的闕失而未能如期遣返故國。
在有關鴻臚寺職責的相關記載中,没有記載入唐質子授官是否屬於歸鴻臚寺的職責範圍,*除了上引《唐六典》外,請參考《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第1885頁;《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第1257—1258頁。但我們從具體史例中可以知道,鴻臚寺除了掌管對外交往一應事務外,還負責爲諸國質子授受官職。開元六年(718),西域吐火羅國質子、吐火羅國王的弟弟僕羅,曾因爲唐朝政府所授官品太低,且多年未能遷轉,向朝廷上書申訴,稱:
(前略)僕羅兄前後屢蒙聖澤,媿荷國恩,遂發遣僕羅入朝,侍衛玉階,至願獻忠殉命,以爲臣妾。僕羅至此,爲不解漢法,鴻臚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類流例,高下相懸,即奏擬授官。竊見石國、龜兹並餘小國王子、首領等入朝,元無功效,並緣蕃望,授三品將軍。況僕羅身恃(特)勤,本蕃位望,與親王一種,比類大小,與諸國王子懸殊,却授僕羅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弟娑(婆)羅門、瞿曇金剛、龜兹王子白孝順等,皆數改轉,位至諸衛將軍,唯僕羅最是大蕃,去神龍元年,蒙恩敕授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至今經一十四年,久被淪屈,不蒙准例授職,不勝苦屈之甚。*《册府》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第11721—11722頁。“恃勤”應作“特勤”,“娑羅門”應作“婆羅門”,據《宋本册府元龜》(中華書局,1989年,第4040頁)改。
唐玄宗特别下敕,指示鴻臚卿“准例定品秩,勿令稱屈”。這是一條了解唐代外來質子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内容涉及質子制度的方方面面。就本文討論的問題而言,從這條史例可以確知,與外來事務的其他方面一樣,唐朝外來質子官品的擬定和授受,也屬於鴻臚寺的職責範圍。
根據上文,代宗時代,鴻臚寺行政功能一度癱痪,未能履行遣返“四夷使者”的職責,致使大量使臣被迫長期滯留在了長安;*唐德宗貞元三年,也針對外來人大量滯留進行過一次規模龐大的清理行動。但清理的原因有所區别,一是因爲“事多留滯”,一是因爲道路斷絶。參見《通鑑》卷二三二貞元三年七月,第7492—7493頁;《新唐書》卷一○七《王鍔傳》,第5169頁。同樣作爲鴻臚寺職責範圍的外來質子官品授受,自然也會因爲行政功能的闕失而受到影響。據此推測,與四夷使者因“事多留滯”,在肅、代之際不能如期返國一樣,突騎施王子光緒在入質長安期間没有被授予官職,也是因爲安史之亂後鴻臚寺行政功能的闕失所致。
由於史料的局限,以往對安史之亂後西域的了解,主要限於安西、北庭諸軍鎮的堅守和吐蕃、回鶻在西域的活動,對突騎施政權及其與唐朝的關係所知甚少,相關研究也不多。通過對《墓誌》的研究可知,至少一直到代宗大曆之前,唐朝政府與突騎施黑姓一直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在此期間,突騎施黑姓可汗不僅接受唐朝的册封,派遣王子入質唐朝,奉德可汗和其子光緒還接受了唐朝授予的漢化的可汗號和漢名。《墓誌》的記載填補了突騎施黑姓可汗世系的空白,豐富了肅、代之際突騎施歷史的内容,有助於全面認識安史之亂後的西域歷史進程,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
2016年7月,40— 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