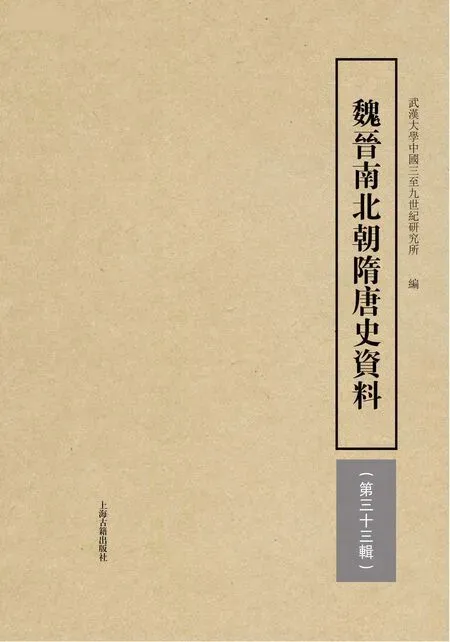敦煌本《靈寳經目》與古靈寳經分類時間邏輯問題論考
王承文
敦煌本《靈寳經目》與古靈寳經分類時間邏輯問題論考
王承文
一、 序説: 古靈寳經分類“時間邏輯”問題的由來
敦煌本陸修靜《靈寳經目》中古靈寳經的分類,是國際道教學界關注和爭論的焦點之一。現存敦煌本《靈寳經目》是按照“元始舊經”和“新經”對古靈寳經進行分類的。相關爭論主要集中在《靈寳經目》之“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録的幾部“元始舊經”上,他們分别是《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洞玄靈寳自然九天生神章》、《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太上洞玄靈寳真一勸誡法輪妙經》。而爭論的焦點是這幾部經典究竟是“元始舊經”還是“新經”。大淵忍爾以及近年出版的《道藏通考》等,都認爲敦煌本《靈寳經目》保留了“元始舊經”和“新經”分類的原貌,即他們都屬於“元始舊經”。*(日) 大淵忍爾: 《道教とその經典》,東京: 創文社,1997年,第100—121頁;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215-239. 王承文: 《敦煌本〈太極左仙公請問經〉考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輯“敦煌道教文獻專輯”,北京: 三聯出版社,1998年,第156—199頁。收入王承文: 《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 中華書局,2002年,第86—137頁。然而,按照“元始舊經”和陆修静(406—477)等人的解説,所有“元始舊經”都是在遠古劫運中的“上皇元年”出世的。而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對於以上數部“元始舊經”中爲何出現“葛玄”和“張道陵”等這些現世中的歷史人物,卻一直未能提出合理的解釋。
另一種觀點則以小林正美等爲代表,認爲敦煌本《靈寳經目》中靈寳經的分類,已經被陸修靜作過重大改動。主張應該重新將古靈寳經劃分爲“元始系”和“仙公系”兩種不同的經典。其主要依據體現爲兩方面,一是古靈寳經在最尊崇的經典和最尊崇的主神以及有無“三洞經書”等方面存在重大的差異;二是在以上數部經典中,出現了“葛玄”和“張道陵”等這樣一些晚近的歷史人物。小林正美認爲,由於“葛氏道派”所創作的“元始舊經”出世數量嚴重不足,因此,陸修靜在整理古靈寳經之時,将“天師道三洞派”所創作的“仙公系”靈寳經(實即“新經”)抽出來,用來填補《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的空缺,並因此改變了《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原有的結構。*(日) 小林正美: 《劉宋におる靈寶經の形成》,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六二號,1982年6月。收入小林正美: 《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 創文社,1990年,第138—188頁;見小林正美著、李慶譯: 《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9—175頁;
小林正美實際上也最早提出了有關古靈寳經“時間邏輯”*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一文,則進一步而且也最明確地提出了古靈寳經在“教理上的出世時間”即“時間邏輯”問題。這一命題,强調應該按照古靈寳經“元始系”(即“元始舊經”)和“仙公系”(即“新經”)各自原有的“教理上的出世時間”來重新劃分。小林正美認爲“元始系是元始天尊在上皇元年的説教的經典”。*小林正美著、李慶譯: 《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36頁。而“元始系”之所以稱爲“舊經”的原因,“這是由於認爲他們在地上世界出現雖然遲,但在天上的紫微宫中從上皇之劫的古代開始就存在着之故。還有,仙公系《靈寳經》被稱爲‘新經’,是由於認爲仙公系《靈寳經》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小林正美著、李慶譯: 《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42頁。劉屹博士近年來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對於小林正美的上述核心論點作了比較詳細的闡述。*劉屹: 《“元始舊經”與“仙公新經”的先後問題——以“古靈寳經”中的“天尊”和“元始天尊”爲中心》,《敦煌學》27輯,臺北: 樂學書局,2008年;《“元始舊經”與“仙公新經”的先後問題——以“篇章所見”的古靈寳經爲中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古靈寳經出世論——以葛巢甫和陸修靜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0頁。最近,王皓月博士則根據幾部“元始舊經”中有“舊”和“今”的表述,進一步提出“元始舊經”中所稱的“舊”是指龍漢之劫,而其中的“今”則是指代開皇劫或者上皇之劫。至於“仙公系靈寳經(即“新經”)記録的是太極真人等對葛仙公的宣教等内容”,“其在教理上的成書時間就是在葛玄的時代,即三國吴”。*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第87頁。以上幾位學者都强調要以經典本身的“時間邏輯”來討論古靈寳經的分類及其教義思想。
受這種爭論的影響,學術界有研究者因爲以上“元始舊經”中出現了“葛玄”、“張道陵”等歷史人物,所以認爲陸修靜在敦煌本《靈寳經目》中所作的“元始舊經”和“新經”的劃分,並不是一種具有真正宗教意義的經典分類。也有研究者將“元始舊經”《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的内容一分爲二,認爲是“葛氏道派”和“天師道三洞派”各自創作了這部古靈寶經的相關部分。*小林正美著、李慶譯: 《六朝道教史研究》,第205—228頁。還有一部分研究者提出,《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等“元始舊經”中與“葛玄”和“張道陵”等有關的内容,都是後來道教中人仿效“仙公新經”而續寫添加而成的。*吕鵬志: 《靈寳六齋考》,《文史》2011年第3輯,第118頁;謝世維: 《傳授與融合——〈太極五真人頌〉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4期,2009年3月。可見,有關古靈寳經“元始舊經”和“新經”的“時間邏輯”問題,直接關係到對古靈寳經文本結構和教義思想以及創作者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研究。它既是近數十年來困擾中外學術界的難題和諸多分歧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我們今天討論敦煌本《靈寶經目》和古靈寳經分類所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的問題。
我們經過研究認爲,無論是“元始舊經”還是“新經”,其創作者其實都没有真正遵循特定的“教理上的出世時間”,即所謂“時間邏輯”。從“新經”出世的整體情況來看,並不真正存在“仙公系《靈寳經》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這樣一種特定的“出世”模式;而在“元始舊經”中,遠古劫運時期的宗教神話其實可以同“葛玄”和“張道陵”以及古靈寶經創作時代的人間事物融合在一起。雖然古靈寶經也試圖用大乘佛教的“本行”觀念來解釋這種現象,但是,我們認爲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無論是“元始舊經”還是“新經”,在本質上都是東晉末年劉宋初年“葛氏道派”所創作的經典。因此,如果我們今天用特定的“時間邏輯”對古靈寶經進行重新分類,或者進一步將他們歸結爲不同的道派,可能既不真正符合古靈寶經本身對“元始舊經”和“新經”兩種經典性質的界定,也不太符合自陸修靜以來道教對這兩種經典的説明。爲此,我們有必要將古靈寳經“時間邏輯”問題重新置於古靈寳經各種具體文本結構中,進行更加專門的考察和研究。
二、 古靈寳經“仙公新經”中的“時間邏輯”問題辨析
(一) 古靈寳經本身所見“仙公新经”之“出世”年代和地點辨析
古靈寳經有數部經典都記載了其“出世”的經過,並成爲後來道教各種相關記載最主要的依據。我們試對此作專門討論。
1. 敦煌本《靈寳經目》著録有“元始舊經”《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小林正美等認爲該經原本屬於“仙公新經”。該經在其《前序》和《洞玄步虚吟十首》、《太上智慧經讃八首》之後,又明確記載:
太上太極五真人,於會稽山(上)虞山授葛仙公洞玄靈寳經。*《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道藏》第34册,第627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經始終未出現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仙公新經”這一情節,反而記載了葛玄在天台山向其門徒鄭思遠等傳經。該經末尾稱:
太極左仙公葛真人,諱玄,字孝先,於天台山授弟子鄭思遠、沙門竺法蘭、釋道微、吴時先主孫權。後思遠於馬迹山中,授葛洪。洪乃葛仙公之從孫,號抱朴子,著内外書典。鄭君於時説仙師仙公告曰: 我所授上清三洞太真道經,吾去世之日,一通付名山洞臺,一通付弟子,一通付吾家門子弟,世世録傳。至人若但務吾經,馳騁世業,則不堪任録傳,可悉付名山五嶽,不可輕傳非其人也。有其人者,宜傳之,勿閉天道也。*《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道藏》第34册,第628頁。另見《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所引《太玄都玉京山經》,《道藏》第24册,第731頁。
該經所稱葛玄在天台山爲其弟子鄭思遠等傳授的“上清三洞太真道經”,應與其前面所説葛玄在會稽郡上虞山所接受的“洞玄靈寳經”即“元始舊經十部三十六卷”含義相同。因而,如果把《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當作“新經”,其内容顯然并不符合“仙公系《靈寳經》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這一結論。
2. 敦煌本《靈寳經目》著録有“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寳真一勸誡法輪妙經》。而小林正美等認爲該經原本屬於“新經”,或稱“仙公新經”。該經記載:
太極左仙公(即葛玄)於天台山靜齋拔罪,燒香懺謝,思真念道……齋未一年,遂致感通,上聖垂降,曲盻幽房,以元正之月庚寅日夜……天真並下。第一自稱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鬱羅翹,第二自稱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第三自稱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定光。三真並集……請《真一勸戒法輪妙經》。*《太上洞玄靈寳真一勸誡法輪妙經》,《道藏》第6册,第170—171頁。
以上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一是“三真人”在天台山爲葛玄傳經的時間,僅僅提及是在“元正之月庚寅日也”,卻没有提及具體的年份。所谓“元正之月”,是指正月元日,即元旦。《尚書·舜典》稱“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藝文類聚》卷七十引漢崔瑗《三子釵銘》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二是“三真人”所傳授的,始終只提及作爲古靈寳經之一的《真一勸戒法輪妙經》,在該經中又稱爲《太上真一勸誡法輪妙經》、《太上靈寳洞玄真一勸誡法輪妙經》,卻完全不涉及任何其他的古靈寳經傳授。如此也就意味着《真一勸戒法輪妙經》並不包括在天神給葛玄某次大規模所傳經典系列中。三是作爲“五真人”之首並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太極真人——徐來勒,並未出現在此次天台山傳經的現場。該經甚至還借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鬱羅翹説:“太上命太極真人徐來勒,保汝爲三洞大法師。今復命我來爲子作第一度師。”
然而,南朝陶弘景(456—536)所撰《洞玄靈寳真靈位業圖》卻稱:“太極法師徐來勒,吴時天台山傳葛仙公《法輪經》”;緊接着又稱“太上玄一三真,吴時降天台山,傳葛仙公《靈寳經》”。*(梁) 陶弘景《洞玄靈寳真靈位業圖》,《道藏》第3册,第276頁。也就是説,陶弘景有關太極法師徐來勒“吴時天台山傳葛仙公《法輪經》”的記載,其實與古靈寳經的原文並不完全相符。因此,從以上討論來看,該經文本及相關内容,其實也難以真正符合“仙公系《靈寳經》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這一結論。
3. 敦煌本《靈寳經目》著録有“新經”《仙人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經》。《道藏》本作《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因緣經》。該經開篇即稱:
吴赤烏三年,歲在庚申,正月一日壬子,仙公登勞盛山,靜齋念道。是日中時,有地仙道士三十三人,詣座燒香,禮經旋行。*《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因縁經》,《道藏》第24册,第671頁;敦煌本P.2454號《仙人請問本行因縁衆聖難經》同。
以上記載有幾點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該經明確記載時間是孫吴赤烏三年(240)正月一日,而地點卻是在勞盛山,并非天台山。古代勞盛山是指今天山東省青島市著名道教名山——嶗山。古代嶗山曾有勞山、牢山、勞盛山、不其山、大勞山和小勞山、輔唐山、鼇山等多種名稱。*(明) 顧炎武《日知録》卷三一《勞山》條稱:“《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欒保群、吕宗力校點: 《日知録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96頁)。在早期道書中,勞盛山又大多與道教傳經特别是靈寳經有關;*葛洪《神仙傳》卷二記載,樂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因到霍林山,遇仙人,授以服巨勝赤松散方”,“乃入海登勞盛山而仙去也”。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卷下記載“勞盛山上刻石作文。仙人樂子長作,吴王夫差寫取”(《道藏》第6册,第337頁);而《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開篇即稱“此乃太上寶之於紫微臺,衆真藏之於名山洞室,一曰祕於勞山之陰。”(《道藏》第11册,第632頁)《雲笈七籤》卷六引《四極盟科》云:“洞玄經萬劫一出,今封一通於勞盛山。”又引《太玄都四極盟科》曰: 洞玄經萬劫一出,今封一通於太山,一通於勞盛山。”(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 《雲笈七籤》卷六,第89頁、第93頁。)二是該經全經均爲葛玄自己對衆多“地仙道士”説法,卻自始至終都没有出現太極真人徐來勒等神真及其對葛玄説法傳經等内容。顯然,無論是該經的“時間邏輯”和傳授地點,還是其相關内容,都是與“仙公系《靈寳經》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這一結論相矛盾的。也不符合王皓月博士所作的“仙公系靈寳經記録的是太極真人等對葛仙公的宣教等内容”這一判定。
4. 敦煌本《靈寳經目》著録“新經”《太上太極太虚上真人演太上靈寳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上卷》。該經《正統道藏》失收。敦煌文書P.2356、P.2403、P.2452號爲其鈔本。該經也出現了在古靈寳經傳授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太上太極五真人”及“五真人頌”。敦煌文書P.2452號稱:
太極真人稱徐來勒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時,於會稽上虞山傳經給葛玄,字孝先。玄於天台山傳弟子鄭思遠、沙門竺法蘭、釋道微、吴先主孫權。思遠後於馬迹山傳葛洪,仙公之從孫也,號曰抱朴子,著内外書典。鄭君於是説先師仙公告曰: 我日所受上清三洞太真道經,吾去世之日,一通副名山洞台,一通傳弟子,一通付吾家門子弟,世世録傳。至人門宗子弟,並務五經,馳騁世業,志在流俗,無堪任録傳者,吾當以一通封付名山五嶽,及傳子弟而已。吾去世後,家門子孫若有好道,思存仙度者,子可以吾今上清道業衆經傳之,當緣子度道,明識吾言。抱朴子君建元六(二)年三月三日,於羅浮山付(葛)世,世傳好之子弟。
以上内容十分重要。首先,該經明確將太極真人徐來勒爲葛玄傳經的時間,記載爲“己卯年正月一日”,此應該是指東漢獻帝建安四年(199)。*古靈寳經所記載葛玄受經的“己卯年”,一部分研究者認爲是指三國孫吴時期,應誤。這裏的“己卯年”應是指漢獻帝建安四年(199)。因爲孫吴時期的“己卯年”是吴景帝永安二年(259)。而葛玄生於公元164年,卒於公元244年。然而其傳經的地點卻是在會稽郡上虞山。由此也可以推定,前引《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所稱“太上太極五真人,於會稽上虞山授葛仙公洞玄靈寳經”,其比較確切的時間也應該是在漢獻帝建安四年。
其次,該經通篇内容均與《靈寳赤書五篇真文》有關。該經将其表述爲《太上洞玄靈寳天書》、《靈寳真文》、《靈寳文》、《靈寳經》、《靈寳自然經》、《太上靈寳至真五篇太真道上經》等等。*王承文《敦煌本〈靈寳經目〉與古靈寳經的分類及内在關係考釋——以〈靈寳赤書五篇真文〉與〈道德經〉的關係爲中心》,《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3期。但是在敍述靈寳經在“葛氏道”内部的傳承時,卻又將其所傳承的經書稱作“上清三洞太真道經”。因此,這裏的“上清三洞太真道經”與《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一樣,我們認爲都是指由《靈寳赤書五篇真文》演繹出來的“元始舊經十部妙經三十六卷”。
最後,該經稱葛玄在天台山將靈寳經傳授給弟子鄭思遠等,鄭思遠又於馬迹山傳葛洪。然後又記載葛洪於東晉建元六(二)年(344)三月三日,於羅浮山傳葛世等。也就是説,該經也不符合“仙公系《靈寳經》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這一結論。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認爲古靈寳經明確記載“元始舊經”是在東漢獻帝建安四年(199)通過太極真人徐來勒等“五真人”在會稽上虞山傳授給了葛玄。而古靈寳經本身其實並未申明所有“仙公新經”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
(二) 從“仙公新經”的相關内容看其“出世”的“時間邏輯”問題
以上所列舉的均屬於古靈寳經中葛玄“受經”和“傳經”的記載。此外,在所謂“仙公新經”中也大量出現了葛玄身後的歷史人物和相關内容,從而證明古靈寶經並没有將“仙公新經”其“在教理上的成書時間”都確定在三國孫吴“葛玄的時代”。*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第87頁。
1. 《太上洞玄靈寳五符序》。該經不僅是最早出世的“新經”,同時也是在所有古靈寳經中最早出世的經典。*王承文: 《論古靈寶經“天文”和“神符”的淵源——以〈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的釋讀爲中心》,載《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敦煌本《靈寳經目》著録“《太上洞玄靈寳天文五符序經》一卷”,然而接着又稱“仙公在世時所得本,是分爲二卷,今人或作三卷”,是説早在葛玄的時代,該經即有一卷本存在。而在陸修靜之前,該經已有一種二卷本存在。在陸修靜之時,這部經又被分成了三卷。20世紀初,劉師培撰《讀道藏記》,稱這部經“系六朝以前古籍”,*劉師培: 《讀道藏記》,《國粹學報》1911年。載《劉申叔先生遺書》第69册,寕武南氏鉛印本,1934年。即将其出世時間確定在东漢时期。施舟人則將其確定在三國時期。*施舟人: 《〈老子中經〉初探》,載施舟人《中國文化基因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08頁。然而,該經卷中“靈寳黄精方”卻稱:
弟子葛洪曾聞之於鄭君,言識其始,云: 子服戊己壽不已,子服長生之精,與天相傾。*《太上洞玄靈寳五符序》卷中,《道藏》第6册,第330頁。
以上内容證明,該經最後形成的時間不應該早於葛洪(283—344)在世的時代。葛玄去世在公元244年,而作爲其從孫的葛洪出生在公元283年。也就是説,在這部名義上爲孫吴時期葛玄在天台山所稟受的經典中,卻出現了在葛玄去世數十年之後才出生的葛洪以及他的老師鄭思遠的名字。如果我們强調要從“教理上的成書時間”即所謂“時間邏輯”來理解這部“新經”,顯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2. 《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如前所述,該經原爲“元始舊經”,小林正美等學者將其認定爲“仙公新經”。然而該經卻稱:
太極真人之辭,衆仙常所耽誦,不宣於下俗之人,祕蔵金闕玉房之内也。仙公曰: 宜傳至人脩靈寳齋者也,不可示浮華之徒,慎之哉,慎之哉。玄師太元真人臨授許常侍、掾《太洞玄經玉京山訣》,作頌三首,同夕,右英夫人亦吟誦之。*《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道藏》第34册,第627頁。
該經徵引的三首頌詩亦見於陶弘景《真誥》中。*陶弘景: 《真誥》卷四,《道藏》第20册,第512頁,《真誥》卷三,第507頁,《真誥》卷四,第512頁。參見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Vol. 2. Brussel., pp.434-486,1983. 王承文: 《敦煌古靈寳經與晉唐道教》,北京: 中華書局,2002年,第217—219頁。所謂“玄師太元真人”,即古上清經傳説中的漢代著名方士茅盈;至於“許常侍、掾”,則指東晉上清派的實際創始人許謐、許翽父子。許謐(305—376),一名許穆,許邁第五弟。少侍郡主簿功曹吏,官至散騎常侍。許掾(341—370)是指許翽,字道翔,小名玉斧。爲許穆之子。郡舉上計掾、主簿。許謐和許翽父子的道教活動時間要晚於葛玄去世一百多年。顯然,這不僅不符合“元始舊經”都是在“上皇劫”出世的“時間邏輯”,也不符合“新經”出世的“時間邏輯”。因爲,如果“仙公新經”是指“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的話,就不應該出現葛玄去世一百多年之後才有的内容。
3. 《太極真人敷靈寳齋戒威儀諸經要訣》。該經作爲最具有代表性的“新經”之一,其中也大量而直接地出現了葛玄去世之後的内容。其文稱:
南嶽先生鄭君曰: 吾先師仙公常祕此書,非至真不傳也,萬金不足珍矣。仙人相授於口,今故書之。仙公言: 書一通封還名山,一通傳弟子,一通付家門子孫,世世録傳,知道者也。與靈寳本經俱授之,道家要妙也。
抱朴子曰: 洪意謂大齋日數多者,或是貴人,或是道士,體素羸弱不堪,日夕六時禮拜。愚欲晝三時燒香禮拜,夜可闕也。爲當講法義而已,能六時燒香者,自當全法爾。恐人未得道,氣力極弱,但欲一日一夜齋此,可六時行道也。學者其善詳用焉。*《太極真人敷靈寳齋戒威儀諸經要訣》,《道藏》第9册,第874頁。
以上“南嶽先生鄭君”即葛玄的弟子鄭思遠。鄭思遠所稱“吾先師仙公”,明顯是對已經故去的葛玄的尊稱。“抱朴子”則是指作爲葛玄從孫的葛洪。其“吾先師仙公常祕此書”,所謂“此書”,應該是指《太極真人敷靈寳齋戒威儀諸經要訣》這部“新經”本身;而所謂“與靈寳本經俱授之”,其“靈寳本經”應該是指《靈寳赤書五篇真文》,或由此演繹出來的“元始舊經十部三十六卷”。*關於這部“新經”與《靈寳赤書五篇真文》的關係,參見王承文《敦煌本〈靈寳經目〉與古靈寳經的分類及内在關係考釋——以〈靈寳赤書五篇真文〉與〈道德經〉的關係爲中心》,《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3期。如果從古靈寳經“新經”在“教理上的出世時間”來看,孫吴赤烏年間徐來勒等在天台山爲葛玄傳授的“新經”中,顯然不應該出現這些遠在葛玄身後的内容。
4. 《太上太極太虚上真人演太上靈寳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上卷》。小林正美認爲是最有代表性的“仙公系”靈寳經(即“新經”)之一。前引敦煌文書P.2452號敍述太極真人徐來勒於漢獻帝建安四年(199)在會稽上虞山傳經給葛玄(164—244)。*古靈寳經所記載葛玄受經的“己卯年”,部分論著認爲是三國孫吴時期,應誤。應是指漢獻帝建安四年(199)。因爲孫吴時期的“己卯年”是吴景帝永安二年(259)。而葛玄生於公元164年,卒於公元244年。其後,葛玄在天台山傳弟子鄭思遠等,鄭思遠於馬迹山傳葛洪。然後又記載葛洪於東晉建元六(二)年(344)三月三日,於羅浮山傳葛世等。没有證據表明這些遠在葛玄身後的内容是後來者添加進來。
可見,“仙公新經”的作者並没有把這些經典都界定爲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而這些經典的創作本身也没有形定一個特定的“教理上的出世時間”或“時間邏輯”。
(三) 古靈寳經之後道教對“新經”出世的説明
陸修靜是最早整理古靈寳經的道教宗師,其著作曾經多次提到了與葛玄有關的靈寳經的出世和傳承。小林正美有關“仙公新經”出世“時間邏輯”的觀點,就是從陸修靜的相關著作中概括和總結出來的。*小林正美著、李慶譯: 《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36頁。然而,陸修靜相關論述的具體内涵仍值得仔細斟酌。我們對此試逐一辨析。
1. 陸修靜《靈寳經目序》稱:“雖高辛招雲輿之校,大禹獲鍾山之書,老君降真於天師,仙公授文於天台,斯皆由勳感太上,指成聖業。”*(宋) 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 《雲笈七籤》卷四,第52頁。其所稱“仙公授文於天台”,劉屹博士認爲“是指葛仙公在天台山領受太極真人所傳的靈寶經”。*劉屹: 《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第157頁。不過,從前面“老君降真於天师”的表達來看,“老君”和“仙公”均是行爲的主體,因此,其“仙公授文於天台”之“授文”的表達,應該是指其“傳授”而不是指其“領受”,即其實是指葛玄在天台山向其弟子鄭思遠等傳授靈寳經。而且“傳授”也更符合前引多部古靈寶經本身的説明。
2. 陸修靜《靈寳經目序》又稱:“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其所謂“今條《舊目》已出”,是指《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録的“元始舊經”;而其稱“並仙公所授事”則是指由葛玄所親自傳授的“新經”。陸修靜明顯是把所有“新經”,都看成是由仙公葛玄所親自傳授的靈寳經。也就是説,陸修靜在此並没有强調所有“新經”都是徐來勒等所傳授之經。
3. 在敦煌本《靈寳經目》中,陸修靜將所有“新經”概括爲:“右十一卷,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説行業新經。”其中“所受教戒訣要”,應包括了徐來勒等神真所傳授的經典。而“説行業新經”,則應該也包括了葛玄自己在勞盛山對其地仙道士的説法所形成的“新經”——《仙人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經》等。
4. 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表》稱:“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陸修靜: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表》,《道藏》第9册,第839頁。其中“並仙公所稟”即指“新經”。所謂“稟”代表承受。意即“新經”是葛玄所承受的經典。然而,陸修靜在此卻既未强調真人徐來勒的傳授,也没有説明具體的時間和地點。
5. 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又稱:
次師告丹水文: 某嶽先生大洞法師臣某甲,告弟子某甲等: 元始天尊於眇莽之中,敷演《真文》,結成妙經。劫劫濟度,無有窮已,如塵沙巨億無絶。靈文隱奧,祕於金閣,衆真宗奉,諸天所仰。逮於赤烏,降授仙公,靈寳妙經,於是出世度人。*《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道藏》第9册,第852頁。
所謂“元始天尊於眇莽之中,敷演《真文》,結成妙經”,顯然是指由《靈寳赤書五篇真文》向“元始舊經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的演化;而“靈文隱奧,秘於金閣”,則是指“元始舊經”被珍藏在太玄都玉京山玄都紫微宫中。至於其所稱“逮於赤烏,降授仙公,靈寳妙經,於是出世度人”,這裏的“靈寳妙經”,從邏輯上來説應該是指“元始舊經”。也就是説,在吴主孫權赤烏(238—250)年間,太極真人徐來勒等在天台山向葛玄傳授的其實只是“元始舊經”,並未涉及“新經”的傳授。因此,陸修靜有關“元始舊經”傳授的説法,與《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等古靈寳經本身的説法其實有較大的差距。
根據以上討論,陸修靜其實也没有將“仙公新經”都界定爲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在陸修靜之後,還有多種資料都涉及靈寳經的傳授。
1. 唐代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所引《太玄都四極盟科》曰:
太極真人、夏禹通聖達真,太上命鈔出《靈寳自然》,分别大小劫品經……徐來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時,於會稽上虞山傳仙公葛玄。玄字孝先,於天台山傳鄭思遠、吴主孫權等。仙公升天,合(令)以所得三洞真經,一通傳弟子,一通蔵名山,一通付家門子孫。*《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引,《道藏》第24册,第813頁。
其中“《靈寳自然》”,应该是指“新經”《太上太極太虚上真人演太上靈寳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而其所稱“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時,於會稽上虞山傳仙公葛玄。玄子孝先,於天台山傳鄭思遠、吴主孫權等”,也與前引這部“新經”内容相同。而這條資料也不涉及“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這一結論。
2. 《雲笈七籤》卷六所引《太玄都四極盟科》亦云:“徐來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時,於會稽上虞山傳仙公葛玄。玄字孝先,後於天台山傳鄭思遠、竺法蘭、釋道微。道微傳吴主孫權等。仙公升化,令以所得三洞真經,一通傳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門子孫,與從弟少傅奚,奚子護軍悌,悌子洪。洪又於馬迹山詣思遠盟而授之。”*(宋) 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 《雲笈七籤》卷六,第94頁。以上内容實際上也不涉及“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
3. 唐末閭丘方遠《太上洞玄靈寳大綱鈔》稱“天尊於龍漢劫初,從碧落天降大浮黎國,在大地東方説法,演《靈寳自然天書五篇真文》”,“至吴太極左仙公,年十三,於會稽山陽石巖下精思,年十八感通。後於天台山精思,太極三真及太極法師徐來勒,重授靈寳諸法,仙公因合成七部科戒威儀齋法。仙公以吴赤烏二年八月十五日,於天台山白日升天”。*閭丘方遠: 《太上洞玄靈寳大綱鈔》,《道藏》第6册,第376頁。以上這條資料有多處值得斟酌。一是葛玄生於公元164年,其在會稽山“精思”並“感通”神真,古靈寳經説是在“己卯年正月一日”,即東漢獻帝建安四年(199),此時葛玄年齡應爲35歲,而非18歲;二是該書將太極三真和徐來勒在天台山的傳經,説成是“重授靈寳諸法”。根據我們對古靈寳經教義思想的理解,閭丘方遠的真實含義是説葛玄在此生此世之前其實就已被傳授過靈寳諸法。對此,我們將在後面作進一步討論;三是其稱葛玄在吴赤烏二年八月十五日,於天台山白日升天,也與前引《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因緣經》開篇所稱葛玄於吴赤烏三年正月一日壬子在勞盛山的説法相矛盾。陶弘景撰《吴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稱“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長往不返”。*陶弘景: 《吴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陶隱居集》卷下;陳垣: 《道家金石略》,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2頁。元代《歴世真仙體道通鑒》和譚嗣先《太極葛仙公傳》等也均記載赤烏七年升仙。*趙道一: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二三《葛仙公》,《道藏》第5册,第229頁;譚嗣先: 《太極葛仙公傳》,《道藏》第6册,第847頁。
4. 《雲笈七籤》卷三《靈寳略紀》記載靈寳經的傳承與其他資料多有不同。其文曰:
至三國時,吴主孫權赤烏之年,有琅瑘葛玄,字孝先。孝先乃葛尚書之子,尚書名孝儒,年八十乃誕玄。玄多靈應,年十三,好慕道德,純粹忠信。舉孝廉不就。棄榮辭禄,志尚山水。入天台山學道。精思遐徹,未周一年,感通太上,遣三聖真人下降,以《靈寳經》授之。其第一真人自稱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鬱羅翹,其第二真人自稱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其第三真人自稱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定光。三真未降之前,太上又命太極真人徐來勒爲孝先作三洞法師。孝先凡所受經二十三卷,並語稟請問十卷,合三十三卷。孝先傳鄭思遠,又傳兄太子少傅海安君字孝爰,孝爰付子護軍悌,悌即抱朴子之父。抱朴從鄭君盟,鄭君授。*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 《雲笈七籤》卷三,第40—41頁。
以上所謂“凡所受經二十三卷,并語稟請問十卷,合三十三卷”,其“受經二十三卷”是指“元始舊經”;而“並語稟請問十卷”就是指“新經”。以上資料將“太上三真人”在吴赤烏年間在天台山爲葛玄傳授的是所有“元始舊經”和“新經”。
5. 南宋謝守灝所編《混元聖紀》記載,汉靈帝光和二年(179)己未正月朔旦,“老君敕太極真人三洞法師徐來勒等同降於天台山,老君乘八景玉輿,從官千萬,正一真人侍焉。老君自號太上玄一真人,真定光爲洞經高玄法師,命侍仙玉郎王思真披九光玉韞,出《洞玄大洞靈寳經》凡三十六部,以授仙人葛玄,及上清齋法二等”。*謝守灝編: 《混元聖紀》卷七,《道藏》第17册,第848頁。從南宋開始,太上老君已進入靈寳經的傳授過程。
6. 元代趙道一所編《歷世真僊體道通鑑》記載,“仙公本大羅真人下降,以後漢桓帝延禧(熹)七年(164)甲辰歲四月八日誕世”,“靈帝光和二年(179)正月朔,感太上老君勑太極真人徐來勒等同降於天台山,老君乘八景玉輿,從官千萬,正一真人侍焉。老君自號太上玄一真人、真定光爲洞經高玄法師,命侍經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韞,出《洞玄大洞靈寳經》,凡三十六部,以授仙人葛玄,及上清齋法二等,并三録七品齋法”。*趙道一: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二三《葛仙公》,《道藏》第5册,第229頁。
7. 元代譚嗣先《太極葛仙公傳》記載“仙公生於漢延熹七年(164)甲辰四月八日”,“漢光和二年(179)正月朔,仙公於天台上虞山感太上遣玄一三真人太極徐真人授以三洞四輔經録,修行秘訣,金書玉誥符圖”。*譚嗣先: 《太極葛仙公傳》,《道藏》第6册,第846—847頁;劉師培: 《讀道藏記》稱“此書出自元代”。該書將徐來勒爲葛玄傳經確定在東漢光和二年(179)正月,地點卻變成了天台上虞山,而其所傳則爲“三洞四輔經録”等。顯然,這些較晚期的資料也增加了一些古靈寳經原始記載中所没有的内容。
(四) 小結
長期以來,我們似乎已經比較習慣於用“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這樣一種特定的模式,來理解“仙公新經”出世及其“時間邏輯”。然而,以上討論卻能證明,古靈寳經本身包括陸修靜以及後來的道教學者,對於葛玄從天界神真那裏接受“仙公新經”的時間和地點等等,其實並没有一個統一的或固定的説法。古靈寳經的創作者也没有特别强調其“新經”本身的“時間邏輯”。因此,如果我們今天特地要確定其“時間邏輯”,並以此來對敦煌本《靈寳經目》所著録的古靈寳經進行重新分類,可能反而並不真正符合古靈寳經的實際情況。
三、 古靈寳經“元始舊經”之“時間邏輯”問題辨析
小林正美等學者都非常强調“元始舊經”是元始天尊在“上皇元年”所説教的經典,並把這一特定的“時間邏輯”作爲重新劃分敦煌本《靈寳經目》所著録古靈寳經最重要的依據之一。最近,王皓月博士所發表的《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一文,則進一步提出要對“教理上的元始舊經”和“實際存在的元始系《靈寳經》”加以區分。他認爲“教理上的元始舊經”早在最初的“龍漢劫”就已出世,而“實際存在的元始系《靈寳經》”則是在“開皇劫”或“上皇劫”才出世;現存“元始舊經”中所出現的“舊”,都是特指最早的“龍漢”之劫,而其中的“今”,則是特别“指代開皇劫或者上皇之劫”。*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第87頁。他强調,“如果認爲元始系《靈寳經》本身就是元始舊經,那經典之中的時間邏輯顯然是不成立的”。*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第88頁。他又以此爲基礎,對古靈寳經的文本結構和形成過程等諸多重要問題都作了具有顛覆性的研究。不過,我們認爲其核心論點和研究方法都還可以作進一步討論。
從“元始舊經”的整體情況來看,我們認爲“元始舊經”中所有“舊”與“今”的表達,並不必然代表“龍漢劫”同“開皇劫”或“上皇劫”的區别。王皓月從十多部“元始舊經”中發現有“今”的表述總共有兩處。一處是《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該經卷上稱:“五帝真符以元始同生,舊文今祕於玄都紫微宫。”*《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卷上,《道藏》第1册,第787頁。他認爲這裏的“今”,“是發生在‘今三天戾運,六天道行’的上皇之劫”*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第88頁。。另一處是《太上洞玄靈寳滅度五鍊生尸經》,該經稱:
今當更爲上智童子開諸法門,申明龍漢舊典九幽玉匱女青玉文,拔度幽牢地獄,積夜寒鄉,三塗五苦,餓鬼死魂,令悉見光明。
王皓月博士認爲該經中的“今”就是指“開皇劫”,並與“龍漢劫”時期的“龍漢舊典”相對應。而以上兩條資料也是其判定“元始舊經”和“元始系《靈寳經》”原本屬於兩種不同版本最主要的依據。
然而,國内外研究者都一致認爲,《正統道臧》所收《太上洞玄靈寳滅度五鍊生尸經》其實並不是一部完整的經典。敦煌文書P.2865號、S.0298號爲該經抄本。*Ofuchi Ninji,“On Ku Ling-Pao Ching”, Acta Asiatica 27(1974). 譯文見劉波譯、王承文校: 《論古靈寳經》,載陳鼓應主編: 《道家文化研究》第13輯“敦煌道教文獻專輯”,北京: 三聯書店出版社,1998年;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230. 王卡: 《敦煌道教文獻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02頁。而敦煌文書P.2865號稱:
天真皇人曰: 此諸君皆積學滅度,道業垂成,而得受此文,以還生人中。皆超虚步空,上升金闕,受號自然也。其並悠遠世人所不能明。考其近者,衍門子師夜光,高丘子師石公,洪崖先生師金母,並受靈寳滅度五練之法,升天之傳。衍門子死於漁陽洛縣長丘山,高丘子死於中山聞喜縣高附山,洪崖先生死于武威姑臧縣浪山中,並受此文以鎮其墓。衍門子卌年墓崩而形化,後入蒙山大洞黄金之庭,受書爲仙卿。高丘子七十二年墓〔崩〕,爲人所發,捬棺而形飛,今爲中嶽真人。洪崖先生百廿年墓開,尸形飛騰,受書爲青城真人。此之諸賢,並受滅度之法,升天之傳,鎮靈之道,而得崇虚陵清,策空高霞,游晏紫微,受號真人也。此之近事,非復悠遠之傳。元始天王今披元始之寶藏,以告太極上仙,遇之者將前生萬劫,録名上清,應得仙道者也。諸天男女可不承女青之旨,秘而寶之焉。*《正統道藏》正一部所收《靈寳錬度五仙安靈鎮神黄繒章法》與此相同,《道藏》第32册,第734頁。
以上引文對於我們探明“元始舊經”在“教理上的出世時間”並真正理解其内在的“時間邏輯”,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義。
首先,該經借“天真皇人”稱“此諸君皆積學滅度,道業垂成,而得受此文,以還生人中”,是説“五老帝君”(又稱“元始五老”)等神靈生死輪轉的經歷,其實都與《靈寳赤書五篇真文》具有不可分割的因緣關係。而其相關事迹,除見於《太上洞玄靈寳滅度五鍊生尸經》之外,更詳盡的記載見“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寳真文度人本行妙經》中。*王承文: 《古靈寳經“五老帝君”與中古道教經教學説的建構》,載《2006年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昶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9月,第233—260頁。而以上引文又稱“元始天王今披元始之寶藏,以告太極上仙”。衆所周知,“天真皇人”和“元始天王”都是“元始舊經”重新創造的遠古劫運時期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神靈,而且都出現在最早的“龍漢劫”時期。*王承文: 《敦煌古靈寳經與晉唐道教》,第691—739頁;關於“天真皇人”與“龍漢劫”的關係,《太上靈寳諸天内音自然玉字》卷四稱:“天真皇人告五老帝君: 我嘗於龍漢之中,受文於無名常存之君(即元始天尊)。”(《道藏》第2册,第563頁)。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該經卻又借天真皇人稱“五老帝君”事迹“其並悠遠世人所不能明。考其近者,衍門子師夜光,高丘子師石公,洪崖先生師金母,並受靈寳滅度五練之法,升天之傳”等。這部“元始舊經”所列舉的這些人物,卻都是現實世界的歷史人物。至於漁陽洛縣、中山聞喜縣、武威姑臧縣等,也是古靈寳經創作時代的人間地名。而且這些内容也都是直接在《抱朴子内篇》、《真誥》等前代道書的基礎上形成的。*關於高丘子、石公、洪崖先生等人物事迹,《抱朴子内篇·極言》記載彭祖之弟子中有“高丘子”等,“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葛洪撰,王明校釋: 《抱朴子内篇校釋》卷十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242頁);《真誥》卷五《甄命授》記載:“昔高丘子,殷人也,亦好道,入六景山,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黄素道經,服餌术,後合鴻丹以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升太清也,今爲中嶽真人。”(《道藏》第20册,第518頁)《真誥》卷一四《稽神樞第四》稱:“吞琅玕之華而方營丘墓者,衍門子、高丘子、洪涯先生是也。衍門子墓在漁陽潞縣,幽州漁陽有潞縣,今〔上〕黨亦有潞縣。衍門即羨門也。高丘子墓在中山聞喜縣,中山有安喜縣,聞喜乃屬河東。洪涯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涼州記》作姑臧縣。此三郡縣人,並云上古死人之空塚矣。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末,又受服琅玕華於中山,方復託死,乃入玄州,受書爲中嶽真人,於今在也。衍門子今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洪涯先生今爲青城真人”(《道藏》第20册,第577頁)。早期上清派將“高丘子”等看成是道教“尸解”的典型。《无上祕要》卷八七《尸解品》引《洞真藏景録形神經》稱:“飛琅玕之華而方營丘墓者,高丘子、衍門子、洪崖先生是也。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水,又受飛琅玕之華於中山,方復託死乃入玄洲,受書爲中嶽真人。衍門子今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洪崖先生今爲青城真人。”(《道藏》第25册,第245頁)在這部古靈寳經中,這些修煉者事迹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强調他們都是通過修煉靈寳經的“靈寳滅度五鍊之法”,而非“金丹”等其他的途徑,才實現了“尸解”升仙。而所谓“元始天王今披元始之寶藏”,即指元始天王將元始天尊所創造的“五鍊生尸”之教法披露於人間。
我們要特别指出的是,該經作者在此清楚地説明了這部“元始舊經”的敍述爲什麽要從遠古劫運時期突然轉入現世人間的原因。作者非常明確地説,是因爲“五老帝君”等神靈事迹“其並悠遠世人所不能明”,意即“五老帝君”等神靈事迹太過悠久和遥遠,很可能讓世人難以明白和信服,因此,需要特地列舉現實人間奉道者事迹來加以證明。然後又稱“此之近事,非復悠遠之傳”。而這些内容,我們認爲恰恰極好地證明了“元始舊經”作爲“人間宗教”的本質和基本特徵。
其次,該經以上有關時間的表述,先後出現了“考其近者”、“此之近事,非復悠遠之傳”、“今爲中嶽真人”、“元始天王今披元始之寶藏”等等。以上材料一方面證明了這部“元始舊經”的作者,並没有將“今”與“舊”的對應,都看成是“龍漢劫”同“開皇劫”或“上皇劫”的區别;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元始舊經”中,億萬年前遠古劫運時期的神真事迹與現實人間靈寳經的修煉經歷,竟然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説,“元始舊經”並没有特地按照“龍漢”、“開皇”這樣一種所謂“經典之中的時間邏輯”來敍述。而“元始舊經”也没有刻意要把遠古劫運時期的宗教神話與人間現實世界完全隔離開來。
與此類似的情況亦見於其他“元始舊經”中。敦煌本《靈寳經目》著録“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寳真文度人本行妙經》,已散佚。敦煌文書P.3022v以及《无上秘要》等道教類書保留了該經大部分内容。*王承文: 《靈寶“天文”信仰と古靈寶經教義の展開——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を中心に—》,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京都: 臨川書店,2007年2月,第293—336頁。該經在前面分别敍述了太上大道君和五老帝君等神靈在遠古劫運時期的本行事迹,而《无上祕要》卷四七《齋戒品》所引《洞玄本行妙經》亦爲該經長篇佚文。其文云:
道言: 昔有道士,持齋誦經。有一凡人爲賃,作治除(厨)*唐代《齋戒籙》作“厨”,《道藏》第6册,第1007頁。齋堂。道士見其用意,至日中持齋,因喚與同食。食竟,爲其説法,語此賃人: 今隨吾持齋,功德甚大,可至明日中時復食,勿壞爾齋,徒勞無益,能如此者,將可得免見世窮厄。此人稽首,受戒而去。暮還家,其婦一日待壻還食,壻具以道士戒言喻婦。其婦不解,遂致嗔怒。賃人不能免其婦意,遂壞其齋,與婦共食。其後命過,天使其主蜀山千歲樹精,恒給其中食,其樹茂盛。暑夏之月,有精進賢者三人經過,依樹而息。賢者歎曰: 此樹雖涼,日已向中,何由得食?此人於樹空中曰: 當爲賢者供設中食,無所爲憂。須臾,食至,賢者共食。食竟言曰: 我今覓道,〔道〕在何許?即此自然,豈非道也。因問樹曰: 不審大神,可得暫降形見與不?此人於樹空中答曰: 我非能使人得道者也,具説姓字處所,昔常爲道士,勸使持齋,爲婦人所壞,功德不全,致令使我守此樹精,不能得出。天以我昔經齋中食,今每至中,給我齋食,口腹之饒,無緣得遷,欲屈賢者,爲至我舍,道我如此,能爲我建三日齋戒,我身便升。賢者感此人意,爲尋其家,具以其言語家人如此。家人即爲建齋,請諸道士,燒香誦經,三日謝過。此人即得飛行,升入雲中,於景霄之上,受書爲遊散仙人……*《无上祕要》卷四七《齋戒品》引,《道藏》第25册,第167頁;按唐代《齋戒籙》之“持齋”條引《无上祕要》與此相同,《道藏》第6册,第1007頁。《雲笈七籤》卷三七《持齋》所引相同,北京: 中華書局,2003年,第820—822頁。
以上“道士”勸誡“凡人”持齋受戒的故事,顯然發生在現實人間。其稱“天以我昔經齋中食,今每至中,給我齋食”,其中的“今”,顯然也不特指“開皇劫”或“上皇劫”。而所謂“精進賢者三人”當屬於人間修道之士。尤其是其中所稱“天使其主蜀山千歲樹精”,這裏的“蜀山”,亦爲人間世界的巴蜀名山,指今四川北部綿延於川、甘邊境的岷山。曹魏時期張揖所撰《廣雅》卷九《釋山》稱“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蜀山謂之崏山”。“崏山”与“岷山”相同。而岷山與中國古史神話傳説關係密切。《水經注》所引漢代緯書《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又稱:“故《書》曰: 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北魏)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 《水經注校證》卷三三,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766頁。西晉左思《蜀都賦》亦稱“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而《洞玄本行妙經》所稱“天使其主蜀山千歲樹精”,也與古代蜀山丰富的神怪傳説有關。《山海經》稱“岷山,江水出焉”。又稱岷山“其上多金玉”,“其獸多犀象,多夔牛,其鳥多翰鷩”。而郭璞(276—324)則注稱:“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曰夔牛。”*袁珂校注: 《山海經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6頁。西晉張華《博物志》稱:“蜀山南髙山上,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玃。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晉) 張華撰、范寜校證: 《博物志校證》卷三,北京: 中華書局,1980年,第36頁。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劍南道茂州通化縣,“蜀山在縣東北六里”。*(唐)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二《劍南道茂州通化縣》,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第813頁。因而,這部“元始舊經”雖然在前面用主要篇幅塑造了劫運時期太上大道君、五老帝君等各種神靈本行事迹,但是其内容卻也包括了現實人間的齋戒修道事務。
“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寳金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也證明了這一點。陸修靜所撰《洞玄靈寳説光燭戒罰燈祝願儀》稱:
《經》言: 夫齋法之大者,莫先太上靈寳齋。靈寳之文是天地之元根,神明之户牖,衆經之祖宗,無量大法橋也……太上所重,衆真所尊,皆鑄金爲字,刻書玉篇,封之於無上大羅天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七寶玄臺。此臺則是太上所治也……十方至真,三千大千已得道大聖衆,及自然妙行真人,皆一日三時,旋繞上宫,稽首行禮,飛虚浮空,散花燒香,手把十絶,嘯詠洞章。讃九天之靈奧,尊玄文之妙重也。今道士齋時,所以巡繞高座,吟詠《步虚》者,正是上法玄根,衆聖真人朝晏玉京時也。行道禮拜。皆當安徐雅步,審整庠序,俯仰齊同,不得參差。*陸修靜: 《洞玄靈寳齋説光燭戒罰燈祝願儀》,《道藏》第9册,第824頁。
敦煌文書S.6841號《靈寳自然齋儀》所引《金籙簡文》與此相同。根據我們的研究,以上陸修靜所引“《經》言”的内容,實際上直接出自《太上洞玄靈寳金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這是一部《正統道藏》失收的“元始舊經”。*王承文: 《中古道教“步虚”儀的起源與古靈寳經的分類考釋》,《中山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該經一方面詳細敍述遠古劫運之時神真在玄都天界通過“步虚”儀以表達對《靈寳赤書五篇真文》的高度尊崇,然而,另一方面卻又稱“今道士齋時,所以巡繞高座,吟詠步虚者”,意即人間道士們的靈寶“步虚”儀式,其實是對天界神靈“步虚”儀式的模仿。而該經作者在此所稱之“今”,明顯是指東晉末年古靈寳經創作時代道士的靈寶“步虚”等齋法活動。
可見,如果我們過於拘泥於“元始舊經”的所謂“時間邏輯”,那麽,這些經典就只能敍述其在“上皇元年”出世以前天界神真之間的傳承内容,而不應該出現以上人間世界特别是東晉末年的任何内容。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根據以上考察,我們認爲“元始舊經”的創作者並没有爲了證明這些經典因爲年代極其久遠,而去刻意地回避“開皇劫”和“上皇劫”以後甚至是東晉末年古靈寳經形成年代的人間事物。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的是,王皓月博士所提出的按照“教理上的出世時間”區分“元始舊經”與“元始系《靈寳經》”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些可以商討的地方。一是他從數十萬字的“元始舊經”中所發現有“今”的表述總共僅有兩處,所涉及的文字不超過一百字。如果試圖用這樣的一個思路來對所有“元始舊經”的形成過程都作重新解釋,顯然很難説有真正的可操作性。二是他將東晉末年“元始舊經”的文本結構,直接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十日談》和阿拉伯故事集《天方夜談》相提並論,認爲他們都體現了“文學創作領域”所常見的“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結構”。如果考慮到這兩種文本在性質上的根本不同以及二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巨大差異,我們認爲其中真正的可比性似乎太小。三是他特别强調“元始舊經並没有獨立出世的,而只是作爲元始系《靈寳經》的内容而出世”。*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第88頁。但是在具體討論過程中,他卻又反復證明“元始舊經與元始系《靈寳經》之間的不同,不僅僅是經名和卷數的不同,二者在經典成書時間和經典内容上也不一樣,不能視爲同樣的經典”。*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第88頁。而這樣的論證也就意味着,他一方面强調“元始舊經”本身是一種根本就“没有獨立出世的”經典文本,但是,另一方面他卻又專門來論證“元始舊經”和“元始系《靈寳經》”兩種版本之間在經名、卷數成書時間和經典内容等諸多方面的重大差異。因而這種論證邏輯本身似乎也是前後矛盾的。
“元始舊經”的創作者的確聲稱存在“龍漢劫”和“開皇劫”或“上皇劫”這些不同劫運時期的版本,那麽,這種説法究竟是否可以作爲研究的證據呢?古靈寳經的“龍漢”、“延康”、“赤明”、“開皇”、“上皇”等劫運觀念,均直接源於印度佛教。“劫”,梵語kalpa,巴利語kappa,最初爲古代印度婆羅門教中一種極大的時間單位,認爲世界應經歷無數劫。對於“劫”的長度,佛教資料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爲一劫相當於人間四十三億二千萬年。而且至劫末有劫火燒毁一切,此後又重新創造世界;另一種説法認爲一劫有四時,包括圓滿時、三分時、二分時、爭鬥時,四者凡四百三十二萬年。而且四時相較,時間上愈形短少,人類的道德也日趨低落。至爭鬥時結束即成劫末,世界亦即毁滅。*慈怡主編: 《佛光大辭典》,高雄: 佛光出版社,1989年,第2810—2815頁。佛教對“劫”的觀念亦加以沿用和發展,在大多數情況下,佛教均以“劫”來説明世界生成與毁滅的過程。而古靈寳經的創作者將其經書的起源或相關内容,都追溯到這些劫運時代,然而其表述矛盾很多。如果我們今天依據這些材料來試圖弄清“元始舊經”在“龍漢”或“開皇”、“上皇”等不同劫運時期的版本源流,無疑等於是把古靈寳經這些荒遠無稽極富想像力的宗教神話都完全當成了信史。
那麽,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元始舊經”形成過程中的“時間邏輯”呢?在此我們試以大致隋朝成書的《洞玄靈寳玄門大義》爲例。該書之《釋威儀第七》稱:
三元本有威儀俯仰之格三(應爲“二”)千四百條。龍漢之後,文多不備。今所出有二百四十條,此以末世不堪,故略不傳耳。*《洞玄靈寳玄門大義》,《道藏》第24册,第738頁。
以上資料被王皓月博士所征引,並用以證明“元始舊經”的版本早在“龍漢劫”就已經存在。按以上内容實出自南朝宋文明《靈寳經義疏》,敦煌P.2256號《靈寳經義疏》論述道教“十二部義”,其中第七部“威儀”,宋文明釋曰:
三元本有威儀府(俯)仰之格二千四百條,龍〔漢〕以後,聞多不備。今所出有三(二)百四十條。此皆以人情薄弱,不堪具受,故略以示之。
而《道藏》本《洞玄靈寳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應爲這一説法的較早來源之一。該經稱元始天尊告太上大道君曰:
洞玄靈寳中元宫中玉籙簡文神仙品目,舊有上元、中元、下元三部威儀,部有八百條,三部合二千四百條。皆金書玉字,仙都左公總録於中元宫中。自經龍漢之後,淪於混沌。其文改易,多不全舊。至赤明元年,上聖撰校,抄集要用,部有八十條,三部合二百四十條,秘於三元宫中。*《洞玄靈寳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道藏》第9册,第864頁。
這部古靈寶經應屬於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録的《太上洞玄靈寶金籙簡文三元威儀經》的一部分。*王承文: 《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第449—457頁。可見,《靈寳經義疏》和《洞玄靈寳玄門大義》所説的“今所出有二百四十條”,其所謂“今”,所代表的應該是比“開皇劫”更早的“赤明劫”,而非“開皇劫”或“上皇劫”。由於“龍漢劫”和“赤明劫”相距在億萬年以上,因此,以上比較合理的解釋,不應該看成是“龍漢劫”時期的“三元本有威儀俯仰之格二千四百條”大量遺失,至“赤明劫”時期真的就僅剩下“二百四十條”。而其真相應該是,在東晉末年古靈寳經創作者才創作出這“二百四十條”,以勉强充作其原先预定的“威儀俯仰之格二千四百條”的數目,但是卻爲今後的大規模重新創造留下伏筆。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認爲歷史上並不真正存在所謂“元始舊經”與“元始系《靈寳經》”的區别。至於現存“元始舊經”中某些“今”與“舊”的表述,包括“龍漢劫”與“開皇劫”、“上皇劫”的區分,僅僅是古靈寳經的創作者爲了神化其經典以達到宣教目的的策略而已,不宜直接將其當作一種具有實際意義的歷史資料來討論。
四、古靈寶經中的大乘佛教“本行”觀念與“元始舊經”出現“葛玄”和“張道陵”的原因
在以往的討論中,我們認爲敦煌本陸修靜《靈寳經目》中“元始舊經”和“新經”的劃分,保存了古靈寳經出世的原貌。陸修靜並未改變古靈寳經原有的分類。但是,在《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録的數部“元始舊經”中,卻出現了“葛玄”或“張道陵”等歷史人物的名字。例如,《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就出現了作爲“五真人”之一的“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張天師”並爲葛玄傳授靈寳經。該經末尾還出現了葛玄在天台山爲弟子鄭思遠等傳經的記載。至於《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和《太上洞玄靈寳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中則都出現了作爲“仙公”或“太極左仙公”的“葛玄”。對此,小林正美認爲這些經典本來屬於“天師道三洞派”所傳的“仙公系”靈寳經,是陸修靜將他們抽出以填入“元始系”靈寳經的。近年來,劉屹博士則對此有反復申論,他强調,“葛玄是三國吴人”,“故仙公所傳的經典當然不應該被列入元始諸經,而元始諸經也絶對不應該出現葛仙公”,“敦煌本‘靈寳經目’所載的‘元始舊經’中,至少有《升玄步虚章》、《自然五稱文》、《法輪罪福經》這三經中,都是以葛仙公的授受爲主要内容的。這就和‘元始舊經’本是上皇劫期中産生的天書概念相矛盾,難道葛仙公早在上皇劫期中就領受過元始天尊所傳的靈寳經?”*劉屹: 《敦煌〈靈寳經目〉研究》,《文史》2009年第2輯,第70頁。他又稱“所謂‘舊目’所載的元始十部妙經,都是在無數劫之前就存在的,是隨劫應運而出的。而葛仙公只不過是這一劫期和這一世代中的人物”;*劉屹: 《“元始舊經”與“仙公新經”的先後問題——以“古靈寳經”中的“天尊”和“元始天尊”爲中心》,第279頁。“‘元始舊經’出世的神話,存於天宫隨劫輪轉的元始諸經中,是不應該出現三國人物葛仙公的”;*劉屹: 《古靈寳經出世論——以葛巢甫和陸修靜爲中心》,第160頁。“‘元始系’經典從其出世神話上,就決定了其中不應該出現葛仙公這個人物”。*劉屹: 《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第151頁。而王皓月博士亦强調,“成書於開皇之劫和上皇之劫的元始系《靈寳經》不應該出現葛仙公的名字,成書於龍漢的元始舊經更不會有葛仙公的名字”。*王皓月: 《再論〈靈寳經〉之中‘元始舊經’的含義》,第88頁。至於以上數部“元始舊經”中之所以出現“葛仙公”或“張道陵”的原因,我們認爲主要與古靈寳經本身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教義思想和其“佛教化”的“時間邏輯”密切相關。
(一) 古靈寳經中“太極左仙公”與葛玄的“佛教化”
葛玄的確是漢末三國時期的歷史人物,但是在古靈寳經中,他卻屬於已經被改造過而且徹底“佛教化”的特殊神靈。其作爲“太極左仙公”神格的塑造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根據研究,敦煌遺書和《正統道藏》所保存的古靈寳經文本,其相關内容在南北朝後期和隋唐時期其實有比較明顯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原先大量佛教化的内容已經被删除了。*王承文: 《敦煌古靈寳經與晉唐道教》,第31—85頁。例如,唐初釋法琳《破邪論》卷上所引《靈寳法輪經》,即“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寳真一勸誡法輪妙經》,其文稱:
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 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升天。仙公〔師〕自語子弟云: 吾師姓波閲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法琳: 《破邪論》卷上,《新修大正大藏經》卷52,第477頁。
按以上内容在唐代敦煌寫本和《正統道藏》中均已被删除了,但是卻可以肯定是屬於原經的内容。以上有两點值得注意: 第一,《靈寳法輪經》所稱“吾師姓波閲宗,字維那訶”,在“新經”《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宿緣經》中也有同樣的記載。該經記載徐來勒稱:“我師是太上玉晨大道虚皇,道之至尊也。我是師第六弟子,大聖衆皆師之弟子。弟子无鞅數也。我師名波悦宗,字維那訶。今以告子,子祕之哉。蓋真人之名字,亦難究矣。此名字多是隱語也。我名徐來勒,字洪元甫。”*《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宿縁經》,《道藏》第24册,第670頁。據此,所謂“姓波悦宗,字維那訶”,其實是太上大道君的秘號。太上大道君與太極真人徐來勒和太極左仙公葛玄之間的關係爲: 葛玄師從太極真人徐來勒,而徐來勒則師從太上大道君。至於法琳《破邪論》所引《靈寳法輪經》中“仙公自語弟子云”,我們認爲應該是“仙公師自語弟子云”的錯誤;第二,葛玄出生時的神異色彩及其與佛教的關係,在敦煌本《靈寳經目》所著録“新經”《太極左仙公起居經》中也有反映。然該經已佚。而法琳《破邪論》卷上所引《仙公起居注》記載:
(葛玄)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繞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法琳: 《破邪論》卷上,《新修大正大藏經》卷52,第477—478頁。此據道宣: 《廣弘明集》卷一一所收《破邪論》校補(見《新修大正大藏經》卷52,第162頁)。
可見,無論是“元始舊經”還是“新經”,都明確將葛玄的出生稱爲“善思菩薩”或“西方善思菩薩”轉世。善思菩薩又稱善思尊者。據佛教《大寶積經》記載,善思尊者曾參加佛陀在王舍城耆闍崛山内舉行的法會。彌勒菩薩爲轉輪王時,善思尊者對其有啓迪之功;佛乞食毗耶雜城時,善思尊者又獻花禮佛,誓爲菩提,佛陀乃爲其説法,證無生忍。東晉著名佛教高僧支遁(314—366)撰寫有《諸菩薩讃》,其中即包括有文殊師利菩薩讃、彌勒菩薩讃、維摩詰菩薩讃、善思菩薩讃等。*支遁: 《諸菩薩贊》,載道宣: 《廣弘明集》卷一五,《大藏經》卷52,第197頁。也正因爲如此,古靈寳經的創作者認爲,生活在漢末三國孫吴時期的葛玄,其真正的出身本爲“西方善思菩薩”轉世而來,而且也是佛教徒所應尊崇的神靈。又據元代譚嗣先《太極葛仙公傳》稱:
按《别傳》云: 仙公父素奉道法,即遣人詣本里玄靜觀求香水浴兒。時有自然道士支道紀,莫知其所由來,欣然謂曰: 吾昨夢通玄真人自大羅天下降,明日當往賀尚書生奇男。越一日,果來賀,求兒看。父令抱兒出,道紀起敬,尚書驚問。道紀曰: 此兒有紫氣覆之,狀如寶蓋,神光焕耀,當爲神仙,非常兒比。尚書曰: 仙聖寥邈,得壽考以爲宗嗣足矣。道紀因作禮十方仙聖,爲讃曰: 身雖輪聖化,魂神無暫滅。宿福積重縁,昔願非今日。大羅真人降,仙聖含真出。天龍漱香花,濯我鍊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玄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無想,放則大乘逸。頌畢,長揖而出,倏然不見。*譚嗣先: 《太極葛仙公傳》,《道藏》第6册,第846頁。
以上所引“《别傳》”是指南朝時期成書的《葛仙翁别傳》。《藝文類聚》卷五十引作《葛仙公别傳》,其卷九七及《太平御覽·道部》均引作《葛仙翁别傳》,此書“蓋依陸修靜《靈寳經目》所著録‘新經’中的《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内傳》一卷和《太極左仙公起居經》一卷撰成”。*王承文: 《敦煌古靈寳經與晉唐道教》,第106頁。明代所編《道藏闕經目録》著録有《洞玄靈寳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内傳》和《洞玄靈寳太極左仙公起居注》,證明了這兩部古靈寶經“新經”直至元代仍然存在。《葛仙翁别傳》等强調葛玄是大羅天通玄真人降世。支道紀的讚頌詩稱其“身雖輪聖化,魂神無暫滅”,“大羅真人降,仙聖含真出”,也就是説葛玄能夠成爲“太極左仙公”,其實並非是由此生此世的勤苦修煉決定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鑒》葛玄傳的内容與此近似,其文曰:
仙公本大羅真人下降,以後漢桓帝延禧(熹)七年(164)甲辰歲四月八日誕世。仙公父素奉道法,即遣使齋香華錢詣本里玄靜觀,求香水浴兒。時有自然道士支道紀,莫知其所由來,聞尚書得男,乃欣然與來使曰: 吾昨宵夢見通玄真人從大羅天下降,與吾言: 昔别已經劫,子將忘我耶?予作禮稱: 弟子願得無上正真道眼。汝歸,悉告尚書,明日當往賀君生奇男。使者歸,以實聞。越一日,道紀果來賀,尚書告曰: 始有此子,圖爲宗嗣計,式副願望。道紀求兒看,母有難色。父令抱兒出,道紀見兒,不覺起敬。尚書驚問,道紀曰: 吉之先見,敢以爲賀。此兒有紫氣覆之,狀如寶蓋,神光流轉焕耀,當爲神仙,非世間常兒比。尚書曰: 仙聖寥邈,變化茫昧,深不可測。願得壽考,以爲宗嗣足矣。道紀曰: 聰明智慧,暫經人世,九天稱慶,七祖同歡,生者被福,死者登天。道紀遂念真人宿世之功,因作禮十方仙聖,永保元吉。禮竟,爲仙公作讃,其辭曰: 身雖輪聖化,魂神無暫滅。宿福積重縁,昔願非今日。大羅真人降,仙聖含真出。天龍漱香花,濯我煉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玄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無想,放朗大乘逸。頌畢,道紀長揖而出,倏然不見。*赵道一: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二三《葛仙公》,《道藏》第5册,第229—230頁。
以上也强調葛玄原本是天界大羅真人,有“宿世之功”,其出生時間四月八日本爲佛誕日。而其出生亦僅僅是“暫經人世”。也正因爲如此,我們就應該按照古靈寳經本來的教義思想來理解作爲“太極左仙公”的葛玄在“元始舊經”中的出現。
葛玄在古靈寳經中以“太極左仙公”的神格出現,其實是按照佛教佛陀形象塑造而成的,并在極大程度上借鑒了大乘佛教“本生”和“本行”的觀念。所謂“本生”,梵語jāta,巴利語同,音譯作闍多伽、闍陀伽,意譯爲本起、本緣,等等。主要講述釋迦牟尼在過去世受生爲各種不同身形及身份而行菩薩道的事迹。根據佛本生故事,這個未來的佛陀,即菩薩(boddhisattva)(覺有情)在兜率天(tusita)裏其實就選擇了他的父母親。而古靈寳經中葛玄的出世即與此相似。大乘佛教的“本行”概念,是指成佛陀以前尚在菩薩位(因位)時之行迹,爲成佛之因之根本行法。慧遠所撰《維摩義記》即稱:“菩薩所修,能爲佛因,故名本行。”*慧遠: 《維摩義記》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卷38,第427頁。自東晉以來,中古佛教有專門的《佛説菩薩本行經》、《佛本行經》、《佛本行集經》、《佛本行贊經》,等等。印度佛教不同於古代婆羅門教的地方,就是佛教不承認有“天帝創始説”那樣的創世主。佛教因緣論認爲宇宙本身也是因緣的産物。宇宙中的一切皆由因緣變幻無常,一切皆空。因而宇宙没有本體,佛陀亦非造物主和宇宙之神,同其他萬物一樣,只是因緣和合的産物。三國吴支謙所譯《佛説太子瑞應本起經》開篇稱:“佛言: 吾自念宿命,無數劫時,本爲凡夫。初求佛道已來,精神受形,周遍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譬喻盡天下草木,斬以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支謙譯: 《佛説太子瑞應本起經》,《大正新修大藏經》卷3,第472頁。佛陀的前生經歷了無數的輪廻過程。其所謂“本爲凡夫”,即釋迦牟尼本來是凡夫俗子。正因爲如此,佛教的宗旨是引導人們修證成佛。而教主佛陀正是修道而“覺悟”的典範。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從西晉竺法護所譯的《正法華經》開始,佛教“本生”、“本行”觀念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爲該經開始强調佛陀因爲普度衆生而善權方便,曾經以無數種化身深入衆生説法教化。至於那位誕生在迦毗羅衛王宫,出家後“坐於樹下”而成佛的釋迦牟尼,其實只是佛陀無數個化身中的一個。而釋迦牟尼的真身,其實早在不可計數的年代就已經得道成佛了。例如,《正法華經》之《如來現壽品》稱:
於時世尊告大衆曰:‘今吾宣布詔諸族姓子,如彼士夫取無數五百千億佛界中塵,舉一塵過於東方不可計會億百千姟諸佛國土,乃著一塵,如是次取,越爾所國土復著一塵。如斯比類,取無央數五百千億佛界所有土地一切之塵,一一取布著諸佛國,悉令塵盡。吾逮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已來,其劫之限,過於爾所塵數之劫。諸族姓子等,見吾於此忍界講法,復在他方億百千姟諸佛世界而示現,皆悉稱吾爲如來、至真、等正覺、錠光如來,以諸伴黨若干之數而現滅度。諸族姓子,吾以善權方便,演説經典,現無央數種種瑞應……佛言: 吾從無數不可計限億百千劫,發無上正真道意,懃苦無量,每行權便,示現教化,發起群生。*(西晉) 竺法護譯: 《正法華經》卷七《如來現壽品》,《大正新修大藏經》卷9,第113—114頁。
該經記載佛陀自稱“吾逮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已來,其劫之限,過於爾所塵數之劫”,其意就是指早在極其久遠的過去其實就已得道成佛。至於他“於此忍界(按指現實世界)講法,復在他方億百千姟諸佛世界而示現”,僅僅是爲了“每行權便,示現教化,發起群生”。
古靈寳經“元始舊經”和“新經”對大乘佛教的“本行”觀念都有大量借鑒。例如,“元始舊經”《太上靈寳智慧定志通微經》就一方面詳細地敍述“元始天尊”作爲一個道士“樂靜信”修證得道的經歷,而且元始天尊還曾經“或賣身供法,或身投餓虎,或割肉飴禽,或殺身施蟲,或質致妻子,或以頭施人。諸如此例”;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强調元始天尊早在極其久遠的劫運年代就已經得道。至於該經所列舉的修道經歷,“並是得道真人共作視見,勸化愚蒙”。*《太上洞玄靈寳智慧定志通微經》,《道藏》第5册,第893頁;相關研究參見王承文《敦煌古靈寳經與晉唐道教》,第49—54頁。《太上洞玄靈寳諸天内音自然玉字》則塑造了“天真皇人”修證得道的“本行”經歷。*《太上靈寳諸天内音自然玉字》卷四,《道藏》第2册,第554—563頁。尤其是《太上洞玄靈寳真文度人本行妙經》,其經名就直接使用了“本行”概念。而該經中的“太上大道君”、“元始五老”等,其所有“本行”事迹均證明他們是具有佛陀“本行”特徵的神靈。*王承文: 《古靈寳經“五老帝君”與中古道教經教學説的建構》,第233—260頁。《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所引《靈寳真文度人本行經》,即“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寳真文度人本行妙經》,其文曰:
元始五老非以後學而成真者也。所以寄胎託孕,生於人中,或因水火而練化者。爲欲隨世改運,輪轉因緣,經麤入妙,以勸戒學者,令勤爲用心也。*《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道藏》第24册,第731—732頁。
可見,古靈寳經中這些地位崇高的神靈之所以會以各種身份“寄胎托孕,生於人中”,而且極力勤苦修道,並不是因爲他們自己需要不斷努力修證才能求得升仙得道,而是爲了“勸戒學者,令勤爲用心”。因此,他們在人間的所有修證過程,就如同釋迦牟尼一樣,具有“每行權便,示現教化,發起群生”的特殊意義。
“新經”《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宿緣經》中的“太極左仙公”葛玄就擁有其自己的“本行”經歷。*《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宿緣經》,《道藏》第24册,第666—670頁。前引敦煌文書P.2454號《仙人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經》(《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因緣經》同),其經名就也突出了“本行”概念。其開頭記載,“太極左仙公”即葛玄在孫吴赤烏三年(240)正月一日,在勞盛山對三十三位“地仙道士”講解自己的“本行”經歷。其文稱:
道士於是避席請問曰: 下官等學道彌齡,積稔於今六百甲子矣,而尚散迹於山林間。師尊始學道,幸早被錫爲太極左仙公,登玉京,入金闕,禮无上虚皇,不審夙因作何功德,爰受天職,致此巍巍,三界北酆所仰,願爲啓説宿命所由因緣根本也。*《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因縁經》,《道藏》第24册,第671頁。
以上道士自稱“學道彌齡,積稔於今六百甲子矣”,是説他们學道已經三萬六千年了。可見,葛玄在勞盛山説法的對象——“地仙道士”,其實並非人世間的凡夫俗子。而且該經還通過道士之口强調,葛玄“始學道,幸早被錫爲太極左仙公,登玉京,禮無上虚皇”等。也就是説,葛玄能夠成爲太極左仙公,並非是作爲“這一劫期和這一世代中的人物”勤苦修道所致,而是因其“宿命所由因緣根本”所決定的。葛玄去世是在此次勞盛山説法後的第四年,即吴赤烏七年。而葛玄在此世之前其實早已被天界封賜“太極左仙公”的名號。
該經還由葛玄講解了地仙道士們在各種“前世”修道不精終成“地仙”的原因。其中一個仙人名叫紀法成,葛玄指明其爲“前世弟子”,並且早在“昔帝堯之世”,就跟隨葛玄在嵩山學道。葛玄亦講解自己的“宿世本行”,稱自己曾“生爲貴人”,然而,由於“扶强抑弱,死入地獄。生爲小人,貧窮陋疾,孤寒煢然”。因爲發念,“後生富家,珍寶充足”,又因“苦酷奴婢,死入地獄”。又因爲發念,“後生爲貴人,乃復殺害衆生,漁獵爲事,死入地獄”,“罪竟後生爲豬羊,以報昔怨”。後又反復生爲下賤人、女人、道士、國王等等。總之,此生此世的葛玄實際上已經經歷了無數次的輪廻轉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轉生國王家爲太子時,曾與三侍臣以及釋道微、竺法蘭、鄭思遠、張泰等一起共同發願修道。葛玄又轉生“爲諸人作師”。後又轉生賢家,“復爲道士沙門,復得同學,相爲師徒,復受大經,齋戒行道,是故上聖盻目覷真,降教於我也。爾時蘭、微、張、鄭盡侍座,今日相隨,是宿世之緣願故爾。諸生莫不釋然,四座咨嗟,乃歎曰: 天尊上人,求道積久,彌劫歷稔,故以得仙公之位,諒有由也。”
這部道經基本上就是按照佛陀來塑造葛玄的神格的,并且證明了這樣兩點: 一是葛玄能成爲太極左仙公,並非是靠此生此世勤苦修道所致,而是“求道積久,彌劫歷稔,故以得仙公之位”。所謂“彌劫歷稔”,實際上是指葛玄的修道經歷貫穿了各種“劫期”,此生此世之前早已就是地位崇高的道教神靈;二是《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等經書所載孫吴赤烏年間,葛玄在天台山向弟子釋道微、竺法蘭、鄭思遠等傳授靈寳經,其師承關係包括靈寳經本身的傳授,其實也早在他們此生此世之前就已經確立了。至於葛玄在漢末孫吴時期的修道活動,包括孫吴赤烏年間在天台山傳經以及在勞盛山對地仙道士們説法,等等,實際上就如同釋迦牟尼生於迦毗羅衛王宫,出家後“坐於樹下”而成佛一樣,都只是作爲對世人“每行權便,示現教化,發起群生”的一種教化方式而已。而前引唐代閭丘方遠《太上洞玄靈寳大綱鈔》所稱太極三真和徐來勒在天台山的傳經,説成是“重授靈寳諸法”,其真實含義是説葛玄在此生此世之前其實就已被傳授過靈寳諸法。
“新經”《太上洞玄靈寳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的開篇,則通過葛玄自己陳述了其在遠古劫運時期的修道經歷。其文曰:
仙公於天台山靜齋念道,稽首禮拜,請問靈寳玄師太極太虚真人曰: 弟子有幸,得侍對天尊,自以微言,彌綸萬劫,洞觀道源。過泰之歡,莫有諭也。*《太上洞玄靈寳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道藏》第6册,第155頁。
以上“靈寳玄師太極太虚真人”,敦煌本作“太極法師真人徐來勒”。所謂“弟子有幸,得侍對天尊”,是指葛玄自己在輪廻轉生的過去世中曾經覲見元始天尊。所謂“彌劫”的“彌”,代表“滿”和“遍”。《漢書·司馬相如傳》稱“彌山跨谷”。顔師古注稱:“彌,滿也。”*《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557頁。《周禮·大祝》稱“彌祀社稷,禱祠”。漢代鄭玄注稱:“彌猶遍也。”*(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 《周禮注疏》卷二五,《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811頁。而“彌綸萬劫”的“彌綸”,指統攝,籠蓋。《周易·系辭上》稱:“《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孔穎達: 《周易正義》卷七,《十三經注疏》,第77頁。《朱子語類》卷九八亦稱:“彌綸天地,該括古今。”至於古靈寳經中“劫”的概念,如前所述,直接源自佛教的“kalpa”,《隋書·經籍志·佛經序》稱宇宙的“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而唐李少微注古靈寳經《度人經》稱:“按天地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薛幽棲亦稱:“天地世界,一期運終,是名爲一劫也。”*《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卷二,《道藏》第2册,第201頁、第224頁。有關古靈寶經劫運的相關討論,參見王承文: 《敦煌古靈寳經與晉唐道教》,第637—643頁。因此,古靈寳經所謂“彌綸萬劫,洞觀道源”,一方面也表明葛玄並不只是“這一劫期和這一世代中的人物”,而是超越了宇宙各種劫運的循環往復的神靈;另一方面,葛玄還與“道源”即大道的根源相聯繫。該經又記載作爲“五真人”之一的“高玄真人”亦稱讚葛玄曰:
此子累劫念道,致太極玉名,寄慧人中,將獨步玉京,超逸三界,巍巍乎太上仙公之任矣。故慈心於天人,念度於後學也。常以外身而濟物,有德而弗名,玄都所銓,諒不虚矣。*《太上洞玄靈寳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道藏》第6册,第155頁。
可見,葛玄是因爲“累劫念道”而超越“三界”並升太玄都玉京山充當太極左仙公之任的。根據以上討論,古靈寳經完全是按照早期佛教“本行”觀念來重新塑造葛玄作爲“太極左仙公”的神格的。因而,“元始舊經”和“新經”所突出的太極左仙公葛玄,與作爲漢末三國時期歷史人物的葛玄,其實已經没有什麽真正的聯繫了。
當然,古靈寳經如此大量地借用佛教觀念對葛玄神格進行重新塑造,也招致了南朝上清派代表人物陶弘景的嚴厲批評。他在注解《真誥》時稱:“葛玄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許謐)所以有問,令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寳》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梁) 陶弘景: 《真誥》卷一二《稽神樞》,《道藏》第20册,第561頁。所謂“《靈寳》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就是針對古靈寳經所提出的尖銳批評。*王承文: 《敦煌古靈寳經與晉唐道教》,第325頁。陶弘景所撰《吴太極左宫葛仙公之碑》一方面表現了對葛玄神仙事業的推崇,並自稱是葛玄的“邦族末班”,然而,另一方面卻又稱“俗中經傳所傳,云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誥》并葛氏舊譜,則事有未符。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説”,*(梁) 陶弘景: 《吴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陶隱居集》卷下;陳垣: 《道家金石略》,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2頁。也是針對古靈寳經過分神化葛玄的批評。
(二) 古靈寳經中“正一真人三天法師”與張道陵身世的“佛教化”
作爲漢末天師道創立者的張道陵,與江南“葛氏道”的代表人物葛玄之間本無任何師承關係,但是在古靈寳經中,張道陵卻被塑造成爲向葛玄傳授靈寳經的“五真人”之一。其根本原因就是古靈寳經中的張道陵其實也不是普通的歷史人物,而是一位已經被彻底“佛教化”的神靈。古靈寳經中神化張道陵的篇幅並不多,然而卻具有關鍵意義。“新經”《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因緣經》記載仙人向葛玄請教張道陵相關事迹,其文曰:
仙人請問曰: 近登崐崘玄圃宫侍座,見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道陵降座,酆都伺迎,三界稽首,諸天禮問動靜,龍駕曜虚,頂負圓明,身生天光,文章焕爛,先世何功德,故是得道,其獨如是乎?願聞之。答曰: 天師本行所歷,亦彌劫勤苦,齋戒讀經,弘道大度,高範玄真,耽味希微,轉輪求道,尤過於吾,不可具。其志大經,行大道,故得三天法師之任,太上正一真人之號矣,豈不大乎!*《太上洞玄靈寳本行因縁經》,《道藏》第24册,第673頁。
張道陵出現在“昆侖玄圃宫”,以及“酆都侍迎,三界稽首,諸天禮問動靜”等,都顯示古靈寳經中的張道陵的神格,與漢晉天師道和早期上清經中的張道陵已有極大的區别。當仙人詢問張道陵“先世何功德,故是得道,其獨如是乎”的時候,葛玄回答稱“天師本行所歷,亦彌劫勤苦”。如前所述,“本行”是一個極爲典型的大乘佛教的概念,因此,所謂“彌劫勤苦”、“轉輪求道”,都是指張道陵在宇宙各個劫運時期都一直在勤苦修行。而這部經典通過葛玄自己來强調張道陵“轉輪求道,尤過於吾”,就使其對張道陵的神化和尊崇發生了最具有關鍵意義的轉變,并且與古靈寳經創造者即“葛氏道”派最尊崇的家族神靈——葛玄聯繫在一起。古靈寳經中作爲“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的張道陵,顯然已經不是作爲一位漢末歷史人物而被記載的。東漢獻帝建安四年(199),他在會稽上虞山同其他太極“四真”一起向葛玄傳授“元始舊經”,本質上就如同《正法華經》中釋迦牟尼在世時對其弟子宣講佛法一樣,也只是“每行權便,示現教化,發起群生”而已。
總之,按照古靈寳經本身“佛教化”的“時間邏輯”,在數部“元始舊經”中之所以出現“葛玄”和“張道陵”以及相關經書傳授,源於他們本身就不是被當作普通歷史人物而被記載的。古靈寳經充分借鑒吸收了大乘佛教的思想,將“葛玄”和“張道陵”都塑造成超越劫運輪轉的神靈。因此,葛玄於漢末在會稽上虞山、於吴赤烏年間在天台山等地接受靈寳經,其在吴赤烏三年在勞盛山對地仙道士説法,以及在天台山傳經給鄭思遠等等,這種宗教敍述貫穿着一種濃厚的佛教“本行”和“示現”的觀念。
在以往的討論中,我們認爲敦煌本《靈寳經目》所著録的古靈寳經“元始舊經”,其出世要早於“新經”。*王承文: 《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第99—107頁;《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和“新經”出世先後考釋——兼對劉屹博士系列質疑的答復》,《中山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在《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洞玄靈寳自然九天生神章》、《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太上洞玄靈寳真一勸誡法輪妙經》等“元始舊經”中,最先出現了作爲“太極左仙公”的葛玄和作爲“正一真人無上三天法師”的張道陵,而在後來出世的多部“新經”中,則將他們的“本行”身世進行詳盡的説明。而這一點恰恰也證明了古靈寳經“新經”在本質上確實是對“元始舊經”的闡釋和補充。
五、餘論:“元始舊經”和“新經”之“時間邏輯”問題的本質
近三十多年以來,小林正美先生的古靈寶經研究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十分深遠。其最核心的觀點之一,就是主張按照“教理上的出世時間”即“時間邏輯”來討論古靈寳經的分類和教義思想以及道派歸屬。强調所有“元始舊經”都是元始天尊在“上皇元年”所説教的經典,所以其中決不能出現“上皇元年”以後的事件特别是“葛玄”和“張道陵”這樣的歷史人物。而“新經”則必定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寳經》”,所以其“教理上的出世時間”就是孫吴。小林正美又提出由“葛氏道派”所創作的“元始舊經”和由“天師道三洞派”所創作的“仙公新經”,二者在最尊崇的經典和最尊崇的主神以及有無“三洞經書”等方面存在重大的差異。在此基础上,小林正美對敦煌本《靈寳經目》所著録的古靈寳經進行了重新分類,從而使這部陸修靜完成於 1500多年前並於百餘年前重新發現的道經目録發生了重大改變。一是本來由《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洞玄靈寳自然九天生神章經》、《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太上洞玄靈寳真一勸誡法輪妙經》等,從“元始舊經”改變成了“仙公新經”;二是使本屬於“新經”的《太上洞玄靈寳真文要解上經》卻又改變成爲“元始舊經”;三是使本屬於“元始舊經”的敦煌本《洞玄靈寳(自然)九天生神章經》一分爲二,變成了“元始系·仙公系”,即其中一部分屬於“葛氏道”所創作的“元始舊經”,一部分則屬於“天師道三洞派”所創作的“仙公新經”。*(日) 小林正美著、李慶譯: 《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73—175頁。正是受這種研究方法的影響,目前似乎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熱心於對現存各種古靈寶經的經典文本結構進行分解、分割和剖析,越來越强調“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在教義思想以及教派歸屬等多方面的重大差異。不過,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卻將這種研究方法批評爲“誤入歧途”。*Stephen R.Bokenkamp,“The Silkworm and the Bodhi Tree: The Lingbao Attempt to Replace Buddhism in China and Our Attempt to Place Lingbao Taoism,”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ed. John Lagerwey(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vol.1,p.336. 又見(美)柏夷著、孫齊等譯: 《道教研究論集》,上海: 中西書局,2015年,第12頁。從我們以上對敦煌本《靈寳經目》與古靈寳經分類時間邏輯問題的討論來看,這種研究方法確實存在比較明顯的局限。
首先,這種研究方法在某種意義忽略了《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本身的神聖性質,忽略了“元始舊經”和“新經”在道教神學意義上的重要區别。在古靈寳經的創作者看來,“元始舊經”均爲《靈寳赤書五篇真文》所直接演化而來,而且在名義上均爲元始天尊所説,曾經珍藏在最高天界——太玄都玉京山紫微宫,因而具有“新經”遠不能比擬的神聖地位。《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既然是一部在陸修靜之前即業已存在並且爲道門内部知曉的目録,而陸修靜在其《靈寳經目序》中又對前人“回换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圖,或以充舊典”等偷樑换柱的現象作了嚴厲批判。因此,如果陸修靜自己也用“新經”來充當“舊經”的話,也就意味着他與其所批判的對象並没有什麽差别。《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等作爲“元始舊經”的經典究竟能否成立的問題,毫無疑問,陸修靜和宋文明應該最有發言權。宋文明的《靈寶經義疏》對陸修靜《靈寳經目》進行注疏,其中對陸修靜未能完全遵循古靈寳經的教義思想其實有比較嚴厲的批評,*王承文: 《“靈寶自然天文”與中古道教經教體系的構建》,收入《道教與星斗信仰》,濟南: 齊魯書社,2014年,第79—81頁。然而卻没有對《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等這些經書的性質提出疑問。我們或許可以换一個角度來理解,如果在《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所著録的數部“元始舊經”中,一旦出現了作爲歷史人物的“葛玄”和“張道陵”,就會嚴重損害其作爲“元始舊經”的權威性,並必然引發道教信徒對這些經典本身的懷疑的話,那麽,陸修靜和宋文明等這些以嚴謹和卓越著稱的道教宗師,爲什麽還要主動地將這樣一些經典編入《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呢?比起今天作爲研究者的我們,陸修靜和宋文明顯然應該更加關心其經典本身的神聖性和合法性問題。正因爲如此,我們認爲陸修靜不太可能有意地用“新經”來充當“元始舊經”。敦煌本《靈寳經目》應保持了《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的原貌,陸修靜並未改變古靈寳經“元始舊經”和“新經”原有的劃分。*王承文: 《敦煌本〈靈寳經目〉與古靈寳經的分類及内在關係考釋——以〈靈寳赤書五篇真文〉與〈道德經〉的關係爲中心》,《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3期;《古靈寳經“元始舊經”和“新經”的主神考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7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敦煌本〈靈寳經目〉與古靈寳經的分類及内在關係考釋之二——以“三洞經書”觀念的傳承爲中心》,《敦煌學輯刊》2013年第2期;《中古道教“步虚”儀的起源與古靈寳經的分類考釋——以〈洞玄靈寳玉京山步虚經〉爲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其次,我們的討論證明了無論是“元始舊經”還是“新經”,其實都没有完全按照某一特定的“時間邏輯”來結構其經典。特别是“元始舊經”並没有把傳説中的“上皇元年”作爲一個絶對的時間分界線。而陸修靜以及後來的道教中人,也從來没有人堅持必須按照某一特定的“時間邏輯”來理解和區分“元始舊經”和“新經”。那麽,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古靈寶經内部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呢?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引用德國哲學家卡西爾有關宗教的兩段著名論斷加以説明。卡西爾説,宗教“給予我們一個遠遠超出我們人類經驗範圍的超驗世界的諾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卻始終停留在人間,而且是太人間化了”。*(德) 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 《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93頁。他又説,“宗教的反對者總是譴責宗教的愚昧和不可理解性。但是一當我們考慮到宗教的真正目的,這種責備就成了對它的最高褒獎。宗教不可能是清晰的和理性的”,“它所默示的論據,不可能作任何理性的解釋”,“宗教絶不打算闡明人的神秘,而是鞏固和加深這種神秘”,“宗教絶不是什麽關於上帝和人以及兩者的相互關係的‘理論’”;“因此可以説,宗教是一種荒謬的邏輯;因爲只有這樣它才能把握這種荒謬,把握這種内在的矛盾,把握人的幻想中的本質”。*(德) 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 《人論》,第17頁。因此,古靈寳經的“時間邏輯”問題,應該按照宗教神學邏輯來理解。以歷史上的老子爲例,他本來是春秋時期千真萬確的歷史人物,但是,從漢代開始,他卻逐步被神化爲遠古傳説中的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時期的“帝師”,乃至成爲宇宙本源的“道”的化身。而且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老子又不斷在各種特定的場合出現並傳經或傳教。又如漢代著名方士茅盈(前145—?)、王襃(前36—?)以及魏晉时期方士魏華存(252—334)等歷史人物,卻又能作爲上清神真從公元365年開始爲早期上清派的代表人物許謐(305—376)、楊羲(330—386)、許翽(341—370)等人傳授上清經典。很顯然,如果我們仍然把他們都看作是普通的歷史人物,這種宗教現象就無法得到解釋。古靈寶經則大量借鑒了大乘佛教“本生”、“本行”等觀念,把“葛玄”和“張道陵”都神化爲歷過無數“劫運”并且具有佛陀神格色彩的神靈。而在《太上洞玄靈寳滅度五鍊生尸經》等“元始舊經”中,我們可以發現遠古劫運時期的神靈事迹完全可以同現世的人間事務融合在一起。古靈寳經創作者的目的,一方面極力將其教義思想的創始追溯至遠古劫運時期,並賦予其非常神聖的色彩,然而,另一方面卻又盡可能爲其現實中的宗教活動尋找合理的依據。在古靈寳經“元始舊經”中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與一般宗教普遍存在的邏輯矛盾有關。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6頁。“元始舊經”和“新經”都是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的“葛氏道派”中人所創作,而各種宗教經典包括古靈寳經,本身都是人間社會的産物。因此,如果我們今天試圖用某種特定的“時間邏輯”來對古靈寶經重新分類,表面上看似乎更加符合我們現實世界的“時間邏輯”,然而很可能卻又背離了古靈寶經本身的“宗教邏輯”。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
2016年7月,177— 210頁
——從德勒茲《差異與重複》來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