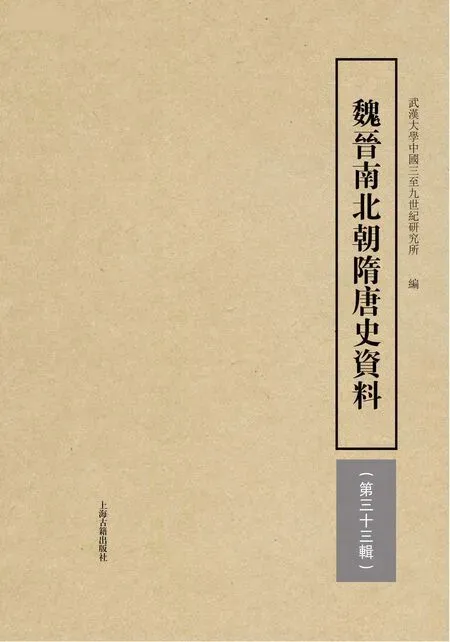中古佛教齋會疏文的演變
曹 凌
中古佛教齋會疏文的演變
曹 凌
本文希望討論佛教齋會疏文的基本情況及其在南朝到宋代的發展。
唐五代佛教齋會宣述齋意時會使用名爲齋文的文書。賴敦煌遺書中齋文材料的發現,相關研究得以有較好的展開,成果頗爲不少。*關於齋文的研究,較具總論性質的有郝春文: 《敦煌寫本齋文及其樣式的分類與定名》,《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第91—97頁、第20頁;郝春文: 《關於敦煌寫本齋文的幾個問題》,《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第64—71頁;湛如: 《論敦煌齋文與佛教行事》,《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1期,第66—78頁;宋家鈺: 《佛教齋文源流與敦煌本〈齋文〉書的復原》,《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70—83頁;王三慶: 《敦煌佛教齋願文本研究》,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2009年;太史文: 《試論齋文的表演性》,《敦煌吐魯番研究》2007年第10卷,第295—307頁;王三慶: 《敦煌文獻齋願文體的源流與結構》,2014年普林斯頓大學“展望未來20年的敦煌寫本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4年9月6日—9日,等。也有對一组文本進行研究者,如王三慶、王雅儀: 《敦煌文獻印沙佛文的整理研究》,《敦煌學》2005年第26期,第45—75頁;荒見泰始: 《敦煌“莊嚴文”初探——唐代佛教儀式上的表白及對敦煌變文的影響》,《文獻》2008年第2期,第42—52頁,等。此外還有不少對於《齋琬文》、《諸雜齋文一本》等個别文本的研究,如梅弘理著,耿昇譯: 《根據P.2547號寫本對〈齋琬文〉的復原和斷代》,《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第50—55頁、第39頁;張廣達: 《“歎佛”與“歎齋”——關於敦煌文書中的〈齋琬文〉的幾個問題》,收入《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0—73頁(後又收入《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92—210頁);王三慶: 《敦煌文獻〈諸雜齋文〉一本研究》,《敦煌學》2003年第24期,第1—28頁,等。其中也有不少就齋文整體情況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見。此外在整理的方面,則以黄征、吴偉編校: 《敦煌願文集》(長沙: 嶽麓書社,1995年)最爲系統,其前言部分也對所謂願文作了綜論性的探討。同時有學者注意到藏内外存有同樣用於齋會但與其有微妙差别的文書,然而在相關討論中,人們往往以“願文”之類較爲寬泛的概念統攝這些材料,而未能充分説明其與齋文的差異。實際上,在這些被稱爲願文的作品中包括了一些與齋文有所區别的重要文書類型,被掩蓋在了齋文的陰影之下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視。而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齋疏。
關於齋疏的先行研究,王三慶先生最近發表的會議論文《敦煌文獻齋願文體的源流與結構》最有創見。由於採用了新發現的《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以下簡稱爲《五杉集》)作爲研究中的重要參考,彼文不僅注意到了疏文的存在,並且提示它和日本的所謂“諷誦體願文”及後代儀式中廣泛使用的疏文有密切關係。
正如王先生所提示,疏文是宋以降佛教科儀中重要的一類文書,直到今天仍然廣泛行用。因此這類文書在中國宗教儀式的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王三慶先生能夠較早加以注意並且與齋文聯繫起來討論可見其眼光獨到。然而作爲開創性的研究,王文似乎仍未能清楚説明疏文的基本特徵,因此對其發展的歷史也有些誤判。例如文中認爲疏文是10世紀從齋文中分化出來的文書門類,而就筆者管見,疏文應當在南朝已經産生,並曾長期與齋文共存。
王三慶先生的研究以關於《五杉集》的討論爲切入點,以五代、宋的相關文獻爲主要參考。其結論似乎也受到了這些較晚出資料的誤導。因此本文希望换一個角度,以《廣弘明集》所收諸齋會祈願文爲切入點,嘗試分析其與以敦煌齋文爲代表的齋文類文書的同異,説明其性質與特點,究明其源流與演變,以展現疏文在南朝到宋數百年間的發展過程及其與齋文的交涉。希望這篇小文能夠爲佛教儀式研究以及敦煌齋文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參考。
一、 兩類齋會祈願文的異同
張廣達先生在《“歎佛”與“歎齋”——關於敦煌文書中的〈齋琬文〉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到“人們今天從道宣《廣弘明集》看到某些願文……雖然設齋讚願之立意與唐代齋文相類,但文字結構頗爲不同”,*張廣達上揭文第209頁。並列舉了一些造藏經、寺院的願文作爲例子。但就筆者所見,此書中與敦煌齋文最接近者當推卷十九《法義篇》及卷二十八的《啓福篇》和《悔罪篇》中所收的一系列用於齋會祈願的文本。然而正如張廣達所觀察到的,他們又與敦煌齋文有着體制化的不同。
在此先須就上文所提到的《廣弘明集》中諸文書的情況略作説明。*具體來説,本文所涉及的《廣弘明集》中的文書包括《南齊皇太子解講疏》、《竟陵王解講疏一首》、《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捨身願疏》、《南齊南郡王捨身疏》、《千僧會願文》、《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摩訶波若懺文》、《金剛波若懺文》、《勝天王般若懺文》、《妙法蓮華經懺文》、《金光明懺文》、《大通方廣懺文》、《虚空藏普薩懺文》、《方等陀羅尼齋懺文》、《藥師齋懺文》、《娑羅齋懺文》,其中講經所用疏文由於涉及宣講法義被收入卷十九《法義篇》,見《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52册,第232頁上—232頁下。其他文本則收入卷二十八《啓福篇》和《悔罪篇》,散見於《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52册,第323頁上—334頁下。
古代乃至近現代,與儀式相關的知識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師徒間的傳授而非研究文獻來傳承。這種特點導致了相關術語隨着時代、地域、師承的不同而會有很大的差異。此外由於儀式本身是實踐性很强的活動,因此很多内容也並不需要一致而規範的名稱。所以儀式文獻中存在嚴重的同名異指、異名同指的現象,是相關研究中必須直面的問題。
本文所關心的這些短文散見於《廣弘明集》卷十九和卷二十八中,其題名同樣也並不一致,無法簡單以文獻原題來確定討論範圍。因此本文擇取相關文書的標準,主要基於其齋會祈願文書的性質及與敦煌齋文格式與使用方法上的類似性。*《廣弘明集》中所收文書可能部分出自作者的文集,但無法確定道宣引用時是否對其題名有所改動。南北朝文集中儀式文書題名似乎也有一定隨意性。如後文將會提到的《周趙王集》即是如此。其中性質相同的一組文書雖大多題“序”,但亦有題“唱禮文”者。且題序的文書也並不遵循相同的命名方式,有的以使用場合而稱《中夜序》,有的以齋會性質稱《藥師齋序》,等等。因此這些作品雖然可能出自文集而並非由儀式的操作者命名,但其題名仍然僅具參考價值,無法作爲確定文書性質的最終依據。
本文中所説的齋會祈願文書,如其字面就是指在齋供法會上使用的有祈願内容的文書(包括範本和實用文本)。敦煌所存齋會祈願文書有多種類型(如啓請文、結願迴向文等),其格式與在儀式上的使用方法各有不同。學界習稱爲齋文者主要是指其中的一種特定類型。這類文書以敦煌遺書中的各種亡文、社邑文、二月八日文等的範文爲典型,其正文格式大致可分爲讚歎、齋會情況及祈願三個部分。*從敦煌的齋文材料中可以知道當時人有不同的分段方法,如“號頭”、“歎德”、“齋意”、“道場”、“莊嚴”的所謂五段式等。然而正如王三慶在《敦煌文獻齋願文體的源流與結構》一文中所論,古人的各種範文和論述中會有不同的分段方式,但實際寫作還需要參考齋主的意願與實際情況來定,不會完全拘泥於成規。上文所述(除去頭尾格式)分爲三段的作法則是希望取各種資料中的公約數。雖然可能有些粗略,但大致已足以表現其文體的特徵。相似的三段式分法可參見前揭《根據P.2547號寫本對〈齋琬文〉的復原與斷代》一文。太史文在《試論齋文的表演性》中嘗試將此類文本分爲七個部分。這種區分方法非常細緻,但是似乎又太具有針對性。當涉及更長期的演變時無法兼顧寫作風格與典範的變化。此外王三慶上揭文中還援引了《玉澤不渴鈔》中的十番分别,同樣是非常具有針對性的細緻分段,也可參看。從歷史上説,它與後代佛教科儀中歎佛宣疏的節次有顯然的聯繫,是作爲一會或一節之大綱在法會上宣讀的文書。*關於“齋文”的定義學界似乎仍有一些異見。其中筆者較爲讚同的是郝春文: 《關於敦煌寫本齋文的幾個問題》一文中的論述。他從兩個方面對齋文進行了定義,一方面是儀式中的運用,即提出“齋文是在佛教徒組織的齋會上宣讀的開場白”;另一方面則是從寫作風格上進行了把握。這樣的定義已經相當周到,也能夠符合時人對“齋文”一詞的使用,因此上文基本遵循了這一定義方式。然而隨着研究的深入,或許還可在此基礎上進行補充和細化。關於寫作風格上文注中已經有所説明。就其儀式中的使用情況,正如郝春文所指出,齋文是齋會(或者大型儀式中相對獨立節次)開場所要宣讀的一道文書。然而啓請文等文書同樣符合這一定義,因此仍可再作進一步的限定。即如下文所會説明,筆者認爲齋文是指在齋會近開始處歎佛呪願節次中所宣讀的以齋會主持者角度寫作的祈願文書。又,如同郝春文上揭文中所指出,佛堂文、畫像文等文書類型與齋文的關係非常微妙。《齋琬文》等文集往往會收入這些文書,但其寫作風格及在儀式中的運用卻並不完全與典型的齋文相同,並且有些文書中也有將其作爲一個獨立類型敍述的傾向。因此本文將此類文書暫時排除在討論範圍之外,希望將來有機會專文討論。
這裏尤其須要注意的是“讚歎”的段落。這一段落的源頭當可追溯到印度讚歎禮敬的儀式傳統,而與翻譯經典中讚歎佛德的韻文和散文具有類似的性質。如《齋琬文·序》中自稱爲《歎佛文》便可看到其中的傳承脈絡。*王三慶認爲齋文和疏文中的讚歎段落源於漢代以降祭文或祝盟文中的讚神内容,對此筆者並不讚同。這些文書都是在宗教儀式中對神宣讀,兩者之間的互相影響確實很值得作進一步探討。但是在宗教儀式中稱讚神靈並非是罕見的現象,由此無法得出兩者存在源流關係的結論。何況這兩類文書不僅寫作風格有很大不同,其背後更潛藏着非常不同的儀式傳統,其參與者、操作者以及儀式過程也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同樣是讚,在儀式中的意義卻完全不同。從儀式總體來看,齋文和疏文中的讚歎内容作爲歎佛呪願的一部分,而與禮佛、遶佛等共同構成了對佛的禮敬。又如敦煌講經莊嚴文中常見的套話“以此開讚功德”所示,這種讚歎本身就被認爲是能夠帶來功德的行爲,是儀式得以生效的重要途徑之一。而這些儀式結構的産生又根植於印度的禮敬法傳統及功德思想,並非佛教傳入之前中土宗教所固有。在齋會中,這類文書所對應的儀式節次即歎佛呪願。*關於歎佛呪願的作法及其與齋文的關係,可參看侯沖: 《中國佛教儀式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第172—177頁。所謂歎佛呪願,就是讚歎佛德並祝願的儀式格式。*讚歎部分主要是讚佛、三寶等,也可以讚歎和宣揚與齋會目的有關的教法。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讚歎部分會以對國主的讚歎爲主,不過即使在與皇家有關的儀式中這種作法也並非常例。它往往出現在儀式的近開始處,有總括一齋意旨的意義。
這種歎佛並祈願的儀式結構不僅出現在齋供法會當中,也是寺院日常行道禮佛時不可或缺的環節。如《國清百録·敬禮法》爲隋代國清寺天台僧團日常所用儀軌(類似於現在的早晚課),其中行道(遶佛)後接歎佛呪願的節次,其組成先以“色如閻浮金”一偈歎佛,*歎佛可以用歌唄(梵音、梵)或口白(直音)的形式,其意旨相同。如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卷二稱如來條即是歎佛呪願的節次,其中即開二門,分别是梵讚(如來妙色身偈)與直讚。見《卍續藏》,東京: 國書刊行會,第74册,第382頁上—中。有些情況下梵讚和直讚的選擇與儀式類型也有對應關係。例如敦煌講經法會似乎普遍採用梵音莊嚴的形式(參見荒見泰始《敦煌“莊嚴文”初探——唐代佛教儀式上的表白及對敦煌變文的影響》),這屬於歎佛呪願作法之下的進一步分化,限於本文主題,不再就此進行細分。後接“歎佛功德。三界天龍皇國七廟師僧父母造寺檀越一切怨親等會真如共成佛果,上座當用智力自在説。”*《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46册,第794頁中。有趣的是這裏將歎佛梵稱爲“呪願”而將祝願施主的部分稱爲“歎佛功德”。雖然看來是顛倒的,但隋代似乎通行這樣的稱呼。如敦煌所存的《七階禮》系統的寫本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提法,參見汪娟: 《敦煌禮懺文研究》,臺北: 法鼓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19—120頁、第166頁。不過本文涉及相關内容時仍採用通常的理解,即將讚歎佛德的部分稱爲歎佛,將祝願施主的部分稱爲呪願。由於並無特定的齋主且儀式規模較小,寺院常行的禮拜僅對國家、父母、地方神等對象進行泛泛的呪願,依仗上座法師的“智力”隨意發揮不須寫作文書。在齋文文書中,歎佛的部分即對應了文書第一部分的讚歎(在敦煌遺書中也常稱爲號頭或號),因此相關的儀式作法歷代都有歎佛或歎願等稱呼。從儀式的角度上看,兩者具有結構上的共通性。因此號頭的部分雖然是正文三個部分中最程式化的内容,卻同時最有標誌性。
本文所涉及的《廣弘明集》中的諸文具有與齋文相類似的格式,其旨意同樣是爲了説明齋會的大致情況,並作祈願。在其正文部分的開頭也有讚歎的段落,寫作風格及内容都與齋文號頭並無二致。這一點顯示了這些文書與齋文一樣,和歎佛呪願的節次有密切的關係。這也爲我們將其與齋文進行比較提供了基礎。
《廣弘明集》所收的這些文書不僅題名不同,格式亦隨之有些變化。綜合這兩方面的差異,相關文書大體可分爲兩組。一組是悔罪篇所收諸懺文,另一組則是在法義篇和啓福篇所收各種題名並不一致的文書,包括題疏(如《竟陵王解講疏》)、願疏(如《捨身願疏》)*從内容來看實際是八關齋會所用疏文。和願文(如《千僧會願文》)者。其中,懺文類文書格式相對統一,*題懺文者中有江總所撰《群臣請陳武帝懺文》一首,實際爲贖身的願文,並無明顯懺悔之意,也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内容。此例也可再次證明這些文書的原題並不能作爲判斷其基本性質的依據。這在題疏、願文等的部分更加明顯。大多數首尾分别有齋主稽首和南三寶(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與“稽首敬禮常住三寶”的套語(如《摩訶波若懺文》),但也有些没有開頭的套語(如《方等陀羅尼齋懺文》)或首尾都套語皆闕(如《藥師齋懺文》)。這應當是引者有所省略。其正文則如前文所述可分爲三個部分。懺文以外的作品正文部分也是同樣的寫法,若有開頭套語也類似懺文類作品,但並不那麽整齊。如《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開頭爲“維年月朔日弟子皇太子諱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捨身願疏》則爲“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等等,幾乎各各不同。其結尾部分大多没有給出套語,惟《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有“謹疏”作爲結尾。
這兩組文書之間的區别,似乎可以有兩種假設。第一,南朝的大型懺會有不同的儀式作法,採用了與其他法會有所不同的文書格式。然而這一假設似乎不具有很强的説服力。從懺文類以外的作品來看,此類文書寫作當有一定自由發揮的空間。甚至有如沈約《捨身願疏》這樣特異而有鮮明個人風格的作品。*沈約此疏實際爲自己在天監八年(509)集衆行八關齋時所用疏文。與一般較爲程式化的疏文不同,沈約對一些人“招屈名僧寘之虚室,主人高卧取逸閑堂”的作法提出了批評,並且在本應作祈願的部分以“功德之言非所敢及”一語帶過。這兩個特異的段落,應該都是爲强調八關齋的修行意義而刻意爲之。然而懺文類文本雖然是出自梁陳兩代,格式與用詞卻出奇地整齊嚴格,反而有些不自然。就儀式性質而言,在懺文類中亦有《無礙會捨身懺文》爲施捨並設無礙會,《娑羅齋懺文》實際爲齋百僧並設無礙會,其所對應的儀式都不是金光明懺之類大型懺儀,而與非懺文類的《千僧會願文》亦接近。由此可見這些懺文所對應的儀式也並無絶對的排他性。從南朝佛教儀式普遍重視禮懺的情況來看,也可推測其懺文之名並不實指對應的儀式都是同一類的大型懺儀。因此筆者傾向於第二種可能,即這些文獻的統一性與文獻的來源有關。這些題名懺文的作品正文例都隱去姓名年月等具體事項,很可能是先被用作儀式文書範本集出,再由道宣轉引到《廣弘明集》中。出於實用的目的,收集者或許對其中文書的格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統一。
雖然上述文書格式並不完全相同,但將其與敦煌齋文比較,卻又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即這些文書都以齋主的視角寫作。*在此需要排除卷十九所收《竟陵王發講疏(並頌)》。發講疏與一般齋意文的重要區别在於要讚歎講經法師的功德。而這件講疏又極爲特殊,蕭子良在其中兼有講師與齋主的身份,因此寫作方面也有些特别之處,似乎是以作者沈約的口氣敍述。而同卷所收諸解講疏及《國清百録》所收《永陽王解講疏》的寫作方式與《廣弘明集》所收其他諸文相同。此外從敦煌遺書中的齋意文來看,講經法會開始時宣揚齋意的方法似乎也與一般齋會有所不同。這一點從其開頭部分齋主稽首和南的套語就可以看出。事實上,這些文書不少是由他人代筆,如《南齊南郡王捨身疏》是沈約所寫,但是在開頭仍以“弟子蕭王”名義禮佛僧。這顯示了文書敍述角度與文本實際作者並無關係,而是具有文體上的意義。
當然,這種敍述角度不僅體現在開頭的套語中,也表現在正文中。如懺文類中不少會以“弟子”如何如何開始説明齋會情況的段落,然後以第一人稱説明自己的情況。與之相對,敦煌的齋文除了有些亡文情況特殊之外,大都是以儀式主持者(導師)的角度敍述。*敦煌齋文中有些亡文會採用近乎齋主的語氣,敍述亡人之德以及齋主對其的感情。這樣的作法顯然有加强文書感染力的作用,或許也有照顧齋主感情的考慮,應當是較爲特殊的處理方式。其用來承上啓下,介紹齋主的套語如S.2832號“今晨某乙公所陳意者何?奉爲……”,Ф.263號“厥今坐前施主捧爐虔跪設齋所申意者”*這類説明齋主在宣讀齋文時捧爐而跪的套語在敦煌遺書中頗爲常見。這個儀式細節頗有趣味。宋代佛教科儀中宣疏節次齋主也採用捧爐跪聽的姿勢,某些文獻中將其稱爲跪爐。如宗賾《禪苑清規》云:“引施主行香竟,當筵跪爐,維那表歎宣開啓疏。”(《卍續藏》,東京: 國書刊行會,第63册,第538頁下)。這個細節也可佐證齋會中宣讀齋文的節次與宋代以降歎佛宣疏的傳承關係。都表現了這種寫作角度。同時敦煌齋文在介紹齋主時也有明顯的誇張傾向,這當也與其採用了儀式主持者角度寫作有密切關係。
從以上的考察似乎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即南朝時期以齋主角度書寫的文書在此後的數百年中演變成了以儀式主持者視角寫作的敦煌齋文類文書。但是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一個重要的反證是,趙宋以下佛教科儀中所用疏文實際都是由齋主提供,採用了齋主的視角進行敍述。如果認爲這兩類文本之間存在簡單的遞代關係,並且在8—10世紀佛教齋會中已經全面改用齋文類的文書,那宋代疏文這種“返祖”式的發展便難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更進一步檢索資料,可以發現這兩類不同敍述角度的文本曾經長期並存。爲了便於敍述,我們權將以齋主視角書寫並往往帶有齋主稽首和南諸賢聖套語的類型稱爲《廣弘明集》型文本(如後文所述,更合適的名稱是疏或疏文),而將以敦煌齋文爲代表以儀式主持者視角書寫並且不具有前述格套的文類稱爲敦煌齋文型文本。
在與《廣弘明集》所收南朝諸文大致相同的時期,其實已經存在着具有敦煌齋文型特徵的齋會祈願文書,其例可見於《聖武天皇宸翰雑集·周趙王集》。
《聖武天皇宸翰雑集》(以下簡稱《雜集》)是日本聖武天皇所抄撰的文集,現存本由光明皇后施入東大寺,抄寫年代爲天平三年(731)。此書抄録了一些久已亡佚的中國佛教著述,尤其包括了一些與齋文關係至爲緊密的内容,此前也已經頗爲學者所關注。*此書早年即引起過内藤湖南的注意,見内藤湖南: 《聖武天皇宸翰雜集跋》,《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東京: 筑摩書房,1997年,第24—26頁。最近則有如王曉平: 《晉唐願文與日本奈良時代的佛教文學》,《東北亞論壇》2003年第2期,第88—92頁;《日藏漢籍與敦煌文獻互讀的實踐——〈鏡中靈實集研究〉瑣論》,《藝術百家》2010年第4期,第183—188頁等就其中所收諸齋會祈願文與敦煌文獻作了專題性的考察,並就日本所發表的相關研究作了述評。同時王曉平先生還對此書進行了録文,見《日本正倉院藏〈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釋録》,《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104頁。其中《周趙王集》部分相對獨立當是從同一文獻(很可能是個人文集)中抄出,而其作者周趙王即北周趙王宇文招。因此這些文書的成立時間較《廣弘明集》所收齊梁諸文略晚,而與南陳諸文平行。*參見内藤湖南上揭文。
《周趙王集》收有《平常貴勝唱禮文》(一組四首)、《無常臨殯序》、《宿集序》、《藥師齋序》、《中夜序》、《兒生三日滿月序》六種(組)文,都與佛教儀式活動有關,格式也基本相同。以《平常貴勝唱禮文》第一首爲例,其體先以“夫”領起一段讚佛之文,再以“今日是諸弟子某甲”領起一段,讚歎施主並説明其在私宅齋僧之事,最後則以“願齋主乘斯福善”領起祈願。其三段的格式非常明確,且就讚歎施主的部分來看頗類敦煌齋文的體例。而從其套語、對施主的誇張讚歎以及“願施主”的祈願格式都可以看出是以儀式主持者的角度敍述。因此可以説這些文書符合敦煌齋文類文書的基本特徵。
在南北朝晚期到盛唐,兩類文書都被傳承了下來,並有所發展。關於這一時期的情況,我們可以舉出如下的例子:
屬於《廣弘明集》型者:
(1) 《國清百録》所收南陳《永陽王解講疏》*《國清百録》卷二,《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46册,第800頁中—下。
所謂解講及解講疏的情況涉及講經儀式擬另文再作探討。就此疏而言,其所敍功德爲“謹於今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並度人出家”及造像,實際是講經結束設齋度人所用的疏文。其開頭爲“菩薩戒弟子陳靜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寶幽顯冥空現前凡聖”,然後以“伏惟”領起歎佛文,再接齋會情況以及祈願内容。
(2) 《國清百録》所收《少主皇太子請戒疏》及《王受菩薩戒疏》*《國清百録》卷二,《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46册,第800頁上、803頁上—下。這兩道文書對應的儀式都是齋千僧並授菩薩戒。雖然授戒法事有一定特殊性,但如此兩例文書所示,向在家人授戒的儀式活動大都同時有齋僧内容,仍然具有齋會的儀式框架可歸入此類。因此請戒的疏文當亦會在法會中宣讀,但其主要齋意在於請戒而非一般的求福或度亡。
這是南朝末到隋初的兩件文書,其撰作時代非常接近,且性質基本相同。
《少主皇太子請戒疏》當是陳後主受菩薩戒所用文書,其後附牒文一件列出施物。正文中前兩部分與《廣弘明集》所收諸文大體相當,但最後無明顯的祈願部分較爲特殊。不過就請戒疏的性質來看,或許可以理解爲以請戒替代了一般的祈願。在性質相同的《王受菩薩戒疏》中有祈願的内容,可證明這一作法並非絶對。
《王受菩薩戒疏》爲楊廣受菩薩戒時所用的疏文,寫作時間爲開皇十一年。同樣附施物牒一件與之配套。其開頭的套語較爲繁複,不僅有稽首上啓,並有奉請諸聖證明之辭。*逐位奉請應當是在南北朝時期出現的儀式作法,在南北朝晚期到隋代已經成爲儀式中必不可少的程式。這一儀節的出現對於宣述齋意節次的位置及其寫作方式都有一定的影響,而形成了楊廣此疏的形式。但至少在隋唐時期它對文書正文的寫作並無太大影響。因此本文仍將其納入研究的範圍。關於奉請作法的出現,參見小林正美: 《天台智顗の懺法における“奉請三寶”について——道教の醮祭儀禮との關聯にお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991年第40卷第1號,第65—70頁;阿純章: 《天台智顗の懺法における奉請三寶の由來》,《天台學報》2006年第49期,第93—102頁。其後接“竊以”領起的歎佛文、齋會情況及祈願等三段内容。結尾爲“楊廣和南”。參考《少主皇太子請菩薩戒疏》,則其中請佛證明之辭也並非必須。*《國清百録》所收疏文較多,其中如《發願疏文》等極具參考價值。然而由於這些疏文有些並非用於齋會,有些則屬於造像、佛堂等類(如《發願疏文》乃發願修復石像所用疏文,未見建齋事宜),前此已將其排除在討論之外,故此處不作爲例證羅列。
(3) 聖武天皇《雜集》所收《鏡中釋靈實集》諸“齋文”
聖武天皇《雜集》中有一部分題《鏡中釋靈實集》。這位釋靈實情況不詳,但從内文與標題可以知道是唐開元時期活躍在越州的一位僧人。這些文例當是從其文集中抄入。其中包括了一系列有齋文、願文等題名的文書,是他爲齋會法事寫作的齋會祈願文。尤其是《爲人父母忌齋文》、《爲人父忌設齋文》、《爲人父母忌設齋文》、《爲人母祥文》、《爲人妻設齋文》、《爲人妻妊娠願文》、《爲人息神通舉及第設齋文》、《爲人息賽恩設齋文(並爲母慶造經成了)》等,題材、標題都與敦煌齋文類似,且涵蓋了各種目的的法會。其基本的格式是以“弟子某頓首稽首十方三寶”的套語開頭,後接以“恭惟”、“竊以”等詞領起歎佛之辭,接着説明齋會情況並祈願。大部分文書明確以齋主爲敍述者,結構與《廣弘明集》諸文相當。
此外處於相近時代可作參考的,還有空海《遍照發揮性靈集》中的文書。這些短文多是爲度亡的法會所作,但格式與題名並不完全統一。其中可明確判斷寫作角度者大多是以齋主口吻寫作,*如此書卷六《爲中納言大使願文》中以第一人稱敍齋主赴唐事,卷七《葛木參軍設先考齋願文》開頭爲“弟子葛木魚等歸命三寶”,卷八《三嶋大夫爲亡息女書寫供養法華經竟説表白文》則有“弟子正五位上三嶋真人助成歸命三寶”的開頭等,都可以肯定是以齋主視角寫作。然而其中亦有數首似乎是以法師視角寫作,如卷八《有人爲亡親修法事願文》以“今日檀主”領起説明齋會的段落,同卷《有人爲先師修法事願文》中歎亡人段落不用“亡師”而用“故禪尼厶甲”開頭。何以兩類文書雜陳其中難以完全了解,但由此亦可見兩種文書在8世紀並行於世的情況。關於這些文書,又參見王曉平《空海願文研究序説》,《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5—112頁。有一些(主要是題作表白文的一組以及其他題名的幾件)還保留了齋主上啓的格式套語。*表白一詞在五代以前的儀式文獻中尚不多見,《宋高僧傳·道氤傳》中提到了傳主行表白之事(《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50册,第734頁下)。敦煌遗书中有《唐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僧洪辯悟真等告身及贈悟真詩》提到“内道場表白”一職。《册府元龜》卷六一載清泰二年爲賜紫立條式,其中有表白一科。則唐末五代時表白已成爲官方的術語。宋代科儀文獻中的表白主要是指人,即歎佛宣疏的維那(導師)。總之,從唐宋以來表白一詞的用法及《性靈集》中表白文的格式等方面來看,唐代表白一詞大致就是指齋會中歎佛呪願之事,蓋取其對凡聖啓白之意。《性靈集》中表白文雖然有一定的個性,但似乎不是一種獨特的體裁。如下文所述《本朝文粹》中所收日本人所撰齋疏並無題表白文者,但其中不少與《性靈集》中的表白文格式相若。在《佛祖統紀》又收有虞世南還願設齋疏文一道,云出自法帖而系於貞觀八年。從内文來看這道文書確實是以齋主視角寫作。雖然所引内容並不完整,只包括了齋主情況和祈願兩個段落,但亦可作唐初疏文的一個例子。*《佛祖統紀》卷三九,《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49册,第364頁中。
屬於敦煌齋文型者如下幾種:
(1) 《法苑珠林·洗僧部》歎德文*《法苑珠林》卷三三,《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53册,第544頁上—下。
道世云本文的意旨爲“歎德”,可知此即是歎佛之文用於齋會上歎佛呪願節次。
這是一篇非常長大的齋會祈願文,從性質來説是特定地用於佛誕浴佛及僧並轉《温室洗浴衆僧經》法會的文書。此文可分爲前後兩段,在結構上頗爲特殊,下文我們會再分析。然而本文主體是以僧人角度寫作,其前後兩段歎佛之後分别有“如今此處摩訶施主某官”及“然今施主等……”的提示,與敦煌齋文的表現非常接近。從其内文來看,對施主頗多莊嚴,當非自讚之辭。
(2) 善導《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歎願文*《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卷下,《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47册,第437頁下—438頁上。
本書中僅有一處有歎願的内容,見於全書尾部。原文將其稱爲歎佛呪願。其格式先以“竊以”領起歎佛段,後以“然今清信弟子某甲等爾許多人”開始説明施主及法會的情況,最後爲祈願。
此書所記儀式性質較爲特殊,總體上可看作是轉經儀式的一種變體。然而從内文可知其使用場合是信徒結衆念佛已畢於私宅齋僧而舉行的法會,與前文所述解講文類似。
(3) 道氤開元十六年設齋讚願文(P.2547、P.3535、P.4027)*此文先有陳祚龍先生作過整理,最近王招國(定源)《敦煌本〈御注金剛般若經宣演〉の文獻學的研究》(東京: 大東出版社,2013年,第70—82頁)一書使用新發現的殘本做了進一步的復原與研究,可參看。
此文是道氤爲一行塔前建碑齋會而寫的文書,其敦煌本原題爲《敕爲大惠禪師建碑於塔所設齋讚願文》。此文以主持儀式的僧人而非齋主的角度寫作,也不具有齋主上啓等套語。其格式總體上仍可分爲三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説明齋會情況的部分出現了以“是日也”領起讚歎齋會盛況的段落,顯然對應了S.2832中“道場”段,故其體式已非常接近所謂五段式的文體。
(4) 《齋琬文》
《齋琬文》現在僅有敦煌遺書所存之殘本,是敦煌齋文研究的核心資料之一。綜合研究者的不同意見,其成書年代當爲8世紀中晚期。*關於《齋琬文》的寫作時代,上揭梅弘理、宋家鈺、王三慶的論文中都有所考辨,可參看。其序言中自題“歎佛文”,可見其主要收録對象是歎佛呪願所用文書。就可恢復的部分來看,其中大部分文例當亦是採用儀式主持者的角度書寫。
此外在空海《性靈集》中也有數則似乎屬於此一類型,參見上文注。
可備作參考的還有道教資料《三洞奉道科戒營始》轉經儀、中齋儀中的對應内容。*見《道藏》第24册,北京: 文物出版社,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756頁上—下、763中—764中。學界一般認爲此書成立於南梁到唐初之間,至遲到7世紀晚期已經爲王懸河所引用。關於《三洞奉道科戒營始》的成立及學界相關討論,可參見孫齊《唐前期道觀研究》,濟南: 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第18—19頁。其中,中齋儀(敦煌本作《午時齋儀》)將此節次明確稱爲“歎道功德”,這無疑是從歎佛節次借鑒而來的作法。其歎文的格式也具有三段的區分,寫作採用了法事主持者的視角,並且没有齋主上啓等套語。
這些文獻大體都撰於6—8世紀,由此可見兩種文本曾長期共存,並且都用於歎佛呪願的節次。且兩者使用的儀式類型似乎也没有嚴格的界限,均可用於度亡、祈福等各種齋會。那麽這兩種文獻在儀式中究竟如何使用呢?這恐怕還需要看一看更晚些的資料才能有所了解。
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及《五杉練若新學備用》所見齋疏與齋文
了解9世紀兩種不同類型文書使用情況的線索可見於圓仁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以下簡稱《行記》)。《行記》根據圓仁的所見記録了數種儀式活動的基本流程,是研究晚唐佛教儀式的重要資料。其中赤山院講經儀式中云“釋題目訖,維那師出來,於高座前讀申會興之由,及施主别名、所施物色。申訖,便以其狀轉與講師。講師把塵尾,一一申舉施主名獨自誓願。誓願訖,論義者論端舉問”。*圓仁著,小野勝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修訂校注,周一良審閲: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92頁。這個節次大致相當於敦煌講經中的説莊嚴段,*參見荒見上揭文。但與敦煌的講經莊嚴不同,此處是由講師(法師)和維那(導師)共同完成。其程序是先由維那讀狀,再由講師“誓願”。誓願這個詞較爲模糊,但關於其他儀式的記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意義。如承和五年十一月廿四日條齋食法中云:“行香畢,先嘆佛,與本國咒願初嘆佛之文不殊矣。嘆佛之後,即披檀越先請設齋狀,次讀齋嘆之文。讀齋文了,唱唸釋迦牟尼佛。”*《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第71頁。此處採用了歎佛呪願的形式,隨後同樣連宣了兩道文書,包括“設齋狀”和“齋歎之文”。*這一點還可參見圓仁所記竹林寺齋禮佛式,文云“行香盡遍了表歎,先讀施主設供書,次表讚了,便唱‘一切普念’”(《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第272頁)根據上引兩則材料可以了解,其中設供書當即狀文,表讚則對應了齋文。這段記録也可以更進一步證明宣讀這兩道文書的儀式環節即是歎佛呪願。其中齋狀當即赤山院講經儀式中的狀文,而齋歎之文也即誓願所用文書。關於此處所用的狀文,如《行記》新羅一日講儀式中所記“釋經題目竟,有維那師披讀申事興所由。其狀中具載無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數。”*《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第192頁。綜合來看,是一道由施主提供的,包括了施主别名、所施物色、會興之由、無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數等多方面内容的祈願文。圓仁筆下的齋歎之文則應當就是齋文。在上引文中圓仁即已經明確用“齋文”一詞來指齋歎之文,而敦煌遺書中也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證齋文可稱歎齋文或歎佛文。如《齋琬文·序》將其所收文類稱爲“嘆佛文”,廣爲援引的S.2832中則將宣讀齋文的活動稱爲“歎齋”,P.3444則有《諸雜齋表歎文》的題名,等。根據圓仁所述,“唐國之風,每設齋時,飯食之外,别留料錢。當齋將盡,隨錢多少,僧衆僧數,等分與僧。但贈作齋文人,别增錢數。”則此道齋文無疑是由僧人所寫。
由此可見9世紀佛教中齋及講經的儀式中都有在歎佛段連宣兩道文書的作法,這兩道文書分别是由齋主所提供的齋狀與僧人所寫的齋文。在約一個世紀之後成書的《五杉集》卷下,更進一步給出了當時兩類文書的文例,並證明這種作法可用於度亡、還願等各種各樣的齋會。
《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三卷爲南唐僧應之所撰,現存有駒澤大學藏朝鮮天順六年(1462)刊本一件,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關於《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參見王三慶《敦煌文獻齋願文體的源流與結構》一文中的介紹。其中卷下收有一系列齋會祈願文例,多是以兩件文書爲一組,分别名爲“(某某)疏”與“齋文”。在此略舉其中《爲亡妻齋疏》及配套的《齋文》格式如下:
爲 亡 妻 齋 疏
右稽首三身調禦十地聖人羅漢一切聖衆,咸廻慈證,俯察哀誠,所申意者,伏惟亡妻……某七今晨,是以敬敞軒庭,特開法會……當願便承佛記,永脱塵機……伏請表白。謹疏。
齋 文
恭聞楓葉早凋,露珠易墜……即日某人令室云亡攸經某七,追悼去識,有兹會焉。伏惟某氏……伏願身抛有漏,法悟無生,速歸覩史之天,永絶閻浮之想。*《五杉集》中所列疏文、齋文的格式與同類的敦煌文書有些顯著的不同,頗可進一步研究。例如在其中並不見所謂道場段。可見這個段落雖然在道氤撰寫齋文的開元年間即已存在,但長期以來並非必須的構件。此外“所申意者”的套語在敦煌的疏文與齋文中都可以看到,但在《五杉集》中僅見於疏文。
其中齋文的部分顯然與敦煌遺書中的齋文相類。雖然有些文書的表述很模糊,但如上揭例中“即日某人令室”以及《還願疏子》所配齋文中“即某人之所設也,恭惟某人……”的表達都可以看出是採用了儀式主持者的角度敍述。而疏文的部分則顯然是用齋主的口吻上啓神佛。類似的疏文其實也見於敦煌遺書之中。*對於敦煌的疏文及圓仁《行記》中的相關記述,前賢學者已有過關注。如宋家鈺先生《佛教齋文源流與敦煌本〈齋文〉書的復原》即已提到圓仁所述狀文當與敦煌所存疏文對應,並猜測齋文因此而有願齋文等名。可惜對此没有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如P.2704即抄録了四道疏文。其中第一道作:
請大衆轉經一七日,設齋一千五百人供,度僧尼一七人。 紫盤龍綾襖子壹領,紅宫錦暖子壹領,大紫綾半臂壹領(其襖子于闐宰相换將),白獨窠綾袴壹腰。已上施入大衆。 布壹拾陸疋。施入一十六寺。 細緤壹疋。充經儭。 緤壹疋。充人事。
右件設齋、轉經、度僧、捨施,所申意者,先奉爲龍天八部,調瑞氣於五涼;梵釋四王,發祥風於一郡。當今聖主帝業長隆,三京息戰而投臻,五府輸誠而向化。大王受寵,台星永曜而長春;功播日新,福壽共延於海岳。天公主抱喜,日陳忠直之謀;夫人陳歡,永闡高風之訓。司空助治,紹倅職於龍沙。諸幼郎君,負良才而奉國。小娘子姊妹恒保寵榮。合宅宫人同霑餘慶。然後燉煌境内,千祥並降於王庭;蓮府域中,萬瑞咸來自現。東朝奉使,早拜天顔;于闐使人,往來無滯。今日大衆,親詣道場,渴仰慈門,幸希迴向。
長興四年(933)十月九日弟子河西歸義等軍節度使檢校令公大王曹議金謹疏*録文參北京圖書館敦煌吐魯番資料研究中心主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録》(三),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第85頁。在此請注意本文所討論的齋疏與另一類稱疏的文書——請疏的區别。請疏源於印度佛教請僧時施主提前到寺院邀請的制度,在中國文字化爲一道書信性質的文書。現存較早的例子如《國清百録》卷二所收《陳義同公沈君理請疏》,爲請開法華題的疏文,其全文如下“菩薩戒弟子吴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内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謹和南。”可見這種作法在南北朝時期應該已經成立。這類請疏在敦煌文獻中亦有留存,如P.3388及《新集雜别紙》中的《屈僧》文即爲其例。在形式上,請疏與齋疏最大區别在於啓白對象不同。請疏的對象是請來作法事和參與齋供的僧人,齋疏的啓白對象則是佛或三寶。
上引這道疏文中“所申意者”和“謹疏”的套語都與《五杉集》如出一轍,顯然是同一類的文書。由此也可以確證圓仁所謂的狀文就是疏文,其中“所施物色”的部分當如此疏之例列在文中前部。而《五杉集》中諸疏開始都有“右”字,實是指前文所省略的施物列表爲言。
如前所述,《廣弘明集》所收南朝祈願文與敦煌齋文的最大不同,在於其以齋主爲第一人稱的敍事角度。而晚唐五代佛教齋會中接連宣讀的兩道文書——疏文和齋文也正是分别以齋主和僧人的視角寫就。就細節而言,《廣弘明集》中所收諸文也頗有稱疏或願疏者,甚至也有以“謹疏”結尾的例子。由此似乎可以確認,《廣弘明集》中所收此類文書的性質即是疏文,而唐末五代的疏、狀則是由南朝疏文發展而來的。在南北朝到五代的時期,疏文都一直與齋文共存,並且至少在9到10世紀存在於齋會中接連宣讀這兩道文書的作法。然而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廣弘明集》中所收的文獻,其寫作風格實際上更接近於唐、五代的齋文而非疏文。以下筆者即希望梳理其中演變的過程以解釋其中的疑惑。
三、 齋疏的演變——從南朝到五代
筆者在别處曾經對南朝的唱導及導文進行過探討,其中提到宣讀《廣弘明集》中所收的齋意文書的工作是廣義唱導的一個部分,且這些文書即對應了《高僧傳·唱導》中所説的懺疏。同時我也注意到一點,即南朝時期宣述齋意的工作並非導師工作中可足稱道的一部分,以至於没有任何現存的南朝文獻在討論唱導時强調這一工作(這與入唐以後文獻的記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參見拙文《關於南朝的唱導》(待刊)。如果齋會中僅宣疏文的話,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爲這些文書原則上是由齋主提供,即使請人代寫也未必要請齋會的導師寫作。因此它自然不算是導師展現才智的領域。*有趣的是《周趙王集》中所收諸文雖然同非僧人手筆,但從中可以看到與南朝唱導作法更强烈的關涉,似乎可以想象主持儀式的導師參與此類文書寫作的可能性。但若當時已經存在了宣讀兩道文書的作法,則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了。此外,南朝留下的文獻資料相對較多,但卻全無齋文類的文本存世,也頗可怪。所以就南朝而言,我並不認爲存在着宣讀兩道文書的作法。*筆者推測在南朝齋會中並不使用齋文類文書,但在宣疏之後會有一些白語爲施主作祝願。只是這種祝願語既不需要特别寫作文書,也並不具有齋文的格式。在南朝道教靈寶科儀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結構。而根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所存《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録中關於呪願的部分所列出處也可推測,當時此一節次中僧人可以直接使用經中的簡單祝願語(《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55册,第91頁中)。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對於南北朝時期佛教齋會的具體操作仍有很多曖昧難明處,有待進一步研究加以釐清。
南朝最晚期到隋代的疏文有《國清百録》所存兩道請戒疏。這兩道疏文正文寫作與《廣弘明集》所收南朝諸文相類,但其後都附了一道牒文,詳細列舉施捨的物件。*張小艷先生提示,這種作法可能源自同時期書信中别紙的作法。同樣的情況在涉佛書信中也頗爲常見,如同書所收《皇太子弘〈淨名疏〉書》並非法事祈願文本,但其最後也附録了施物。《國清百録》中所收文書如此之類甚多。在《廣弘明集》中也可以看到《南齊皇太子解講疏》言明要施九十九物,《南齊南郡王捨身疏》提到施捨一百一十八物,沈約《捨身願疏》捨百十七物等,恐怕也與這兩道請戒疏文相同,另有羅列施物的附文。因此這種作法可能是沿襲了5世紀既已形成的舊規。*可作參考的是撰於5世紀的道教經典《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道藏》第5册,第895頁中—下。關於此經的撰作時間,請參看大淵忍爾著,劉波譯,王承文校: 《論古靈寶經》,《道家文化研究》第13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485—506頁)。此經最後列有授經辭,辭文云“辦信如法,條牒如左”,其後則别附列有信物的牒文。關於此辭與佛教齋會中所用文書的關係問題無法在此詳細説明,但可以看到文後附牒文羅列施物的作法似乎是南朝佛道教儀式通用的。
在此須略作説明的是,王三慶先生在分析疏文性質時引《文心雕龍·書記》之説,提出疏爲布列施物的文體,而認爲《國清百録》所收《發願疏文》等疏與五代以下所謂疏子是同名異實。*王三慶先生所列《發願疏文》等格式與齋會疏文同,不過並非用於齋會。如《發願疏文》是爲了修造佛像而寫的疏文,其使用方式與齋會疏文有别,故本文並未列入討論範圍。這當是受到五代以下文獻關於疏文記述的影響而産生的誤解。從《國清百録》所記兩道請戒疏的附文可以看到,當時羅列施物的文書爲與疏文配套的牒文而非疏文本身,且牒文的寫作與後代疏文迥異。道藏中存有諸多宋代道教齋疏,其中如《無上黄録大齋立成》所收黄籙齋六幕之疏都不列施物、功德,而是以陳願爲主。雖然這些疏文的性質與本文所討論的齋疏略有不同,但由此可見宋人概念中疏文的文體非以施物列表爲特徵。如果將南朝疏文與同時期世俗文書實例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其寫作體例與書信,尤其是涉佛的書信最爲接近。如疏文開頭常見的齋主稽首和南的格式即是當時給僧人致信時所用的標準格式。*相關書信之例甚多,藏内所存者如《廣弘明集》所收梁元帝《與蕭諮議等書》可爲例證。見《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52册,第304頁中—下。關於稽首和南三寶的格式,又請參見吴麗娱《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252—258頁。因此齋疏的稱呼當是源自“疏”作爲書信的意義。其最重要的特點,如上文所論,在於以齋主視角寫作的方式,是在齋會上表露齋主心意的文書。
《釋靈實集》中所收的諸文與《五杉集》一樣没有施物列表,然而其中《爲人妻妊娠文》云“謹捨前件,貼營功德,庶憑福善,保佑妊娠”,可見當時已經出現了在宣疏之前宣讀施物的作法,甚至兩者可能已經結合爲一道文書。然而其正文寫作方式與《廣弘明集》所收疏文並無二致。
由於《釋靈實集》中並未羅列齋文,也没有説明相關的儀式操作,由此無法了解當時兩類文書在齋會上的使用情況。要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則需要對《法苑珠林》中的歎德文進行分析。
此則文例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道世“恐邊遠道俗不閑法用,故略明法事以標厥致”。此“歎德文”可以分爲前後兩個部分。前部先歎佛、歎施主、歎法師(洗僧儀式中包括了講《温室洗浴衆僧經》的講經内容,故須歎師),然後羅列施主所供七物並各加讚歎。在讚歎七物之後有一個套話,云“七物並皆精備一心奉上,惟衆慈悲,爲歎祝願(别本作‘讚歎呪願念佛法僧’)。”在此套語之後則接有一段與齋文格式大致相同的段落。如果將這兩段分拆開來,則前部的格式頗有與疏文相類之處。如《五杉集》中疏文結尾多有“伏請表白”,上引敦煌的疏文則爲“幸希迴向”,與其連接兩個部分所用的套語非常接近。此外前部羅列施主所供浴僧七物的作法也與疏文羅列供物的作法相類。更有趣的敍述角度的問題。如前所述,這道歎德文總體上是以儀式主持者的角度書寫。然而前述的這段請衆祝願的文字卻似乎换用了施主的角度,從而令文意有所紊亂。由此可見此文書前段的原型應當是一則以齋主身份寫作的文書。
無論從此類文書發展的歷史,還是從文本自身的完整性來看,道世所列的這種歎德文都像是一種“湊合”出來的東西,並不那麽圓滿。似乎可以推斷,它是將疏文與齋文進行了整合,因此才出現敍述角度以及文體的錯雜。然而就唐晚期及五代的疏文與齋文來看,這種作法似乎並未成爲主流。無論如何,這則文例提示了在7世紀中期應該已經出現了宣疏文再宣齋文的作法,並且兩道文書之間已經出現與五代時期疏文結尾套語相類的格套。
前文已經提到,唐初齋文的格式與疏文的正文基本相同,其間的區别,一者在於敍述者角度的不同,二者則是疏文意在表達齋主心願而齋文則會敷衍對齋主的讚歎,兩者儀式作用有别。雖然有此不同,但在儀式上接連宣讀兩道形式相類的文書,似乎頗有疊床架屋之感。而這種儀式結構的出現,很可能是南北分裂結束後對雙方儀式操作進行整合的結果。從隋唐人士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有延續舊有傳統的慣性,另一方面則也有對其加以調和、重整的必要。道世所舉歎德文雖然是一個較爲特殊的例子,但從中也可以看到整合的傾向。然而在五代時期普遍流行的作法並非是像《法苑珠林》之例,將兩文整並爲一通以儀式主持者角度寫作的文書,而是仍然區分兩道文書。在寫作上,則爲避免重複逐漸將疏文簡化,同時加强齋文的寫作。
《釋靈實集》中所收疏文仍然有非常完整的三段結構。而根據圓仁的敍述可以知道,9世紀度亡齋會所用疏文仍然有“無常道理”之類的内容,應當就是讚歎的部分。同時還要詳列施物以及提供儀式需要的背景信息(亡逝時間等)。而與《釋靈實集》大致同時的道氤齋文則出現了“是日也”領起的所謂道場的段落,可以看到齋文寫作風格愈發趨向精緻。
《五杉集》的疏文多保留了南朝以來齋主稽首和南三寶的格套(或採用其變體的形式),有些文例中仍然有簡短的類似號頭的内容(如《亡妣用》疏文開頭爲“右伏聞,生育恩深,既垂言於古訓;懷擔德重,亦著在於真經”其下略歎亡人之德),但也已經出現了一些直陳其事而不以讚歎開頭的疏文(如上引《爲亡妻齋疏》)。甚至有些疏文連讚歎亡人功德(歎德)的部分亦加省略,形成了至爲簡單的結構(如《僧爲本師齋疏》全文爲“右謹設見前僧齋一中,奉爲先師和尚[某月]*“某月”,原文雙行寫之。《釋氏要覽》引用此則疏文作“某甲”,似可從。見《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54册,第309頁下。日用嚴報也,伏惟尊衆慈悲念誦,謹疏”)。敦煌所保存的疏文雖或有些文學化的敍述,但是在結構上基本對應於《五杉集》中簡化的類型,在施物之後簡單説明情況並作祈願。雖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到10世紀疏文結構逐漸簡化的傾向較爲普遍地存在。
由以上資料可見,疏文與齋文寫作格式分化的過程應該就發生在8世紀到10世紀之間。在此過程中,疏文格式和内容都趨於簡化和程式化。文學性較强的號頭部分日趨簡略,甚至最終消失。歎亡人功德的部分亦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構件。與之相對,齋文的寫作則被强化,形成了更爲複雜的格式。原本並不突出或可有可無的段落逐漸被分析出來,從而形成了更加細緻的體例。作爲這一變化的結果,五代時期疏文實際已經不被重視。如《五杉集》中很多文例都省略了疏文,甚至標註了“疏子隨意作”的注文。而敦煌遺書中則保存有大量齋文範例卻少有疏文範文。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也有其經濟上的動力。如上文所提到的,在晚唐時期存在着給寫作齋文的僧人别施料錢的作法,其所得較其他僧人多出十倍有餘。*五代時期敦煌的小型的齋會似可完全不用疏文。如S.4417述中齋儀便僅提到以一文表嘆施主,而這顯然是指齋文。不過這種作法當非完全通行。《五杉集》中云“小小齋筵”僧人只要先宣讀疏子,然後將其中“意語”(齋意)加入“通用莊嚴”中即可,不必另作齋文。兩種不同作法的出現或許與儀式操作的地域差異有關。
在日本的《本朝文粹》卷十三和卷十四中存有一些公元10世紀到11世紀的日本願文,從性質上説屬於疏文。其時代雖然較晚,但是保留了不同格式的疏文體例,從中頗可窺見疏文發展的過程。在此作爲補充略作説明。
這些文書有願文、諷誦文等兩種不同的題名,全都是以齋主角度寫作。就格式而言大體可分爲三種主要的類型,以下以a、b、c三型稱之。*這些文書雖可歸爲三種主要類型,但具體的寫法或多或少有些不同,甚至有些間於不同類型之間難以簡單歸類。例如《爲左大臣息女女御修卌九日願文》不在文前列舉施物類似a型,但其正文中卻並没有歎佛的内容。在此無法窮舉,只是作粗略的分類。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到實踐中疏文格式會根據具體情況有所變化。這與王三慶對齋文的觀察是一致的。
其a型可以大江朝綱《村上天皇爲母后卌九日御願文》*大曾根章介等校注: 《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27·本朝文粹》,東京: 巖波書店,1992年,第368—369頁。爲例,格式與《廣弘明集》所見南朝諸文相類,以“皇帝某諱稽首和南三寶境界”的套語開頭,正文第一部分爲歎佛,接着是齋會情況的説明,然後祈願。最後以“稽首和南敬白”結尾。
b型可以大江匡衡所撰《一條院卌九日御願文》*《本朝文粹》第367—368頁。這則疏文格式較爲完整故此處選作例子。然而其齋會情況説明的部分卻有一些特殊之處。其中詳細記述了在母親病重期間齋主計劃爲其舉行延壽法會,並列舉了所要施捨的物件。由於未到預定時間其母已經亡故,原計劃無法執行,便改爲舉行七七忌辰的追善法會並按計劃施捨。所施捨的物件及齋會的情況由於之前已經説明,所以後面有所省略。更爲一般的情況則可參見《爲二品長公主卌九日願文》(同書第369頁)。這件願文並没有齋主啓白的開頭格式,可能是在收入文集時有所省略。爲例,首先列施物“奉造金色釋迦牟尼如來像、同阿彌陀如來像、同彌勒菩薩像各一軆。右,先皇爲後世菩提,在生之日所造。奉寫金字《妙法蓮華經》一部八卷,《開》、《結》二經、《阿彌陀經》、《般若心經》各一卷。右,四十九日聖忌所奉寫。”其後以“以前佛經旨趣如此”的套語過渡,後接一三段式的段落,最後以“敬白”作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朝文粹》中的b型疏文多帶有明確的號頭部分,正可補充《釋靈實集》到《五杉集》之間的空白,從而完整地顯示出在施物加疏文正文的格式形成之後,號頭的部分逐漸簡化並最終完全消失的過程。
c型是其中題爲諷誦文的類型,*諷誦文是諷誦事所用文書。諷誦事是日本一種較爲獨特的法事,與一般的追善法會有别,而類似於轉經法會。自平安時代以來頗爲流行。在儀式中,諷誦文由所謂誦經導師誦讀。參見《望月佛教大辭典》第4415—4416頁諷誦條。以“(敬白)請諷誦事”開頭,再列施物,然後交代事項。如《在原氏爲亡息員外納言卌九日修諷誦文》*《本朝文粹》,第376頁。的事項部分爲“右,員外納言,受病之時,變風儀而脱俗累;臨終之日,落雲鬟而歸空王。仍擎此方包袍之具,捨彼圓照之庭。妾少後所天,獨流血淚於眼泉;老哭愛子,誰抽紫笋於雪林。人皆以短命爲歎,我獨以長壽爲憂。若有遄死,豈逢此悲。燈前裁縫之昔,曳龍尾之露,淚底染出之今,任鷲頭之風。魂而有靈,受此哀贈。所請如件。敬白。”雖然非常文學化地抒敍了亡子之慟,但從結構上看已經不具有三段的形式。
如果和中國的同類文書進行比較,可以發現a型基本與南朝時期疏文相類。b型施物加三段式正文的形式則接近《釋靈實集》所見唐初的形式及《五杉集》中仍保存疏文號頭的文例。c型則對應了《五杉集》中最爲簡約的類型。不過中日兩國所用的套語有些不同,如日本的b型疏文以“以前佛經旨趣如此”之類的套語作爲施物與疏文正文之間的過渡,前引《五杉集》疏文對應段落則仍然部分保留了南朝疏文的寫作模式,採用了“稽首三身調禦十地聖人羅漢一切聖衆咸廻慈證俯察哀誠,所申意者”*“所申意者”這個過渡套語在敦煌齋文中也非常常見,但是無法確定其最早是用於齋文還是疏文的寫作。作爲過渡,前引敦煌歸義軍時期疏文則採用“右件設齋、轉經、度僧、捨施,所申意者”之類與敦煌所存齋文較爲接近的套語過渡。此外日本的疏文結尾普遍採用“敬白”而非“謹疏”,不過在南朝的文獻中已經可以看到將“敬白”用於類似文書的例子。*“白”之作爲敬語,可參見吴麗娱《敦煌書儀與禮法》,第193頁。
比較這三種類型的文書,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南朝到唐代疏文使用的情況。例如比較a型和b型的文書可以發現,其中其實都列有施物,不過位置不同。a型將其列入正文第二段齋會説明的部分,且並不採取一事一行的格式。如《爲二品長公主卌九日願文》中云“奉書寫黄金字《妙法蓮華經》一部八卷,《開》、《結》經、《阿彌陀經》、《轉女成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便就法性寺敬奉供養”,以寫經爲功德。《村上天皇爲母后卌九日御願文》則列有造像、寫經兩類功德。與之相對,b型同樣也是以造像、寫經爲功德,不過列在文前。由此反觀中國的疏文例,如《釋靈實集·爲人母祥文》中也列了“又寫育王寶塔一區,造銅鐘一口”等功德,則可能它並不再别列施物,整體的情況類似此處a類。由此來看,唐初疏文寫作中這兩種不同做法可能也是並存的。*空海《性靈集》中諸文亦多在正文中部詳列寫經、畫像等功德,可作參考。
最爲難解的問題是c型的諷誦文與b型不僅格式不同,所列施物的種類也有所不同。b型所列都是畫像、寫經等功德,而c型則都是捐贈其他物品。然而這種作法似乎在中國並不通行。例如《淳化二年馬氏醜女回施疏》(S.86)、《清泰二年九月十四日比丘僧紹宗疏》(P.2697)等疏文中所列功德都是既有設齋轉經等事,也有施布、糧等物。而下文將會提到的《新集雜别紙》中的疏文例雖然是用於中齋的齋供,卻是只羅列誦經的品目和遍數。但同時,在敦煌遺書中也有一些以“請爲念誦”或“請爲懺念”結尾的短小疏文(如P.2837V所抄十四道疏文),其所施物色也都是各種雜物而不包括寫經、齋供等功德,形式與上述c型疏文頗爲類似。因此此類文書或是疏文中較爲獨特的一個亞型,其特色或許與其儀式使用有關。具體情況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 宋代歎佛宣疏作法的出現——代結語
上文我們探討了疏文從南朝到五代時期變化的軌迹,在此略作整理,並簡單説明一下其在宋代的演變。
疏文是一種以齋主身份啓諸凡聖説明齋會意圖並祈願的齋會應用文。它在南朝已經出現,在法會上由導師在歎佛呪願節次宣讀。同時在北方存在着以儀式主持者的角度敍述齋會意圖的所謂“齋序”。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尚難以完全釐清,但可能南北兩方有不同的儀式模式,即南方可能並没有與齋序相當的齋會應用文存在。
南朝疏文的寫作模式延續到了隋朝。從現存的南朝末及隋朝疏文來看,當時存在在疏文之外别附牒文羅列施物的作法。雖然並無實際的例子存世,但這種作法可能在5世紀就已經存在。
唐代初期很可能已經出現了在儀式上連宣疏文與齋文兩道文書的作法。這種作法顯然有些重複拖沓,因此也出現了將其進行整合的嘗試。然而以道世《法苑珠林》中所列歎德文爲代表的,將兩道文書合併爲一的作法顯然並不成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同時一些五代時期疏文格套也已經出現。
盛唐時期的疏文可以《釋靈實集》所收疏文爲代表。這一時期疏文可能已經與羅列施物的牒文合併爲一,不過疏文正文的寫作仍然沿襲舊規。這種情況在9—10世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根據圓仁的記述,當時歎佛呪願節次可能較普遍地宣讀兩道文書,且其中齋文的地位似乎較高,故作者可以得到别料的賞錢。這種情況無疑加强了齋文在儀式中的地位。*雖然齋文的作者可能同時也寫作疏文,但如圓仁《行記》所透露出來的,其重點在於齋文的部分。然而同時的疏文仍然有説“無常道理”的内容,也即包含有類似齋文號頭的歎佛詞。到南唐時期的《五杉集》中,雖然有些疏文仍然沿用了這種體例,但同時卻又出現了非常簡化的寫法,即在施物列表之後直陳齋意並簡單祈願。從其省略部分文例中疏文的作法也可以看出,當時對疏文的重視程度已經相當低。敦煌遺書中所存疏文格式則大多採用《五杉集》中簡化的作法,即在施物列表後直陳其事,不再包括號頭的部分。就具體的行文方式以及套語使用來看,即使與《五杉集》相當時期的敦煌疏文亦有些不同的表達,顯示了疏文寫作可能有地方性的差異。但是在對疏文進行簡化的方向上,兩者基本是一致的。同時在敦煌遺書中存有大量齋文的範本,也可以看出在晚唐五代時期儀式應用文書的寫作重點已經完全移向了齋文,疏文寫作則非常程式化了。
有趣的是,進入宋代以後疏文和齋文的的地位又出現了戲劇性的顛倒,實際上是以疏文爲主體對齋文和疏文進行整合,由此出現了所謂歎佛宣疏的節次*在文獻中,歎佛宣疏的節次也有白佛宣疏、讚歎宣疏等異名,從其作法來看都是源自歎佛呪願,故此處以歎佛宣疏稱之。取代了固有的歎佛呪願(宣讀疏文與齋文)。並且這種作法也對道教有所影響,由此成爲了中國宗教儀式中較爲通用的一種作法。*宋代佛教科儀中歎佛宣疏作法可能與道教科儀有密切的互動,但兩者形式又有相當的不同,各有其特色。關於道教科儀中相關作法的演變及其與佛教科儀的關係,擬另文再作討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宋代道教儀式中有一部分稱爲“疏文”的文書實際性質並非本文所討論的齋疏,而是以法師名義向神真啓奏的文書,在儀式中也往往用於和歎佛宣疏節次並無對應關係的節次之中。然而在宋代以後,齋疏的類型在道教科儀中得到了更爲廣泛的運用。例如在《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卷三五和卷三七所列疏式雖然格式又有所變化,但都是以齋主視角寫作列有施物的文體。見《藏外道書》第17册,第459頁上—466頁中、第511頁中—523頁中。限於篇幅,在此只能以宋代禪宗的情況爲主,説明其大概。*雖然宋代佛教科儀中普遍使用歎佛宣疏的作法,但具體安排又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有時又和宗派的傳統有關。例如天台系統的懺法以智顗的軌式爲基礎,而智顗所作懺文多在奉請後接歎佛呪願,因此遵式、仁岳等天台門人所作懺儀都會將歎佛宣疏節次安置在奉請之後,與禪宗的作法有所不同。此外宋代文獻中可以看到一些特定的疏文名稱,如開啓疏、滿散疏和功德疏等。從中可以了解到宋代大型儀式中可能會使用多道疏文,承擔略有不同的作用。這應當是五代末到宋代出現的新發展。
根據現存最早的清規文獻《禪苑清規》,叢林中有齋主設供供養粥飯時需要安排歎佛宣疏的節次,整個儀式的性質即成爲齋供儀式。其儀式情況如下:*較供早餐粥飯更爲正式的當是中齋的儀式,不過由於此書中齋部分介紹較爲簡略,所以此處以粥飯設供爲例進行説明。關於中齋的宣疏作法,參見同書卷六中筵齋條。《卍續藏》,東京: 國書刊行會,第63册,第539頁上。此外中齋部分提到齋會可不用宣疏,由維那唱梵後代白齋意。從操作者來看當視作與宣疏對應的變通作法。
行香罷,跪爐,次槌一下云:“(‘稽首薄伽梵,圓滿修多羅,大乘菩薩僧,功德難思議。’或云:‘佛法僧寶,最勝良田,凡所歸投,皆彰感應。’或云:‘水澂秋月現,懇禱福田生,唯有佛菩提,是真歸仗處。’葢槌邊不可誦長偈也。)今晨修設有疏,恭對雲堂,代伸宣表,伏惟慈證。”
宣疏罷云。上來文疏已具披宣,聖眼無私,諒垂昭鑒。仰憑尊衆念(良久云)“清淨法身”等。*《卍續藏》,東京: 國書刊行會,第63册,第525頁中。
鳴槌後先舉歎佛的偈子,然後以“今晨修設有疏”等白語過渡,宣讀疏文。這種作法也通用於其上堂、開堂的法事。禪宗的開堂、上堂的儀禮在有特定施主的情況下也有齋會的性質,其宣疏法的較早的例子如楊岐方會的語録中即有如下一段:
師於興化寺開堂,府主龍圖度疏與師。師纔接得,乃提起云:“大衆!府主龍圖駕部諸官盡爲爾諸人説第一義諦了也。諸人還知麽?若知,家國安寧,事同一家;若不知,曲勞僧正度與表白宣讀,且要天下人知。”表白宣疏了乃云:“今之日,賢侯霧擁海衆臨筵,最上上乘,請師敷演。”師云:“若是最上上乘,千聖側立,佛祖潛蹤。何故如此?爲諸人盡同古佛,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大家散去。若不散去,山僧謾爾諸人去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下略)”*《楊岐方會和尚語録·後住潭州云蓋山海會寺語録》,《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47册,第641頁上。
雖然歎佛宣疏前後的内容與前述供養粥飯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同樣都由維那宣疏,並且都安排在儀式的近開始處。*上堂、開堂法事中宣疏之前應當也會先有一節歎佛梵,不過這並非語録所要記的内容,而并入到宣疏部分不作交代了。在較晚的清規文獻《敕修百丈清規》中可以看到,聖誕、佛誕日上堂都會由維那“白佛宣疏”。所謂白佛,實即歎佛。如佛誕日白佛辭爲“一月在天,影涵衆水,一佛出世,各坐一華,白毫舒而三界明,甘露洒而四生潤”,即是讚佛偈子。見《敕修百丈清規》卷一,《大正藏》,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第48册,第1113頁中;同書卷二,第1115頁下。禪宗的上堂、開堂法事與講經儀式性質較爲接近,因此我們可以將其與圓仁所記唐代晚期講經儀式試作比較。可以看到,兩者都由導師(維那)宣疏,但是在圓仁所記講經法事中法師會接作誓願,宣讀齋文,而宋代禪宗的法事中法師僅僅是聊作數語以過渡到三捻香的節次。因此齋意的宣揚已經完全歸并到了宣疏的節次中。
除此之外,在禪宗叢林的體制中,此類書疏的寫作也已交由專人負責。在《禪苑清規》中,這一職務被稱爲書狀。其卷三書狀條云“書狀之職,主執山門書疏……院門大牓、齋會疏文,竝宜精心製撰,如法書寫。”*宗賾《禪苑清規》,《卍續藏》,東京: 國書刊行會,第63册,532頁上。在這一前提下,唐晚期給寫齋文僧“小費”的作法可能也已經不再流行。這種專人負責制度的産生也限制了疏文寫作的文學化,而使其進一步轉爲程式化的寫作。*這一階段大型科儀中也出現了各種其他文書,如榜、狀、移、牒等。其中不少應當是受到道教科儀影響而産生的。書狀一職的出現應當與這些複雜的文書類型的湧現有密切的關係。
在撰寫於1025年的《新集雜别紙》中列有一則設齋疏文,雖然有些“非典型”,但仍可以爲11世紀初佛教儀式所用疏文提供一個樣本。其全文如下:
具官,伏爲妻王氏疾病捐,起建道場,轉念功德數(具經遍數)
右件功德並以圓就,今因齋次請爲表因(白),謹疏。*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南京: 鳳凰出版社,1997年,第141頁、第153頁。
這則疏文範文是追善道場結束後設齋供僧時所用,性質類似於同時代道教齋後設醮所用醮詞或醮狀,都是在儀式最主要的段落結束後作爲下一個相對次要段落的綱領宣讀的文書。由於這種特殊的性質,此則文書在下啓次段法事之外還有承上説明齋會主體情況的作用。因此其文中所列功德實際爲之前道場中轉念遍數。同時或許也是因爲這種特殊的性質,《新集雜别紙》中這個範文結構非常簡單緊湊,並不具有一個大型儀式綱領性文書所當具有的形式與規模。但無論如何,我們仍可以看到一系列繼承自南北朝以下疏文寫作的特徵。包括它以齋主視角寫作的風格,文中羅列功德的作法,及其結尾處所使用的“請爲表白”的套話——這類套話在唐初的《法苑珠林》中既已存在並且廣泛見於五代的疏文文例中。由此也可以進一步確認宋代佛教齋會中所用的疏文確實源自南北朝以下疏文寫作的傳統。
在本文的最後,筆者想列入一則道藏中所存的南宋時期齋會疏文式作爲結尾,以供參考。
觀察此道疏文與《新集雜别紙》中的文樣可以發現兩者都會在功德列表之前以“伏爲”領起一段説明齋會的目的及情況。對應部分《新集雜别紙》所列文樣非常簡略,而道教《開經疏》則説明了整個黄籙齋醮的儀式内容,兩者結構相同。與之相應,在功德列表之後都不再重述齋會的具體程序或内容。雖然形式略有不同,但我們亦可在晚唐時期崔致遠所寫的齋疏(《天王院齋詞》及《爲故昭儀僕射齋詞》二首,見《桂苑筆耕集》之卷十五,其文顯然屬於齋疏並且尾亦題“謹疏”)中看到類似的作法。其中《天王院齋詞》似乎受到了道教齋醮詞文的强烈影響,在齋主銜名之下加入了一段對於齋會情況的説明再接啓白對象。因此這種格式變化似乎是在道教影響下於齋疏發生急劇變化的9—10世紀間出現,並且在宋代成爲主流。*關於同時期道教齋醮詞文的形式及其演變參見拙文《宋代齋醮青詞及其歷史》(待刊)。
與《新集雜别紙》極爲簡短的體式不同,這則《開經疏》的内容非常豐富,可能更接近大型法會中作爲綱領的疏文。尤其有趣的是在這則疏文中法事功德列表之後有一個短小的號頭性質的讚經文。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疏文與齋文整合之後疏文的寫作逐漸向較爲完整的形態回歸的過程。而在宋人文集中常見的齋會疏文右文,即是指這段文字。
這則疏文是《無上黄録大齋立成儀》卷十二所收《開經疏》:*宋代黄籙科儀中所用文書非常繁多,其中稱疏者亦有多道。此處所列的開經疏是正齋之前開啓轉經所用,也稱爲開啓疏。此處所涉轉經儀式雖然是黄籙齋的一部分,卻是作爲預備儀式較爲獨立的節次,而此疏則是統領此節儀式的大綱。故就其在開啓轉經部分的作用而言,大體與佛教科儀歎佛宣疏時所用疏文接近。此外《禪苑清規》卷六看藏經條記録了請僧人看經的儀式過程,其中所宣疏文也名爲《開啓疏》,應當是與道教開經疏更可直接對應的疏文類型(《卍續藏》,東京: 國書刊行會,第63册,538頁下)。這道道教疏文的原文見於《道藏》第9册,438頁中—439頁下。關於其具體使用的方法則請參看同書卷二五與卷三七的對應内容。
開 經 疏
大明國某布政使司某府州縣居具位臣姓某*道教科儀文書在編入明《道藏》時國名及住所的部分往往會經過更改,寫成大明國某布政使司云云。(原註: 普薦門云某人等,後並同)謹罄丹誠,上干洪造。臣伏爲(原註: 入齋意,至“醮用物儀”)具狀,投上清三洞法師某君門下,乞請道士一壇,就某處建立靈壇,關行齋法(原註: 再入齋意。正薦自“仰仗道慈”起,普薦自“所資功德”起,並至“福佑見存”)蒙於某月某日預告,先颺寶播,上聞齋意。取某月某日開啓齋壇(原註: 如未有定日,則云“尋别擇日,開啓齋壇”)。恭按玄科,宣揚祕範。正齋行道,三日九朝,請謝十方,告盟三界。滿散修設謝恩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仰祈霈澤,普祐沉淪。所有回獻三界聖真、十方仙宰,醮筵内外,一切威靈,並資悼亡魂,普薦幽爽。太上諸部真經、天尊睿號,謹預於某日爲始,開函看誦。今先具品目,敷奏如後。
一請道士看轉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幾卷
《太上洞玄靈寶昇玄消災護命妙經》幾卷
已上,並用普伸,回奉奏獻上三界十方聖真仙衆,醮筵主宰,侍衛威靈。
一請道士看轉
《太上靈寶天尊説救苦妙經》幾卷
已上,並用回奉,上獻係醮冥官主宰,一切威靈。
一請道士看轉(原註: 如别看經禮懺,則逐一别項填入)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幾卷
《太上洞玄靈寶九天自然生神章經》幾卷
《太上靈寶九真妙戒金籙九幽拔罪妙經》幾卷
《太上靈寶天尊説救苦妙經》幾卷
《元始天尊説生天得道經》幾卷
《元始靈書中篇》幾卷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寶號幾聲
太乙救苦天尊睿號幾聲
九幽拔罪天尊睿號幾聲
十方洞靈睿號幾聲
已上功德,並用資薦亡故某乙,超生仙界(原註: 普薦云“在會係薦一切魂儀,各超仙界”)
一請道士看轉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幾卷
《太上洞玄靈寶九天自然生神章經》幾卷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説救苦妙經》幾卷
《元始天尊説生天得道真經》幾卷
《元始靈書中篇》幾遍
某經某號(原註: 逐一子細開列)
已上功德並用資薦門中遠化,各超仙界(原註: 或有附薦名位,依此逐一開列)
一請道士看誦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幾卷
《太上洞玄靈寶九天自然生神章經》幾卷
《太上洞玄靈寶九真妙戒九幽拔罪妙經》幾卷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説救苦妙經》幾卷
《元始天尊説生天得道真經》幾卷
《元始靈書中篇》幾遍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寶號幾聲
太乙救苦天尊睿號幾聲
九幽拔罪天尊睿號幾聲
朱陵度命天尊睿號幾聲
已上功德,並用資薦六道四生、孤魂滯魄,各各離苦,同遂生成。
右恭以: 玄科奧典,寶藏靈文,爲濟苦之津梁,作拔亡之梯磴。敢憑勝妙,用薦沉迷。切念亡親某乙(原註: 如普薦,則以會首所薦姓名爲首,添入及在會係薦亡魂)等涉世塵緣,歸魂地遠。慮業緣之未盡,致仙化之無期。願仗真乘滲漉之功,普度苦海流吹之識。將宣寶範,先啓琅函。仰希洞鑒之聰,允納預聞之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疏,上奏以聞。謹疏。
太歲某年 月日具前官位臣姓名疏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
2016年7月,152— 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