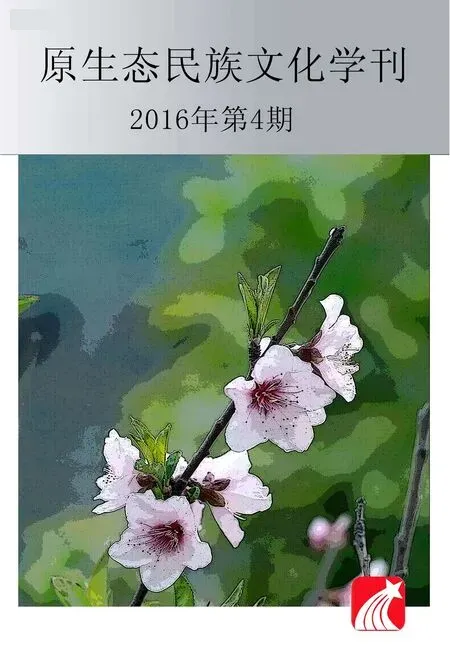关于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契点
李义辉
(中南大学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关于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契点
李义辉
(中南大学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民族的文化印记,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该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与人本特征决定了对其传承人扶助应为题中之关键。民间法缘起背景及鲜明特征,既与该文化遗产产生因由存有共性又对其传承人倾情相助,由此民间法在该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中的作用不应轻视甚或漠视。但它作为地方性知识,缺陷在所难免,对此应理性视之进而寻求其在参与该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理想进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其活态性、传承性、无形性、历史性等特征而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1]。它蕴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活动和审美观念,凝聚着该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展现了该民族充沛的文化创造力,是值得倍加珍惜的精神家园[2]。故而,在现今市场大潮等多方面的冲击之下,对其进行抢救和保护而求人类文明得以承传,一国一族文化身份得以认同即乃题中之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虽言及它部分需以“物”为精神产品载体,或讲究它与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种不同,但究其本质,它的精髓要义不在于“物”与“非物”的区分,而在于它的文化内涵和“活态传承”,而核心即在于该文化传承之人[3]。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固态存在,对其保护不存在传承人问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向度彰明,需依附黏着于人这一载体,该文化遗产的濒危,基本上即是说传承人的濒危,故对该文化遗产的保护重点和关键即是对该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民间文化传承人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就存活在这些杰出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渠道,而传承人即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4]。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传说、技艺、风俗、实践等囊括其中。依其不同,传承人认定困难有之,且需有所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达的中心意思乃民族民间文化[5],其烙刻着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影子,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生态下所培育、型塑的产物。加之,该文化传承人终归要生活在一定的村落、社区文化氛围中,接触、感受在周围的民风民俗下,故民间法于该文化遗产的发展及其传承人的生活样态的影响是不应小觑和忽视的。其实,民间法作为乡土规则,有地域性、自发性、非正式性等特征,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背景、构成理路有诸多重合,也自然而然地“内控”“预期”着包括传承人在内的诸多社区/村落民众的行为和操守,继而对传承该文化遗产也有天然“亲密性”。本文旨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切入点,探究民间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而求与国家法形成合力来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绵延不息。当然,对于民间法在此方面的不足与缺陷亦应斟酌、谨慎为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及其传承人的认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简明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岁月长河中,各个民族都曾或大或小地创造了优秀文明和灿烂文化。文化为人所创造,同时文化也成为了个体或一族群的生活需要和内在必需[6],也都带着异于他人的地方文化印记。梁治平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总是生活在一种文化氛围中,社会群体之中,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在无形地规范着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编织着这一人群的思维结构和知识体系。非物质文化培育着民族的认同情结,维系着人群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和谐团结,凝聚着人们在无形中的向心力。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精华部分,尤为值得人们珍惜、重视和传承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无形的文化财产,在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有着严格的定义,刘魁立将其简而言之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7]。另外,因人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即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适时创新。在保证人们具有认同感和历史感的同时,又促进了文化多样性、激发了人类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不以凝固之物为载体,但它也绝非有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它虽然有时也涉及物象的具体表现,但它的重心还是在于透过这一物质事件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传统,而归根结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载体乃是该文化传承之人,代表性传承人或群体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的属性是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可以说‘活态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它是当下人们正在实践着的生活方式,是活的文化事实”[8]。它反映着人群生活的当下样态,与人的行为运作可谓“如影随形”。有传承人,才有传承活动,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而非标本。“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居于核心概念地位,而担负这一职责使命的乃该文化传承之人。所谓“承”,乃承上之意,即对前人优秀成果的一种习得和接受;所谓“传”,乃启下之意,但这并非简单的原封不动、如“接力棒”式的承接,而是随事境变迁而有传承人实践才智、创新因子等参加其中,之后不断推广、承传下来的实践过程。那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认定
2008年,国家文化部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为:“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人。”201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传承人被认为须具有如下条件:(1)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在一定区域内被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3)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在学术领域,许多学者基于田野调查、规范分析等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了大同小异定义:苑利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9]。祈庆富认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且他/她应受相关法律保护[10];田文英,谢勇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应当通晓本地区或民族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内涵、形式、组织规程,熟练掌握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技艺,并大量掌握和保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原始文献和其他实物、资料[11]。周安平,龙冠中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乃是在特定民族或地域内,通晓一定技艺或占有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并愿意以自身努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人[3]。
笔者无意在列举相关学者对一事物定位以后,再拾遗补缺、扣扣减减地得出自己的定义,以此使得对一事物的界定越来越多,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却越来越混乱,事物没有明晰,倒反添更多的困惑。但如上观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质、特征可有如下把握:第一,传承人应代表着一种或几种非物质文化,或者掌握着某项技艺的核心内容,且该文化有着重要的民俗价值;第二,传承人在一定区域内为人认可,公信力较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产生带有地域色彩,承载该文化之人应在相关领域、地域内为人知晓,而如若要成为其传承人还应获得当地人群的认可,且公信力要强;第三,传承人愿意将该文化传承下去。国家对认定之后的传承人给予了精神、物质等方面的诸多支持,其目的即在于祖国优秀文化得以承继。权利义务需统一,传承人在获得、拥有相关权利后应履行相关的义务。其实,这一点既是传承人认定之前的要件之一,也是传承人被认定之后的义务操守。即如若一人不愿、不肯将其所掌握、承载的技艺等传给后人,那国家是不应将其认定为传承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传承,而人起中间桥梁作用,或其本身即有内而化之功用。该文化遗产活态属性,使得有学者认为和要求的“原汁原味”“一丝不变”传承变为不可能。它应当适应社会生态环境,而非社会生态环境为它而改变[11];社会,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社会,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情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文化传承之人亦非“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地在传递,而是有自己的心智、创造、创新加入其中。简言之,他/她把遗产接下,又在实践中加入智识。“从文化建构论出发,传承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创新,把一种文化纹丝不动地保留下来既不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事实,也不符合文化发展逻辑,文化总是在其遭遇的环境中朝着自己的方向现实地生长着”[8]。当然,传承人的创新非应“唯商业论”“唯市场论”,其创新的工夫也应把握一定的度,不能将该文化的本质丢失掉。
如前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起民间,产生于地方,是地方的区域文化表达。其传承载体又为人之本身,无论是代表性的个体传承人,还是群体性的一般传承人,所以该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人本性”,对传承人以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扶助、保护是极力避免该文化“无承无继”以至灭绝的重要举措。
传承人作为社会成员一分子,根据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研究,其大多深居、深处民间/草根、乡土社会,那么他就要受到民间法调整和规制。如果民间法营造的环境、氛围适宜、舒适其生活,继而其所承载的文化遗产就会绵延、接续甚至发扬光大,而反之则亦然。所以我们在极力倡导以国家法,无论公法或私法,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对于民间法可作用其间的力量、力度和深刻度是不应小觑的[12]。另外,民间法与该文化遗产的天生“亲和度”甚至本源同生、水乳交融状也使我们不应轻视甚或漠视民间规则。
二、民间法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有形适用
(一)民间法之百家争鸣
依照马克思的阶级学说观点,法紧随国家产生,国家是法得以产生的唯一主体,法具有国家性、强制性、统一性等特征,其他的社会规则体系只能算是“类法”“准法”,而不是法。当然,对于这样的解读和概括,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人们更愿意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立场/视角来看待法律,比如埃里希的“活法论”,霍贝尔的具有物质强制且为社会所承认的官吏/集团合法、科学使用其的社会规范论,“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区分论等。民间法作为学理概念,与国家法相对,惟其缘由,其界定就见仁见智,其代表学说如下:
1.梁治平的“知识传统说”。即从中国传统语汇出发,认为“民间”对应于“官府”,所以在国家法之外,存在着民间法。它是出自民间,生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时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的一种知识传统,且因有国家法类似功能,因而体现出法的意味[13]。
2.郑永流的“行为规则说”。他认为民间法即存在于国家法之外,自发或预设形成,由一定权力提供外在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则[14]。田成有将穿行于农村中活生生的礼仪、人情、习惯等称为中国式“民间法”,是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则[15]。另外还有朱苏力的“本土资源说”,谢晖的“地方知识普适性说”[16]以及范愉等人的“民间规范说”等。
综合各位老师和前辈们的观点,可以找出他们的共同所指以此来给出“民间法”的大致界定: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对,是特定地域的人们在长期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调整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解决各类纠纷,规制人们行为的且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它包括运行于特定人群的习惯、习俗、礼节、仪式、舆论、禁忌、村规民约、家法族规、行业规章、宗教戒律等。既然民间法作为地方性知识和生活经验总结,时间性、空间性、人群性等特色显现,对具有人本性、地域性、历史岁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有着天然契合的优势。
(二)观民间法特征透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所架构的是一套特定的社会秩序,以此给人们确定行为预期和进行有条不紊的生活。与国家法比较,民间法的差异性和特色就会显露无遗。
1.地域性。民间法是特定区域的人们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和传统的累积,相对于国家法追求的普适性、普遍性、统一性、抽象性、共性,它是分散的、零碎的、具体的、个性鲜明的,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杀猪杀尾巴,一个地方一种做法”。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塑造着人的性格和社区文化,民间法由此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由缘起。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存在样态和彰显的特色,比如陕北民歌多高亢,京剧内涵兼容并包,秦腔与川剧、桂剧多有不同,豫剧题材与黄梅戏内容多有出入,京津、江浙地区蕴含该文化遗产丰厚等,即知该文化遗产因所处各不同区域文化生态的不一而使得其形态各异和“存储”细密疏落有别,由此其产生、发展和特色“张扬”就与民间法起源有着相同或类同根基,进而用此法来对其保护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势和情真意切之感。
2.乡土性。“法律是地方性知识”。此处的地方,不仅是指空间地理方位,还指特色,即把对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17]。民间法植根于乡间,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人们反反复复地磨擦以此调适、适应、整合、认同了一套彼此都谙熟于心、心照不宣的本地化知识,透出“一方水土,一方人情”的韵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缘起民间、深植土地、“亲和”民众而乡土色彩性浓郁、“地气”充裕,比如马戏、杂技、道情、剪纸、舞蹈、歌谣、文学等都与本土文化紧密相关而在乡土民众中形成相似心理认知和情感共鸣继而受到人们的认可、喜爱和接受而乐于参与其中、支持该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本土乡土规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就“乡里乡亲”而其间指导和规制人们的自然的自发的无意识的“人心所向”的行为在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承接延续中更发挥重要作用。
3.非正式性。民间法乃自发形成,不同于国家法的理性建构和自觉创制,它是一个缓慢进化过程的产物,而在这进化过程中,更多的经验和知识被纳入其中,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人能完全知道[18]。民间法注重事后经验、智识的总结和归纳,遵循着向“后”看的传统,不善于前瞻和疾步向前。它没有完整、明确的条文体系,而以人们的口耳相传、身体力行来继承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由来,其初始的缘起也并非人们的“专门设计”而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实践的产物而方显“随机”和“随意”,且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地被冲刷并最终得以沉积和流传。该文化遗产的动态传承须依附于人体,即人殁则艺灭,人存则艺续,因此如若使该文化遗产代代相延承续,就应不断地培养和培植其新的传承人以保其“健在”和“健康”。而这与民间法的传续是同途同归且“结伴同行”的。另外,民间法的传承性也因其厚实、丰富的历史基础,自然、生态化的自我演进而无形实现该文化遗产的代代相传和有效发展[19]。
民间法虽没有国家法那“显性”“耀眼”的规则,但生活着的人们却默守和践行着其中的秩序,因为民间法的产生本是传统的积淀和智慧的彰显,它得到该社区人们内心的信仰、认同和服从,它有自身的一套“内控”法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各行各业中,“出没”于乡村与城市,表现各形各色,展示“五彩纷呈”,内控法则,即行业规章、家法族规、宗教教义、习俗惯例,明示或默示,有诸多方面和内容是有利于其保护、传承和发展的[20]。
三、民间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存其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天南海北、条件悬殊、风貌迥异,且该文化遗产的地缘性、“接地气性”,又因现今社会经济状况,使得许多传承人是久居民间且处境不甚乐观。传承人的生活状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可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质量和品质以至其能否存续问题。即如前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乃该文化传承之人。其保护模式大体分为如下三种*①具体内容可参见黄永林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研究——以湖北宜昌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刘德培和刘德方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第一,静态保护模式,即通过各种保护性措施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生命,以高科技为手段,通过录音、录像、数据存储等诸多方法来抢救该文化遗产。此模式大多针对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者实行,是一种“温室型”的保护;第二,活态保护模式,亦称整体性保护,即尊重传承人的传承习惯,保护文化传承的生态环境,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与当地人打成一片,采取的是融入自然的活态保护。这大多针对身体健康、能自食其力的传承人;第三,生产性保护模式,即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使得一成不变,原装不减的保护不切实际和不可能,而适应社会生态的文化创新才是其根本出路。当然,此种创新应尊重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与文化要义,且该文化本身具有或能转化为市场价值而有的放矢。当然,上述保护模式是一种简化型的理想情景,而现实情况肯定会复杂很多。
现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学界研究,或是商界支持及媒体报道等多是从国家正式规则角度来探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保护作用,而鲜少有人从民间法视角来探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保护。那民间法于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可能发挥的作用又在哪里呢?
(一)民间法扶持传承人物质生活
文化传承人一旦确定,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乃当务之急,定期生活补助显得尤为重要。传承人在才艺、技能、智识上多“超凡脱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但是对于日常琐事却多不得心应手,甚至有时缺少谋生的手段,他们凭借着聪明、技巧而勉强过活,物质匮乏、生活拮据。当然,传承人的生活补助多来自于政府提供,有时也可来自社会团体或个人捐助。但是,在“传承人”被确定以前,其生活乃至生存已面临威胁、陷入困境。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传承。如果一项文化遗产未被命名,那传承人自然也无法落定。但是,未被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就代表它不存在呢?当然不是。相反,它在历史上已存有了相当长的时间,只不过是在某个阶段以后,国家或其他机构才对它进行一个事实上的确认罢了。被确认之前,它的延续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传承人”,个体或群体,即为该文化自然传承的文化主体。人们之间,通过家传、师徒或社会整体传承等方式而使得该文化在代际之间被自然传递下来。不可否认,每一样文化的发展都经由个体创造,每一种文明的弘扬都离不开个别伟大人物的智慧卓著和高瞻远瞩。但是,这样一种文化的生成更源自于社会群体的集体造就,这样一种文明的发展更是本身就浸透着群体文化的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而乃地域整体创设的产物。传承人个体感受着集体的氛围,并受其影响;传承人群体创造了这样一种文化,并在潜移默化中将其成为一种生活需要和自己的日常必需,尽管有时它是如此平常,而让我们感觉日常(谢晖语)。而这种文化氛围、社群文化即是属于民间法的范畴,而其间的人们当然要受它的规制与调整;另一个是,这与上文谈到的静态保护模式的针对对象有些相像。如上所讲,并非传承人被确定之后,他/她才会生活艰难,或需要以本就是一种“温室型”的全方位保护。另,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其传承之人尤为众多,仅仅依靠国家方面的认定及后续保护,那于该文化遗产的保护并非时时奏效和唯一良方。故而,在国家法之外,我们还应关注社区、村落文化等民间法及其功用。
在平凡或危急的日子里,是什么确保传承人平安过活?是民间法主导下的周围人们对传承人的物质帮扶。大家生活在乡土民间,熟人特征明显,传承人多年岁较大,身体不佳者居多,生活条件不高不言而喻。当有生活困难时,子女孝顺应为常态,但子女很难长期固守,最主要和重要的是社区内人员帮助、体谅和关怀。比如这家可供给房屋,那家可提供口粮,有人提供创作材料,有人在医疗时看护等。如果传承人没有子女,那这样的关心和扶助是举足轻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人们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却倾心相助,为何?因为地缘使得大家彼此集聚而由生亲切,因为共享乡土规则使得人们在困境中懂得“可怜”他人,因为民间法浸染到人们的骨髓里而自然去帮衬自己的“二爷”“三叔”“四伯父”。人们的“各司其职”或者有村干部的组织或者是有脸面的人的倡导或者这本就是自发。社区民众为传承人提供物质给养,不管物质多少或优劣几何,以保“生态存活”,又为带去心灵慰藉而深深体现人们的“念念不忘”和“人文彰显”。继而传承人就想着去回报和感谢大家,而所采取的方式可能就极为独特,即用精美的工艺作品和优秀的演绎艺术来报答曾帮助自己的人们且“手耕不辍”。久而久之,传承人作品不但会受到社区民众的肯定、乐口相传和“名扬社外”,更会在“返璞归真”、文化多元的市场大潮中成为城里人、收藏爱好者的宠儿,这样就可极大的解决传承人的衣食担忧和充实其心灵愉悦。万事皆有缘,是邻里乡村人先前看似“无意”的举动帮助传承人渡过难关、“柳暗花明”间而传承人类文明和瑰宝中发挥了至为可贵和可敬的作用与价值。
(二)民间法呵护传承人精神生活
大多传承人多注重精神文化,而较看轻物质生活。生活条件的衣食无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传承困难。他们虽已进入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之年,但他们仍需精神鼓励和奖励,渴望人文关怀与问候。政府固然可以给工艺传承人“民间工艺大师”等称号,但传承人资格的取得一则是其技艺精湛,一则是得到社会认可,且“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传承人生活在乡土民间最重要的是获得本土民众的“谅解”、鼓励和打气,人们源源不断的称赞才是让传承人不懈奋斗和精益求精的动力。以湖北宜昌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为例,她因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而被采取以静态保护模式关照,生活条件虽然有了很大改观,但因离开了原先熟悉的乡土生活,使得她很难再有优秀的作品产生。林继富说:“离开了乡土情境和邻里社会的孙家香,口中那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故事渐渐少了,过去激情讲述故事的场面不再出现。”[21]这里指明了静态保护于传承人的一定弊端,而间接折射出了活态保护于传承人的有利影响,可以说,只要条件允许,让传承人适居于原有环境,拥有熟悉群众于该文化及他/她自身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当然,这其中应尊重传承人本人的意愿。
民间法的传统,即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脸面甚为重要而非简单的权利和义务之分,利益瓜葛纠缠,对传承人赞许、尊重者居多且热情流露,对传承人误解、不友好者有之但会刻意“藏着”“掖着”而礼节终有,这就使得人们对传承人行为包容、理解、敬重也好,误解、平淡也罢,但多是“善意”体贴呵护的。另,这里还涉及到一点内容,即传承人的认定工作。从理论上看,若严格遵循传承人的条件、程序来认定,传承人应受人尊敬和爱戴。但是实践中,存在着官方认定和民间认同的不一致情况[22]。官方认定的传承人至少在具有同样背景和从事该文化之人看来,前者是没有资格作为传承人的。如果其传承人的资格一直保留,享受着“技不如人”却待遇优裕的种种权利,那会挫败其他非官方传承人传承该文化的积极性。其实,这里就涉及了上面所提到的“群体性/团体性传承人”的重要性。而且,被认定的传承人也会知晓自己的“斤两”“底细”,也会明白同行或社区民众对他或好或歹的评价,这些道德、舆论等民间规则对该文化及他自身都会产生影响。
德国著名学者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曾经指出,渴望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这就是想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发生关系、逃避孤独的需求。感到完全的孤独会导致精神失常,正像身体的饥饿会导致死亡一样”[3]。传承人从事精神文化活动,但并不代表他们总是喜欢长期独处甚至与世隔绝,相反,他们渴望获得更多人情和适时问候。他们的人格应得以被尊重,他们不是在“游手好闲”和“特立独行”,他们在为新时代传承中华文明和保持文化多样性做贡献。我们对他们的事业应更多崇敬和敬仰。民间社区,生存空间本身狭小,信息不过个把小时而全村皆知,农闲时节走户串门、嬉笑玩耍着比比皆是,对传承人嘘寒问暖、思想交流自不待言,使其在生命岁月中知道邻里乡人懂得宽容、理解、惦记、扶持自身而倍受温暖,由此渐成文化自信和文明共识。是民间规则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也更抚慰着传承人的心坎使其拥有延续中华文化的自觉和使命而再接再厉、不辱重托[4]。
(三)民间法“附和”传承人艺术作品
对人最大的鼓励,莫过于对其成果的赏识和肯定。传承人有着较为宽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状态才能创作出精致的作品。但作品的优劣不是作者自身盖棺定论,而是民众/专家在雪亮眼睛目睹下发自内心的首肯来判断。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取法民间,问道生活”以及在民间法的耳濡目染下,使得民众对其有天生的好感和憧憬寄托。面世的新作品、怀世的旧作品都给民众带来浓郁情结而对其“附和”、赞扬。在乡村中,一段戏曲,搭戏台年年唱,老人们年年听,传唱者唱不厌,老人们也听不烦;一张纸剪纸,在传承人手中“脱俗”而成,形态各异,工艺精美,传东家送西家,人人喜气洋溢;一首首歌谣,人们儿时会心倾听,青年时节鼓足力气使之绕梁三日,中老年时仍会频频回忆,传承人更要将其与三光而同光;一曲曲舞蹈,人们相映成伴,三五成群,浸染祥和氛围,乐此不疲…这就是传承。其间蕴味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作品的喜爱、肯定和“趋之若鹜”。民间规则乃是特定空间的人们长期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的累积、总结而为民众内心遵从、服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色彩特征鲜明,与该规则产生和存在缘由类同,与该地区民众有天然情感认同,所以传承人作品在乡土规则导向下民众那里能够获得认可、附和与拥护是见怪不怪、水到渠成的。
(四)民间法并非时常“怜爱”传承人
刘作翔先生在“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中这样写道,我很清楚地知道,在“民间法”中存在着大量好的习俗、传统、惯例等等。并且,它们中有许多是形成法律的渊源之一。我同时也知道,作为一个研究者,不应该只讲一面,而不讲另一面。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提醒那些对“民间法”赞美者、赞誉者、歌颂者、粉饰者、倡导者们,在你们对“民间法”这一抽象概念和名称进行赞美、赞誉、歌颂、粉饰、倡导的同时,不要忘了在“民间法”中还有陋习存在。这些陋习带来的是悲惨、悲哀、伤害和死亡。也是想提醒诸公,不要把“民间法”想像的那么温馨、那么浪漫,在“民间法”中也有残忍、残酷、血腥、暴力、苦难和悲伤。我们的一些人士有时沉浸在一种虚幻的想像之中,把“民间法”想像的像田园牧歌一般那样温馨和美丽,经常会被这种虚幻的想像遮蔽了眼睛。而想像终究代替不了事实和现实[25]。西塞罗也说,人“最愚蠢的想法”就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全都是正义的。而且,他追问道:难道一个暴君制定的法律也是正义的?一部规定暴君无需通过审判就可任意处死他的公民的法律是正义的?显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国家实施的有害的法律法规,是不能称之为法律的。因为这种法规无异于一伙强盗在其集团内部所可能制定的规则[26]。他们发出的声音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和谨记。
在有关此次课题研究的调查与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少或基本上没有人主动从反面角度看待民间法于该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在大家的思维中,好像法律,不管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只要沾着法的边儿,就全部都是良善的。这可能与我国的法律宣传有关。其实,无论是国家成文法,还是民间规则中,都有些不成熟、不优良的法律。比如前者的收容教育、劳改制度、收容遣送、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后者的“亲上加亲”、以礼杀人、同态复仇等。这在人心中应该树立这样一种意识,而不能对所有法律,不假思索地点头应承、俯首称臣,遇到恶法时,不知反抗、不服从为何物。
民间法固然可以保护和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它同样可以破坏、摧毁和放逐后者而并非常常表现“仁慈”和“博爱”。传承人可能得不到政府的及时帮助,民间法下的人们也可能袖手旁观而让其成为“孤儿”而自生自灭;年纪青青或年岁较长的传承人整天“耍猴弄偶”“说唱蹦跳”而被人奚落、轻视、远离,加之市场经济冲击而使其放弃所载负艺术;民间法的一些错误观念在该文化遗产中沿袭,如“主男不主女,主内不主外”,传承人数限制,传承手艺的保留等;民间法的地域性使其对该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不为外界所知而对传承人的扶持也大为削减;民间法的自发性、非制度性使得其对传承人的“守护”并非总是那样的有效和有力并确保其供应传承人资源的可持续问题;乡土色彩的民间法会拒绝传承人对其作品进行合理、积极演化,甚至认为其是在“改弦易张”而阻碍其艺术创新等[27]。
由此在反对无视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民间法在其间有过也正在发生的缺陷和不足而应当寻求民间法和国家法在保护该文化遗产上的融合。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生命的记忆,一旦消解、失传将不复存在,对其进行极力保护和修复不言自明且事关重大须尤为上心。该文化遗产的不同存在形态表征其属性不一,对其传承人认定亦须作具体考量。其中,群体性传承人万不应忽视。其传承方式的独特性和人本性,决定了对传承人应拥有“礼敬”、“包容”、关怀之心。且理想观之,可有三种保护模式与此相关。民间法因其产生缘由及其具有乡土性、地域性、非正式性等特征而与该文化遗产有天生“紧密”和“亲密”状态,对其传承人的物质、精神生活、艺术作品也是倍加支持、理解与呵护。因此在倡导以国家法为主导来保护该文化遗产而风生水起、风起云涌时,民间法对其的有声或无声“关爱”之情是不应冷漠甚至视若无睹的。当然,民间法作为地方知识,有其固有缺陷而非时常以“善良”示人而可能给该文化遗产以致命创伤,对此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和慎重待之,以此寻求民间法参与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想进路。
[1] 赵亚敏,王云庆.档案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J].浙江档案,2006(8).
[2] 李荣启,唐 骅.新世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J]. 广西民族研究,2010(1).
[3] 祈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 西北民族研究,2006(3).
[4] 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47.
[5] 吴效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写在栏目前的话[J]. 河南社会科学,2007(1).
[6] 周安平,龙冠中.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J]. 知识产权,2010(5).
[7] 刘魁立.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河南社会科学, 2007(1).
[8] 普文芳,魏美仙.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及传承人意义[J]. 学术探索, 2014(4).
[9] 苑 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 探索与争鸣, 2007(7).
[10]田文英,谢 勇. 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法律地位[J].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5.
[11]黄永林.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研究——以湖北宜昌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刘德培和刘德方为例[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12]徐辉鸿.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公法与私法保护研究[J]. 政治与法律, 2008(2).
[13]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4]郑永流. 法的有效性与有效的法[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2(2).
[15]田成有. 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6]谢 晖. 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7]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M]//载梁治平. 法律的文化解释. 邓正来,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
[18]邓正来. 邓正来自选集[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9]高其才. 中国习惯法论[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0]邓江凌,吴安新. 论行业规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J]. 文化遗产, 2014(2).
[21]林继富. 民间叙述传统与故事传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2]刘晓春.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 思想战线, 2012(6).
[23]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125.
[24]萧 放.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其传承人[J]. 文化遗产, 2008(1).
[25]刘作翔. 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中的考察[J]. 浙江社会科学, 2003(4).
[26]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9.
[27]包哲钰,罗 彪. 论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性[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责任编辑:吴 平]
On the Folk law 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LI Yi-hui
(SchoolofLaw,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3,Chin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 nation’s culture, has various type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s duty-bound. The cultural heritage’s living normality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that its inheritance people should be the key of the protection. Folk law’s original background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are common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us its role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person should not be disregard. However, as a local knowledge, defect is inevitable, and we should be rational to seek its ideal route in involv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the Folk law; protection
2016-11-25
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项目编号: 2015zzts136 )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义辉(1990-),男,河南太康人,中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
D92
A
1674-621X(2016)04-006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