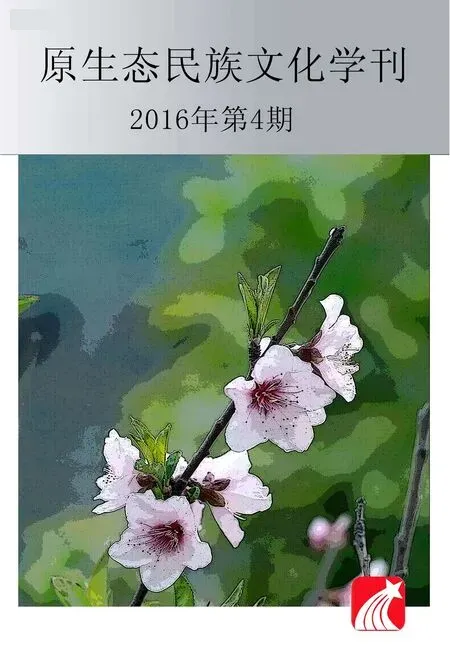亲密类型的跨越:基诺族性少数文化现象的考察
张 实,胡 敏
(1.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31;2.贵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亲密类型的跨越:基诺族性少数文化现象的考察
张 实1,胡 敏2
(1.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31;2.贵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基诺社会存在着“考卜拉”文化,其内容包括个人自由的性取向及性别选择,社会对此种选择的包容与尊重。这种独特的社会事实为性少数群体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并为性及性别的多元提供了一种实践的可能性。通过对传统基诺文化的梳理,以及当代基诺山性少数生活个案的观察,试图更深入地解读独特的基诺性少数文化,同时对主流社会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
基诺族;性少数;性别;个体;宽容
一、引言
性少数群体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他们长期以来都在接受主流文化的想象,而难以摆脱边缘化以及失语的状态。在西方文化中,随着公元4世纪基督教作为罗马宗教的建立,同性恋行为开始被罗马成文法界定为违法行为而不受保护。中世纪早期,所有同性性交行为都被认为是违背天性,欧洲的教会和一些国家制定了多种惩处同性恋的法律, 其中包括长期监禁和苦役, 甚至将同性恋用火刑、绞刑等方法处死。中国的传统社会基于儒家封建礼教传宗接代的目的,性少数人群也从未登上过大雅之堂。自20世纪以来,追求“本质”的医学科学体系也试图将这个群体也纳入讨论范围,它将性少数定义为偏于正常性行为的行为方式,又称性偏差,也被视为变态行为的一种。医学科学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由性别偏离和缺陷引起的病态,并利用其合法性介入了社会控制的领域,这样的话语一直活跃到1950年代。这样“罪行化”“病理化”的过往加深了大众对这个群体的误解,在当代,当同性恋又与艾滋病联系起来之后更是使其彻底的“污名化”。即便通过多年的抗争,性少数群体的地位趋于改善之后,关于他们的“出柜”仍需要承担很大来自于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很显然,在由异性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以同性恋为代表的性少数总是在引起人们的焦虑(尤其是在生殖方面),因此他们一直被排斥在外,并任由主流文化对其进行想象与建构。
因此,在异文化中找到一种性少数群体与性多数群体和谐共处的模式极具吸引力,这不仅对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增加性少数群体的福祉有着相当的作用。作为我国西南边境里人口较少的一支民族,基诺社会早已发现了性少数人群的存在,在杜玉亭教授所著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一书中可以窥见。在20世纪50年代,基诺族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公开的男性与男性居住在一起的现象,一个男性同时拥有几个同性情人。更为特别的是,同性情人与异性妻子之间还可以和平共处202。更进一步的是这样的现象在基诺族社会中并没有受到周围人群的歧视与排斥,而是存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和谐共融的社会现象。这样多边的亲密关系类型已经突破了以往的认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尤为难得的想象空间。本文将以基诺山中的两个村寨为调查点,对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试图对人类社会的性别文化进行更深一层次的理解,并为当今时代下性少数群体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种实践中的可能性,更为主流社会中性少数与性多数之间存在的区隔赋予反思意义。
二、基诺社会性少数群体存在的文化根基
基诺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府景洪市东北部的基诺山,绝大部分居住于基诺族乡,全乡共有常住人口3 863户人家,人口约1万4千多人,基诺族占全乡人口83.7%,其他人口包括少量汉族、哈尼族、傣族、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全乡辖7个村民委员会,46个村民小组。随着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新风对基诺村寨的席卷,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茶叶和橡胶的种植,而代替了传统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式的农业生产。笔者的田野调查主要在老寨和新寨两个自然村完成。新寨距离乡政府较近,60年代就完成了村落的建设,且位于两条道路主干道旁边,居民的生活较为方便。老寨则是较为古老的村落,交通相对闭塞,没有大量的人口流动,到目前还未每家每户都修通水泥路的村落。这样对比性的选择将有助于笔者对基诺族文化的独特性做比较全面的考察。
老寨历史上出现过非常有名的性少数者,在没有进行新的行政划分以前,七八百人的村落中生活着数十个性少数者,尚有白腊则和白腊耶健在。如今规模已经减小的村子中,50户居民有两对也就是四个性少数者;而新寨115户人之中也有两户是性少数,另外还出现了易性者,一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也被视为性少数。性少数现象在基诺族社会的存在与延续,体现了基诺文化对这样的个体选择和有别于异性恋婚恋方式的尊重与包容。这种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与基诺社会中关于婚恋观念、育儿方式、对性别的塑造等方面的内容紧密相联。
(一)以个体自主权为中心的婚恋传统
对基诺社会婚姻制度的研究,通常会将其与血缘制*①血缘制婚姻家庭是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于19世纪70年代依据遗留在夏威夷群岛的马来亲属制和群婚的残余推论出来的。这一家庭的典型形态是一代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姐妹,也互为夫妻。婚姻家庭联系在一起。杜玉亭对此做了认真的调查,他认为基诺族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前母系制的血缘婚遗风。氏族内男女虽然不能结婚,恋爱却不被阻止,包括同居。所以氏族内相互爱慕的一对青年就会在婚前互赠信物,等去世以后带入埋葬之地,同时还需要到祖先所在之地再成婚8。而时至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基诺社会中婚姻制度主要以一夫一妻制为主,恋爱模式也主要为一男一女间的异性恋。杜玉亭指出,基诺青年男女的恋爱过程主要分为3个阶段:用基诺语来说就是“巴漂”“巴宝”和“巴里”202。此三个恋爱的阶段,一环紧扣一环,是成婚之前需要经历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从恋爱到结婚,基诺男女的行为都是以爱情为中心,只要是已到成年,*②一般在十三、四岁,会举行成年礼。家庭内部不会过多对此事进行干涉。因此,杜玉亭也指出基诺族婚恋的五个特征在于:其一,婚姻恋爱自由,不由父母包办;其二,恋爱双方年龄相当;其三,恋爱的三个阶段反应了人类性爱的一般自然过程;其四,婚姻缔结的基础是性爱,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其他;其五,从恋爱到婚姻,双方主体有一系列相互考验的步骤,并有充分的自由选择余地202。基诺社会不会太重视“童贞”的说法,对恋爱期间的同居也有着较为宽容的态度,即便是经过同居最后没有结婚或者是离婚,男女双方也不会有类似被抛弃、被遗弃或者痛不欲生的感觉,更不会以此为“辱”,旁人也不会因此投来异样或者同情的目光。在他们看来,这是较为正常的意见事情,只要是两人已经不再有感情,不再情投意合,不在一起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在程序上,离婚也不如现代社会中那样复杂,“只要在一块喝喝酒,将结婚时作为结婚见证所收藏的三两三钱瓷碗片抛撒出门即可”。基诺男女都在平静的接受着对方的选择,并给对方最大的自由与权力,彰显了男女在性及婚恋方面的平等。正如牛江河所言:“在基诺族的人格观念中,个人属于个人自己,个人具有个人人格,个人是各自独立的,个人对自我有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恋爱自由自主,结婚自由自主,生育自由自主,离婚自由自主。”正是这样在血缘婚遗存的基础上,且强调自我,相对自由、独立与宽容的婚恋文化基调,造就了基诺族文化传统中对多元性别以及性少数群体宽容与理解的可能性。
(二)较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塑造
长期以来,基诺族居住于山林中,与外界少来往,靠打猎、挖野山药、摘棕榈树果为生,在农业生产方面刀耕火种是基诺传统社会的主要生计方式。由于居住地域有限,环境并不是十分恶劣,造成相对平衡均匀的男女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在传统基诺社会中,基于生计方式的社会分工并没有给男女在劳动分工上造成巨大的、不可弥补的差距。只有那些需要强体力的劳动只有男性参加,此外的各种生产劳动,比如现在的割取橡胶、采摘茶叶等等。这是基诺族人在日后社会性别的自由选择方面十分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并且提供了一种十分有利的空间。长老对家族婚姻的管理,虽也有禁止氏族内婚的习惯法,但又有这样一条变通的办法:一对相爱的同一血缘氏族的男女如欲结婚,只要举行一个认其他氏族的长者为干爹的办法,便可得到习惯法的许可,达到结婚的目的。可见,即便是主事的长老对婚姻的干涉力度和影响力也始终有限,不然在不允许氏族内通婚的部族,不会出现因氏族内通婚人群就产生出为此变通的习惯法。
家庭及社会的对个体所进行的文化濡化,从婴孩的出生便已经开始,对个人的性格习性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基诺族普遍较为团结,并且信奉自然,乐于天命,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展示出的民族性格较为温顺。男人和女人在出生之初除了生理器官有明显的区别外,其他地方并无不同。社会性别理论强调的就是人的性别认同是经由后天塑造而成,并非天生的。大部分社会都将人的性别限定在非男即女上,而且围绕着男女生理特征的不同制定了两套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规范。然而,在基诺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孩子是老天赐给的,无论男孩女孩,都是宝贝。且是神的意志,不可违抗”。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导致在男女差异的塑造上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刻意与强烈。与民族发展程度和经济情况相似的布朗族相比,在基诺族的传统教育理念中,男女性别平等的观念明显强于布朗族。作为一种教育的惯习,基诺族对人性的尊重,对当下基诺社会中人们的性别观念及性的实践产生着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三)独特的“考卜拉”性少数文化
在基诺族社会,性少数群体占有一定比例,且被单独划分为一类用基诺语称作“考卜拉”。“考”即“人”的意思,“卜拉”是“变掉”的意思8。在这里“考卜拉”的本意指的是除异性恋者以及拥有异性婚姻之外的一切人的总称,具体来看又包括了男性“考卜拉”(即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女性“考卜拉”(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又被称为“考忒”),没有结婚的女人,以及一些易性者,这3类较为特殊的人群,如果夸大其外延,则包括了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恋者,可以现代意义上的LGBT*①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LGBT”一词十分重视性倾向与性别认同文化多样性,除了狭义的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即性少数者。人群对应[10-2]。在《基诺族传统文化》中杜玉亭第一次对“考卜拉”进行了解释,并以生动的实例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基诺社会尚存的“考卜拉”。当时在上千人的基诺山上生活着数十个“考卜拉”,他认为基诺族社会同性之间的爱情是普遍的8。现今,在笔者调查的村寨中,当年杜玉亭书中所提到的者不勒和白腊约、乍什和法耶、白腊则和白腊约、白佳林和先卜拉等原有的“考卜拉”,只有白腊则和白腊约仍健在,他们算是老一代的“考卜拉”。
相比于其他社会,基诺族社会中性少数群体不仅在数量上人员较多,情感模式与关系比较复杂。上文提到的“白腊耶”和“白腊约”是一对至今已经70多岁且仍健在的一对女同性恋者。二人自成年礼后就同居,直到现在也未分开,一生从未与男性性接触。另有一对同性恋人,二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后来他们先后与异性结婚,但二人依然来往密切。在村社喜庆宴会时,两人并肩而坐,形如夫妻。如果二人相互串门,晚上住下时,妻子会主动给他们让出床位,他们同睡一床203。在基诺族传统社会中,同性恋爱与异性恋爱都是自由的,同性恋和异性恋同时享有正常的爱情权利,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由长老们在尊重当事人爱情权利的前提下出面调解,并且礼俗还在相当程度上是尊重和保护同性恋的[10-15]。时至今日,随着公路的修建以及村级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基诺山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更为方便,交往范围也更广泛。除原有的“考卜拉”之外,又有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考卜拉”发展出来,部分还组成了同性家庭,甚至出现了易性者等新形式的“考卜拉”[10-23]。可以说,“考卜拉”是基诺社会特有的,难得一见的以尊重性少数群体选择的文化现象。以下笔者对“考卜拉”文化的详细考察将从一对女同性恋的日常生活开始。
三、“考卜拉”的实践:一对基诺族性少数的日常生活
在美丽的基诺乡山寨里,“考卜拉”的故事却还在延续着。丽和君的故事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也是调查过程中接触最为频繁的两位“考卜拉”。笔者在初见她们时,她们与普通夫妻无异,君在两人居住的小院中刷牙,丽在喂鸡,屋子里的音响开得震天响。君有1.65 m左右的个头,精炼的短发,穿着粉白相间的男式条纹衬衣,外面还套着一件白绒背心,脚上一双人字拖,看上去颇似男人,但又比男人瘦小很多,声音也清脆。丽也有1.65 m,身穿黄色花纹短褂,下面试齐膝短裤,也着人字拖,但她皮肤黑黑的,声音也粗糙,身体明显发福,看上去比君要壮。她们之间情感的经历与故事,不仅可以让我们瞥见基诺社会中“考卜拉”群体的生活现状,是她们日常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更能让我们对基诺文化中固有的关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以及对待性少数群体的文化态度及惯习有更进一步的认知与了解。
(一)从“异性”到“同性”的叙事
丽与君相识于小的时候,她们的故事是从同性的友谊开始。据君说,最早认识丽是在丽七八岁时。当时君的哥哥在新寨做上门女婿,她不时会去哥哥家。一天,看到了扎着两个小辫子的丽和伙伴玩得很开心,但那时比较羞怯,*基诺族的小孩一般遇到生人人都会较为羞涩,与文化儒化有关。并没有主动去打招呼。1980年,君到新寨参加小学毕业考试,两人同在一个考场,从此二人相识。但考试完后,并未再联系,直到1981年两人重逢于老寨的露天电影场。从此二人相熟起来,并经常一起看电影,有时看完太晚丽就会在君家宿下,一来二去,两人之间几乎无话不谈。直到1982年,君与老寨生产队队长杰谈起了恋爱,据村民说,君采完茶叶后到杰那里称重量,君当时留着长头发、面容清秀、干活勤快、手脚利落、对人热情,同时杰也是一个活泼幽默的优秀男青年。4年后,也就是1986年,君与杰结婚了,当年便就有了一个女儿。在此期间,君与丽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人也会进行换工。*②1982年,基诺山开展“两山一地”,即把责任山、自留山、轮歇地承包到户,1984年土地正式承包落实到户。包产到户后,在劳动力的数量上就有所差别,劳动力少的人家活干不完,劳动力多的人家活干完了没事做,换工是一种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方法,大大解决了劳动力不平衡的情况。直到现在,换工依然是基诺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劳作形式。1988年,丽也与同村人结了婚,办酒席时君背着一岁多的女儿也去了。此后君和丽又各自生了儿子,因为各自都有了家庭,两人也就少来往了,走在路上会打招呼,从好朋友转化为普通朋友关系。
转折源于二人的原先所组成的异性家庭关系的恶化。在的家庭中,君和丽的家庭生活并不尽如人意。杰是村里的干部,开会与出差的机会很多,通常去就是好几天,家务活和地理的活都是君一个人干,同时君还要负担养育两个儿女的职责,日子过得比较辛。丽的丈夫性子温和,但是有些木讷,脾气也古怪,和丽闹别扭后,从不主动言和,总是丽主动和丈夫说话言和,丽带着两个儿子,拖着沉重的家庭负担,让丽患了风湿病,并从此落下了腿疼的毛病。1997年的除夕,丽回忆说:“过年那天我家杀猪,邀请君来我家过年,*③基诺山各家各户宰年猪,喝酒唱歌,就算是过年了。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喝了点酒,晚上君在我们家住下了,我老倌(“丈夫”的意思)也没说什么。我担心她一个人睡害怕,就和她一起睡。这天晚上,我们就发生了性关系。”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而生活再也不能平静了。虽然二人平日里依旧在与各自丈夫组成的异性家庭里进行生产与生活,但是交往又频繁起来。利用换工的机会,丽经常到君家里帮忙采茶叶和割胶,君有时也到丽家帮忙,两人同吃同睡,甚至会穿一样的衣服,也就是情侣装,遇到农闲,两人经常结伴出去游玩。
虽然原本的家庭还在维系中,但君的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缺失。2002年,在与丈夫杰发生了一点争执之后,君选择在第二天到乡政府民政所与丈夫办理了离婚。离婚时,他们的两个未成年的子女儿选择跟着杰一起生活,其他财产则均平均分配,主要有橡胶林、茶叶地,还有其他钱粮财物、牲畜等等。此后,君带着自己名下的各项财产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庭与妈妈、哥哥一起生活了一年,次年她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在附近建盖了属于自己的一室一厅落地式瓦房,持有个人户口簿,独立成为一户。盖房时,丽为君提供了一千元钱的资助,并亲自帮忙参加了建房过程。在君离婚后,丽与家庭的关系也并未得到改善,一边要带孩子一边要忙于农活的丽请求公婆照看小孩,但是遭到公婆的拒绝,丽与公婆的关系原本就不好,此次更为恶化,甚至升级为恶语相加,加上丈夫在其生病期间对她的不闻不问让丽对家庭的期望彻底化为乌有。经过几天的考虑,丽决定搬到君家,与君同住。同时几乎断绝了与原来家庭的所有联系。之后几个月里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由此,君与丽组成起了属于她们自己的“新家庭”。
(二)“新家庭”亲密关系的构建
自从住到一起之后,君和丽便共同精心打造起两人的居所。君和丽房子前面有个小院子,院子与水泥路之间用竹编的栅栏隔起来。院子里靠近水泥路边有一个安装了太阳能的小型卫生间,与卫生间一墙之隔的是矮小的猪圈,猪圈里没有猪,而是放着收橡胶用的塑料桶。房子右边的空地上有一个低矮的柴房,架子上堆满了干的柴火。院子左边的角落上有一个小小的鸡圈,几只小鸡仔在地上叽叽喳喳地觅食。房子后面是一个高的坡坎,坡坎上种了几十株李子树,开着细碎的白花,在雾气迷漫的早晨里安静得如小家碧玉一般。房子是一个平层,四周板壁是用编好的竹排、粗加工的长木板和破旧的门板围起来的,顶上铺着黑色的挂瓦。在屋子的左边,火塘上架着铁三角架,边上放着柴火,两口大铁锅靠在板壁上,角落周围的板壁被烟熏的黑黑的。饭桌左边有一个竹编的板壁把卧室与外厅隔了开来。
现今她们已经公开的以夫妇的名义在村子里生活,也形成了一致对外的关系。她们之间互相以基诺语中的“老公”与“老婆”相称,而且对于情感的经营自由她们的方式。在一起生活的四五年时间,她们对现在的生活还比较满意,最有意思的是两人还过起了纪念日。君说:“1997年2月6日是我们认识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我们要买酒杀鸡。去年喝了三件啤酒,杀了两只鸡,叫来几个人一起庆祝。”丽说:“刚来那段还是会想回家,有点后悔,但是又不敢回去,很尴尬,但是她对我太好了……现在不后悔了,过一天算一天,只要快乐就好。”相对来说,在两人的关系中,君显得比丽主动,也更认可这段关系,君对笔者说:“我现在觉得很满意,没有她(指丽)我一个人活不下去,我们相互依赖。”丽说:“说不上是依赖,我们互相扶持,走一步算一步,能过一天是一天,不想以后。”
当然有时也会磕磕绊绊。2008年1月30日,丽从君那里回去以后,好久没有回来,君急了。那时两人都有了手机,君就经常打电话发信息给丽,丽很少接电话和回信息。丽说:“那时我家在10公里外,她天天打电话给我,一打就哭,后来我就不接了。后来我又回到了君的家1次,她在家喝了三件啤酒,还打烂了一个板凳。”对于这次事件,君腼腆地笑着对笔者说:“她不回来,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天天喝酒,如果她不回来,我今天就不在了,或者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丽看了君一眼说:“她对我太好了,我舍不得丢下她一个人。”
(三)性别角色的分工与塑造
在君和丽的同居生活中,家庭劳动既有分工也有协作。在家庭劳动中,君承担了大部分重的劳动,如上山下山负责搬运、拿工具和重的东西,在家里修灯泡、厕所、杀鸡等,承担了一个家庭中丈夫的角色。相比之下,丽的劳动比较轻松,一般是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如扫地、刷碗、洗菜做饭等,同时也参与采茶、割胶和摘李子等劳动。平时家里的生活用品是两人一起去买的,并实行AA制。
君在穿着上有强烈的男装倾向。君喜欢条纹或者格子衬衫,喜欢扎腰带,风格很男性化。君说:“我不爱穿女人衣服,穿男的衬衣和裤子舒服,她买的衣服我不喜欢。”君的衣服大都是衬衣,腰间常扎着腰带,脚穿褐色运动鞋,嘴里常常吹着口哨,这是君的日常装扮。劳动时,君总是头戴红色鸭舌帽,身上穿着浅蓝色牛仔夹克,腰间扎着一把小砍刀或者是肩上扛着两把砍刀,打扮如当地的基诺族男子一般。丽背着一个小挎包,包里有水、烟、打火机之类的小物件,亦步亦趋地跟在君的后面。丽喜欢颜色鲜艳一点的、风格比较女性化的衣服。丽回应:“她买的衣服我也不喜欢,我喜欢好看的、颜色亮一点的。”不仅衣服风格不一样,就连两人用的手机款式也是大相径庭,君的手机是金黄色宽屏直板手机,这种手机在市面上基本上是男人在用。丽的手机是粉红色翻盖的,很是小巧可爱,丽很喜欢,老嘲笑君的手机难看。
相比之下丽比较懂得“保养”,会买一些化妆品,洗面奶、保养霜、唇膏之类的,价格不便宜。丽说:“年轻的时候喜欢用香水,现在也用,我喜欢闻这种味道。”相比之下,君就不用保养品和花露水之类的东西。家里买了花露水,丽的衣服上常有花露水的香味,洗澡的时候也要放上一些花露水。俩人换下来的衣服经常是丽洗,如果丽的身体不方便,君也会洗衣服。君和丽现已四十多岁,在生理上来说,还没有到性冲动完全消退的年龄,那么她们是怎么解决生理需要的。我曾问过她们这个问题,她们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丽还是说:“年轻的时候过(性生活),现在不过了,老了,不想了。”君笑了笑说:“我叫她去找老伴,她不去,她也叫我去找(老伴),我也不去,我们都不去,晚上看看电视,吹吹牛就睡觉了。”君还对笔者说:“没有她我睡不着,她不在,我就找她没有洗过的衣服穿着睡,和她睡在一起心里才踏实。”丽调侃道:“那是因为有我的味道。”
四、对基诺族性少数现象的分析与讨论
性少数群体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类型,因为他们的性别认同、性的取向等方面有异于社会中的主流行为,因此一直被视为异类,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但是我们惊奇的发现,基诺山基诺族社会中不但存在相当数量的性少数群体,而且人们对于性少数群体难得的宽容与理解的态度较为友好,社会对于个体性别的认定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们的性取向,同时对性别认同在不同时期的转变也有着相当的容忍度。相比之下,主流社会对于性别多元的认识是随着当代以酷儿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才得以开始,才对性别的二元分类进行反思,并逐渐意识到应该尊重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可以说,以同性恋为代表的基诺族“考卜拉”性少数文化具有一种优先性与天然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焕然一新的视角。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及社会现象,它颠覆了我们对性少数与性多数之间关系的认知,同时带给我们的是对主流社会中性、性别、家庭及情感更多的反思。
(一)基诺社会流动的性与性别
婚姻与性别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尤其对婚姻形式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出社会的组织的结构,也可以了解社会组成的基本方式。而性与性别作为婚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了解婚姻的重要窗口。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往对基诺族婚姻及性的讨论主要在血缘婚的范畴内得以重点关注,实际上,基诺族婚姻形态、性别及性关系研究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从现代性别及性研究的角度来讲,基诺社会近几十年来性少数群体的存在与生活的变迁,勾勒出的基诺族文化中性别及性文化的历史,尽管任何文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通过对基诺山性少数群体存在的讨论,可以用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基诺文化,并可以窥见传统基诺文化之上如何看待人及定义人这个最基本哲学问题的本源。
通常我们认为,人的生理性别一出生便得到确定,是不可更改的。但是通过君与丽的市场生活发现,在基诺社会中性别的认同,性行为的取向以及情感的方向并非如此的单一。在君未婚以前,君与丽已经为普通的同性好友,在基诺语中被称为“昌玛”。在君与杰结婚之后,君进入了社会主流的异性恋及婚姻阶段。婚姻存续的后几年中,在与丽发生性关系之后,君的状态从单一的性别及性取向阶段步入了多边的阶段。在这样的关系中,人的性别并非固定的非男即女,性行为的对象也未限定在一个人身上,并且跨越了单一性别的取向,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多边取向。直至君的婚姻破裂独居,丽也从原来的家庭出走,搬来与君同住。这时君与丽改变了之前多边性别及性取向的阶段,进入同性家庭组合阶段。并且基于主流社会中家庭的男女建构的规范与标准将性别角色与劳动分工进行了重新定义。在新的家庭中君明显具有男性特质,丽明显扮演女性角色,君表现得主动,丽表现的被动,即君为社会男性,丽为社会女性。这种根据情景来进行性别身份认同重新建构的过程,有明显的向社会中主流的异性恋进行学习的迹象。
这个过程清晰的展示了不同时期内,虽然人的生理性别自生下来就固定,但是人对性别的心理认同却是能够发生改变的。君与丽在性、情感及家庭上在不同时期的选择,证明了一个社会中性的多元与性别流动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及关于性别的自我认同并不是一一对应、不可转变,而是随着情感和认同的转变可以转变。存在于基诺社会的性少数群体和他们在性别和情感上的多元选择,挑战了社会性别的二元分类,也挑战了对性别刻板印象的严格划分。
(二)基诺社会的个体与自主性
在大部分的社会里,人们普遍认为,人存在的理由与目的是为了生育和延续后代,如果离开了生育与繁衍这一目的,任何的性形式与结合形式都是不正常、不道德的,甚至在有的社会还可能是罪恶的。因此,除了男女的结合或者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其他类型的结合与方式的行为都会被视为不正常,被社会所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为突出,古语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生育能力的男人和女人被人们嘲笑,他或她的缺陷在冲突中变成别人攻击的武器;不结婚的男人和女人被认为是异类,结婚而不愿生育子女的丁克家庭也备受争议。生育只限于异性之间,同性之爱与同性结合就是天理不容。
然而很显然,基诺社会性少数群体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模式。在婚恋选择方面,个人的意志选择决定了与谁恋爱,与谁结婚,谁能成为自己的性伴侣,并且这样的选择不是一成不变。当然,这样的结果与历史情境中的血缘婚姻的遗存不无关系,但是,这背后还是让我们看到对个体感情的强调几乎是基诺人恋爱与婚姻结合的唯一条件,爱情在文化中得到歌颂,被赋予最为神圣的地位。因此,在每一次的选择中,都能够看到个体情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君与丽的第一次婚姻中,均为异性恋为基础形成,结合是基于感情的基础做出的一种自愿的选择,而当感情不再,已经破裂,离婚就成为了各自重新考量日后生活的选择。面对第一次婚姻中留下的孩子们,君和丽没有因为他们受到羁绊,在感情出现变化无法维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离婚。离婚之后与孩子也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个体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彰显。在君与丽基于感情的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二人选择脱离家庭矛盾重重的原来家庭,主动选择了能够得到更多关心与爱护的新爱人,并居住到一起。她们的目的早已超越了传宗接代,而是二人情感一种自然升华状态。她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行为让她们组成了新的家庭,显然在这个家庭中是不以生育为目的的。
相比于主流社会中,性少数人群在面对性别身份认同及性取向方面的困扰,基诺社会的个体显得坦诚而大胆,基诺社会的恋爱与性对象也比较多元,自成年礼以后,就可以根据意愿做出自由的选择。在感情之中的时候,二人通过彼此的关爱与珍惜,维持了感情。而一旦不再有感情便能够较为理智的退出。这与基诺社会个体从小受到的文化儒化是难以分开的。基诺文化从小便给婴孩与儿童所灌输的勇敢、个性化的,以及基于一种男女平等及性相对自由的教育,使得他们在成年以后能够勇于选择。
(三)基诺社会的社会宽容度
君和丽身边的亲人与朋友对她们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尊重与包容的态度是大多数的声音。如丽的儿子上过高中,对母亲的做法是不赞同的。相比之下,君的女儿和儿子就比较宽容一些。君的儿子和其前夫以及前夫的现任妻子一起居住,离君的房子只有两百多米处。村大部分人家里安装了太阳能,君家里也安装了。而君的前夫家里没有安装太阳能,所以君的儿子就经常过来洗澡。2010年2月2日,君去女儿家过年,丽也同去。君的女儿不仅没有为难她们,而且还有说有笑。这说明,君的女儿对母亲的行为是能理解的。君的妹妹家在距君的房子30 m处,是君和丽出去玩耍和劳动的必经之地。君和丽路过的时候,看见君的妹妹及其家人都会互相打招呼和说笑,君的妹妹偶尔也会去君家里玩,而君的妹夫是丽的酒友。君离婚后住在娘家,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建造了房子,并把房子建在了离哥哥房子的20 m处,君和丽没事的时候会去君的哥哥家聊天或者打麻将,有时也会互相帮工。君的母亲傍晚的时候会偶尔到君家的院子里坐坐,晒晒太阳,抽抽旱烟。
在基诺族的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性少数的存在。君和丽的故事,大部分基诺山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在提起她们二人时,会用“同性恋”这个词,言辞上并没有侮辱性话语,而且大家都称习惯了。周围的邻居并没有因为君和丽的特殊身份就停止与她们的交往,据笔者的统计,在农闲时节,她们家平均每天客流量在5-13人左右,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有中年妇女和中年男性,还有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们聚在一起时会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包括打牌、喝酒、唱歌、跳舞等。这样看来,君和丽的感情是得到大多数亲人和村里人的宽容和理解。同时,她们也并不会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通常都以公开的形式存在,接受社会对她们的审视与检验。
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不同,基诺山人们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存在并没有那么的恐惧与反感,在他们的观念中虽然两个同性的人居住在一起不太寻常,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尊重是最重要的原则。这体现出在血缘婚姻的探讨范围之外,在婚恋方面基诺社会别样的发展方向。对性少数群体如此宽容与包容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性少数人群在社会中较为宽松的生存空间,由此造就了基诺社会性少数与性多数平等宽容、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人类学对不同文化中性少数现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在一开始人类学家接受了并未对男人、女人、同性恋和异性恋这样的普遍分类框架和概念进行过过多质疑[11]。直至90年代,基于后现代结构浪潮的酷儿理论兴起,将对同性恋的解构推向高潮,开始进行全面颠覆和开放式的探索。在这条道路上,人类学应该尽其所能为以同性恋为代表的性少数群体发出声音,为其正名,为他们的生存提供更为宽松、稳定的社会生存环境。同时应该进一步探索异文化中的性少数群体特征,为性少数与性多数的和谐共处提供更多的范例以及实践的可能性。基诺族性少数群体的存在并未引起强烈的关注度,一是源于性少数群体研究的敏感性,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中的性少数群体问题,很容易被曲解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其次,对于基诺族的研究,作为中国最后一个被承认的民族,且人数较少,对其独特身份的关注掩盖了性少数群体这样一个较为边缘的课题。
米德在《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中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没有文化压抑的青春期,萨摩亚的亲年男女少了,以此来证明青春期的存在是受社会教养方式及文化模式熏陶的结果,尤其是在美国,导致了青少年青春期的紧张压抑、情绪不稳定及拥有挫败感而变得叛逆的现象,由此激起了人们对另一种文化世界的想象。基诺社会中独特的“考卜拉”文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关注异文化中性少数人群生活的窗口,不仅对探讨酷儿理论的实际应用有着指导价值,同时基诺社会对待性少数较为宽容的社会事实,也给挣扎在主流社会的性少数群体提供了一种希望。这种希望是建立在对主流社会中的性多数与性少数的平等与和谐共处,以及性少数能够拥有像基诺社会一样的性别及性的自主权的想象。其实,基诺族社会这样独特的性少数现象及文化是基诺族的祖先及后代们在长期积极适应和改造环境以求繁衍和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知识的体现。是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相关和生活相关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独特性文化以及较为宽容的性少数文化体系。作为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基诺族中的性少数人群及文化的探讨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1]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371-378.
[2] 潘晓明,段晓慧.性学领域几个关注问题简析[J].中国性科学,2011(2).
[3] 富晓星.疾病、文化抑或其他?——同性恋研究的人类学视角[J].社会科学,2012(2).
[4] 赵万智.求“异”存“同”——北京男性“同性恋”人群文化的描述、理解和阐释[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13.
[5] 杜玉亭.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6] 牛江河.基诺族婚恋习俗的心理内涵[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6).
[7] 杜玉亭,阮芳赋.从基诺族的调查看近亲通婚之害[J].人口与经济,1981(5).
[8] 傅金芝,韩忠太,杨新旗.基诺族性格特征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1991(3).
[9] 毕天云.基诺族和布朗族在教育场域中性别平等观的实证研究[J].思想战线,2004(4).
[10]邹珍珍.在中间:基诺族“考卜拉”性少数文化现象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0.
[11]王 凯,沈海梅.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同性恋研究[J].中国性科学,2010(2).
[责任编辑:刘兴禄]
Across the Style of Intimacy:Inspection the Culture of Sexual Minorities in Jinuo Society
ZHANG Shi1,HU Ming2
(1.Yunnan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31;2.SchoolofHumanities,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01)
There is a kind of “Kao Bo-La” culture in Jinuo society, which includes individual’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choice, people’s tolerance and respect. This unique social facts provides a relaxed living space for sexual minorities, it also provides a practical possibility for the gender diversit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f traditional Jinuo culture and case study on Jinuo, this paper tried to give a deeper interpretation of this unique cultural of “Kao Bo-La” in Jinuo and make a reflection about social status of sexual minorities i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Jinuo; sexual minorities; gender; individual; tolerance
2016-11-22
张 实(1961-),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胡 敏(1986-),女,仡佬族,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G122
A
1674-621X(2016)04-01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