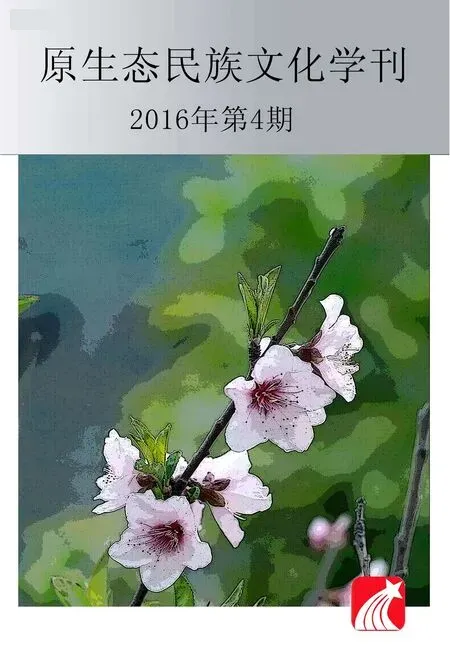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日本端午节“药猎”习俗形成探析
金 晶,陈兴秀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200241)
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日本端午节“药猎”习俗形成探析
金 晶,陈兴秀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200241)
“药猎”是日本端午文化的初始形态,指日本贵族采草药和猎取鹿茸的活动。“药猎”作为一种端午仪式,属于文化记忆的一种,它不是自行生成,而是目标极为明确的记忆政策努力和干预的结果。其“药”元素深受中国端午节采百草习俗和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反映了日本贵族渴求轻身、长寿的愿望。而“猎”元素则受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双重影响。对其的摄取直接反映了日本民族对尚武精神的偏重及皇族巩固王权统治的意图。由此可见,日本最初的端午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混合体。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可以用来分析日本端午文化“药猎”产生的原因与过程以及日本的文化记忆模式。
端午;药猎;文化记忆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范围极广的概念。与记忆直接相关的文献、文物,旨在进行或者促进记忆的形式和活动都可以被纳入到文化记忆的范畴,诸如仪式和出版普及文化传统的活动和过程等。文化的传承方式可分为“仪式性关联” 和“文本性关联”两大类别[1]。这一理论主要应用于解答各个文明、民族、宗教等传承、发展或者消亡的轨迹与原因,以及重构文化层面上各种元素的关联。本文借用该理论则欲探讨日本端午文化“药猎”产生的原因与过程以及日本独有的文化记忆模式。
在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文明圈中,端午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也分别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各自形成了丰富的节日文化和民俗活动。端午节的前人研究成果颇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学者对端午节的某些习俗进行解释,如《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所引《武陵竞渡略》一文,详细记载了龙舟的造法和端午风俗,可谓是研究端午节时最为详尽的古代文本资料。在探索端午起源的论著中最重要的是闻一多、江绍原、黄石的研究。抗战时期,闻一多在经过大量历史考证后,在《端午考》中指出端午节是古代吴越地域龙图腾阖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2]。进入现代,众多学者则对端午节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关童在《端午新考》中从“恶日”和“续命”两个角度推导出端午节的原型是“祈求生育”和“成人节”并举的节日[3]。随着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定名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的研究视角已经外延至东亚乃至全球,为端午节的话题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可能。刘晓峰在《端午节与东亚地域文化整合——以端午节获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中分别考察了端午节对古代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琉球和越南等地区的影响与传播情况,并指出这一影响与传播,是发生在以中国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内部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古代东亚地区文化共享性的积极结果[4]。
通过对上述前人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日本、韩国的端午文化在节日起源和内容上与中国端午节既有相通之处,也兼具其本土化色彩。其中,“药猎”活动在中日韩三国的“异化”过程折射出的文化记忆特征尤其值得关注。所谓“药猎”是指端午节刚刚传入日本时宫廷举行的采草药、摘鹿茸的活动,是日本端午文化的初始形态。该仪式虽来源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端午节文化,亦异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端午节文化,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是目前学界对此课题的研究关注甚少,所以本论文以此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从传承与变迁的关系中探讨端午文化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传播与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日本独有的文化记忆模式及其特点。
一、端午文化在中日韩三国的传承与变迁
端午文化的形成始于夏商周至两汉时期[5]。据汉代的记载,彼时人们普遍认为五月是恶月。《风俗通义》曰:“俗云五月到官,至晚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6]。至于重五之日更是恶日。农历五月五日所生的孩子也被看作是不祥之兆,多被父母遗弃不养。“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据南北朝梁宗懔所撰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中国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荆楚地区的端午节习俗主要有采艾、采药等。如:“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是日,竞渡,采杂药。”[7]
端午节自古的习俗主要是采百草、赛龙舟、包米粽、饮雄黄等。它一直是以祛病驱邪的吉祥节日传下来的,随着时代变迁,渐渐加入了纪念地方性名人的内容 。例如,楚地纪念屈原,吴越纪念伍子胥或越王勾践及孝女曹蛾等。需要指出的是,端午节不仅是个全民性的民俗大节,从当时记载的宫廷习俗也可以看出,它也是宫廷、上层贵族的节日,这也就为后来的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端午习俗的仿效与流动奠定了基础。
关于中国的端午节是如何传入日本的,学界见解不一。武宇林指出是遣唐使将端午节的风俗传入日本[8]。周晓波则认为日本是从韩国先民那里了解并引进了端午节俗,其根据在于朝鲜半岛离日本更近,并且长久以来两者存在着频繁的交流关系[9]。另外,亦有学者认为传入日本的端午习俗可能源自中国端午的北方地区,与契丹骑马射柳有某种关系,由“汉人”或“韩人”传入,也可能由天皇朝廷直接带入。
有关古代日本五月五日活动的最早记事见于《日本书纪》,现将原文摘录于下:
十九年(即611年)夏五月五日、药猎于菟田野。取鸡鸣时集于藤原池上。以会明乃往之。粟田细目臣为前部领、额田部比罗夫连为后部领。是日、诸臣服色、皆随冠色、各着髻华。则大德·小德并用金、大仁·小仁用豹尾、大礼以下用鸟尾[10]。
可见,日本端午节最初是一种以“药猎”形式登场的宫廷仪式。该段文字中提及的活动地点为菟田野,即今日奈良县宇陀郡大宇陀町附近。藤原池是推古15年(607年)新建的4个池子之一,位于现在日本的奈良县明日香村小原一带。值得注意的是,官员的服帽穿戴以及发饰的隆重程度,不亚于日本古代新年的朝贺礼仪,可见此项活动是宫内的一项盛大活动。日本学者鸟羽正昭指出,圣德太子仿效隋朝的官位等级和服饰官帽制定了本国官吏的等级和服饰,即“冠位十二阶”制度。具体内容包括以德、仁、礼、信、义、智分官位等级,共计十二级官衔,并以紫、青、赤、黄、白、黑6种颜色各分浓重的冠帽来区分官位的高低。这篇记载中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均表示官位等级,表明药猎活动是遵循正式的官位秩序着装。由此可见当时药猎活动的正式性与隆重性。
《日本书纪》中端午节药猎的相关记载还有如下几处:
1.推古二十年(612年):夏五月五日、药猎之。集于羽田、以相连参趣于朝。其装束如菟田之猎。
2.推古二十二年(614年):夏五月五日、药猎也。
3.皇极元年(642年):五月乙卯朔己未、于河内国依網屯仓前、召翘岐等、令观射狩。
4.天智天皇七年(668年):五月五日、天皇纵猎于蒲生野。于时大皇弟·诸王·内臣及群臣皆悉从焉。
5.天智八年(669):夏五月戊寅朔壬午、天皇纵猎于山科野。大皇弟·藤原内大臣及群臣、皆悉从焉。
6天智十年(671):五月丁酉朔辛丑、天皇御西小殿。皇太子·群臣侍宴、于是再奏田舞。
另外,《万叶集》也有药猎的相关表述,与之前记载最大的不同是,药猎活动中第一次有女性加入。天智七年(668年)五月五日,天智天皇游猎蒲生野,额田王皇妃与大海人皇子随同伴驾。其间,大海人皇子对曾经的情人额田王示爱,额田王劝他谨言,有如下咏叹:“紫草园中,围禁场里,骋往驰来;不怕守场人看见?你这般举袖场袂。”大海人皇子回复:“妹也艳于紫,钟爱在吾心;岂为他人妇.普恩不自禁。”[11]这首流传至今的紫野赠答歌,不仅富有文学价值,更具史料价值。我们可以推测之所以天皇将游猎地点选定为蒲生野,大概由于此地栽培着贵重的药材——紫草,女官们可以采草药以怡情。
天智十年(670年)起,端午节活动地点由宫外移到宫内,由野外狩猎、采草药发展为宫内的骑射及宴会活动。《续日本纪》中有如下记载:
1.神龟四年(727年)五月丙子:天皇御南野榭、观餝騎·骑射。
2.天平元年(729年)五月甲午:天皇御松林、宴王臣五位已上、赐禄有差、亦奉骑人等。
3.天平七年(735年)五月庚甲:天皇御北松林、览骑射。入唐迴使及唐人、奏唐国、新罗乐挊枪。五位已上赐禄有差。
4.天平十三年五月(741年)乙卯:天皇幸河南,观校猎。
5.天平十五年(743年)五月癸卯:宴群臣于内裏。皇太子,亲节五节。
6.天平十九年(747年)五月庚辰:天皇御南苑,观骑射、走马。是日,太上天皇诏曰:昔者五月之节常用菖蒲为缦。比来、已停此事。从今而后,非菖蒲缦者、勿入宫中。[12]
由记载的人物、地点、活动内容可知,日本端午节的活动内容包括采鹿茸、摘草药、挂菖蒲、骑射走马和举行宫廷宴会。其初始乃宫廷贵族阶层的专属活动,后天皇逐渐号召平民加入,并给予赏赐,有与民同乐的意味。另外,活动地点由宫外移到宫内的意图在于,天皇想通过以端午节为首的仪式活动的展开,兴朝廷礼仪并逐步实现日本社会的礼法化。文武天皇于大宝年间(701年),发布律令即“杂令”,规定1月1日、7日、16日、3月3日、5月5日、7月7日、11月的大尝祭为节日。至此,端午节被正式列为节日。
端午节传入日本的时代对应的是中国的隋唐时期。端午习俗在隋唐进入了繁盛期,典籍对端午习俗的记载繁复细致,“竞渡”和“龙舟”一些词语开始出现在史书中,宫廷活动规模更为盛大热闹。“竞渡”与宴会之风在唐朝尤其盛行,上至宫廷,下至民众,均乐在其中。至于“竞渡”习俗未被日本接受的原因,大概在于两点,第一,“竞渡”习俗出自楚地为屈原招魂的信仰,具有地域性,日本不具备祭奠屈原的文化土壤。第二,由于地缘关系,端午习俗很可能是中国北方传入日本的,而中国北方由于水域稀少,气候干旱,缺乏“竞渡”条件,自然也就没有“竞渡”习俗。
至于端午节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虽然没有具体的文字资料记载,但可以确定在新罗时代(公元前57年-935年)已经存在端午节文化习俗。韩国的端午在时间上与中国农历的五月初五相同,他们也称之为“重午、重五、端阳、五月节”。在韩国学者的叙述里,韩国的端午则被上溯至2000多年前。韩国端午节在具体风俗活动上与我国有所不同,包含了锯神木、迎神、演戏等,祭祀内容浓重[13]。但是,韩国端午祭的所有细节与中国端午节俗都可以进行具体的、同一的对应。从东亚汉文化圈整体上看,毫无疑问,在夏代或夏代之前便已存在的中国端午节是本源,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端午节是传播之支流[14]。
二、“药猎”中的“药俗”
中国端午的采药习俗来源于五月被认为是“恶月”这一普遍认识。《礼记·月令》中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生,毋躁。”[15]另外,由于气候上潮湿闷热,各种疾病容易滋生,蛇虫等活动日益频繁。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曝床荐席,及忌盖屋。”因此人们把五月五日作为恶月的恶日,在这一天举行采百草为药、蓄兰沐浴辟邪等一系列的活动。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的信仰在民间一直被延续下来,对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也很忌讳。王充《论衡·四讳》中如实记载了当时的风俗:“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以举之,父母祸死。”[16]这也是中国把端午节当作恶日,进行驱邪避恶活动的根据之一。
驱邪避恶的活动内容之一就是采草药的习俗。自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开始,民间普遍认为端午节采药最有效。据《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可以看出,端午习俗中有踏百草、斗百草的活动,并且会专门采艾悬挂在门上,以防止毒邪之气的入侵。另外,会以菖蒲入酒。《荆楚岁时记》有如下记载:“是日,竞渡,采杂药。”此处的杂药即为“百药”。《岁时广记》卷二十二列举了宋及前代众多的端午“药俗”:送术汤、掘韭泥、炼苋菜、刈枲耳、取木耳、服龙芮、乾麕舌、挂商陆、荐汉术、收蜀葵、晒白矾、丸青蒿、种独蒜、食小蒜、汁葫荽、灰苦芙、羹蘩蒌、摘苤苢、啖蓰蓉、制豨莶、相念药、相爱药、能饮药、不忘药、急中药、丁根药、金疮药等[17]。唐韩愕《岁华纪丽》中记载:“五月,百药可蓄,端午日,结庐蓄药,斗百草。”所谓“斗百草”是指用草根或草茎比试坚韧的游戏。《本草纲目》等药学著述多有于端午日收药的习惯。很多民谚也反映了端午节采药有奇效的观念。比如“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变成药”等。
关于日本的端午节,《日本的年中行事》一书中写道:“旧历五月,高温多湿,瘟疫易发,害虫出没,被称为‘恶月’。”[18]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五月“恶月”说与中国十分接近。“恶月”之说是《荆楚岁时记》特别强调的,而早在奈良时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到日本,在现存的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载有《荆楚岁时记》一卷。因此,日本的“恶月”之说受到《荆楚岁时记》影响的可能性极大。
那么,日本端午节所采草药的种类与功效又如何呢?前文中提及的天智七年(669年)五月五日所采的紫草,据《日本书纪》皇极三年(644年)的记载:“三月顷者菟田郡人押坂直与一童子欣游雪上、登菟田山。便见紫菌挺雪而生、高六寸余、满四町许。乃使童子采取还示邻家、总言不知。且疑毒物。于是押坂直与童子煮而食之、太有气味。明日、往见都不在焉。押坂直与童子由喫菌羹、无病而寿。或人云、盖俗不知芝草、而妄言菌耶。”可知,紫草是芝的一类,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采紫草的活动体现了求仙、长生的神仙思想。这种思想源于商周之际已经出现的东方长生不死观念,以及后来在战国时期以长生不死观念为基础形成的东方神仙思想。
另外,在奈良时代,寒食散已存在于日本。受中国道教思想的影响,贵族阶层对求仙问药十分关心。日本在大宝元年(701年)指定《本草经集注》为当时医学生的教材。《本草经集注》为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著的药学著作,该著作不仅对中国中医药学带来了深远影响,亦推动了日本古代医学的发生与发展。从大宝令藤原宫遗址出土的记载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上卷内容的木简可以看出,《本草经集注》对当时日本宫廷的影响。其中卷三至卷五记载了适宜采草药的时间,特别强调在三月三日和五月五日采的草药具有极佳的疗效,采草药的上品是石龙芮、车前子、肉苁蓉,中品是葛根,下品是练实、苦芺、钓樟根皮和麇舌。肉苁蓉具有益精气的功效。葛根具有起阴气、解诸毒的功效,制药方法是五月采根,暴干。另外练实具有久服头不白、轻身的功效;苦芺具有处处有之,人取茎生食之的特点;钓樟根皮和麇舌具有适宜五月五日采的特点。可见在端午节这一天所采草药的种类主要分2种,第一种是按生长周期适宜在五月采摘,而且端午节这一天采摘疗效最好的草药,比如葛根、苦芺、麇舌;第二种是具有符合道家神仙思想——不老、益精气、头部白、长生的功效的草药,如车前子、肉苁蓉、练实。这也印证了日本药猎活动中的采药之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其一是通过采草药并服用来实现强身健体的目的;其二,所采集草药的功效符合了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延年益寿、不老、轻身的愿望。
在韩国,中国端午习俗和道教思想的影响也很深远。根据刘晓峰研究,韩国端午节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
1.颁艾虎于阁臣。用小杆缠束彩花。蔌蔌如蓼穗。这一节俗直接参考了中国《岁时杂记》中“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的作法,所以《东国岁时记》交待说“国制仿此也”。
2.宫内与朝官家门上要贴朱砂写的“天中赤符”,符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
3.内医院造醍醐汤进供,又造玉枢丹进上,国王赐给近侍佩之禳灾。醍醐汤的成分为:神曲2两,官桂2两,干姜(煨)2两,盐10两(炒过),甘草7两(净者),乌梅8两(净洗,拍碎)。玉枢丹成分为:山慈菇3两,红大戟1两半,千金子霜1两,五倍子3两,麝香3钱,雄黄1两,朱砂1两。
4.男女儿童取菖蒲汤洗面,皆穿红绿新衣,以菖蒲根作簪,遍插头髻以辟瘟,号“端午妆”。
由1和4两项的戴艾叶、菖蒲汤洗面可知,受到中国端午节挂艾叶、喝菖蒲等习俗的影响,端午节强身健体、驱邪避害的思想深入人心。而从3和4两项中:贴朱砂写的天中赤符,而朱砂是道教中用于驱邪的物品;符的末语“急急如律令”念咒驱除鬼神的末语;服用的醍醐汤、玉枢丹的成分包含雄黄、朱砂等可以看出,韩国端午节的药俗受到中国道教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中日韩三国的端午节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各国端午民俗的基础部分,大多是以“药物”和“镇物”为手段,达到防疫和辟邪的目的[19]。
三、“药猎”中的“鹿”元素
日本“药猎”的对象主要指鹿。在中日韩三国,自古以来鹿被视为祥瑞、长寿、王权的象征。鹿因其角每年定期的生长与脱落,被认为有反复再生的能力,后来因为鹿角的再生能力进一步演化出长生不死的涵义[20]。
在中国,受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鹿被视为长寿的象征。《神农本草经》中有食鹿茸能“益气强志,生齿不老”与鹿角胶“久服,轻身延年”之说。中国东晋时期葛洪所著的道教著作《抱朴子》提及虎及鹿、兔皆寿千岁。更重要的是,鹿也是王权的象征。《汉书·蒯通传》云:“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21]据王海燕研究,在古代中国的理念中,夏至的鹿角脱落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还被上升到关联执政者统治的高度,鹿角被视为兵的象征,而鹿角的脱落则与夏至之时的阴气弱相连,意示不宜动兵的“天意”。如果夏至之时鹿角不脱落意味着“兵戈不息”。在古代中国,自然界的不正常现象一向被认为是执政者的失政,或统治的不安定的表现。据此,夏至之时的鹿角脱落也被作为衡量时政安定与否的标志之一[22]。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没有在端午前后采集鹿茸的记录。
在日本,鹿特别是白鹿是祥瑞的象征。日本平安时代文德天皇时期的史书《文德实录》(九)云:“天安元年二月乙丑,是日改元为天安元年。缘美作常陆二国献白鹿连理之瑞……(中略)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美作国白鹿献进奏。如是嘉瑞,是薄德令感致物非,挂畏山陵慈赐示赐物。为贵喜受赐,御世名改天安元年事。”[23]其中记载的进献白鹿给天皇象征着统治的巩固、国家的太平。食用鹿肉还是“服食成仙”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人们食用鹿肉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鹿茸也被当做十分珍贵的药被皇室贵族享用,它是不老不死、吉祥的象征,具有滋养强壮、强精剂的作用,也用作媚药[24]。《万叶集》中有一首描写药猎情景的和歌,记载了贵族猎鹿食用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服役出药猎,艰难往登攀。偏辞深山里,藏身两採边。梓弓搭在手,响前扣在弦。但等鹿儿出,箭发项刻间。一只牡鹿来,悲切诉为王献吾身,一死在眼前。
吾角饰伞盖,吾耳做墨罐。吾眼为明镜,吾爪嵌弓丹。吾毛制御笔,吾皮剪箱衣。吾肉剁细脍,吾肝供宴席。吾胃作酒肴,渍盐咮美甘。
在朝鲜半岛,鹿也是长寿的象征。在朝鲜半岛,有“十长生图”的绘画形式,指十种象征长生、长寿的物象——太阳、山、水、石、云、松、不老草(灵芝)、鹤、龟、鹿,其中就包含鹿。“十长生”是在自然物崇拜思想的基础之上,吸收中国道教神仙思想而形成的,很符合道教主张“服其药以求仙”的思想。在古代,有三月三日猎猪、鹿的风俗。根据《三国史记》卷第三十二的记载,“高句丽,常以三月三日,会猎乐浪之丘,获猪鹿,祭天及山川”,可知高句丽国有三月三日猎猪鹿,以祭天和山川的风俗。从吉林集安县境内集安洞沟(当时高句丽国领地)古墓群壁画,生动再现了彼时高句丽国狩猎的场景。其中一幅描绘了帝王狩猎的景象:在一个灵水涌流、花草茂盛、鸟兽嬉戏的乐园,帝王正在猎鹿角。原因在于高句丽人将鹿视为不死的象征,鹿茸具有强精剂、不死不老、获得吉祥安宁的作用[25]。
从前文中列举的《续日本纪》关于药猎活动的描写可知:就活动的目的而言,与高句丽不同的是,日本的药猎不是为了祭祀天及山的神灵,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游猎色彩的宫廷节日娱乐活动。而且某种意义上也是天皇赏赐群臣、显耀势力的一种方式。日本药猎活动中的采鹿茸由高句丽国的风俗传入的可能性很大。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日本学者原田淑人指出,在宇陀野举行的药猎活动所穿的服装与高句丽人三月三日狩猎祭天活动中所穿服装相似[26]。其次,从钦明朝(531年)至推古朝,日本受到高句丽文化的影响。第三,据《日本书记》的记载,很多乐浪郡的遗民经过百济国来到日本,还有高句丽有很多百姓也来到日本,他们很可能带来这个风俗。基于这三点思考,日本药猎的起源受到高句丽影响的可能性很大。至于日本采鹿茸的时间不是三月三日,而是五月五日的原因在于日本与朝鲜半岛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朝鲜半岛的鹿茸一般于三月成熟,而日本的鹿茸在三月还未成熟,所以采鹿茸被延迟到五月。另外,高句丽国的狩猎对象还包括猪,而在日本却没有。这是因为在日本,猪被视为不洁的动物,故只以灵兽鹿为药猎对象[27]。
综上所述,日本端午初始所盛行的“药猎”活动,其“药”元素体现了日本贵族渴求轻身、长寿的愿望,可以窥见中国端午节采百草习俗和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而“猎”元素则受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双重影响。端午节东传至日本而孕育出日本本土的端午文化不仅富含中国道教神仙思想,亦受到了朝鲜半岛民俗的辐射,所以说日本最初的端午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混合体。
四、“药猎”与日本文化记忆模式
关于日本端午文化“药猎”所折射出日本文化的这种杂糅亦或“杂种”特质,加藤周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杂种文化》一书中就曾指出。在其启示下,加藤秀俊进一步指出,外来文明并非作为“异国情趣”镶嵌在日本文化中 , 而是在日本文化的熔炉中脱胎换骨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药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通过追溯“药猎”的发生及发展过程,可以再现日本文化记忆模式的形成过程。
根据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总是以自我为核心,被记忆和回忆的东西经常带有身份认同的成分。文化记忆带有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一个社会以怎样的过去作为其存续的基础,又从中获取怎样的身份认同要素,实际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性质和它所追求的目标。
“药猎”作为一种端午仪式,属于文化记忆的一种,它不是自行生成,而是目标极为明确的记忆政策努力和干预的结果。端午文化初传入日本的时期,正值飞鸟、奈良时代。彼时的日本受中国六朝、隋唐文化影响浓厚,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艺术等文化精髓的汲取,日本实现了由古代国家体制向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过渡,完成了体制上的革新。通过对中国端午文化“药”元素的摄取,得以确认并强化自己身份——成为像中国那样的先进强国。而“猎”元素作为迥异于中原文化的异文化,来源于朝鲜半岛,对其的摄取直接反映了日本民族对尚武精神的偏重。猎“鹿”这个行为,则被视为巩固王权统治的有力手段。平安朝后,日本端午逐渐演变成崇尚武力的所指,并使之从除邪避恶的节日变异为一个以实战练兵、炫耀武力、荼毒生灵为目的的“尚武之节”。这其实从其初始形态“药猎”就可以初见端倪。
“药猎”仪式的形成可以说是日本民族建立在文化记忆与集体同一性基础上的一种文化身份构建的实践。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类型可分为冷回忆和热回忆。在冷回忆社会中,每种试图通过进入历史来获取些什么,并以此改变社会结构的尝试,都会遭到令人绝望的抵抗。而热回忆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回忆是为了审视当下并寻找改变现状或走出困境的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无疑是热记忆社会的范例,而这种文化记忆模式则直接影响了其文明的走向。日本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他者”来重新发现“自我”的历程,伴随着“自我”的激活,其国策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迹。近代日本最终选择了成为东亚霸主并为此不惜发动侵略战争,这促使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记忆的选择模式进行深刻思考。
[1]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
[2]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五)[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 关 童.端午新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6).
[4] 刘晓峰.端午节与东亚地域文化整合——以端午节获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5] 宋 颖.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6] 应 劭.风俗通义校释·佚文二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436.
[7] 宗 懔.荆楚岁时记[M].宋金龙,校注.山西:太原人民出版社,1987:103.
[8] 武宇林.中日端午民俗文化比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9] 周晓波,王晓东.中日传统节俗比较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176.
[10]日本书纪[M].小島憲之,直木孝次郎,西宮一民,蔵中進,毛利正守校注,译.东京:小学館,2013.
[11]万叶集[M].赵乐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26.
[12]菅野真道,等.续日本纪[M]. 东京:岩波书店,1992.
[13]刘 金,杜文轩.中韩申遗之争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端午节和江陵祭为例[J].科教导刊,2010(12):217-218.
[14]何星亮.从传统节日看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以端午礼俗为例[ J].民族研究,2008(3):41-50.
[15]朱 彬.礼记训纂:卷6 [M].饶钦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248-249.
[16]王 充.论衡校释(第三册)[M]. 黄 晖,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06:977.
[17]陈元靓.岁时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54-264.
[18]新谷尚纪,监修.和のしきたり―日本の暦と年中行事[M].东京:日本文芸社,2007:114.
[19]周 星.端午节和“宇宙药”[J].节日观察, 2014(1).
[20]李 佳.神仙食鹿考源[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21]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75.
[22]王海燕.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56.
[23]藤原基经,等.文德实录(九) [M]. 1883: 4-5.
[24]杉山二郎.薬猟考:鹿茸精の効きめ[J].ファルマシア,1976(8):633-634.
[25]王纯信.朝鲜民间刺绣中“十长生”图考释[J].艺圃,1995(2):26-31.
[26]原田淑人.冠位の形態から観た飛鳥文化の性格[M].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78.
[27]和田萃.日本古代の儀礼と祭祀·信仰[M].东京:塙書房,1995:93-149.
[责任编辑:刘兴禄]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Herb Hunting” in Japanese Dragon Boat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JIN Jing,CHEN Xing-xiu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Herb hunting” is the initial form of the Japanese Dragon Boat culture, which refers to the Japanese aristocracy gathering herbs and hunting activities. As a Dragon Boat Festival ceremony, “herb hunting” belongs to a kind of cultural memory, it is not self-generated, but the goal is very clear memory of policy efforts and intervention affect the results. The “herb” element is influenced by China Dragon Boat Festival customs and Baicao immortal Taoism, which reflects the Japanese noble’s desire for a light and long life. The “hunting” element is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directly reflects the emphasis and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warrior spirit of the Japanese nation to consolidate the intention of kingship. Thus, Japan’s first dragon boat culture is a mixture of multi culture. The German scholar Jan Assmann’s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Japanese Dragon Culture “herb hunting” causes and Japanese cultural memory model.
Dragon Boat Festival; herb hunting; cultural memory
2016-10-28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44760180)的阶段性成果。
金 晶(1982-),女,辽宁营口人,华东师范大学日语系讲师,日本大阪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文学及文化;陈兴秀,华东师范大学日语系学生。
K89
A
1674-621X(2016)04-01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