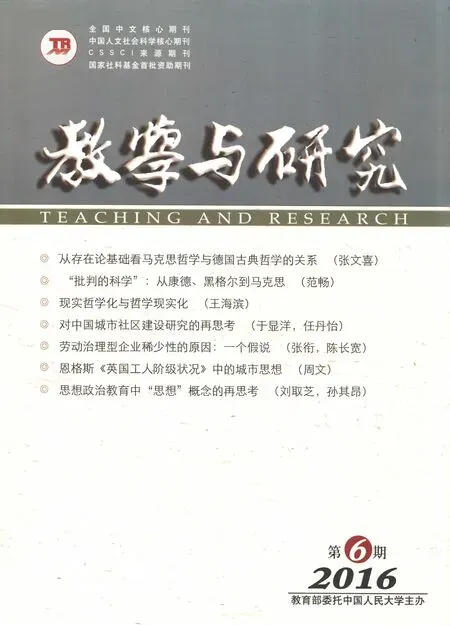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概念的再思考*
刘取芝, 孙其昂
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概念的再思考*
刘取芝, 孙其昂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对思想进行清晰的科学界定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当前学术界对思想的界定多数停留于哲学的抽象层次,未能从现代科学意义上阐明“思想”的概念内涵。在现代科学意义上,“思想”以人的高级认知活动为基础,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其实质是对事物或现象的概括性和间接性认知及其倾向性;思想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内生性与外源性、内隐性与外显性,具有多种的存在形态。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分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具有政治性和形态多样性以及思想的一般特征。从“思想”出发,可以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在的思想格局,找到改进教学方法的一种路径,为提高教学效果寻求新对策。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许多学者认可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探究思想和行为之间的规律;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或元点。然而,长期以来,关于“思想”的概念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特殊视域中“思想”概念的探讨并不充分,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界而言,“思想”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思想概念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边界的模糊,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正是因为未能阐明思想概念的内涵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的不同侧面,妨碍了寻找和采取正确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首先需要对“思想”进行清晰的科学界定,以形成独特的学科基础理论。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概念的研究现状
许多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概念进行过界定。这些定义大多采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方法或语言学方法,也有少数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及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界定。
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定义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定义方式。许多学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从两个方面揭示“思想”的含义[1]:其一,思想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这种观点从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出发,强调思想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摹写、印象,即哲学上的认知。其二,思想是理性阶段的认识。毛泽东说,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飞跃,形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也是列宁所说的“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想的定义无疑是必要的,但哲学式的定义具有抽象性和一般性特点,对思想本质及其形成发展规律的研究需要对其更加具体深入的概念剖析。
语言学方法的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思想”二字的起源上考察。如尉平、永恒对《说文》中“思想”二字进行了词源考察:思,睿也,绎理为思;想,冀思也,希冀;思想一般表示思量、想念的意思。如“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乡”。[2](P230-239)另一类从语言学角度对思想的考察是从词性来考察,即将思想区分为作为名词和作为动词的思想,认为作为名词的思想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体系或者指人的理性认识的结果,作为动词的思想是指人的理性认识的过程。[3](P70)就这两类观点而言,前者对“思想”的释义不够全面。语言本身具有社会历史性,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同一语词常常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实质上是语言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结合,本质上还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少数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思想进行定义。如苏振芳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思想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人的心理活动的结果。他认为,形成思想的心理活动包括人的认知、情感、意志,也包括人的气质、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征。[4](P123)缪志红认为,思想现象是个体经过思维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属于心理现象中个性方面的内容;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心理过程同步,同样经过知、情、意、行的过程。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说,从心理学角度探索思想的形成及本质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已有的关于思想的心理学定义呈现出笼统、模糊和不准确的现实,尚未真正到达心理科学的层次。
还有学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或内容结构的角度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含义。如金林南认为,应该从思想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把思想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结构和发展过程中来思考。他认为,思想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定群体的活动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精神意识层面自觉性不断提升、思想主体不断扩大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思想研究的重心不在于思想的内容,而在于思想由以生成和传播的条件。[5](P144-145)孙其昂则从内容结构的角度,认为思想包含观念、知识、方式及其关系,因而是一个结构存在。[6](P154-161)金林南社会历史的观点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新的方向,推动和深化了思想的概念探索;但思想生成和传播的条件是否应该成为思想研究的重心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孙其昂关于思想内容结构的观点看到了思想内部可能存在的要素与结构,是思想概念探索的一个很大进步;但关于思想内容的概括是否准确和全面值得推敲,尤其是知识是否属于思想的范畴需要进一步考虑。
概括而言,上述论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思想的内涵。但已有探索或者停留于哲学的抽象层次,或者不够成熟准确而未能从现代科学意义上阐明“思想”的概念内涵。笔者认为,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要建立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仍然需要对“思想”本身展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探究。
二、“思想”的现代科学含义
从具体科学中探寻“思想”的本质和规律,是对思想展开现代科学意义上研究的根本。那么,在具体科学视域下,“思想”是什么?
《新汉英大词典》对“思想”的英文解释包括thought、thinking、idea、ideology等。再反过来考察《新英汉词典》,thought和thinking都是think(使用大脑以获得主意或得出结论,即思维)的名词形态,thought表示通过人的思维活动所获得的想法、观念、意向等,thinking则表示思维过程本身;idea表示观念、主张等;ideology则表示思想体系,是系统化的思想。综合上述表达,“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需要从几个方面加以全面理解:(1)从内容上说,思想包含观念、想法、主张,以及思想活动本身(即语言学角度的动名词含义)。观念、想法、主张本质上是人关于事物或现象的内在联系及规律的认知及其倾向性;思想活动本身则意味着一定的认知活动与认知方式。(2)从成分上说,思想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思想的内容首先是一定的认知判断,但当一定的认知判断成为个体的主张和意向,即个体对某一认知内容持有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时,思想便具有了情感和动机的成分。(3)从形成过程上说,思想是情感、动机参与下高级认知活动的结果。人的认知心理活动过程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言语等过程。但单纯通过感觉、知觉获得的认知不能称之为思想;在感觉、知觉基础上,通过注意、记忆、思维、语言等综合认知形成的对事物和现象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才有可能称之为思想。而注意、记忆、思维、语言等认知过程往往伴随着情感、动机因素的参与。
因此,结合思想的内容、成分和形成过程,我们认为“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1.思想的内生性与外源性。
按照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观点,人的认知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它包括感觉输入的变换、简约、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认知加工的过程首先以外部信息输入为前提。因此,思想不是人脑的无端创造,而是需要以外部世界的信息为基础,从这一点上说,思想具有外源性。但思想不是外部世界的机械反映,作为具有丰富的心理活动的人,对思想有其主观建构。福柯说:“所谓‘思想’,我认为就是在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建构真理与虚假的游戏,并因而建构作为认知主体的人。”[7](P258)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人的思维加工过程是人脑内在的加工过程,受个体的认知方式以及人格、情绪、需要、兴趣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内在性。西方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开展的大量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表明,社会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上层所建构和传播的意识形态,而是在遗传、人格、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建构和选择。[8]因此,思想虽以外界信息输入为基础,具有外源性,但同时又通过内在的思维建构过程而形成和发展,具有内生性,是内生性与外源性的结合。
2.思想的理性与非理性。
思想具有认知、情感和动机的成分,全面认识思想不仅要将思维置于人的认知系统,更需要将思维置于人的心理活动的整体系统,采用系统性的视角。前文已述,人的思维活动作为复杂认知活动,一方面,以对外部客观世界的信息输入、感知觉和记忆等认知活动为基础;另一方面,作为认知系统,又受到人的情绪、动机、愿望等过程的影响。正如诺曼(Norman)所说,人的信息加工系统包括认知系统、情绪系统和调节系统三大成分,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人的思维加工过程等同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过程。[9](P15-16)按照认知图式理论,主体的需要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主观心态构成人脑对信息客体的选择、整合和理解的方式,形成一定的认知方式,从而影响个体思想的形成发展。这些要素既有动机、材料工具、思维等理性要素,也有情绪、兴趣等非理性要素,因而思想本身也就具备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属性。
3.思想的内隐性与外显性。
思想的形成发展是外显和内隐认知协同作用的结果。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仅从抽象、外显的认知功能、意识性思维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的认知能力及其发展是不全面的,应当从综合、历史、辩证的角度看待人类的认知功能及其发展。即人类的认知活动不仅包含有明确目的、以概念为基础的外显认知,而且包含非直接目的性、自动加工的内隐认知。几乎所有复杂的知识都是通过二者的协同作用而获得的。因此,思想不仅仅是逻辑思考和符号表达的产物,而是个体无意识的、自动的内隐认知过程共同参与的结果。这从形成过程上说明了思想的内隐性与外显性结合的特点。
三、“思想”的表现形态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思想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呈现为不同形态。当前学术界关于“思想”研究的混乱,一定程度上与对思想的形态把握不清晰有关。因此,进一步明确思想的内涵,需要区分和明确思想的表现形态。为此,笔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思想”的形态表现及特征作如下考察:
1.“思想”的个体形态与社会形态。
作为人脑对输入信息进行思维加工活动的结果,“思想”可以存在于个体的空间范围内,也可以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形成个体形态的思想和社会形态的思想。个体形态的思想是社会形态思想的基础,社会形态思想由个体形态思想抽象而来;反过来,社会形态思想又可以成为个体形态思想的信息来源之一,表现为个体对社会思想的选择和加工。
由于加工深度和广度的不同,个体形态的思想与社会形态的思想具有不同的系统性和抽象化水平。受个人思维广度和深度的影响,除作为社会思想生产者的个别思想家之外,个体形态的思想往往零散而不够系统、具体而不够抽象。而社会形态的思想经过专门的建构加工过程,理论抽象和系统化程度较高。
此外,社会形态的思想在经过许多个体进行抽象加工之后,往往超越和独立于具体的个体,成为一种观念或理论的实在。因此,社会形态的思想通常较为稳定。而存在于个体空间范围内的思想则时刻受个体的情绪、认知、需要、动机等心理过程的影响,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
2.“思想”的非系统形态与系统形态。
思想的个体形态与社会形态是依据思想的主体所作的思想形态划分;从思想本身的存在出发,“思想”有非系统形态和系统形态。系统形态的思想是深度认知加工的产物,常常经由长期的发展过程,或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系统形态的思想通常表现为一定的学说、理论,可以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空间,也可能为某一特定的个体如理论家、思想家所拥有。非系统形态的思想同样可以存在于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表现为零散的观念、想法、主张等。可以说,系统形态的思想是自觉的深度认知加工产物;非系统形态的思想则通常是自发的认知过程产物。
3.思想的内在形态与外化形态。
尉平、永恒认为,人的思想以大脑信息输出为界限,可以分为内在思想和外化思想。[2]内在思想是尚未从大脑中输出的思想,它可能是混沌的思想萌动,尚未经过系统的思维深加工;也可能是经过较为系统深入的思维加工后比较成熟的思想。内在形态的思想可能稳固为个体的信念,但也可能转瞬即逝或逐渐淡化消失;因为没有表达外化出来,内在形态的思想主要受个体意识的控制,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和不可控性。外化形态的思想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文字、行为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外化思想因其加工深度的不同,可能是系统形态的思想,也可能是非系统形态的思想。同时,个体形态的思想外化后可能经过集体加工而积淀成为社会形态的思想。因此,外化思想可能是个体的,也可能是社会形态的思想。
四、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思想”概念的梳理是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边界从而促进学科发展成熟的前提。从一般意义上说,无论是哲学认识论还是现代认知科学关于思想的概念无疑都是适合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而问题是,作为一个具体学科,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思想”具有何种特殊性?对此,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初步探索。
1.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主体。
思想的主体问题是探索思想属性的基础。从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来看,从以“君权神授”、“封建伦理”等思想为核心的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到启蒙运动以来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为获得政治权利而展开的意识形态竞争,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宣传工作”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思想工作,都涉及两个思想主体:统治阶级或一定政权主体的思想和一定社会成员的思想。由此可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所用以教育的思想,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或处于历史前沿地位的一部分人所生产、主张和信仰的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所生产、主张和信仰的思想;而目标则在于启发和改造一定社会成员(对象)的思想。正如张耀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社会、组织、群体与其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引导其成员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促进其成员知、情、意、信、行均衡协调发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实践活动。”[10]这里,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即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以一定的“思想”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建构自己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由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的思想出发,落脚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
由此,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具有两个主体,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二是一定社会成员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体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主体是统治阶级或一定政权主体的代表,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自然人”,两种不同主体有各自相应的背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构成复杂的思想组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实质上正是不同主体及其相应的思想共同建构起来的场域,必然造成教学活动的复杂性和实现教学效果的难度。
2.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内容具有怎样的范围边界?这个问题涉及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内容等问题的认识,学界存在颇多争议。
纵观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本质的诸多观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内容范围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以政治为核心的思想的观点。如孙其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政治为核心的思想教育”,[11](P5)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12]由此说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主要是政治思想。二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主要是意识形态。如陆庆壬、王勤、秦在东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13][14][15]按此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三是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观点。如邱伟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16](P1)张耀灿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17](P4)这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包含了一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四是发展的观点。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历史发展性,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内容也是历史发展的。如孙佩锋、尉天骄认为,政治性是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则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其内容应该结合时代课题进行转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则不再以政治教育为核心内容,而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8]
以上四种观点中,前三种观点都相对静态,其中意识形态的观点由于意识形态概念模糊性和使用中的否定性乃至“妖魔化”倾向,因而不可避免带有歪曲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主要区别在于思想的范围,第三种观点,思想的范围更广,不仅包含了政治思想,而且包含了政治思想以外的思想内容,如一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第四种观点体现了历史性,主张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笔者认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问题的模糊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内容范围模糊性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边界不清晰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常‘混迹’于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治教育、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19]因此,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内容边界需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问题进一步加以探究。
3.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特征。
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具有怎样的特征?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郑芸、孙其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具有意识形态性、学科性和实践性;[20]王贤璋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具有政治性、现实性和宽泛性。[1]二者都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意识形态性或政治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是与政治或意识形态有关的思想,而不包括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思想等。笔者以为,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第一属性,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首先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团体所主张或信仰的思想,其内容本质是一定的政治主体对政治观点或观念的集合,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一定政治利益集团的统治或帮助一定政治主体实现其政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第二重特征是思想形态的多样性。前文已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或主张者,其思想的表现形态是系统性和社会性形态的思想,是经过系统加工的超越于个体而存在的系统化观点存在。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则通常是个体化、非系统化的存在。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通常情况下在形态上是零散的,在加工深度上是不一致的,在变化规律上是“活”的、多变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就是要使系统化形态的“理论”转化为个体化存在的“思想”,就必须研究和掌握个体化存在的“思想”的形成变化规律,掌握“活”的思想的运动规律。
与一般性思想相比,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也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内生性与外源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等特征。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的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在上述三个维度方面具有不同的强度。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的思想由于常常在形态上是经过系统加工的系统化思想,因而具有较强的理性;在思想的产生发展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有时本身就是思想的生产者,因此,对同为思想生产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来说,其思想产生发展过程中个人的思维加工成分较多,因此,思想的内生性更强;同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的思想通常是外化形态的思想,在集体加工的过程中,内隐性的认知过程影响因素较小,而外显的认知过程影响较大。相比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则由于是一定社会个体的思想,一方面受个体的情感、动机、兴趣等因素影响,较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的思想具有更强的非理性。在思想的生成发展方面,由于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接受的思想主要是政治性思想,其思想信息主要来源外部世界。西方一些学者甚至将个体政治思想定义为来源于外部权威的宗教、政治或哲学信念和态度体系。[7]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接受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外源性。最后,在内隐性与外显性维度上,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的思想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较多地包含非直接目的性、自动加工的内隐认知过程,是有意识的外显认知和无意识的内隐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理性与非理性、内生性与外源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等维度上的特征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复杂性,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发展和探索的方向。
综合上述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活动,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教师和学生分别属于两种思想主体,同时又具有相应的思想特征,教师的思想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内容),更多地倾向于理性、外源性、外显性、社会形态、系统形态、外化形态等特点,而学生的思想更多地倾向于非理性、内生性、内隐性、个体形态、非系统形态、内在形态等特点,由此组成相应的思想“格局”。这种“格局”潜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机制,有待于我们去揭示。就是说,教师传递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要内化为学生的思想,需要综合考虑两种思想的特点,实现有机契合,最终转化为学生的思想。
[1] 王贤璋,卢士才,程建波.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思想”界说[J].探索,1999,(3).
[2] 尉平,永恒.论思想的含义、形成和发展[A].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编撰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2001)[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3]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 苏振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5] 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 孙其昂.启动对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丛,2013,(3).
[7] 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 刘取芝,孙其昂,施春华,陈友庆.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及作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3,(11).
[9] 王甦,汪安胜.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 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7).
[11] 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4.
[12] 孙其昂.政治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J].南京社会科学,2006,(3).
[13] 陆庆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14] 王勤.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15] 秦在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16] 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7] 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8] 孙佩锋,尉天骄.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兼谈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J].学术论坛,2011,(10).
[19] 金林南.从政治的意识到意识的政治——思想政治起源的政治哲学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0,(19).
[20] 郑芸,孙其昂.论思想政治教育学视角中的“思想”[J].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 李文苓]
Rethinking of the Concept of “Though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u Quzhi, Sun Qi-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y; su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lear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ought” is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 most of the “thought” studi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re stuck at the abstract level of philosophy, and the concept of “thought” is not explained in the sense of modern science. In the sense of modern science the thought can be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implicit and explicit. Therefore, thought has a variety of existing forms. The though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cludes the thought of the executo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thought of the obje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have the political nature, the nature of morphological diversity as well 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ought. From the concept of thought, we may found the intrinsic thinking struc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then turn up some methods to improve our teaching methodology to achieve more satisfactory teaching effects.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现代化视野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合研究”(项目号:13BKS08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路径和工作机制研究”(项目号:2014ZDIXM010)的阶段性成果。
刘取芝,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讲师;孙其昂,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