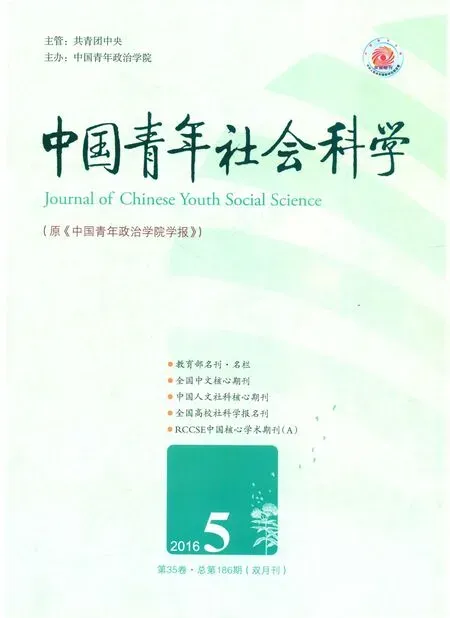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价值蕴含
■ 王建敏 邸天利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编辑部教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原副庭长,博士)
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价值蕴含
■ 王建敏邸天利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编辑部教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原副庭长,博士)
在当前形势下,构建独立的少年法院或是家事法院都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而涉少案件与家事案件审判理念的趋同使得二者能够整合,形成一体两翼的工作格局,实现司法-社会一体化的价值追求。
一、我国少年家事审判制度现状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我国涉少案件审判制度改革就此拉开帷幕。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议,会后,少年法庭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1991年通过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办案程序,发布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建立起“政法一条龙、社会一条龙”的工作制度;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将少年法庭工作纳入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体系;1995年第三次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工作会议提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1998年第四次全国法院少年审判工作会议确定中级法院设立专门合议庭, 有条件的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与此同时,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提出“少年法庭”的名称;200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少年法院”构想;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试点设立少年法院;2006年第五次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工作会议要求试点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2012年全国增加32个中级人民法院参与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
自少年法庭诞生以后,涉少案件审判制度逐步从主审刑事案件到少年案件综合审判转变,在这期间虽然提及少年法院的概念和试点,但自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批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设立少年法院的方案以后,设立少年法院的努力暂告一段落。与此同时,鉴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我国各地法院也为家事审判制度改革作出努力,建立了诸如婚姻家庭合议庭、女子合议庭、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如湖北襄樊市中级法院的婚姻家庭合议庭、广安市岳池县法院的女子合议庭、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的特色制度,旨在维护家庭稳定,保障妇女、儿童利益。但构建独立的家事法院亦存在司法资源紧张、缺乏共同认知等现实障碍。然而,在现阶段完成建立独立的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的终极构想出现改革瓶颈时,涉少案件与家事案件趋同的审判理念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因而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将二者合一,作为实现独立的少年家事法院目标的桥梁。
二、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理念
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动因是保障未成年人权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妇女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妇女担负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功能减弱,许多少年过早步入社会,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导致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带来许多失控现象,少年违法犯罪现象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的偏刑化制裁方式已经不能够起到预防、控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作用。随着生物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实证犯罪学派兴起。实证派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探究人们犯罪的原因,主张在刑事处理时更加关注犯罪人本身,即刑罚个别化。于未成年人犯罪而言,基于生理及心理的特殊性,他们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因此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有效途径宜在刑罚之外。因而,我国接下来的少年家事审判改革应始终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司法-社会一体化,形成司法与社会的双向工作机制,更加注重庭前的有效预防、庭中的教育感化、庭后的延伸帮扶。具体包括:
(一)国家亲权
在我国近代社会以前,父权被视为家中的最高权威,既可以“立规矩”,又可以“举杖罚”*《说文解字》中将“父”解释为“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父”既可以立家庭行为之规矩,又可以在家庭成员违规时举杖而罚之。。随着人治社会的深入发展,君王成为所有国民的父,“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先”的宗法思想即蕴含了君王作为最高监护人有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力,但这种“君主亲权”更偏向于君主权力的行使。步入现代社会,“君主亲权”逐渐被“国家亲权”*国内又译“国家监护权 ” 、“国亲 ” 、“公民家长 ”、“人民之父 ”等 。取代,更加强调国家作为国民最高监护人的应尽职责。英国最早将“国家亲权”作为处理有关涉少案件的理念,通常认为,国家亲权理论有三大基本内涵:其一,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承担并应当积极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其二,国家亲权高于父母亲权,即便未成年人的父母健在,但若其不具备保护子女的能力或不履行、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时,国家可以越过父母之亲权而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保护;其三,国家在充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时,应当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行事[1]。故而,国家作为“超级父母”,有义务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要坚持“保护优于刑罚”的原则。加之“慈幼恤孤”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因而在少年家事审判改革中应当始终以国家亲权理念为导向。
(二)未成年人福利
据《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福利有两层涵义: 其一,系指任何情形下的幸福(well-being)及繁荣(prosperity);其二,系指向急需帮助的经济窘困之人提供诸如食品券(foodstamp)及家庭津贴(family allowance)[2]。 “社会福利”作为“福利”概念的延伸,旨在突出国家作为福利提供者,当出现社会或家庭无法满足社会群体或个体的基本需求时,有责任弥补这一缺失,满足其基本需求。未成年人福利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也包括两层涵义:其一是指“政府或社会针对全体儿童的普遍需求,为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及社会潜能的最佳发展而提供的各种服务”;其二是指“政府和社会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及家庭提供的各种支持、保护和补偿性服务”[3]。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侧重点在于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有效预防、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及延伸帮扶,即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佳保护。鉴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在他们违法犯罪时,更迫切需要社会的有效保护和指导,使他们在将来重新适应社会生活、健康成长。我国将来的少年家事审判改革应当以实现未成年人福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恢复性司法
与未成年人福利相承接,少年家事审判改革还当以恢复性司法为指引,与实现未成年人福利形成一体两面的工作格局。传统的刑事司法将犯罪行为视为对被害人及国家利益的损害,由国家代替受害人对犯罪行为人施以惩戒,这一方面忽视了受害人自身的诉求,另一方面剥夺了犯罪行为人采取其他方式加以弥补、悔过的机会。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就意识到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恢复性司法开始萌芽,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通过“社区司法”、“家庭组会议”等形式的刑事和解方式,深层次化解双方矛盾,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得以盛行,与涉少司法审判的联系日益紧密,开始注重对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教育,特别是庭后的帮扶。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与我国的“和”文化一脉相承,即注重恢复被扰乱的社会秩序,平衡国家、犯罪人和受害人三方的利益。未来的少年家事审判改革应当以恢复性司法为理念,在保护与惩戒的博弈中更加偏向未成年人利益的最佳保护,减少二次伤害。司法-社会一体化的理念旨在实现少年司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整合司法与社会两个维度的资源,建立起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屏障。
三、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价值追求
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指向”[4]。那么,以上述司法-社会一体化理念为指引的少年家事审判改革,其欲实现的价值是何?
(一)预防少年违法犯罪
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首要目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往往出于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原因,未成年人尚不具备完全辨别是非的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极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作为“国民之父”,国家有责任本着为少年谋福利的理念,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防止其在社会化过程中步入歧途并及时挽救轻微越轨少年。然而,并不存在完全能够防止未成年人偏离正轨的保护体系。恢复性司法理念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围绕被指控少年为什么会违法犯罪,国家、社会、少年自身谁应该负更多的责任的问题,侧重于教育、感化,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其不受二次伤害,并对其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处置措施,从而使得该类少年重新适应社会,预防其再次犯罪。
(二)实质平等
平等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成长而不断解释和实践的过程 ”[5],它具有双重维度——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前者指法律和制度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个体,机会平等、平等对待、程序正义、权利平等往往是其表征;后者指结果上的平等,是为了矫正由于形式上的平等所带来的现实的不平等,承认差别的存在。“不同情形不同对待”的实质平等,正是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价值追求。少年违法犯罪行为人的生理和心理并不成熟,应确保处置措施与违法犯罪行为情况及本人的情况相称。例如,考虑到行为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或具有痛改前非的意愿,而给予特别对待。这种“相称”旨在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处置措施符合少年的福祉,而不是单纯的惩罚。与传统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有所区别。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4款所规定的“照管、指导和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 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即是确保对触法少年的处置符合其福祉以达到与成年违法犯罪行为人在结果上的平等。
(三)教育与矫正
少年家事审判改革注重庭中的教育感化,就是要以教导未成年人为价值追求。首先,教育价值与“德主刑辅”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对触法未成年人的处置更应侧重道德教育的力量而不是法制的强制力;其次,以教育代替刑罚,寓教于审,整个处置过程都蕴含着教育感化的力量和价值追求;最后,以教育保护为依归,在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处置时,首先必须考虑保护性处分,只有在保护处分不奏效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当的刑事处分。需要指出的是,对触法未成年人的教育不仅表现在对其思想品德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实现这一价值,不论未成年人是否被处以监禁,社会必须担负起教育职责。“矫正”价值是教育价值的延伸,不仅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更能彰显少年家事审判的科学精神。大多数触法少年在心理上都会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缺陷,如抑郁、固执、偏激等,这种人格缺陷往往是道德教化所力不能及的,这就不得不依赖于作为“准医学”模式的矫正,通过司法机关的介入,由专业机构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辅导和治疗,矫正他们的不良性格及性情,以便他们在社会中顺利成长。教育与矫正的价值追求面向触法未成年人的未来,最终目的是使其复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四)个人、家庭与社会协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法社会学思潮兴起并发展壮大,此时期突出强调社会为个人之集合,两者休戚与共,个人对社会有应尽之义务,社会于个人亦应负保护之责。法社会学具体到少年司法领域,则孕育出这样一种思潮: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并非其个人原因所致。因此,对触法少年不能如同成年犯罪行为人一样适用刑罚,而应侧重对其违法犯罪原因的探求,教育感化其思想,矫正其不良心理,令其重归社会。实际上,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还存在一种实体即家庭,个人组成家庭,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少年家事审判改革一个重要的价值追求便是促进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少年审判与家事审判的一体两翼使实现上述价值成为可能。两者在具体案件中具有牵连性,即涉少案件的成因往往基于家庭生活的不幸;在审判方式上具有同质性,即都要在个案之外寻找双方冲突的根源;两者都具有社会性,即都借助于社会力量保护未成年人或者妇女权益。故而,未来的少年家事审判宜向少年审判与家事审判整合,一方面利用少年司法的“政法一条龙、社会一条龙”工作机制来处理家事纠纷,尽可能维护家庭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妥善处理家事纠纷,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健康有序的家庭环境,从而有效减少其违法犯罪的诱因。
结语:在构建独立的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还不具备现实条件的情况下,将涉少案件与家事案件合二为一,形成一体两翼的工作格局,是一种适宜的过渡手段。这种少年家事审判改革应当在司法-社会一体化的司法理念指导下,以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现实质平等、注重教育与矫正、实现个人、家庭与社会协同发展的价值为依归,最终为平稳过渡到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创造条件。
[1]姚建龙:《国家亲权理论与少年司法——以美国少年司法为中心的研究》,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2]张鸿巍:《儿童福利视野下的少年司法路径选择》,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12期。
[3]徐月宾:《儿童福利服务的概念与实践》,载《民政论坛》,2001年第4期。
[4]王雪梅:《论少年司法的特殊理念和价值取向》,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第5期。
[5]王立:《平等的双重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载《理论探讨》,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向宁)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研究”(课题编号: 15FXB027)、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法律规制研究”(课题编号:15SFB5031)、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研究课题“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课题编号:2016B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