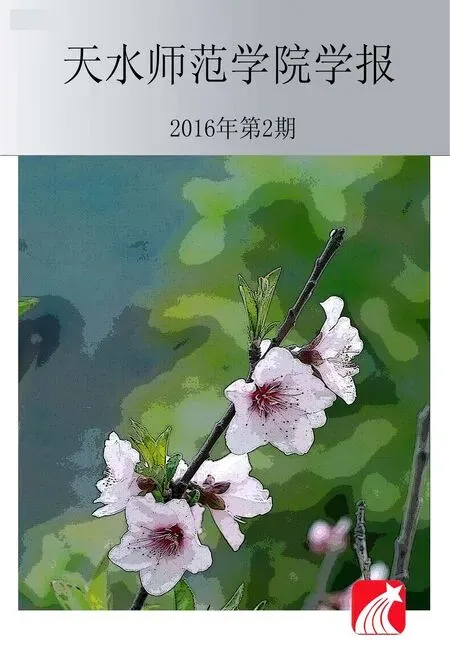以甘肃省宗教传播现状为例谈谈网络宗教
王 红,王 瑛(.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天水师范学院 财务处,甘肃 天水 7400)
以甘肃省宗教传播现状为例谈谈网络宗教
王红1,王瑛2
(1.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2.天水师范学院 财务处,甘肃 天水 741001)
互联网作为一个无限巨大的多媒体综合信息平台,将当今世界置于无处不在的信息化中,宗教传播也不例外。网络在其公开性、共享性、包容一切的特点之下也具有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这就使得网络时代的社会结构由稳定的金字塔式向扁平化转变,加剧了其不稳定性。“蝴蝶效应”也比任何时候更极致化,原本牢固的形象在网络世界变成了易碎品。另外,宗教作为一种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现象,以“虚拟意识”的力量来影响人的思想和社会行为。因而对于网络这一新媒介与宗教的结合,其社会功能对于不同个体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其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网络宗教;新媒介;传播方式
一、甘肃省概况及网络发展现状
(一)甘肃省概况
甘肃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根据《甘肃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3164756人,占90.57%;各少数民族人口为2410498人,占9.43%.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74个百分点。目前,甘肃境内共居住着44个少数民族,世居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依次为:回族、藏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保安族、蒙古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和满族等民族;除了这10个主要少数民族外,还有维吾尔、壮族、土家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成份。[1]东乡、裕固、保安为甘肃省的3个特有少数民族。
甘肃也是中国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重要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区。甘肃现有5种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其中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信仰的人口较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是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哈萨克族;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2]此外,道教也有很长的传播历史,相对而言,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和信仰较晚。虽然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在各民族中都有信仰,但人数不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来,五大教派之间互相尊重,团结稳定,成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相互理解的文化基础。
因此,甘肃省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省,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而言,宗教信仰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间所形成的关联较之于一般大众的文化传统更为密切。在这种特殊的文化传统绵延至今的承传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宗教信仰体系,拥有难以分割的精神关联。因而宗教信仰的传播也是文化传播中最为复杂而玄奥的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人们在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也无法剥离开无所不在的宗教文化语境。
(二)甘肃省网络发展现状
根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中国居民上网人数已过半;其中,2015年新增网民3951万人,增长率为6.1%,较2014年提升1.1个百分点,网民规模增速有所提升。[3]
《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甘肃省网民规模达100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38.8%,网民增速为5.7%,普及率排名居第28位;手机成为甘肃省网民上网的第一大终端,使用率为80.8%.此外,甘肃省网站数为9364个(不含.edu.cn),去重之后网页总数为266,891,205个,其中静态网页171,214,001个,动态网页95,677,204个。《报告》中按更新周期分类的网页比例对甘肃省网页做出统计,统计显示,一周更新的比例为10.2%,一个月更新的比例为25.4%,三个月更新的比例为32.4%,六个月更新的比例为22.1%,六个月以上更新的比例为9.9%.甘肃省网民结构统计结果,从网民年龄结构来看,20~29岁网民居首,30~39岁次之;从网民学历结构来看,高中/中专/技校学历者居首,大学本科、高中/中专/技校学历者比例较2014年增长较为明显,网民结构更趋稳定成熟;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有效改善农村地区居住环境,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农村非网民的转化率,农村网民在全省网民中的占比增加,充分反映出2015年农村互联网普及工作的成效。由一系列数据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甘肃省互联网产业发展稳中有升,全省网民规模稳步增长。由以上数据可见,甘肃省网络媒介发展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这也为甘肃省网络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和活跃的可能性。
二、“网络宗教”
(一)“网络宗教”的界定
“宗教”这个词原为外来词。《说文解字》中对宗教的解释为:“宗,尊宗庙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通俗地讲,就是有其创始人,也就是崇拜的对象,即为“宗”;有虔诚的崇拜者,有其自身的祭祀礼仪与宣传活动,即为“教”。在任继愈《宗教大辞典》中的解释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其特点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信仰者相信这种超越一切并统摄万物,拥有绝对权威,主宰着自然和社会的进程,决定着人世的命运及祸福,从而使人对这一神秘界产生敬畏和崇拜的思想感情,并由此引申出与此相关的信仰认知和礼仪活动”。[4]从这一定义可以得出结论,宗教之所以能够为广大教徒所信仰追随,一方面有其教义本身的因素,还需要有相关的宗教礼仪活动,以便于其进行宣扬和传播。而我们可以把宗教传播看做是这些活动的总和。由此可见,宗教如果想其教义传播广远,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不论全球性还是区域性宗教,都必须与一定的传播方式相结合,否则宗教的信条就不会为人所知,更谈不上作用于人类社会和影响历史的发展。至此我们可以界定“网络宗教”,即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宗教信仰,是宗教活动在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是宗教组织或教徒在网络平台所有与宗教相关的活动的总和。网络宗教是网络时代的必然发展趋势。
(二)“网络宗教”的现状
在互联网业高速发展的今日,网络宗教类信息数量及其庞大,早已无法用数字来精确衡量。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网络宗教形式为:宗教网站、宗教论坛、宗教博客及微博、宗教虚拟社区、宗教聊天室、即时通讯群组、宗教音视频、网上宗教电台、宗教用品和印刷品交易网站、宗教类手机WAP站,以及移动互联网上的“微信”群和各种各样的宗教类APP软件等等。各宗教在网上已经极其活跃,比如宗教类用户或信息在当下最火爆的“微博”和“微信”平台随处可见。[5]
网络时代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网络化,思维网络化,宗教与网络的结合也必然会顺应这一网络化的趋势。然而关于Web2.0时代“网络宗教”的兴起众说纷纭。一些宗教领袖认为,在线宗教团体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宗教群体形式,如宗教组织、宗教社区等。他们担心人们会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网上的宗教聊天室或电子邮件团体上,而不再去教堂(或现实中的宗教活动地点)。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种担心某种程度上是多余的。詹姆斯卡茨和罗纳德赖斯通过研究发现,那些热衷于网上宗教活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宗教热情和参与度以及对宗教组织的归属感往往更强。而且这种归属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互联网应用,一般既不会刺激,也不会削弱他们对线上宗教团体的参与程度。卡茨认为,互联网不但不会替代现实中的人际交流,却恰恰是其有益、必要的补充。[6]事实上,无论网络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或是中性,宗教与网络媒介的相互作用都是革命性的。
三、网络宗教——传统宗教传播在网络视域下的新态势
媒介技术的飞跃发展重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时空经验。新旧媒介的交替也给宗教传播带来了新的面貌。无论是作为宗教传播载体的新媒介本身,还是与新媒介结合后的网络宗教,都蕴藏着巨大的可能性,给宗教以一个全新的传播领域。
首先,媒介形式的变革导致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行为发生变革,[7]也就意味着网络宗教下人们进行宗教信仰的方式和行为发生变化。传统宗教系统下的教民接触宗教大多通过阅读宗教书籍,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金刚经》等等,或者教民在生活中参与宗教类仪式或活动来进行宗教信仰活动。而网络宗教系统下的教民,他们接触宗教的方式网络化,如电子书籍、网络聊天室、网络社区(论坛)、网络聊天群组等新兴的方式,让他们可以不需要像传统教民那样亲身参与到宗教仪式现场就可以进行宗教信仰活动。网络宗教传播不仅是一种方式还是一种行为,教义从话语和行为——即传播的工具化中分离出来,那么不仅仅增加教义宣传的可能性,同样也会改变教民对宗教的感知。
其次,新的媒介的诞生必然导致宗教传播方式的变革,网络宗教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宗教仪式形态,开始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宗教“虚拟世界”。传统的宗教传播,主要的传播方式是人际传播,以语言和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控制手段,面对面进行传教,教堂(或者说是各类宗教规定的聚集地点)是主要的宗教传播场所。传统宗教的传播是教义和教会仪式,传统宗教传播的过程往往是单向的,自下而上地进行宗教传播。即使有互动也是受到限制的,教民大多虔诚地接受教义,很少会提出自己有别于其他教众的理解。而网络宗教传播,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传播方式,以掌握互联网即使通讯技术作为传播的手段,传教的场所虚拟化,对于信仰得教的途径,也不再是“上传下应”的,而是一种共享信仰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同一宗教系统的教民而言,宗教思想是公共的,其核心是将教民以共同信仰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宗教传播方式。再进一步说,网络宗教相对于传统宗教而言,改变的不仅是宗教传播方式,还有整个宗教活动的仪式。这种新的宗教传播方式,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的再现或者描述,事实上它是对宗教世界的改造与构建。当然在传统宗教中是很难实现的,而随着网络宗教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可能。
再次,作为网络宗教载体的网络不仅是宗教传播的工具,其本身作为一种信息可以看做是宗教传播内容的创新。正如伊尼斯所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8]网络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公开化、共享性的综合性媒介。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在其整个历史中都在宣扬其教义和主张,传统宗教和网络宗教都是基于同一目的——即宣扬教义的不同形式的传播。至今我们仍承认教义在一个宗教思想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然而网络以一种公开化的互动信息形式,对宗教所传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播内容不仅有宣扬教义,描述宗教历史中的经典传说或故事的部分,而且还需要力图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及信念明晰化,站在自己的地盘做自我辩护,而不是装模做样地搬出“上帝怎么说”或“神明怎么说”。这就淘汰了一些讲神话编故事以塑造“神”(造物主)无所不能的形象的宗教传播内容,少了一些玄学和宿命论,多了一些科学理性的话语和对信仰的理性思考。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改变看做是对宗教传播内容的修改、创造、或是一个共享宗教文化的过程。这就使得网络宗教成了网络文化一种独特的文化构成。
另外,网络宗教基于网络的内在性质,尤其是其开放性、匿名性和共享性,使得宗教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受到削弱。媒介的变化通过改变高地位人物的可接触性,也会影响到宗教等级制度,支持物质隔离和社会不可接近性的媒介,会支持等级的神秘化;而危害这种关系的媒介,可能会降低许多角色的高地位。在传统宗教中,宗教等级极为严格,宗教内部的上层人物等同于造物主在人类社会的“代理人”,地位神圣而不容侵犯。网络宗教使得宗教等级在网络的平台上趋于平等化,宗教内部上层人物不再是神秘而不可为人知的。同时,网络宗教的受众也在放生变化,他们可以是虔诚的教徒也可以是无信仰的民众,只要是通过网络宗教平台的注册用户,都有接触宗教并且发表言论的机会,宗教神圣的地位也在网络背景下被削弱。
最后,究其传播效果,网络宗教相对于传统宗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了无限的延伸。传统宗教的传播往往是区域性的,比较倚重于时间的传递。传统宗教在面对面传教的过程中,对教民的影响是直接的,其传播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而在网络形成的虚拟时空环境下,宗教组织也转变为“虚拟社会群体”,这一虚拟社会群体超出了空间上的界限,其范围可以是区域性的也可以是全球化的。其网络宗教活动在整个地球上同步传播,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网络教民甚至是接触网络的民众都具有了获取这些信息的相等机会,带来了新媒介下的宗教文化共享的网络氛围。然而虽然网络宗教传播的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其传播效果相对于传统宗教则相对较弱。网络宗教虽然可以通过网络将其教义迅速抵达广大教众,但是同时也将其传播效果分散化。网络虽无孔不入,但它像墙和窗户一样可以显示某些东西,也可以隐藏某些东西,既能够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也能给出排斥和隔离感。加之,网络传播渠道中充斥着“噪音”,不易形成针对性直接性的影响力,较之传统宗教直达教民内心的传播效果,网络宗教的宗教文化科普性功能更强。
在目前网络宗教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妨把网络宗教看做是宗教在与新型传播媒介结合的过程中吸纳包容的一种手段。除了其传播教义的功能之外,更是一种交流和讨论,甚至是基于宗教信仰对于一种对事物更开放的看法的表达。传统宗教欠缺用来开展这种开放式交流所必需的方式和场所。而网络宗教开辟了传统宗教没有的空前开放的文化交流平台,承担起听取某些观点,领会教众的想法,拓展教义的理解疆域,商讨其他可追求的实现传播教义目标的功能。在网络传播中,其双向和互动性使得传者和受传者的身份界定较为模糊,传播也由单向向着一对多、多对多等多维度的模式转变。网络宗教中,网络成为最大程度上争取教徒、传播教义、开展宗教礼仪活动的新型传教平台。可以说,网络宗教是对传统宗教的创新,使宗教这一特定的世界观在网络世界得到了描述和强化。这一种宗教的网络传播不仅达到了传播教义的目的,而且获取了教民的信息反馈,在满足了教民内心信仰需求的同时,也使宗教自身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地革新以更好地实现其传播。
四、网络宗教对网络及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
宗教信仰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属于私有领域的半自治组织,允许矛盾纷争,又是意识形态激烈争夺之地。因而与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建设有着及其密切的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网络宗教,是网络时代宗教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其影响力也随之空前放大
网络将过去社会依赖物质地点作为接触或隔离他人的首要决定因素的状态被打破,[9]至少在网络虚拟时空里宗教的传播是全球性的,即时性的。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如果将他们(宗教、道德、权威、传统价值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通过精神传输的习惯予以电子物资化,他们的威力将会倍增:电子传教士与互动式基本教义派网络比起那种遥远的、具有领袖魅力的面对面传输方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更有效率、更具穿透性的教化形式。”[10]那么我们可以确定,网络宗教是宗教传播在时空上的迁移,是宗教在网络上的传递。传播教义是这种时空迁移背后的主要动机,它的最高目的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宗教世界,[11]并史无前例地穿越了整个地球。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避免与之接触,其传播速度之快,波及之广以及影响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就意味着网络宗教在传统宗教基础上,其威力是“爆炸”性的。首先,网络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次,借助于网络,人类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密切的相互关系、无法独居孑然一身的、紧密联结的小社区。在网络宗教社区中,不同身份的用户彼此互动,信息语言的暴露也更为充分和全面。为人们开拓眼界和分享新的体验提供机会的同时,也会加剧人对事物整体感知和思维的特性及各种社会功能的聚合效应。不仅当前的宗教传播活动对人们的宗教信仰行为有所控制,还将过去一切分离了的宗教及功能都在这网络虚拟时空中重新聚合起来,既是形式上的聚合,更是内在功能的聚合。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是可以在瞬间发生的、蔓延至全球的,其威力堪比“氢弹爆炸般猛烈”。[12]
(二)网络的不确定性决定网络宗教传播具有不稳定性
麦克卢汉说过,就像鱼并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媒介构成了我们的环境,并维持这种环境的存在。[13]网络并不单纯是两个或多个环境之间传递信息的渠道,而且也是一种环境。网络文化,它代表了人类生活的本质、人类生活的条件与意义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的表现,而宗教作为一种独特历史文化存在于网络,其不稳定性是由网络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决定的。在这个网络社会环境里,削弱了在现实社会中的权威、身份、传统的眼光的控制,通过网络与他人建立“联系”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网络没有制造社会入口,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里,传统媒介中对信息传递的空间的隔离和入口的防卫在网络面前起不了任何作用。首先,网络宗教以网络作为开放性的平台,其传播者和受者的身份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既可以是虔诚的信徒,也可能是其他身份的个人或团体。其次,网络宗教使宗教个人化,私人化。换句话说,网络使个人独立完成宗教信仰活动成为可能。网络教民具有强烈的个人自主性,通过网络教民可以自主地、有选择地进行宗教信仰活动。再次,世界是一种熵。网络世界永不停息的信息重置更是给信息熵提供了培养皿。这就使得宗教在网络的传播中其内容和形式存在着不可预测性。加之,网络所传递的宗教信息在个人价值观念及文化差异等因素的作用下也很容易造成误读甚至出现断章取义。此外,网络监控体制的缺陷,对于有意使用迷惑对方或对对方采取支配态度的隐语并不能完全甄别并杜绝,这也给了极端主义势力扩张的可能。
由上述的风险,本文建议为保障网络与国家安全,国家有必要建立起网络宗教管理机制,以促进网络宗教和谐健康地发展,从而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五、结语
我们从传播媒介受技术的影响而产生的变革与更新方面可以得出,互联网技术的分散性、无中心性不但没有削弱宗教与社会生活之间交互影响的关系,反而进一步密切了宗教与社会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在网络环境中的宗教活动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前景,同时也暗潮涌动,两者的关系特征也会在网络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步显现。
最后,通过传播方式在宗教传播中的转变来观照宗教传播,这是宗教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但就目前“网上宗教”所处阶段而言,还只是传统宗教在互联网平台的延伸,还未有研究明确表明互联网传播方式对宗教意识、行为及其组织结构的深层影响,因而本文也不会过早地对“网络宗教”的性质盖棺定论。
[1]种媛.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析——以西北省区甘肃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3,(8):894-897.
[2]宫玉宽.民族认同与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认同的影响[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8):18-24.
[3]CNNIC:中国网民达6.88亿上网人数已过半[EB/OL].中国搜索互联网.
[4]吾淳.理解信仰问题的主要视角[J].世界宗教研究,2007,(2):11-20.
[5]赵冰.“网上宗教”现象在中国的现状、特征与影响[J].世界宗教文化,2015,(1):100-105.
[6]赵冰.宗教的虚拟化传播与国家安全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
[7]约书亚·梅罗维茨.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8-64.
[8]哈罗德·伊尼斯.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7-48.
[9]保罗·利文森.熊澄宇,译.软边缘:信息革命历史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91.
[10]曼纽尔·卡斯特.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65.
[11]詹姆斯·W·凯瑞.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12]黄晓钟,等,主编.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50.
[13]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 王小风〕
An Analysis of the Online Religion——Taking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ang Hong1,Wang Ying2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nzhou Gansu730030,China;2.Finance Division,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With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the world has been put in the ubiquity of information,even reli⁃gions is no exception.Internet is an infinit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platform.Un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ity,sharing and virtual,it also has some possibility and uncertainty.Social network structures would become vulnerable with some complicated and uncertain network factors.The social structure is changing from pyramid to flattening.A value much greater than one would lead to a chaotic system,as in the butterfly effect.In addition,the religion is an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phenomenon in human society which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believers'thoughts and social behaviors.Religious organization has turned into a virtual community on line.In the new mode of trans⁃mission,the religious composition is more complicated.Therefore,the network religious claims our highest attention.
online religion;new media;mode of transmission
B920
A
1671-1351(2016)02-0060-05
2016-01-13
王红(1991-),女,江苏徐州人,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