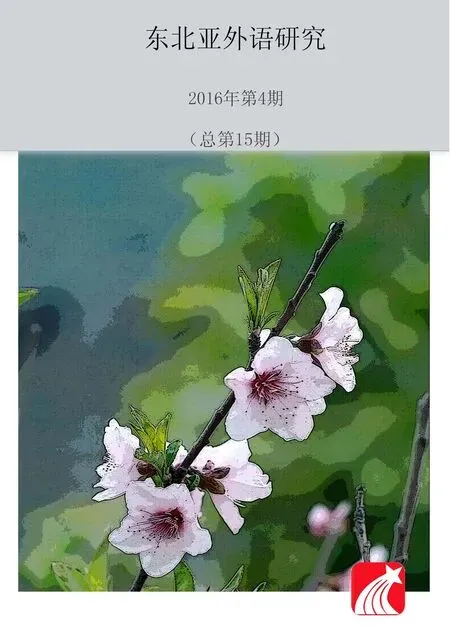圣经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罗约翰和李树廷圣经韩译为例
陈艳敏
(华中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圣经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罗约翰和李树廷圣经韩译为例
陈艳敏1
(华中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主体性包括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在圣经翻译中,译者的能动性、受动性与为我性分别在神译名翻译、信仰背景、译经原则中凸显。本文对比罗约翰和李树廷的信仰背景、翻译原则及神译名翻译的差异,指出在圣经翻译方面,译者的信仰背景是至关重要的要素,译者信仰背景塑造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决定译经策略与神译名的翻译。
罗约翰;李树廷;译者主体性;信仰背景;神译名
一、译者主体性
自从“主体”和“主体性”等哲学概念被引入翻译研究中,译者主体性便受到译界关注,并成为译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引发了一场关于“何为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仲伟合、周静(2006∶43)在诸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做出了比较全面的界定:“译者主体性指在尊重客观翻译环境的前提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译入语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体现了译者在语言操作、文化特质、艺术创造、美学标准及人文品格等方面的自觉意识,具有主动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受动性等特点”。有关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的讨论,金胜昔、林正军(2016∶116)总结出三种观点:“一是能动论,认为译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凸显,这种观点聚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二是制约论,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受动性,译者受到来自内外部条件的制约,三是辩证统一论,主张译者主体性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能动论者认为,“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简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陈先达,1991∶115),“主观能动性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查明建 田雨,2003∶21);制约论者认为,“译者主体性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然受到原作、原作者和其他外部力量的控制”(陈梅,2006∶51);辩证统一论者认为,“主体性说到底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主体性只有在与客体的对象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陈大亮,2004∶4),查明建、田雨认为主体性的特点除了能动性和受动性之外,为我性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为我性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查明建 田雨,2003∶22),笔者赞同查明建、田雨的观点。这三者的辩证关系可以解释为:“译者的受动性是其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而译者的主体性也正是建立在其受动性基础上的能动性的发挥”(阮玉慧,2009∶85),译者的为我性正是建立在受动性基础上。在圣经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等三个特征分别表现在神译名翻译、信仰背景、翻译原则上。最凸显译者主体性之能动性的就是神译名翻译,因为圣经启示的那一位神,是译入语民族所不认识的,在译入语中也没有对等语,因此神译名的翻译最能体现译者的能动性的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译者信仰背景制约,信仰背景包括对圣经的认知程度、神学体系构架及差会派别等,这些因素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使译者无法超越信仰背景的局限。译者采用何种翻译原则体现了译者的为我性,“译者主体性中的‘为我性’,在翻译理论上的表述,就是汉斯·弗美尔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查明建 田雨,2003∶22),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否能达到,翻译原则起到重要作用。在圣经翻译中,译者的信仰背景、译经原则、神译名的翻译是辩证统一的,译者的信仰背景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基石,译经原则的确立、神译名的翻译就是建立在信仰背景这一基石之上的。
二、从信仰背景差异探究译者主体性之受动性
在圣经翻译中,译者主体性与译者信仰背景密不可分,特别是译者神学知识框架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虽然罗约翰和李树廷都是基督徒,同样敬畏神,但他们信仰的深度不同,对圣经认识的深度与广度各异,同时,神学知识构建体系不同,这些因素制约了罗约翰和李树廷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1842年8月9日,罗约翰出生在苏格兰北部的尼格,1865年罗约翰进入爱丁堡的联合长老会神学院学习,1870年神学毕业。读神学期间,他一直在苏格兰西部使用盖尔语的岛上的一间教会服侍,毕业后立志向使用盖尔语的人传福音,这一愿望落空后,他决志去中国宣教。1871年末,罗约翰决定去中国宣教,并向苏格兰海外宣教部提交了材料,1872年2月27日海外宣教部选派他为中国宣教士,同年3月20日罗约翰被按立为牧师。1872年4月初受苏格兰长老会的差派,携妻子远渡重洋,8月23日到达中国的烟台,在苏格兰圣公会负责人Alexander Williamson的劝告下,10初前往商埠营口,购地筑室开始宣教工作。他用一年时间学习汉语,1873年5月12日首次用汉语讲道20分钟。1875年,着手在当时不允许外国人常住的沈阳设立宣教部,他效法保罗,在中国东北巡回传道。1874年,高丽门之行,在中韩边境遇见韩人,这激发了罗约翰向韩民族传福音的热情。当时,韩国闭关锁国,禁止西方人入境。在这种情况下,罗约翰能做的是将圣经翻译成韩文,因为圣经记载了福音真理,向韩民族传福音的捷径是让韩国人阅读自己民族语言的圣经,因此,将圣经翻译成韩文成为罗约翰向韩民族传福音的首要任务。“为此,罗约翰不惜高价聘用韩国人学习韩国语言文化历史,组建译经团队,从1875年到1887年翻译出版了韩文新约全书”(陈艳敏,2015∶82)。
李树廷1843年左右出生于汉阳,属王室血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成为政府史官。1876年韩日签订《韩日修好条约》,此后,韩国多次派团去日本考察访问。1882年9月,李树廷随团到达日本横滨,之后,作为东京大学的韩语教师留在东京。为了学习农学知识常去拜访日本著名农学家津田仙②,津田仙家中墙上写着“山上宝训”③的牌匾引起李树廷的注意,以此为切入点,李树廷从津田仙那儿了解了圣经知识,津田仙成为李树廷的圣经导师。津田仙送给李树廷一本中文圣经,并介绍他跟长田时竹学习圣经,1882年12月25日,津田仙把李树廷带到筑地教会,参加圣诞节礼拜,借此机会,津田仙将李树廷引荐给安川亨牧师。1883年4月29日,安川亨牧师给李树廷施洗(이만열,2015∶7)。李树廷成为首位受洗的韩人基督徒。李树廷受洗的消息受到美国驻日宣教士路米斯的关注,他深信福音将藉此进入朝鲜半岛,他认为如果让李树廷将圣经翻译成韩文,可以打开韩国的福音之门。于是,路米斯亲自登门拜托李树廷,邀请李树廷将圣经翻译成韩文,李树廷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路米斯没有像罗约翰一样,校对李树廷的译稿,而是请诺克斯和安川亨帮助李树廷,路米斯认为有了这二人的帮助,就不必担心翻译的准确性。因此,李树廷成为在日本翻译韩文圣经的主译者,从1883年到1885年翻译出版了马可福音,史称“李树廷译本”。
综上所述,罗约翰和李树廷的信仰背景有很大的差异。罗约翰读过神学,被按立为牧师,乐于传福音,成为苏格兰派往中国东北的宣教士,并效法保罗,在东北巡回传道。翻译韩文圣经时,罗约翰已经是明白圣经、热心传福音、信仰成熟的宣教士,他不仅是韩文圣经翻译的发起者,而且是韩人译员初稿的校对者、决策者。而李树廷在日本信耶稣几个月后,就开始翻译圣经,他没有读过神学,作为初信者,他也不是太明白圣经,在他的信仰告白中,引用圣经约翰福音14章的“夫父在我我在父”,将此理解为神人感应,可以看出他还不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与世人不同。二者的信仰背景差异塑造了二者不同的主体性,这也在二者的圣经译本中留下了烙印。
三、从翻译原则差异探究译者主体性之为我性
圣经翻译采用何种翻译原则,体现了译者的意向性与目的性,译者的“意向性与目的性是主体性的内容”(刘军平,2008∶54),译者翻译圣经的意向与目的决定翻译标准的走向。“译者能够有意识地厘定自己所遵循的翻译原则,而且这种原则因人而异,是译者主体性介入的生动体现”(朱献珑 屠国元,2009∶122),译者目的性彰显了译者的为我性,译本的风格是译者意向的表现形式。在翻译风格上,罗约翰译本是通篇韩文的大众文体(如图一所示),李树廷译本是韩汉文混用的学者文峰(如图二所示)。在翻译原则上,罗约翰是专用韩文、符合韩语语言习惯意译,李树廷是韩汉文混用的直译。
专用韩文是罗约翰翻译韩文圣经的总方针,这一方针的制定与他的宣教目的息息相关。罗约翰翻译韩文圣经的出发点是“让每个韩国人能读懂圣经”(Ross,1883a∶209),罗约翰认识到有80%的韩国普通百姓不懂中文,而韩文是任何阶层的人都容易诵读的,因此,在语言的使用上选择从贫民到贵族都懂的韩文,不使用汉字,而且在选词上尽量避免使用占韩文词汇70%的汉字词,甚至有的可以用汉字词的地方,罗约翰刻意用韩文固有词的方式表达。
“符合语言习惯地呈现原文意思”是罗约翰翻译韩文圣经的总原则,罗约翰认为“必须把原文翻译得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单纯直译不总是符合语言习惯”(Ross,1883b∶494)。因此罗约翰在译本中进行了重大改写,朝鲜语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对人的社会地位都有拘泥形式的区分,年龄和级别相同的可以直接使用第二人称“你”。对不熟悉的人或社会地位高的人不能直接使用英语和希腊语中的第二人称“你”,对他们使用第二人称代词是极其失礼的。这一点影响了整个译本,当用第二人称表达神时,罗约翰使用了间接表达方式。比如,在主祷文中,“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面的“你”都译为“父”。当门徒称呼耶稣时,总是被间接地译为“主”或“老师”,罗约翰认为这种改写对准确翻译圣经至关重要。
其次,标准化猪舍是规模化养猪的必备条件。选择与饲养规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是提高生猪生产水平和养猪效益的关键。一定要根据种公猪、繁殖母猪、仔猪、育肥猪的生理特点,建造科学合理的猪舍。在施工过程中可根据不同地形、地质情况、建筑材料等适当调整,做到科学合理、经济适用。
李树廷在诺克斯和安川亨的指导下,从1883年到1885年翻译出版了马可福音。他在翻译韩文圣经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翻译原则,只是借鉴了日汉文混用圣经的模式,在翻译韩文圣经时,采用韩汉文混用的方式,将中文圣经直译成韩文。李树廷是崇尚中文的韩人官吏,他的中文水平与中国学者不相上下,在翻译韩文圣经时,他没有舍弃自己钟爱的中文,同时,这也是他受日本日汉圣经文本影响的结果。他首次尝试翻译韩文圣经是给中文圣经加上了韩文的助词和语尾,出版的马可福音借鉴日汉文混用圣经,翻译出版了韩汉文混用马可福音。

图一 1887年罗约翰译本马可福音第一章

图二 1885年李树廷译本马可福音第一章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之为我性在翻译风格与原则的选择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罗约翰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为翻译团队制定了翻译原则及方针,明确要符合语言习惯地呈现原文意思、专用韩文。这些原则的制定也跟罗约翰的宣教热忱及精通韩语息息相关,正因为他通晓韩文及韩文化,才使他能符合韩语语言习惯地翻译韩文圣经;正因为他有向朝鲜半岛人民传福音的热忱,才使他坚持只用韩文、不用汉字的原则,将韩文圣经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而李树廷没有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尽量按照自己的中文实力,将中文圣经直译成韩文,并且借鉴了日汉文混用圣经的结构,将韩文圣经翻译成韩汉文混用的模式。二者的主体性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译经原则,孵化出截然不同的韩文圣经译本:一个是专用韩文、译语符合韩语的语言习惯;一个是韩汉文混用、译语直译中文圣经。称前者是中文圣经的再创,后者是中文圣经的重现,也不为过。
四、从神译名差异探究译者主体性之能动性
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神译名的翻译最能体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凝聚了译者的创造性与实践性,而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受制于译者的信仰背景。罗约翰和李树廷圣经韩译分别得到了苏格兰圣公会和美圣公会的资助,这两个圣公会在中文神译名翻译上的立场不同,此立场差异同样影响了韩文圣经神译名的翻译。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为例比较译本和底本神译名如下:
上帝子耶稣基督福音之始也 (麦都思,1852∶31)
하나님의아달예수키리쓰토복음의처음이라
(John ross,1887∶44)
神之子、耶稣基督之福音、其始也
(裨治文 克陛存,1863∶30)
神신의子자耶稣예슈쓰基督크리슈도스의福音복음이니그쳐음이라
(이수정,1885∶1)
作为苏格兰圣公会的宣教士,罗约翰站在“上帝”版的立场,在底本圣经的使用上,选择了1852年出版的“上帝”版的委办译本《新约圣书文理》。如何翻译底本圣经出现的“上帝”,是罗约翰首先考虑的问题。在神名翻译上,罗约翰借鉴了中文圣经翻译上神译名之争的教训,没有将中文圣经中的“上帝”或“神”按照中文汉字的语音形式对等地译成韩文,罗约翰认为中文采用的任何一种译名都不适合应用到韩文。在韩文中,神对应两个词,一个是汉字词“上帝”,一个是韩文固有词“Hananim”。罗约翰认为“上帝”是道教词汇,道教虽在中国盛行,在韩国却找不到道教追随者,“上帝”一词,在传统意义上仅被学者知道,普通民众根本不知道这个词(Ross,1891∶391)。“神”一词,在韩文中从来不被单独使用,总是与“鬼”这个词一起使用,发音为gooi-shin,这两个术语的顺序总是不变的,极像罗马的拉瑞斯和珀那忒斯。“韩文的Heaven是‘haneul’,Lord是‘nim’,由二者合成的词‘Hananim’跟至高者的意思最为接近,这也是朝鲜半岛人民人人皆知的词汇”(Ross, 1883b∶494)。罗约翰以多种方式在韩人中验证了这一术语,他深信借用别国术语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此罗约翰在神名的翻译上使用了韩民族本土词汇“Hananim”。
李树廷译本是在美圣公会支持下完成的,美圣公会主张使用中文“神”版圣经,李树廷理所当然地采用“神”版1863年裨治文译本《新约圣书》为底本。“神”版圣经的中文译名直接影响了李树廷译本神译名的翻译,李树廷将神译名按照汉字语音,将神译名翻译成“신(shin)”。李树廷在翻译马可福音时,虽然得到路米斯等人的指导,但翻译主要是他独自完成的,作为信主不久的信徒,没有上过神学院,没有扎实的神学基础,对圣经的理解也不如西方宣教士透彻。因此李树廷在神译名的翻译上没有像罗约翰一样深思熟虑,单纯地按照中文圣经底本音译神名,在神译名的翻译是否恰当上,也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综上所述,在罗约翰和李树廷神译名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圣公会的制约,在底本的选用上,依附于圣公会的偏好。李树廷受美圣公会的制约,参照“神”版中文圣经,音译神名。罗约翰虽然遵照苏格兰圣公会的主张,参照“上帝”版中文圣经,但是由于他读过神学,明白圣经,了解中文圣经译名之争,在翻译神译名时,突破底本限制,将神译名翻译成韩国本土词汇,这是罗约翰信仰背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五、结语
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包含了基督教教义和基本真理,因此圣经翻译不同于普通著作的翻译。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信仰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译经原则的确立、神译名翻译的选择受制于译者的信仰背景。译者的信仰背景如同为译者圈定好的地界,在整个译经活动中,译者都不能跨越这一地界。换言之,译者的信仰背景塑造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译者信仰背景的制约。罗约翰与李树廷的信仰背景相差悬殊,罗约翰受过正规神学教育,明白圣经及福音真理,远渡重洋,在中国东北宣教,是信仰成熟的宣教士。李树廷在日本访学期间,得到日本信徒及教会的栽培,受洗后,得到美公会路米斯的青睐,受托着手翻译圣经,李树廷没有读过神学,信主几个月后就开始翻译圣经,是信仰刚刚起步的初信徒。二者的信仰背景塑造了二者不同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差异在神译名的翻译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使二者的能动性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二者受各自圣公会的制约,在中文圣经底本的选择上,罗约翰用了“上帝”版圣经,李树廷用了“神”版圣经。罗约翰为了避免中国神译名之争在朝鲜半岛重演,在神译名的翻译上比较谨慎,他没有借用中文版圣经的“上帝”或“神”,他明白神译名的翻译影响韩民族认识圣经启示的那位真神,他专研韩国历史文化,发现了比较恰当的韩语本土语神译名,此译名沿用至今。李树廷对神译名没有深刻的认识,他本人也是正在逐渐认识圣经启示的那位真神,在神译名的翻译上,依赖中文底本的译名,将中文底本的神译名直译成韩文。同时,译者的翻译原则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之为我性,罗约翰翻译圣经的目的是使整个韩民族人民都能读懂圣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确立了专用韩文的翻译原则。李树廷将读者层设定为知识分子,因此他遵循了韩汉文混用的原则。二者为我性的彰显也受到了其信仰背景的制约。
注释:
① 罗约翰是苏格兰派往中国东北的宣教士,他凭借向韩人传福音的热情,组建了以罗约翰和马勤泰为中心、以朝鲜义州青年为助手的圣经翻译团队,从1875到1887年之间在中国东北将新约圣经书卷陆续翻译成韩文,并于1887年出版了韩文版新约圣经。李树廷在美圣公会路米斯和日本教会的帮助下,于1885年在日本将新约圣经中的马可福音翻译成韩文,并出版发行。
② 津田仙1837年出生在佐仓城内,1867年赴美研究农学,回国后为日本的农业改良做出贡献,1875年在东京麻布设立农学社,开办《农学杂志》。监理会牧师Julius Soper为他施洗,为日本初期各教派的联合运动做出贡献。
③ 山上宝训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的内容,李树廷当时看到的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3-10节中的内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 Ross, J. 1883a. Corean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J]. United Presbyterian Magazine, (10)∶206-209.
[2] Ross, J. 1883b. Corean New Testament [J].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4)∶491-497.
[3] Ross, J. 1891. History of Corea [M]. London: Elliot stock, 62, raternoster row.
[4] Ross, J. 1887.예수성교전서[M].경셩:경셩문광셔원.
[5] 이만열.2015.이수정의 성경번역과 한국교회사의 의미 [J].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 (43)∶5-21.
[6] 이수정.1885.新约圣书马可传[M].横滨:日本横滨印行.
[7] 裨治文 克陛存.1863.新约全书[M].上海:苏松上海美华书局.
[8] 查明建 田雨.2003.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1)∶19-24.
[9] 陈大亮.2004.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3-7.
[10] 陈梅.2006.外部力量与译者主体性的建构[J].外语与外语教学,(6)∶50-52.
[11] 陈先达.1991.关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J].哲学原则,(9)∶115-118.
[12] 陈艳敏.2015.罗约翰朝鲜文圣经翻译考[J].外国问题研究,(3)∶80-85.
[13] 金胜昔 林正军.2016.译者主体性建构的概念整合机制[J].外语与外语教学,(1)∶116-121.
[14] 刘军平.2008.从跨学科角度看译者主体性的四个维度及其特点[J].外语与外语教学,(8)∶52-55.
[15] 麦都思.1852.新约圣书文理[M].上海:上海圣书公会印发.
[16] 阮玉慧.2009.论译者的主体性[J].安徽大学学报,(6)∶85-89.
[17] 仲伟合 周静.2006.译者的极限与底线[J].外语与外语教学,(7)∶42-46.
[18] 朱献珑 屠国元.2009.论译者主体性[J].外国语文,(2)∶120-124.
A study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Bibl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why and how the translators’subjectivity inf uences translation and explain the restrictions and purposes on the translators, by draw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John Ross’s translation and Lisujeong’s transl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us background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name of God. It reveals that the translators’ religious backgrounds are crucial factor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Bible. Both initiatives of and restriction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ome from their religious backgrounds. The initiatives of translators in selecting name of God, and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ccount for their restrained subjectivity.
Ross; Lisujeong;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religious backgrounds; name of God
H059
A
2095-4948(2016)04-0091-05
本文为2016年中央高校科研专项项目“基于译者主体性的中文圣经韩译研究”(CCNU16WY04)的阶段性成果。
陈艳敏,女,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韩中语言文学翻译、圣经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