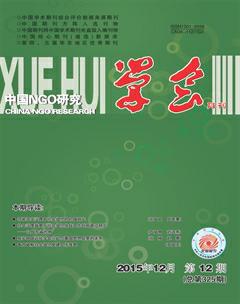邻避冲突治理中社会组织的价值研究
张广文++周竞赛
[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的邻避冲突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集中、更密集,冲突方式亦多有变化。常态化的邻避冲突治理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政界、学界孜孜探索,不断探寻行之有效的治理路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邻避冲突,挖掘社会组织的公共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邻避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怎样定位社会组织在协同治理中的角色,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功能如何等问题亟待探讨和分析。本文从社会组织的社会角色入手,基于社会资本力量,分析其在邻避冲突治理中的价值表征。
[关键词]社会组织 邻避冲突 治理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使高密度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日渐增加,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类是趋于城邦的”,在今日中国城市规划进程中,公民对城市公共环境、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公共设施的健全与全方位跟进。那些惠及全民、弊于周边居民的邻避(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设施,因特殊的城市功能性和社会价值,导致了我国诸多邻避项目陷入了“论证(环评)——开工——协商——暂停(终止)”的微死循环。邻避情结或因此激化形成社会矛盾,或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乃至群体事件的发生。邻避冲突的发生或使政府、企业在治理环节中双双失灵,专家、学者以及官员都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基于已有的冲突解决方式,笔者发现,社会组织独具的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特征,使其成为天然、有效的邻避冲突治理的“行家里手”,为有效解决邻避冲突提供了最具优化的路径依赖。
一、邻避冲突治理的居间人
邻避冲突多因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与周边居民的利益关系而导致了不和谐事件的发生。邻避设施作为一类公共项目,通常是城市规划中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设施,旨在使全体居民受益。然而,在邻避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未妥善协调好与周边居民的利益分配,利益补偿机制缺乏,导致政府、企业与邻避设施周边居民之间出现分歧,产生冲突。当周边居民在利益缺失无处投诉之时,政府即成为冲突的当事方,或被视为是企业一方利益的辩护人,故而冲突治理主体缺位或缺失的现象屡见不鲜,居民已无法对政府、企业产生信任和信赖,在居民利益受损的前提下,邻避项目自然无法继续开工,邻避冲突治理更无从谈起。比如,2012年7月2日,四川什邡民众因担心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到什邡市委、市政府聚集,并逐步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在个别人的怂恿、煽动下,少数市民再次强行冲击市委机关大门,机关大门被推倒、毁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据报道,此钼铜项目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重点项目、四川省特色优势产业重大项目和四川省“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如此大型的重点项目,由于实施之前没有与当地民众很好的沟通,导致政府和企业均成为本次群体冲突的当事方,当地民众无法信任他们的解释、说词,继而遭到民众的极力反对,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项目也宣告停止[1]。无独有偶,2014年3月30日,茂名群众为了表达对拟建芳烃(PX)项目的不满,部分群众聚集茂名市委门前表达意愿,PX事件愈演愈烈,但政府对项目的公开透明环节没有做足前期工作,使得茂名邻避冲突日渐升级,政府难以控制局面。钼铜、PX两项重大项目的“惨败”,显然是周边居民对项目的排斥,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企业的嫌恶造成的。假如在项目立项之前,政府、企业能够通过社区或环境协会等社会组织进行广泛的科普宣传,一定会增加民众了解项目、接纳项目的可能性。
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型中,政府首先是社会冲突调停的当然方或应然居间人,然而现实中因邻避冲突引发的不稳定并不能因此而得以缓解。鉴于政府邻避冲突在治理上的无效状态下,对比社会组织因其独具的功能性和社会属性,更易于成为解决邻避问题的“调解员”和“居间人”。一般而言,社会组织相对独立,具有中立、无偏私的优势,更易于被冲突的双方接受、认可。作为被法律承认的社会组织,承担了一定的公共责任,具有一定的非营利性质,其参与冲突治理的过程中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因而社会组织成为解决邻避冲突重要的调解员。同时,根据邻避项目的特征,可以分析出许多冲突产生或升级的关键原因就是由于政府、企业对周边居民在利益补偿上无法最大化地弥补居民的损失,而社会组织则恰恰可以成为减少成本收益率的有效群体,通过稳定冲突各方的不稳定情绪,营造适于政府与居民谈判的外部环境,推动政府与民众在合法合情的约束下交流、对话,从而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缓和民众与政府、企业的矛盾。如果可能,将社会组织作为信息沟通、传递、减缓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客观上就会减少因邻避冲突引发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失序现象。
二、邻避冲突治理中的维权支持者和减压阀
周边民众往往是邻避冲突中的受害方、弱势方。一般而言,邻避项目建设多是由政府支持或在城市规划中利于城市整体发展而立项上马的公共项目(有些只征求部分民众的意见),施工企业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委托建设相关邻避项目。对于邻避项目周边居民而言,或因尚未知晓邻避项目本身的具体情况,或因对建设风险的理解角度存在差异,对邻避项目产生了抵触情绪,但由于政府对居民的想法和利益知之甚少,同时也没有想了解居民意愿的主动行为,从而导致了周边居民深感被欺骗和蒙在鼓里。对于这样无法正常表达自己对于邻避设施的不悦和反感,当公民个人意愿无法通过政府得到了解并改善其方法时,寻找合理的、能够表达诉求的场所和组织,是利益受损群体颇为重要的渠道。“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此时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独立于政府的特征,无疑是公民赖以依靠,表达诉求的良好途径[2]。早在1986年,我国台湾地区著名的“鹿港反杜邦事件”则是一例鲜明的社会组织担当减压阀和维权支持者角色的事件。当时,当地政府计划将鹿港区土地200多公顷开辟为农药制造区域,将全台69家农药厂都集中于此,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凝聚力量,避免因分散的抗议得不到冲突当事方的重视,无法表达意愿和诉求,当地居民以“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这一社会组织作为发声筒,以多种抗争形式表达对化工厂的厌恶和排斥,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带动了台湾地区民间环保组织的蓬勃发展。endprint
社会组织在常态下多为公民交流活动的重要组织,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相对较为熟悉,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高效的行动力,可以成为居民表达愿望与诉求的维权平台。弱势方——居民往往因集体上访等正常途径无法畅通表达意愿,而对企业和政府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发社会冲突。2013年3月,我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重点培育、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抓住改革的契机,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能力,在出现利益分歧和利益共享冲突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对话机制交流信息,克服有限理性的欠缺,将邻避冲突的各方利益主体锁定在既定的利益相关责任范围内。
在非常态下,邻避冲突爆发之时,社会组织亦可成为冲突的减压阀,在为弱势方——公民代言的同时,给公民提供有效表达自身诉求的通道,减少冲突造成的公共财产、公共设施乃至人员的损失和安全问题。社会组织正在逐步成为沟通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面对邻避项目建设中各类冲突的有效途径和可信途径。
三、邻避冲突治理中的合作者
众多迫于周边居民拒绝合作而终止的邻避项目的现实状况,证明对于邻避项目的认知偏差,双方或多方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导致邻避项目无法进行。政府、企业以及周边居民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和相应的协作,导致邻避项目的终止。社会组织固有的社会自治功能,不断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使周边居民能在社会组织中不断提高自身适应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社会组织的协调,将邻避冲突化为整体治理,促使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责任一致化、统一化,深入居民心中的是社会责任与合作。公民不再是邻避冲突的唯一受害者、弱势群体,不再单枪匹马地向政府问责、向企业寻求利益的合理补偿,取而代之的是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培育公民的合作与责任意识,成为冲突治理中的合作者,而不是谈“邻”色变[3]。
社会组织以合作者的角色参与邻避项目建设与否的合理论证行列时,从公民社会的角度讲,也是社会多方参与治理的一种表征。2009年,在我国宝岛台湾著名的“国光石化案”恰好证明了社会组织作为众多参与主体之一的价值。“国光石化”列入“大温暖大投资旗舰计划”,是全力推动的重点项目,但因其选址在具有国际级湿地的彰化以及环境污染等原因,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期间政府召开了听证会、环评、重新规划项目等方式,当地民众借助当地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的力量,充分利用“湿地计划”扩大影响,推动了事件的解决,民众捍卫着自己手中的权利,保护了生态环境。高度的组织化和高行动化,推动了“国光石化案”的解决。“国光石化”推出台湾经济圈,这一事件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环保案例的一个标杆。我国大陆的江阴污染门事件处理过程中,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接到民众反映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在江阴市黄田港口从事铁矿石粉作业过程中产生铁矿粉粉尘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的空气质量和居民的生活环境,并将含有铁矿粉的红色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冲洗排入下水道,影响了附近居民饮用水的安全。介入到江阴事件中,对企业许诺空头支票,未进行补贴赔偿的行为进行法律诉讼,成为中国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环保公益诉讼第一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其间,中华环保联合会极高的组织化程度、完善的维权方案,是本次事件和解的关键因素,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的重要价值。
四、邻避冲突治理的监督者
在邻避冲突发生之时,最优、最理想的状态是公民作为邻避项目实施的一方主体参与其中,然而,现实总是因利益分配等原因未能及至理想。公民往往是以冲突方的角色出现,政府亦即含混不清地卷入冲突中,因而政府本应具有的权力、权威,规避社会冲突发生的监督角色无法扮演,尤其是在社会稳定风险激增之时,政府往往扮演了“强制”的角色,而“治理”这一方式早已不知去向。此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可以担当起监督邻避冲突恶化、推动政府提供服务的社会责任。客观上,督促政府行为,敦促政府对此类冲突采取措施,保证公民的权益得到保护,力争使企业的社会资本丰盈,确保政府在邻避事件中保持中立,不偏不倚[4]。
被冠以国内邻避事件妥善解决标杆的厦门PX事件,既是各方主体充分博弈的良好体现,又是各社会组织在提供充分技术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基础上,通过跟踪报道、新闻宣传,在疏导居民不满情绪的同时,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企业重新测评项目的可行性等途径,社会组织有效地监督了政府和相关企业,提高了群体之间的行动效率,促进了这一事件的高效解决。社会组织在邻避冲突治理中扮演的监督角色在现实中屡有呈现,在北京六里屯垃圾场事件中,政府与周边居民从始至终都是参与的主体,虽有数次冲突、抗议,但在“自然之友”等社会组织和大众媒体的介入和参与下,通过联系专家学者、官员以及提供技术咨询、提高影响力和法律援助等方式,使得政府采取行政复议、行政审批等手段干预垃圾场事件,居民也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向社会传递了个人诉求,取得了政府叫停垃圾场项目的终极胜利。
从邻避冲突发生时各方冲突主体来看,社会组织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冲突全过程,可以协调各冲突主体的利益所在,分析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带来损失的有效途径。
五、社会组织的邻避治理之路任重道远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首次使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概念,社会组织的重要价值及其功能被进一步证实和表达。中国社会全面转轨时期,社会组织正在逐渐脱离政府的主导和影响。
培育良好的社会组织需要有公民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在我国已有的社会组织功能和责任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组织体系的多元治理合作架构,提供多元的公共服务[5]。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政府将继续“瘦身”,向社会组织放权,将社会组织培育成政府治理的重要力量,推动其在邻避冲突中发挥治理功能。然而,社会组织在我国公共治理主体中方兴未艾,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以及承载功能尚需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建立广泛网络,拓宽参与渠道与范围,逐步建立一种合作关系的发展模式,从而逐渐淡化人为“分割”治理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本文探析的社会组织在邻避冲突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仅是规避社会稳定风险路径的有益探索的尝试,以期能在未来实现解决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理想路径。
参考文献
[1]王锋.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型研究——利益相关者的视角[J].新视野,2012(4):58-62.
[2]谭爽.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及防范——基于焦虑心理的视角[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3):25-29.
[3]涂晓芳.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8(3):17-21.
[4]胡象明. 重大工程项目安全危机中的民众心理契约及政府管理对策初探[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27-32.
[5]赵伯艳. 社会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的作用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