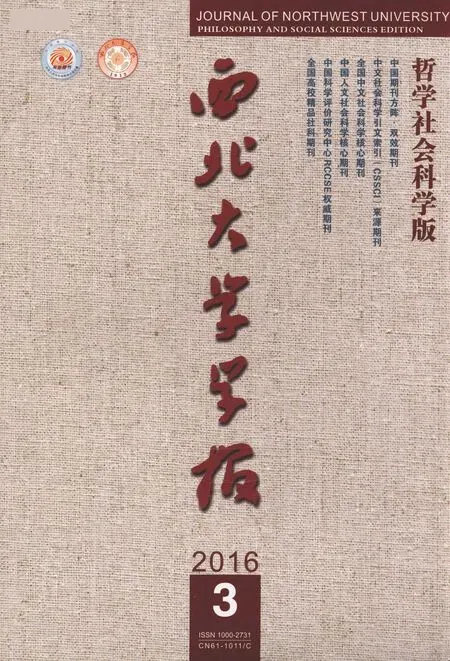“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大江健三郎《形见之歌》①与鲁迅《希望》比较研究
霍士富,王 晶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文学研究】
“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大江健三郎《形见之歌》①与鲁迅《希望》比较研究
霍士富,王晶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710049)
摘要:在“暗夜”中探寻光明是大江从鲁迅文学中继承下来的精髓所在。通过对大江《形见之歌》与鲁迅《希望》的比较研究发现,直面“希望”与“绝望”的现实问题,二者都是通过叙事者“我”在思想上的认知转变,关注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国家的独立与复兴。但在表现形式上又存在着明显不同:直面“黑暗”,鲁迅是始终凝视“黑暗”,将其内化为“希望”,但其底色仍然为“黑暗”;而大江是在凝视“黑暗”的过程中,将其外化为象征“希望”的“星星”或者“新人”,在“暗黑”中窥视“星星之火”。鲁迅主张“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是“改造”主义;大江则力主“宽容”异端下的“希望”,是“改良”主义。因此,如果说鲁迅是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家,大江则是改良国民性的启蒙家。
关键词:国民性;反抗绝望;希望;生存境遇
在中日近代文学史上,像大江健三郎这样如此垂青鲁迅文学者可谓是凤毛麟角。他说:“我不仅读鲁迅,而且怀着敬意和羡慕的心情阅读‘因为接触到鲁迅,给自己留下自愧不如之记忆和痛苦的人’的文章。因为阅读这些人的文章能引起我的共鸣,并给我冲动。”[1](P423-424)那么,大江在如此热心阅读鲁迅文学中究竟读到了什么?他又说:“鲁迅在《药》中,给不幸死去的青年的墓上,凭空添上的‘一圈红白的花’,虽不能使荒凉而暗黑的风景瞬间变成春天之白昼,但我们从由此送来的如暗香那样的问候声中,仍能获得类似的东西。”[1](P434)在此,那“类似的东西”无疑暗示着暗夜中显现的光明,绝望中窥见的希望。即在“暗夜”中寻找光明是大江从鲁迅文学中继承下来的精髓所在,与鲁迅文学的哲学命题“绝望的抗争”一脉相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对鲁迅《野草》中《希望》一文的深切感受,就直接透露了这一思想的渊源。他说:“我每次读到《野草》中的这节‘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会动摇我以前的想法,从而进入沉思。……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我从自己的青春到老年,一直往返在鲁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经验以及各种切实的感受中。此时,我在想:在今后的短暂人生中,直面这两种‘虚妄’,我将会依从何种‘虚妄’而活呢?”[2](P148-149)这就是大江在晚年对鲁迅《希望》一文中直面的两种“虚妄”的思考,并在其晚年作品《形见之歌》(2007)中得以直接体现。即这首诗歌虽距鲁迅《野草》中的《希望》(1925)的发表已过八十余年,但两部诗作在主体表现上却有着深层的相通之处。
鲁迅在《希望》中写道“我大概老了”,不仅头发苍白,而且连“灵魂的手”都在颤抖。在“我”的心中,过去“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可“现在何以如此寂寞”?由此吐露出“我”对“希望”的迷惘。此时,“我”放下“希望之盾”,听到Petöfi Sándor (1823—1849)的“希望”之歌,通过独自的“肉薄”否定“绝望”。最后想到:“现在虽没有星和月亮”,然而象征未来的“青年”犹在,于是将希望寄托于“身外的青春”,进而超越“虚妄”,提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现代生存论之命题。大江在《形见之歌》中首先写道:“老年的我”直面“初孙”时,在幻觉中觉得年迈的“老人”装扮成“婴儿”在哭啼。“我”在年轻时满腔热血为之奋斗的“战后民主宪法”,如今正被以小泉纯一郎首相为首的“右翼分子”肆意践踏和篡改。在此“我”和“婴儿”之哭啼的重叠,暗示着“我”对日本未来的迷惘。此时,“我”想起萨义德在与“白血病抗争”的病床上发来的邮件:“艺术家在死亡面前选择的生存样式”,由此获得“勇气”,否定“绝望”。最后悟出:“面对孩子,老人想回答/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从而超越了“虚妄”。即两文本都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首先吐露了自己内心的寂寞;然后以年迈的“老人”如何从走出迷惘的困境为线索,最后导出现代生存论之命题。在此,叙事者“我”对人生的体验和认知,由个人的生命反省和感悟,推及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殊途同归地探寻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本文将以鲁迅《希望》与大江健三郎《形见之歌》为对象,从“迷惘”之境,否定“绝望”,超越“虚妄”三点切入,对两文本的叙事主题展开比较研究。
一、“迷惘”之境
两文本从一开头就分别刻画了一个身心皆陷困境(predecament)的“老者”,渲染了一个深受迷惘之境的“困兽”形象。鲁迅在《希望》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静: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3](P32)对于“我”痛切感受到的内心寂寞和精神之衰老,孙玉石指出:“在这寂寞和衰老的心情中,鲁迅尝味着对现实斗争前途的绝望所带来的痛苦。” 但“使自己陷入绝望心境的,并不是自己主观上的战斗意志的衰退”[4](P50),而是源于客观的历史背景。从《野草》完成于1924—1926年来看,当时鲁迅正处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黑暗势力笼罩的北京,即使在写《题辞》的1927年,也是国民党实行所谓“清党”,进行白色恐怖的大屠杀的广州。即“在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为之奋斗的“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如今瞬间化为泡影。二是在此背景下,曾经和“我”并肩战斗的“友人”的背离: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5](P469)
这就是鲁迅在创作《野草》时的心境:独自一人“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且在无奈下用“刊物上做文字”喊出自己的心声。但这独自的“呐喊”,也只有空洞的回音。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里告白:“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可见,鲁迅作《希望》时,其内心是何等地迷惘。
大江在《形见之歌》一开头就写道:面对“婴儿”的“哭啼”,“步入老年的我”在幻觉中认为,那不是自己“装扮成婴儿”在“哭啼”吗?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真的步入老年的困境”:
一人形影相吊/唯与否定的感情相伴。/我不仅对自己经历的世纪/累积而成的、破坏世界的装置/持否定态度/而且对许多人企图解体这些装置/也心存疑惑/至此,自己凭借想象力所做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想到此,我眼冒金星地蹲在地上。[6](P146-147)
在此,叙事者“我”经常是孤独一人,对一切都持否定态度。即“我”不仅对自己经历的这个世纪积累而成的“破坏世界的装置”——诸如核武器——持否定态度;就连许多人试图将这些“装置”解体的主张,“我”都表示怀疑。“我”甚至怀疑迄今为止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所做的“工作”,一切都归于徒劳。想到此“我眼冒金星地蹲在地上”。可见,此情此景下的“我”是何等地孤独和迷惘。那么,面对现实“我”为何如此迷惘?究其原因:首先,这首诗是大江在70岁时,也即2005年有感于“初孙”的诞生而作。对此诗的创作背景,他在2006年完成的《作为一个孩子流出的一滴眼泪之代价》中告白道:
近几年来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再度陷入困境。因为我在文学创作时,始终是把战后的日本人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本主题。可是,只要将这一主题作为现实问题去思考,我则对以下两个问题清楚地意识到:直到自己死去那天也不会找到具体的希望之路。
这两个问题是:(1)在东亚营造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基地,并以此作为世界废除核武器的第一步;(2)在战争结束时,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且带来了悲惨而大量的死亡。同时,从战后直至现在,冲绳仍然作为巨大的美军基地而存在。我所关注的问题是日本何时能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关于这两大课题,在至今一直为之奋斗的工作中(我虽然是一个悲观的人),如果从长期发展的事态来看应该说一定会得到改善。[7](P189-190)
在此,大江清楚地表明:自己为之奋斗的两大课题,在其有生之年肯定无望解决,也找不到具体的出路,这无疑表明他对日本未来的迷惘。但他又坚信: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事态应该会得到“改善”,虽然“我”是一个悲观的人。这就是大江文学观与鲁迅文学观之不同:即直面黑暗的现实,鲁迅是用黑色的眼睛凝视现实,以“没有出路”的出路暗示未来;而大江则是在黑暗的世界中发现“星星之火”,洞悉光明的未来。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鲁迅的这一文学观是基于“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8](P411)。而大江文学的这一世界观是继承了日本战后文学创作原则:基于战后民主主义理念的“对世界和社会的能动姿态”[9](P230)。即二者虽然都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但前者是为了避免“消极”在文本中加点“亮光”;而后者是给文本中积极地赋予“星光”。
经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两个文本的共同点为:第一,叙事者“我”都已步入孤独、寂寞的“老年”,且体力和精神皆已衰退。第二,对当下的现实二者都处于无限“迷惘”的困境。对此,鲁迅通过回忆过去:“我的心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可是,当下“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以此吐露自己当下为何如此迷惘和孤独的深层困惑。与此相比,大江也是通过“回忆过去”的技法——我在十岁之前/举国上下在战争/还是孩子的我们曾歌唱/只要死在“天皇”身边绝不回头/在“天皇”/用人的声音/宣告战败的那一天/站在收音机前的村长绝叫道/我们不能重生!——凸显其迷惘的心境。但是,由于二者“回忆”的内容不同,又蕴含了二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意义之不同。鲁迅回忆的内容主要凸显了理想与现实的相悖。即鲁迅回忆的过去是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民众曾用“充满过血腥的歌声”,为“祖国的复兴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可眼下却如此的寂静。其目的是想通过回忆唤起“青年”再度崛起,而大江回忆的内容却旨在再现日本的历史。因为“诗歌相比哲学更注重历史,它与人的心象和实例密切相关。所有伴随意义的言语结构,都是通过作为思考的、人们难以捕捉的心理乃至生理的过程——尽管受错综复杂的情绪、唐突的不合理的确信;微妙的无意识的洞察;合理化的偏见;无名的恐惧和惰性的障碍等要素的羁绊——之语言的模仿而实现”[10](P116)。即大江旨在通过自己对日本这段特殊历史的“回忆”,提醒日本民众要时刻警惕:不要盲从小泉首相修正“战后宪法”的行为,以免重蹈二战惨败的覆辙。
二、否定“绝望”
两个文本中的叙事者“我”虽对各自民族的未来深陷“迷惘”之境,但并未因此而绝望,而是在绝望中奋起反抗。同时,叙事者“我”为了走出困境,都以“互文”的形式双重地否定“绝望”,表现了“我”如何走出困境的心路历程。波林·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说:“每个文本都处于另一个文本的交互文本关系之中,因此都是属于互为文本的”[11](P51)。在《希望》中,叙事者“我”先后引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希望》(1845)和“致友人凯雷尼·弗里杰什的信”(1845年7月17日)中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曲折地鸣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呐喊”。与此相比,大江在《形见之歌》中,叙事者“我”则通过引用来自同时代的友人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的信件,发挥了异曲同工的作用。即通过“互文”两文本在共振和交响的层面,双重地否定了“绝望”。
同一心境下的“共振”。鲁迅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作家,但是二者有着相同的“爱国”情结和直面同样的民族存亡之危机。文中写道: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öfi Sándor (1823—18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他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为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3](P32-35)
对此, 丸尾常喜指出: “将‘希望之盾’放下之际, 鲁迅想到的裴多菲题为《希望》的诗。 据北冈正子研究,这首诗是1845年裴多菲在其短暂生涯中由于内外矛盾交困而身处绝境之时所写。 对鲁迅来说, ‘身外的青春’的衰亡究竟是何等沉重的打击, 裴多菲这首诗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即此“诗苛酷地描写了‘献身’和与此相对的‘背叛’, 也就是以极大的魅力诱惑人、 最终又背叛他们的‘希望’之‘虚妄’”, “强烈地打动了咀嚼着同样苦味的鲁迅的心”[12](P202)。 此见解从裴多菲创作《希望》的历史背景切入, 敏锐地指出鲁迅创作《希望》时与匈牙利诗人当初所处的“困境”发生共鸣。 但我认为鲁迅引用此诗旨在通过“互文性”使两文本之间发生共振才更加意义深远。 即从这位抒情诗人兼“爱国者, 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之行为不难看出,他在其短暂生涯中因“内外矛盾交困而身处绝境”写下的“希望”之歌, 其内涵与鲁迅在寂寞中的“呐喊”处在同一频率上。 换句话说,正因为“我放下了希望之盾”后, 在同一频率上与裴多菲发生共振, 才奏出了“悲哉死也,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之感叹!但不同的是, 裴多菲此时发出的是否定“希望”的绝叫; 而鲁迅喊出的则是在“感叹”之后为之崛起的“呐喊”。
大江在《形见之歌》中也采用“互文”的形式,实现了与同时代友人萨义德直面现实之态度的共振。文本中以引用“友人”在病房里发给“我”的“最后的传真”的形式写道:
与丧失国家的同胞/共同拥有不确切的记忆/且为此并肩战斗/与白血病抗争的友人/在其晚年的研究课题是/有一种艺术家,在选择死亡面前的/表现形式和生活样式时/他们不是满足稳妥的娴熟技法/而是拒绝传统、拒绝与社会调和/在否定性的漩涡中/一人独自屹立,并/抵达前所未有的独创彼岸……/从纽约的病室里发来最后的传真。[6](P146)
在此,关于这位“友人”的原型大江在文本中用注释明确表明:此引文是出自“友人萨义德的私人信件”。即大江与来自“友人”的“私人信件”有两点处在同一频率上。第一,在病痛中仍不放弃与“同胞”并肩前行,为国家的独立和民主战斗的精神。即萨义德虽然身处“白血病”晚期,且身在异国他乡,但仍以一个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争取国家主权和领土的独立与完整。这点与大江始终关注的、美军军事基地冲绳问题——日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处在同一频率上。第二,一个步入“晚年”的艺术家,在迫近死亡面前对艺术的追求:拒绝墨守成规;拒绝与当今社会妥协;追求“抵达前所未有的独创彼岸”。
不同情绪下的交响。裴多菲在完成《希望》之歌两年后,才在一次偶然的体验中醒悟自己过去对“希望”的否定缺乏辩证性。1845年7月17日他在“致友人凯雷尼·弗里杰什的信”中写道:“乘着那样恶劣的驽马……我内心充满了绝望……我相信是不会预期到达”目的地的,可没想到“这些瘦弱的马驹用这样快的速度,在一天里就带我飞驰到萨特马耳来”了。此时此刻的裴多菲感慨道:“我的朋友,绝望是那样的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可见,写此信时的裴多菲旨在否定绝望。即裴多菲在完成《希望》之歌两年后,才悟出“希望”的不确定性,由否定“希望”转变为否定“绝望”;而鲁迅则完全不同,他在写《希望》时已经醒悟。换句话说,前者在完成这一思想转变中奏出的自我情绪是由消极转向积极的变调;而后者始终是积极态度下的低调“呐喊”。正如冯雪峰曾指出《希望》“这篇作品虽然用意和态度都是积极的,但作者却掩饰不住地让自己的失望的伤感、寂寞的情绪以及思想上的希望与绝望的矛盾,都吐露出来了”[13](P169)。因此,在探讨“希望”这一哲学命题时,鲁迅在内心深处与裴多菲鸣出了别有趣味的心声,从而实现了文学艺术上的“交响”。
大江与萨义德相比虽未身患绝症,但二者遇到的疑难问题却是相通的。萨义德遇到的问题是发生在地中海领域的、以色列共和国与阿拉伯诸国之间的巴勒斯坦领土权,当时作为一个身患“白血病”者,很显然此问题在他有生之年无望得到解决;但躺在病床上的他为何能写出:“不要恐惧撕裂内心的矛盾/认清困难,直面对方/将手伸出去/立足于不确切的脚下”的豪言壮语激励对方呢?对此,迈克尔·伍德的见解给我们做出了很好地回答:
直面巴勒斯坦问题,他还能始终保持乐观,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想他的乐观主义完全是靠意志的力量。在一个时期,他也看到了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希望……但是,他认为只有坚持抱有希望,此外别无出路。这并不意味着他找到了出路,而是因为他痛切地感到:人需要坚信事态必将会得到改变!即人类不会永远如此继续下去,总有一天要改变。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的看法是正确的。[14](P233)
即他正因为有如此坚强信念的支撑,才能在“困境”中坚持“直面对方”。而大江也正是从中汲取了这一内在精神,才将其人和其言作为激励自己的楷模。他说:“萨义德无论是从与白血病抗争的肉体内部,还是来自社会的压力,在其晚年都充满了深重的苦闷,但是,在其苦闷中又蕴含独特的光明。”[15](P132)即具体地说,大江在“晚年”遇到的深重“苦闷”有两点:一是日本政府露骨的政体改革,也即当下安倍晋三对“第九条宪法”的不断篡改;二是核电站问题。他说:“福岛核电站爆炸时,我首先感到从广岛原子弹爆炸延续下来的问题,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再现于我们面前。”[16](P366)而这两个难题对大江而言,在他有生之年也是无望解决。因此,萨义德通过对大江的信件鸣出了自己内心的“苦闷”;而大江却借用他者的“苦闷”,曲折地喊出自己的心声,进而在不同层面上与萨义德的苦闷形成交响。
可见,鲁迅和大江通过“互文”的形式,实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否定“绝望”。但是,二者之间又有所不同:鲁迅借用裴多菲的思想转变——通过“驽马”的事实,改变了两年前曾说“希望是娼妓”的观念,进而否定“绝望”——重构了自己对“希望”与“绝望”的新认识:既然“希望”是诱惑人的“虚妄”;“绝望”也是骗人的“虚妄”,那么,在《影的告别》中明确表明:“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的“我”,就应把自认为“不明不暗”的现实作为“虚妄”来把握。于是提出“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的新命题。而大江是借用萨义德的坚强意志,看到了“苦闷中又蕴含独特的光明”,从而提出“面向孩子,老人想回答……”的新命题。
三、超越“虚妄”
鲁迅在《希望》中通过对“虚妄”一词的哲学认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决定走出《影的告别》中“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处境,进而提出一个新的人生命题:“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缥缈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由此实现了人生观念的转折。
“虚妄”的哲学意蕴。在《影的告别》中是“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而在《希望》却提出:“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缥缈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在此,“我”对人生的态度由“虚妄”转向“寻求”。从这一思想转变不难看出,“我”已走出“彷徨”,将重心直指“虚妄”。徐麟指出:“‘虚妄’概念在鲁迅那里,至少内含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即存在、荒谬和不可判断性。存在是一个‘有’,是对虚无的否定;荒谬是有限性和境遇感,是对实在性的否定;而不可判断性则是指经验层面上的不可把握性,因而是对存在者的有限性和确定性的否定,并指向了无限性和不确定性。”[17](P39)可见,“鲁迅的‘虚妄’概念的生命力,则首先表现为一种荒谬性的张力,因而这是一个富有生命能量的概念,实际是鲁迅哲学的最高范畴。它高于希望,也高于绝望。正是靠它,鲁迅才完成了超越。”[17](P44)即正因为有这一“富有生命能量”的支撑,鲁迅超越了“希望”的背叛和“绝望”的荒谬,进而跃入新的人生——寄予“身外的青春”。
“身外的青春”的寓意。在《希望》中关于“身外的青春”先后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将其象征性地表现为:“星和月光,僵坠的蝴蝶,笑的渺茫,爱的翔舞……”在此,鲁迅用“星”和“月光”的视觉意象象征性地寄予“青年”之希望;僵坠的蝴蝶是指蝴蝶在雌雄交配后,雄蝶随即“僵坠”而死去,雌蝶业主产卵后“僵坠”,由此象征着生命的世代交替与延续。比如,丸尾常喜就认为:文本中“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一句,“显示出鲁迅之‘生命的延续性’,也就是‘生命’本身之世代相关的顽强本性。”[12](P203)不过,对于这样的“身外的青春”,过去的“我”“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所以曾有过“梦想”;可现在却“失去”了这样的“青春”。为此,“我”决心用“身中的迟暮”,通过“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唤醒沉睡中的“身外的青春”。最终,将“我”不能完成的“希望”之火炬传递给他们,进而完成“我”和“身外的青年”的延续性。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正如“地上的路”,只要有人“走”,就一定会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即使“我”今天不能完成,还有“身外的青年”去“走”,由他们去开辟一个崭新的历史。
与鲁迅相比,大江在《形见之歌》中用“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通过“我”与“我们”的重心转换,将希望寄予“身外的青春”。即大江在文本中,首先是日本在二战惨败,村长站在广播前高喊:“我们不能重生!”而对此“我”母亲坚决否定。她叹惜道:
在孩子们听着的地方/怎么能说/我们不能重生!/接着,母亲对着我/长时间地说了一番谜语般的言语/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6](P147-148)
在此,首先必须明确一个问题:村长代表日本的纵轴社会结构,也即“天皇制”下的日本社会。大江说:“对出生在农村的人们而言,从战争中的孩提时代起,就是看着巨大的纵轴结构成长起来的。在这根纵轴的上端是天皇;中间是东京的警察组织、国家机构和超国家主义;最下端则是村庄社会、村庄共同体和父亲。”[18](P100-101)即此时位于“最下端”的“父亲”,无疑等同于“村庄共同体”的代表“村长”。换句话说,此结构下的日本近代化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呢?大江说:“从明治、大正到昭和,经过三分之一的近代化的狂奔,日本走进了战争的泥潭。首先挑起亚洲的战祸,进而是冲绳战祸,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战祸,最后是以东京为中心的大部分城市遭受空袭的战祸。那么,日本如何从战败的废墟中振作起来,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日本人在经历了这样的历史,陷入空前的困境下完成了日本战后宪法。”[7](P157-158)由此可见,“母亲”对“村长”所发言论的否定,其实暗示着对“天皇制”的否定,也是对日本“父性原理”的否定,从而转向“母性原理”。
“母性原理”的登场。“婴儿”出生一年后,“我”再度面对“婴儿”时,文本中写道:
婴儿诞生后一年/我从孙子身上/丝毫没有窥见老年的影容/紧绷的皮肤,亮晶晶的发光/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6](P147-148)
在此,与一年前的“我”相比,“我”的境遇发生逆转:“婴儿”由“哭啼”变为“紧绷的皮肤,亮晶晶的发光/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此时此刻,那“发光”的皮肤无疑象征着“希望”。文本中继续写道:
如果老年的我/想深化这份否定的感情/从不确切的地面上/伸向高处的手/难度就不可能触摸到/那种不确切的存在吗?/所谓确立否定性/不是对不现实的希望/甚至对任何绝望/也绝不与其同调……/在此仅有一岁的、纯洁的孩子/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坚持不懈地/探索。[6](P149)
在此,直面“不现实的希望,甚至是任何绝望,也绝不与其同调……”,不正是“老年的我”超越一切不确切的“虚妄”,立志“一切”将从头开始,坚持不懈地探索。而且,这一希望是通过“仅有一岁的、纯洁的孩子”完成,由此实现了“死”与“再生”的轮回。也即过去“老人”面对“孩子”无法回答,而如今:“面对孩子,老人想回答/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
经以上分析发现,两文本中“我”内心情绪变化的共同点:都是寄“希望”于“青年”;且都以再度重复的形式表现了“我”对“希望”的最终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相同的“重复”中蕴含着二者的不同。鲁迅是“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的暗夜了……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这一重复,尾丸常喜认为:“诗篇最后再一次重复‘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表现出鲁迅在这个无论‘希望’也罢‘绝望’也罢、‘友’也罢甚至‘敌’也罢,同样都是‘虚妄’的茫茫世界上,要独自抵抗、继续彷徨的意志。”[12](P203-204)即文本中的“重复”旨在强调:在茫茫的沙漠中,一人独自、继续去反抗“绝望”。与此相比,大江是“在我内心/母亲的言语/都变得不再是谜语/面对孩子,老人想回答/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 正如小野正嗣就指出:“大江在其最后的小说《晚年样式集》中,引用《形见之歌》的末尾两句——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作为其结尾,从中不难看出作者赋予其多么深切的希望。”[19](P405)即这里的重复旨在强调:过去是“我”一人在前行,而现在的情势却大相径庭:面向孩子,老人不再是“无法“回答,而是想回答。可见其“情绪”的乐观和积极。那么,二者都是在探索希望与绝望的矛盾心境,为何在文本的结尾部分表现其情感时会发生如此不同呢?这是因为二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鲁迅处在中国的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前;而大江却处在“战后民主宪法”下日本整体的上升时期。
四、结语
直面“希望”与“绝望”的现实问题,鲁迅与大江都是通过叙事者“我”思想的认知转变,与社会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关注国家的独立与复兴,民族的过去与未来,从而构成了二者的共同点。但是,在创作主题的表现形式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鲁迅的《希望》从文本开头的“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到结尾的“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及“青年们很平安”,始终是独自一人孤独地在沙漠中前行。而大江的《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却完全不同:文本一开头就是象征着“希望”的“哭啼”中的“婴儿”之诞生,进而与文本的结尾——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遥相呼应。即二者的文本主题虽然都在表现“反抗绝望”,但在表现特质上却明显不同。日本学界称大江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可是在表现现实之“黑暗”时与鲁迅的“暗度”有所不同。
日本作家武田泰淳指出:“黑暗。日本战后文学也表现了形形色色的黑暗,但绝没有像鲁迅文学表现的那样黑暗——像古代的铜镜或铁镜所具有的那种坚硬的暗光,冷彻透亮的黑暗。”[1](P24)即二者在批判和揭露社会与时代的“黑暗”时,那种“暗度”的差异正凸显了其创作理念的异同。大江曾在《凝视世界末日的表现者》中写道:“在听惯了狂欢性的语言的沸腾中,我的耳际响起了从鲁迅那里承接下来的、令人怀念而沉重的主题变奏:刚刚抵达火星的人类曾充满希望。即与现在生活在火星上的人类相比,那时的确是有希望的……不过,我对现在的火星仍然没有绝望。因为,绝望是人们自己在脑子里空想出来的。同样,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希望也是人们自己在脑子里空想出来的。”[20](P153)从中不难看出,大江从鲁迅那里继承下来的“令人怀念而沉重的主题变奏”,几乎等同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即文本中“形影相吊”的“我”,虽对现实中的一切持“否定”态度,但对 “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之主张,同样表现“疑问”。可见,大江文学继承了鲁迅文学中“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但在继承中又有明显的变异。即直面“黑暗”,鲁迅是始终凝视“黑暗”,将其内化为“希望”,但其底色仍然为“黑暗”;而大江则在凝视“黑暗”的过程中,将其外化为象征“希望”的“星星”或者“新人”,在“暗黑”中窥见“星星之火”。前者主张“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而后者力主“宽容”异端下的“希望”。一方是“改造”主义,另一方是“改良”主义。因此,如果说鲁迅是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家,大江则是改良国民性的启蒙家。
参考文献:
[1] 大江健三郎.中野重治·鲁迅·花.持続する志[M].日本:讲谈社,1991.
[2] 大江健三郎.不明不暗の『虚妄』のうちに.定義集[M].日本:朝日新聞社,2012.
[3] 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鲁迅.《自选集》自序[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大江健三郎.詩集《形見の歌》より二編[J].新潮.日本:新潮社,2007(1).
[7] 大江健三郎.「伝える言葉」プラス[M].日本:朝日新闻社,2006.
[8]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大江健三郎.戦後文学から今日の窮境まで――それを経験してきたものとして.最後の小説[M].日本:讲谈社,1994.
[10] ノースロップ·フライ.『批評の解剖』[M].海老根宏,等译.日本:法政大学出版社.1998.
[11] 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12] 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M].秦弓,孙丽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3] 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4] 大江健三郎.読む人間[M].日本:集英社,2007.
[15] 大江健三郎.話して考えると書いて考える[M].日本:集英社,2004.
[16] 尾崎真理子,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身を語る[M].日本:新潮社,2013.
[17] 徐麟:论鲁迅的生命意志及其人格形成[J].文学评论,1998,(2).
[18] 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再发见すばる編集部[M].日本:集英社,2001.
[19] 小野正嗣.流さないひとしずくの涙をつたえてゆく[C].M/T和不可思议的森林物语(解说).日本:岩波书店,2014.
[20] 大江健三郎.世界の終わりを見据える表現者.定義集[M].日本:朝日新聞社,2012.
[责任编辑赵琴]
(薛辑)
The Life Philosophy of “Revolting Despair”:A Comparative Study of Oekennzaburo’sSongofKatamiand Lu Xun’sHope
HUO Shi-fu, WANG Ji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Search for light in “Dark Night” is the quintessence Dajiang inherits from Lu Xun’s literature.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ajiang’s Song of Katami and Lu Xun’s Hope, the paper finds that, facing the real problem of “Hope” and “Despair”, through the narrators’cognitive change in thoughts, the two writers form their common ground by concerning about their nations’past and future, their countries’independence and renaissance. But distinct differences still exist in their respective literary expressions: facing “Darkness”, Lu Xun always stares at it, internalizing it as “Hope” with “Darkness” as its grounding, while Dajiang chooses to externalize it as “Star” or “New Person” symbolizing “Hope” and peep at “Sparks” in “Deep Darkness”. Lu Xun advocates “Transformationism”of “Destroying hope of the iron house” while Dajiang insists “Reformism” of “Tolerating hope” in heresy. In fact, with Lu Xun considered as an enlightener devoted to trans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 Dajiang can be viewed as one committing to re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
Key words:national character; revolting despair; hope; living circumstances
收稿日期:2015-09-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5YJA752003);陕西省社科项目(2014I24)
作者简介:霍士富,男,陕西绥德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10.96/.97;I1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3-024
①大江健三郎:《形见之歌》二首,本文只以其中一首《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为研究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