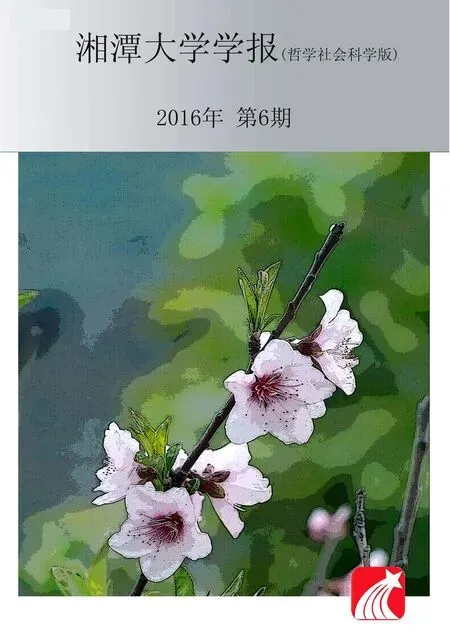论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的效力*
李林启
(河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论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的效力*
李林启
(河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裁判的法律效力是审判机关作出的确定裁判所产生的诉讼法上的效果。明确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的效力问题,是该裁定能够得以快速、正当、高效执行的基础。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对人民法院具有拘束力,是审判权得以实现的保障。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作为终局裁定,具有形式确定力。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具有给付内容,产生执行力。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能够变更担保财产在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具有形成力。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非讼性特征及非讼程序设置的简略性,使得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无既判力产生的根据。
担保物权;非讼程序;法律效力
民事诉讼中,案件经过人民法院的审理,最终需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做出裁判。严格意义上,民事裁判只有判决和裁定两种形式。[1]112非诉案件中,通常并不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实质上的审查,故法院的裁判通常以裁定的形式为之。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特征与非讼案件的特征具有一致性,《民事诉讼法》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程序规定属于非讼程序,[2]81-85人民法院依此程序作出的裁定即为非讼裁定。然而,在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的执行中,必然面对诸多复杂的情形,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因此明确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的效力问题,是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能够得以快速、正当、高效执行的基础,不仅有利于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制度价值和功能的发挥,也有利于推动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不断落实,促进司法公正的不断实现。本文参考、借鉴诉讼裁判效力的相关理论,对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的效力问题进行解读。
一、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具有拘束力
裁判的法律效力是审判机关作出的确定判决所产生的诉讼法上的效果,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制度。[3]69-79裁判的效力可分为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所谓裁判的形式效力,即依据裁判的外形所产生的效力,而裁判的实质效力,则是凭藉裁判的内容而产生的效力。裁判的形式效力主要包括拘束力与形式确定力,[4]225其中拘束力是首先产生且在所有裁判中都具有的效力。拘束力的基本含义是指裁判一经作出,作出裁判的法院即应受其拘束,不得任意变更或者撤销。[5]282在诉讼程序中,判决对作出判决的法院具有稳定的拘束力,这是判决强制性的效果体现,是形成法的安定性的要求。
非讼程序中,法院对非讼事件依法作出的裁定如判决一样,是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主要方式,同样存在拘束性的要求,这是审判权实现的保障。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依法作出的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对作为裁定制发者的人民法院亦具有拘束力。这是因为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是人民法院运用非讼裁判权对担保物权的实现方式所进行的确认,裁定作出后,纵使原裁定的制发者发现有违法之处或者不当之瑕疵,也不得随意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即使双方当事人基于各种原因一致同意对裁定进行变更或者予以撤销,法院也不能轻易更改或者废弃,否则,法院裁定的效力将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国家通过公力途径确认社会民事生活的司法制度将首先从法院内部开始崩溃,法院通过非讼许可裁定确认担保物权人私法权利,进而形成新的私法秩序的目的也难以达到。[6]30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裁定具有拘束力,要求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裁定的执行中,执行法院应严格按照人民法院的裁定执行,不得任意变更、撤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中,基于便利、快捷、效益等法律价值的考量,在宣告失踪(死亡)、认定公民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财产无主等案件中,设置有裁判变更程序。如《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裁判变更程序在性质上并不是新程序,而是原审人民法院因裁判基础变化或者发现裁判不当时对裁判行为及时进行自我调整的一种附随程序。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申请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其目的并非请求人民法院解决相关的实体争议,而是请求人民法院作出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以获取执行名义,并借助于该执行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从而迅速便捷地实现担保物权。因而,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许可裁定不应适用变更程序。
二、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具有形式确定力
拘束力是针对法院而言,形式确定力则是针对当事人,是裁判对于当事人的拘束力。对于判决而言,其形式确定力意味着,在通常的救济程序内,当事人已丧失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该判决的可能性。判决的实质确定力,原则上以形式确定力的存在为发生要件。判决形式确定力的产生原理是基于以下认识:虽然作出判决的法院不能随意变更或者撤销判决,但有权提起上诉或者异议的当事人提出申请时,上级法院仍有可能对判决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然而,即使是上级法院也没有权力随意变更或者撤销判决,其只有基于当事人的上诉或者异议才能依职权为之。若这些通常的救济手段已用尽,也就意味着该判决为确定的判决,具有形式上的确定力。[7]154
非讼裁定亦不排除“确定”的概念,如我国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第39条规定:“关系人得声请法院付与裁定确定证明书。裁定确定证明书,由最初为裁定之法院付与之。但卷宗在上级法院者,由上级法院付与之。”《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第45条规定,决定申请异议或者上诉期间届满,即属于确定裁判。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尤其是特别程序中没有“裁定确定”、“确定裁定”等条款的明确规定,但并不能以此否认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形式确定力的存在。根据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具有形式确定力的裁判,以终局裁判为限。而终局裁判,是法院对受理的事件所作出的终结其审级的裁判。至于做出裁判的法院是何级别、裁判的内容是什么,皆非所问。[8]552即终局裁判作为法院对受理的事件所作出的终局性应答,是终了程序的最正常原因。只要是终局裁判,均具有形式上的确定力。而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在程序设计上,以有效降低权利实现成本、达到各项成本“最小化”而各方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强调担保物权实现的快捷、高效。具体来说,《民事诉讼法》规定担保物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8条关于特别程序审级的一般规定,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人民法院的裁定书送达后立即发生强制执行效力,申请人即使对人民法院的裁定不服也不得提起上诉,人民法院也不能自行依职权予以变更或撤销。即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为终局裁定,作为终局裁定,自然应具有形式确定力。
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具有形式确定力,要求在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的执行中,担保物权人及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应严格按照人民法院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裁定所载内容行使权利,即使对人民法院的裁定不服也不得依通常的救济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对裁定进行变更、撤销,以维护裁定作为终局裁定的权威性。
三、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具有执行力
执行力是裁判的实质效力之一,是指能够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裁判中所记载给付内容的特定效力。对法院的判决而言,一般来说只有给付判决才具有执行力。对于非讼裁定的执行力问题,一般认为,在非讼程序发展的早期,法院对非讼事件所作的裁定原则上没有执行力,这与当时社会中非讼事件的范围较为狭窄、非讼裁定大多只具有形成性内容而不需要执行有很大关系。随着非讼事件的范围不断扩大,要求为一定给付的非讼事件逐渐出现,非讼裁定的执行力也得以确立。特别是随着诉讼事件非诉化的日益发展,具有执行力的非讼裁定不断增多,在各类非讼裁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针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作出的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许可裁定就是其中一种。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并非担保物权本身受到了侵害而请求人民法院解决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关于担保物权的实体纠纷,其主要是在实现担保物权的条件成就后,双方就实现担保物权的方式不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以获取执行名义,并借助于该执行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从而迅速便捷地实现担保物权。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因具有给付内容,所以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产生执行力。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采用裁定形式处理实体问题,不仅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特定情形下可使用裁定处理实体问题的一般机理,更是对裁定功能的扩大、发展。因为原有使用裁定处理的实体问题多是对实体问题状态的暂时确定,如《民事诉讼法》中的保全制度,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则是对实体问题的终局处理。[9]152-159需注意的是,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裁定的执行力来源于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本身,而不是担保物权人与担保人签订的担保物权协议。依法成立的担保物权协议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其自身不会产生强制执行力,只有通过人民法院的裁定将担保物权协议的内容上升为裁定的内容,才具有强制执行力。《民事诉讼法》第197条亦明确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依据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
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具有执行力,要求在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的执行中,一方面,申请人有权依据该裁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可根据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对担保财产进行拍卖、变卖;另一方面,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必须依据裁定所载内容,而非实现担保物权协议。如果依据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后所得的价款仍不能够清偿担保物权人的全部担保债权,则权利人只能通过诉讼等途径就债务人所有的其他财产获取执行请求权,并通过强制执行来清偿剩余债权。
四、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具有形成力
形成力是裁判的又一实质效力,是指通过法院的裁判改变原有法律状态的效力,即引起某种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效力。[10]77民事裁定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种法定裁判形式,其适应范围非常广泛,已成为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民事程序所处理的案件性质不同,裁定可分为争诉裁定和非讼裁定,二者在目的、功能、性质等诸方面存在着区别。[11]24非讼裁定中,针对非诉事件作出的许可裁定以形成裁定居多,法院通过形成裁定,从而变更或者消灭原有法律关系、形成新的法律关系。裁定的形成力是一种对世效力,涉及到任何不特定的第三人。即只要裁定所形成的法律上的状况存在,任何人都应当尊重,而不能否认。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担保物权人及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寻求国家公力的介入,其目的在于获取对一定行为强制执行的名义,即请求人民法院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从而变更担保财产在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适用非讼程序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进行审查,其根本目的在于定纷止争,恢复可能或将要失衡的私权关系,预防私权争执的发生;其直接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就担保物权实现方式上的矛盾纠纷,通过非讼许可裁定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担保物权法律关系予以认可,确认担保物权人的私法权利;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的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具有形成力。同时,准予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具有形成力,还表现在该裁定不仅可羁束任何第三人,对作出裁定法院以外的其他人民法院及行政机关也具有约束性。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裁定具有形成力,要求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裁定的执行中,其他人民法院及行政机关在需要配合的时候应积极配合,以保证人民法院裁定的顺利执行;其他任意第三人也均应尊重通过该裁定形成的新的权利状况,以促进新的私法秩序的形成。
五、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不具有既判力
既判力是判决效力的核心内容,指的是判决确定后判决内容在该程序之外所产生的通用效力。具体来说,判决确定以后,对于判决中针对当事人请求作出的实体权利义务问题的判断,任何人不得在同一程序内再次进行争执,也不容包括作出判决在内的人民法院等任何机关随意改变。[12]398在司法实践中,判决的既判力产生双重效果,其一是“一事不再理”,其二是“当事人法律关系基准的确定”,从而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及法的安定有序性。
在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中,因缺少对立主体在实体权利义务上存在争执的前提,其程序较为简略,没有给双方主体足够的程序保障,既判力与非讼程序追求的基本价值完全相悖,无既判力产生的根据。首先,既判力以纠纷中双方当事人存在实体权利义务上的争执为前提,[13]42而担保物权实现中,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实体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当事人双方不仅对主合同上的债权及担保物权是否存在没有争议,对担保物权人请求实现其担保物权的目的也没有争议,只是在以何种方式实现担保物权上难以达成共识,存在不同的看法。[14]87-91换言之,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并不存在对立的当事人,反之,在尽快使实现担保物权得以实现这一问题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甚至具有某种一致性,其既是担保物权人的合法诉求,也符合担保人的切身利益。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不存在实体争议的特征,使得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失去了既判力产生的根据。其次,既判力是民事诉讼制度程序保障的基本要求,[15]474-475而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设置较为简略。为达到高效快捷之立法目的,我国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在程序设计上与普通审判程序相比具有诸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审级制度上实行一审终审,申请人不服人民法院的裁判也不得提起上诉;二是审判组织上原则上采用独任制,只有重大、疑难案件才采取合议制;三是案件审结期限较短,《民事诉讼法》规定为立案之日起30日;四是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如此的程序设计,难以为双方主体提供足够的程序保障,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也就没有既判力。
实现担保物权非讼许可裁定不具有既判力,并不意味着允许申请人就许可裁定重复向人民法院提出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申请。申请人若基于同一事实反复申请,则为无实际法益,欠缺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应不予准许。
[1]王甲乙、杨建华、郑健才.民事诉讼法新论[M].台北:广益印书局,1983.
[2]李林启.我国实现担保物权的程序性质[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3]陈刚、程丽庄.我国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制度再认识[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6).
[4][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M].汪一凡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7][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M].白绿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8]吴明轩.中国民事诉讼法(上册)[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
[9]郝振江.非讼裁判的效力与变更[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2).
[10]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胡思博.民事裁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2]柴发邦.中国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13][日]铃木忠一.非讼事件的基础问题[M].东京:弘文堂,1961.
[14]李林启.我国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及适用——兼评新〈民事诉讼法〉第196、197条之规定[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15][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饶娣清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on-litigation License Ruling of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
LI Lin-qi
(SchoolofLaw,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Henan453007,China)
Referee legal effect i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procedural law arising from the referee to make the judiciary.To ensure the non-litigation license ruling of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termination being executed quickly,legitimately and efficiently.It is binding to the People’s Court,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trial implementation.As a final ruling, it has a form determined force.Disapproving the auction, sale of secured property licensing ruling has paid content, resulting in execution.The secured property legal relations can be changed in the substantive law,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force.The realization of non-litigation features and the simplicity of non-litigation procedure make the license have no judicata basis.
security interest; non-litigation procedure; legal validity
2016-06-30
李林启(1970—),男,河南原阳人,法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实证研究”(15BFX162)系列成果。
DF718
A
1001-5981(2016)06-00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