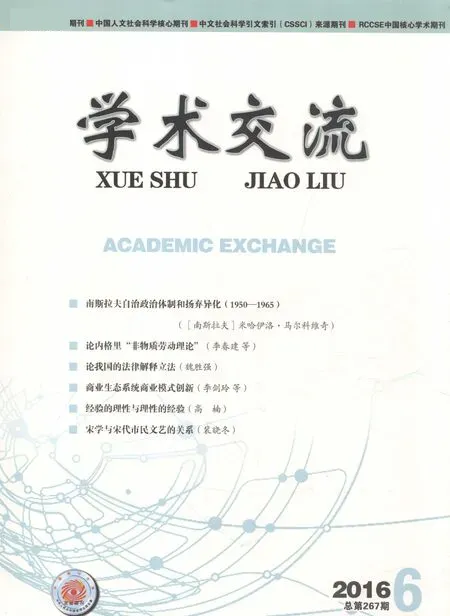赫斯的货币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
高 天,张元庆
(1.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沈阳 110031;2.辽宁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沈阳 110161)
赫斯的货币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
高天1,张元庆2
(1.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沈阳 110031;2.辽宁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沈阳 110161)
[摘要]19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是一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行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其货币哲学中的人本经济学异化理论,即货币异化理论的建构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模式,他将费尔巴哈抽象的宗教批判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货币)批判,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根据对货币哲学与唯物史观思想形成中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以“人本质的异化”、“货币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为主线,可以清晰发现赫斯的货币哲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莫泽斯·赫斯;货币异化;马克思;唯物史观
自20世纪初期,国外学者们就已经掀起了对莫泽斯·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的理论热潮。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是莫泽斯·赫斯的货币哲学思想影响了青年马克思,因为货币哲学中所内涵的经济领域内的“货币异化”与马克思思想中生产领域内的“人的异化”以及“劳动的异化”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同时,在对于经济领域中人本质的异化与经济秩序中社会阶级关系对立、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以及消除异化等概念的理解也极为相似。然而,马克思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进行分析,从而将货币哲学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相结合展开分析,实现了理论上对经济领域中的货币哲学的超越,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
一、 马克思与赫斯异化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
(一)货币的本质:从宗教批判到经济批判的内在一致
在费尔巴哈看来,“类本质”是人的真正本质,“类”是人的至高与完善的存在,但是,随着“类本质”的生成,它在宗教信仰中形成了一种外在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力量,就是“类本质”的异化。因此费尔巴哈认为“类本质”通过宗教的异化表现为人们心中的“上帝”。“人的这种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它被人格化了,它奔驰在人之外,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格出现,作为一种理性的化身,意志的化身出现。这也就是上帝。”[1]莫泽斯·赫斯将费尔巴哈认识领域内“宗教异化”的批判框架延续至现实经济领域内“货币异化”的批判中。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货币本质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异化。“上帝对理论生活所起的作用,同货币对颠倒的世界的实践生活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人的外化了的能力,人的被出卖了的生命活动。”[2]145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成了外化于人的异己存在力量,并且驾驭人的生活,迫使人不得不牺牲和忽略属人的本性,出卖个体的自由,将代表经济利益的货币收入作为生活的目的。马克思与莫泽斯·赫斯关于货币本质的批判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在论述经济异化理论过程中明确展开了宗教和经济的批判,指出货币的本质:“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3]448马克思将由于追逐经济货币收入而异化了的人按照“经济秩序”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社会阶级,并且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由于货币异化产生的剥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过分追逐剩余价值,在贬低个人价值的同时淹没了人自身的“主体性”。所以,与莫泽斯·赫斯相同,马克思认为货币的异化是导致现实生活异化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已经抽象为一种价值的概念。
(二)劳动的本质:从交换领域到生产领域的领域转换
在莫泽斯·赫斯看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就是被人们所出卖的作为人的基本生命活动的社会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配原则使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了以劳动交换为手段的生存方式,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其本质(劳动)的交换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继续交换其本质。此时人的本质便被贬低到交换领域内成为一种求生手段,取代了原有的劳动交换。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所奉行的基本原则不再是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而成了维持个体存在的“利己主义”,与基督教内部的“利己主义”原则相同。赫斯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运用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模式,指出了人们在宗教生活与现实生活中异化的一致性,即在信仰中,人们追求灵魂平等而寻求依靠上帝的拯救,在生活中,为了个体生存而出卖自身的本质取得货币收入。因此,天国中信仰上帝成为拯救灵魂的手段,而现实中出卖个人劳动的本质是持续肉体生存的手段。莫泽斯·赫斯通过对于交换领域中劳动本质的分析,以及其内部与宗教利己主义原则的一致性论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货币异化,是马克思生产领域中劳动异化理论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宗教相一致的利己主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体现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存在,马克思通过经济异化指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货币收入的经济差距,产生了阶级分化的对立冲突。马克思聚焦于生产领域,通过对生产方式的考察深入地分析了私有财产。“马克思认为,经济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对于这种现实生活的异化,马克思主要是从货币异化这个角度来论述的。”[4]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展开物质生产生活的活动,即属于人的本质的类活动。马克思将领域转换到生产的发展内,扩展了莫泽斯·赫斯的交换领域局限性,从劳动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双重角度来理解劳动的本质,要改变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三)批判的对象:从货币异化到劳动异化的视角转变
莫泽斯·赫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颠倒体现在维持人的个体生存被提升为目的,而人本质的类生活却被贬低为手段,产生了“人的生活”和“自然生活”的根本颠倒。赫斯指出,从个人本质的类生活即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目的,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生活作为手段,是人类社会的应然状态,然而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颠倒”。在赫斯看来这种颠倒的状态就是一种异化状态。在社会生活中,赫斯延续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认为基督教的天国世界是宗教领域中“颠倒”的表现形态,而资本主义的小商人利己主义社会便是资本主义中“颠倒”的现实形态。这样,赫斯指出,在现实中,一方面人的类生活以上帝的形式表现在精神世界的宗教中,另一方面,它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世界的小商人社会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颠倒社会中的“货币”等同于基督教天国中的“上帝”。“现代商业世界(Sacherwelt)的资本即货币,是基督教的实现态。……上帝不过是观念化的资本,天国不过是理论上的小商人世界。”[2]149黑格尔指出,宗教给予了人们对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自身需求的强烈期望以补偿,他指出,“上帝”拥有“永恒的意志”,不会被任何事物的“偶然性”所左右,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可以在信仰世界中得到完成。马克思运用黑格尔宗教补偿机制的辩证逻辑在实践领域中延续了赫斯的货币哲学,同样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颠倒人们的颠倒个性。在他看来,货币的存在,刚好给予社会中的人们维持和改善社会生活的愿望以现实补偿。
莫泽斯·赫斯指出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小商人世界与基督教天国的内在一致性。从宗教异化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本质的异化,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以差别性为逻辑起点,将货币异化从认识领域转入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中,运用辩证思维,在实践领域延续了货币异化的思想。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现实事物的“偶然性”是指由他物决定自身的存在,也就是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一定源于另一具体事物,即整个世界是一个有中生有、有生有灭的逻辑循环过程。“这种外在的、特定存在着的偶然性便是一种预先设定了的东西,它的直接定在同时即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就其规定来说,也是被扬弃了的,于是偶然性就是另一事物的可能性,也可以说是另一事物的条件。”[5]在这里,“可能性”与“偶然性”作为现实性的两个环节,内外合而为一的更替便形成了事物“必然性”的本质。“必然性”作为本质在事物自身建立起来,这样,万事万物完成了自己生成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和谐的自然规定性。黑格尔从辩证思维的差别性出发,拒斥的是知性思维的统一性逻辑起点,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内部的联系,是由不同事物在自身建立起“必然性”并形成相互联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有差别的矛盾运动。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来分析赫斯的货币异化理论,在实践领域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性矛盾运动发现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劳动异化,他在实践的生产领域中转变了批判的对象,从“货币异化”转向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马克思在生产领域中提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41马克思通过批判领域的转变看到了生产领域中存在的剥削关系,要在实践中寻求消除异化、解放人类的道路。
(四)现实的路径:从异化消除到人性复归的革命变革
莫泽斯·赫斯在货币哲学中提出了消除货币的异化来建构共产主义联合体的理想。在赫斯看来,颠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奉行的是利己主义原则,货币成为人们生活的目的,是驾驭和驱使人的异己力量,货币异化造成了人与人的本质的分离,形成“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样,赫斯提出,只有消除货币的异化,实现人与人之间劳动的直接交换,才能消除货币的中介作用,实现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建立起个人本质之间的真正联合,取得彼此的相互需求,实现以劳动为目的的人的类生活。通过货币异化的消除,赫斯提出建立起以劳动为核心的共产主义联合体,在其交换领域内实行自由的劳动交换。在赫斯看来,货币的异化造成了生产领域中的片面性,使生产无法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最终会走向人性与货币的双重毁灭。这种毁灭是相互的,因为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矛盾无法实现调和。这样,在资本主义的颠倒社会中,由于货币的异化必然会形成经济收入的两级分化鸿沟,社会会呈现出金字塔型的经济收入结构,当聚集在塔底的人数越来越多,势必要变革资本主义的制度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联合体。在货币哲学中,莫泽斯·赫斯发现了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并且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发展与队伍的必然壮大以及变革社会制度的道路。但是赫斯并没有指出消除货币异化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具体方式。
马克思科学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原因在于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他看来,社会阶级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他明确地将资本主义中的社会阶级进行了区分,划分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不仅看到了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而且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的历史使命。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最后彻底消灭阶级,消除人的异化,才能真正走向人自身的复归之路。马克思将赫斯基于伦理分析中货币哲学的“抽象批判”提升为实践经验分析中的“革命批判”,对于共产主义联合体展开了科学的论述。马克思提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变革方式,才能彻底消除异化,真正地建立共产主义联合体。“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91
二、赫斯的货币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
(一)从共同活动到感性活动
莫泽斯·赫斯在货币哲学中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即“共同活动”,它是人的现实本质。“因此一切现实的生命活动,即理论的及实践的生命活动——都是类活动(Gattungsact),是各种不同的个性的共同活动。”[2]139在“共同活动”中人与人相互交往并产生人的精神。因此,“共同活动”是个人思维和行动的内外统一的类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感性活动”,其中“感性”体现了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带入实践的生命活动范围内,“活动”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发展了赫斯的“共同活动”,在实践中更加重视人的自由主体性,指出体现人现实本质的生命活动是自由和劳动相互作用构所成的“感性活动”。马克思认为,在人的本质的类活动中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它是一种个人为维持肉体存在而进行的必然活动,是作为个人其他活动基础的实践活动。人作为类的存在,通过有意识的“感性活动”与动物相区分。“感性活动”在人的实践生活中指导人们进行合规律合目的性的生产来改造对象化的自然环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础,只有充分地开展人的“感性活动”才能发展先进的生产力,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行。在“感性活动”中,人实现了人自身的现实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活动”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73马克思建立起了用抽象概念来解释现实的思维模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性是感性活动的基础。在“感性活动”中,个人既可以满足自身外在的生存性需要也能够实现内在的精神性享有,实现人在实践领域中的自由主体性,因此,“感性活动”是保证个人类生活实现、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联合体的前提和基础。
(二)从货币关系到生产关系
莫泽斯·赫斯指出了由货币关系导致的资本主义整个社会中“人(本质)的异化”,他从普遍性出发来看待货币关系引起的人与自身本质相分离的异化状态,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吞噬”的颠倒图景。这种异化的范围充斥着包括“无产者”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人。在赫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小商人社会中所盛行的是利己主义的“货币关系”价值标准。他指出,在中世纪的宗教等级制度下,产生的标准是按照信仰来区分和评价人。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小商人世界的异化社会中,货币的收入程度成了评判人的准则。由此,莫泽斯·赫斯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与自身相分离的两条路径,分别是在彼岸天国中的人格化上帝和此岸现实中的中介性的货币。“货币关系”发展了私有财产,生活中由于货币的异化,使财产具有神圣性,它带领人们继续追逐货币利润,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将“货币关系”带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践中展开分析,指出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原则产生的源头。他延续了赫斯对于“货币关系”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破除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无产阶级的先进生产力,形成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彻底地消除人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3]86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阶级矛盾,以经济秩序为标准重新划分了“社会阶级”,指出了无产阶级拥有先进生产力,并且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普遍交往”就是生产关系。他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联合体中所要建立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生产力普遍发展以及世界性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
(三)从利己主义到共产主义
莫泽斯·赫斯指出在消灭了奴隶制社会,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现代小商人世界的这种在原则上得到了实行的利己主义不仅在今世而且在来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会把一切直接的交往、一切直接的生活消灭掉,只是还允许这些东西作为私人生存的手段。”[2]152在资本主义的小商人社会中,盛行的是重视私利而忽视公利的利己主义原则,在赫斯看来这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颠倒。马克思在货币异化带来的资本主义利己主义原则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论述了赫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私利”与“公利”的相互颠倒是源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之间的颠倒,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41这就是生产领域内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指出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来改变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抽象的理论批判都没有真正地触动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因此,不能带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终极联合。无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反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价值平等理念,还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平等观念,都只是展开了在部分人中间的“重新分配劳动”,无法变革资本主义中的利己主义原则。马克思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转换了批判视角,从社会生产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方式,是全人类消灭阶级本身,消除异化,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走向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与赫斯一样,从普遍性出发,提出了在实践中消除“利己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消灭社会阶级的存在才能最终消除异化,建立起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转变社会中货币异化的“利己主义”走向实践中的“共产主义”。
(四)从货币异化的历史到生产异化的历史
莫泽斯·赫斯在货币哲学中延续和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模式,从宗教与现实社会内在机制关联性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异化的颠倒性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基督教是利己主义的理论、利己主义的逻辑。而利己主义实践的典型基地就是现代的、基督教的小商人世界……在我们的小商人世界,个体在实践上是生活的目的,类只是生活的手段,正如在基督教天国,个人在理论上是生活的目的,类只是生活的手段一样。”[2]144莫泽斯·赫斯从宗教的历史出发,以宗教异化入手来阐述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交换领域内的货币异化,论证了基督教的“天国”与资本主义的“小商人世界”中相一致的利己主义原则,对货币的异化进行了历史梳理。用普遍性的逻辑起点来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看到了无产阶级队伍必将壮大的趋势,但是,在抽象的宗教批判理论模式的框架下,赫斯仅局限于交换领域内的货币异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以及无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
马克思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将货币异化带入生产领域进行分析,从差别性出发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出必须变革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消除两极分化所产生的压迫剥削,从而彻底地消灭阶级,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即“普遍交往”。这样才能消除人的异化以及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以莫泽斯·赫斯货币哲学为理论基础,从生产发展的实践视角思考货币异化的历史,通过生产中劳动的异化理论,阐述了整个人类生产异化的历史,在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内重新解释交换领域中的货币哲学,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货币哲学的理论提升,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建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种历史观始终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3]92
[参考文献]
[1][苏]马利宁B A,申卡鲁克B H .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M].曾盛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125-126.
[2][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M].邓习议,编译.方向红,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高文新.马克思理论基本范畴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144.
[5][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3-304.
〔责任编辑:杜娟〕
[收稿日期]2015-06-07
[基金项目]2012年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历史存在论——后形而上学背景下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视域”(YJSCX2012-266HLJ);辽宁行政学院博士科研咨询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高天(1986-),女,辽宁本溪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6-00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