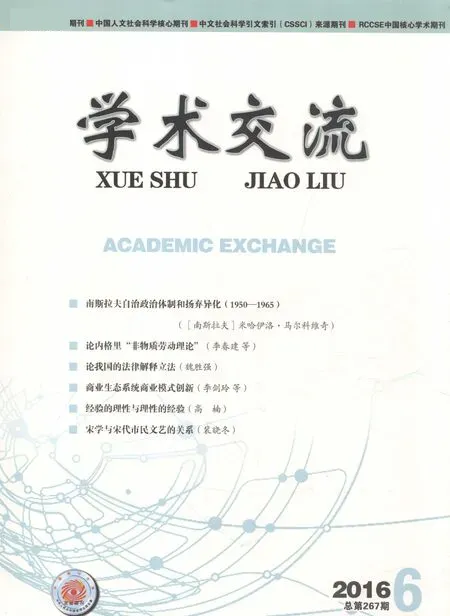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律相生”结构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陈广思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律相生”结构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陈广思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正如广松涉所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除了表达出异化论的逻辑之外,同时酝酿着另一种逻辑,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人与世界历史之间“二律相生”的逻辑:世界历史通过规定现实个人而使自己按照人为它制定的方式生成,同样地,现实个人通过规定世界历史而使得自己按照它所“允许”的方式生成。通过“对象性活动”、“类本质”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定的个人”等概念,我们可以充分地确立这种二律相生的结构,并将其表达为“一定的个人�社会关系”。二律相生结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现实个人和世界历史的关系的深刻把握,它深入现实历史的本质之中,并对我们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理解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具有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二律相生;对象性活动;类本质;“一定的个人”;广松涉
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人与世界历史(包括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的理解基本上定格于相互影响或相互作用这种关系之中,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位,但是我们还可以对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这种相互关系还可以更深入地被理解为人与世界通过相互规定而相互生成的二律相生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它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本文集中于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与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费尔巴哈篇”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对象性概念,马克思区别于黑格尔的主要一个地方在于,黑格尔把对象理解为纯粹由主体所设定的,因而它对于主体而言是虚无的,最终可以消弭于主体的运动之中;马克思则把对象理解为现实的、感性的、具有独立实在性的现实事物,它对现实个人能够起到现实的限制作用。但是,马克思又根据对象性这个概念认为,人的对象是依存于人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的“作品”和“现实”。[1]163于是在马克思那里就似乎出现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外部世界是具有不可被取消的实在性的,但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作为人的对象又必须依存于人。这个矛盾在施密特看来就是自然存在独立于人和依存于人的关系的“难题”。[2]69
人与外部世界的这个“矛盾”从来都不只是纯粹哲学的问题,它具有深重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以及人们通过逐渐兴盛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的支配,都使得外部自然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人类活动的素材而被纳入人类活动之中,面对这个现实,“在哲学上的反思是:客观性的种种规定越来越纳入主观之中,以至在康德之后所完成的思辨中,被全部吸收到主观性中去了。”[2]16施密特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黑格尔否认对象的实在性的做法之时代背景的挖掘,这种时代背景也是促使马克思从对人有效用性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原因,因而间接的也是马克思认为外部世界必须依存于人的原因。但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兴盛时代的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劳动并不是人类财富的唯一来源,包括自然资料和历史条件在内的外部世界与人类劳动一样,都是构成人类物质财富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掠夺自然社会的资源和压榨剩余劳动同样重要。正是由于对这个事实的认识,才促使马克思形成否定黑格尔否认对象的实在性的观点,而认为外部世界是具有自身不可消除的实在性的、可以对现实之人及其活动有现实的作用关系的东西。
人们对外部世界既“否定”又“肯定”的历史关系可以说是促使马克思谨慎地对待对象性概念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上由此形成一种二律相生的独特立场:在对象性关系中,现实个人与现实对象以相互规定的方式相互生成,对象通过规定人而使自己按照人为它制定的方式而生成,反过来说也一样,人通过规定对象而使得自己按照对象所“允许”的方式生成。
由此可见,《手稿》所说的人与对象的关系并不是笼统地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等说法就能够表达出来的。这种关系用《手稿》中的例子来说就是,正如人眼的对象是以一种恰好成为人眼的对象的方式而成为这种对象一样,感性的人的对象也必然以一种“恰好成为人的对象”的方式而成为人的对象,也就是说,人“设定”对象的过程是以被对象“设定”的方式进行的,人与对象在一种相互“设定”的关系中相互生成:“它(对象性存在物)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209但这种相互“设定”不是从纯粹思维层面上来进行的,也不是如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样,从纯粹的感觉、直观或爱的方式进行的,它是以现实的、感性的和实践的方式进行的,人以改造对象世界的方式与对象世界相生相成,而动物只能以消极适应对象世界的方式与对象世界相生相成。人与对象世界相互生成关系的成立依赖于双方彼此“选择”对方、彼此相趋的性质。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1]191人眼的性质决定了人眼的对象,而与此同时,人眼的对象又以它所特有的性质决定了人眼的性质,这种相互规定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因为人是自然界的存在物,所以人被自然界设定,人正是在这种被设定的情况下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而再现自然界,使之成为对自己有效用的东西,这个过程就是自然对人的生成和人对自然的生成。由此,自然界与人以一种相互规定而相互生成的方式同时为对方而存在,这是一种排除外在的“造物者”而达到的“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Durchsichselbstsein)。[1]195
这是马克思在《手稿》里对对象性概念的独特理解,如学者吴晓明说: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与构成近代哲学之本质概括的“对象性”一词具有“完全不同”“近乎相反”的旨趣和含义。[3]它所表达出来的人与对象之间的循环因果关系或“本体论”颠覆了西方传统哲学中单向的因果关系或“本体论”。在传统哲学中,人的存在或世界的存在基本上都是从一种本身不包含着“人”或“世界”的纯粹因素(本原)中单向地被设定出来的,这是一种“A→B”的结构。正是由于这种单向性,“A”倾向于被理解为一种离人和世界越来越“远”、越来越纯粹和抽象的形而上学范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正是根植于人类理性的这种“A→B”思维方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思辨理性必然在一切有条件者身上预设一个本身不再具有条件的“无条件者”并以此来理解有条件者,可以说是针对这种“A→B”(无条件者 → 有条件者)思维方式的批判。而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历史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结构:“人对象”(AB),“”指的是一种双向的、通过相互规定而相互生成的本体论关系,因此,在“人对象”中,“人”与“对象”两个因素相互将对方当作自己的结构性因素,相互包含着对方,正如自然界是有人的自然界一样,人也是有“自然界”的人;正如世界历史是有人的历史一样,人也是有“世界历史”的人。只要讨论到人的现实性或现实的人,那么也就必然意味着讨论到作为其对象的感性自然和世界历史。
与施蒂纳彻底反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Guttungswesen)概念做法不同,马克思在《手稿》中接受了这个概念,但他吸收了赫斯《货币的本质》一文的观点,不是从宗教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类本质的问题。他以类似于费尔巴哈的口吻说,人因为能够把自己的类本质当作对象,因此才成为类存在物(Guttungswesen)。一方面,自然界作为使得人的肉体生活得以存在和维持下去的资料,是人的类本质;另一方面,社会历史也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说明后一点,他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穆勒摘要》)一书摘要中认为,在生产中无论是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5]170,交换或物物交换都是一种社会的、类的行为[7]173。在《手稿》中,马克思更清晰地认为,由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都是维持人作为人的本性得以存在的因素,因此,它们都是人的现实化的和公开化的类本质,因此,无论自然还是社会历史,都是被中介了的存在,是人的普遍存在。
类本质是构成一类存在者之所是的要素,它对类的每一个成员有效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类本质对于类的成员而言是普遍性、绝对的。动物由于不能把类当作对象,因而并非真正的类存在物。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人的类的一份子而存在的(因而也就能够区分出其它不同物种的类,从而能够自由地把不同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并能够根据这种意识而进行实践活动,因此,人是类存在物,能够把自己的个别性存在提升到类的普遍性存在,具有普遍性的规定。就此来说,人的本质不是个别性本质,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共同本质。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认为,在非异化的状态下人的个别性的实现就是其普遍的共同本质或社会本质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5]170*引文把Gemeinwesen改译为“共同本质”,原译是“社会关联”。关于Gemeinwesen,国内学者张一兵和韩立新都赞同改译为“共同本质”或“共同存在性”,本文采取“共同本质”的译法。改译理由请参阅: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209页;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人的普遍性的类本质是社会性,这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现实个人的个别性与其社会性之间的相互生成的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共同本质”理解为在社会关系中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生产关系,人在现实劳动中全面地产生了自然和社会历史,而这些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为人的劳动提供了特定的条件,从而规定了人的劳动所必须采取的实现方式。只有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个别性的人才能够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性的事物(Sache),劳动是现实个人的个别性规定与社会性规定相互发生关系的中介。正是通过规定劳动,社会关系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产物才能够在被人们规定(改变或产生)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个体无法逃避和摆脱的先验因素规定着个体的对象化活动。这种相互生成的关系中前面我们曾经表述为“人对象”,现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更进一步地表述为“个别性社会性”。
人与世界的二律相生的结构显然与《手稿》中另一种逻辑结构——异化——不同。在《手稿》中,当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与异化问题联系起来时,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思路:未被异化的本真历史→异化的历史→扬弃异化后达到的更高层次的本真历史(A→B→C)。这种思路被广松涉称为“异化论的构图”[8]48-60,它充满了黑格尔的色彩,用张一兵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非科学”的“隐性的黑格尔神学构架”。[9]231异化论的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结构框架(“A→B”)不无关系,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方面揭示了思辨理性通过预设无条件者来理解有条件者的逻辑运用原则,另一方面又揭示出,所谓的无条件者不过是理性自身的概念(先验理念),因此,当思辨理性促使知性的一切内容朝向无条件者进行大一统的运动时,实际是理性将一切知性内容收归自身。这可以说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理性(绝对精神)通过外化自身又最终回归自身的异化论逻辑的雏形,“A→B→C”的异化论逻辑是形而上学“A→B”结构的复杂化和变种。上述把马克思关于现实个人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表述为“AB”式(“人对象”和“个别性社会性”)的二律相生结构,显然是对异化论逻辑的克服与超越。二律相生的结构克服了异化论逻辑通过先验地预设一个大写的“人”,从而把现实历史的发展理解为这个“巨大的主体”客体化、然后再主体化的过程的立场,而认为,现实个人通过发挥自己的共同本质和社会性而构建出现实世界,并在被自己构建出来的社会关系的规定下继续发展自身以及社会关系。这种二律相生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广松涉所谓的“物象化论的构图”。广松涉在分析马克思的《手稿》时,通过把人的本质与“共同态”、“社会性”或“关系态”等概念联系起来,发现了《手稿》除了异化论的逻辑之外,还蕴含着物象化论的逻辑。[10]38我们可以说与之殊途同归,我们从《手稿》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对象性活动”和“类本质”等概念中发现了这两种不同的线索。
殊途同归不过是偶然的事件,关键是这两个相同的发现共同说明了,《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阵地”,不同的思想立场在其中存在着冲突和对立,其中由现实个人与世界历史的二律相生的关系所彰显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虽然尚属“隐性”,但已经显示出不可忽略的发展劲头和理论深刻性。而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有更为精彩和深入的体现。
《手稿》之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类”或“类本质”的概念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态度实质是马克思对自己在《手稿》中所表露出来的异化论立场的反思。在他们看来,错误真正来说并不在于他自己所使用的“类”或“类本质”等概念,而在于“哲学家们”(黑格尔左派)对这些概念的习惯性用法,这是因为,“哲学家们”习惯于把制约着现实个人的历史条件与现实个人脱离开来,把那种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纯粹体现的、大写的“人”强加于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个人,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从而把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人视为这个大写的“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的结果就是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1]582这种思辨的思考方式实质就是异化论的逻辑。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则上并不反对把人理解为对象性和类的存在物的观点。现实中单个人在受制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能动的活动而发展出普遍性的社会关系,这种“个别性社会性”二律相生的结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关于现实个人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把人的现实性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正如广松涉所说的那样,这还只是一种“一般性的提法”[8]36,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逐渐具体起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现实性本质,到《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真正找到了思想轴心,他们开始谈论“一定的”(bestimmte)社会关系,并且在关于对现实个人的表述中加入了“一定的个人”(bestimmte Individuen)这个新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只是字面上的转述,但实质包括着丰富的内容。
在《形态》的“费尔巴哈篇”中,“一定的”(bestimmte)这个寻常的单词出现得如此频繁*据统计,在《形态》的“费尔巴哈”篇中,“一定的个人”这种意义上的“一定”出现次数达30多次。,以至于都几乎不需要作引用来证明它的存在,但无论它是用来形容人还是其他主词,向来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张一兵教授在其著作《回到马克思》中曾注意到它,并准确地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话语”[9]538])。人们的普遍忽视是有理由的,因为在一般的语境中,一定的个人就是现实个人。但是如果要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深处,那么这两者有着不可忽略的区别。“bestimmte”除了被译为“一定的”之外,还常被译为“规定的”“特定的”,我们在德国哲学中常遇到的“规定性”(“Bestimmtheit”)和“规定”(“Bestimmung”)都与这个词同词根。因此,一定的个人就是有规定的个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现实个人之所以是现实个人,就是因为它是有具体的、现实的规定性的,例如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纯粹的、无现实规定的抽象之人相区别,在这种意义上“一定的个人”就是“现实个人”。但是,“现实个人”只是一般地指示有现实规定或处于任何历史阶段中的个人,它没有对不同的历史阶段作出区分,没有对这个一般性的“现实规定”有更进一步的限定,没有表达出个人只能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个人之意。“一定的个人”的“一定”则包含着这种区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723在这里,马克思就借用“一定的”这个限定词,对现实个人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作了区分,黑人在任何历史中都是现实个人,但只有在奴隶制社会中才是奴隶,因而他的“奴隶”这个规定是与特定的历史关系相联系着的,这相当于“工人”这个规定是现实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具有的规定一样。“一定的个人”之“一定”是对现实个人必然处于某特定的历史关系、是这个特定历史关系的总和这种现象的表述,因此它比“现实个人”内涵更大。现实个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的个人则只是“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在《形态》中,最为准确地反映了这层意义的“一定的”这个词的无疑是这句常被引用的话:“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523一定历史阶段的个人与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相互对应,奴隶制下的黑人无论怎么劳作,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奴隶制原则上也无法把黑人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意义中的“工人”。任何现实中的个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个人,它只是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对历史的阶段性不加区分,那么就很容易导致类似于统治阶段将自己的特殊性变换为普遍性蒙骗人的情况。这就是要区分“现实个人”和“一定的个人”的重要之处。
一定的个人的历史阶段性反映着现实中的个人与他所处其中、一定范围内的历史条件通过相互制约而相互生成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一段话准确而集中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519一定的个人的生产方式是被它处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而这种社会关系本身又是被这些个人产生出来的,一定的个人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一定的社会关系则是一定的个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例如,中世纪城市的市民在反抗封建阶级时产生了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反抗过程中所产生出的新的生活条件成为一种共同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1]569一定的个人总是自己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就是被决定的决定者,每一个时代或每一段历史都是通过被历史地决定着的个人能动的改造性和生产性的活动而不断地推进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545的关系。这种二律相生的关系可以表达为:“一定的个人社会关系”。
现在,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二律相生结构已经有了三种表达方式:“人对象”“个别性社会性”“一定的个人社会关系”,前两者是从对象性和类本质的角度对人与世界的二律相生关系的反映,而后者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更为准确地反映出这种关系,它是历史唯物主义二律相生结构的最好说明和最直观的表现,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真正生成,这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义:现实历史的发展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人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在作为这种对象化结果的社会历史中获得对自身的确证的过程,自然、历史、政治和经济等种种因素被这种决定活动纳取进来,从而成为组建人与世界二律相生的关系的要素。这个过程被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集中地表达了出来:“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也更新他们自身。”[11]
因此,正如广松涉所说,在《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历史、一定、存在”的基本构图展开[8]48,我们认为,区别于黑格尔思辨哲学所具有的“A→B→C”式的历史发展构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境域中,现实之人与世界历史之间所具有的“一定的个人社会关系”的二律相生结构将会形成这样一个构图,它由人与世界的相生相成关系出发,以涟漪层层扩散的方式伸展为如下一个绵绵相关、缘缘相生的不断涌现和翻新的现实过程:
四、余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欧力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5.
[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360.
[5][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1.
[7][美]Paul Kockelman.Four Theories of Things: Aristotle, Marx, Heidegger, and Peirce[J]. Signs and Society, 3(1):153-192.
[8][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10][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M].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6.
〔责任编辑:杜娟〕
[收稿日期]2016-01-12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15ZDB001)子课题“基于MEGA2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研究”
[作者简介]陈广思(1987-),男,广东茂名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6-00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