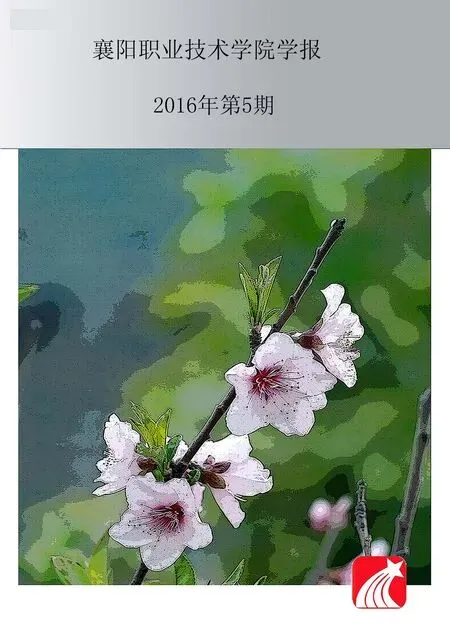惶恐背后的出路
田媛媛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西安 710127)
哈罗德·品特(1930—2008)是20世纪后半叶公认的杰出的剧作家,被誉为英国戏剧舞台上继萧伯纳之后最为重要的剧作家,被评论界认为“本世纪以来对戏剧的语言、行动和人物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和变革的英语剧作家”。2005年10月3日,瑞典皇家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品特,以表彰其在戏剧创作上的创新与成就——“品特揭开了日常闲谈之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被压抑者紧闭的房门,”并且“让戏剧回归它的最基本元素: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可预测的对话,人物相互之间都可能被对方击败,虚饰土崩瓦解”。
《归于尘土》创作于1995年,剧中冷漠对峙的人物,现实与记忆的错位,破碎的故事凭借,隐隐的暴虐恐惧,潜在的惶恐不安,沉默无声的反抗,都是典型的“品特式风格”的立体呈现。
从表面上看,《归于尘土》是丈夫德夫林和妻子瑞贝卡的闲谈。德夫林不断地审问瑞贝卡关于她情人的信息。在催眠的作用下,瑞贝卡开始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叙述她的情人。她的情人对她既粗暴又温柔,“攥紧拳头”,“摩擦我的嘴唇”,让她“亲吻他的拳头”,“非常轻柔”地用手抓住她的喉咙,并压迫她的喉咙。他在一家像工厂一样的旅行社做向导,非常受人尊敬,他“总是去当地的火车站,走上站台,从那些哭喊着的母亲手里把她们的婴儿抢走”。对于这些,瑞贝卡都表现得若无其事,无所谓赞同或反感。在整个叙述过程中,瑞贝卡都感到隐隐的惶恐不安,即使去看电影也感觉有个死尸一样的男人如影随形,让她想远远地离开。她站在市内一座非常高的建筑顶层的一个房间里,看见手拉着手行走的一个老人和孩子,后面跟着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瑞贝卡突然发现她自己就是那个女人,紧紧搂着孩子,感受她的心跳和呼吸。随着瑞贝卡亦真亦幻的叙述,德夫林走向她,抓住她的脖子,把手掌放在她的嘴上,压迫她的喉咙。瑞贝卡沉默地反抗,德夫林终于松开了手。瑞贝卡又开始讲述火车,女人,孩子,抢孩子的男人,一句一顿,伴着回声。最后是静场,长时间的静场。
剧中,在丈夫德夫林的问询下女主人公瑞贝卡对暴虐事件进行了恍恍惚惚的回顾,体现了暴虐事件给受害者带来的终身难忘的心理创伤,同时通过回顾叙述也帮助瑞贝卡将创伤记忆外化为叙事记忆,从创伤记忆的阴影里走出来,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在提醒现代社会人们该如何走出暴力记忆所带来的胁迫和惶恐,让创伤记忆入土为安,心灵回复平静。
关于《归于尘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剧的怪诞以及真实和记忆方面的分析。穆海亮在《超越荒诞,直面人性的梦魔》中阐释以超越怪诞的姿态,直面人生的梦魇。张友燕的《记忆与真实之间》分析《归于尘土》中瑞贝卡在记忆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来回交错,传达了创伤记忆者身心上难以消磨的暴虐记号。
本文主要分析《归于尘土》中瑞贝卡经受丧女之痛,深陷创伤记忆无法自拔,终日惶恐不安的现状以及在丈夫德夫林的充满爱的问询之下,她试图寻找走出创伤惶恐的突破口,最终通过叙述创伤事件,将创伤记忆外化,走出了惶恐,回归精神上的安宁。
一、惶恐之现状
瑞贝卡是一位为情所伤的受害者,她“最好的朋友”,她“付出了所有感情的男人”残忍地从她怀里抢走了她的女儿,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罪恶感中。丧女之痛的创伤记忆不断袭来,令瑞贝卡终日惶恐不安,导致她心理异常、梦魇不断。
(一)心理异常
瑞贝卡反感丈夫叫她亲爱的,“你叫我亲爱的,真是太奇怪了”,“多滑稽啊”,这说明了她和丈夫感情的疏离。但是她却试图向德夫林倾述,从他那里去寻求摆脱惶恐的出路。当德夫林询问她为什么不安的时候,她敞开心扉向他说明了原因,“要是我不能告诉你,我还能告诉谁呢?好了,我来告诉你吧”。从中可以看出瑞贝卡和丈夫感情的疏离但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了她心理的极度异常不安。
当听到警笛声消失了的时候,瑞贝卡感到非常不安,“我讨厌警笛声消失……我讨厌它离我而去。我讨厌失去它……我要它属于我,永远”。在瑞贝卡看来,呼啸而来又匆匆远去的警笛声是“多么美妙的一种声音”,她企盼在警笛声中寻找安慰,这让人看来实在是滑稽可笑。从中我们也不难得出,瑞贝卡在创伤记忆的折磨下,已经丧失了正常的思维。
而在和德夫林的对话中,瑞贝卡总是答非所问,思维混乱。德夫林让她说说关于她情人的情况,她回答的却是写便条的时候用的钢笔从桌子上滚下去了,并不停地为那只钢笔辩护,“那只完全清白的钢笔”。从中可以看出遭受过暴虐的瑞贝卡内心深处一直不能平静,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不能正常地面对处理生活中的事情。
在德夫林请求瑞贝卡重新开始的时候,瑞贝卡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我们开始过了。我们没法再次开始。我们可以再次结束”。关于这个问题,两人争执了许久,德夫林提醒瑞贝卡说她用错词了,但是瑞贝卡还是坚持己见,“我们可以再次结束。然后再次又再次。然后再次”。不可再次开始却可以再次结束,瑞贝卡荒唐梦游般的语言表明了她心理的错位和飘忽不定。
曾经受到的创伤始终萦绕着她,令她陷入无法自拔、难以控制的重复讲述状态。由于丧女之痛事件发生得太突然,太无防备,瑞贝卡在对这一事件反复的体验中,导致了一系列的心理异常。在整个对话过程中,瑞贝卡处于梦幻游离的状态,意识模糊,语言逻辑含混不清,时时感到有一种压迫的惶恐。
(二)梦魇不断
创伤记忆挥之不去,瑞贝卡精神上不断地受到梦魇的惊扰,隐隐的威胁时时刻刻地存在着,压迫着她的神经,让她迷失在丧女之痛中,无法自拔。
随着瑞贝卡的叙述,她看到了一大群人在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大海,潮水慢慢地淹没了他们。他们的行李在波浪中四处漂浮着”。在创伤记忆的侵蚀下,瑞贝卡如同一个溺水的女人般无助无奈,而这种荒谬恐怖的场景正体现了瑞贝卡的精神困境。
瑞贝卡感觉自己会在一个“肉汁的汪洋大海中窒息”,这“很可怕,但这都是你自己的错,你自作自受。你不是它的受害者,你是它的肇事者。因为首先是你把肉汁洒了,正是你搞出了这一大堆麻烦”。这种恐怖的窒息感或许是每一个遭受过暴虐有着创伤记忆的人的精神梦魇吧。
即使去看电影,瑞贝卡也能感觉到有一个“僵尸一样的”男人“坐在我的前面”,让她想远远地离开。
在市区一座非常高的建筑顶层的一个房间里,瑞贝卡看到了一个跟在一位老人和小孩后面走着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女婴,“她亲吻她的孩子”,倾听孩子的心跳和呼吸。忽然间,瑞贝卡意识到这不正是她自己吗?于是她搂紧孩子,感受孩子的心跳和呼吸。然后德夫林走向她,将她从梦魇里带了出来。
二、惶恐之出路
走出创伤记忆的前提是打开记忆阀门,真实地叙述自己的创伤记忆。在叙事过程中,将自身的创伤记忆转移到别人身上,实现自身心理创伤的外化,这是走出创伤记忆带来的惶恐的重要途径。
当瑞贝卡开始关注自我、关注现实生活的时候,她已经做出了走出创伤记忆走出惶恐的尝试。在德夫林爱的感化下,瑞贝卡还原创伤事件的真实情境。在叙事过程中,将自身的创伤记忆转移到别人身上,实现自身心理创伤的外化。瑞贝卡平静地叙述受虐过程,使她完成了对心灵的自我疗救,慢慢走出创伤。
(一)变顺从为反抗
在与德夫林的交流中,瑞贝卡尝试性地去反抗和摆脱困扰她的威胁,试图寻找突破惶恐的出口。当德夫林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不能坐在那儿这么说话”,瑞贝卡马上反驳道,“你不相信我有权在我住的地方坐在这把椅子上?”
在建筑顶层,幻想中的瑞贝卡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亲吻她的孩子,感受孩子的呼吸和心跳,已然没有任何人能从她的手中抢走孩子。
面对丈夫德夫林的施虐,“他把手放在了她的喉咙上,轻轻压迫。她的头向后仰”,瑞贝卡选择了静止不动和沉默不语来进行无声的反抗。终于,德夫林“把手从她的脖子上拿开”。此时,瑞贝卡的抗争已然超越了自己的恐惧。
(二)创伤记忆外化
当个体受到创伤时,被创伤记忆所折磨时,他人的爱和帮助是受伤者复原的一剂良药。爱是创伤后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关系的基础,也是打开受创者封闭的内心世界的钥匙。在爱的感化和安抚之下,受创者可以将内心的痛苦释放出来,重新建立对自我的认识,重拾生活的信心。
在《归于尘土》中,德夫林称呼瑞贝卡为“亲爱的”,并耐心地一次次询问试图用爱和包容去打开瑞贝卡的创伤记忆闸门。瑞贝卡讨厌警笛声消失,德夫林安慰她:“别担心,它一定还会有的,相信我,你很快就会再听到它的。……你再也不会孤独,你再也不会没有警笛声陪伴,我保证。”瑞贝卡在丈夫关爱的话语之下,终于卸下防备,开始叙述创伤经历,释放内心的惶恐和痛苦。瑞贝卡断断续续地叙述着她的创伤经历:“他们把我们带上火车……我带着我的孩子,我把她裹在我的披巾里……我把她做成一个包裹……我把它挂在我的左臂上……然后我走过去,带着我的孩子……可是孩子哭了起来……然后那个男人把我叫了回去……他说你那儿有什么……他伸出手来摸包裹……我给了他包裹……那是我最后一次拿这包裹。”根据创伤心理治疗理论,创伤叙事可以最大限度地将自身的创伤记忆转移到别人身上,实现自身心理创伤的外化。戏剧最后瑞贝卡说“我不知道什么孩子”,说明通过对丧女之痛的创伤记忆的叙述,她已经将过去搁置,完成了对心灵的自我疗救,从而走出伤心惶恐,达到了心灵的宁静。
三、结束语
作为一部创伤记忆的佳作,《归于尘土》是品特用充满诗意与怪诞的意象,展示了一种生命与死亡、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现实梦魇相互冲突的存在。剧中,丧女之痛的创伤记忆带给瑞贝卡的灾难和痛苦是无尽的,她心里时时刻刻惶恐不安,生活被梦魇纠缠。但是在丈夫德夫林充满爱的话语的感化下,瑞贝卡终于打开创伤记忆的阀门,真实平静地叙述自己的创伤记忆,还原创伤事件的真实情境,实现了心理创伤的外化,最后走出了惶恐,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这部作品也在提醒现代社会的人们,只要心存爱意,坦诚面对过去,真实再现暴虐过程,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定会入土为安。
参考文献:
[1]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42-75.
[2]Gale.Sharp Cut:Harold Pinter's Screenplays and the Artistic Process[M].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3:04-53.
[3]Victor L.Cahn.Gender and Power in the Plays of Harold Pinter[M].Macmilla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4:11-63.
[4]陈红薇.《虚无乡》:品特式“威胁主题”的演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3(1):81-87.
[5]哈罗德·品特.归于尘土[M].华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263-285.
[6]刘红卫.哈罗德·品特戏剧伦理主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7]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M].华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22.
[8]穆海亮.超越荒诞,直面人生的梦魇[J].新世纪剧谈,2011(4):55-59.
[9]罗洛·梅.爱与意志[M].宏梅,梁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55.
[10]罗洛·梅.心理学与人类困境[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24.
[11]王燕.哈罗德·品特戏剧话语里沉默现象的语用文体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0.
[12]任俊玉.创伤记忆人道情怀——哈罗德·品特戏剧创伤主题探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
[13]孙琦.流沙上的互动:哈罗德·品特的博弈话语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14]袁曦.威胁性生存中的选择与反抗[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15]袁晓华.综合的艺术,艺术的综合——哈罗德·品特及其创作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3-37.
[16]张友燕.记忆与真实之间——解读哈罗德·品特的戏剧《归于尘土》[J].山花,2013(14):144-145.
[17]赵冬梅.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