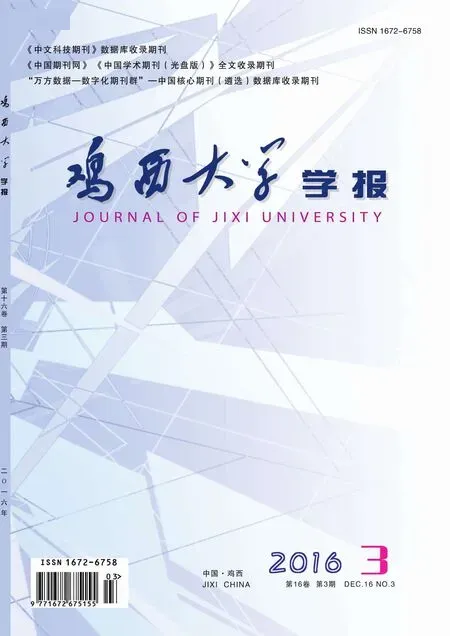汉语祈使句的研究现状
司罗红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汉语祈使句的研究现状
司罗红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祈使句是人类重要的语用语法范畴,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前人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祈使句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了十分可信的研究结论。试总结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的各个层面成果,归纳出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祈使句;特点;研究现状
高明凯《汉语语法论》之前的语法著作虽然也提到祈使句并且认为祈使是一种重要的句类,但是大多数的学者都将其归为语气,在语气词中进行讨论,很少从表达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高明凯指出祈使句表示命令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问题,祈使是一个句法问题,命令的表达是依靠整个句子来表示的,开创了对祈使句进行全面分析的先河。现代汉语祈使句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祈使句的主语问题
朱德熙《语法讲义》认为祈使句的主语往往是第二人称代词“你、您、你们”,不过祈使句的主语常常略去不说,并且指出第一人称的“我们、咱们”也可以做祈使句的主语,有时用听话人的名字来作祈使句的主语,这时“人名”是第二人称,否则句子是陈述句不是祈使句,例如:小赵把门关了。
如果这话是对“小赵”说的,此时的“小赵”是第二人称,这个句子是祈使句;如果这句话是对“小赵”以外的人说的,这时的“小赵”是第三人称,这个句子就不是祈使句,而是典型的陈述句。
邢福义先生认为,祈使句的主语在词面上往往是第二人称,但实际上隐含了含有命令成分的“我命令(你)、我要求(你)”,祈使句的结构实际上是“(我要)你VP”,通常只说了“你VP”,主语是呈现第二人称。当隐含的部分全表达出来,构成“我要你VP”时,主语便是第一人称。
沈阳(1994)将祈使句的省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通常要有省略,但必要时可以补出;另一大类是通常要出现,但有时可以省略。马清华(1995)认为应当区分主语和祈使的被传人,祈使句的主语并不总是话语的接受者。
由于祈使句常出现在对话中,带有明显的口语特征,陈建民(1984)指出口语中零句多,大部分是无“主—谓”形式的省略句;周斌武(1983)认为汉语祈使句的主语根本不出现;高明凯(1975)认为祈使句的主语可以随便使用,出现与否许多情况下是自由的;安妮·桥本(1973)认为祈使句的主语可以根据某些条件被随意删去;刘月华(1985)运用统计的办法研究祈使句,在对曹禺《雷雨》《日出》《北京人》进行数据分析后指出,祈使句主语出现的概率为50%;马清华在对百万字的材料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是出现主语与否的次数比是1:1.4,由此得出结论,汉语祈使句的主语在字面上出现与不出现相差无几。
二祈使句的谓语
高明凯《汉语语法论》和朱德熙《语法讲义》都认为祈使句的谓语只能是表示动作和行为的动词或动词性结构。很明显不是所有动词都能进入祈使句,祈使句对进入其中的动词都有什么样的限制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前辈们从不同角度给动词分类,探求其中的规律。
刘月华(1985)运用统计的手段和方法,统计分析了曹禺三部作品的祈使句,指出只有自主性的动作动词可以进入祈使句的肯定形式,非自主动词不能进入这一格式。从意义上说,具有褒义的动词或具有积极意义的动词容易进入肯定形式的祈使句,而不能进入否定形式。于此相反,具有贬义的动词可以进入否定格式,但不能进入肯定格式的祈使句。蒋平(1984)认为形容词也可以进入祈使结构表达祈使功能,并对形容词进入祈使句的现象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与刘月华相似:具有褒义的形容词不太容易进入“别太A、别那么A”之类的否定格式祈使句,而容易进入“A一点儿”之类的肯定格式;贬义的和具有消极意义的形容词与之相反不容易进入肯定格式。
袁毓林(1991、1993)对祈使句式与动词的类别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指出只有自主性的可控动词可以进入祈使格式,各种格式对动词的要求并不相同,一般具有自主性的褒义动词,一般只能进入肯定性的祈使句,不能进入否定性的祈使句,例如“尊重、爱护……”。自主动词的贬义动词一般只能进入否定祈使句“别V”格式,例如“欺骗、埋怨、敲诈”等等。一部分的非自主动词也能进入否定性的祈使句,不能进入肯定性祈使句;而中性的自主动词可以进入肯定格式的祈使句,也可以进入否定格式的祈使句。
王红旗(1996)研究祈使结构的否定形式,根据“别VP”所表示的意义,将祈使格式“别V了”区分为六种不同的意义类型,这些意义决定了这一格式的动词的语义特征。
三语调
一般认为,语调是表达祈使语气最主要的手段,例如胡明扬(1995、2002)指出,语调是句子中必备的语气要素,可以向听话人传递某种语气信息,如“陈述、疑问、允许”等,有相同观点的还有邢公畹,马庆株(1992),“句子都有一定的语气,主要靠语调来表达”。胡附、文炼(1995)、高更生(1984)认为祈使句的语调特点是降调。邢福义(1996)认为“祈使句是表示命令或请求的句子,语调逐渐下降”。吕翼平(1983)也认为“祈使句的句尾语调一般下降”。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张志公(1959)、吴启主(1986)等等。
但将语调简单的称为降调过于宽泛。罗常培(1956)指出降调不是祈使句所特有,陈述句、感叹句和特指疑问句也多用降调。赵元任(1926)指出,语调跟口气有关系,祈使句由于说话者口气的不同,可以表现为多种不同的语调。胡明扬(1987)指出,“只说句末语调下降,不能全面、准确的反映实际问题”,并认为应当以严格的理论来区别祈使句的语调,认为祈使句的语音特点是在语速上节奏快,每一个都很短促,并且音节之间的间歇也很短。
齐沪扬(2002)指出,语调是任何一个句子所表现出的语气都必须具有的形式标志,而且认为语调是区分“陈述、疑问、祈使、可能、允许”等等句类的一个必要过程。马清华(1995)认为以语调来区分句类,不但不能证明语调对祈使句有决定性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祈使句这一类别存在的合理性,并指出劲松(1992)在通过语调划分的句类中,几乎所有的祈使句都可以归入陈述句的某一次类。胡明扬(1987)指出如果全句在语义上已经足以表达命令语气,就不一定再用命令语调。吕叔湘(1988)指出在划分四大句类时并没有将语调作为主要因素考虑进去,不然,语气也就不只是四类了。安妮·桥本(1973)指出将语调作为祈使语气的主要表达手段和划分句类的主要标准,“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十分模糊不清的”。
徐杰(2010)明确指出语法的问题应当从语法形式上得到根本解决,语调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语法问题,而是语音学的问题,不能作为语法的主要标准。贺阳、劲松、沈炯等都通过实验的手段将语调分为有区别意义的三个语域类型并指出五种基本句型在音高的调域上有不同的表现,但这些都是语图仪上的语波形式,是语音学的研究对象,对语法研究有重要的参看价值,但不能作为语法研究的标准。
四祈使句的标点
齐沪扬认为语调的形式标志应当是标点符号,“选用标点符号的形式标志,尽管不如其它的那些特征严密,但它的优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将语调分为三类:句号类、问号类、叹号类,其中请求语气为句号类和叹号类,而命令语气为叹号类”。胡附、文炼(1956)以为祈使句标点使用情况与其它句类有区别,认为祈使句在书面语中只能凭着语气词和标点符号来识别。高明凯(1957)认为表示命令,在书写语言时一般使用“!”号,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张静(1986)、吴启主(1986)等,但北京大学(1960)则认为祈使句一般使用句号,只有强调的时候才可用感叹号。但徐杰(2010)指出祈使句在书写上采用叹号不是祈使句的形式标记,标点符号的使用不是典型的语法问题而是一种书写问题,不能用做祈使功能的判定标准。马清华(1995)指出祈使句使用叹号和非叹号的比例会随书写人风格等多种随机因素的改变而改变,例如在老舍的《茶馆》中两者之比为2:1,而在曹禺的《雷雨》中两者之比为1:2.5,得出结论为祈使句不只单使用一种标点符号,也不以某种标点为主。标点对判别祈使句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凭标点识别祈使句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五祈使句的语气词
祈使句的语气词问题讨论的较早,也一直以来是语法界研究中的领域和热点问题,得出的结论和研究成果也非常的丰富。马建忠(1898)在讨论助词时就分析了“谕令之句”和“禁令之句”中出现的助词。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认为祈使句的句尾能够出现助词“了”,这一助词的作用是使语气变得缓和,不用助词则请求变为命令,劝阻变为禁止;语气助词“罢(吧)”可以出现在祈使句中,传递一种商榷的语气。吕叔湘(1944)指出祈使句的语气词是以支配人的行为为目的,祈使句与语调有很大关系,但也借助于不同的语气词。祈使语气的语气词常用“吧、啊”两个,有时也会用“呢”。“吧”的主要作用是劝阻,有时表示准许,语气直率,接近于命令;“啊”在语音上比“吧”要响亮,有较重的督促语气,含有的劝阻意味较少,“呢”表示讽喻口气。丁声树等(2002)《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认为语气助词“啊”主要是催促和嘱咐语气,“吧”则包含较浓的劝说意味。黄伯荣、廖序东(1991)《现代汉语》认为祈使句使用语气助词相对自由,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使用两个不同的语气助词会产生不同的附加意义。“呢”主要表示商量语气,“啊”有缓和语气的作用,“哟”用来表示劝告,“了”则表示变化。邢福义(1996)指出常用于祈使句的语气助词有两组,第一组“吧”,常用于要求别人做或者不做某事;第二组为“啊”,常用来表示敦促和叮嘱,两组不同的语气助词表示不同的语用和语义功能。齐沪扬、朱敏(2005)指出语气词的选择与多种因素有关,肯定式祈使句带语气词的比例高于强调式和否定式;肯定祈使句的句末语气词主要以“吧”以及“啊”的变化为主,强调式和否定式则常用“啊”;在语气词的功能上,“吧”以缓和语气为主,“了”更多的是用于表态,“啊”本身的话语标记功能在于强化命题内容,它又有延缓语气的作用。齐沪扬(2001)指出:从真实文本的大量语料看,“吧”的最大用途是用在祈使语气中。
尽管有很多学者研究祈使句中的语气词,但也有人认为语气词不是祈使句的主要特征,马清华(1995)指出“祈使语气并不凭借语气词来表达”,主要理由是现代汉语祈使句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语气词,同一语气词可以出现在祈使句中,也可以出现在陈述句中。胡明扬(1988)认为“现代汉语中没有专门表示祈使语气的语气助词”。何荣(1942)认为“我们中国语言里的语句,并不是都要用助词的,依助词研究表达的语气来分别句类,就有许多语句是无类可归的了”。
六现代汉语祈使句的语义、语用研究
祈使句的语法研究成就卓著,学者们对祈使句的语义和语用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吕叔湘(1944)《中国文法要略》指出祈使句在意义上有刚柔缓急的差别,可以分为命令、请求、督促、劝说,有时祈使句可以加上“请、愿”等字,否定的命令为禁止,语气柔和的可称为劝止,这类句子必然要用否定词,即禁止词。王力(1943、1944)《中国现代汉语语法》也认为祈使句按意义可以分为命令、劝告、请求、告诫,用“罢”时表示委婉,商量或恳求。若不用则表示非如此不可的意义。高明凯(1948)《汉语语法论》认为根据语义命令式可分为强制式和客气式,权威命令是一种强制的命令,而客气的命令为请求式的命令。袁毓林(1993)《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认为祈使句可以从形式和意义上进行分类,其中按意义,根据语气的强弱可以分为三类六种,分别是命令式和禁止式,建议句和劝阻句,请求句和乞求句。
祈使句表达祈使特征,这一功能的体现必定要受到语用条件的约束。袁毓林(1993)认为表达祈使句时,是否有明确的接受对象,听话人是否在现场对祈使句的使用起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语用方面祈使句受到的约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祈使句语用选择的约束,二是祈使句的语用常规的约束,三是祈使句语用预设的约束。徐阳春(2004)认为祈使句的构成必然包含祈使人、祈使与受使人和祈使内容四个要素,实际表达中常常为了表达的简洁在不影响必要信息的传递语用目的表达的前提下省略某人或某些部分。祈使句是否有意义的充要条件是是否拥有合理的预设(祈使句的预设是祈使人在支配受使人),一般预设包括三个方面:对说话的预设;对受使人可能具备完成能力的预设;对受使人原有行为意图的预设。祈使句语用必须遵循“合应”“合境”的恰当性。
七现代汉语祈使句的其它研究
除了对现代汉语祈使句从结构、语义和语用方面进行研究外,学者们对特殊格式的祈使句也从成句添加、表达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张谊生(1997)从语义基础、语法限制和语用约束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性的层面考察影响和制约“把+N+VV”的成句因素。袁毓林一系列关于祈使句的论文,对“V+着”“V+了”“V+C”等格式的祈使句成立的限制进行了论证。王红旗(1996)讨论了祈使句的否定格式“V了”表达的六种主要意义和所受的限制。司罗红(2010)讨论了“V+了+N”类祈使句的成句条件,认为“了”可以进入祈使句,并对这一格式表达的意义进行了论述。肖应平(2009)分析了祈使句不同于陈述句的时间范畴的特点。倪劲炜(2009)分析了祈使句所特有的语气副词“给我”,赵微(2005)讨论了两类典型的祈使句“V着!”和“V了!”在表示否定时的主要区别。
八结语
前贤们对祈使句的研究虽然没有疑问句深入和细致,但是研究理论和方法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层次,研究的问题也几乎涵盖了祈使句的各个方面,得出的结论也非常具有可信性,为我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从句法结构描写得到的关于祈使句的特征:一般为第二人称作主语,使用语气助词,语调逐渐下降,句末使用的标点为感叹号等等都不能完全的作为祈使句的基本特征,都有大量的语言事实与之相背,也就是说前贤们所列举的特征不能涵盖所有的祈使句,另外有些特征并不是纯粹的语法问题。可见祈使句这一祈使功能的基本特征还要进一步讨论。另外,不难发现前贤们的研究多是对祈使句的细致描写,并没有真正的触及到隐藏在祈使句背后的深层规律和原因,按照当代科学的精神,祈使句的案件还处于研究的初始描写阶段,祈使功能特征的表现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探索。
参考文献
[1]高明凯.汉语语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1986).
[2]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社,1982.
[3]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沈 阳.祈使句主语省略的不同类型[J].汉语学习,1994(1).
[5]马清华.论汉语祈使句的特征问题[J].语言研究,1995(1).
[6]陈建民.汉语口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7]周斌武.漫谈句子[A].载上海语文学会主编,语文论丛(2)[C].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8]安妮·桥本.现代汉语句法结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3.
[9]刘月华.从《雷雨》《日出》《北京人》看汉语的祈使句[A].载语法研究和探索(三)[C].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0]袁毓林.祈使句式与动词的类[J].中国语文,1991(1).
[11]王红旗.“别V了”的意义是什么——兼论句子格式意义的概括[J].汉语学习,1996(4).
[12]胡明扬.北京话初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3]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4]徐 杰.句子功能的性质与范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2).
[15]徐阳春.祈使句的构成、预设及恰当性[J].绍兴文理学报,2004(4).
[16]司罗红.祈使句式“V+了+NP”分析[J].兰州学刊,2010(4).
Class No.:H146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Imperative Sentences Studies
Si Luoh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imperative sentence is a significant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pragmatic, which occupies a significant field i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 A certain conclusions, in various angles and levels of the analysis, have already been drawn from the former linguistics. This paper, from all levels of achievements, summarizes the modern Chinese Imperative Sentences, and made some summaries to status of Chinese imperative sentence.
Key words:imperative sentences; traits; status quo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758(2016)03-0137-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语用特征对句子生成机制的影响”(12CYY051);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祈使特征对副词的选择性研究”(2014CYY022)。
作者简介:司罗红,博士,副教授,郑州大学。研究方向:语言理论、对外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