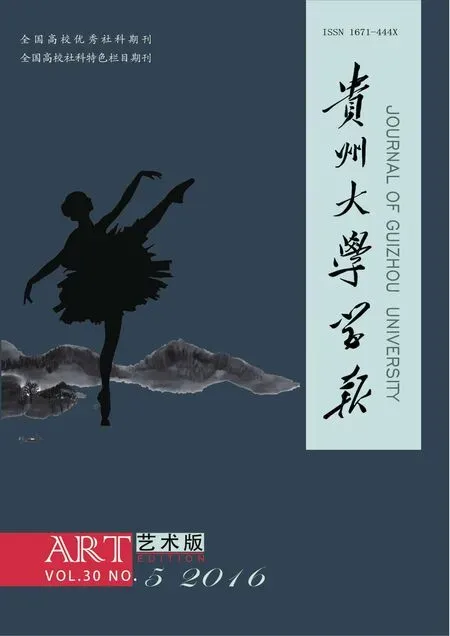戏剧与徽州人的精神世界
洪永稳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戏剧与徽州人的精神世界
洪永稳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徽州人喜欢看戏,戏剧对于徽州人的精神生活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戏剧充当伦理教化的教科书,宣传儒家道德礼教,感化人心,帮助徽州人建立宗法制的礼教思想;第二,戏剧更是徽州人精神慰藉的栖息地,陶冶他们的情操,给他们以精神上的享受,让他们在辛劳的现实生活之外,获得一份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戏剧使徽州人的心灵得到健康的发展,对徽州人精神世界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
戏剧;徽州人;高台教化;审美享受
徽州人是个地域文化的概念,一般是指世代休养生息在古徽州一府六县土地上的人,也包括一些旅徽、客居徽州的人,具体是指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一直到徽州一府六县的解体(1912年)这一时间段生活在徽州版图上的人。徽州人是徽文化的创造主体。在长达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徽州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内容涉及到哲学、绘画、建筑、戏剧、文学、医学 、教育、科学等众多学科,这充分显示了徽州人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当下对徽州人创造成果的研究比较详尽,但对徽州文化创造主体本身(即徽州人)的研究尚显薄弱,而探索徽州文化创造的主体即徽州人的精神世界是个有意义的话题。徽州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徽州人的精神世界与徽州文化之间又存在何种微妙的联系?本文试从戏剧和徽州人的关系入手探讨徽州人精神建构的问题。
一、“徽俗最喜搭台观戏”
对徽州的戏剧研究发现,戏剧在徽州明清时期的发展和繁荣极为昌盛,其发展历程为:徽州的戏剧演出在明代中期开始兴起和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并走向鼎盛。这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从艺术形式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的艺术发展到宋代以后,出现了新的转折,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兴起,艺术向着市民化的方向发展;随着各门艺术的发展成熟,不同艺术之间互相影响,宋代以后,艺术又向着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到明代,已经完成这种综合化的历程,明式家具和戏剧便是这种综合艺术的代表。作为市民化和综合化的戏曲艺术趋于成熟为徽州戏剧的兴起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第二,从社会文化潮流来看,明代是中国戏曲发展自元杂剧以后的第二个高峰,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享乐的需要以及积极的提倡,思想文化的自由,戏剧艺术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潮流,全国上自王公大臣,下自黎明百姓,对戏曲的热情高涨,戏曲活动风靡全国,正如戏曲研究专家金宁芬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明代“上自帝王宫廷、士大夫官邸,下至民间庙台、戏所,无论东西南北,不分春夏秋冬,鼓乐之声不缀,观众如醉如痴的程度”。[1]这样的戏剧热潮氛围推进了徽州的戏剧的兴起与繁荣。第三,从地理环境来看,南曲自南宋“永嘉杂剧”诞生以来,在东南沿海一带流行,形成了号称南戏的四大声腔:昆山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徽州、池州、安庆一带,临近南戏的发源地,自然也属于南戏的流行区,在明代,随着四大声腔在徽州的传播,徽州的戏剧活动逐渐兴起。第四,从外部的经济状况来看,戏剧在徽州的繁荣,要得力于徽商的崛起和经济的繁荣。明代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诞生了名冠一时的商帮——徽商,由于徽商具有“賈而好儒”的人文情怀,他们对于戏剧艺术情有独钟,许多商人蓄养家班家乐,从事戏曲活动。徽商的财力支持和大力倡导,使戏剧在徽州形成繁荣的局面。正是以上这些条件促使戏剧在徽州的繁荣和盛行。
根据朱万曙先生的研究,戏剧在徽州的传播最早可以追寻到明代正统元年(1436年)之前,到万历年间,徽州的戏剧演出活动频繁,徽州的地方志多有记载,如《歙志》卷九就有专门的“艺能·戏艺”条目。到明代中后期,徽州的戏剧活动更加活跃,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戏的四大声腔在徽州的传播。据徐渭的《南词叙录》记载:“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2]《南词叙录》成书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说明余姚腔至少在嘉靖年间已经在池州、太平、徽州等地传播。关于海盐腔在徽州的传播,潘之恒的《鸾啸小品》卷三记载:“金娘子凤翔,越中海盐班所合女旦也。余五岁时,从里中汪太守筳上见之……”[3]219潘之恒五岁那年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说明海盐腔几乎和余姚腔同时在徽州流传。据专家考证,弋阳腔较早就在徽州一带传播,魏良辅的《南词引正》说:“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南词引正》成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说明徽州早已就有了弋阳腔的传播。昆山腔在徽州的流行大约明万历年间,潘之恒《鸾啸小品》记载:“十年以来,新安好事家多习之,如吾友汪季玄!吴越石,颇知遴选,奏技渐人佳境,非能偕吴音,能致吴音而已矣。”[4]这里的吴音就是指昆山腔 ,“新安好事家多习之”说明昆山腔在徽州的盛行。也就是说南戏的四大声腔在明代中后期在徽州已广为流传,可见徽州的戏剧活动开始兴起。
其次,随着四大声腔在徽州的传播,徽州的演戏活动日益兴盛,明中叶以后,看戏成了徽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据明代傅岩的《歙纪》卷五《纪政绩·事迹》中记载:“地方恶少,每逢节令神诞,置立龙灯!龙舟等会,科敛民财,迎神赛会,搬演夜戏,男女混杂,赌盗奸斗,多由此起。”这里提到的“每逢节令”、“搬演夜戏”,说明当时的演戏是常有的一项活动。《歙纪》卷九《逐流娼》记载道:
迩来国蔽民贫,奢俗不改,徽俗演戏,恶少科敛聚观,茹盗赌斗,坐此日甚。近复有地方棍徒招引流娼,假以唱戏为名,群集匪人,惑诱饮博,以至游闲微逐驰鹜若狂。大则窝引为非,小则斗争酿衅,大为地方之害,合行严禁。为此仰通县人等知悉:凡有戏妇尽行驱逐出境,不许容留。地方里约保长逐户挨查,如有仍前隐匿住歇及戏子容留搭班搬演者,即时禀报,以凭拿究。该地方每月朔日具结投递,纵隐并惩。
《歙纪》卷九《禁夜戏》记载道:
徽俗最喜搭台观戏。此皆轻薄游闲子弟假神会之名科敛自肥及窥看妇女,骗索酒食,因而打行赌贼,乘机生事。甚可怜者,或奸或盗,看戏之人方且瞪目欢笑,不知其家已有窥其衣见其私者矣。本县意欲痛革此陋风,而习久不化。然尝思尔民每来纳粮,不过一钱二前便觉甚难,措置一台戏,量钱灯烛之费、亲友茶酒之费、儿女粥饭果饼之肥等来,亦是多此一番喧哄,况又从此便成告状和事,一冬不得清宁者乎?且今四方多事,为尔民者只宜勤俭务本,并力同心以御盗贼,设法积赀以纳钱粮,切不可听人说某班女旦好,某班行头新,徒饱恶少之腹也。其富室庆贺,只宜在本家厅上;出殡搬演尤属非礼。如有故违之人,重责枷示。
明万历抄本《茗州吴氏家典》卷七记载:
吾族喜搬演戏文,不免时届举赢,诚为糜费。
从以上几则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徽州人对戏的痴迷。“奢俗不改,徽俗演戏”说明演戏和看戏是徽州人的传统,以致成为一种风俗;“徽俗最喜搭台观戏”,说明搭台看戏是徽州人最喜欢的一种风俗传统,以致超过其它的风俗;《吴氏家典》的“吾族喜搬演戏文,不免时届举赢,诚为糜费”进一步说明徽州人对戏剧的嗜好,这是对整个徽州人的戏剧情结的真实写照,徽州人不惜财力,把戏剧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次,徽商家班家乐的戏剧活动。徽州普通人的戏剧活动主要是观看戏剧演出,而那些有财力的徽州商人不仅是观看演出,而且还亲自参与演戏活动,训练家班家乐,亲自指导演出。从明代开始有不少徽州商人都有家班、家乐,如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吴允,“以财雄于丰溪,所居广园林,侈台榭,充玩好声色于中”, 有“姬百人,半为家乐”。盐商汪宗孝,“择稚齿曼容千金百排者贮之,教以歌舞,尽一时之选”。戏剧理论家潘之恒的好友吴越石和汪季玄都有家班家乐,不仅拥有家班,还亲自指导,据潘之恒记载:吴越石训练家班演汤显祖的《牡丹亭》,“主人越石,博雅高流,先以名士训其义,继以词士合其词,复以通士标其式。”[3]215徽州商人汪季玄也是蓄养家班并亲自指导家班的演艺,从演员的举步发音到演唱的音律节拍,他都一一指导,精心培养出一批演技精湛的优秀演员。由于徽商的参与,扩大了戏剧在徽州的传播,增进了戏剧演员的表演技巧,使戏剧逐渐在徽州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清代的徽州戏剧活动更为普遍、广泛,演出更为频繁。从官府的公演到民间的义演,从各种节庆的演出到家庭有重大事情的演出,从村头田野到集镇街市,到处都有戏剧的足迹。从现存的县志和府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戏剧演出的盛况。如:休宁县的孚潭,“二月选期演戏,古例昆腔三台,弋阳腔四台,今则随首家丰俭以为增减,亦有迟至三月而后演者,但毋过清明,过者则有罚。”(雍正元年《休宁孚潭志》卷二“岁时”)再如:歙县的丰南,三月九日有“太阳会”,直到端阳节的晚上才结束;五月十三日为关帝圣诞,要“致祭演戏”;六月初旬,要在“仲升公祠前演戏酬神”,并且此习俗“传之已久”(民国《歙县丰南志》卷一)。像这样的文献记载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徽州众多的文书里除了记载演戏的情况外,还记载着特殊的“罚戏公约”,甚至在一些村头街口还刻有“罚戏碑”,由此可见,清代的戏剧已深入到徽州人的生活深处。
总而言之,在明清时期,戏剧活动在徽州非常红火,徽州人对戏剧尤其爱好。众多的古戏台就是徽州人喜欢戏剧活动的明证,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徽州在明清两代建设的大大小小的戏台多达上百座,至今还有古戏台的遗址,如徽州现存最古老的戏台是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绩溪县大石门古戏台,而且,这些戏台大多修建在宗祠旁边,与祠堂并立,可想而知,戏台、戏剧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和祖宗祠堂并驾齐驱。除了看戏赏戏之外,在徽州还产生了众多的影响全国的戏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如汪道昆、潘之恒、汪廷讷、郑之珍、方成培、凌廷堪等。更重要的是,在皖南以及徽州地区还诞生了对后来的中国戏剧产生重要影响的戏剧种类——徽剧。这就是说,徽州人和戏剧有不解之缘,既有消费这种艺术的嗜好,又有创造这种艺术的实践,戏剧成了徽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重要的精神粮食,从而形成了“徽俗最喜搭台观戏”的局面。
二、戏剧:徽州人伦理教化的教科书
戏剧在徽州人的心中地位如此之高,那么,徽州人为什么如此痴迷戏剧呢?戏剧与徽州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关系?若从道德伦理的层面上来看,这大概是戏剧的教化功能与徽州人的伦理精神发生了关联,这就是所谓的“高台教化”。
戏剧其实具有极强的社会教化功能,戏剧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肩负着社会的“风化”,这是对诗经以来的文学讽谏功能传统的继承。中国的戏剧诞生较晚,是在诗文成熟的背景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就渗透着诗经以来儒家的“诗教”和“乐教”的传统。明代初年的戏曲家高明在《琵琶记》一开头就说: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明确提出戏剧的中心任务是“曲关风化”,这里的“风化”是指戏剧表达的思想要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宣扬的是“子孝共妻贤”的伦理道德理想。在明代建国之初,程朱理学依旧是官方的指导思想,明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励精图治,发展社会经济,曾下过几道禁止戏剧的政令,大概是看到戏剧的煽情和娱乐功能对于治国的不利影响,正统的程朱理学也是排斥戏剧艺术的,这就像西方的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一样,认为文艺祸国,对建设国家不利,如朱熹就说过:“俗之淫荡于优戏者在悉屏戢奔遁”(《朱子守漳实迹记》),认为戏剧艺术是“小技”,俗且淫荡,不登大雅之堂。戏子的地位不高,称他们为“优娼”,把他们和妓女划为一列。但是,随着戏剧的发展,明代的统治者逐渐看到了戏剧对维护封建社会的有利一面,可以利用戏剧向人们宣传儒家的伦理纲常,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其统治有重要的作用。于是,改变了先前的敌视态度,转向提倡戏剧活动,他们的重心是放在戏剧的劝善讽谏功能上,这可以从生于王室的朱权和朱有燉以及为官四十载的明朝重臣丘濬的戏剧观上看出来。朱权在《太和正音谱》的自序中写道:“踦屿盛哉!天下之治也久矣!礼乐之盛,声教之美薄海内外,莫不咸被仁风于帝泽也。”[5]他提出戏剧的政治教化和歌功颂德的功能;这种观点在丘濬那里说得更具体,他在《伍伦全备记》(副末开场)中说:“书会谁将杂曲编,南腔北曲两皆全,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这就明确地表达了官方对戏剧的观点。从此以后,戏剧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与因戏剧的教化功能而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徽州的戏剧活动在明清得到很大的发展,盛极一时,其根源也就不难理解。
徽州曾被称为“东南邹鲁”和“程朱阙里”,是儒家文化极盛的一块文化之乡,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宗族礼教思想深入人心,历史上产生了新安理学的哲学流派,捍卫儒道,维护人伦成了他们自觉的追求。自宋代以来,徽州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儒学的卫道士,例如,宋代的朱熹、程大昌,元代的许月卿、程复心、胡炳文等,明代的有朱升、郑玉、赵汸等,清代有江永、程瑶田等。八百年的徽州道德史谱写了一曲“非礼勿听,非礼勿学,非礼物用”的礼学赞歌。在这样的理学之乡,为了加深人们宗族礼教思想,巩固宗法制的封建统治,徽州的乡绅、宗族统治者当然不能忽视戏剧的教化功能,对徽州的乡民进行礼法教育。戏剧的繁荣,对于宗族文化的捍卫,对于伦理道德的守护有莫大的关系,戏剧成了宣传宗法礼教的教科书。这一点可以从明清的徽州戏剧演出的内容看出来。虽然不能具体地知道在明清的徽州演戏的详细情况,但通过一些典籍可以知道在明清的徽州舞台上,教化剧颇受青睐。例如,据潘之恒的《鸾啸小品》卷三记载:“余五岁时,从里中汪太守筵上见之……试一登场,百态轻盈,艳夺人目,余犹记其《香囊》之探,《连环》之舞,今未有继之者。”[3]219这段文字描述了他在汪道昆家看戏,著名的女演员金凤翔所演的《香囊记》和《连环计》的精彩表现。如果撇开女演员的表现技巧,从两剧的内容看,《香囊记》宣传的是“孝友忠贞节义”的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观念,此戏曲的结尾所说:“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这正是徽州伦理社会价值观的经典表达。《连环计》宣扬忠君爱国、杀生取义的献身精神,这也是徽州宗法制社会所需要的“大义”。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徽州的剧作家的创作看出来。例如,明代徽州戏剧家汪廷讷著有传奇《环翠堂乐府》十八种,其中《三祝记》、《义烈记》、《天书记》均是礼义教化之作,宣扬忠孝节义的儒家伦理观。《三祝记》写北宋名臣范仲淹父子行义之“惠爱”,最终得天之眷顾,人之祝福:多福、多寿、多男子。剧本通过范氏父子的心怀慷慨,仗义疏财的一系列情节,表达了忠孝、友友、亲亲之义的人生道德观。《义烈记》写东汉义士孔文达行义而舍身的故事,表达“苟能全义,誓死不辞”的主题。《天书记》写战国时代孙膑和庞涓的故事,从反面表达庞涓行“不义”的下场。这些作品借历史人物表达作者的伦理观,刊行和演出无疑对徽州的伦理教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徽州剧作家郑之珍改编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卷本,此戏文100出,风靡整个明清的戏剧舞台,盛演不衰。此剧写目连历经千辛万苦去地狱救母,最终感化佛祖,救出母亲。剧中宣扬的是惩恶扬善,劝恶从善,因果报应的思想,也穿插了大量的宣传儒家的忠义伦理教化的思想。
总之,戏剧在徽州的盛行并非偶然,它在徽州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当宣传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对于徽州人人伦教化有重要的意义。礼学所宣扬的儒家之道、人伦之道,在戏剧中得到很好地体现,戏剧利用直观的艺术形式宣传礼教思想。徽州人就是从儒家的宗族观念出发,利用戏剧的艺术形式加强道德教育,这种“高台教化”加深宗族社会的团结,增强宗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使人们更自觉地守护他们的宗族信仰,这应该是“徽俗最喜观戏”的深层根源之一。
三、戏剧:徽州人精神慰藉的栖息地
戏剧作为教科书宣传礼教思想因而在徽州盛行只是一个方面,这也仅仅只是统治者的初衷,事实上,戏剧在徽州的盛行最主要的根源还是戏剧的审美功能为辛勤劳作的徽州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从主体的精神需求来说,支撑徽州文化的两大支柱是儒学和徽商,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和以徽商为中心的商业文化共同构成了徽州文化的内核。儒学宣扬的是社会人伦,国家集体,而不重视个人的精神生活,它的家天下的伦理体制在徽州深入人心,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礼学体系,统治了人们的精神思想,控制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徽商文化是以经济为轴心实用主义的商业文化形态,以盈利为目的,利益为先,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实用主义的影响。这两大文化支柱对于徽州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有不利的因素,它片面地强调了伦理性和实用性,把人们的精神始终束缚在纷繁的社会层面而忽略了个体心灵的精神自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人是现实的存在,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既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既要有社会性的一面,也要有个人性的一面;西方哲学家也把人的精神结构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人除了有伦理道德需求、实用知识的需求,还要有情感的需求;海德格尔提出人的“诗意的栖居”的命题,强调人快乐的生存模式,重视人个体精神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人的现实存在要保持精神的全面发展和平衡,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感性的存在,不仅有实用的需要,也要有精神的慰藉,不仅有社会伦理的需求,也有个人情感的渴望。徽州人面对森严的宗族伦理文化和赤裸裸的商业文化,精神审美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而戏剧艺术便是这种精神慰藉的主要形式。
从戏剧的审美功能来说,戏剧能给人以审美享受和快感。这一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讨论悲剧时早就指出了戏剧的这一功能,他在《诗学》第十四章中说:悲剧“只应当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既然这种快感是诗人通过模仿来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而产生的。”[6]28《诗学》第六章说:“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起卡他西斯作用。”[6]12亚理斯多德认为,悲剧能使人的情感得到宣泄,心灵得到净化,从而产生快感,这是因为悲剧能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通过这种怜悯和恐惧使心灵得到净化,从而产生快感。 这里的“卡他西斯作用”就是指陶冶、净化心灵的作用。他说的悲剧也是戏剧的一种样式,也就是说,戏剧也同样具有使人们产生情感上的愉悦,给人以快感,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净化,使人内心情感得到平衡。正是这样的戏剧审美功能,能够给徽州人的人伦之心和功利之心以外一份心灵的鸡汤,还原其一颗审美之心,在“义”与“利”和“美”之间(即在道德、利益和审美之间),保持一种良好的动态平衡。作为一种精神补偿,在枯燥的伦理生活和世俗的经济生活以及繁琐的日常生活之外,增加一种新鲜的审美生活,以促使人的精神全面发展,这才是明清时期徽州人对戏剧有如此大的兴趣的根本原因。
从戏剧发展的历程来说,中国古代对戏曲陶冶性情审美功能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与明代中期以后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戏剧“言情”本质观的确立是连在一起的。随着明代中期阳明心学的兴起以及晚明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思潮的勃兴,人们对戏剧的抒情性特质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哲学领域里,王阳明的心学提倡“吾心良知”的思想,“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心即理”,“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和“仁”、“义”、“孝”、“忠”等伦理道德是合在一起的。在心学思想主导下,王阳明倡导“性情”论,认为,“心统性情”,他说:“性,心之体,情,心之用”,“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也。”[7]王阳明强调了“情”的重要性,将“情”视作人心合有之存在,作为一种主观精神的存在。“情”的地位的提高,冲破了程朱理学“以理制情”樊篱。在文学领域,晚明思想家李贽提倡“童心说”,强调“真情论”,所谓童心,就是“一念之初心”,“赤子之心”, 并认为:天下之至文,都是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同时,认为戏剧同样是“天下之至文”,高度评价了《西厢》、《拜月》,并称之为“化工之作”。在公安三袁的推波助澜下,“情本体”成了文学艺术书写的对象,戏剧的“言情观”得以流行,汤显祖的言情戏剧观以及“为情而作”的《牡丹亭》的诞生,把戏剧的言情观推到了极致,经过沈璟这样的大戏剧家和徐渭等一些思想家、戏剧理论家的提倡,戏剧的言情观得以定型,戏剧终于获得了和诗文平等的地位。戏剧的言情本质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创作的角度讲,戏剧言情本质观要求戏剧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戏剧创作是作家心灵情感的表现;从欣赏的角度讲,肯定了戏剧的审美功能,观众通过看戏,获得审美的快感,精神的满足。
而中国的戏剧言情本质观形成之时,正是徽州戏剧活动日趋兴盛之时,这种观念对徽州人的戏剧观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表现在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给徽州人带来精神审美享受的自觉认识上。他们自觉地感受的是戏剧给人的快感和享受,可以先不考虑伦理的说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面引用的《歙纪》卷九《禁夜戏》所透露的信息:“看戏之人方且瞪目欢笑,不知其家已有窥其衣见其私者矣”。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从官府的角度来看,戏剧给民众带来的是一种危害,看戏人沉浸在欢笑中,竟然不知家中的财物被盗等,所以要禁戏;如果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徽州人为了来看戏赏戏,以致他们不惜破费平日辛苦劳作得来的微薄的薪酬,这充分说明徽州人对戏剧艺术的渴望和需求;如果从戏剧艺术给人带来精神审美享受来看,戏剧使徽州人“瞪目欢笑”,沉醉痴迷,竟然忘乎所以,不顾家中财物的安全。无论哪一方面都能清楚地说明,徽州人对戏剧的热爱与渴求,以致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同时也说明戏剧给人带来的精神享受如此之大,大有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感觉。
综上所述,戏剧在徽州的盛行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戏剧的讽喻教化和艺术审美感染力共同发挥张力的结果,也是徽州人心灵世界渴望慰藉和需要精神调节的结果。聪明的徽州人一方面重视传统的礼教文明,一方面又重视现实的实用理性,同时又利用艺术的审美净化功能作为精神调节剂,神奇地把儒家文化、商业文化、艺术文化圆通地融合起来,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奠定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明标本,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其中戏剧对徽州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和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
[1]金宁芬.明代戏曲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
[2]李复波,熊澄宇.南词叙录注释[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37.
[3]吴晟.明人笔记中的戏 曲史料[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4](明)潘之恒. 潘之恒曲话[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7.
[5]梁晓萍.中国古典戏曲品评观念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3.
[6][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7](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答汪石谭内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6.
On Drama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uizhou People
HONG Yong-wen
(Collegeofliterature,HuangshanUniversity,HuangShan,Anhui245041;CollegeofArts,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Huizhou people are fond of drama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spiritual life. It can be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drama has been acting as the textbook for ethical cultivation by promoting Confucian ethics and rites and it has helped Huizhou people to establish patriarchal ethical codes. Moreover, drama has been the spiritual sanctuary for Huizhou people, nurturing their soul and offering spiritual comfort and solace in the harsh reality. It is concluded drama has been beneficial to Huizhou people’s spiritual health and has occupied a great position in constructing Huizhou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drama; Huizhou people; drama as a means of social education; aesthetic enjoyment
2016-06-12
安徽省教育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传统戏曲的民间审美追求研究——以徽剧为例”(项目编号:sk2014A107)。
洪永稳(1962—),男,文学博士,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西美学,文论和艺术学。
J825
A
1671-444X(2016)05-0084-07
10.15958/j.cnki.gdxbysb.2016.0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