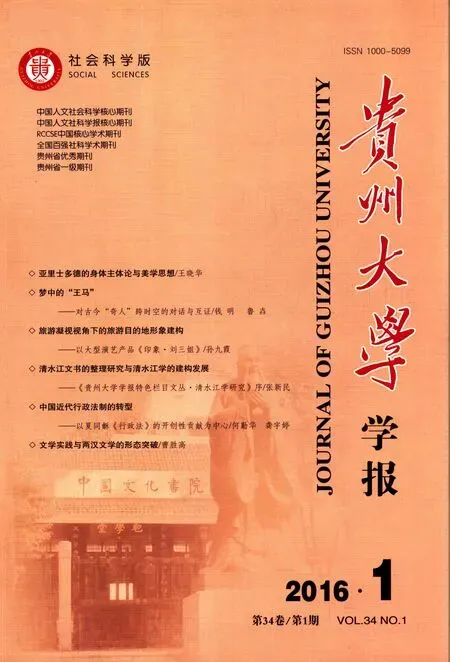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与苗族农耕文化
蒋欢宜
(铜仁学院 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院,贵州 铜仁 554300)
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与苗族农耕文化
蒋欢宜
(铜仁学院 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院,贵州铜仁554300)
摘要:苗族椎牛及巴岱经书《椎牛卷》蕴含了丰富的农耕文化信息。《椎牛卷》折射出了苗族以农立家的重农思想,以及以五谷神为核心的农业祭祀等农耕文化特色。《椎牛卷》所蕴含的生态平衡、绿色健康等农耕观念,对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苗族;《椎牛卷》;农耕文化
椎牛是湘西苗族最隆重、最主要的祭典之一,也是湘西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苗族传统的椎牛仪式不仅是一种信仰的表现形式,而且反映了湘西苗族人民慎终追远、怀念先祖、驱害避邪、祈福求祥、渴望人畜平安、五谷丰登的文化诉求。然而,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浪潮,当代苗族的椎牛活动被赋予了过多的表演成分,传统椎牛祭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幸得《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椎牛卷》的整理出版,为我们一窥苗族传统椎牛仪式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可能。
《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是民国时期苗族学者石启贵在湘西苗疆历时四年(1933—1937年)的调查实录。该书分为《椎牛卷》(上、中、下三册)《椎猪卷》《接龙卷》《祭日月神卷》《祭祀神辞汉译卷》《还傩愿卷》《文学卷》《习俗卷》8卷10分册。《椎牛卷》位于卷首,详实地记录了湘西苗族椎牛大典的全过程,内含“吃猪”“敬雷神”“敬谷神”“敬家祖”等23堂法事的科仪及巴岱唱辞,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湘西苗族的农耕生产生活状态及其文化诉求。
一、苗族农耕传统及巴岱经书《椎牛卷》
苗族有着悠久的农耕传统。苗族先民最早居住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据吴起《战国策》所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1]三苗是苗族先民,这一点江应梁在其所著的《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中早有论断:“古代的三苗即汉以后的南蛮,也便是今日之苗民。”[2]可见,苗族先民曾居住在今江汉、江淮平原及江西、两湖一带,是这片富饶的湖滨地区最早的开发者之一。湿润的气候、充沛的降雨、肥沃的土壤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苗族先民较早地进入了“火耕水褥,民食鱼稻”[3]的农耕社会,也获得了“苗族”即“在水田里种草的人”的称谓。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史前栽培水稻遗址有90多处,其中有70多处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南道县蛤蟆洞、澧县玉禅岩、湖南彭头山、广西桂林甄皮岩、浙江罗家角、余姚县河姆渡等地,均发现了距今几千甚至一万年前的稻谷遗存,有力地证实了居住在这一区域的苗族先民创造了农耕文明。
秦汉以后,苗族先民经历了长期残酷的战争及多次大规模的迁徙,最终散居于湘、黔、滇、川、桂等地偏远的山区。苗族农耕文化的表现形态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改变,逐渐由“以水稻栽培为主的、水旱兼营的稻作文化”转变为“以山地旱作为主”和“稻作梯田文化”[4]。无论形式如何嬗变,农耕文化始终是苗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是苗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耕文化影响着苗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其对苗族宗教的影响而言:其一,在时间上,苗族宗教活动紧扣农耕节律而行,在迎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保持完整的农业周期的前提下,依时间序列安排具体的宗教活动;其二,为了确保农业的丰收,在苗族宗教活动中往往祭拜多方神灵,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些充分体现在湘西苗族传统祭祀活动“椎牛”中。
椎牛俗称“跳鼓脏”“吃牛”,苗语称之为“农业”(nongx niex),是湘西苗族对大祖神“岭斗岭茄”(lioub doub lioub nqet)的祭祀活动,也是湘西苗族最大的原始宗教祭祀习俗。苗族椎牛与苗族农耕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红苗归流图》载:“农毕鼓脏:苗人于农毕冬月,跳鼓脏以祀神,亦蜡腊之遗意。冬乃藏谷之时,‘谷葬’与‘鼓脏’声相近,蛮语遂伪为‘鼓脏’云。”[5]242可见,苗族椎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秋收冬藏之喜而酬谢神灵,以确保来年丰产。椎牛仪式根据其组织者的不同,可分为个人私祭和合寨公祭两种形式:个人私祭主要是出于对久病不愈或求子不得的无奈,不得不叩许祖神。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多为每年的亥、子两月,即农历的十月、十一月;合寨公祭是多个苗寨联合举办的祭祖活动,多定于“农毕冬月或数年始一,亦于亥、子两月”。[5]242苗族椎牛紧扣农耕生产的各环节进行:或在秋收完毕,农闲之际,举行椎牛祭,酬谢神灵,庆祝丰收;或在新春之时,合寨椎牛,一来以牛之生机唤醒大地,复苏万物,二来提醒同族为春耕做好准备。
为了确保农耕丰产,苗族椎牛所祭祀的神灵较多。在苗族椎牛仪式的“吃猪”“祭雷神”“敬谷神”“祭日月神”“巡察酒”“祭家祖”“剪纸”“迎舅酒”“迎宾饭”“总叙椎牛”“祈福”“讲述椎牛古根”“栽秧播粟”“赎谷魂”“清扫屋”“小庭院敬酒”“套牛扯纸”“发梭镖椎牛”“倒牛”“交牛头”“合死牛”“归还桌凳”“敬牛肝饭”等23堂法事中,多次祈求、酬谢祖先神及雷神、谷神、日月神等自然神灵,企图集众神之力共同完成对大地丰产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对谷神和祖先神的祭祀尤为隆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苗族的万物有灵观念,同时也说明苗族人已经认识到农耕丰产是自然、社会、个体等多种因素整体有序综合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
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是对苗族椎牛的调查实录。该书不仅详细记载了椎牛仪式中每一堂法事巴岱的唱辞,而且进行了汉译和注解,是非常珍稀的苗族巴岱文化资料。“由于稻作农业的周期性特征及对节令、历法的需要,一些稻作民族产生了紧密对应于农事生产各阶段、各环节的神灵祭祀。”[6]苗族椎牛是为了适应农耕活动的周期性及节令而产生的,对应于秋收、冬藏的神灵祭祀活动。因此,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中蕴含了丰厚的农耕文化信息。
二、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所反映的农耕文化信息
1.以农立家的重农思想
农耕经济是湘西苗族主要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对湘西苗族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湘西苗族逐渐形成了顺天应命、守望田园、辛勤劳作、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其以农立家的重农思想愈加凸显。
湘西苗族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在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中描绘苗族农耕生活的唱辞比比皆是。比如,第一堂“农琶”(吃猪)第四节“扭业”(买牛许愿)有记:
一个银鼓拿来许愿,一面大锣拿来标良。做成五呈酒,做好五碗肉。一个银鼓,鼓敲犹如大钟响。一面大锣,锣响好像炸雷鸣。打到正月来到,打到二月来临。打到三月来到,打到四月来临。打到五月来到,打到六月来临。打到七月来到,水田稻穗像小鱼游玩,旱地粟穗如小鱼戏耍。稻粒饱满,粟粒密匝。鸟吃鸟破嘴,鸟啄鸟断牙。打到八月来到,主人收稻满屯,收粟满仓。打到九月来到,打到十月来临。一家大小,一屋老幼。记住曾许岭斗钱神的诺,记起曾许岭茄财神的愿。[7]34
在本堂第二十一节 “培酒先”(敬肉酒)中,对苗族的农耕生活有着更为细致、更为生动的描述:
正月来到,二月来临。带儿出屋,引孙出门。拿柴刀出屋,拿镰刀出门。到山上去砍树枝,到坡上去割茅草。年头好天气,开春好阳光。山上烧叶,山头烧草。回到家中,回到屋里。带儿出屋,引孙出门。牵水牛出屋,牵黄牛出门。牵水牛去犁田,牵黄牛去犁土。再回来引儿出屋,引孙出门。扛锄头出屋,抬撮箕出门。叶子刨往两边,葛藤刨往两处。二月来到,三月来临。从屋柱上取下粟把,从屋梁上取下粟种。去到九块熟地,去到十坵熟土。播撒一堆种子,长出千根千颗秧苗。播种一把种子,长出百株百颗禾苗。稻禾发的像山药,粟苗发的像芋头。稻禾长得茂密,粟秧长得茂盛。要让山头绿油油,要让山头青幽幽。四月来到,五月来临。六月来到,七月来临。田里稻穗出齐了,地里粟穗出全了。稻穗饱满沉甸甸,粟穗籽壮重沉沉。七月来到,九月来临。黄灿灿的稻谷满坝子,金灿灿的粟穗满山坡。引儿出屋,引孙出门。十块八块地,十丘八丘田。去到种粟的地里,去到种粟的田坝。稻神你们见了满坝收稻人莫害怕,粟神你们见了满坡收粟人莫惊慌。三五成群在山上收粟子,成群结队在田坝收稻谷。零散的稻穗不要掉,零散的粟穗不要丢。抬谷慢慢回家,抬粟悠悠回程。抬稻回来的人们像蚂蚁行亲,抬粟回来的人们像蚂蚁走戚。稻谷收满仓,粟子装满桶。主祭有余钱,主祭有剩米。[7]96-97
从上述唱辞,可以窥见,湘西苗族以农立家的重农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农耕生产是湘西苗族生活的主要部分,是立家之本。无论是农忙还是农闲,苗族的生活总是与农耕生产息息相关:二月砍柴除草,三月播撒谷种,四、五、六月精心呵护秧苗,七月硕果累累,八月喜获丰收,九月颗粒归仓,十月至正月择时祭祖酬神,祈求来年丰收。湘西苗族深谙以农立家之道,往往“带儿出屋,引孙出门”,举全家之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其二,湘西苗族对农作物的生长过程非常重视,这是以农立家的保障。从选种、下种、培育秧苗、除虫除草到收割无一不是殚精竭虑。播种之后时刻关注其长势:“播撒一堆种子,长出千根千颗秧苗。播种一把种子,长出百株百颗禾苗”,精心培育秧苗,使“稻禾发的像山药,粟苗发的像芋头。稻禾长得茂密,粟秧长得茂盛”,细心呵护稻穗、粟穗,使“稻穗饱满沉甸甸,粟穗籽壮重沉沉”“水田稻穗像小鱼游玩,旱地粟穗如小鱼戏耍”,最终迎来了“黄灿灿的稻谷满坝子,金灿灿的粟穗满山坡”“收稻满屯,收粟满仓”的丰收之喜。
2.以五谷神为核心的农业祭祀
一个农耕民族的生存与繁荣,主要依附在五谷粮棉的丰盛之上。在苗民的观念里,五谷神是主宰农业、决定年成丰欠的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与个人及村寨的富足息息相关,因此,苗民对五谷神的崇拜尤盛,对五谷神的祭祀仪式愈加隆重。苗族椎牛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耕丰产,祭祀目的性神灵——五谷神成为了椎牛仪式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它与对服务型神灵——祖先神、日月雷神等自然神灵的祭祀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椎牛祭祀体系。
在椎牛活动中,对五谷神的祭祀庄重而肃穆,第三堂“习滚农”(敬谷神)有详载:“太阳还没出山,月亮还没出岭。找来一张桌子祭稻神,得了一张桌子祭粟神。凉水洗净,雨水擦亮。桌子洗得干干净净,刷得光光亮亮。抬一张祭稻神的桌子,扛一张祭粟神的桌案。放在堂屋边,搁在中柱旁。拿盘来摆,取碗来放。拿得八个银碗,取得八个金碗。洗得干干净净,刷得亮亮光光。拿来覆在祭稻神桌四面,拿来覆在祭粟神桌四方。又做成八碗肉,做成八碗饭。敬送女稻神,敬给男粟神。还有三碗苏子,还有三碗芝麻。敬给先公先婆,敬送先父先母。全都给了,全都得了。”[7]118
综上,我们可以窥见:一方面,苗民对五谷神的祭祀极为重视,在祭祀器具、祭品等方面都有较为严苛的标准,要求祭台、祭具干干净净、亮亮光光,祭品丰盛;另一方面,五谷神的核心地位凸显。在“敬谷神”中,为了确保五谷神的关照,在邀请了五谷神之后,还要邀请祖先神前来协调沟通。祖先神在这场法事中起到辅助性作用,其祭品规格远不如五谷神。
在苗民的观念里,五谷神极易受到惊吓而逃跑,也容易被人带走,故而需要经常安抚。在举行浩大而嘈杂的椎牛大典之前,为避免五谷神被吓跑,或跟随某个富人跑掉,巴岱要先作法,即“习滚农”(敬谷神)对其进行安抚。但这种安抚有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尤其是在稻谷成熟之后,谷魂往往容易从生长的土地上流散,被人们带到各地。苗民深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认为生命体是灵与肉的结合,灵魂依附之上则生命体强大,灵魂离散则生命体衰微。丢失了谷魂,稻谷失去了生机,则农耕丰产无望,故而巴岱要继续作法,请“三千葵妈”和“三百奴妈”到各处赎谷魂:
三千葵妈赎稻魂粟魂,三百奴妈赎籼魂糯魂。你们要拿块圣布帮去赎,要拿块圣布帮去找。去家中狗窝赎稻魂,到屋坪猪圈赎粟魂……去到九块熟地,去到十丘熟土。到你们放扎笼的地方去赎,往你们放背笼场所去找。扎笼放满地边,背笼放满山岭……水牛群背去不仲(苗语音译,指牛栏门),去不仲赎转。黄牛群背往不嘴(苗语音译,指牛栏门),去不嘴赎回。斗古背去冬腊追补(苗语音译,指后山后岭),就往冬腊追补赎回。住刀背往冬牙追人(苗语音译,指后山后岭),去冬牙追人赎回。仲免(苗语音译,动物名)背去没戎(苗语音译,地名),就往没戎赎回。仲把(苗语音译,动物名)背去没把(苗语音译,地名),去没把赎回。翠鸟背去河边,就去河边赎回。穿山甲背去钻到土里,就钻往土里赎回。麻雀背到稻草堆去,就去稻草堆赎回。奴度(苗语音译,动物名)背去及秋加流(苗语音译,地名),就往及秋加流赎回。乌鸦背去国列茶树林,就去国列茶树林赎回。喜鹊背往国卡栗树林,就去国卡栗树林赎回。虫子背去竹里,就去竹里赎回。蜗牛背往树里,就往树里赎回。崖鼠背去石洞岩缝,就去石洞岩缝赎回。小鼠背去树洞竹筒,就往树洞竹筒赎回。蜘蛛背去园头,就去园头赎回。蜘蛛背去圃尾,就往圃尾赎回。到树叶里去赎,去竹叶里去找。担心洪水背去,到涨洪水地方去赎。洪水背去潭底,就去潭底赎回。洪水背去河滩,就去河滩赎回。洪水背去天涯海角,就往天涯海角赎回。洪水背去王季,就往王季那里赎回。赎得稻魂粟魂,赎得糯魂籼魂。[7]192-193
苗人认为,谷魂容易被狗、猪、牛、斗古、住刀、仲免、仲把、翠鸟、穿山甲、麻雀、奴度、乌鸦、喜鹊、虫子、蜗牛、崖鼠、小鼠、蜘蛛等飞禽走兽及洪水背走,要到狗窝、猪圈、九块熟地、十丘熟土、不仲、不嘴、冬腊、冬牙、没戎、没把、河边、土里、稻草堆、秋加流、列茶树林、国卡栗树林、竹里、石洞岩缝等地一一赎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谷魂从野外赎回,仍不能放松警惕,还“要赎盘中的魂,要赎碗里的魂。要赎砧板上的魂,要赎筷子上的魂。要赎瓢里的魂,要赎铲里的魂。要赎瓢里的魂,要赎铲里的魂”,[7]194直至“取得谷魂,抬谷魂徐徐上路,扛谷魂慢慢回程。抬回住所,抬回院坪”[7]195,才算大功告成。谷魂赎回,祭主来年丰收有望,“请兄来喝,邀弟来吃”[7]195共同庆祝。
三、苗族《椎牛卷》农耕观念的当代启示
苗族农耕文化是苗族先民在历史迁徙过程中,依靠集体的智慧,充分利用山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创造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及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苗族《椎牛卷》所蕴含的生态平衡、绿色健康等农耕观念不仅在过去为苗族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农业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也不断发挥着它的当代价值。
1.生态平衡的农耕观念
当前,产业化的农业生产在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土壤污染、地表水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综观国内外农业发展趋势,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以产业化的形式发展农业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应该只关注短期利益,以一网打尽的灭绝性方式攫取生物资源,而是要注重维护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链的延续,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苗族《椎牛卷》所体现的生态平衡农耕观念值得借鉴。
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并育等生态平衡的农耕观念。《椎牛卷》中对祖先神及五谷神、雷神、日月神等自然神灵的隆重祭祀,体现了天、地、人三方因素和谐相处的理念。在谷魂丢失之后,巴岱并没有凭借强力抢回谷魂,而是从狗、猪、牛、斗古、住刀、仲免、仲把、翠鸟、穿山甲、麻雀、奴度、乌鸦、喜鹊、虫子、蜗牛、崖鼠、小鼠、蜘蛛等飞禽走兽处一一赎回。对其他生物怀揣敬畏之心,万物并育理念可见一斑。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天、地、人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汲取苗族《椎牛卷》所蕴含的生态平衡观念,健全农业系统整体循环运行机制,改变以往人为切断中间链条、一味求快的错误做法。
2.绿色健康的农耕观念
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转基因等现代科技手段粉墨登场,剧毒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剂毫无限度地使用,一批批毒大米、毒蔬菜纷纷涌入市场,流向餐桌,严重危害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农药残留造成的土壤板结、地表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更是不容小觑,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被打破。苗族传统的农耕生产,遵循自然的理念,采取原生态的生产方式,利用无公害的生态有机肥,进行绿色健康生产,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中蕴含着绿色健康的农耕观念。在《椎牛卷》所记录的苗族农耕生活中几乎看不到“化学”的影子:播撒的种子是丰收之际精挑细选留下的,只待来年开春“从屋柱上取下”“从屋梁上取下”;给农作物施加的肥料是通过“山上烧叶,山头烧草”自制的有机肥。丰收之际,主要依靠人力,“三五成群在山上收粟子,成群结队在田坝收稻谷”,直至“稻谷收满仓,粟子装满桶”。这种绿色健康的农耕理念正是现代农业所亟须吸取的。
四、结语
苗族椎牛及巴岱经书《椎牛卷》与湘西苗族的农耕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苗族椎牛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祭祀大祖神“岭斗岭茄”、家祖及五谷神、雷神等自然神灵,求得庇佑,确保农耕丰产。苗族巴岱经书《椎牛卷》反映了湘西苗族独特的以农立家的重农思想,以及以五谷神为核心的农业祭祀等农耕文化信息,其所蕴含的生态平衡、绿色健康等农耕观念对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汉〕刘向.战国策·魏策[M].北京:国华书局,2006.
[2]江应梁.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J].边政公论,1940(4).2003.
[3]〔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李云峰,杨甫旺.苗族稻作与祭仪初探[J].贵州民族研究,2001(1).
[5]〔清〕阿琳.红苗归流图[M].伍新福,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8.
[6]黄泽,洪颖.南方稻作民族的农耕祭祀链及其演化[J].云南大学人文社科学报,2001(1).
[7]石启贵.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祭祀神辞汉译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钟昭会)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1-0093-05
作者简介:蒋欢宜(1988—),女,湖南安化人,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民族宗教文化。
收稿日期:2015-11-2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