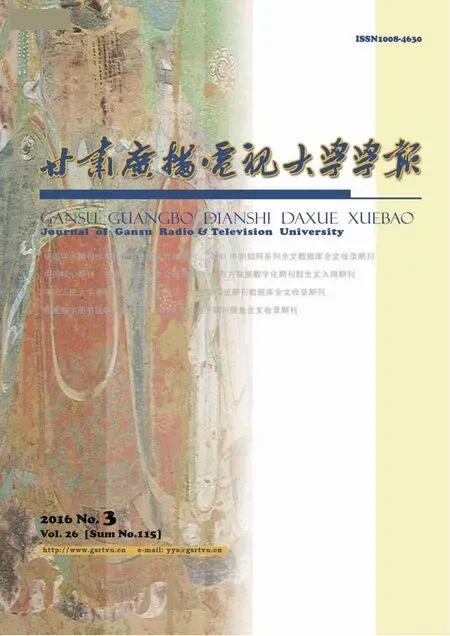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证据规则的非诉化面向
——读福盖德、盖拉德、戈德曼《国际商事仲裁》第四编第二章
张 建,严 黎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8)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证据规则的非诉化面向
——读福盖德、盖拉德、戈德曼《国际商事仲裁》第四编第二章
张建,严黎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100088)
[摘要]国际仲裁程序在证据出示、证据调取、证据采认等方面拥有不同于诉讼的非诉化面向。国际仲裁证据规则的协调化要求逐步弥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律冲突,由当事人与仲裁庭自行决定仲裁证据规则不仅是灵活性的体现,也是仲裁契约性、自治性特征的要求。福盖德、盖拉德、戈德曼合著的《国际商事仲裁》一书被奉为仲裁学界与实务界的经典论著,其在证据章节方面着墨颇多,揭示了国际仲裁程序中书证、证人证言、专家证据等证据规则的独特性。
[关键词]证据规则 ;国际仲裁 ;证人证言 ;专家意见
一、引言
国际商事仲裁由于程序简便、保密性强、易于跨国境执行和当事人享有极大自主权而在商事争议解决中越来越频繁地被采用,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的复杂性和近二十年经济与法律领域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企业与法律工作者接触、掌握、应用国际仲裁规则的难度。法国法学家福盖德、盖拉德、戈德曼合著的《国际商事仲裁》一书因其体系清晰、结构安排独到、理论与实务并重而著称。本书最初成书于1996年的法文版,因国际仲裁立法与实践的发展日新月异,萨维奇等人于1999年对此进行了修订并出版英文版,其中着重将20世纪末期国际仲裁界的最新成果予以纳入:在仲裁立法方面,1996年《英国仲裁法》、1998年《比利时仲裁法》、1999年《瑞典仲裁法》都体现了最新的制度优化成果;在仲裁规则方面,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机构仲裁规则》、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与《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将仲裁实务的前沿予以成文化;法院与仲裁庭不间断地拟定出与国际仲裁有关的裁判文书,同样彰显出仲裁业界的发展脉络与演进趋势。考虑到该著作的影响力,中信出版社于2004年在大陆地区发行了该书的英文影印版,为我国的涉外仲裁实务工作与仲裁法学界教学科研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纵览全书,作者以仲裁程序的推进为主线,将全面而细节的仲裁法律问题有逻辑地加以展开,涵盖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管辖权、仲裁员资格、派生请求权、仲裁法律适用、多方当事人仲裁、裁决的撤销与执行等关键论题。对实践工作者而言,该书所引述的例证涵盖面相当广泛,尤其对金融争议、投资争议、国际货物买卖争议、证券争议、房地产争议等皆有涉猎。在章节安排上,全书总共分六编,分别为:定义与渊源、仲裁协议、仲裁庭、仲裁程序、争议事实问题的法律适用和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各编下设章,例如仲裁程序编由程序问题的准据法、仲裁程序、临时与保全措施、仲裁裁决四章组成;各章下设节,例如仲裁程序章由仲裁程序的开始、仲裁程序的组成、仲裁文书与证据三节构成。考虑到全书信息量庞大,短期内消化各章节存在困难,本文甄选其中第四编第二章,就作者所论及的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规则非诉化问题进行讨论。
二、仲裁证据规则的法律冲突及其成因
从实在法出发,在各国现行有效的仲裁立法中,绝大多数皆将广泛的权力赋予仲裁当事人及仲裁庭,俾使其解决仲裁中可能产生的任何程序性问题。理论上,前者凸显仲裁的契约性本质,后者则尊重仲裁庭之仲裁权。以《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95条为例,对于在法国境内进行的国际仲裁,如果仲裁程序受法国法支配,则关于仲裁协议、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的规定仅在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前提下适用,且受制于第1493条(仲裁庭的组成)与第1494条(当事人的或辅助的仲裁员的决定程序问题的自由)。对仲裁员而言,除了当事人意图外,其仅受到国际程序性公共政策的限制,例如当事人平等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此类原则的违反将导致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
在此类仲裁制度自由化的国家所开展的仲裁程序,往往能吸收并兼而利用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不同证据规则的天然优势,而这类差异在法院诉讼程序中却依旧显而易见[1]689。首先,在英国与美国诉讼中所运用的审前证据开示程序(pre-trial discovery procedure)毫无疑问属于普通法系所独有的制度,其使得一方当事人有权获取对方当事人所持有的任何与争议事实认定相关且不受特免权所涵盖的文件,但不同法律体系下证据开示义务的范围各异,总体上美国法较英国法对当事人规定了更多的开示义务。大陆法系虽鲜有开示程序,但立法中却多见强制性的证据披露义务(compulsory disclosure of documents),这种强制披露通常以特定的方式加以实施。其次,由各方律师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也被视为在英美法系庭审中所形成的质证模式,大陆法系则以迥然有别的态度处理证人证言,往往要求将证人陈述转换为书面方式加以呈现,并由法院负责对证人的口头询问。
《国际商事仲裁》一书三大作者之一的伊曼纽尔·盖拉德(Emmanual Gaillard)对两大法系证据规则差异存在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在诉讼模式上,大陆法系的纠问式与英美法系的对抗制是造成证据规则表象冲突的内在成因;在制度衔接上,英美法系之所以更强调证人证言的口头询问程序,与其陪审团制度不可分离;在价值取向上,英美国家严格奉行当事人平等原则,赋予各方当事人就案件文书质证以及直接就证人证言进行审查是确保公平的重要路径。尽管全球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仲裁法的趋同化,但当各国律师或仲裁员参与国际仲裁时,其国内诉讼程序中证据规则的区别仍然不可避免地渗入国际仲裁中,以致于国际仲裁的证据规则形成了相当明显的交融色彩。总体而言,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书面审理阶段基本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上,英美律师不得不承认其在书面证据问题上受欧洲模式的主导,即从己方所掌握的所有书证材料中选取足以支撑己方请求者加以出示;而口头阶段则在较大程度上受英美法影响,即便在大陆法系国家开展的仲裁中,各方当事人也能够凭借普通法方法审查证人证言。这种潜在的交融无疑已经有了成文化的表达,国际律师协会所拟定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商事仲裁取证规则》(简称《IBA证据规则》)即为典例[2]。
三、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规则的特殊方面
(一)法律备忘录与证据的提交
与诉讼的法定性不同,仲裁中的证据提交事项主要依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进行,无论此类约定是否包含在审理范围书之内。此外,在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及当事人公平待遇等程序性公共政策的前提下,任何可适用的仲裁规则中有关证据的规定也发挥关键作用。最为常见的仲裁程序中,当事人通常需相继开展两套书面陈述的交换,即仲裁请求—仲裁反请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答辩—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辩驳所作的答辩(rejoinder)。在某些情形下,当事人能够在询问证人后甚至在最后一次听审后提交进一步的观察报告,即所谓“庭审后辩论意见”(post-hearing brief)。
仲裁当事人除了向仲裁庭提交证据外,还必须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且证据交换必须涵盖向仲裁庭所提交的全部事实与法律要素,仲裁庭也有义务确保这一环节的落实,否则会损及仲裁裁决的程序正当性。在诉讼中,案件所涉法律规范的内容通常属于免证事实,无需当事人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在仲裁中这种免证情形并不存在,尤其当国际仲裁的各方当事人来自不同国家,而一方提出某国内法律文本时,其不仅需向国际仲裁庭出示该法律,亦需就此向对方进行证据交换。盖拉德称,之所以存在此种特别要求,原因在于国际仲裁庭即使在某国开庭,其仍保留应有的国际性,除受之于仲裁地法的强制性规则制约外,其不属于任何一国的国内仲裁,因而对于仲裁庭而言所有的国内法皆为外国法,需遵循必要的外国法查明过程[1]692。不过,盖拉德所提出的无论在普通法国家抑或大陆法国家外国法皆被视为事实问题的主张似乎有失偏颇。英国将外国法定性为特种事实,适用外国法的问题必须由当事人提出,且须由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美国将外国法/外州法视为法律,纳入法官知法的范畴,尽管适用外国法仍需由当事人提出,但证明外国法的资料显然不及其他事实证据那般严格,将法官从形式主义的证据规则中解放出来,并影响了仲裁程序[3]。
当然,当事人在证据交换中向对方进行证据披露的义务受到种种限制。例如,商业秘密、专有技术等信息一旦为竞争对手方所知晓并利用,会剥夺证据提供方在商业竞争中应有的优势或致其受到巨额经济损失。考虑到这一点,部分仲裁证据规则设置了防御性制度,如2012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22条第3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就程序的保密性发布命令[4]。盖拉德从实务操作与利益衡量的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当事人可以请求包含此类信息的书证仅向仲裁庭提交而不进行证据交换,但这有可能被理解为对正当程序的违反并进而成为撤销裁决的理由,因而旨在依赖此类证据实现某种仲裁请求的当事人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出示并披露此类证据以证明待证事实,要么维护其保密性以避免商业信息外泄。考虑到仲裁证据规则的契约性,为了避免此种两难境地的出现,双方当事人可以特别约定此类证据仅向仲裁庭而不向另一当事方出示,通过此类约定各方明示或默示放弃了就此类证据进行陈述申辩及质证的权利,这是为国际仲裁的公共政策所允许的,仲裁庭也有权认可此类证据并据此裁断。在双方无此类约定时,一方根据保密性请求对某些证据仅披露给仲裁庭,而另一方请求强制性披露时,应由仲裁庭审查并决定请求不披露的理由是否成立。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由保密证据持有方向对方当事人有条件地披露此类证据,即以知晓此类书证的双方当事人、仲裁庭、仲裁机构签署保密协议为条件,签字方有义务将已披露的证据仅用于与仲裁紧密相关的目的,并在仲裁结束后归还所有原件及副本。然而此类保密协议的执行存在困难,一旦保密协议为公众所知晓,如何确定保密信息发布的责任方并非易事,保密证据披露方因此类信息外泄而遭受的损失也难以证明。
在厘定了需出示的证据材料的范围后,应当明确提交书面形式的证据材料的时限,该时限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在无特别协议时则由仲裁庭指定。与举证时限相关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逾期提交的证据的采认问题。通过观察国际商事仲裁的大量实践并与诉讼进行比较分析,盖拉德提出总体的趋势是仲裁中尽量避免对未遵循截止日期而在此后提交证据或其他文件的当事人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言外之意,仲裁庭如果认可了逾期提交证据的可采性并据此认定事实,并不当然导致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被不予执行。但仲裁庭允许此种逾期的底线是不得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及当事人平等原则,这意味着在采信一方提交的逾期证据的同时,仲裁庭亦有必要延长另一方的举证时限,以防止“证据突袭”状况的发生。
不过有必要指明,仲裁员没有义务背离当事人最初约定的举证期限,其接收逾期证据必须要求逾期方存在延误提交证据的法定事由,如不存在此类事由,仲裁庭当采取坚决的态度拒绝接收逾期证据及其他文件,当然这种逾期提交证据的事由合法与否在后续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中仍有可能被重新评定。尽管法院并不鼓励仲裁员持续延长举证期限,但必须承认,一方面仲裁员有义务尊重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提交证据证明足以支撑己方请求的待证事实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仲裁员有义务确保仲裁程序以合理的步骤推进并避免出乎意料的恶意拖延,为此,盖拉德例举了法国仲裁实践中的举措,即仲裁庭通过签发“证据关门命令”(ordonnance de cloture)设定某日期,在此日期之后一概不得提交新证据、新文件。当然,这种实践并未实质上影响逾期证据的效力,因为“证据关门命令”是可以推迟的,但其却促使举证期限正式化。
接下来,当事人既然负有在特定时限内出示证据的义务,那么谁有权力要求当事人举证呢?毫无疑问,这应当属于仲裁庭仲裁权的权限范围。具体而言,在证据事项方面,仲裁庭不仅有权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可采性、相关性、实质性和重要性加以确定,还有权命令证据持有方出示证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60条与1495条分别规定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中仲裁庭均有此项权限,该规定为仲裁当事人提供了据以实现普通法证据开示程序中文件披露义务的请求权基础[5]。国际上主流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也有类似规定,例如2015年《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2条第2款。不过,盖拉德经过实证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即便国际仲裁实践也存在协调化趋势,但总体上,仲裁地位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仲裁庭对强制披露问题仍旧秉持相对保守的态度,毕竟仲裁不同于诉讼,仲裁庭不具备法院的司法强制性,其所出具的命令(injunction)效力有限,且有赖于司法的协助与强制执行。另外,仲裁庭出具的要求出示证据的命令能否附加惩罚性的法律效果,在学理上与实践中对此争执已久,一方面仲裁庭不具有司法强制性,另一方面并不存在成文法禁止仲裁员这样做。对此,盖拉德做了独到的阐释,如果仲裁协议条款的起草足够宽泛而未排除这种惩罚性的选择,例如仲裁协议以“所有产生于本合同的争议”拟就,则国际商事仲裁员没有理由不对仲裁命令附加惩罚,法国法院在案例中支持这种仲裁中的惩罚性措施,荷兰与比利时仲裁立法也明确肯定了仲裁员的此项权限[1]697。
(二)证人证言
在商事仲裁程序中,是否采信并听取某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往往由仲裁庭根据案件事实的认定情况据以决定。在某些案件中,如果仲裁庭确信其根据书面证据已经足以知晓案件主要事实,即便某方当事人提出证人证言,仲裁庭也可以拒绝;在其他案件中,如果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清楚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可指令当事人提供证人。仲裁协议并不会因为证人证言的采信与否而被撤销,除非当事人之间在仲裁协议中明确限定了证人证言的采用。通常而言,在书面证据与证人证言之间,英美法系的仲裁庭更青睐后者,这与英美的诉讼程序相似,即证人证言被视为判定当事人陈述真实与否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只有法官或陪审团亲自听审证人并展开交叉询问后才能揭示真相,而大陆法系的律师对于每个案件中是否都需要证人出庭表示怀疑,反倒更信赖书面的成文化的证据。从现代化的国际仲裁庭对待证人证言的实践观察,大陆式的观念逐渐让位于英美式的观念,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得以凸显。
那么,究竟哪些主体具备成为国际商事仲裁中证人的资格?首先,仲裁当事人自身能否作为证人以陈述待证事实,英美法系允许此种实践,德国则完全拒绝,法国法规定当事人可以作为证人出现,但受到特殊规则的调整,而国际仲裁中如果当事人没有相反的另行约定,则由仲裁庭决定是否认可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的作证资格及其证明力。其次,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仲裁实践在处理针对技术问题的专家意见时也差异显著,前者由仲裁庭指定独立专家,后者则多见于由各方当事人所委任的专家,二者在国际仲裁中都有使用,但仲裁庭仍保留最终的认证权,其并不承担必须听取某种专家意见的义务。再次,在证据法领域,存在所谓“作证特免权”规则,即便证人具备作证的适合性和可被强迫作证性,该证人仍然有权以某种理由为依据而拒绝就特定案件事实作证,如配偶、近亲属特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职业与公务特权等。某些证人之所以拥有特免权,系出于保护法庭之外的关系、利益等外部政策考虑,同时意味着在发现案件事实之外还需就其他法益进行衡量[6]。
在审理证人证言的程序上,通常遵循如下步骤:(1)在开庭伊始,仲裁庭会向当事人设定提交证人姓名及其证明事项的截止期,此外仲裁庭自身也可在法院协助下传唤证人到庭。(2)当事人多被要求提供以书面形式呈现的证言,尽管这并不排除后续对证人进行口头审理的可能性,但却有助于使仲裁庭先就证人证言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初步评估,并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口头审理证人的持续期。(3)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当事人是否有权与出庭证人进行沟通以阐明自己希望达到何种证明目的。在普通法系这种行为并不违法,但其他法系则明令禁止并将其视为违背律师职业伦理的行径。国际仲裁中采取折衷手段,如果仲裁庭认可此种沟通,则必须确保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接触证人的机会。(4)部分仲裁程序受诉讼化影响,要求出庭证人履行宣誓程序。盖拉德则尤其提及,法国法中的仲裁院本质上仍属于私人而非公权力代表,其无权强行命令证人宣誓,但证人陈述前却会受到仲裁员对真实作证义务以及伪证刑事责任的提示。(5)在证人询问阶段,国际仲裁庭审中开始广泛吸收普通法系由双方当事人依次向证人盘问的通例,但仲裁庭仍然保留具体盘问方式的决定权,除非当事人另有特别约定。在证人询问阶段,仲裁庭起到关键的主持作用,其不仅决定了如何盘问及盘问主体,且必须确保证人询问的顺利进行并适时打断不必要的或与涉案事实无关的问题。有必要强调的是,在仲裁案件涉及多名证人时,仲裁庭会尽可能将不同证人分离,以防止串供或相互干扰他们对所涉事实的陈述。具体而言,当某证人出庭接受询问时,暂时不受询问的其他证人将退出开庭室,询问完毕但在同一开庭期内需接受后续询问的证人彼此之间也有必要隔离等。当有必要时,仲裁庭会安排对证人陈述进行录音或速录,以备后期调取或在当事人对证词内容质疑时使用。
(三)专家证据与现场勘验
无论在主要的常设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抑或在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而拟定的仲裁立法中,仲裁庭都可依职权主动或依当事人申请而指定某领域的专家就特定问题发表意见。专家费用由请求出示专家证据的当事人承担,且专家的职能仅限于就仲裁员自身所不熟悉的专业知识相关的问题作证,但无论仲裁员是否采信该意见他们始终拥有裁量权。国际仲裁中的专家证人须保持独立性与中立性,且仲裁庭并不从与当事方有业务往来或竞争关系的主体中传唤证人,否则将构成回避的法定事由。在作证专家确定后,由仲裁庭起草法律摘要(brief)划定需有证人回答的事实与法律问题的范围。在作证过程中,专家证人同意必须严格遵守正当程序原则与当事人平等原则,任何来自专家的通信必须同时向各方当事人寄送,任何会晤需在双方到场的前提下展开,专家证人与仲裁庭之间的沟通也需向全体当事方公开①。专家证人的职能通常在出具书面报告后结束,并由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上就该书面报告进行评论。但也有某些案件会由仲裁庭对专家证人进行口头询问,这也需在双方当事人皆到场的情况下进行。在例外情形下,仲裁庭在认为必要时也会命令现场勘验,这多见于建筑工程争议解决过程中双方就完工质量、施工进度等发生的纠纷[7]。
四、对国际仲裁证据规则协调化的展望
证据规则是仲裁制度的核心,但就形式和实质而言,仲裁证据却越来越具有诉讼证据的实质性特征,这一现象被学界定位为“仲裁证据诉讼化”,这深刻体现在举证、质证、认证等方面[8]。作为不同于诉讼的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仲裁对纠纷解决妥当性的追求优先于对法律适用严格性的要求。从本质上讲,仲裁的契约性与自治性决定了仲裁员并无义务严守诉讼中的证据法。仲裁证据的诉讼化不仅将英美法与大陆法在诉讼法律文化中的冲突引入仲裁,也对制度自身的吸引力带来影响;反之,仲裁证据制度的非诉化则是国际仲裁证据规则协调化的内在驱动力。通过阅读盖拉德对仲裁证据规则的见解,不难发现,尽管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存在种种冲突,但国际仲裁却试图扬长避短减少冲突,就如何处理证据事项的基本理念、方法、制度选择达成共识,形成相对确定的制度框架,充分展现仲裁的制度优势[9]。
反观中国内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于1995年9月1日施行以来已适用二十年,其中涉及仲裁证据的规定仅有4个条文,分别涉及举证责任、鉴定、仲裁机构收集证据的权利及证据保全。由于仲裁证据立法的缺位,在商事仲裁实践中,受诉讼化思维束缚,仲裁员适用或参照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现象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各仲裁机构也在仲裁规则中就证据事项加以处理,典型者莫过于2015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证据指引》(简称《证据指引》)。有必要提及的是,《证据指引》在前言中明确规定,其并非《仲裁规则》的组成部分,因而并不因当事人对仲裁机构或仲裁规则的选择而自动适用。相反,《证据指引》的适用依赖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这意味着非经当事人在具体案件中约定,《证据指引》并不适用。当事人有权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其中的证据规则进行增删和修改后,全部或部分地并入仲裁协议。就规则冲突的解决方面,《仲裁规则》与当事人约定适用的《证据指引》不一致时,仲裁庭应适用《证据指引》,相关证据事项皆未规定,当事人亦未做特别安排的,应由仲裁庭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加以处理。显然,《证据指引》充分把握了以《IBA证据规则》为代表的国际仲裁证据规则的主流趋势,对我国主体参与国际仲裁实践以及在我国国内开展的涉外仲裁活动提供了规范蓝本。
注释:
①对此,盖拉德在书中专门举例,在某国际仲裁案件的专家作证过程中,因某方当事人缺席,另一方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向法院提出异议,最终被法院撤销裁决,理由在于未出席的当事人在仲裁后就专家证据提出异议并不能像到场方一样有平等的机会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因而违反正当程序。(See CA Paris, Feb.6, 1997, Carter v. Alsthom, 1997 REV. ARB. 556, and P. Mayer’s note.转引自Fouchard, Gai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ITIC Publishing House, 2004:705.)
[参考文献]
[1]Fouchard, Gai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M].Beijing:CITIC Publishing House, 2004.
[2] The IBA Working Party.Commentary on the New IBA Rules of Evidence[J].Business Law International, 2000(2):16-17.
[3] 梁西,宋连斌.法学教育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63.
[4] 加里·B.博恩.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M].白麟,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67.
[5] 乔欣.仲裁权研究:仲裁程序公正与权利保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0.
[6] 卞建林.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126-127.
[7] 拉斯·休谩.瑞典仲裁法:实践和程序[M].顾华宁,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47.
[8] 宋朝武.仲裁证据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22-26.
[9] 崔起凡.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问题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29.
[责任编辑龚勋]
收稿日期:2016-02-20
基金项目:2015年度北京仲裁委员会科研基金项目“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规则的制定与适用问题研究”(YJPKC06)。
作者简介:张建(1991-),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私法与国际商事仲裁。
[中图分类号]D99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6)03-00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