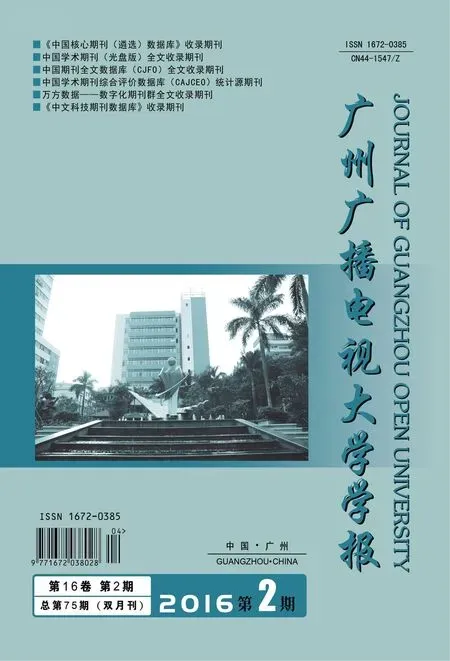论“物感”说之“感”
谭 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论“物感”说之“感”
谭鑫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在“物感”说中,“感”居于最关键的地位。“感”即感应,起源于《周易·咸卦》中的阴阳相感,在“物感”说中则表现为人(心)与物的双向互动。这一双向互动的运行过程是“感”的最精妙之处,经过发展与演变,最终臻于心物交融的境界。
关键词:物感;感;心物关系
“物感”说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滥觞于《礼记•乐记》,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成熟。它涉及文艺的发生、文艺活动的心理动机以及创作与鉴赏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
“物感”说的要素包括主体“人”(心)、客体“物”以及它们的沟通环节“感”,其中“感”是“物感”说的中心,是艺术生成的关键。对“物感”说之“感”进行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物感”说的认识。
一、“感”之释义及哲学基础
何谓“感”?《说文解字》解释道:“感,动人心也。从心,咸声。”“感”就是人心之动,是人受到外物触发,内心产生感情的过程。同时,《周易•临卦》初九“咸临”注云:“感,应也。”[1]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2]可以看出,“感”和“应”是密不可分的。在“物感”说中,“感”是外物对人心的感发,“应”是人心对外物的自然回应,有“感”必有“应”。因此,“感”就是感应,它不是外物对人心的单向作用,而是心与物的双向互动,是一种“交感”。
这种感应、交感的思想起源于《周易•咸卦》。其中的《彖辞》云:“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郑玄注曰:“咸,感也。艮为山。兑为泽。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故曰‘咸’也。”[3]提出天下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相感应而产生的,观察“感”这一现象,就可以了解天地万物的情况。黄寿祺对此说明道:“《咸》卦之主旨,从广义而看是普遍阐明事物‘感应’之道。”[4]也就是说,除了阴阳二气的感应之外,事物之间也普遍存在着感应。而万物相互感应的基础是什么?这就需要注意到“气”这一范畴。
阴阳二气相感应而产生万物,那么“阴阳二气便是构成万物最基本的原质”[5],“气”就成了万物共通的基础。《礼记•乐记》云:“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周易正义》中也说道:“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6]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互相感应,是因为它们共同禀有“气”,属于同类事物,能够“相动”、“共相感应”,这样它们之间的相互感应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人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自然也是由“气”组成的。《庄子•知北游》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阐明了人与万物相通的道理。正因如此,人才能与其他事物互相感应,这样就奠定了“物感”说的哲学基础。
二、“感”的主体与客体
(一)“感”的主体——人(心)与“性情”
“感”的主体是人,而人感物而动,是人性情中的本能欲望。人的性情使得人在受到外物感发后得以产生情感。
《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孔颖达疏云:“正义曰:‘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者。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人的天性是静的,但天性中有一种贪欲,形成了“动”的倾向,它受到外物的感发之后而动,就产生了“好恶”等情感。又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血气”、“心知”是人所具有的天性,但情感是多变的,受到不同事物的感发,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可见,“感”的发生,是有“性”及其特点作为基础的。
“性”是先天的,而“情”也是自然产生的。《礼记•礼运》云:“何为人情?喜、怒、哀、俱、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人的这七种感情,是不需学习就具有的本能。
关于“性”、“情”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可见,先有性而后有情,情是从性中产生的,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人的先天禀赋。《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是情的本体,情是性的表现形式。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性与情,好像一株树生长的部位。根的地方是性,由根伸长上去的枝干是情;部位不同,而本质则一。所以先秦诸子谈到性与情时,都是同质的东西。”[7]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性、情是一体的。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肯定了“情”是人心感物的基础。《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里的“七情”即喜、怒、哀、俱、爱、恶、欲,是对《礼记•礼运》说法的延续。人天生具有这七种情感,受到外物的刺激后就会发生感应,产生表达情感的冲动,进而吟唱出内心的情志,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钟嵘《诗品•序》也说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可见,物对人的感动,是通过“摇荡性情”来实现的。这些说法与《礼记•乐记》中“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的观点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正是先天的性情赋予了人以特殊的感物能力。如刘勰所说:“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四季景物的变化对动物尚且影响深远,而人拥有卓越超拔的明惠之心,更无法对其无动于衷了。
(二)“感”的客体——物
与“人”相对,“物”是“感”的客体。“物”这一范畴的含义,在历来对“物感”说的论述中,不断发生着演变。
《礼记•乐记》注重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提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即强调音乐感化民心,改变风气,治理社会的作用。因此,《乐记》中提出的“物”也是与政治、社会紧密相关的事件。“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这些伦理内容,都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社会、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都是感人之“物”,被表现在音乐之中。同时期的《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记》中的“物”就相当于这里的“事”,即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人们在生活中受到不同事件的感发,产生了不同的情感,进而用诗表达出来,成为了统治者观风俗、知得失的重要来源。
到了西晋陆机那里,“物”的含义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赋》中的“物”不再局限于社会政治生活层面,感发人心的往往是自然景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人们看到季节的变迁、草木的盛衰而心生感慨,思绪纷纭,在情感的驱使下创作出文学作品。陆机诗作《赴洛道中作》写道:“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萧瑟、凄凉、险恶的自然景象触动了作者的内心,使其产生悲凉、忧愁的情感,可以说对《文赋》中的“物”做了生动的诠释。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也说道: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很显然,这里的“物”指的是四季的不同景物。自然景物对人心的感发作用是很强的,人面对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物,会相应地产生“悦豫”、“郁陶”、“阴沉”、“矜肃”的情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感情产生之后,用相应的文辞表达出来就产生了文学作品。因此,这里的“物”的含义与《文赋》是相近的。
紧随其后的钟嵘完善了“物”的范畴。《诗品•序》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又云: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离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钟嵘一方面延续了陆机和刘勰的思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表明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景物对作家具有很强的感发作用;另一方面,“嘉会”、“离群”、“楚臣去境”、“骨横朔野”等社会事件和个人境遇也能“感荡心灵”。如写“嘉会”的《小雅•鹿鸣》,写“离群”的《小雅•采薇》,写“楚臣去境”的屈原诗作,写“骨横朔野”的曹操《蒿里行》,都是由不同事件触动心灵而创作出来的佳作。《诗品》“物感”说的“物”涵盖了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礼记•乐记》、《文赋》和《文心雕龙》相关论述的综合。
由“物”的两种不同含义,衍生出了两种不同的“物感”说。从景物的意义上来看,《文赋》、《文心雕龙》、《诗品》中的相关论述都构成了这一派的代表,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自然、山水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中的重要表现对象。从社会事件和个人境遇的意义上来看,从《礼记•乐记》开始,到《诗品》中的论述,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等,都表明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对作家的感发作用。
三、“感”的运行
发生在心、物之间的感应,是一种复杂、微妙的活动。“感”的结果不是心对物的简单再现,而是心与物交融而共同呈现的更为复杂、广阔,也更具诗意的状态。要了解“感”的妙处,就需要对“感”的运行状况进行探究。“感”最终达到心物互动、交融的理想状态,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一)从“物感”到“感物”
作为“物感”说的起源,《礼记•乐记》云: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孔颖达疏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于人心者,由人心动则音起。人心所以动者,外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者。”[8]由“使”字可以看出,人心动而产生情感,是由外物触发引起的。情感产生后,必然通过“声”表达出来,再经过文饰,配以乐器、舞蹈,“乐”就产生了。在这个过程中,“物”是居于第一位的,人心产生的情感是由外物触发而产生的结果,人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
在《文赋》开篇,陆机说道: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在这里,人因四季的变迁而感叹,因万物的盛衰而思绪纷纭,因“劲秋”的“落叶”而心生悲情,因“芳春”的“柔条”而感到喜悦。人的情感随着四季景物的变化而变化,面对不同的景象产生不同的情感。可以看出,“物”对人的情感的产生还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遵”、“瞻”两个词生动地展现了人主动接触自然,观察万物的状态,人不再处于“被感”的消极地位。与《礼记•乐记》中人处于被动地位不同,《文赋》开始重视人在心物感应中的主观能动性。
刘勰延续并深化了陆机的这一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人在心物感应中的主动地位。《文心雕龙•物色》说道: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
刘勰在这里提到的“感物”,与“物感”有所不同。虽然历来论者多认为“感物”即“物感”,二者为同一概念,可统归于“物感”说,但我们认为,“物”、“感”二字顺序上的调换,可以反映出观念上的演变和发展。“物感”可以理解为“物感人”,人处于受物感发的被动地位;而“感物”可以理解为“人感物”,即人主动地去与物相感。虽然感应都是发生在人与物之间,但这种不同反映了人在感应活动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刘勰所持的“感物”观,表明了他对人在心物感应中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和强调。这通过“联类”、“流连”、“沉吟”等词可以得到说明。“联类不穷”指的是人在感物后产生无穷的联想,进入一种思绪的活跃状态;“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指的是诗人在各种各样的景象中流连玩赏,在视觉听觉的范围内吟味体察。这些都强调了诗人主动融入周围物象,进行观察和体味,并主动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展开联想。《神思》篇也说道:“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里也是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主动去接触外物。
从“物感”到“感物”的演进,表现了诗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主体性的日益彰显,也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必然结果。
(二)从心物分离到双向互动、心物交融
上文提到,“感”是感应、交感,而“物感”和“感物”的共同进行就形成了心与物的双向互动。但这一观念直到刘勰那里才得到充分的认识,并达到了理论上的成熟。
《礼记•乐记》中的心物关系是从物到心的单向运作,并且心和物保持着相分离的关系。在《文赋》中,陆机虽然强调了人主动感物,但物仍然是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物象,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
而刘勰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出: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这里的“随物宛转”源于《庄子•天下》中的“椎拍輐断,与物宛转”,意为顺随旋转,与物推移变化,即人的主观情思要顺随客观事物的变化,符合其内在规律。“与心徘徊”则是与之相对的过程,即客观物象必须符合主观情思。对此,王元化先生解释道:“‘随物宛转’是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为主,而以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服从于客体。相反的,‘与心徘徊’却是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主体的作家的思想活动为主,而用主体去锻炼,去改造,去征服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两者“相互补充,相反而相成”[9]。可以看出,“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是相对进行、同时存在、密不可分的心物之间的双向互动。“随物宛转”是传统的“人心感于物”,是从物到心;“与心徘徊”则是从心到物,它不仅是人主动感物,并且还用主观情思对物进行改造,使客体之物成为心中之物。此时客观事物已经不是它本然的形态,而是附上了作家的主观情感。进而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物”,也是主客观融合后形成的与客观事物截然不同的意象。如罗宗强先生所说:“万物已不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进人心中,成了心中之物,加进了主观色彩,经过组合、改装,是在心中重新展开的物象。”[10]
《诠赋》篇也提出: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
这里的“情以物兴”相当于“随物宛转”,“物以情观”相当于“与心徘徊”。“‘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11]再如《神思》篇的“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它们都表明了心与物之间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外物深入并感动人心,使人产生相应的情感;另一方面,人心也会深入外物,把情感投赠到外物上,使其附上自己的情感,从而将其改造为心中之物。
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心与物就逐渐实现了融合。南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道:“《捣衣》清而彻,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愁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苟无感,何嗟何怨也!”这里的“内外相感”精辟地说明了“物感”是由内外因素、主客因素相互作用、融合形成的。如李白诗《独坐敬亭山》写道:“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一方面,在“鸟飞”、“云去”的处境下,沉稳的敬亭山触发了诗人的诗情,使诗人感觉如有一好友相互守护陪伴;另一方面,正是在诗人孤独情绪的投射下,敬亭山才从无情的自然事物变成了具有人格的诗歌意象。这首诗传诵千古而魅力不减的原因就在于外在景物和主观情感融为了一体,既有景的美丽,又有情之动人,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物色》篇“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一段话可谓生动绝妙地描绘了这种情景交融的境界。“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表现了人主动观察景物时情感活跃的状态;“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则写出了人与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像两个好友一样,“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十分能打动人心,这样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也是感人至深的。
刘永济先生对此论述颇为全面:“盖神物交融,亦有分别,有物来动情者焉,有情往感物者焉:物来动情者,情随物迁,彼物象之惨舒,即吾心之忧虞也,故曰‘随物宛转’;情往感物者,物因情变,以内心之悲乐,为外境之懽戚也,故曰‘与心徘徊’。……是以纯境固不足以谓文,纯情亦不足以称美,善为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双会之际矣。”[12]可以看出他对“情境交融,物我双会”的创作境界十分赞赏。《文心雕龙》体现出来的“心物交融”标志着对“物感”说对心物关系认识的成熟,也是“感”的理想状态。
四、结语
哲学中的“感”起源于《周易•咸卦》,意为感应、交感,进入到文论中就发展为“物感”说,即发生在主体“人”(心)与客体“物”之间的感应。“感”是“物感”说要素中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复杂、微妙的活动,是心与物的互动与交融。但“物感”说一开始并没有达到这种完善的状态,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和“物”范畴的不断完善,才在刘勰那里成熟,达到了心物交融的境界。这一境界成为文学家们在文学创作中不断追求的艺术境界,同时也对后世文论中的“意境”等理论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2][6][魏]王弼著.[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5,18,140.
[3][清]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314.
[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4.
[5]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0.
[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9:233.
[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51.
[9]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03.
[10]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321.
[11]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5):34.
[1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43.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6)02-0060-05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谭鑫,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生态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