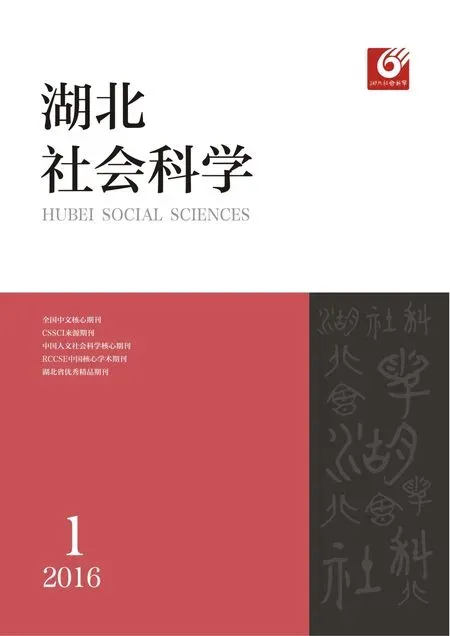论《庄子》中的生命之“化”
余静贵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庄子》中的生命之“化”
余静贵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化”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它也贯穿生命体验的始终。从生命构成来看,生命之“化”包括形化与心化。从时间维度来看,生命之“化”有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作为生命的发生之由,即“气化”;二是作为生命的现实存在,即“心化”;三是作为生命的理想境界,即“外化”。气作为生命的基础,气的变化表现为生命的状态;“外化”是对“心化”的超越。只有实现“外化而内不化”,才能成为得道的真人。
生命;气化;形化;外化;物化
“化”是《庄子》(本文所引《庄子》文本均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只标明其所在的篇目。)文本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出现共计92次,其中内篇28次,外篇45次,杂篇19次。鉴于外篇与杂篇对“化”的使用频率较高,故对“化”的研究涵盖《庄子》内篇、外篇与杂篇。从词性来看,全篇中的“化”有两种使用情况:名词与动词,都是“变化”的意思。从“化”的性质来划分,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物化。常表示万物的变化之意,如“无为而万物化”(《天地》)。第二,形化。“形”可以被包括在“物”中,这里仅指人之形而已,以区别于自然之物,如“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第三,心化。指人的内心发生的变化,泛指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寓言》)。甚至文本中没有出现“心”字,亦可指“心化”之意,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第四,外化。其概念稍显复杂,“化”的主体是人,具体讲是人之形,但这里的形化不同于第二点中的“形化”,第二种情况是形自化,而这里的形化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是人为,如“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第五,没有使用“化”字,但用“变”字代替“化”,概念基本相同。如“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
对《庄子》文本中“化”的分析可知,“物化”这个词出现频率多,其次是“形化”,“心化”没有连在一起使用,但描述“心化”思想的很多,“外化”在外篇中出现,但全篇描述其思想也非常多,“气化”以“气变”的形式出现。从它们的关系来看,“物化”既可以指自然之物的变化,也可指人的形体的变化。根据庄子的形、心生命构成来看,“形化”与“心化”都是指人的生命的变化。可见,“化”的理论内涵与庄子的生命观联系密切,即使“物化”是《庄子》文本中认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庄子处处讲“物化”、“齐物”等观点,但是,《庄子》文本的主旨还是落在了“人”上,因为人生、生命是《庄子》文本的思想主旨。
学界对庄子的生命哲学都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从“化”的角度来诠释庄子生命观的不多,而且多局限在“物化”的理论层面上,因为“物化”这个词在文本中出现频率高,且大多通过“物
化”这一层面来讲人对生死的超越。但是,庄子的生命体验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生命的变化有“形化”(属“物化”层次),还有“心化”。“心化”立足于现实,“形化”却是一种超越。无现实的生命存在,何来超越生命现实,这是由庄子哲学的矛盾性所决定的。可见,“物化”是生命之“化”的部分,但不能涵盖生命变化的全部。就生命的变化而言,除了“物化”层面的阐发,还有“气化”、“心化”与“外化”的生命体验过程,它们之间呈现交叉性与递进性。
一、气化:作为生命的发生之由
“气”在《庄子》文本中出现多达46次,是《庄子》文本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世间万物的基本组成。《则阳》曰:“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气有阴阳二气,为道所生,这受到了老子道气论的影响,因为庄子之道与老子之道基本相同。[1](p186)庄子和老子都认为阴阳二气的交合产生万物。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庄子说:“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气作为“道生一”的“一”,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存在于所有事物的根底之中。刘笑敢说:“天地万物、生命现象、精神活动都离不开气,气是万物存在变化的基础,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2](p136)气是生命的基本元素。
从气的性质来看,气是无,也是有。气是无,表现为虚的性质,“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这里的气,指一种空明的心灵境界。可见,在生命的本初阶段,人的心灵是无染于世俗的心性;气也是有,可以化为人形,形成人的生命,如《至乐》说:“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气是无,决定了它在宇宙大化过程中的包容性,也是生命可以超越现实的基础。气是有,说明它是实际存在物,是生命的起点,秉承着“无为”的道性孕育出世间的无穷生命。
气何以形成人的生命?庄子认为气的运动是生命形成的动因。《说文解字》云:“气,云气也。”而气的甲骨文图形也呈现出云气蒸腾上升的样子。可见,运动是“气”的一个重要特性。此外,气为道所规定,道的“周行而不殆”也决定了气的运动特性。气的运动会产生生命。《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的聚集与散开形成生命的生死状态。庄子还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生命的产生需要气的“交”、“和”,都是气的动势的表现。气的运动是生命变化的表现。当气的运动到达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或气化为形,或形复归于气,生死由是而生。
气化而为生命,反过来,生命的状态常常表现为气的变化。《庚桑楚》说:“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矣;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欲静则平气,欲神则顺心。”人在发怒的时候,脸上有怒气,人何以发怒,在于气的变化,所以庄子强调要“平气”,气不动,心则静。《人间世》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庄子认为因忧虑而产生“内热”是由于阴阳之气失调的结果,可见,庄子的生命气化论与中国传统中医也有一定的联系。人的生命状态的变化常表现为气的变化。当气的运动与变化到一定程度时,气就会完全散开来,人也就死了;气复归于运动,又会产生新的生命,庄子将这个过程称之为“物化”。《天道》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与死之不过是气的运动到一定程度时在人身体上的反应,一会儿化为动物之形,一会儿化为人形。可见,“物化”是“气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气化”是“物化”的本质所在。
二、心化:作为生命的现实存在
庄子认为生命由形与心构成,故生命的变化包括形化与心化。庄子常将“心”“形”对举用于议论,如“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人间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齐物论》)可见,心在内,形在外,心主而形从。心既可以是生理之心,也可以是精神之心,《庄子》文本中的心一般是后者,含有精神、思想之意。生命一旦由“气化”而生成,它就不断处于变化之中。《齐物论》曰:“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形化是自然的生命过程,属“物化”层次;心化虽不是“物化”,但也表现为生命本质之气的运动,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论及。形体发生了变化,心也跟着变化,那就是莫大的悲哀,这是庄子所不倡导的。
“心化”即人的内心感受所发生的变化。《庄子》文本中虽未标明“心化”这个词,但在《齐物论》与《寓言》中多处同时出现了“心”与“化”两个字。如在《寓言》中说:“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锺而不洎,吾心悲。’”曾子何以由“心乐”到“心悲”,都是由于父母的生死变化
让曾子的内心产生了情绪变化,由于不堪承受父母生命的“形化”,而产生了心情的过度悲伤。根据“气化”理论可以得知,心情的过度悲伤背后,是气的剧烈运动的表现。庄子在《庄子·杂篇》中还引用了蘧伯玉与孔子的故事来说明“心化”的产生过程。蘧伯玉与孔子都是“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这里的“化”都是指心态发生的变化。庄子不主张心化,认为要专一心志而顺万物之化。《田子方》曰:“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天地万物的变化是没有穷尽的,何以让心也变化无穷以逐物,这样只会让心为物所累、所伤。所以,面对万物的变化,人所能做的只有守住“中和”之气,保持虚静之心。
“心化”是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产生的内因,也是世间儒墨之争和生命残害不得保全的主要根源。《齐物论》曰:“喜怒哀乐,虑叹变,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庄子认为“心”乃是“喜怒哀乐,虑叹变,姚佚启态”产生的根源,故而庄子提出了“莫知其所萌”的反问,答案很明显:心。庄子还认为“心化”表现在人的“机心”的形成上。《天地》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求“机事”就是求知巧的过程,有知巧就会有“机心“,就会用其算计于人。《齐物论》曰:“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搆,日以心斗。”为了个人利益,人们勾心斗角,“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于是有“儒墨之是非”。庄子将这些是非争辩归结于“成心”的形成,“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齐物论》而当“成心”演变为“不肖之心”的时候,则可能产生恶的念端,如同发怒的野兽一般。“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于是并生心厉。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无论是“机心”、“成心”,还是“不肖之心”,都是“心化”的表现,它们的本真之心都是“常心”。
“常心”是人的本真之心,是没有被世俗浸染的心,也可称之为“真心”。《德充符》曰:“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庄子用“止水”来比喻“常心”,用“流水”来比喻“成心”。很显然,只有静止的水才可以清晰地照出自然界的样子,客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而“成心”是异化之心,有世俗成见的心,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对象。“常心”是没有被世俗浸染的纯净之心,就如同涉世未深的小孩一样,能够客观地感知自然世界。具有“常心”的人被称之为“童子”。《人间世》曰:“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童子长大而为成人,心也容易随之而发生变化,受到仁义礼乐的浸染,人就会显示出“擎跽曲拳”的样子,“童心”也就化为“成心”了。
庄子认为“知”是产生“心化”的重要因素。知通智,表现为知识或智慧之意。庄子认为知有大知与小知之分,“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大知是真知,是真人的智慧,为庄子所推崇,小知为世俗之知,会成为人逐物的工具,为庄子所严厉批判。《人间世》云:“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在庄子看来,知成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的工具和凶器,成了人心之化的主要“凶手”,人求知的目的无非就是满足一己之私利,故而庄子大力批判这种运用智慧的伎俩与手段。此外,知是人为,是违背人的自然之性情的,会伤身伤心。《骈拇》曰:“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小知不合自然之性情,故不可得。《在宥》曰:“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斤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求知会伤害人心,从而导致天下大乱。只有通过对道的体悟而形成的知才是大知、真知。求道即求自然之道,知“道”才能“明理”,才能使自己不为外物所伤害,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
此外,“仁义”也是“心化”产生的重要因素,为庄子所批判,因为它不符合人的自然之性情,是人为而非天为。《在宥》谓:“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庄子认为“仁义”禁锢人的行为,改变了人的自然性情,残害人的生命,最终导致天下衰败。
“仁义”与“巧知”都是浸染人心的罪魁祸首,都应予以否定。庄子主张无知无欲的生活,进入到一个纯粹经验的世界。[1](p200-202)“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列御寇》)只有去除人的心知,才能虚化自己的内心,才能顺任自己的性情而实现自由遨游。尽管否定一切人类文明回而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也是消极的,但庄子批判了现实,揭示了生命异化的本质原因。李泽厚说:“庄子的意义,并不在于这种‘回到自然去’的非现实的空喊和正面主张,而在于它们揭露了阶级社会的黑暗,描述了现实的苦难,倾诉了人间的不平,展示了强者的卑劣。”[3](p189)
尽管“心化”非自然之为,但从庄子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心化”含有一定的必然性。庄子不倡导杨朱的避世之游而选择游于“人间世”,就必然会“与物相刃相靡”;此外,求知乃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属性,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因素。所以,庄子所谓之“心化”有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属性。既然“心化”难以避免,而又要保留“常心”,只有通过不断的修心养性,将“异化”之心返还到“常心”,实现本真生命的回归。
三、外化:作为生命的理想境界
生命的构成为形与心,两者相依相存而构成了生命之化的主旋律。心向内,形向外,两个方向的共同作用构成生命的境界,如庄子所说回归到“古之人”的生命境界。何谓古人,《知北游》谓:“颜渊问乎仲尼曰:‘回尝闻诸夫子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回敢问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庄子认为生命的理想境界就是“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是生命境界的外在表现,“内不化”是生命境界的内在动因。
何谓“外化”?它意指人由形朝外而与物变化,以达到人与物的合一。就“外化”具体词义来看,成玄英疏:“外形随物。”[4](p765)林希逸曰:“应物而不累于外为外化。”[5](p598)陈鼓应译为:“顺物运转”[6](p628)可见,“外化”反映为人与物的一种关系,具体来讲就是形合于物。庄子主张“形”要“随物”、“应物”与“顺物”,或者说是“与物化者”(《知北游》)。《知北游》说:“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与物化者”也是表达形与物的关系,即“外化”。
可见,“外化”已经超越了“物化”的内涵,“物化”是物、形本身的自化,是“天”化,而“外化”是“人”化,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主动去顺物,乃至顺世。但是,《庄子》文本中的“天”是要高于“人”的,他反对“与人为徒”,而主张“与天为徒”,那么这里的“外化”是否与《庄子》的主旨存在矛盾?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外化”也是要通过不断训练和心性的养护,而最终将“人为”达到“天为”。庄子在下面的故事中就讲述了“人为”达“天为”过程,《达生》谓:“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手指动作随着所造的器物而变化,而根本不用思索。[7](p280)不思索等于“无心”,不用心思考而让“形”自觉与物化,这样就达到“人为”似“天为”了。
《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即通过人为的技艺练习,让人的形体顺任物的变化而变化。“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彼节者有閒,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庖丁解牛的故事讲述技道关系,但它更重要的是要传达一种生命观,即人在“人间世”的生存境界。庖丁讲“解牛”,其实就是讲人生,解牛之道等于生存之道。牛的骨骼纹理就好比世间的是非利益关系,众人刚开始面对世间的是是非非往往会显得不知所措,“与物相刃相靡”,人就会被“物”所伤,这就好比庖丁三年前解牛的情形,刀刃变钝,每月乃至每年换刀。若能领会“人间世”的胫骨脉络,展开自己的生命而能顺任自然,则达到了庖丁三年之后解牛的境界:“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如此人的生命没有损害而得以全生,而且能够生存于“人间世”以至于“游刃有余”,这就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这也是一种至高的生命境界。
“外化”形于外,是生命境界的外在表现;“内不化”形于内,是生命境界的内在动因。就“内不化”而言,成玄英疏:“内心凝静。”[4](p765)“内不化”即心不发生变化,与“一不化者也”是同一个意思,都强调心静的意思。虚静之心也即“常心”。然而,生命的现实是“常心”已经化为“成心”,必先要得到“常心”才可以守得住虚静之心。《德充符》谓:“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凭借世俗知巧不可能化“心”为“常心”,这里的“知”是合于自然之道的“真知”。《大宗师》曰:“且
有真人而后又真知。”要成为真人,那就需要闻道,这需要一个不断忘天下、忘物、忘我的过程。《大宗师》曰:“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成玄英疏:外,遗忘也。[4](p253)通过不断忘记心外之物,如同老子为道的“损之又损”,才能彻底摆脱对心的束缚,而入于不死不生的境界。闻道的过程中,真知也慢慢显现,用符合于自然之道的真知寻求自己内心的觉醒,再用自己心识求得符合生命本性的“常心”。
“忘”是闻道过程中的关键,旨在忘记一切心外之物,其中主要有忘“我”与忘“知”。形体对世界的欲望和巧知对人本性的伤害都是“心化”产生的主要因素。《大宗师》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肢体就是人之形,聪明就是人之知,忘记两者而合于大道,这就是“坐忘”。“坐忘”是要通过否定来肯定精神的自由。陈鼓应说:“‘忘’并不只是否定意义,它兼有正反两面的义涵,其逆向作用在于破除束缚,摆脱困境;其正向作用在于使精神超越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6](p57)人何以能忘掉一切,庄子由外及内,对内心展开充分的自省。忘记一切就是不断虚化自己内心的过程,庄子称之为“心斋”。《人间世》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郭象注:“虚此心则至道集于怀也。”[5](p138)内心充满了欲望与知巧,何以能容得下的道的介入。所以,要排除心内之物,而呈现出中空的状态,才能“虚而待物”而不为物伤,才能集道。可见,“心斋”与“坐忘”本质上是一个层面的意思,意在排除世俗杂念,目的都是要让生命回归到“常心”的状态。
“外化”针对于形,“内不化”针对于心,两者基本可反映为形与心的一种关系。若有心而无形,则难以感受生命的现实存在;若有形而无心,则生命也不能长久。所以说,“外化”是“内不化”的外在表现,“内不化”是“外化”的前提基础。“内不化”在先,“外化”在后。钟泰说:“言外化而必言内不化者,外化所以顺物,内不化者,灵明以为之主也。若夫失其灵明,则逐物而迁,将迎之心起,于物反昧其轻重本末之序,以为顺物,而实与物之本则相远,如人每盛言客观,而卒则师心自用者……由是论之,则必有一不化者在,而后可与物化。”[8](p511)无论是生命的现实存在,还是对生命现实的超越,庄子都将“心”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在生命的形、心二元构成中,心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此外,庄子对“心”的突出可能受到“知”的影响,因为“知”是人为的、不符合自然本性的,它是引起“心化”的重要因素。
综上分析可知,庄子的生命之“化”是一个以时间为维度而展开的生命历程。“化”是永恒的,不为人的意念所止息;“化”是绝对的,没有目的的,它只为显现自身而存在。生命之“化”有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气化、心化与外化。气化是生命的基础,心化是生命的现实,外化是生命的境界。心是生命之“化”中的一个重要基点。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通过心的作用而展开理性思考。所以庄子将“心”在生命的展开中凸显出来,心的作用具有多面性。心是人遭受苦难的根源,但心又具有自省功能,人通过心灵的意识作用可以实现对生命现实的超越,从而能够保身全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外化”境界。庄子的生命之“化”不是单一的“物化”概念,因为人的生命构成有形与心,形化属“物化”层次,而心化是形而上的层次。生命之“化”也并非繁冗难以理解,因为生命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气的运动,气贯穿了生命变化的始终。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2]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5]崔大华.庄子歧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曹础基.庄子[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8]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高思新
B223.5
A
1003-8477(2016)-01-0110-05
余静贵(1982—),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北长江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