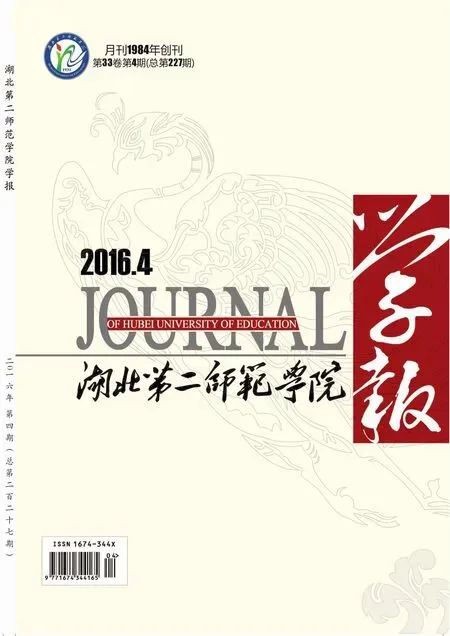后现代形式下的后殖民叙述:解读库切的《凶年纪事》
朱晓媛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500)
后现代形式下的后殖民叙述:解读库切的《凶年纪事》
朱晓媛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500)
摘要:库切的小说《凶年纪事》植根于霸权与边缘文化语境,颠覆现行叙事模式,将文本写作立场置于南非后殖民语境中,充分借用后现代叙事策略揭露了历史写作中的权力结构,从而体现了对历史与殖民话语权威的反抗,最终形成了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颠覆。因而,《凶年纪事》所体现的是在后现代形式影响下的后殖民叙述,是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兼收并蓄。
关键词:后现代; 后殖民; 话语权威; 叙述结构
西方文化思想史就是从一个“中心主义”走向另一个“中心主义”的历史,后现代主义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也强调其自身的“无中心、不确定、碎片化”等特征。而后殖民理论中所谓的颠覆中心,并非企图让“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或者说让“边缘”中心化或者“中心”边缘化,而是要通过颠覆的过程达到让边缘与中心恢复对话与交流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正是后殖民“边缘”话语颠覆与“中心”解构的结果。戏仿解构、文体游戏、混杂身份意识等都是对西方主流价值的背叛。库切《凶年纪事》文本中,后现代的痕迹显而易见。整部小说在叙述结构上结合了多重视角,穿插政论和随感,结合多人的叙事视角,以“边缘”的声音来消解“中心”的话语权威。
库切的作品立足边缘,却用“边缘”发出的声音对抗欧洲文化霸权,通过不断的自我质疑、自我发现、自我揭露、自我否定,逐渐腐蚀自我的文化成见,最终达到拆解中心的目的[1]11。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形式的《凶年纪事》,文本语言的结构性关系和拆解与南非后殖民语境中的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在库切的笔下,后现代主义的外在形式被结合进了立意于把殖民者的殖民策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后殖民叙述[1]15。
一、库切混杂性身份和边缘书写
库切生于南非开普敦,这是殖民主义权力结构和种族歧视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英裔和荷裔争夺南非统治权的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直至南非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而库切却是17世纪迁居南非的荷兰裔移民的后代,他从出生到成长都在这种种族争夺的影响之下。
库切因自身的流散经历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其流散主题在遭遇“他者”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感,而恰恰是通过小说,为他自己的流散身份找到了一条合理的认同之路。库切获得文学和数学学位后,而数年后又辗转到美国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因参加反越战游行最终未获得美国绿卡的库切再次回到南非,任教于开普敦大学。库切作为荷裔,处于欧洲殖民霸权权力的边缘地带,位处政治“边缘”的他,却开始以文学作品为武器与霸权作斗争,通过坚韧地对人性自由的追寻,成功立足“边缘”向“中心”发出呐喊,在殖民过程的混杂状态中寻找到一个新的身份。库切内心对身份的寻求并没有让库切停止他的流散生涯,精神的流亡一直在继续,他自己“天生就是异乡人,一辈子都在做异乡客”。
像众多流散作家一样,库切选择了边缘的言说位置,边缘的位置使得库切的创作从多方面呈现出与文化权威的对抗。《分离的土地:当代南非小说读本》中体现了库切对南非文字审查制度的抗争,《论文字审查制度》探讨了南非种族制度下文字审查制度的政治性,库切认为作家“写的书在南非被禁是一种荣誉”。《等待野蛮人》和《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中对监禁、管制和酷刑的描写和关注正体现了后殖民时代下,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者的反抗,边缘政治对于“中心”的消解。在《凶年纪事》中,库切指出人类心甘情愿地被国家统治,这种意愿根深蒂固到本性中都失去了对自由的热爱。
库切的小说世界总是一个叙述者和其他语言的建构物,由于语言的流动性,这一世界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因而丧失其权威性,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他在作品中对种种结构性关系的关注、源自身份的危机意识、从边缘对中心进行的颠覆、对文化权威的挑战、对种种形式的暴力的反复描写,都是将他的文本放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
二、多声部叙述结构对殖民话语权威的解构
《凶年纪事》由《危言》和《随札》两部分组成,上栏主要是争论和随感,可视为身处霸权中心人民的声音,他们自由的讨论着国家、民主、社会、艺术、文学、生活等等,他们的发声是自由的,无拘束的,他们在《危言》中通过自己的声音抨击国家政府的不堪行为,旨在维护他们的权益。在《论国家起源中》就有这样的书写:“公民的生死并非国家关心之事。国家关注的是公民生存与死亡的记录”[3]5。此外,9·11事件后,反恐新安全法不仅在英美两国通过,澳大利亚也坚决追随了英美两国的脚步,而这一立法导致了很多公民权利被无限期中止,而历经了到英国、美国寻找身份认同的库切,深知英美两国的政治、民主、社会现状,通过《危言》发声,暗指澳大利亚与英美越来越相似,无形中透露出对澳政局的失望。库切在《随扎》部分的《政治的喧嚣与骚动》披露,移居澳大利亚后,他受邀去堪培拉国家图书馆朗读他的作品,库切饶有深意的选择了《等待野蛮人》。新法案实行不久后的澳大利亚陷入政治恐慌之中,《等待野蛮人》中详尽描述的虐待方式竟然与2004年以来美军在巴格达市郊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湾拘留营虐囚的照片惊人相似。这些都是从霸权中心发出的呐喊[3]5。
《危言》意指“言出而身危”,库切笔下的主人公与库切同名,却又描述为一个像库切又不是库切的人。库切早在美国时因参加反越战游行而未获得绿卡,深知当局霸权的严格管控,因而在《凶年纪事》中使用三栏叙述,其实是想将作者之言与主人公之言适当隔离,意用主人公之言来表达作者的想法,却又将作者表现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用来自霸权中心的声音颠覆当局的话语权威。
而在二三栏中,老C先生被塑造为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安雅被塑造成一个文化程度低、在家待业的女子,但在受聘为C先生整理手稿时,她也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创作。安雅来自菲律宾,却从未在菲律宾呆过,她的父亲是一个澳大利亚外交官,在马尼拉时娶了鸡尾酒会上遇见的女子,安雅曾在一家妓院做迎宾员,与男友未婚同居,从作者对主人公身份的刻意安排,无疑是将安雅描绘成一个来自于边缘的被殖民地区的,却又不得不在殖民环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子。身处“边缘”、社会底层的她,拥有姣好的容貌,曼妙的身材,却没接受过多少教育,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帮C先生记录书稿时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艾伦让她窥视C先生财产时巧妙推脱,在艾伦对C先生实行远程监控,企图挪用C先生存款时与他果断分手。这种种描述将安雅构建成一个充满道德感和正义感的女主公。安雅与艾伦的分手也反映了如果新政权无视道德正义、法律规则,最终会自食恶果。这其实也是来自“边缘”的声音反抗“霸权”的话语权威。
三、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后殖民文学形态
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着共同的目标:拒绝帝国话语,反对中心——边缘等级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殖民理论因后现代理论而壮大,扩大了后殖民写作的非同质内涵,而后现代文化策略也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下增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方向。
库切的写作深受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在《关于写作的笔记》的论文中,库切以“书写”为例分析了现代语言学提出的三种声音:主动的、中间的和被动的[1]13。在《凶年纪事》中,主动的声音来源于C先生,他纵观国际政治趋势,主动发生抨击暴力的国家机器进行野蛮的统治。安雅的发声既可视为主动,也可视为被动。安雅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C先生的政论大多不随意发表意见,但涉及到她本人有所体会与了解的,她便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主动发声的体现。但相对于C先生,安雅和艾伦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发声是来自底层的声音,来自边缘的声音。中间的发声来自于作者本人,在《凶年纪事》中,库切是C先生,却又不是C先生。作者既可以依附于C先生的政论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态度,也可从老C先生的生活中跳出来,充分发挥作家的观潜能力。
后现代主义是欧美发达国家文化向所谓“边缘”的输出和辐射,后现代具有同质化的文化趋向,它试图以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模式去涵盖、阐释全球不同地域的文化。而后殖民写作则是“边缘”向西方文化中心的运动,是一种反同质化倾向的文化选择,它虽以颠覆西方文化霸权为主要目标,但并不是要以形成的东方话语去取代西方话语,而是主张文化的协商,弘扬多元性[1]17。库切的写作立足于对第三世界后殖民政治的关注,当后现代主义以后殖民文化情境的方式被改写时,二者的兼收并蓄、不可分割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结语
在《凶年纪事》中,库切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直接描述殖民主义的罪恶面貌,而是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叙事策略,从不同的叙事视角颠覆传统现实小说,从而揭露历史写作中的权力结构,最终达到用来自边缘的声音反抗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目的。作为一个在殖民势力影响下的作家,库切敢于立足边缘,为被殖民者争夺话语权,将小说的空间维度无限扩展,从后殖民的发声到后现代的多重叙述,以其独特叙述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后殖民后现代兼收并蓄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高文慧. 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M].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08.
[2]朱晓媛.复调:从音乐到小说——解读库切《凶年纪事》的音乐结构[J].云红河学院学报,2014,(3).
[3]库切著,文敏译.凶年纪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2,6.
[4]许志强.老年C先生与“小故事”写作——读库切新作《凶年纪事》[J].中国图书评论,2011.
责任编辑:陈君丹
Post-colonial Narration Under the Form of Post-modernism—The Interpretaion ofDiaryofaBadYear
ZHU Xiao-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 650500, China)
Abstract:J.M. Coetzee’s novel Diary of a Bad Year roots in the context of hegemony and marginal culture and greatly deconstructs the current narrative mode of traditional novels. In addition, the writing context of the novel is based on South Africa post-colonalism, in which the post-modernism narration has been utilized to expose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resistance to historical and colonial discourse authority has been made, finally contributing to the subversion of imperialism Cultural hegemony. In a word, the all-embracing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alism have been exposed well in Diary of a Bad Year.
Key words:post-colonalism; post-modernism; authority of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收稿日期:2016-02-20
作者简介:朱晓媛(1988-),女,云南宣威人,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后殖民文学与后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6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6)04-0005-03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藻海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