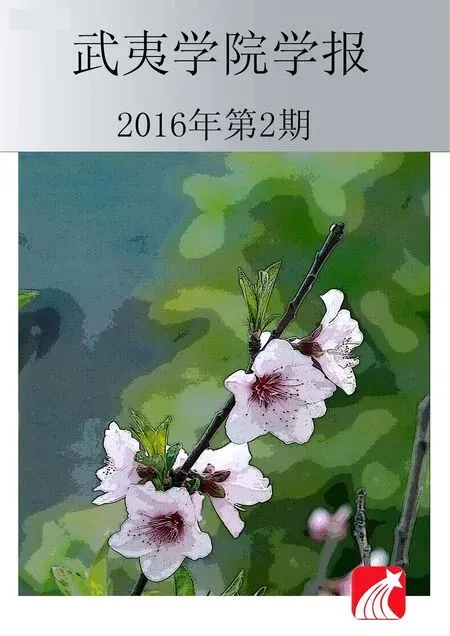“郁结”下的“求索”
——叶维廉“文化模子”理论
陆志胜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郁结”下的“求索”
——叶维廉“文化模子”理论
陆志胜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摘要:针对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文化主体性丧失的危机,叶维廉先生提出的“文化模子”理论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否决和消解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中心主义,通过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来促进彼此间的“互照互识”;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下,西方工业文化对非西方国家民族意识弱化和文化独特性破坏的危害以及其中潜藏的某种权力关系,在方法论的层面,为我们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和重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指导。
关键词:郁结;文化模子;互照互识
近代以来,我们从被动到主动,自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到形而上的制度层面,向着西方学习,全面地推进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然而,当我们为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辉煌而沉醉,并逐渐习惯于把西方文明的标准拿来作为衡量我们自身的标准时,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由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在无意识中代入为这个体系下被言说的乃至是被同化的“他者”。于是,在中西文明的对话中,我们处于文化“失语”的状态,又时刻面临着丧失文化主体性的严重危机。如何在现代性话语中重塑中国的文化主体?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是如何建构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何从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拯救中国主体?[1]这些追问就如同“魔咒”一般,是凝结在当代中国文化自觉者们身上的无法摆脱的“郁结”,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批评理论具体运用的问题上,为了避免造成对彼此的文化本源的曲解,更好地接近彼此的文化本源,实现中西文化的互照互识,叶维廉先生提出了“文化模子”理论。就如叶维廉先生在原文中所举的寓言[2]:
话说,从前在水底里住着一只青蛙和一条鱼,他们常常一起泳耍,成为好友。有一天,青蛙无意中跳出水面,在陆地上游了一整天,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如人啦,鸟啦,车啦,不一而足。他看得开心死了,便决意返回水里,向他的好友鱼报告一切。他看见了鱼便说,陆地的世界精彩极了,有人,身穿衣服,头带帽子,手握拐杖,足履鞋子;此时,在鱼的脑海中便出现了一条鱼,身穿衣服,头戴帽子,翅夹手杖,鞋子则吊在下身的尾翅上。青蛙又说,有鸟,可展翼在空中飞翔;此时,在鱼的脑子便出现了一条腾空展翼而飞的鱼。青蛙又说,有车,带着四个轮子滚动前行;此时,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带着四个轮子的鱼。
在他看来,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别,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模子,所以在跨文化研究中,就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对其他文化进行评价,而应该站在该文化本身的立场上对其予以评价。同理,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所以有着不同的文化模子,对中西文化的研究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模子出发,而不能单纯地以西方的文化模子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恰恰是西方文化逐渐占据话语权,逐渐成为唯一标准,中国文化处于“失语”状态。因此,这一理论对我们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和重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具有着启发性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否决和消解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中心主义,通过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彼此间的“互照互识”;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下,西方工业文化对非西方国家民族意识弱化和文化独特性破坏的危害以及其中潜藏的某种权力关系,在方法论的层面,为我们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和重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指导。
一、无法摆脱的“郁结”——文化主体性丧失的危机
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全盘西化”的做法造成了我们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中处于“失语”状态,从而使我们始终处于由西方文化话语为主导的全球话语体系的控制之下。中国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根源性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断层”更是使我们面临着文化主体性丧失的危机,我们正在沦为“被言说的他者”乃至是“被同化的他者”。
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从一开始便是与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辩证下的蜕变与转化,其过程复杂多面,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传统中固有的统治制度和与之抗衡具解放性的自然思想,一方面对西方意识形态中背后深藏着另一种统治形式的解放思想(科学与民主)做出诡奇多样有意识、无意识的迎拒……是我一度说过的中国人不得不承受的“郁结”。[3]
这份“郁结”,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沦为“被言说的他者”乃至“被同化的他者”的文化危机时,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的种种非理性做法和错误的反思,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诉求。它饱含着以叶维廉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自觉者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的不尽忧郁,对中国文化面临文化主体性丧失危机的无尽焦虑和忧郁。叶维廉以学者、游子、翻译家及诗人等多重身份一直与他古老的母语文化传统、他所处的时代、他现在所生活的西方文化区域、他母语文化区域以及这个时代、这些区域中不断发生的文学和文化事件血脉相连的故事,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4]而透过叶维廉先生多重的身份转换的经历,将能使我们更深刻、直观地感受这份化不开的“郁结”。
(一)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无尽忧郁
叶维廉先生出生的时候正值日本侵略者肆虐中国,他曾这样描述童年:
在无尽的渴望,无尽的饥饿里,在天一样大地一样厚的长长的孤独里,在到处是弃置的死亡和新血流过旧血的愁伤里,我迅速越过童年而成熟,没有缓刑,一次紧接一次,经历无数次的错位,身体的错位,精神的错位,语言的错位……[5]
无尽的动乱、饥饿和死亡,这是古老中国在日本侵略者暴虐下的真实写照。人们一面承受着现实无尽的苦难,一面追忆和渴望着曾经那个雄踞东方的大国——强盛、富足、安定的家园。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产生巨大的精神张力,其中饱含着叶维廉先生那一代人对饱受日本侵略者摧残的国家、民族和血脉相连的同胞的前途命运深深的焦虑和郁结:
卢沟桥的残杀是长大以后才读到的,但我年幼的心灵中的碎片又何尝不是卢沟桥的颤栗呢。我两个哥哥在每天忍受鸡粪的臭味之后是逃过了掘山洞挖战壕的酷刑,但我无千无万的其它的兄弟们呢![5]
(二)“游子”的“郁结”
其实,透过叶维廉先生“游子”身份的转换来看,将会使我们对这份萦绕心头的“郁结”有着最深刻和最直观的体味。国共内战后,由于时局原因叶维廉先生从内地辗转到香港。作为殖民地,英国对香港的统治采取一贯的做法:
英国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采取利诱、安抚、麻木制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务的工具,制造原住民一种仰赖情结,使殖民地成为殖民者大都会中心的一个边远的羽翼,仰赖情结里还包括弱化原住民的历史、社团、文化意识,并整合出一种生产模式,一种阶级结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的环境,直接服役于大都会结构与文化,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工业”,即透过物化、商品化、目的规划化把人性压制、垄断并将之工具化的运作,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识的帮凶,殖民文化的利诱、安抚、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经济化商品化到一个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5]
在英国殖民者的不懈努力下,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在无形中被弱化:
我在《自觉之旅:从裸灵到死——初论昆南》(1988)一文里拈出五六十年代两个常见的文化符号:“白华”(黄色皮肤内在化为了殖民者的政治议程和心态的中国人)与“皇家”(从会考到打政府工或会考后念港大再留学英国回来当新闻官、督察不假思索或无自觉地热衷于“为皇家服务”的现象),就是殖民教育里弱化民族意识的一些征象。[5]
中国人是苦难的。是命定苦难的吗?人口登记。在香港出生就是英国居民。黄皮肤黑眼睛仍然是英籍居民。台湾是祖国。大陆是祖国。国家的巨体分成两截,民族的气魄流散了。中国人仇视中国人。中国人杀害中国人。外国人统治中国人,外国人劫掠中国人…中国人何去何从?[5]
显然,英国政府的殖民策略是成功的。人们在吃、穿、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规划在了“文化工业”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体系中。而体系在运作中不断地消磨着他们的民族意识。那些“白华”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民族意识被弱化和消磨后,便不假思索或无自觉地热衷于“为皇家服务”,“中国人仇视中国人。中国人杀害中国人”。这注定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而文化高度的商品化、经济化使得中国本源文化在这里不断地流失。叶维廉为此深感焦虑,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文化的错位和根性的虚位。[6]本土文化的失落、断层乃至消亡,民族气魄的流散,在个体群体大幅度放逐、文化解体的废然绝望、绞痛、愤怒、悲伤、无奈、恐惧和游疑中,曾经的精神家园、文化家园在渐渐地被侵蚀着。
而后,在台湾和美国求学期间,叶维廉先生发现,在中西文学的双向对话中,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文学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非常浅薄甚至是想象和歪曲的层面。例如,欧美学者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往往因为语言、语法、句法等差异和对中国古典文化认知的不足,有意或无意地从西方的文化、文学批评理论出发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阐释,得出了偏离中国文化本源的、充满着幻想(善意的或恶意的想象)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学双向维度的批评的层面上,我们自身总是处于“失语”的状态,尽管西方的批评理论确实对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自近代以来,出于西方文明的强大而产生的盲目崇拜心理和文化自卑心理,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批评理论作为标准的,而似乎从未考虑过用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理论来评价自身。叶维廉则深感西方的批评模子无法贴切地评论中国古典文学;西方的哲学理论、价值尺度以及审美视角都难与中国传统文化合拍。[4]在中西文学双向交流上严重失衡,拿西方文学、文化的思想来思考中国的文化、文学,我们更像是“被言说的他者”抑或说“被同化的他者”。
从山河破碎的战争年代到羁旅漂泊的求学之路,在这不断飘泊的过程中,叶维廉先生面临着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漂泊。他既是地理空间意义上漂泊异国的游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和我们一样更是文化意义上的“游子”,母语文化的失落与“断层”和现代性下西方的文化渗透、侵蚀,使我们共同面临着失去“文化家园”的危机——中华传统文化失落、文化主体性丧失的危机。我们民族赖以传承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家园正面临着解体的风险,作为个体的我们也正面临着文化身份消解的危机。这是承自近代那段血泪史的“郁结”,也是文化自觉时代的我们在思考如何重树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时的“郁结”。因为,在文化主体性丧失的危机下,中华民族一旦失去了赖以传承的“文化家园”,我们就会如同没有根的浮萍一样,变成失却文化身份的“游子”。
二、“文化模子”理论——“郁结”下的“求索”
作为文化自觉者,叶维廉先生在向世人诉说现代性进程中凝结在中国人身上的那份“郁结”时,也在进行着理论探索,“文化模子”理论正是先生对于这份“郁结”的“求索”,是对中西跨文化、文学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问题的正视。“文化模子”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五四和现代性进行反思,对现代性进程中所潜藏的某种“权力神话”去进行解构,对传统予以正确的定位,为我们重新树立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支撑;使我们得以重新去阐释传统并找寻中西两种文化的汇通之处,从而促进中西文化达到“互照互识”的状态。
(一)“文化模子”理论
1975年,叶维廉先生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模子”这个概念。他用那则鱼的寓言生动而又形象地说明了:所有的心智活动,不论其在创作上或是在学理的推演上以及其最终的决定和判断,都有意无意地必以某一种‘模子’为起点。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选择方式和不同的组合方式。[7]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子”,文化模子在特定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衍伸、丰富和变异,最终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族群的个体在语言、价值观念、审美尺度和更广泛的文化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共同文化心理,即“文化模子”的显现。
当然,“文化模子”理论在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时,并不是在关闭跨文化交流的大门。恰恰相反,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因为文化的主体性就体现在差异性上,这是每种文化赖以存在的本质属性。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都是以一种文化宰制其他文化,对异己文化进行消融和同化,达到的不是平等对话而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极端摧残与破坏。“文化模子”理论对文化间的差异性的强调,就是对多元文化的文化主体性的维护,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只有在充分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性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在区分不同文化的“基本差异性”的基础上,找寻出不同文化的“基本相似性”即不同文化的汇通之处,并以此实现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的互照互识。由此观之,“基本相似性”就是跨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不同文化的不同模子中有没有共同的美学结构行为(规律),这个共同区域如何设定为好?[4]
“共同的美学结构行为”抑或说“基本相似性”的提出依据,是道家美学思想。道家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本源——“道”。当我们破除掉语言概念化、公式化等种种对事物限制、歪曲的主观因素(“名”)后,便能达到“本真”的状态。因为“名”是依附着情见、意欲,所以由各种“名”圈定出来的意义架构往往是含有某种权力意向。[8]在叶先生看来,跨中西文化的“共同美学结构行为”也是存在的,中西文化正是这种“共同美学结构行为”在中西各自历史发展中的“投影”。
(二)“文化模子”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西方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西方学者乃至许多中国学者也是常常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西方的那一套标准来对中国文化进行价值评价。而那则鱼的寓言则向我们诠释了这样的道理:西方人以西方文化模子研究、批评中国以及其他文化种类的文学,结果会和鱼以自己的模子想象人类一样,与实际的现象、存在相去甚远。[4]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人们常常会从自身的角度和标准出发,对事物进行圈定。在无形中,这种圈定往往是伴随着我们隐秘的情见、意欲乃至某种权力意向等主观因素,这就会使得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与实际发生了偏离。任何以某种“文化模子”为标准去衡量其他文化的行为,都会造成文化间的隔阂和误读,形成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并由此陷入极端的文化中心主义。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从一开始便是与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辩证下的蜕变与转化,我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主动和被动中、从形而下的器物到形而上的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推进着古老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并逐渐习惯于用根植于西方文化的那一套“普世价值”的文化标准,来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价甚至是改造,在不自觉的过程中参与了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建构,丧失了话语权。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中,我们就处于了文化“失语”状态,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也面临着丧失文化主体性、沦为“被言说的他者”乃至“被同化的他者”的危机。
叶维廉先生的“文化模子”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从理论层面上否决和消解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中心主义,通过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彼此间的“互照互识”;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下,西方工业文化对非西方国家民族意识弱化和文化独特性破坏的危害,以及其中潜藏的某种权力关系,在方法论的层面,为我们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和重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指导。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叶维廉先生的“文化模子”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的重建确实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然而,在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同时,并非意味着对现代性进行全盘否定,对经典和传统的全面回归。“文化模子”理论的初衷是要打破一个极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同样,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也必须防止陷入另一个极端——文化保守主义。
参考文献:
[1]丛晓梅.周宁和他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N].中华读书报. 2012-03-21(10).
[2]叶维廉.比较文学[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3:2.
[3]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59.
[4]李丽.跨文化比较中模子的确认及应用:叶维廉诗学理论支点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8,19,19,20.
[5]叶维廉.走过沉重的年代[A].叶维廉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C].2008:209,210,216,216,216.
[6]丰雅楠.寻求跨文化的秘响旁通——叶维廉“文化模子”理论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3:14.
[7]叶维廉.叶维廉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9.
[8]闫月珍.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现代阐释[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8.
(责任编辑:陈果)
The Search under the Depression: Cultural Mould Theory of Yip Wai—lim
LU Zhi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In face of the crisis of loss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ty,Yip Wai—lim put forward Cultural Mould Theory,which has two great meanings:First,the meaning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which will conducive to realize Inter—cogmition of multi—culture;The second,under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al hegemony has weake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which has damage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Cultural Mould Theory has responsed to the cultural appeals,which contains the resistance of other nations to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its own cultural subjectivity,avoiding being the Others who were ruled and assimilated.
Key words:depression;cultural mould;inter-cogmition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6)02-0017-05
收稿日期:2015-09-17
作者简介:陆志胜(1990-),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文化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