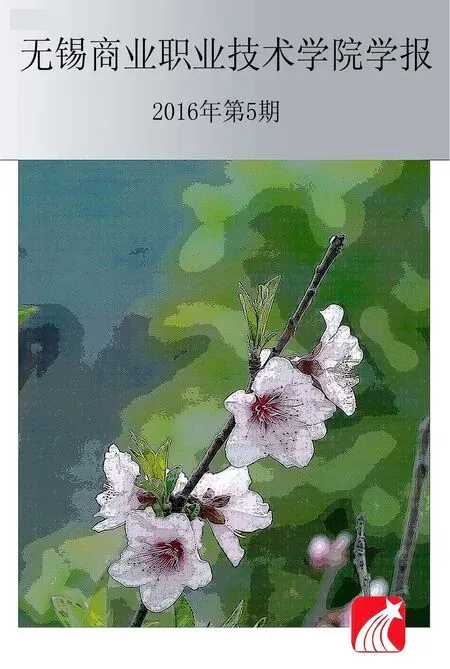自我的“他者”
——简析小说《一个人到世界尽头》
左存文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401524)
【文史哲研究】
自我的“他者”
——简析小说《一个人到世界尽头》
左存文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401524)
托马斯·格拉维尼奇的小说《一个人到世界尽头》,反思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物质水平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个体像一架架高速运转的机器,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逐渐物化为一个个符号。孤独和荒诞成为人类面对的共同困境,但是,信息时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冲卷了每一个角落,人们又仿佛失去了自我独处的空间。主人公约纳斯在摆脱这种“约纳斯困境”时又纠缠于“约拿情结”,逐渐丧失自我意识,成为自我的“他者”。
《一个人到世界尽头》;约纳斯困境;约拿情结;自我的他者
托马斯·格拉维尼奇(1972—)是当今备受瞩目的奥地利新锐作家之一,其小说《一个人到世界尽头》(以下简写为《一个人》)出版于2006年8月,并于当年获得奥地利国家文学促进奖。整部小说只有一个主人公约纳斯,在他虚虚实实的感受中,出现了与他处处作对的“睡中人”,以及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却让他充满恐惧的“狼罴”。主人公约纳斯构成了现代人的一个隐喻,他集中表现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以他的名字命名,将他这种无所适从、充满恐惧的生存困境,称为“约纳斯困境”;相应地,小说在结构上也与《圣经》构成对应关系,约纳斯开车经过英吉利海峡的描写,与《约拿书》中约拿被鱼吞入腹中的情节相对应,而约纳斯与约拿谐音,更让小说表现出马斯洛的“约拿情结”意味;处在约纳斯困境中的现代人类,对自我的寻找囿于约拿情结,小说中的“狼罴”实际上是这一情结的具体化身,而“睡中人”实际上是自我意识沦落后的状态,也就是自我丧失之后形成的“他者”。于是,从代表人类生存状态的约纳斯困境,到现代人从这一困境下自我追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约拿情结,逐渐构成了自我意识丧失后的他者。
一、约纳斯困境
《一个人》的主人公约纳斯是一家家具公司的职员,在一个工作日的早晨醒来后,一切变得不再平常,甚至不可思议地诡异。所有人都不知去向,只有空旷的街道和建筑物。跟所有人一样,约纳斯本能的反应是“要不就是他在做梦。要不就是他神经错乱了”[1]13,他在反复的寻找中终于相信,这世界真得只剩下他一个人,甚至连生物或者说一切有着一丁点生命迹象的东西都没有。他在寻找别人的生活痕迹的同时,也到处留言,但世界给他的不是冰冷而是无望的答案。渐渐地,一个人的生活令他无法认清现实和梦境,开始变得迷狂。他总是觉得“好像随时会有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把他给抓住”[1]153,但周围的一切又总是与他毫不相关。其实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觉:人总是在无处不在的威胁中孤独地生存着。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人们开始偏处于自己的一隅以寻求保护和安慰。每个人开始害怕陌生的环境,不管是物质层面的变化还是精神层面的冲击,一旦脱离既定的生活方式,他们便惶惶不可终日。正如《一个人》中的约纳斯那样,“他根本不可能想像自己会长时间待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在那种环境里,他会觉得,每走一步都是在战斗”[1]100。小说中,约纳斯面对的那些建筑物和停在路边的车其实是被物化了的人的符号载体。这些没有生命力的物体明显不会对他构成伤害,但正是这些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物化符号,使他的安全感荡然无存。这时的约纳斯已经有些迷失自我了,“这个世界的存有是通过主观的创造活动所产生出来的存有,这是如此自明,以致任何一种其他的世界都是根本不可思议的”[2]134。但是在约纳斯的眼里,“到处都是雕像。满世界都是小雕像,塑像,雕着各种面孔的墙饰”。[1]106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当下在人与人之间持续的冷漠中,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特征似乎也在逐渐瓦解,代之而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隔阂和不信任,甚至人开始沦落为一座座雕像,难怪他会觉得“仿佛整座城市里有越来越多的雕像正慢慢从一栋栋楼房的墙里面爬出来似的”[1]161。更可悲的是,在他人变为自我世界的雕像的同时,约纳斯成为他人眼中的雕像的可能性都被忽略了,“没有一尊雕像朝他看。可是每一尊雕像都有面孔”[1]106。在面孔林立的世界,不被关注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向内心寻求慰藉成为约纳斯唯一的出路。他从开始一个人占有超市、车库……甚至整个城市乃至整个世界的狂欢中渐渐冷静了下来,他开始意识到拥有的一切似乎缺少了什么,于是他开始寻找。与其说他在寻找他人生活的踪迹,不如说他在追寻心灵的归宿。从父母居住过的老屋到童年度假的村庄、从青年时期的郊游的路线到穿越英吉利海峡,他所走过的地方其实是回忆里最温情的地方。但在这过程中,往昔的永远不再和噩梦的侵扰使他更加恐慌,尤其是在摄像机下死一样寂静的夜晚,他开始觉得“再没有什么时候能够比午夜时分更令人绝望了”[1]241。向内心寻求慰藉的途径只能走向纯粹的自我追问,于是他不错过一点点细节地在摄像机中关注着梦中人的行动,因为他宁愿相信这个梦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另一个与他密切联系但又独立的存在。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在梦中人那可怕的眼光里瞬间破产,因为“在这眼光里只有高傲,平静,冷漠——以及空虚,而且这空虚清楚地表明是与他相关的。渐渐地这空虚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完全可以看出那正在形成的歇斯底里的全部征兆”[1]196。这样荒诞的情境在现实中明显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当剥落表象的叙事层之后,人们不难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物化中已成为雕塑与雕塑间的冷漠,都互相冰冷地忽略了别人的存在,同时也渐渐地迷失了对自己的定位。小说整个结构或者说叙事背景,完全建构在这种约纳斯困境之上,从这一困境的形成,到自我觉醒后的寻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寻找又很自然地陷入到约拿情结中去,在反复的自我迷失中构成了个体的他者状态。
二、约拿情结
在《一个人》中,当约纳斯发现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仍然在他人构成的陷阱里左冲右突,他惧怕所面临的环境,但又追寻着生活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这种对最高成功既追崇又害怕的心理,叫做“约拿情结”。在每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时,他总是下意识地求助于刀和枪以得到安全感。即使是去他父母曾经的住处,当周围毫无生机的环境中有着隐秘的危险时,“他的手在牛仔裤深深的裤兜里紧紧攥住刀把”[1]25。这种隐秘的危险实际上仅仅存在于他的心里,同样,对刀子的依赖正是他缺乏安全感的最直接体现。从“刀子握在手里保持着随时出击的姿势”[1]31到“双手抱着枪”[1]54,既是约纳斯在自我保护过程中走向更深层次的恐惧和迷失,又是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物质根深蒂固的依赖。从刀到枪,貌似是从原始到现代的武器发展,但更深层次地讲,在表面上从握刀的紧张到抱枪的悠然这种进步中,正暗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人对他者越来越不信任的社会现实。
可喜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约纳斯困境中等待作茧自缚。约纳斯追忆着以前一幕幕温馨的生活片断,父母的爱、郊游、与女友玛丽的交往……遗憾的是,回忆里却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尤其是他与玛丽的交往,“他从不习惯做出种种浪漫姿态,一向厌恶虚情假意,但他知道这样可以讨得玛丽的欢心”[1]43。约纳斯在追寻记忆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或许只有爱情才可以让荒诞的处境变得有意思起来,但这里所表现出的爱情交往明显是违心的。于是,从小说中又读到了信仰的拯救。约纳斯与《圣经》中的先知约拿的谐音是否有某种象征意义呢?郑冲先生认为,约纳斯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的描写暗含着约拿在海里被大鱼呑入腹中三天三夜的故事(见《旧约·约拿书》)[1]400,但约纳斯的无功而返显然是对信仰救赎这条道路的否定。因为事实是只有“陷入危难的人们多半都祈求圣母玛利亚的保佑”[1]73,而整个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归宿——宗教信仰已经不再热衷了,甚至连“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menschliches Dasein)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2]17。
人对自我的肯定本来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然后又可以顺其自然地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认同,从而找到自我价值的归属。但是,这样看似简单的理想却让每个人又觉得遥不可及。就像约纳斯一样,当他一旦失去他人的对照,就再也无法定位自己的身份,他有着一个人走到世界尽头的豪情却没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支撑,最终只能在绝望中融化到蓝天里。它反映了一种对自身伟大之处的恐惧,是一种情绪状态,并导致我们不敢去做自己本来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甚至逃避发掘自己的潜能。这也正是约纳斯困境形成的真正原因,人们本可以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实现自我的认知,但是,对他人的恐惧又迫使人们在互相不信任中举步维艰,最后只能走向孤独和被文明的物化,因为“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3]导言1。小说中,约纳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虽然他也在反复努力地理清自我,不管是用回忆的方法,还是主动出发去寻找,但这一过程显得苍白,并无实质性的效果。
三、“他者”的形成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4]118在《一个人》中,约纳斯的空间明显地受到他者的侵略,在没有任何人存在的情况下,他依然有着本能的防备,即使在精疲力尽的时候,“他真想坐下来,可是他有一种受到监视的感觉。就好像有人正等着他这样做似的”[1]74,他所有担心的事情不是自己将会怎么样,而是每一步行动每一次选择都正好进入别人的陷阱。在自我建构过程中他者如影随形的影响,使约纳斯对他者产生某种依恋性但又同时伴随着强烈的反感,“正是这种他异性和不可知性使他者具有一种神秘感,同时在面对他者时,自我也会感到某种威胁,产生对他者进行收编、控制的冲动”[4]120。所以约纳斯始终拿着刀或枪,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他都有着莫名的恐惧和强烈的征服意识。但同时,对他者的防备和控制又是一个自我被他者化的过程。就这样,人在面对他者时本身就成为对方的他者,就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讲到的“注视”[5]319,他者的注视视促进了个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这种注视显然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凝视,因为自己对他者的凝视使得他者处在存在的状态,相反,“只有当我们成为凝视的对象时,我们的自我才得以诞生,因为他人的承认昭示了我们的存在”[4]119。再回过头来看约纳斯逃避镜子中的目光以及反复关注屏幕中梦中人的目光,正是通过他者的凝视建构自我的积极尝试。
但是,《一个人》中所表现的他者又是物化的世界以及自我的另一个方面。对于约纳斯来讲,无论是对他者的反观还是对自我的建构,都只能在自我这一个载体中实现。因为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这是不可超越的处境,纵然他可以循着记忆来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但当面对眼下的环境时,他有着很清楚的意识,“他感觉到那里有个人,同时又知道那里没有人”[1]41,有的只是形单影只的他。在这无法摆脱的命运面前,人们通常要以他者为镜子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特征,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他者视角审视自己的时候,自我的身份才得以确立。然而,事实上,“我们不太可能做我们自己生活的纯粹的旁观者,因此我们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投身于自己的生活,同时能以观看稀奇之物的态度看着它,仿佛观看一种陌生的宗教仪式”[6]23。当人们自我意识无限膨胀之后,对他者的控制欲也前所未有地增强,而当生活中的他者载体——形式上的人突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像约纳斯所面临的那样),世界除了荒诞,再不可能留下多余的什么。其实“许多人的生活是荒诞的,暂时的荒诞或永久的荒诞”[6]15。只是格拉维尼奇将物化世界里的人抽象出来后集中在约纳斯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而已,因为人的物化靠着人这一形体的依托还不显得那么彻底,一旦这一形体变为雕塑或虚无,那么精神层面的自我便会在瞬间坍塌得一无所有[6]9。
和《一个人》中的约纳斯与梦中人之间的相互敌视一样,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一个敌对的梦中人,这个梦中人正是人们无法认识和把握的“自我的他者”。因为物质的飞速发展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享受的同时,人的生活也逐渐被程式化了,人不过是社会机器的生产线上的一个符号,“人们实际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变得多余、无所谓和毫无意义了”[3]9。一旦失去表现个性的空间,他者的凝视就会凸现出它的意义,如上文分析,最强悍的他者是个体内心对自我恐惧所形成的“约拿情结”。对自我身份无法定位的时候,自我的他者性就会粉墨登场。就这样,人在程式化的生活里将他者物化的同时也物化了自我,但每个人又不甘心沦为他者的影子,于是又都仇视他者的存在,而没有他者的存在,自我的建构也失去了其可能性。这必然会带来自我的异化,人逐渐沦为“自我的他者”。当然,这个“自我的他者”就是物化了的自我,是人迷失自我之后的一种荒诞存在,是内心的陌生人。本能的自我意识又促使人去虐待这个陌生人,因为这个人是个体内心恐惧的外化,是在他者的凝视中被物化了的自我,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被反复异化又被反复仇视的自虐怪圈,“当人们认为他者构成了威胁,并对他者实施暴力,是因为人们无法面对内心的‘陌生人’”[4]120。约纳斯摄像机中墙上的那把刀就是自我与自我的他者之间的关系的象征,当自我意识为建构自我而凸现时,他能将刀轻易地插入坚硬的墙体却拔不出来,而当自我的他者凸现时,他轻易地将刀从枪上拔出来却无法再刺进去。就这样,一个个自我被沦为一个个自我的他者的现实,才使格拉维尼奇感叹“每个人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笼子”[1]223。通常,人们认为这个笼子来自于他人,来自于社会的需求,但更多时候,也是最为隐秘的笼子,它恰恰来自于自己。
综上所述,在当今物质飞速发展将人物化的背景下,约拿情结与这一背景的契合产生了对自我建构的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使每个人都处在约纳斯困境中。既然每个人都逐渐沦为自我的他者,那么,人应该在这荒诞的处境中自生自灭,还是积极寻找建构自我的途径?也许,格拉维尼奇在《一个人》中有着先知性的启示,他认为“同自身和世界保持纯净和谐的人,将会感觉更舒适更惬意”[1]393。也就是说,意识到他者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必然条件,建构自我才能够成为可能。
[1]托马斯·格拉维尼奇.一个人到世界尽头[M].郑冲,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张剑.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
[5]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编辑:张雪梅)
Self-Otherness:An Interpretation of Night Work
ZUO Cun-wen
(Chongq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Chongqing 401524,China)
Night Work,one of Thomas Glavinic’s novels,reflects on the individuals,who are,like rapidly working machines,coerced by the modern times and materialized into symbo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raises the level of material-life and accelerates the pace of life.The solitude and absurdness are what human beings have to confront,while the information age provides nowhere for them to stay alone.The protagonist tries to escape Jonas’dilemma but is entangled with Jonah complex,thus becoming a self-other instead of gaining self-consciousness.
Night Work;Jonas’dilemma;Jonah complex;self-other
I 106.4
A
1671-4806(2016)05-0091-04
2016-04-10
左存文(1984—),男,甘肃陇西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学与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