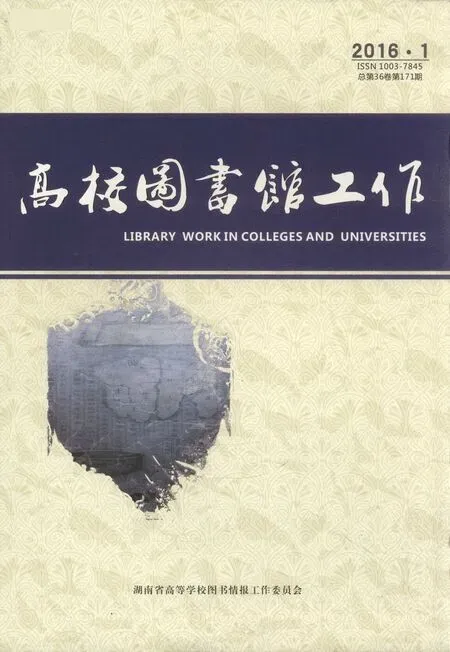网络时代阅读推广馆员的知能结构
●陈 亮 (南京艺术学院 南京 210013)
网络时代阅读推广馆员的知能结构
●陈亮(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
[摘要]文章从“阅”与“读”两个字入手,介绍了浏览式与精研式两类阅读法,并结合“书”与“网”的阅读与利用,探讨了阅读推广馆员的“知”与“能”, 力求在网络时代建构以阅读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达到多种知识融会贯通,知行合一,更好地投身到阅读推广的实践。参考文献11。
[关键词]传统阅读网络阅读数字阅读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进入互联网时代,许多人已经过着“左书右网”的生活。许多年轻人已经是网络新一代,对于他们来说电脑和网络,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已经融入生命中,他们的阅读方式和接受方式都具有数字化特征。作为阅读推广馆员,要想得心应手地在书与网中穿行,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1“阅”与“读”
阅,表示看、察看的意思。与阅连用的词有阅览、阅读、阅报、翻阅、传阅等。《说文解字》中对阅的解释为“具数于门中也。”在门里面点数字,一目了然,很清楚。阅多用于“大略地看”,如“阅人无数”,很少说读人无数,因为见过的人可以有许多,但是根本读不过来。有时“阅”也会有仔细阅读的意思,如详阅、批阅。
读,依照文字念。如读经,读书,宣读,朗读,诵读。还有看书、阅览的意思,如阅读,速读,默读等。《说文解字》对读的解释“读,诵书也”,“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 。读有出声与不出声两种。有一首歌说“读你千遍”,对特定的人,仔细地读,反复地读,读千遍是可能的。但不说“阅你千遍”。因为阅扫视的意味比较重,读则更注重品味、领会。
清朝的语文教育家唐彪已经把阅与读放在一起来谈,他说:“学人当问之事理无穷。获遇有大学识者当前,细琐之事不必问及也。 最要之大端,莫如问其当读者何书、何文?当阅者何书、何文?当置备以资考核者,何书、何文也?”他把读物分为“读、阅、备考”三类。并且认为“尤切要者,在问当读、阅、备考之书、文,何刻为善本”,“若所读阅之书得善本,自然见识高,才情长。若所读阅之书非善本,自然见识卑,才情劣矣”[1]。
晚清名臣曾国藩,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在诗文、书法方面也很有造诣,对阅读也颇有心得:“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并通过打比方:“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说明看书与读书“二者不可偏废”[2]。
梁启超在《治国学杂话》中说“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 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钞录的随读随 钞;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页,遇有想钞录的,也俟读完再钞,当时勿窒其机”[3]。
民国年间夏丏尊先生也认为:“阅读两个字不妨分开来用,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懂它的内容,不必从文字上去瞎费力,只要好好地阅就行,像国文、英文两门是语言文字的功课,应在形式上多用力,只阅不够,该好好地读。属于一般科学的该偏重在阅,属于语言文字的,只阅不够,该偏重在读。……这样看来,任何书籍都可有两种说法,如果就内容说,只阅可以了,如果当做语言文字来看,那么非读不可。”“阅读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略读,一是精读。略读的目的在理解,在收得内容;精读的目的在揣摩,在鉴赏”[4]。
笔者在研读前人关于阅读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平时的思考,立足博览与专精,把阅读法分为浏览式阅读法和精研式阅读法两大类型。浏览,就是大略地看,快速地扫描。把要阅读的内容大略地翻翻,泛泛地读一遍。一般采取默读方式,用目光扫视。浏览的目的为全读还是选读或者不读做准备。浏览式阅读法,包括泛读、略读、跳读、速读,主要为快速获取广泛的信息,扩大知识面。精研,就是精细地读,反复读,认真阅读,揣摩研究。是通过浏览筛选之后进行的深层次的阅读。弄清楚字词句段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掌握主题、结构。精研式阅读法,包括朗读、熟读、诵读、精读,主要为获得专深的知识,加以理解和体悟。
2“书”与“网”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对阅读是这样定义的:“阅读是一种从印的或写的语言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阅读就是“看(书﹑报等)并领会其内容。”通俗地说:阅读是读者从读物中获取信息的过程。以读者吸收信息为主,在此基础上,对读物理解与体悟。
阅读者是阅读行为的主体,是在具体阅读过程中从事阅读活动的人。每个人都是阅读者。阅读者有不同的年龄阶段、教育层次、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解能力、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阅读方法等。阅读的效果与阅读者的阅读兴趣、知识基础、阅读能力等紧密联系。
读物是信息与知识的载体,是阅读者需要阅读的对象,是阅读行为发生的基础。读物所包含的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可以记录在纸质材料上,也可以被存储在电子设备及其他介质中。载体被书写与记录以后,就成为了可以阅读的读物。如唐彪所言,读物是否为“善本”,关乎读者的“见识”与“才情”。因此,对读物的研究非常重要。
读者有了读物,还需要有阅读行为,才完成了阅读。三者缺一不可。譬如图书馆、书店,出版社,不管你有多少书,没有读者,谈何阅读?一个想阅读的读者手里没有可以读的读物,也是读不起来的。但是,一个读者把读物拿在手里、揣在包里,从来不读,没有阅读的过程,也便不可能获得信息或知识了。没有阅读者,无论是否有读物,也不会有阅读行为。 有了阅读者,但是却没有读物,阅读也无法进行。既有读者,也有读物,但是却没有展卷去读,阅读行为并没有发生。读者是阅读的主体,读物是必备的条件,阅读行为则需要“发生”。
我们在研究阅读推广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读者与读物(书、网)”,在读者的层面,要考虑“为谁提供?”哪些读者喜欢阅读纸质的?哪些读者喜欢阅读数字的?哪些人偏爱浏览(阅)的?哪些人偏爱精研(读)的?在读物的层面,要考虑“提供什么样的读物?”是纸本的书报刊等资源?还是电子书报刊及网络资源?是供浏览(阅)的读物?还是供精研(读)的读物?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月初发布的《2014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83家,出版图书448 431种,2010年至2014年图书品种数呈上升状态,2014年出版图书品种数增势减缓。2014年新书品种数较2013年减少91种,同比有所下降[5]。
全国每年出版40多万种图书不可谓不多。但是图书馆馆藏的纸质图书情况如何呢?“2014亚马逊上半年图书排行榜-总榜前100名”中,第一名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第二名是《追风筝的人》,在“武汉卷藏”所做的“2014年上半年馆配文学门类TOP20榜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排在第一名,说明图书馆界在馆配方面还是能够抓住热点的。该榜单排名第一的馆配覆盖率25.47%,第50名馆配覆盖率只有15.58%,充分说明了图书馆馆配纸质图书的局限性,在大量品种面前,图书馆能够收藏的图书品种有限,加之收藏的图书品种被馆配商控制,采访人员能够接触到的新书品种有限,而且由于经费及其他多种原因,图书馆的纸质图书建设并不是很能让读者满意。
当当网2014年电子书畅销榜,《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排在第十名,当当网2015年8月电子书畅销榜,《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排在第八名,说明有不少喜爱这本书的读者,通过电子阅读方式阅读了这本书。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推出的“2015年1~4月超星电子图书阅读排行TOP20”里,也有不少图书被读者阅读,充分说明在纸本书以外,也有不少电子书深受读者欢迎。
以往阅读《康熙字典》,查检甚为不便,有了网络以后,在网上可以直接进入原版在线阅读的页面,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笔画和部首,方便地找到需要查检的具体的字。1998年版的《辞源》修订本,厚厚的四大册,很难随身携带,随时阅读,有了电子版以后,可以随时根据需要,点击相关索引,查检所需要的内容。期刊方面,中国期刊网、维普期刊、万方期刊等,大家都很熟悉。此外,“博看网”“龙源网”的刊物也都不错,可以看原貌版、文本版,文本版的可以复制相关文字,直接引用。报纸的电子化也做得非常好,许多报纸都可以原版呈现,在线阅读。这些电子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通过扫描或拍照的方式进行纸质资源数字化,呈现出来的都是原来的版式,与原版的内容完全一致。还有的虽然来源于传统纸本,但是脱离了原版式,有的内容还能做到完全一致,有的内容则有不少讹错。
也有不少来自网络的原生数字资源,完全属于纸本中所没有的,网民在网络中创造,这些文字(网页或者文档)、图片、音频、视频资源,质量有高有低。在“光明网”的阅读频道中有悦读会、名人堂、书评、数字阅读等栏目,“凤凰读书”中有书讯、书评、开卷八分钟、好书榜等栏目,诸如此类的读书频道,有不少经过组织的资源,值得一读。此外,网络中还分布着大量的阅读资源,这些资源则良莠不齐,利用时需要进行鉴别。
网络资源的一大特点是检索比较容易。我们在面对厚厚的大部头著作时,想要快速地找到所要搜寻的内容,并不容易,电脑却可以轻松实现。“汇雅电子图书”和“中华数字书苑”等,都可以深入到图书全文中检索,“中国知网”“维普期刊”“万方期刊”等,都可以深入到期刊全文中检索。在“古诗文网”里,可以很轻松地找到哪些诗词的标题或正文中包含“斜阳”;在“中华诗词网”里,可以搜索到所有提到“栏杆”或“阑干”的诗词,十分方便。
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林先生认为:“任何人都难以仅依靠人工可靠地检索、阅读、分析哪怕狭小领域的所有相关内容。‘只有计算机才能阅读’”[6]从数据检索与分析的角度剖析了数字阅读的深度挖掘的特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认为:“网络改变了一代人的阅读习惯,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读书的人不一定就高尚,读网者也不一定就堕落。其实,无论阅读哪种媒体,都要面临内容选择的问题。利弊关键在人,而不在工具。……对读书的引导应该提倡读什么,而不是通过什么读。”[7]捧着一本书读,或在电子显示屏前阅读,只是阅读方式的不同而已,关键在于“内容的可获得性”。
3“知”与“能”
在网络时代,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信息在互联网上流动,知识在互联网上链接。信息与知识获取主要围绕互联网进行,网络成为提供与获得信息资源的主要场所,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增长迅速,越来越多的读者从网上获取资源,纸质文献利用率越来越低。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58.1%,较2013年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首次超过了图书阅读率[8]。
2015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49亿。使用手机上网的人数为5.57亿,手机上网使用率为85.8%[9];下半年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搜索引擎、网络新闻等应用,使用率在80%以上[10]。
腾讯科技调查了微信用户平均每天阅读文章的数量,每天阅读1篇文章的,达23%,每天阅读2篇文章以上的,合计达77%。据腾讯公司发布的2015微信用户数据报告,微信已经覆盖90%以上的智能手机。近 80% 用户关注微信公众号。用户关注公众号主要目的是: 41.1%为了获取资讯,36.9%为了方便生活 ,13.7%是为了学习知识[11]。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安永欣的微信公众号“九兰斋”,有一则“新书上架”的消息“中国美术史爱好者的福利—标点整理本《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可谓图文并茂。该文既有纸本书的介绍,又有读秀电子书的关联;既有文字的描述,又有图片的展示;既立足于书籍本身,又有丰富的外围资料,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微信阅读推广的例子。
所以说,在这样的新时代,图书馆员的知识与能力需要更新了,既要掌握核心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也要掌握相应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科和计算机应用等基础知识。要达到多种知识融会贯通,形成完美的知识结构。既要具有观察、表达、沟通、交往、实践、服务的能力,也要具有思考、学习、科研、知识管理等能力,要能够掌握所需要的信息技术,进行适当的自我规划,不断地提高自己。
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能力是知识的体现。要做到“知行合一”,既要知道,也要能做到,既掌握知识,又能动手实践,由知识层面到技能层面,由书报刊到网络,由浏览到精读,由己及人。在做阅读推广的工作时,要弄清楚什么是阅读?阅读推广主要做什么?阅读推广怎么做?阅读推广为谁做?读者需要什么样的读物?哪些读物适合哪些读者?哪些读物该浏览(阅)的?哪些读物该精研(读)的?哪些人想浏览(阅)的?哪些人想精研(读)的?到哪里寻求最适当的读物?具体采用何种阅读方法?等等。
阅读推广馆员要做最好的阅读引导员,找出读物与读者间可能的联系,把真正的好的读物推荐给读者,推荐读者读得懂的、对读者有用的读物,注重品质和内容质量(新、快、好),网络里读不到的,尝试找纸本;纸本没有的,则尝试去网络获得,从以前着眼于书,转向书网兼顾,纸质阅读和网络阅读有机结合,由管理载体转向管理知识,不用介意什么载体,给读者所需要的内容,让知识流动起来,为读者所用。
郝明义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越界,就不成阅读的时代。不论错过了多少机会,不论多么晚开始,阅读都在等着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机会。何况在这网络时代,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越读者时代。”《越读者》 笔者的微博与微信都是“左书右网”,并自拟了这样的一副对联:“网海遨游识天下,书林纵览知古今。”作为一个快乐的阅读者,应该能够自在地穿行于纸本与网络之间,捧读与检读并存,有纸本当然是读纸本的好,没有纸本时读电子的也不错。只要能够获得所要阅读的资源,能够实施阅读行为,对于阅读者而言,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本文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文字整理稿,有删节)
参考文献
[1](清)唐彪辑著.赵伯英,万恒德选注.家塾教学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79.
[2](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2010:231.
[3](清)梁启超.读书指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209.
[4]夏丏尊.夏丏尊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279-282.
[5]2014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9/06/c_134593408.htm.[2015-09-06].
[6]张晓林.研究图书馆2020:嵌入式协作化知识实验室?[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1):11-20.
[7]杨鸥.网络,改变的不仅仅是阅读[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06-12(1).
[8]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在京发布[EB/OL].http://www.chuban.cc/yw/201504/t20150420_165698.html.[2015-04-20].
[9]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2/t20150203_51634.htm.[2015-02-03].
[10]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7/t20150722_52624.htm.[2015-07-22].
[11]微信官方数据披露:什么样的文章更受欢迎[EB/OL].http://tech.qq.com/a/20141230/007569.htm.[2014-12-30].
(刘平编发)
Knowledge & Skills of Reading Promotion Librarians in the Network Age
Chen Li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Centering on the concept of read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reading methods: extensive reading and intensive reading of both books and interne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of reading promotion librarian, hoping that they may build their structure of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around read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union of knowing and doing, and do better in reading promotion. 11 refs.
KeywordsTraditional reading. Network reading. Digital reading. Structure of knowledge. Structure of ability.
[收稿日期]2015-11-24
[作者简介]陈亮,研究馆员,现在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中图法分类号]G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16)01-0013-04
【阅读推广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