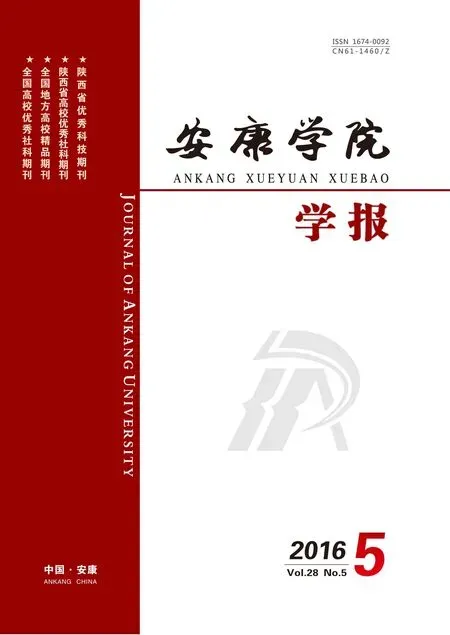论王铎诗歌的“诗史”精神
周璐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论王铎诗歌的“诗史”精神
周璐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王铎在崇祯和弘光两朝,以一颗忧国忧民、救时匡国之心创作了许多具有“诗史”精神和“诗史”意义的诗歌。这些诗歌或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或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或痛惜人民的灾难和困苦,或对农民军和明军进行双重抨击,或对当朝政治和误国臣子表示极度不满,真实展现了明清鼎革之际风云激荡的政治局势、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和不堪回望的破碎山河。
王铎;诗歌;诗史精神
在明末那段风云突变的岁月里,紧张动荡的政治局势和日益衰退的国运世道使得社会思潮、时代需求、文风和学风都发生了转变,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再次被着重强调。在诗歌领域内,杜甫以其诗歌对社会动乱的深刻反映和其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怀又一次成为众多诗人仰慕学习的对象,其“诗史”精神亦又一次得到了张扬,成为当时诗学讨论和诗歌创作的一大热点。作为一位有志于天下国家事的在朝官员和杜甫的忠实崇拜者,王铎“留心经济,志在救时”[1]“亦诗亦史”[2],强调诗歌的政治作用,主张诗不仅要存史,更要忧国轸民,“察风俗,审王化”[1],反映政治之得失,以匡时定国。在崇祯和弘光两朝,他创作了许多具有“诗史”精神的诗歌,或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或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或痛惜人民的灾难和困苦,或对当朝政治表示极度不满。这类诗歌以五、七言古体和律诗为主,遍布于其各个诗体之中,真实呈现了明清鼎革之际风云激荡的政治局势和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
一、对国家离乱、政局突变的沉痛记录
天启、崇祯之际,大明王朝内有各路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外有后金的金戈铁马虎视眈眈,时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每况愈下的政治局势刺激着诗人们本就敏感且脆弱的神经,身逢乱世的他们在诗歌中真实记述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王铎当然不会例外。
天启五年(1625),明军在封疆之地与后金已经开战七年,作战将士和辽东人民都饱受其苦,而朝中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大肆打击迫害东林人士,以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是年,王铎的拟杜之作《子美有歌乙丑都下拟》便以激切的笔调记述了这一内忧外患的局面:“提剑慷慨耻不义,七年驱驰随奔驷。欲归不归呼奈何,焰珰毒火日夜炽”[3]。随着崇祯皇帝的即位,魏忠贤一党的罪恶得以清算,是时党争虽依然存在,但相比尚未结束的辽东战役和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已暂时成为次要矛盾。所以,当时王铎心中最为牵挂和忧虑的便是持久未定的辽东战事和国内的农民起义。其《答明吾》 (四首)便以组诗的形式集中表现了他希望辽东战事早日结束的迫切心情。这一组诗应作于崇祯二年(1629)左右,时明军与后金在辽东一带已经对峙十年,局势依然十分紧张,而李自成、高迎祥等人分别率领的农民军已经在“秦中”(即陕北)纷纷起义,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开篇就叙述了这样一个情况:饱受战火荼毒的辽东已到了“风沙吹朔雪”的季节,但即便是在如此寒冷的天气和恶劣的环境中,战事依然不断,乃至引得“魑魅哭辽城”。这四首诗皆围绕辽东战事而发,且其尾联表述着同一个内容,即希望辽东战事早日取得完全胜利,因为这样不仅解除了国家的外患,而且还可以有足够的兵力和精力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从而使国家安定。如其二云:
远烽还未灭,何日执田禽?
输挽十年事,艰难百战心。
月明边角冷,霜苦阵云深。
定使国忧解,无言鬓发侵。[4]852-853
“远烽”即是后金,“田禽”即为农民军,二者皆是明王朝的心腹大患。所以,他在此诗的首联便表示出了双重忧虑:远在关外的后金战火还未熄灭,哪一天才能平定国内的农民军?接着指出辽东战役持续了十年,而今已经是“艰难百战心”了。因此他在最后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国家解决内外忧患,即使白发丛生也无怨无悔。这既是自己心声的表达,也是对远戍边关的将士乃至全体官员的一种期望。
对于意在图谋天下的后金来说,与明军的战争不能仅限于辽东一隅。在相互对峙十年之后,清军在皇太极的指挥下先后四次大举挥师入关侵明,给明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在王铎的诗歌中有真实的记录。例如:《宿良乡柬长店居人述变》 (五言律卷十九)记述了后金军于崇祯二年(1629)在皇太极的亲自率领下第一次入关侵明的情景,时“烽火逼帝京”,位于京城西南约二十公里的良乡城已被攻破;《丙子》记述了崇祯九年(1636)清军第二次入关之事,诗中道出是年如此繁多的兵患皆由“诏催燕塞上,羽遍楚江西”所致,而清军大举进攻和楚地贼寇遍布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恶果便是“县县称饥馑,门门务鼓鼙”[4]1553;《闻警》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第三次入关时,不仅描述了“岁俭农人歌掘阅,年深罢士怨飘零”的现实景象,而且发出了“烽照甘泉何等事,休将抚议缓雷霆”[4]2273-2274的强烈呼声,强调与清军作战的重要性,反对杨嗣昌等人的议和主张,与其奏疏内容相辅相成;《忧第四次兵》 (七言律卷一)作于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第四次入关时,以哀伤忧愁的笔调展现出一幅“诸城恸哭指骷髅”的悲惨画面。
清军是严重威胁明王朝的外部雄狮,而国内纷纷揭竿而起的农民军也是朝廷的心腹之患。王铎有大量的诗歌记录了明军与农民军的战争进程,如《寇来》 (五言律卷十三)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他回到家时遇到农民军来犯,身为一介书生的他“不欲委城郭”,穿上胄甲,“提刀别内妻”,亲身参与了守城御寇的激烈战斗;《悲南阳》 (七言律卷一)便是在崇祯十三年(1640)仲冬南阳被“贼寇”攻破时所作;《庚辰自北徂南》 (五言排律卷一)在序中叙述了自己在崇祯十三年(1640)从北京回家乡孟津途中先后在张吴店、新乡临清村两次遇农民军并均与之战斗的事情,在正诗中抒写了自己的“心忧”与“咏叹”。
明王朝在清军和农民军的双重夹击下艰难地走过了十七年岁月之后,终于在茫茫血海和满天哀嚎中孤独地倒下,其标志就是崇祯甲申年(1644)三月北京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崇祯皇帝自杀身亡,大顺政权建立。而不久之后,江山易主的大戏再次上演:清多尔衮大军在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引导下第五次入关攻占北京,赶走李自成,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此时,避乱南下的王铎从北来散卒的口中得知城破帝死的消息之后大为震惊,并以无比悲戚的心情写下《始信》一诗。关于“始信”的内容,从表面上看是“始信杜陵叟,实悲丧乱频”[4]941,实际上是在得到确切消息之后不得不相信“衣冠禄秩新”这一改朝换代的事实。之后,他更以《甲申旅处哭》 (八首)来哭悼国家和崇祯,痛斥误国奸佞,然而再多的哀悼、愤恨都已无济于事。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伴随着故国之思而来的是对“空令社稷亡”[4]1506的反思,这在其《前年行》中有着典型体现。其诗云:
前年天子骑青骢,急走齐化东门中。大珰握錀不放走,火器欲击谁得行。当时宰相陈魏辈,龌蹉岂是璟与崇。观稼亭子宫女缢,万岁山前天子死。寺人内应国轴倾,难戮凶渠竟如此。加派四海剥民膏,处处揭竿州县里。神龙已僵海水枯,具日予圣复何倚。战鬼夜出拦路号,五岳四渎破萧条。村无椽瓦人骨堆,螟蠈犁城为空壕。岂是神灵好权诡,仁贤不信致漂摇。血流模糊旗满野,强半乾坤割山椒。吹角鸣镝哨马凶,行人被劫卢沟桥。官军好杀舞长钺,良民夺妇畏蛇蝎。天下一家皆赤子,牛羊卤略益荒忽。至今滇南粤东西,尚费金钱张桓拨。人身朅来蜾蠃同,幸遇贼兵犹自可。若遇官军席卷空,寒风枯桑吼夜火。[3]
这首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以回忆的方式重点叙述了崇祯帝的死亡和崇祯中后期那一段混乱黑暗的历史,亦是对明王朝覆亡原因的总结与反思。据计六奇《明季北略》 (卷二十)记载:甲申年(1644)三月十八日夜北都内城陷落,得知消息的崇祯帝亲手剑杀后宫数位妃嫔及公主之后,于十九日凌晨“手持三眼鎗,杂内监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至齐化门,内监守门者疑有内变,将炮矢相向,不得南奔……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第问计,而纯臣独在外赴宴,阍人辞焉,上叹骂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将曙矣,乃回”[5],天色微晓时在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登上万岁山自缢而死。王铎此诗的前八句述说的正是此事。其中,五、六两句是说崇祯朝最后两任首辅陈演和魏藻德,无才无德,远不是辅佐唐玄宗开创大唐盛世的贤相宋璟和姚崇,这与后面的一些诗句共同反映着第二个重要内容,即皇帝用人不当,总是被奸相、宦官所欺瞒,以至于仁人贤士都被疏远而漂泊异乡。十一、二句揭示了朝廷加派赋税这一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导致不堪重负的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朝廷这一不争的事实。君王的用人不当、朝廷极其错误的政策及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都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但是作者想到的不只是如此。他在诗歌中悲切地诉说着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呈现出空村破败、白骨累累以及血流成河、战旗满地的恐怖情景。最后十句笔锋一转,无情地鞭挞了官军在作战时对普通民众烧杀抢掠的恶行,甚至发出了“幸遇贼兵犹自可,若遇官军席卷空”之言,这其中饱含了太多的无奈与痛恨。同时,倒数五、六句又指出顺治三年的“今天”,“滇南粤东西”等地的局势还没有稳定,清廷还需“尚费金钱张桓拨”才可以平定这些偏僻之地,才可以使此地居民得以安定的生活。回顾昔日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感念今时局势,尚有忧虑挂怀。可见,王铎即便是降仕新朝,也会思念故国,心系百姓。
二、对民生凋敝、百姓困苦的强烈悲叹
明清鼎革之际,许多无辜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深有感触的王铎在其诗歌中以悲苦而愤慨的情感反映出人民在这乱世之中所遭受的苦难,这在他那些以感伤农事、悲叹农民为主题的诗歌中表现的尤为强烈。因长年战乱而遭受苦难最大的莫过于以田为生的农民,他们不仅受到战火的荼毒,而且又频繁地遇到天灾,许多农田因此颗粒无收或沦为荒地,而朝廷“加派”饷银的政策又迫使本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他们不得不缴纳繁重的赋税。如此种种,农民们已被逼入饥寒交迫、穷途末路的境地。王铎家族世代靠土地为生,对农民和农田有着深厚的情感,是时他创作了不少与农民、农事有关的诗歌,基调颇为沉重。其五律组诗《壬申夏秋洛郡淫雨七十余日,庐倾,人伤,禾害,因忆辛未雪五尺冻死数百人》 (三首),其诗题便清楚地道出了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崇祯四年(1631)冬季,天降大雪,导致数百人冻死,第二年又连续降雨七十多天,致使“庐倾,人伤,禾害”“粮莠亦沦亡”,百姓的财产和安全都因此受到重创,遍地破败萧条之景令人触目惊心。而作者在感叹“苦雨联饕雪,百年未曾见”的同时,又将雨雪之灾与“虫飞年月事,霾苦战争心”联系在一起,道出了内心更为深层的想法:“赤子遭时险,皇天用意深”[4]1693。他认为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无休止的战争,致使国家难以太平,百姓不得安定,而这正是上天给予当政者的警示。实际上,王铎在此从侧面道出了对朝廷的些许不满。然而,随着事态的愈演愈烈,他再也忍耐不住内心的伤痛和悲愤。
如果说在此时王铎还对官方有所期冀的话,那么后来他对官方的态度就已转变为直露愤激了。其《行田间》无奈地述说着农人今昔生活的巨大反差:“昔岁蒸秋米,糟床彼一时”,酒食俱足,而今时则因兵患、赋税陷入了“在此聊为计,将来不可知”[4]884的困境。《过村舍》颇似杜甫的“三吏”“三别”,全诗叙述了自己的亲身见闻:一户贫苦农家只有不到十亩田地,而“今年”又遇上旱虫灾害,怎奈“县官重征赋,邻人他乡走”;长子因护守自家粮食而死于贼寇之手,次子前年已远赴蓟门与清军作战,生死尚未可知,而孤守家中的夫妇二人已心衰力竭,过着“忍饥日半饱”的生活,只念想着“西寇不东来,或望数年寿。官家实蠲租,努力耕糊口”[4]602-603。倾听着如此悲惨的诉说,作者心中郁结,“饮不能咽”,最后只得将各种情绪融合在一起,发出了强烈的呼喊和哀叹:“庙堂安得知?民瘵满林薮。哀哀乱世人,枝梧胡能久?”[4]603《庚辰大饥津人食子》更是哭诉了人间母食子的惨剧:崇祯十三年(1640),孟津农人因接连不断的旱涝灾害而颗粒无收,无钱无粮缴纳沉重的赋税,因此便遭到“有司烈刑摧,官军燔煮人”这样的残害,天灾人祸叠加到一起,致使“终知难两活”的饥饿母亲出于“儿死尚可忍,儿啼那堪闻”[4]583的原因吃掉了自己的小儿子。虎毒尚不食子,何况人间最具慈爱之心的母亲,但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了。然而值得思索的是,作者虽然以“骨肉岂不亲,穷极竞无恩”作为此诗的开篇,但全篇并没有痛斥食子的母亲,反倒以“决绝反为快,物气喜不仁”来赞同母亲的做法,这样更能体现出作者对饱受苦难的农人的同情和理解,以及对置农人于死地的“有司”和“官军”的鞭挞,也从侧面让读者回想出当时人吃人的一幕幕惨剧,如此更令人心痛、惊惧。在王铎的诗歌中,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其中反映最为深刻的应是《故乡亲友来》。其诗云:
车马门前至,乃是故乡客。拂座问故乡,久叹为谷麦。寇势稍稍灭,上官无存恤。苛猛万千寇,荐疏诩能识。私派派靡已,数万复何极。不死于寇者,半乃死吏墨。其余未死者,求死反不得。虎寇生啖人,刑酷工雕刻。道路空以目,故旧非畴昔。昔时为儿童,今长杖下厄。今时诸壮者,桁杨听屠伯。旧人在新坟,新人卖旧宅。天地洵无情,官长逾乐易。含愁告乡人,酒且莫酬酢。我别曾几时?言之惊魂魄。乍见亲友来,不觉顿欢悦。不如不问好,一问反不怿。北京二千里,欲救将何策?锋镝酿其凶,人命在燔炙。寥寥恸孑遗,生死不可测。四座皆荆棘,如闻冤鬼泣。庭中惨不言,郁若枯松柏。孰谓九阍遥?墨吏狼豕塞……[4]554-556
从故乡而来的亲友回答了作者关于家乡境况的问题,然而却是这样一番惨不忍睹的景象:久无谷麦,饥民遍野,死者纷纷,道路空荡,活人欲死而不得。然而,导致这一切的不仅有无休止的病患,而且还有沉重的赋税;不仅有凶猛的贼寇,而且还有残酷的官吏。对此,作者在十分震惊之余充满了忧虑。他在见到故乡来人之时是极为欢喜的,但当他得知现在的家乡是这样的惨状之后,便后悔之前问及家乡之事。因为不问就不知,不知就不痛,不痛就会高兴地与来人畅怀饮酒,继续“平静”地生活着。然而,纵使如今知晓,纵使极力欲救,也束手无策,这倒不是因为自己远在两千里之外的京师,而是此事非一人能力所及,亦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在这里,作者不再寄希望于腐败无能的朝廷,而只是对在战乱和饥寒交迫中死亡的乡人表示痛惜和哀悼,因为此时在他心中,酷吏和啖人的虎寇一样恶毒,他们都是夺人性命的凶手。实际上,作者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已然心灰意冷,他不敢面对现实的惨状,只有选择逃避,所以诗歌的最后他“收泪唁故乡”,表示再见到故乡人的时候或谈山水,或谈花石,绝然不问家乡近况。但是,他真的能逃避得了吗?无论处于何时何地,农民们饱受战乱、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生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当然,王铎悲叹的不只是农民这一个群体,而是在这个甚为动乱的时期遭受苦难的全体民众。因此,他一再在诗歌中表现出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祸,流露出早日“休兵”的渴望。
三、对农民军和明廷明军的双重批判
十余年“中外未攸宁”[4]565的巨大动乱使国家和人民落入了万丈深渊,苦不堪言,这无疑是王铎诗歌所反映的重要内容之一。于外,历经数载的辽东战事不仅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定,而且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还需要补充新的兵士来维持原有的军事力量,从而导致人民赋役加重,许多男子在朝廷的一纸诏令下不得不离家远赴边关。王铎《新军别》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昨日”收到军贴而“今日”就要赶赴边关的“远征人”,他在与家人离别之时,“父母为吞声,弱妻为汍澜”,而自己亦“上马泪如雨”。但是,纵然万般不舍,纵然知道等待自己的是边关凛冽强劲的北风和生死无定的战场,他还是将年迈的父母托付给弱妻,“愿此赴关山”,因为他痛恨边土被外族侵略,因为“朝廷有边患,何忍自安全”。然而,即使诗歌在抒发远征人不忍离别的同时彰显出他甘愿为国赴汤蹈火的精神,但在最后终究还是道出了对边关战争长久未平、大军归来遥遥无期的不满:“黄沙日夜来,戍军颇有年。敢论何日归,胜败难为言。”[4]554于内,愈来愈多的农民军严重威胁到了朝廷的统治权威和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农民军在与官兵的斗争中势必会给人民和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出身穷苦而又是朝廷命官的王铎,对农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深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及其产生原因,对农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感到痛惜、愤怒,并且为使民生有所改善而不停地呐喊,甚至不惜冒死进谏;另一方面则对因不堪重负、走投无路而起义反抗的农民军极度痛恨,称他们为“贼”“寇”,甚至“田禽”,因为在他看来,忠君是必须的,即使君主和朝廷实施的政策使人民的生活困苦到难以复加的地步,也不能“造反”,而且正是农民军的横行和敌对给国家增加了又一重忧患,也间接地给人民带来了更多苦难。因此,王铎在许多诗歌中都明确指出“贼寇”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混乱和灾难,将农民军视为仇敌,如“下令仍增戍,奔疲为贼营”[4]838“按剑怒发立,寇氛为我仇”[4]432-433“十人九人死,饥寇酷为疫”[4]339等。崇祯十四年元月,洛阳城破,时中原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农民军攻占,这对于乡情浓厚的王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伤痛,因此他常常“恸感中原事,魂魂向夜生”[4]983,并曾作《汤阴岳王庙》等诗来凭吊宋代誓死收复中原的爱国将领岳飞,迫切希望朝廷能早日恢复中原,但“涕泪中原堕,江山左衽危”[4]836的残酷现实不得不令他仰望苍穹发出声声悲叹。
如果将无休止的兵患都归罪于清军和流寇而置腐败无能的明廷明军不问,那么王铎及其诗歌就不见得有多高的“诗史”精神。显然从上文的多处分析中可见王铎并不是这样,他清楚地认识到朝廷内部的混乱黑暗、加派政策的严重危害、酷吏对人民的恶行,以及官兵的无作为,并在诗歌中予以沉痛的揭示与批判。如在记述农民军战事的《壬申七月》 (二首)中,他首先于序中详尽交代了崇祯五年(1632)农民军侵袭的时间、路线、地点、后果等:“壬申七月至十月,晋寇约七万余,夺太行石城而下,去孟津止百里。济源、河内、武陟、修武,杀焚之惨,喋血为川,林积为尸”[4]2340-2341。“晋寇”来势汹涌,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已让中原境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样的惨状让作者心痛无比,但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朝廷官兵的无能无用,是“募兵无一斗者”的悲凉局面,然而在汝州、叶县、鲁山、嵩县、卢氏等地还有十万“贼寇”盘踞大山,欲以吞噬。面对此景,他只能极为愤慨地哀叹道:“国家养士求其实用,则竟如此……拯民而出之水火者,谁乎?”[4]2341最后,他怀着满腔悲愤,在“辗转郁塞”的状态下作下此诗,发出了“函谷虎牢难可恃,激昂欲着晋人鞭”[4]2342的批判之声。从中可知,王铎作此诗真正的目的并不只是记述寇兵来犯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对中原地带造成的深重苦难,还有对无能官兵的批评。
与鞭挞明军相应的是对时弊和误国臣子的抨击。这类诗歌往往与其奏疏相应,具有较强的纪实性,也体现出他的清刚品格和勇气。《纪往迹》是王铎五古中最长的诗篇(组诗除外),全诗144句,共计720字。此诗真实再现了他在崇祯十一年(1638)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上疏反对加派赋税、反对与清军和议、吴阿衡壮烈殉国、雪中亲守京师城门、两女俱亡于京、乞假归养等,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时政和庸臣的揭露和抨击。在“加派”一策提出时,王铎和许多臣工都极力反对,屡述百姓现在所遭受的凶饥及此策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权衡自有人,诸臣空蹩躠”,对于这样的结果,这些“愤激内心热”的臣子们只能“相视还呜咽”。在是否与清军和议的问题上,王铎的反对更为激烈,他甚至直接谴责那些“和议日用力”的人道:“其心非为国,周岁谋颇密。欲以聋众人,虚徼赍功业。”[4]406此外,他还揭露出当时“中枢多穴隙,誉至掩即墨……阴遣元忠辈,数人入荒幕”[4]405的黑暗官场,对攻伐异己、欺上瞒下的当权者加以批判。
崇祯十一年(1638)是王铎政治生涯中较为活跃的一年,而他最不平凡的一段时光则是在南明弘光政权时期。当时他居于次辅之位,写下了许多关乎朝政得失和治国大计的奏疏和书札,期望可以改善社会民生,挽救国家。据李尔育《王觉斯诗叙》载:“觉斯今宰天下矣……计五越月,得诗文数百,无不语关国计,愤激在廷在镇之误、封疆败国是者。”[1]由此可得两个信息:一方面,王铎在弘光政权这一年内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殚精竭虑;另一方面,王铎在这一时期作的诗歌亦充斥着对误国、败国之人的愤激之情。如其《再冀》:
岂让羽林将,北人望救深。
夙问宽马谡,尚未报孙歆。
剑气冲银汉,鸱音死泮林。
临危休苟免,报国是何心?[4]1532-1533
这首诗作或作于甲申年(1644)末,或作于顺治二年(1645)初,是针对“从贼”案而发。当时北方半壁江山基本上都已沦陷,北方人民急切盼望着偏安江南一隅的南明朝廷能北上收复失地,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王铎认为当务之急是整顿国家,恢复生产,安定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消灭贼寇,接着再图谋北上,因而对于北来的“从贼”,他多抱以宽恕的态度。但是,以马士英和阮大铖为首的阉党却借机打击报复东林党人,极力要求对“从贼”严加惩治,导致许多南来投奔的“从贼”十分惧怕转而又北归,而把持朝政的马、阮却不肯放过他们,便派兵北上追击。王铎与首辅马士英在对待“从贼”的态度上特别是在对周钟等人的处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他对马、阮等人的作法极为不满,故在此诗的最后痛斥他们在国家极度危难之时不能放下私人恩怨,不能以大局为重,并以反问的方式道出他们只为一己之私利,并没有报国之心。
王铎以一颗忧国忧民、救时匡国之心创作的众多反映现实、忧国轸民的诗歌,如同一幅描摹明末风云的巨型画卷,呈现给后世的不仅有历经二十余年的明末三方争战,而且还有百姓在这历史大动乱中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不堪回望的破碎山河,跋扈无能的官军以及朝廷政治的黑暗和腐败等。他的这些诗歌与他极力学习和崇拜的杜诗一样,都极具“诗史”精神和“诗史”意义,值得后世称赞。
[1]王铎.拟山园选集:八十二卷[M].清顺治十年王鑨刻本.
[2]杨观光.王先生诗序[M]//王铎.拟山园选集.黄道周,选.台北:台湾学生局,1970:60-63.
[3]王铎.拟山园选集:七十五卷[M].清顺治十五年王镛,王鑨刻本.
[4]王铎.拟山园选集[M].黄道周,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0.
[5]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454.
【责任编校杨明贵】
On the Spirit in the Epic Com posed by W ang Duo
ZHOU Lu
(Collegeof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Minzu 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Wang Duo created a lot of poems which had“Poetry History”spirit and meaning with his heart about concerning for the country and people in Chongzhen and Hongguang dynasty.These poems writte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or anxieties about the futureand destiny,or dep lore the disaster and hardship of the people,or the peasant army and the Ming army carried out a double attack,or to harm the country and the political dynasty courtiers expressed extreme dissatisfaction.These poems show the re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ng Ding leather turbulentoccasion,destitution and unbearable social conditions look back brokenmountainsand rivers.
Wang Duo;poetry;“Poetry History”spirit
I206.2
A
1674-0092(2016)05-0041-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09
2016-03-23
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王铎与明清之际的中原诗学”(2015-JCZD-006)
周璐,女,河南周口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