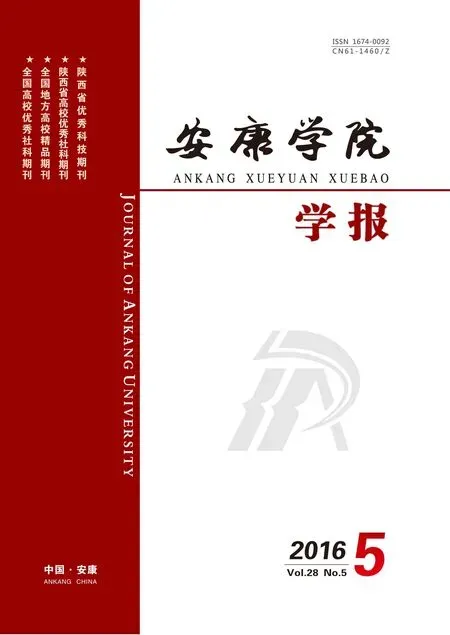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之“女才”独立性探析
施文斐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之“女才”独立性探析
施文斐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才子佳人小说中表现出的“才女”情结与清初“女才”兴盛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之于才女的关注以及对女性教育的重视。然而女才并不具有独立价值,它总是与某种色情化想象交织在一起,并被限制在为男性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这一功能性范围内。为知识所赋权的才女愈来愈不满足于自己被预先设定好的性别角色,其自我展示才华的多种方式也鲜明地透出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味道,男性社会之于女才的矛盾态度由此产生。
才女;女才;独立性;功能性;自主意识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时常表现的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遇合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才子之“才”与佳人之“色”的“才色相合”。其“佳人”之内涵远非“美色”二字可以涵盖,而须“才、情、德、色”四者兼备,其中具有时代色彩的“才”最为才子(包括文人作者)们所关注,譬如《合珠浦》的作者即认为“盖世不患无倾城倾国,而患无有才有情”(《合珠浦》序)。与“色”相较,“才”更为重要。所谓“妇若无才,已非淑女”,在才子的观念世界中,“佳人”几乎等同于“才女”,才子们对佳人的期待心理基本上是“才女”情结的一种反映。
需明确的一点是,尽管“才、情、德、色”四者兼备的“佳人”形象带有文人作者们相当程度上的臆想成分,但“才女”的形象构建却确实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并非完全出于作者一厢情愿地主观臆造。据《历代妇女著作考》载,自汉迄明共得女性作家361家,而有清一代竟有3500多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而据流传最广、篇幅最大的闺秀诗词选集,即嘉庆、道光年间武进女子恽珠所编写的《国朝闺秀正始集》载,该书共收录了清代闺秀930余人的诗作,计1700余首;又有《续集》,共收录了590余名闺秀,诗作达1200多首。其中,作为江南核心区域的苏、浙两地,其妇女作家、妇女著作更是达到了极盛状态,这一点同该地区才子云集的情况相一致。据《历代妇女著作考》,其著录的江苏妇女作家就多达1425人[1]482。另据《清代闺阁诗人徵略》,该书收录了女诗人1262人,其中浙江524人,江苏465人,共989人,占总数的78.37%[2]。这些女性著作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诗文集,约占总数的98%,此外还有小部分学术著作,广泛涉及经学、小学、史学、算学、历法、诗学、词学,甚至还有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1]482-483。
可以说,在清初以苏、杭为核心的江南地区,以诗才为主的女性才华得到了极为强烈地呈现,这不能不引起同在江南地区男性文人们的广泛注意。有许多文人都表达了他们对于“才女”现象的关注与赞美之情,如钱谦益就曾称赞过才女徐媛:“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称为吴门二大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序》)。颇有意味的是,他们在评价女性才华时总是习惯于将男性才华作为参照对象,如“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子”(赵世杰《古今女史》),“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葛征奇《续玉台文苑》),“岂一时清淑之气,不在冠弁而在笄袆……奇藻络绎,庸讵不烈于须眉”(徐媛《络纬吟》题辞),诸如此类言论,与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之于女性才华的赞美之辞可谓如出一辙。就这一点而言,才子佳人小说中表现出的“才女”情结,与清初的“女才”兴盛这一背景密切相关,是这一颇具时代色彩的文化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一、“才女”与“女色”:才华背后的色情化想象
就才子佳人小说中普遍呈现出的“重视才女、赞美女才”这一现象,有为数众多的论者习惯于从现代思维出发,将此现象与尊重女性甚至于女性解放相联系,但如果回归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尊重”与“赞美”总是透着点似是而非的味道。这些才子(当然包括文人作者自身)“在赞美女性才华时与女作家的立场和感受有所不同,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种玩赏的意味”“男性作家欣赏才女之才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到女子外貌等与才学无关的东西”[3]51,43。虽然才子们一再强调他们对那些庸脂俗粉的“世俗”美色极为不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于“女才”的鉴赏又总是与“女色”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才女”之才并非具有独立性的存在。
才子在鉴赏女性才华时,总是会下意识地将“才女”与“女色”相联系,这一点在《女开科传》中的才子余丽卿身上得到了明确体现。在与友人的闲谈中,这位才子首先表示他一定要娶到一位“有才有色,有情有德的绝代佳人终身相对”,否则,“便做到玉堂金马,终是虚度一生”。如此看来,他的理想型应该是一位“才、情、德、色”四者兼备的女子,但当提到之前“曾有一个强作解事的人”说“就是低丑妇人里面,颇有才情”,他对这种说法十分不满,“这一发胡说得紧。无盐嫫母,纵负奇才,对着这副尊颜,怎生看他得过”,因此,“遴选女郎毕竟色为第一”(《女开科传》第一回)。《定情人》中的才子双星也认为与一个“面目可憎的丑妇,朝夕与之相对”(《定情人》第一回)将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毫无疑问,才子们确实看重佳人们的才学,有才学的女子在清初江南的文化氛围中可是相当时髦的,《两交婚小传》中就写到:“这些美人,读书识字,做诗做文,竟成了风俗。做出来的诗词,香隽风流,虽当今的名公巨卿,无不啧啧称赏”(《两交婚小传》第二回)。但女性的才学必须要与美貌相结合,一个丑女的才华是绝不会得到才子赏识的。
不过,只要稍微品味一下那些为才子们所赞叹不已的女性诗篇,就会发现这些诗作似乎远没有才子们说的那么优秀。鲁迅先生曾对此有过评论:“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然所谓才者惟能在诗,所举佳篇,复多鄙倍,如乡曲学究之为。”[4]在清人的文字中也有过类似评论,如“闺秀诗,总有习气,非调脂弄粉,剪翠裁红,失之纤小,即妆台镜阁,剌剌与婢子语,俚俗尤多”(王嵩高《清娱阁诗抄》)。此类负面评论即便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也多有反映,如《女开科传》就曾评道:“女人略会吟诗,便是樊素后身;略会写字,即说蔡琰转世”(《女开科传》第一回)。在《两交婚小传》中,才子甘颐对扬州女子作诗成风一事表达了倾慕之情:“天下繁华,目今要算扬州了。只说人物也美,妆束之精,已过于今古,然犹女子事也。至于诗文,岂女子事哉,竞家吟户诵,有若武城之弦歌,真奇事也”。另一位才子辛解愠却对此颇有微词:“扬州女子虽不少,又皆尽慕诗名,凡拈起笔砚,便思量涂抹这五言八句,以为声价。然而细求之,实不知这五言八句,是咸是淡是酸是甜,又何论兴观群怨,三百之遗哉”(《两交婚小传》第七回)。
以上这些针对女性诗歌质量所做出的评论虽颇为负面,但相较于才子们那极为夸张的溢美之词来说倒显得客观了许多。虽然并不能排除确实有质量上乘的女性诗作存在,也不能排除以上言论或类似言论很可能出自于男性文人之于才女的性别偏见,但就女性诗歌质量的整体而言,或者说,至少就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诗歌质量的整体而言,所谓的“女才”确实有被过分夸大之嫌。
既然所谓的“女才”远没有那么优秀,那么为什么才子们还会毫不吝惜地予以溢美之词呢?究其原因,恐怕正是因为这些诗篇恰恰是出自于为才子们所倾慕的“佳人”之手吧。当我们稍微考察一下为才子们所推崇的诗歌题材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关注点往往都集中在那些为女性所书写的,具有香艳气息的所谓“香奁诗”上。在《两交婚小传》中就写到了男性社会之于女性“香奁诗”的强烈关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色情联想。
这些美人,读书识字,做诗做文,竟成了风俗。做出来的诗词,香隽风流,虽当今的名公巨卿,无不啧啧称赏。近来人闻得张翰林的妹子、王侍郎的女儿、赵司空的孙女、李中书的侄女,都结成诗社。每逢花朝月夕,佳节芳辰,都聚在一处,分题限韵,角胜争奇。勾引得这些少年公子,如醉如狂,都想着要求婚纳聘,就如蜂蝶一般,往来不绝。(《两交婚小传》第二回)
在小说的另一处又写到了一群少年坐在酒馆中一边饮酒,一边品评红药诗社的情景:
只见一个说道:“诗虽各有长短,看来看去,还是辛荆燕的又香又艳,又老到又风流,真要算天下女子中的奇才了。”又一个道:“莫说女子中,就是扬州合城的少年子弟,哪一个敌得她来。”又一个道:“若有少年敌得她来,几早嫁去了,也等不到今日。”又—个说道:“要娶她的春梦,我是不敢做了,但要求她写一柄扇子,却是少不得的。”(《两交婚小传》第三回)
美貌的才女本身就足以引起男性社会的关注,而一大群美貌才女聚在一起大开诗社的群体行为更会引发轰动效应。在红药诗社中,唯有才女辛荆燕的诗成为众多少年品题的焦点。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位才女的诗写得“又香又艳,又老到又风流”,以至于某些才子竟然因此而萌发了娶其为妻的念头,这不能不说是由香艳之诗风生发而来的香艳之联想。
由于女性自身情感的细腻与丰富,生活空间与视野的相对狭窄等原因,她们极易写出那种低回婉转、纤细缠绵、隽永风雅的诗篇。就才子佳人小说产生的江南地域来说,当时确有一些才女并不讳言自己诗作中表现出的某种色情意味,如明末吴江叶氏一族的才女们在其诗作中就大胆地、当然也是艺术地表现了色情以及色情背后的欲望,诸如“思君才色真如许”“展画羞看《出浴图》”之类充满了香艳意味的诗句时常可见。叶氏家族的主母沈宜修还曾写过【浣溪沙】“袖惹飞烟绿鬓轻”等词,在其小序中就明确地表明了其创作缘起竟然是因为“侍女随春,破瓜时善作娇憨之态,诸女咏之,余亦戏作”,在此种创作动机下写就的词其香艳程度可想而知[5]。
应该说,明末清初的女性文人们勇于在自己的诗词作品中大胆地表现情欲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相当程度上是晚明以来个性解放思潮渗透于女性创作中的结果,但男性文人们对女性创作的关注也聚焦于此却不能不说带上了许多性别层面上不可言说的联想。事实上,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与思想境界的提升,清初的一些女性文人已然能够写出颇具巾帼气魄的诗篇,如最具代表性的清初才女徐灿。她的词作绝无闺秀作品常见的那种纤弱、婉转、流丽,相反,时常可见大气磅礴、慷慨悲壮、深沉凝重的气象灌注其间,诸如《永遇乐·舟中感旧》 《踏莎行·初春》 《风流子·同素痷感旧》等作品更是抒发了基于明末清初时事变迁而生发的政治感慨,但此类“运笔阔大处不逊男子”的女性作品尽管会赢得男性文人们的钦佩、敬重之情,却很难成为能让他们口沫横飞、浮想联翩的话题。相较于那些充满了男子气概的女性文人及其同样慷慨激昂的作品,那些“香隽风流”的“香奁诗”及其背后那个同样“生香流艳”的佳人幻影才更易成为才子们的关注焦点。
才女之才并非具有独立性的存在,它总是与这位才女的美貌,或者说对其美貌的某种联想交织在一起。一个丑女,甚至于仅仅是相貌平平的女子的才华是不会引起才子兴趣的。在才子那不可明言的潜意识中,“才”与“色”总是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时常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对女才是多么地珍视,但此类宣言的可信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二、知识与赋权:“女才”问题相关论争的实质
关于女性是否应该作诗一事,明清文人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其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赞成者如明人胡孝思曾有言:“诗言志,歌永言,男女咏歌亦各言其性情而已,安在闺媛之诗不可以公于世哉?子独忘夫古诗三千,圣人删存三百乎?妇女之作,什居三四。即以《二南》论,后妃、女子之诗约居其半,卒未闻畏人之多言遂秘而不传者”(胡孝思《本朝名媛诗钞·自序》)。清人袁枚亦言:“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 《葛蕈》 《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甚至有文人认为,女性的作诗才能远胜于男性,“吾当谓女子不好学则已,女子而好学,定当远过男子。何也?其性静心专,而无外物而扰之也”(徐士俊、汪淇《尺牍新语初编》)。
反对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章学诚的言论:“呜呼!己方以为才而炫之,人且以为色而怜之。不知其故而趋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趋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称,谓之静女,静则近于学矣。今之号才女者,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噫!”(章学诚《妇学》)之所以说章学诚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主要是因为其观点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其一,章学诚敏锐地察觉到了某些男性文人颂扬女才背后的隐秘心理。一些女性由于从男性文人那里获得了肯定而对自己的才华沾沾自喜、有意炫耀,却不知男性文人之所以不吝褒奖,不过是出于某种不可言说的色情联想。作为正统文人的章学诚对此当然极为痛恨,况且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也曾论证过。
其二,某些女性文人的行为已完全违背了女性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发出的“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一种男性焦虑的体现,而此类不满的产生恐怕正与江南女性文人热衷于刊刻诗集、出游结社、拜师求名等社交活动有关。
清初江南地区的女性教育极为发达,为数众多的大家闺秀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即便是那些庶民家庭也会尽可能地为其子女提供学习的机会。当然,其动机未必一定是要培养出一两个才女,而很可能是出于更加实利的考虑。如《两交婚小传》中就分析了何以扬州城的小户人家也争先让女儿接受教育的现实原因,“却说扬州,古称广陵,从来繁华,又兼世际太平,一发繁华。服饰无非罗绮,饮食无非珍馐,触耳尽管弦之声,到眼皆佳丽之色。故人家的女子,自小儿便修眉画眼,扯鬓垂鬟,洗刷得如一泓秋水。到了十五六岁,虽只三分颜色,便已成十分美貌。故娶小置妾,皆以扬州为渊薮。初不过以容貌别妍媸为贵贱,到后来又以能吹箫、善度曲为贵。及吹箫度曲者多,则又以读得几首诗、写得几个字儿为贵了,一时成了风俗”(《两交婚小传》第三回)。从这些卖女为妾的小户人家的现实考量出发,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女子其商品价值显然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具备多种才艺会使其在美貌之外再增添若干的附加值。不管怎么说,出于将女儿培养成才的教育目的也好,出于增加女儿的商品附加值也罢,江南女子较为普遍地接受了文化教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那些有着良好文化传统的江南世族,其家族内的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动机相对来说则更为纯粹而较少世俗功利的熏染。这些大家闺秀们往往以才女自居,她们怀着朴素的愿望从事诗词写作,并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在文学方面有所造诣,有的甚至已然有意识地为女性争取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力。针对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女性不宜学诗”的世俗偏见,才女恽珠就在其所编撰的《国朝闺秀正始集》的弁言中辩论道:“昔孔子删《诗》,不废闺秀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纫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弁言)应该说,此类要求与男性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力的言论已然具有了颇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这种进步性对于整个男权社会来说却是颇为危险的信号。
不仅如此,这些知识女性并不仅仅满足于在笔尖上声讨一下,她们努力地突破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积极拓展社会活动空间,将其笔尖上的诉求充分落实到行动上。这些女性文人们普遍热衷于结社,甚至于拜男性文人为师,并且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女性文人群体,以徐灿为首的“蕉园五子”以及“随园女弟子”群体、常州词派女词人群体等都是清代前中期著名的女性文人群体。此外,女性文人将自己的诗词作品刊刻于世的行为也颇为普遍,“常州庄氏、阳湖恽氏、江都阮氏,太仓毕氏、如皋冒氏、常熟宗氏、言氏、邵氏、屈氏、泰州仲氏、华亭章氏等,这些家庭都有为数众多的妇女著作刊行”[1]491。应该说,此类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诸如“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之类的两性秩序,对这些正统秩序的强调在明清时期的家训、闺训、族规中被不断地重复着,诸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皆以居室为之限耳,古人不亲授受,不共浴,正所以避嫌也,为家而无以别之,男女杂处,则与禽兽无异矣”(《宋氏家要部》),“女妇日守闺房,躬习纺织,至老勿逾内门,下及侍女,亦同约束”(许相卿《许云屯贻谋》)之类的训诫可谓随处可见。
尽管传统两性秩序在以家训、闺训、族规为代表的正统言论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强调着,但这些知识女性的社交活动却充分地表达了她们对传统两性秩序是何等地不以为然,这又怎能不引起正统文人的不满呢?章学诚就在另一处文字中对女性文人漠视两性秩序的行为直接提出了批评,其中重点批驳的那位“无耻妄人”就是热衷于广收女弟子的袁枚:“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章学诚《丙辰札记》)。
通过以上对正反两方主要观点的列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初之于女性才学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女性是否应该作诗这一原初的范围。其实,女性要不要作诗,能不能作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性作诗这一现象背后所潜藏的深层次问题,即女性是否应该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力,以及如何应对赋权后的女性对现有两性秩序渐趋高涨的不满情绪,这才是“女才”问题的关键所在、核心所在。
男性社会之于女性才学有所关注当然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需明确的是,这种关注总是会带上某种自私的功利性。对于那些渴望浪漫情怀的才子来说,女性具备一定的诗才有助于其通过以诗传情的方式来实现“一见钟情”式的自由恋爱。对于正统社会而言,女性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显然有助于提升她们的道德操守,这一点即便在以家训、闺训为代表的正统言论中也得到了体现。如《女诫》中有言:“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内训》中有言:“夫人无姆教,则婉娩何从?不亲书史,则往行奚考?”《女范捷录》中亦有言:“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夫德以达才,才以成德……德本而才末,固理之宜然,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此外,《女范捷录》中还谈到了女性的才智之于治家的重要性:“治安大道,固在丈夫。有智妇人,胜于男子……妇人之明诚,诚可谓知人免难,保家国而助夫子者欤”。但颇为讽刺的是,赋权后的知识女性似乎并不总是以男权社会的期待为满足。尽管有一些女性依然在“女性不宜作诗”的性别偏见下压抑着自己的才华,认为写诗“非女子事,动辄不敢为,偶有小咏,即焚弃之”(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自序),但更有一些女性在知识所赋予的力量与信心的强大武装下,对男性社会为女性划定的条条框框变得越来越不满。
这些知识女性充满热情地展开唱和、结社、拜师、出游等多种社交活动,甚至也不再把针织女红当做女子的分内之事。《两交婚小传》中写到扬州“仕宦人家的小姐,皆不习女红,尽以笔墨生香奁之色,题咏为蛾眉之荣”(《两交婚小传》第三回),《飞花咏》则写到了才女容姑的母亲李氏对容姑终日舞文弄墨十分不满:“女子善于诗文,固是好事,但日后相夫宜家,亦必以女工针指,亲操井臼为本。若只一味涂鸦,终朝咏雪,纵然风趣,未免只成一家,转失那女子的本来,必须兼而行之,方为全备”(《飞花咏》第三回)。显然,有些才女已然无法再安心于传统社会为其规定的性别角色中,她们有了更为远大的人生追求。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曾不止一次地写到才女们幻想着突破生理性别的局限而直接变成男子,如才女山黛就曾自信地表示:“只可惜我山黛是个女子,沉埋在闺阁中。若是一个男儿,异日遭逢好文之主,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气,亦未可知”(《平山冷燕》第二回)。即便到了清中期,《红梦楼》中的探春也发表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这样的反性别宣言。当然,改变性别以建功立业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便有许多才女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凭借自己的诗文才华像“班姬、道蕴至今传诵不已”(《麟儿报》第十回),“倘腕墨有灵,且可流芳香于彤管,以高蛾眉之声价,尚别有机缘未可知也”(《两交婚》第三回)。她们有着成名的强烈愿望,渴望被关注、被认可、被赞美。“幽兰生于空谷,谁则知之?宝剑必悬之通衢,方有识者”“若尘埋于此,便是虚生此身了”(《宛如约》第一回),这正是一种才女焦虑的体现。
可以说,清初的江南才女们之所以热衷于结社、刻集、拜师等社交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以诗才立言、以诗才立名”这一愿望的展现,但此类有违于传统女性角色设定的愿望与行动显然突破了男性社会之于女性才学所做的那个颇为自私的功利性设定。更为可怕的是,“大凡知识女性,总是较一般女性更易于认识到自身的才能和价值,从而也更能深切地体会到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于是往往情不自禁地发不平之鸣”[3]43。她们之于自身性别角色所发出的种种“不平之鸣”总是时时透着一种女性自主意识的味道,而女性主体性的增强势必又会对两性秩序、男权社会造成潜在的威胁。这其间所蕴含的危险气息足以引发卫道士们的恐慌情绪。从这一角度而言,相较于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的私密心理,热心地吹捧才女的男性文人,章学诚的“政治嗅觉”倒是极为敏锐的。
对女学持保守态度的文人除了章学诚外,尚有吕坤、周亮工等人。吕坤在《闺范·自序》中特意强调,他之所以编写这部女教书,正是有感于“自世教衰,而闺门中人竟弃之礼法之外矣”“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闺门万化之原,审如是,内治何以修哉?”在吕坤看来,“闺门中人”“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的行为是有碍于礼教的。有的文人甚至认为女性识字本身就很有可能导致行止有亏,“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耻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6]。因此,女性还是不识字为妙,“《列女》《闺范》诸书,近日罕见,淫词丽语,触目而是。故宁可使人称其无才,不可使人称其无德”(周亮工《书影》)。此外,在上文中我们虽曾论及到了清初江南闺秀刊刻诗集成风,不过还是有许多闺秀不愿将自己的文字流诸于世。除了“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传统训诫外,盖与当时诗集(尤其是合集)的编纂体例有关,“盖自来刻诗者,《方外》之后紧接《名媛》,而贞妇烈女,大家世族之诗类与青楼泥淖并列”。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堪于与僧尼、青楼为伍的闺秀们宁愿“书而藏之,不敢付梓,并其名字,亦不忍露也”(周文炜《观宅四十吉祥相》之五,周亮工《书影》卷一)。此种编纂体例本身就说明了社会上针对女才的偏见依然存在。
以上正反两方面的言论同时存在于明清士人就女性才学展开的讨论之中,这也充分说明了男性文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矛盾心态。他们既希望女性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准和艺术修养,同时又希望文化的储备不要过分开启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精神。他们既希望这些才女们能利用自己的诗才让男性文人的情感生活变得更加风雅,同时又希望她们依然还能安心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之类的传统角色,而不是嚷嚷着开诗社、拜先生、刻诗集,坐着轿子满世界地跑。简而言之,他们希望女性的文化修养仅止于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满足丈夫、尤其是文人丈夫那更为精致的情感需求,更好地管理好家族事物,即完全为男权社会与家族秩序服务。“她所属于的那个领域,处处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闭、限制和支配:不论她把自己抬得多么高,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冒险,她的头上总是有一块天花板,四周总是有墙挡住她的去路。”[7]在对待女性才华这一问题上,期待与限制并存的矛盾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男性自私心理的反映。
男性文人之于女性才学的这种矛盾态度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得到了生动地体现,如《平山冷燕》中才女山黛的父亲山显仁一方面大力支持女儿读书,并将其培养成了一个“宛如一寒素书生”(《平山冷燕》第二回)的才女,但在另一方面又认为“小女闺娃识字”不过是“僭据斯文”而已。在男性文人的矛盾心态下,才女山黛本人的前后言行也跟着变得矛盾起来。尽管山黛刚出场时曾放出过豪言,“若是一个男儿,异日遭逢好文之主,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气,亦未可知”(《平山冷燕》第二回),但最终还是臣服在才子平如衡的脚下,并颇为懊悔地表示“才名为天地鬼神所忌,原不应久占”“今若觅得一佳偶,早早于飞而去,岂不完名全节”(《平山冷燕》第十九回),从此心甘情愿地退回到了传统的女性角色中。可以说,像山黛这样“通情达理”的才女才真正是男性文人所渴望的。因为她们既能给才子带来不少惊喜,又不会制造太大的麻烦。至于她们的才女脾气也大都是无伤大碍、无关大局的,并不会对男性尊严、两性秩序乃至于整个男权社会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她们的奋斗之所以为男性社会所接受,是由于她们最后并没有脱离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定位。”[8]才女们如果懂得自己的“分寸”,才子们当然也就不会吝惜于溢美之词。这不仅无损于男性的权力,反而显示了一种慷慨与宽容。
综上所述,男性文人对女性才华的赞美与推崇是否真正意味着男性之于女才的重视,女性才华是否真正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等问题想必应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解答。
[1]史梅.清代江苏妇女文献的价值和意义[M]//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2]王英志.随园女弟子考评[M]//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698.
[3]顾歆艺.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M]//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164.
[5]陈书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末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之一[M]//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338.
[6]徐梓.家训——父祖的叮咛[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333.
[7]伏波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44.
[8]刘靖渊,王晓骊.解语花——传统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12.
【责任编校朱云】
On the Independence of“Female Talent”of Novels of Gif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Lad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HI Wenfei
(School ofChinese Language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Shaanxi,China)
The“talented woman”complex showed by novels of gif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ladies wome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ackground of prosperity of“female tal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reflect the social concern to talentedwoman and the importanceof women’seducation.But female talent don’t have independent values,is always with some kind oferotic imagination and is limited to providemorequality“service”to themalesociety.The“talentedwomen”empowered by the knowledge aremore and mo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preset sex role being set in advance.A variety of ways of self display of talent also clearly revealed the taste of women’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the contradictory attitude of the male society to the female thus produced.
talentedwoman;female talent;independence;functional;autonomous consciousness
I206.2
A
1674-0092(2016)05-0046-06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10
2016-03-30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资助项目“近世白话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研究”(X2014YB11)
施文斐,女,满族,辽宁沈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近世白话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