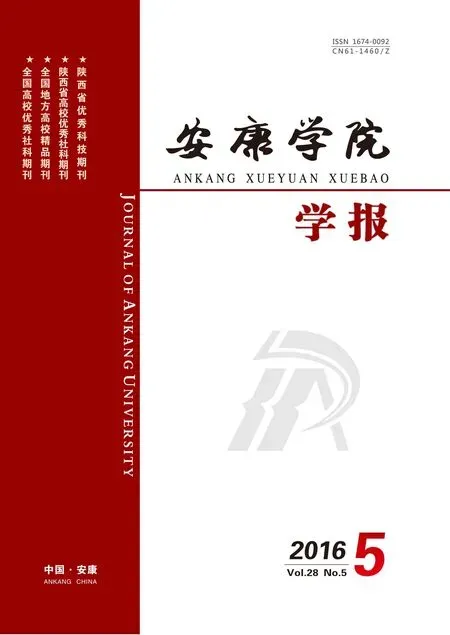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意蕴及其成因
李燕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意蕴及其成因
李燕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萧红是一位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女性作家。她的小说通过对女性生存困苦、女性社会地位卑微及女性生育痛苦、死亡悲剧的书写,反映了女性的悲惨处境及封建思想对女性的奴役和迫害,深刻描写和批判了男性对于女性人格和尊严的践踏,引起人们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对女性解放的思考。
萧红;小说;悲剧;觉醒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位有着极高创作天赋的作家。她的一生短暂凄苦,饱受苦难,然而正是这种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痛彻心扉的生命体验,使她的小说流露出浓重的悲剧色彩。萧红的小说侧重书写女性的苦难悲剧,但并非是自我不幸经历的再现和个人悲苦的抒发。作者基于个人的悲剧经历和真实的人物和情节,艺术地呈现了一个个在生存困境中挣扎、在生死边缘徘徊的妇女形象,从而表现了作者对扭曲人性、损害女性人格的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战乱不断、危机重重的中华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关切,体现了萧红深广的悲悯博爱之情。同时,作者也并未停留于悲观消极的态度之中,而是以抗争的态度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悲痛经历,追求着爱和温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一、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艺术内涵
萧红基于自己的人生遭遇和切身体验,着力描写女性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因而她的作品具有浓重的悲剧意蕴。小说《弃儿》,她就以自己的悲惨人生经历为原型,整部作品充满了悲哀的基调。作为一位命运坎坷的女性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揭示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残害和对女性独立人格、尊严的践踏,同时又流露出了女性自我抗争和精神思索的双重特性;另一方面,表现了女性生育时所遭受的痛苦磨难。
(一)女性生存苦难
在萧红的小说中,着重为读者呈现了女性为求得生存而艰难挣扎的场景,从女性的视角反映了底层劳动妇女的苦难命运。萧红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朴实的农妇王阿嫂为地主辛苦干活,到冬天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当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后,拖着已有身孕的身子将丈夫的尸骨“裹在衣襟里,并发出嚎天的哭声来”,悲痛淹没了她,但是迫于生计,她不得不继续为张地主劳作。张地主嫌她干活不灵活,狠狠地踢了她一脚,导致王阿嫂和还未出生的孩子离开了人世,这样一个贫困的妇女被地主阶级压迫致死,结束了她悲苦的一生。萧红以自身经历为基础,描述了一个劳动妇女的苦难生活,反映了她对于阶级压迫的痛恨。
在《生死场》中,萧红描写了在贫苦的生活中,东北乡村女性们艰难求生的场景,她们受到来自男性和传统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王婆为了生存嫁了三次人,年轻时年幼的女儿死了,年老时儿子又被抓去枪毙,绝望中的她没有了生存的勇气,选择了自杀。在生存面前,女性放弃了很多东西,包括最为珍贵的贞操。金枝因为生计来到哈尔滨谋求生路,做起了缝衣婆,但是最后连这机会都没有了,她为了生存用肉体赚了一元钱。忍受屈辱的金枝将赚得的钱交给母亲时,母亲并没有对她产生关怀之情,母性的无私荡然无存,反而让女儿回城继续给她挣钱,变得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让人惊愕。现实生活的贫穷、男权社会的压迫使无私的母爱被消解了,母亲不再是孩子可以依靠的港湾,而成为了没有母性的灵魂。忍受着贫病的煎熬,缺乏充足的物质,《生死场》中的母亲更关心的是物化东西。王婆将三岁的孩子不小心摔到了铁犁上,孩子不幸死亡,然而在她看来麦子的价值显然要高于孩子的生命价值。这些生存意识完全超越了人类的亲情,人们能忽视掉子女的突然死亡,却不能忽略生存中的物质基础,流露出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轻视和对死亡的漠然态度。在《生死场》中,子女的生命都不如一棵菜,或者一株茅草,生存的价值显得如此的虚无飘渺,这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悲剧。
(二)男权社会下女性卑微的地位
鲁迅曾说:“女人只有母性、女儿性,却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的,社会制度造成的。”[1]自古以来,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从来没有被当做独立的人,一直都被认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时刻都应遵从“三从四德”的古老祖训。在那个以男性为主的时代中,萧红的出生并不被家人期待,反而使全家人都感到失落,尤其是老祖母,特别懊丧。这让萧红在家中备受冷落,直到小弟弟出生时,全家人高兴异常。同时,也促使了家人,尤其是祖母、父亲对萧红更加冷淡。萧红对中国广大劳动妇女处于被冷落、折磨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深入和无情的批判。在萧红的小说中,男性的粗暴、冷漠、残酷使女人陷入悲凉的生存处境。而作为底层社会的女性,受到来自男权尤其是夫权的压迫,都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也都走不出男权压迫的阴影。更可悲的是,她们都没有为争取自身自由和幸福而进行反抗的意识。女性没有作为人的尊严,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没有了生命价值存在的意义。
男权社会给予男性压迫女性的权利,可怕的是,女性自己却默认了这种被奴役的命运,成为集体无意识,妇女的命运在被虐和自虐的两重迫害中沉浮,且女性作为一种性别弱势群体并未获得男性的尊重和爱。在《生死场》中,金枝给人的形象是:“好看”“油亮亮的辫子”和“有力气”。然而,对于成业来说,金枝只是一个有价值的猎物。她的美貌可以满足男人的欲望,她的力气还可以承担农村的体力劳动,成业对金枝并没有多少爱,只是占有与催逼。因而,在金枝的内心深处,承受着心灵的空虚和肉体的痛苦。这正是作者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倾注到金枝身上,才使金枝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怜爱又令人惋惜。在《生死场》中,另一个受男权主义压迫的女性是麻面婆,在她看来自己天生的命运就是服侍男人。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在二里半的内心中,认为麻面婆就是他的仆人和使唤的工具,并没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由于长时间的受到男权社会的压抑和封建思想的浸染,女性已经形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思维模式,对男性的压迫长期保持沉默。不但对自身的悲惨命运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被这种思想浸染后的女性,也成为封建思想的卫道士,从而变本加厉地折磨同类,这种循环往复的模式造成了中国妇女的命运悲剧。在《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就因为长得大方、不知羞,婆婆为了让她能够遵循封建传统道德规章,对她进行毒打,街头巷尾都能听见她凄惨的叫喊,最终她被打病了。愚昧无知的人们却认为她被妖魔附体,将她放在滚烫的水里洗澡治病,最终使团圆媳妇丧失了性命。漂亮的王大姑娘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磨官冯歪嘴子在一起并有了孩子,却被众人奚落,直到死去。作者正是通过叙述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两位女性的悲惨人生经历,控诉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男权主义社会对女性自由的扼杀,表现出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深层次地映射出女性悲剧意蕴的内在文化根源。
(三)女性生育痛苦与死亡悲剧
人类繁衍后代的重要行为是生育。然而,在萧红的小说中,生育却变成了一种“刑罚”。在《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描述了一个独特的生育世界,展现给读者的是血肉模糊、无法忍受的疼痛,甚至一些妇女还因此走向了死亡,女性繁衍的伟大行为被称为“刑罚”。女性的生育只被认为是一个生殖符号,是附庸于男性的生育工具,并未受到男性的重视、爱护。萧红对于生育充满了恐惧,这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关,她每一次怀孕都会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无止境的心理负担。这种身体与心灵的反复割离让她痛苦不堪,使萧红内心深处感到孤独和绝望。
萧红以自身的痛苦历程,在人文情怀上关注着女性命运,展现出女性怀孕和生育时的恐惧、疼痛和鲜血的折磨,反映了她们的生存困境和心灵创伤。在《王阿嫂的死》中,萧红这样描写这位农村妇女的生育情景:“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2],深刻地反映了女性孕育时的深重苦难。女性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因而生育后成为母亲的女性更为神圣美丽。然而,在《生死场》中,她把动物的生育与人的生育放在一起,生育变成了纯动物性的繁殖,是没有爱的行为。当母猪产下小猪、母狗生出小狗时,王姑姑的姐姐在难产中痛苦分娩,丈夫却还呵斥她,甚至还给她泼了一盘冷水,最后作者说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反映了女性痛苦的生育状态;金枝怀孕后变得行动不便,便遭丈夫骂,并且在丈夫欲念的行为下难产;二里半的妻子李二婶在哭喊里小产了,却丝毫没有得到男人的关心。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不知不觉中生育、死亡。”[3]承担着生育神圣使命的女性被男人们轻视甚至打骂,没有了作为母亲的尊严,甚至成了罪人,这是多么痛苦并且没有意义的生育苦难。
海德格尔说:“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4]在萧红小说中,许多女性也都遵循这一规律,即都经历着生育、疾病、衰老和死亡,且都无法避免。《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在生育中死亡,新生儿也在出生后五分钟内死亡;《生死场》中,不到一岁的小金枝被暴怒的父亲摔死,在父亲看来这小女婴的生命是毫无价值的;《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只因大方、不知羞,便被开水烫身治病,最终被虐待致死;《小城三月》里,翠姨在封建社会的伦常中,默默追寻自己的爱,却最终因爱而死。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死亡的普遍性和对生命毁灭所持有的惊人的麻木态度,体现出了生活上的悲剧,充溢着浓郁的悲剧意蕴。
二、萧红小说女性悲剧的成因
作品的悲剧意识,是作家对生活悲剧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审美形态,并通过创作把这种审美意识及悲剧意识艺术地叙述出来。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她们通常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书写着生命的悲歌,寻觅着生活的本真力量,传达了一种对生命短暂局促的悲剧性体验,继而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触动,引起人们对生命的重新审视和思考。
(一)个人的悲惨经历
萧红小说中对女性悲剧的反映及其悲剧性思想的形成,与作者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她的这种悲剧性意蕴,主要来源于作者童年时期的寂寞与孤独。探究萧红的成长经历,会发现她一生流离失所、受尽生活的种种磨难。尽管儿时有外祖父的关怀,但还是缺少家庭的关爱,在生活中受尽了别人的冷落与排斥。成年之后,为了追求自由,躲避包办婚姻,逃离了家庭。迫于无奈与未婚夫同居,最终却被抛弃在旅馆中。这时期还经历了几次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乱,辗转各地。生活上残酷的打击,形成她悲观的个性,使她对人生产生深深的怀疑与失望,尤其是爱情理想破灭,成为她悲观思想意识的来源。
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不同凡响的情感历程,使萧红有了直面现实人生的巨大动力,然而在她内心深处总有着无法遮饰的无家可归的孤独和失落感,以及对命运的无奈和悲凉之感,以至于她说出:“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里要一个人走路似的”。[5]另外,由于这种成长经历,萧红的作品也常常流露出一种对生死麻木轻视的态度。《呼兰河传》中,她以平静的语调叙述着“生存”的民众对生与死的麻木态度,这种冷漠才是人性更大的悲剧。与《呼兰河传》中死亡不同,在《生死场》中,作者通过围绕生死这两个人生必然经历进行剖析,体现了她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感悟。正如评论家所论:“萧红是带着沉重的人生枷锁走上文坛的,她短暂的一生受尽了家庭、社会、个人的磨难。这样的个人经历加剧了她的悲剧感和人生忧患,所以她笔下的故事大都是满含苦难,表现了她对人生的总体感受。”[6]
(二)封建势力残害
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女性总是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萧红也是如此。她儿时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不被家人所重视,在呼兰小城度过了自己孤独、寂寞的童年。后来为躲避封建家庭的专制而逃离家庭,最终以失败告终。无奈中又回到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受到舆论的压力和家族的歧视,被囚禁于阿城福昌号屯中,行动受到限制。在被软禁的这段时间里,她看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之对整个地主阶级更加憎恨。萧红将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转化为今后创作的资料,有关抗日的作品《生死场》,其中很多原型和地名都是从这而来。自身受到压迫,使追求独立自主和个性解放的萧红,阶级意识更为明确,最终走向了与封建地主家庭彻底决裂的道路。
离家后的萧红,对腐朽的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觉得这个社会本身就是残酷黑暗的,更何况是生活在这其中的普通百姓。深度压抑导致的内心痛苦和仇恨,使萧红对人生理解的越来越透彻,使她对封建专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也看的更为清晰。她将自己的主体经验融入到她的文学创作里,使她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丑恶黑暗的社会现实。萧红处在动荡的时代,在悲观和绝望中漂泊,战乱、流亡等等经历,引起她对民族危亡的忧患和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思考。
(三)社会现实的影响
萧红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意识,她经历了五四运动前后两个时期,革命的浪潮冲击着她,使她萌生出了强烈的觉醒意识,渴望着男女平等和思想解放,尤其作为女人应该有追求属于自己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因而,作者不由自主地扛起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大旗。在中学时期,受到左翼老师先进思想的影响,加上大量地阅读进步书籍,为她今后的写作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同时使她思考问题的高度也提高到民族危亡的层面上。在《生死场》中,作者通过对比手法,描述了普通劳动人民在“九一八”前后的精神生活状态,“九一八”事件前人们忍受着贫穷的折磨和愚昧思想的蹂躏;而在“九一八”事件后,民众从亡国的麻木状态下逐渐清醒,开始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兴亡担忧,从而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思想,而这也正体现了作者对民族悲剧命运的思索。在《呼兰河传》中,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呼兰河城中生活的民众呈现出冷漠、麻木等病态精神特质。他们漠然地看着别人的苦痛生活,从而消解着自己悲凉的内心世界。旧的封建制度扼杀着普通大众的身体和灵魂,使人们始终处在痛苦的生活状态。于是萧红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这些病态的民族灵魂,使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被颠覆,民族精神被磨灭。萧红带着悲缅的心态创作这一系列小说,从而审视民族的深重苦难和普通百姓尤其是女性的痛苦生活状态。女性作为最底层的受压迫者,她们的生存境遇无法得到改变,总是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萧红通过对女性悲剧的书写,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从而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和尊严。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在民族危亡和普通百姓的痛苦生活状态的现实中,使其对悲剧意蕴的阐释更加丰富和全面。
三、结语
萧红漂泊一生,临终时曾说:“我一生的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7]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她对于自身悲惨命运的哀叹,也体现了她对广大女性悲惨处境的怜悯。萧红以她独有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身心感受,刻画了女性在特殊时期的生存状态与过程,描绘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悲惨生活处境,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生命悲剧。然而,作者并不是要使男女关系对立,而是要让女性有勇气面对自身的悲剧命运,使社会重新认识两性间的关系,化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期待一个男女平等的新格局,这也正是萧红小说中女性悲剧意蕴所含有的深层次意义。
[1]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58-159.
[2]萧红.萧红作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3]萧红.生死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罗松涛.向死而在—试论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层面上对死亡的思考[J].兰州学刊,2006(6):22-26.
[5]李宗超.论萧红作品女性意识中的孤独情怀与抗争精神[J].菏泽学院学报,2013,35(3):37-40.
[6]周艳丽.略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3):142-144.
[7]黄晓娟.萧红的生命意识与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57(5):540-545.
【责任编校龙霞】
The Tragic Im p lication of the Fem ales in Xiao Hong’s Novels
LI Yan
(School ofChinese Literature,Shaaxi SCI-TECH University,Hanzhong723001,Shaanxi,China)
Xiao Hong is a female writer with a strong tragic color.Through the survival hardship,the humble social status,the pain of childbirth and the death tragedy of females in thenovels were described,it was reflected that slavery and persecution of females was due to tragic situation and feudal ideology.In addition,it was deeply described and criticized that the personality and dignity of female were trampled bymales,draw attention towomen's living condition and thoughtson the ofwomen's liberation.
Xiao Hong;novel;tragedy;awaken
I206.6
A
1674-0092(2016)05-0052-04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11
2016-03-23
陕西理工大学2016年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新世纪文学底层写作研究”(SLGYCX 1601)
李燕,女,陕西周至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
——萧红《生死场》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