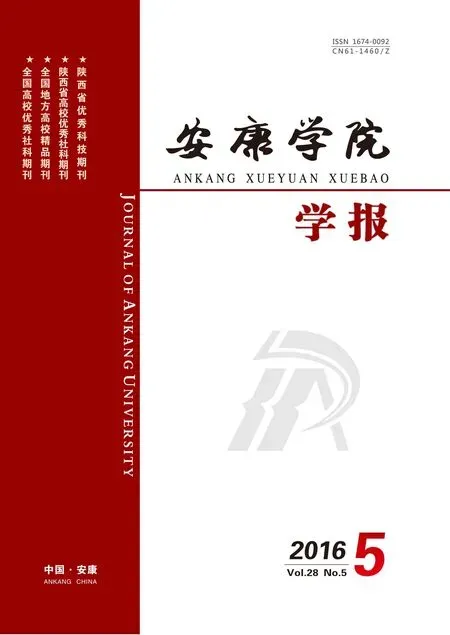温情与悲凉的双重书写——探析《群山之巅》中民间情感的书写
贾晓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温情与悲凉的双重书写——探析《群山之巅》中民间情感的书写
贾晓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迟子建的新作《群山之巅》,透过众多小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命运书写,将温情与悲凉相结合,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北疆世界一隅的民间情感画卷。作者通过民间语言、意象书写的融入以及双重批判方式的结合,凸显了文本中民间情感的特征,即在神性与隐秘的世界中,温情与悲凉的情感交织,展现别样的风景。
《群山之巅》;民间情感;温情;悲凉
探讨民间情感,要从民间这一概念入手。陈思和教授在《民间的还原》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学的民间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指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第二是指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由于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的态度,使这些文学创作充满了民间的意味。”[1]也就是说,民间是具有自身生命力,不受外在影响的审美世界。
在《群山之巅》这部小说中,迟子建站在民间立场上,将温情与悲凉相结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北方龙盏镇一群小人物的民间情感画卷,他们“在群山之巅的滚滚红尘中浮沉,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寻找出路”。本文从文本的民间情感表达入手,来分析迟子建民间情感书写的特点。
一、民间情感的书写
《群山之巅》展现了龙盏镇众多小人物命运浮沉的悲凉之感。以往的评论总是认为,迟子建书写的民间情感缺乏理性与沉重的批判意识。而《群山之巅》在表达细微的传统民间情感的同时,作者针对现代经济社会的批判意识有所增强,更加凸显了作者自身的思想情感。
(一)人与自然的情感书写
人与自然的情感必然包含在民间情感之中。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关注到了人与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和冲突迭起,龙盏镇的小人物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内在情感体验。
1.温情:和谐共生
与自然和谐共生,较为集中的体现在老一辈人身上。他们的情感不是故作姿态的表现,而是不经意间的流露。他们在传统生活语境中,表达着对自然的热爱和崇拜。
小说以辛七杂太阳取火抽烟作为开篇,一下将文本写活了。“他说用太阳火烧的烟斗,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值得等待。”在追求效率的时代,辛七杂却以较为原始而平静的生活方式存在,太阳火的芳香正是自然气息的延续,他追求的是人类自然原生的状态。
作为鄂伦春人的后代,绣娘将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表达出来。绣娘在上山打猎开始之前,总要以酒来敬奉山神。她“喜欢冬季骑马打猎,夏季去河里叉鱼。”尽管已经处于现代社会之中,绣娘依然保留着较为原始的传统生活状态。这一形象让我们联想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乌娜吉。“对迟子建而言,老妇形象常常作为变与不变的辩证隐喻出现。也就是说他们用一生的经验、经历去抵制时代对人心的影响。”[2]她们二人正是与乡土血脉紧密联系的人物形象。乌娜吉在众人搬下山去居住时,她和安草儿永远驻足山上;绣娘则是随着自己的白马风葬而离开人世,“绣娘在白马上,好像仍在驾驭着它,在森林河谷中穿行”。绣娘对自然的崇拜之情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但是与自然和谐与共的情感终究难以逃脱现代化的进程。
2.悲凉:冲突迭起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乡镇也在急剧变化,镇长唐汉成却在与全球化的速度相抗衡着。他对龙盏镇的热爱似乎是无人可敌的,“他在山里长大,热爱大自然。每当他疲惫地回到青山县,看见山,看见清澈的河流,呼吸到新鲜空气,他的血流就畅通了,一路的风尘也被洗去了”。对于资源的开发,他有着自己的理解:“破坏资源的发展,就跟一个人为了抵御严寒,砍掉自己的腿当柴烧一样,会造成终身残疾”。为了保护龙盏镇的资源,在旧货节上,他用鄂伦春马换取辛开溜一篮无烟煤,又在斗羊节上让“黑珍珠”偷袭发现资源工程师。这一切背后的目的只是想要保护龙盏镇的生态环境,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徒劳。
龙盏镇依然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水里的鱼和山上的野兽一样,连年减少,成了黑夜尽头的星空,很难发现闪光点了,渔猎工具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摆设”。因为虫灾而进行人工打农药,使得龙盏镇的动植物都处在萎靡的状态。其实龙盏镇悄然的变化,已经不断激化了人与自然的危机。最终无数的矿藏还是被发现,而被发现的结局必然会是无节制的开采。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书中,迟子建表达了森林被破坏的无奈之感,表达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法减缓资源破坏步伐的悲凉之感。在《群山之巅》中,不论是人与自然情感的和谐共生,还是冲突迭起,都体现了作者本身对自然的观点,即:尽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的情感与敬畏仍然存在,但是她对当今社会无法减缓这样的进程又流露出无奈之感。
(二)人与人的情感书写
在迟子建的笔下,人性恶的一面往往被温情的笔触消解掉,所以在她创作的小说中,难以看到罪犯、恶人被严格的惩治,也难以感悟到迟子建对人物的严厉审判。在《群山之巅》中,众多的小人物人性善恶交织,她也不再一味温情泛滥、缺乏节制地对待底层民众的人性恶习,而是在温情中感动,在悲凉中批判。
1.温情:细微处的动情
迟子建透过这部小说隐含的表达了“每个卑微的灵魂都有梦想,在纷繁芜杂的世界寻求精彩”[3]这一主题。作者聚焦于民间情感的细微之处,刻画小人物卑微的灵魂,展示其动情之处。
在法律层面,辛欣来必死无疑,但是新生命的诞生,使众人原谅了他的罪过。“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4]甚至作为直接受害者的安雪儿也原谅了辛欣来。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乡土社会的“道德机制”;另一方面,也说明安雪儿在神性消失之后获得了“爱情”,她会因为父亲找到辛欣来而流露微笑,也会因为他的一颗肾还活着而冒着风雪去土地祠。安雪儿内心情感的变化是在她不多的言语和表情中展现的,正是细致入微的刻画,让读者感受到温情的力量。
迟子建笔下的爱情故事,是真实的,是充满生活意味的。安平与李素珍的爱情由两双手展开。“他们的手被人冷落惯了,一经相握,如遇知音,彼此不愿撒手。”她没有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其评判,而是以平等的身份来审视,将爱情的态度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底蕴深处,表达他们最素朴的感情。二人是在饱受了苦难之后的灵肉和谐,是亲情般的爱情,但是这样的爱情却因为丈夫的意外死亡造成了李素贞的胆怯与退缩。尽管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悲凉的气氛,但作者还是留给读者希望,为二人最终的爱情归宿留下了一个悬念。
2.悲凉:罪恶中挣扎与消失
在访问中,迟子建曾说:“我在这部长篇里,着力描写了几个矛盾纠葛中的人物,他们挣扎在人性的泥淖中,双足在恶之间,可是他们向往岸上人性纯美的花朵,于是他们挣扎,写他们的挣扎,写人性恶中像祈求月亮一样地向往善,领受它的光明,对我来说是心动的”[5]。最为典型的就是唐眉这一人物的塑造。唐眉医学院毕业后,留在龙盏镇,独居在环境破败的西坡,做军官的情人等一系列异常的行为,是唐眉永远无法摆脱的沉重的十字架压迫所致,她竟然是给自己朋友投毒的人。这样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为了摆脱内心的罪恶,她竟然做了绝育手术。这是北疆世界中令人心惊胆寒之处,在最靠近太阳的地方,人性阴暗面被揭露无遗。但是,他们并不完全泯灭了良心,因为内心的罪恶,让他们在泥淖中挣扎,只能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减缓内心的不安。
在《群山之巅》中,作者表达了“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成为世外桃源,罪恶一样会抵达鸟语花香之地。作为作家,关注时代和社会生活,写它的病,是希望它健康”[6]这样的反思。如果说唐眉这类人还在泥淖中挣扎,那么迟子建更为深入地“直面现实,亮出了批判的锋刃”,消解充满温情与诗意的北疆世界。“民间的善具备更大的力量,它天然的具有一种宽容的力量。”辛欣来的罪恶在发展中不断被消解,换来众人的同情和谅解。如果说民间情感给予他的是同情,那么陈家的灾难则是民间情感的深刻批判。“陈金谷的两颗失去斗志的肾,就像潜伏在身体里的两个叛徒,把他推向了生命的悬崖,让他看到了平素见不到的风景。”陈金谷住院需要肾源,面对难以配型的肾,陈家人竟然除了唐眉其他人都拒绝捐献。陈庆北的不择手段以及陈家最后的败亡,都让我们看到了群山之巅“别样的风景”。
民间情感中最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也是不断变换的。在不断发展中,人与人的亲疏离合都会展现出来,小人物尤其是底层百姓的善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关注到了喧嚣时代的罪恶和腐败,在书写故乡风土民情的同时,也能与现实对话。温情与悲凉的双重书写,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世界描写得更为复杂与深刻,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挖掘其中的罪恶。
二、民间情感书写的特点
《群山之巅》中,作者在原有书写民间情感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以更为出色的笔致构筑民间情感的画卷。
(一)民间语言的融入
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视语言,她说“一部小说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成色”[7]。迟子建小说总是在素朴的语言之中,透射出独特的光芒。首先温情与诗意融合。在王秀满去世后,辛七杂去金素绣家买油,“她看到夕阳中的辛七杂果然瘦了一圈,但他瘦得比以前精神了,腰直溜了,显得挺拔,而且眼睛里多了一种东西——悲伤中的柔情,分外动人”。寥寥数句,却将金素绣与辛七杂的中年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是金素绣心疼辛七杂,一方面凸显出她心中对辛七杂的爱意。
迟子建“描写琐碎与庸常却不止于琐碎与庸常,原料不是山珍海味,她却用最精细的刀法,最完美的火工和最优质的调料制作一道道风味独特有滋有味的佳肴,赏心悦目。”[8]她用比喻拟人这样的手法,在产生诗意的同时又带来了陌生化的效果。“阳光灿烂的夏日,凸透镜瞬间就把火给他盗来了。”一个“盗”字就将凸透镜拟人化,一个“盗”字就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盗火拯救众生,其中就有了轻松而戏谑的成分,语言极具张力,给人更多想象空间。
迟子建崇尚朴素的语言,但是在朴素语言背后却隐藏着无形的力量。“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文本末尾以这样的一句无奈之语结尾,震撼心灵。迟子建自己也说在写到最后一句时,有一种“莫名的空虚和彻骨的悲凉”“我的心是颤抖的”。整个故事以辛七杂独特的取火方式这样充满意趣的场景开篇,却以风雪飞舞中安雪儿无奈的呼喊结尾,这样的语句中隐含着无形的力量,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最后归于的只是无人听见的呼唤,悲凉之感油然而起。正是朴素而又充满力量的语言,为文本构筑了温情与悲凉结合的民间情感世界。
(二)意象书写的融入
文本众多意象的书写,为民间情感的表达增添了诗意,凝聚了民间情感的精神内涵。
批评家雷达先生首先关注到了迟子建小说中意象的使用,他曾在《逝川》发表后,评论到:“世间是否真的有‘泪鱼’,我不详知,但这一意象太美了,太神奇了”[9]。在迟子建笔下的意象总是充满了唯美色彩,使得叙事作品有了诗一般的意境。
杨义先生指出,意象是“借助某个独特的表象蕴含着独到的意义,成为形象叙述过程中的闪光的质点。但它对意义的表达,又不是借助议论,而是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意义蕴含于其间。意象作为叙事作品中闪光的质点,是之在文章机制中发挥贯通、伏脉和结穴一类功能”[10]。《群山之巅》中有诸多通过意象来表达民间情感的情节。在阅读感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多次出现的意象,如月光、太阳这类自然界的普遍存在。尤其是月光的书写,是文本中较为出彩的地方。月光的描写语言不断地变换,折射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以及人物内心的变化。
迟子建笔下的月光这一意象,带有多重意蕴。月光作为自然意象,必然成为了人与自然民间情感的承载体。安雪儿独自住在龙盏镇的北口,一个偏僻的地方。她说:“夜里有月亮和星星,它们的脚长,能跳过窗子,跟我一起躺在枕头上,陪我睡呀。”安雪儿作为龙盏镇神性的象征,她能与月光对话,这里的月光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代表了神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月光不单单是自然层面的意象,也代表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安大营在林大花被带进小白楼的那一夜,“月色皎洁,他甚至看到了清月面上的阴影。他想太阳也是有阴影的……而月亮的背景是黑暗的,所以它光明中的阴影,在夜晚会像花朵一样绽放”。月色明亮的夜晚,安大营看到的却是黑暗,那里的黑暗更多的是象征军队的黑暗,象征他目睹阴暗面的失望之感,展现出民间情感中的现实困扰是难以解决的。
《群山之巅》中的意象纷呈,如“肾”“毛边纸画”“暴风雪”“土地祠”等等。正是众多意象的塑造,使得叙事文本充满了诗情画意,更为重要的是凝聚了作品的精神力量。作者编织出来的充满温情的民间情感,让读者在乡民的愚昧冰冷的态度中感受到了单纯而明亮的质点。
(三)温情与悲凉的批判相结合
《群山之巅》不再是无休止、无节制的“温情批判”,迟子建在这方面做出了进步。她站在民间立场关注底层百姓命运的同时,对人性恶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迟子建曾说过:“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性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他们也许会有种种缺陷,但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人性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才是值得永久书写。”[11]《群山之巅》中仍然存在着有缺陷而又有神性的乡民。不论是安雪儿破身之后,众人将她众口一词地从神坛拉到现实之中,还是众人都厌弃安平的一双杀死无数人的手等等,无不是悲凉的。但是在新的生命毛边诞生之时,众人的善良又显现出来,他们不会因为毛边的身世而鄙夷这个孩子,而是十分的呵护、喜爱。辛开溜因为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他的一生都背负着逃兵的恶名,即便是在死后的灰烬中发现弹片也无人相信辛开溜是一个抗战老兵。而在旧货节上,民众就会自动抹去他的恶名,使其获得平等的尊重。正因为迟子建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作为民众中平等的一份子来书写民间情感,因而她能深入乡民的内心生活,审视自身存在的社会,分析乡民态度的某些合理性。对这样的一类人,她依然坚守着温情的批判。
近年来,迟子建的小说中增加了黑色的力量,不再是仅仅以温情来解读世俗人生。《群山之巅》“让神灵之地升起人间烟火,让天使落入滚滚红尘,不是作者的主观愿望使然,而是生活本该如此。”[12]文本中塑造了在人性的救赎中挣扎的人,还有罪恶深重的人。辛欣来因为嫉妒安家的英雄,嫉妒安雪儿的神性,而做出了泯灭人性的行为,“报复同时还是嫉妒心理的一种延伸性的发展,这种心理是处在弱势的个体对某一方面比自己优越的他者的一种不满,甚至是仇恨”[13]。正是这种嫉妒和报复心理,使得辛欣来犯下了错误。这种民间情感其实是很常见的,但辛欣来却以极端的方式实现快感。文本中众多新闻事件的穿插没有显得过于突兀,反而与这些小人物更好地结合起来,包括唐眉的投毒事件。也正因为这些新闻事件的存在,使得这些人物的描摹更加真实,心理的刻画更加生动。
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将温情与悲凉的笔调相结合,一方面在温情讲述龙盏镇民间情感的温暖与冷漠,另一方面以悲凉的情感基调深入人性深处的罪恶灵魂,把握挣扎在泥淖中的心灵。
三、结语
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以屏风式的结构,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民间复杂情感的画卷。她用温情与悲凉相结合的笔致,以民间情感书写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复杂关系。通过民间语言、意象书写的融入以及双重批判方式的结合,凸显了文本中民间情感的特征,即在神性与隐秘的世界中,温情与悲凉的情感交织,展现别样的风景。作为迟子建“写作黄金年华”的起点,《群山之巅》以独特的魅力展示北疆世界一隅的民间情感,为迟子建以后的创作开启了新的征程。
[1]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M]//李东,李禾.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59-79.
[2]徐勇,王迅.全球化进程与“中间地带”的“乡镇写作”——以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为中心[J].文艺研究,2015(9):66-72.
[3]陈华文.立于群山之巅的文学美意——迟子建新长篇小说《群山之巅》读后[J].出版广角,2015(4):115-116.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7.
[5]欧阳澜,汪树东.边地民间的人性风景——评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3):23-28.
[6]顾佳琪.《群山之巅》中“傻子”形象及其功能的转变[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15(2):55-59.
[7]崔华林.迟子建:“群山之巅”的心灵史[J].齐鲁周刊,2015(5):50.
[8]李莉.论小说意象蕴涵的“气味”——兼谈迟子建小说[J].文艺评论,2004(3):58-63.
[9]方守金.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04.
[10]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76.
[11]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J].小说评论,2002(2):35-37.
[12]程德培.迟子建的地平线——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启示录[J].上海文学,2015(3):105-112.
[13]任诗桐.论迟子建小说的民间立场[D].长春:吉林大学,2011.
【责任编校龙霞】
On the Folk Emotions Described in The top of mountains
JIA Xiaomin
(School of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The top of mountains is newly published length novel by Chi Zijian,which focus on building ordinary characters’image and fate.The novel presents the folk emotion of the Chinese northern border areas for readers.By folk language,imagery and written into the dual combination of criticism of theway,the author highlights the text of folk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Namely,in world of the divinity and hidden,warmth and dismal emotions are intertwined to show another scenery.
The top ofmountains;folk emotion;warmth;dismal
I206.7
A
1674-0092(2016)05-0056-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12
2016-04-06
贾晓珉,女,河北涉县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