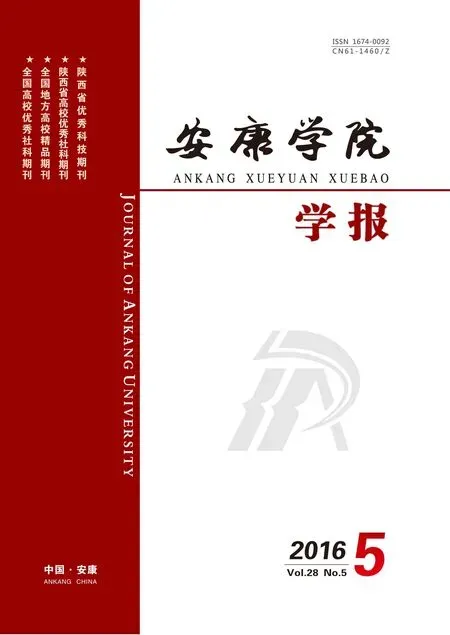罪与罚——探析《店员》与《罪与罚》中的信仰回归之路
辛睿思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罪与罚——探析《店员》与《罪与罚》中的信仰回归之路
辛睿思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马拉默德《店员》中的弗兰克·阿尔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都经历了人性堕落到精神重生之路。犹太教精神和东正教精神在二者的人性回归之路上分别起着重要作用。从中不难看出,这两位作家对生存意义的理解与宗教信仰不可分割,他们都希望通过宗教信仰实现精神救赎和再生,不断为现代人找寻着救赎干涸灵魂的精神出口。
《店员》;《罪与罚》;信仰;马拉默德;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最富于宗教精神的作家之一,有人称赞他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伯纳德·马拉默德(1914—1986)被认为是美国文学中最具“犹太性”的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年代的不同国度,但探讨民族的生存现状,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类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占重要地位。他们寻求生活意义的主题往往和道德、责任以及苦难的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罪与罚”这一主题在马拉默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典型的体现。本文拟通过分析《店员》与《罪与罚》,分别探讨主人公犯罪的原因、惩罚的路径、精神重生的根本,以便对马拉默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人道主义的异同有更深地理解。
一、犯罪:人性迷失
《店员》中的弗兰克·阿尔拜与《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两个年轻人在最美好的年纪却犯下了严重的罪过。读者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和发问,他们为什么会犯罪?本文认为,他们走上犯罪之路既有外在的现实原因,又有人物内在的缺失。其中犯罪的主要根源就是信仰的缺失。
20世纪初,哲学家尼采提出“上帝死了”,指出以往西方人精神所寄托的“上帝”已经不存在了。他否认了上帝,就是否认了过去西方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的最高标准。尼采的观点反映了西方现代人深刻的信仰危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灵魂的依托,成了“灵魂漂泊者”和“精神孤儿”。《罪与罚》和《店员》都为我们展现了信仰沦陷下的社会图景。
《罪与罚》讲述了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为贫困所迫去谋杀抢劫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拿她的钱去周济穷人。并且在犯罪的过程中,杀害了无辜的案发现场见证人,善良的丽扎韦塔·伊凡诺夫娜。作案后,拉斯科尔尼科夫收拾好一切,逃离了犯罪现场。返回自己冰冷阴暗的蜗居后,他的内心陷入了疯狂的斗争中,一场善与恶的交战激烈地持续着,直至他在索尼亚的劝说下向警察自首,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描绘了一幅“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的社会图景。作者对信仰沦陷下的社会黑暗,下层人民充满苦难的痛苦命运进行了揭露。在缺失信仰的时代,无论是挣扎在社会底层、受尽痛苦的小人物马美拉多夫,还是物质丰富、追求享乐的地主斯韦德理加依洛夫,亦或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拉斯科尔尼科夫,人人找不到生存下去的意义。他们游荡在混乱的社会中,精神空虚,迷失自我。拉斯科尔尼科夫付不起学费,交不起房租,找不到工作,他首先面临的是最根本的生存问题。当他踌躇街头,看到的尽是满目凄凉悲惨的社会景象。如何面对苦难?如何改变现实?如何拯救自己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此时,他想到了犯罪。似乎唯有犯罪,才可以找到生存的出路,才可以改变命运。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传统的基督教的信仰正被打破,精神长期处于困惑、迷茫、游离之时,主人公制造出一套特殊“理论”。这套理论是他犯罪的另一个根源。在他的思想中,“所有的人都被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帖耳地过日子,没有犯法的权利,不平凡的人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有权肆意犯法”[1]。相对于超人来说,其他人仅仅是铺向成功的通道,是为培育超人的田地施上的肥料,是实现超人目的的工具。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了证明自己是“超人”,是“命运的主宰”,不顾一切,甚至杀人。这是他犯罪的主要动因,也是他个人主义反抗的写照。
小说《店员》的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给当时的美国带来了破坏性的经济危机,美国社会腐败,经济混乱,一片衰败景象。此时的美国人正处于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的“荒原时代”。这一代的年轻人对政府不信任,对先前的各种学说和道德观十分怀疑,信仰处于动摇和空缺状态,弗兰克亦是如此。《店员》的主人公弗兰克是来自意大利的非犹太移民。在身份上,他既是一个孤儿,又是一个流浪者。弗兰克从小就失去父母,在孤儿院长大。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缺少来自父母和家庭的爱与温暖,缺乏正确的引导,这对他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弗兰克内在和外在的缺失,导致了他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没有家园没有归属的人。长大后,他怀着对“美国梦”的向往来到美国寻找出路。现实却与梦想大相径庭,他从西部流浪到东部,到处找不到工作,夜宿街头巷尾,忍饥挨饿。痛苦的现实生活使他萌生出一个荒唐的念头,即通过犯罪去改变命运。他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不同于一般的平凡的人,可以“干大事”。“如果去犯罪,他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惊险的事业,过着王子般的生活。”[2]96他想通过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犯罪,实现他的“美国梦”,摆脱自己窘迫的现状,满足他对于金钱、女人、地位的欲望。于是,他与沃德·明诺格合伙抢劫了莫里斯的店铺。至此,弗兰克完全与上帝之路背道而驰。没有向善的信念,没有崇高的信仰,在欲望中迷失自我,人性堕落到底层。尽管他觉得抢劫是件愚蠢的事情,在抢劫过程中他的内心也进行了强烈的善恶挣扎,但他还是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内心走向了恶,逐渐离上帝越来越远。
弗兰克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是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共同诱发的结果。一方面社会现实的残酷、黑暗、贫穷压迫着社会底层的人们,逼迫穷人去反抗甚至犯罪,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另一方面,这两位主人公都缺失道德信仰。他们不相信神,只相信自己,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非凡的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无神论的“超人”理论是残酷的,即便这种动因含有救济穷人的想法,但是损害他人的手段与基督教的人道精神断裂,并最终走向反道德反人道的极端。人性脱离了上帝,堕落为非人性。
二、惩罚:精神救赎
纵观《店员》和《罪与罚》,这两部作品都充斥着一种强烈的受难意识。在这两部小说中,犯罪主人公完成救赎的过程是双向的运动过程,而非单一的。除了来自主人公内心主动的忏悔,还有代表宗教“善”的精神导师的召唤和影响。马拉默德塑造了代表犹太教苦难观的形象莫里斯·波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妓女索尼娅身上充分地表现了东正教坚忍、宽恕、博爱的精神。在莫里斯和索尼娅的分别影响下,弗兰克和拉斯科尔尼科夫进行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惩罚,实现了真正的精神救赎。
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并非完全的恶人,在他们身上,人性呈现出善恶交织的形状。《店员》里的流浪汉弗兰克在与人合伙实施抢劫的过程中,就表现得十分犹豫。当发现受害者莫里斯是一个很贫穷且心地善良的犹太人时,他感到良心不安。为弥补自己对莫里斯一家人的伤害,他主动要求做莫里斯店铺里的小伙计。在做杂货铺店员的过程中,弗兰克常常难以克制人性中的弱点,接连犯下许多错误,莫里斯都宽恕了他。在莫里斯的影响下,弗兰克最终弃恶从善,皈依了犹太教,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犹太教徒,感动了海伦,获得了爱情。那么,什么是犹太人?根据莫里斯的话,做犹太人必须要信奉犹太法律。犹太法律,即犹太教最根本的教义。“这意味着要做好事,要诚实,要善良。对别人也是这样……人人都该有美好的生活,而不只是你和我。我们不是畜生,这就是我们需要法律的缘故,这就是犹太人的信仰。”[2]131莫里斯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本性善良,极富同情心,诚实地生活,日夜不息地劳作,宁愿忍受着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幸,也不愿去做伤害别人、欺骗别人的事。他一生虽不富裕也不精彩,但他坚信犹太教法律,本着犹太人的信仰脚踏实地的生活。甚至在临终前,他还一直在懊悔没有照顾好其家人,没有完成女儿的心愿。莫里斯就这样过完了他的一生,他很少为自己考虑,更多的是为他人着想。弗兰克曾问莫里斯“为什么犹太人要受这么多苦呢”,莫里斯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弗兰克又问“你为什么而受苦”,莫里斯的答案却是“我为你而受苦”。由此可见,莫里斯把苦难看作一种使命,苦难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它既是一种恩典,又是一种标记。苦难的价值在于它具有救赎的功能,苦难能够拯救一切。做犹太人必须要承受苦难,为犹太法律而受苦,为全人类而受苦。弗兰克在莫里斯身上学到了善良勤劳的品德,他被犹太精神所打动,继承了莫里斯的遗业,走上了充满忧愁和苦难的道路,承受着生活给他的惩罚。他开始有了希望,从恶魔走向了善的象征——圣方济,找到了精神家园——犹太精神,在宗教的怀抱中得到了心灵的安宁。
在《店员》中,有一段关于弗兰克读《罪与罚》的描写。“《罪与罚》这本书既使他难受,又使他着迷。”[2]112弗兰克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弗兰克相比,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人性救赎之路更加艰难,他所受到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惩罚也更严重些。他本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有正义感的青年。他虽然贫穷,却多次救济苦难的人,体现出他人性善良美好的一面。这些为他犯罪后沉重的自罚、真诚的忏悔奠定了基础。尽管杀人事件没露痕迹,但是他却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随之泯灭了。内心处于痛苦的矛盾冲突中,这种折磨甚至使他病倒,几天不省人事。自我的精神惩罚远远高于法庭的审判。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自己的错误“超人理论”和道德良心之间纠结痛苦时,是索尼娅的基督教精神引导他走向人性复活之路。在《罪与罚》中,索尼娅的形象,可以看作是弗莱提出的“中介新娘”的形象,即“得到宽恕的淫妇,尽管有罪最终又受到宠爱,就是介于恶魔淫妇和启示新娘之间的中介新娘形象,代表了人从罪孽中得到赎救”[3]。“中介新娘”虽然堕落,但并不邪恶,她们充满爱的品质,既救赎了自己也救赎了他人。索尼娅是一个妓女,她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却是为了养活她的一家人。索尼娅从小就饱受苦难、贫穷和欺凌,但她怀着崇高的信仰,敬畏上帝,爱所有人,宽恕一切,把人类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她默默地承受着不公平的命运强加给她的痛苦,用她那坚忍、宽容、博爱、善良的品质去感化和消解人世间的罪恶。索尼娅的生存意义早已超越了“为一己的动物的生存而活”,也不是“为人世间的荣誉而活”,而是朝向“为上帝而活”的层面,即为人类的“善”而活,这是人类的终极生存状态。迷途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娅身上看到了爱与希望的光芒,把上帝、爱和苦难看作是拯救灵魂的支点。他明白了只有怀着对上帝的敬仰,永远不抛弃爱与善,勇于承担苦难,接受惩罚,才能拯救自己的良心,拯救他人,实现人类幸福。在索尼娅的影响下,拉斯科尔尼科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精神自我惩罚,并主动到警察局自首,去西伯利亚服苦役,接受肉体的惩罚。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陪伴下,背上苦难的十字架,怀着对上帝的信和爱,一步步地走下去,实现了灵魂的重生。
这两位主人公背负着罪行,不断自我惩罚,获得了生命新的转机。这种转变一方面来自“善”的召唤,精神导师的影响,信仰的启迪;另一方面取决于“罪犯”自身对道德、责任、苦难的理解和逐渐接受,主动地受难、虔诚地忏悔、走向回归上帝之路。除此之外,这种转变还来自于两位作家的宗教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作家本人对人生所抱的希望和信念。
三、希望:朝向上帝
《店员》和《罪与罚》的结构框架,都是以主人公道德上的堕落为出发点,经过严酷的自审,以及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惩罚,找回信仰,从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复活。作为知识分子,马拉默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济人的使命感。
早在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个人与世界的冲突问题,他看到了历史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将一波又一波人碾压在齿轮下,“苦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中心。对于黑暗的社会现状,不少人怀疑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是正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最高形态是神,而神最堕落的形态是人。人身上虽然具有神性,但人并不完善,人还具备动物性。上帝是正义的,世界上任何人、历史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人不应当无所顾忌。神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权利。选择向善,必然要经历充满苦难、艰辛的历程。选择向恶,无视上帝,人的自由无限膨胀,走向自我崇拜时,人就丧失了同情心,人性则堕落为非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超越性,他力图实现社会真理,更确切地说,他力图实现充满了社会真理的“上帝之国”。对他来说,社会问题具有宗教问题的性质。他在《罪与罚》中揭示了人类自我肯定、不信宗教造成的恶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情人类的苦难,关注现实中人存在的本身、人的精神困惑,并与宗教精神相结合,他完全可以称为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者。他反对暴力,反对“为了使人类的极小部分成为幸福的”,而不择手段去消灭“多余的人”。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一切权威都意味着压迫。他希望通过基督教解决社会问题。在他设想的乌托邦里,教会取代了国家,世界成了充满自由与爱的王国,实现了真正的幸福。他在索尼娅象征的基督教精神中寄予了他对人类的全部希望。“只要存在上帝和神人,那么人类就保持了自己的最高价值,自己的自由以及对自然与社会权利的独立性。”[4]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理,也是俄罗斯思想的主题。
马拉默德曾说“人人都是犹太人,只是他们不知道。”他写犹太人,实际上是为所有人写作。他的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犹太人的苦难,更是整个人类的苦难。犹太人的处境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的缩影。在《店员》中,莫里斯和弗兰克的经历反映了欧洲移民到美国追求生活理想的幻灭,揭露了“美国梦”的泡沫性。在海伦、路易斯、沃德身上,读者可以看到社会问题给青年人造成的心灵创伤。他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马拉默德要表现的正是当代人在社会中的普遍处境和遭遇。马拉默德曾说“监狱是整个历史中所有人困境的隐喻”,他希望通过回归犹太教传统的方式,对现代人的罪进行救赎。他在作品中形象地传达了犹太教的精神。利奥·拜克认为犹太教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核心主题,那就是“犹太人自身的存在与未来都指向古老存在的上帝”[5]。犹太人的生活与犹太教是密不可分的。犹太人的历史充满了血和泪,犹太民族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客民”的社会地位存在和活动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苦难”是上帝赐予犹太民族的恩典,也是犹太身份的标记。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他们就必须要承受与权利相对的义务——苦难。这里多少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父,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人既需要上帝的庇护,又对上帝的权威感到惧怕。马拉默德在作品中深刻地反思了神与人的这种“父与子”关系。人类必须要走上帝引导的路,如果背弃了上帝,必将成为一个失去家园、灵魂荒芜的“孤儿”,这在查理、卡帕、萨姆等已经堕落的犹太人身上得到了印证,他们与莫里斯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在物质层面远远比莫里斯优越,但抛弃了苦难,就失掉了良心与信仰,成为了精神荒芜的“非犹太人”。两次世界大战后,所有人类都像弗兰克一样成了“空心人”。作家马拉默德通过表现莫里斯所代表的犹太传统与弗兰克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碰撞,以莫里斯引导弗兰克重返上帝之路这种方式,为20世纪精神干涸的现代人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意义。马拉默德关注的是生活对人的束缚和人对自我忏悔的认识。他对人类怀有深沉的热爱和希望,呼吁人们回归信仰,告诉人们心中要怀有对上帝之国的期盼,由恶趋善,践行善行,才能找到生存的出口。
殊途同归。同是怀有浓厚宗教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拉默德都在小说中表现了自己的宗教人道主义思想,并希望重构能够救赎人类的真善美价值体系。他们尊重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也看到了人性脱离神性的危机,忧虑人类的命运。从《罪与罚》到《店员》,无论表现的是东正教还是犹太教,这两位作家都意识到只有依靠宗教给予的道德自律才能自救,把自我救赎、自我拯救看作是人类得救的根本途径。他们反对暴力,形象地指出了无神论人道主义的危机,提出了信奉爱的哲学,选择忍耐、宽恕、自我完善、自我拯救。但他们对解决社会问题所提出的宗教人道主义思想,并不具备现实效力。自救要求人类道德自律、忍受苦难,得到再生必须以牺牲和隐忍为手段。这种思想很难做出实际的改善人类社会的事情,反而容易被统治者歪曲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暴力和奴役的社会。这不得不说是人道主义的另一种危机。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对人类精神出路的探索从未停止过。
[1]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朱海观,王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56.
[2]伯纳德·马拉默德.店员[M].杨仁敬,刘海平,王希苏,译.扬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3]诺斯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4.
[4]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96.
[5]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M].傅永军,于健,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5.
【责任编校朱云】
An Analysis on the W ay of Faith in Return in Clerk and Crime and Punishment
XINRuisi
(School of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00,Liaoning,China)
Frank Albay,the hero of Malamud’s Clerk and the hero of Russ Cole in Dostoevsky’s Crime and Punishment,both have undergone the way from degener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spiritual rebirth.Spirit of Judaism and Orthodox respectively p 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turn of human nature.According to those,it is not hard to learn the two writers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survival significance,which is close to religion.Both of them hope to realize redemp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spiritby theway of religion,trying to find an export tosavewithered soul ofmodern people.
Clerk;Crimeand Punishment;faith;Malamud;Dostoevsky
I106.4
A
1674-0092(2016)05-0070-04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15
2016-03-11
辛睿思,女,河南平顶山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