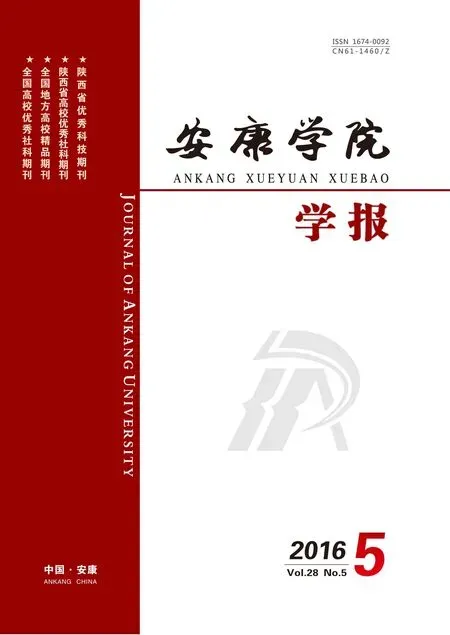诉讼调解:从“经验”到“理性”的僭越——对如何正确发挥诉讼调解作用的思考
张 刚,王成军
(1.安康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中级法院,新疆 伊宁 835000)
诉讼调解:从“经验”到“理性”的僭越——对如何正确发挥诉讼调解作用的思考
张刚1,王成军2
(1.安康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中级法院,新疆 伊宁 835000)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立法层面上规定得过于宽泛,许多规定还仅仅停留在经验性运作层面,远未形成具体和正当化的操作范式。在此情形下,诉讼调解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的正面的积极作用与负面的消极作用亦相伴而生,并发生博弈,以至于一些案件的负面的消极作用还有可能凸显出来,从而引发新的纠纷和矛盾。为控制和消解诉讼调解在审判实践中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对诉讼调解的整个运行过程做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制,从而使诉讼调解不再只是一种“经验”,而更应当是一种“理性”。
诉讼调解;审判;经验;理性;博弈
被誉为“东方经验”[1]的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弥合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情感、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立法层面上规定得过于宽泛,还远未形成具体的和正当化的操作范式。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如何进行调解,以及在调解过程中又如何保证法院的中立地位和调解过程的合法性、公正性,全国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仅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甚至在同一个法院内部的不同法官之间也不尽一致,由此导致诉讼调解的随意化和无序化态势。因而,当前我国的诉讼调解还只是一种经验式的审判权运行方式。
在极力强调案件调解率的大背景下,“重结案方式,轻办案过程”“重实体,轻程序”的不良思想开始抬头。诉讼调解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的正面的积极作用与负面的消极作用亦相伴出现,并发生博弈。以至于一些案件中的负面的消极作用还有可能凸显出来,从而引发新的纠纷和矛盾。倘若任其发展下去,将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以及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为控制和消解诉讼调解作用在审判实践中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对诉讼调解的整个运行过程进行明确和具体的规制,从而使诉讼调解不再只是一种“经验”,而更应当是一种“理性”。
一、诉讼调解作用之现状: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相伴而生,相互博弈
“在能动主义理念中,司法不只是一个把法律适用于具体事实的程式化活动,更是施展其社会功能,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具体实践。”[2]当下,诉讼调解已俨然成为审判权运行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缺乏必要的和正当化的规制以及明确的和具体化的操作范式,以至于全国各地法院在努力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审判工作原则[3]和实现“定纷止争、胜败皆明、案结事了”的审判目标[4]的过程中,正面、积极的作用与负面、消极的作用总是相伴而生,并展开博弈。
(一)正面、积极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运行领域亦悄然发生转变,诉讼调解作用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纠纷解决,而是向着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拓展。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①当下,法院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表现为:正确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有效平息矛盾纷争,大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展平稳快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影响和谐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诉讼调解符合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诉讼意识,体现中华民族追求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参见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1条。下,诉讼调解的正面、积极的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维护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在化解矛盾方面,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主持调解,诉争当事人达成了协议,由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化解,这与开庭审理、合议、制作裁判文书,并送达文书所解决的诉讼纠纷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合意性解决方式,而后者则是一种决定性解决方式,而合意方式更符合社会大众的传统心理和纠纷解决意识,在诸多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其次,在定纷止争方面,由于经过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律上没有对此设置上诉程序,且一般情况下申请再审、申诉、上访比率不高,可以迅速对诉争当事人产生效力,因此在彻底了结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再次,在维护稳定方面,由于我国正处于特殊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多样,一些群体性、突发性、影响面较大以及涉及社会稳定的纠纷案件逐渐增多,人民法院在审判权运行过程中,通过发挥诉讼调解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迅速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其四,在保障经济发展方面,人民法院根据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本质特点,结合当下的基本国情和经济运行情况,在审判工作中通过充分运用诉讼调解,坚定不移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任务,为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五,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人民法院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机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各项事业均取得了显著成就[5]。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法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和保障力量[4],必将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促进公正司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运用诉讼调解还可以起到弥合纠纷当事人情感的积极作用,与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不谋而合,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和谐的普遍理想。
(二)负面、消极的作用
当下,诉讼调解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方式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在自上而下极力强调“大调解”的背景下,调解结案率已成为与法院以及院、庭室领导和案件承办人员工作业绩相挂钩的重要指标。为完成这些硬性指标,审判实践中大量出现“重结案方式,轻办案过程”“重实体,轻程序”的不良思想倾向,从而在社会上产生诸多负面、消极的作用。
首先,导致法院职能和法官职责的异化。在实践中,由于一味地追求调解结案率,法院没有精力、也没有动力再去打造学习型法院;法官也同样没有精力、也没有动力再去钻研审判业务、提高裁判质量,由此,法院在司法权运行中的独特品质和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以及法官公正、清廉、高效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开始发生转变。其次,导致审判的既定目标被篡改。当下,“定纷止争、胜败皆明、案结事了”已成为人民法院的审判目标,各地法院在贯彻执行这一目标过程中,却往往演变为对调解结案率的极力苛求,法官无暇顾及案件调解结案之后,是否还能够达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目标。在调解结案率这一硬性指标的强压之下,极力追求调解结案率已事实上成为了人民法院当下的审判目标。再次,导致违法、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为了实现调解结案率指标,法官则违背当事人意愿强制进行调解,若嗣后当事人反悔、拒不认可和履行调解协议,法官又无疑成为当事人攻击的对象;在一些案件中,明知协议内容违法,也视而不见,以至于嗣后引发申诉、再审等等。其四,导致该上升的指标未上升,该下降的指标未下降。按照“大调解”的设计初衷,应当实现调解结案率与息诉服判率的“两上升”,实现涉诉信访率与强制执行率的“两下降”[3]。然而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的调解结案率上升了,但息诉服判率并没有明显上升,涉诉信访率和强制执行率也没有明显出现“两下降”的态势。其五,导致法律适用能力、庭审驾驭能力和文书制定能力的下降。一些法院在狠抓诉讼调解的过程中,忽视了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在注重调解艺术、调解技能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庭审操作技能、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推理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在注重以情调解、以理调解的过程中,忽视了对裁判文书的说理、对裁判推理逻辑性的严密思索、对裁判结果三个效果上的审慎把握。其六,导致证据证明作用降低,规范意识淡化,法治观念丧失。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加速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而另一方面民众却不按照事先设立的规矩、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及公认的诚信伦理标准来行事,凡事都要和稀泥、谦让、退步、放弃,“好人不点头,坏人不摇头”,正义不鼓励伸张,邪恶不坚决惩治,严重阻碍了我国法治化进程。
(三)两种作用相互博弈所产生的影响
诉讼调解在社会中的正面、积极作用,是不容被否定的。然而,由于诉讼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缺乏必要的和正当化的规制,加之一些硬性指标被非理性地随意设置,以至于诉讼调解在实践运行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负面、消极的作用。这些负面、消极的作用倘若不加以控制、消除,就有可能在各种作用的相互博弈中凸显出来,从而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
首先,调解率上升,则裁判率下降,裁判的功能、作用以及裁判所涉及的范围、领域将缩减,裁判的示范作用也必然受到削弱。没有了裁判,又有什么可以更好地用来发挥法律的示范作用,这显然又成为了另外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局。其次,强调“调解优先”,推行“调解奖惩机制”,将导致法官形成“以调为荣,以判为耻”的不良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裁判权在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中的地位开始下降,法官的裁判能力因得不到必要的奖惩而很难得到提高。再次,“大调解”导致“小审判”,一味地强调调解和片面地扩大调解的作用,将导致审判实践中对审判程序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漠视,“重结果、轻过程”“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便由此抬头。其四,调解结案率与法院以及法官个人的业绩相挂钩,将导致审判实践中为了调解率而调解,调解的宗旨、目的、属性完全被丢弃一边,案件虽然调解结案了,但却并未能够事了。近年来,一些法院的调解率上去了,而调解案件执行率以及申诉、上访率并没有随之下降,正说明了这一点。其五,在诉讼调解方面过多地占用时间,将挤占案件庭审、审判研究、疑难案件探讨和审判经验总结的时间,由此将阻碍法院整体审判理论水平的提高,削弱应用法学的发展,影响法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其六,调解意识在诉讼中的全面覆盖,将导致公民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的失守和沦陷,非常不利于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构建。以上几个方面,若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将影响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功能,削弱人民法院的地位,最终将不利于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树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诉讼调解作用正确发挥之路径:从“经验”到“理性”的僭越
调解的价值是任何原理和逻辑推理都无法否定的[6],然而无限扩大调解的价值,片面抬高调解的作用,并在审判实践中任意操作、随意运行,就会导致庸俗化现象的发生,从而产生负面、消极的作用。为消解诉讼调解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以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对诉讼调解的相关理念以及诉讼调解的整个运行过程做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制。
(一)从“凡案必调,极力调解”到“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在“大调解”的审判工作格局之下,各地法院都在想方设法提高案件调解率。有不少法院在推行“凡案必调,极力调解”的做法,不论是哪一类型的案件,也不论是哪一性质的案件,均一律花大力气进行调解。这种做法往往导致相当一部分案件因长时间、多次调解未能够达成协议,而增加司法成本、耗费当事人的精力、延长案件审理的周期,以至于当事人双方和法院内部都有意见,最终的效果也不一定好。正确的做法是,应当统一到“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审判工作原则上来,要紧紧围绕“案结事了”的目标,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用调解方式处理;要做到调解与裁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论是调解还是裁判,都必须立足于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定纷止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根据每个案件的性质、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诉求,科学把握运用调解或者裁判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对于有调解可能的,要尽最大可能促成调解;对于没有调解可能的、法律规定不得调解的案件,要尽快裁判,充分发挥调解与裁判两种手段的作用”[3]。这些内容应当以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下来,使其法律化、规范化,而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有关的政策性意见中。
(二)从狠抓“调解率”到注重“调解质量”与“裁判能力”
在审判实践中,狠抓案件调解率,尤其将案件调解率作为一项硬性指标来抓,其最终将导致诉讼调解的目标发生异化——案件调解率上去了,但“案结事了”的目标却未能够实现。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在案件审理中发生,各地法院在贯彻和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上,应当十分注重案件的调解质量,努力实现调解结案率和息诉服判率的“两上升”,实现涉诉信访率和强制执行率的“两下降”,真正实现“调解一案,带动一片”的效果。法院要将工作精力切切实实放在“定纷止争、胜败皆明、案结事了”审判目标上来,在个案审理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以诉讼调解的方式来实现,也要考虑以裁判的方式来实现;不仅要加强调解能力建设,而且也要加强裁判能力建设;不仅要对那些通过调解方式实现“案件事了”的法官予以奖励,也要对那些裁判文书制作精良、说理充分、具有较强服判力的法官予以奖励;不仅要注重调解方式,注重调解艺术与调解技能,注重以情调解与以理调解,而且还要十分注重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对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推理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对裁判文书的说理,对裁判推理逻辑性的缜密思索,以及对裁判结果的审慎把握。
(三)从“重结案方式,重实体处理”到“重结案质量,重程序运作”
在审判工作中,一味地强调调解结案方式,苛求调解结案率,就会严重导致“重结案方式,重实体处理”的不良倾向,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常运行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大局均无益处。“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7],正当程序可以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在案件审理中,忽视、轻视,甚至蔑视正当程序,惯常于通过先入为主、直奔主题的方式来实现案件处理结果上的公正,是一种短视行为,是不可取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审判工作原则的提出,并不是强调要一味地进行调解,也不是完全无视程序的特殊功能。一些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重结案方式,重实体处理”的不良倾向,是审判工作原则与审判权实践运行严重脱节的必然结果。在我国政治与诉讼调解的关系中,诉讼调解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进一步升温,人们对诉讼调解的重视不仅仅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法律技术手段,也是满足当下的政治需求,是一种政治行为;诉讼调解已成为一种被强化的态势,在人们的观念和心理上已经把诉讼调解率的提高和诉讼调解的运用作为一种实践中的强势命令;“增强”和“充分”在特定语境下都可能成为强化诉讼调解的“指令”[8]。为消解这一现象给审判工作带来的困惑和难题,人民法院应当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不良心理,尊重司法规律,立足于结案质量和程序运行,这不仅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践行“案结事了”审判目标的出发点。
(四)从个别、分散性的规定到统一调解法的制定
当下,涉及诉讼调解内容的规定,主要包括民诉法中的八条规定、最高院民诉法意见中的七条规定、最高院执行工作规定中的两条规定、最高院简易程序规定中的四条规定、最高院民事调解规定中的二十四条规定以及最高院关于诉讼调解的两个指导性意见中的规定。刑事、行政诉讼以及国家赔偿程序中,也涉及一些零零散散的规定。这些涉及诉讼调解的规定,效力位阶不同,有法律、司法解释,也有政策性意见;涉及的领域也不尽一致,有民事、行政和刑事方面的,也有国家赔偿方面的。这些涵盖在不同程序法中的个别的、分散性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解释和政策性意见,不但不利于个案的具体实践操作,而且对于审判理论研究也带来诸多不便,与诉讼调解在审判工作中的突出地位格格不入,在“大调解”的审判态势之下,已经不适应审判形势的需要。另外,我国诉讼调解制度规定得过于宽泛,一些法院为了追求案件调解率,均不同程度地出现随意性和任意性的经验性做法。这些经验性做法因缺乏具体的和正当性的规制,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所有这些,亟需要通过出台一部能够涵盖全部诉讼调解内容的、统一的调解法来予以明确规定,从而使我国的诉讼调解不再只是一种“东方经验”,而更应当是一种“实践理性”。
[1]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68.
[2]顾培东.司法能动主义的蕴含[J].法律适用,2010(Z1):12.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EB/OL].(2010-06-07)[2016-03-15]. http://www.court.gov.cn/xwzx/fyxw/zgrmfyxw/201006/P02010 0628295591970430.doc.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EB/OL].(2007-03-06)[2016-03-20].http://old.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 =237182.
[5]王胜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几点认识[N].人民法院报,2011-03-01(4).
[6]范愉.诉讼调解:审判经验与法学原理[J].中国法学,2009(6):134.
[7]孙洪坤.程序与法治[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23.
[8]张卫平.诉讼调解:时下势态的分析与思考[J].法学,2007(5):21-22.
【责任编校龙霞】
Lawsuit Mediation:from the“Experience”to“Rational”Trespass
ZHANG Gang1,WANG Chengjun2
(1.AnkangUniversity,Ankang725000,Shaanxi,China;2.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Fourth Division Intermediate Courtof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Yining835000,Xinjiang,China)
Known as the“Oriental experience”of China’s litigation mediation system,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o resolve social conflicts,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However,the litigation mediation system in China's legislative level is too broad,many provisions still only stay in the empirical operation level,far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specific and properoperation paradigm.In this case,litigationmediation in the trial work of the people's courts in positive positive role and negative negative effect also accompanied by and,and the game,that some cases of negative negative effect may also highlighted,which triggered a new disputes and conflicts.Fo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ontrolling and eliminating the litigation mediat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ositive role,it is necessary tomediation,litigation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operation to make clearand specific regulation,so thatmediation isno longer justa“experience”,andmore should be akind of“rational”.
lawsuitmediation;trial;experience;rational;game
D925.114
A
1674-0092(2016)05-0108-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24
2016-04-14
张刚,男,陕西安康人,安康学院教师,陕西理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王成军,男,河南项城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中级法院法官,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