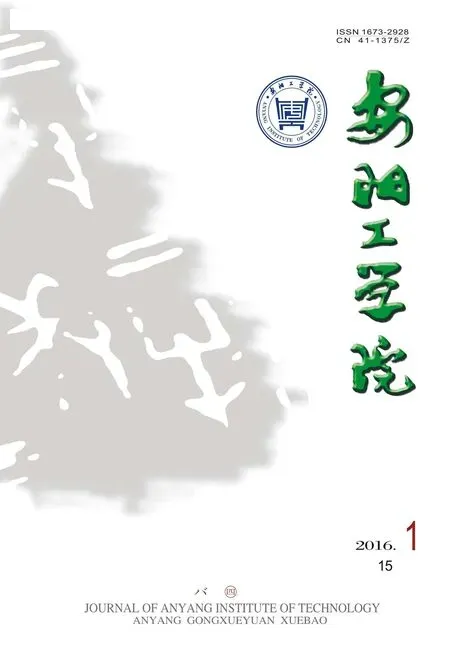试论郝誉翔《洗》中的女性角色认知
王佳欢(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试论郝誉翔《洗》中的女性角色认知
王佳欢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摘要:郝誉翔是20世纪90年代崛起于台湾文坛的“60后”女作家,她在女权主义潮流涌动时代创作的短篇小说《洗》,可谓独具特色。随着女权主义的回归,女性角色由传统的依附于男性角色而存在,变为主动地压制甚至是舍弃男性角色,并由此进行一场女性主义者和自恋者的狂欢,而狂欢落幕之后浮现的则是女性对自己角色的重新审视。《洗》这篇小说正是透过四种畸形恋情的刻画,传达出作者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定位。
关键词:郝誉翔;《洗》;女权主义影响;女性角色审视
20世纪90年代(下文省去“20世纪”)开始活跃于台湾文坛的女作家们,可谓台湾“解严”之后崛起的一批新生代文坛新秀。她们以女性的体验和视角来探讨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的自我意识该被抹杀吗?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吗?毫无疑问,已经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洗礼的女性对此是不认同的。她们对两性关系和女性议题有着自己的审视,她们用文字拆穿爱情的乌托邦,解构男权中心的神话,在文本中表露出自己女性主义的倾向。
出生于60年代的郝誉翔作为上述女作家群落中的一员,有着与其相类似的写作路向。就文化背景而言,受台湾社会转型后的都市化生存境遇影响,“八九十年代以来由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多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交织的文化生态环境,……为她们人生设计与文学路向的多元化选择提供了可能性”。[1]99这些有利条件,使得郝誉翔在女性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出发,拥有了比较开阔的前景。
如果说,80年代的女作家主要关注的是女性解放和女性独立等问题,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的转换,女性主义思潮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女作家从80年代探索女性的性爱、情欲、成长和责任为主,转变为一种寻求情感和情欲平衡点的模式。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延续了80年代的繁盛景况,但是女作家在表现女性角色和女性体验方面,其视角和意识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通过文字,不难发现在经历过女权主义的高潮后,她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疲沓状态以及对男性的厌恶和逃避,因此她们转为探索女性如何在同性恋和自恋的疆域内去寻求一个情感的平衡点。[2]
郝誉翔初入文坛,是以短篇小说《洗》在台湾《联合文学》第十届小说新人奖上崭露头角。《洗》所印证的,正是台湾90年代文学中对女性角色的定位过程。
《洗》叙述了一位都市女性的成长过程。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情感体验作为小说的发展主线,以“我”的视角和意识来表现女性的情欲在都市文明的压抑下所展现出的病态和畸形,而这畸形的恋爱过程也就是作家郝誉翔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过程。小说内容分为A部分和B部分。A部分讲述的是青少年时代的“我”,B部分讲述的是已为人妇的“我”,这种处理方式同时满足了两种不同状态下女性的体验。A和B部分采用首尾接力的形式展现两种生活状态的交织,似乎是“我”在少女时代就已经与嫁为人妇时的“我”搭上了话,并且在彼此之间有了生活的碰撞。小说着力刻画的,是主人公“我”在四种恋爱形态中的情感体验和自我审视。
一、异性恋
主人公“我”在高中时代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第一次贡献给了一个诗人。诗人是“我”的一个学长,他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就约“我”一起上阳明山去。我们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诗人“呼出了一口忧郁的长长叹息,一股温热从我的头顶降临在耳朵上面,全车的人唯独我是因为不断发颤而极度清醒的。”[3]279在天与地交合的山顶上,“我”完成了少女变为女人的仪式,这也是“我”的首次女性体验。一年半以后,诗人以“没有想象力”为由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后来的“我”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过着最不需要想象力的生活。“我”和丈夫之间谈不上有爱情,而“我”却要履行作为妻子的义务。
在“我”和诗人之间,本该发生在青少年身上那种浪漫的爱情情节,尤其是作为一个拥有充分想象力的诗人更应该具备的浪漫基因,并没有被郝誉翔记录下来。“我”因为崇拜而心生情愫,但是诗人并没有给予“我”同等分量的爱,因此“我”和诗人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爱情。“我们”第二次见面就完成了彼此身体的交融,因为“我们”之间更多的是情欲,所以一年半以后“我”终于被诗人遗弃在街头。而成人之后的“我”,丈夫理所应当地使“我”有了另一种感受和体验——“我”并不爱他,但作为妻子却不得不把自己的肉体提供给他。在这一段关系中,“我”的女性体验完全与诗人赋予我的不同。
女性解放当然包括性的解放。“我”正是通过高中时期大胆的举动在宣示“我”的女性角色地位:女性和男性一样,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有完全的支配权,“矜持”再也不能随便把她们的自由意识压垮。可是与诗人分手之后的“我”,成了男人妻子的“我”,女性主体意识却被“妻子的义务”所泯灭。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女性主义作家,都将表现女性角色的视角定格在性的解放上,要么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表现,要么写女性在情欲膨胀之后的心理变化。她们渴求通过书写这种女性体验来挑战男权,用细腻的笔触点破女性微妙的心理回声,从而使女性角色在文本中替代男性角色的主体地位。但是女性的解放和独立并不仅仅从两性关系上来体现,所以,女性主义作家们又将创作视角转换到了女性自身——既然在两性世界中不能寻到一个平衡点,那么就将目光转向女性自身。
二、同性恋
郝誉翔紧随女性主义的大潮,将目光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在小说《洗》中,诗人以“你很美,但是你没有想象力”为由与“我”分了手,一年多以后,“我”高中的死党B告诉我的真相又一次印证了“我”缺乏想象力的事实。原来诗人和“我”分手的那天晚上,他就和B在一起了,B后来没有考上好学校,也是被诗人所害。“我”和B同病相连,惺惺相惜,在互相的注视下,决定“相濡以沫,维系着彼此的生命”。我们相互亲吻、抚摸,拥抱对方,诉说着与诗人发生的一切,却都不记得诗人的长相以及他的声音、嗜好、气味甚至是诗句,我们以同性的身份把从男性那里缺失的爱都补给对方。就这样,“我”和B展开了一场像是救赎自己的同性之恋。遗憾的是,B最后还是离开了“我”,她在出国不到一年的时候划破了自己的动脉,“那种感觉仿佛是发现自己的四肢竟然背叛了自己,不说一声就甘愿悄悄断离而去,或是发现那根本不是自己的四肢。从来也不属于我,然而我却以为我知道。”
郝誉翔从异性恋的失败写到同性恋,正是表明了女性主义的关注点从80年代表现女性的性爱、情欲、成长等方面转变到了90年代的去男性化情感模式,对角色的认知也由女性依附于男性而存在转变为女性角色的自我体验。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作品大多数以同性恋为题材,突出表现在单一性别的情境下女性的一种角色认知和情感体验。然而郝誉翔并没有给同性恋以完美认同,她使B离“我”而去,以此结束了“我”同性恋的生活。
三、自恋
同性之间有爱就会有恨,即使是同性也免不了互相猜忌。“我”在经历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失败之后,反而爱上了自己。“我”每天下午五点整会准时出现在浴室里,脱光衣服对镜窥视自己。“我好像是着了魔般,径自踏入浴室,阖上木板门,卸下衣服,从上衣、长裤、胸罩、内裤,郑重其事地像是在进行一场膜拜祭礼。”[3]283影恋是自恋中最典型的现象。正如拉斯奇所说:“新自恋者凝视自己影子时的目光与其说是在自我欣赏,还不如说像是在毫不留情地搜寻自己身上的瑕疵,倦怠的痕迹和衰败的迹象。”[4]102因此“我习惯性地抚摸颈上的皱纹,捏捏颈右侧一粒小小的赘疣,一股刺痛传入心肺,到底自己还是活着的”,“我”看到“焦黄的发梢摧枯拉朽地横生开来,早已走了型,只怕用力一梳就要灰飞烟灭”,以及自己“无精打采呈现下垂趋势的胸脯”。[3]283“我”通过发现自己身体的不完美来加深那转瞬即逝的镜像。在五点钟的浴室里,“我”就是全世界,全世界也是“我”的,没有人会来打扰,直到有一天,对面公寓出现了一双专注的眼睛。
女性主义作家们已经疲于讨论男女之间平等与否的问题,干脆将研究视角转换到了女性自身,通过同性恋和自恋的题材来表明她们对男性的厌恶和逃避,力图在一种疲沓的状态中寻求一个情感的平衡点。小说《洗》中,“我”在青少年时期失败的异性恋和同性恋经历使“我”丧失了对他人的兴趣,将目光重新定位于自身,成为一个自恋主义者。郝誉翔从异性恋写到同性恋,都没能寻求到一个满意的情感模式和合适的女性角色定位,那么自恋的形式能作为情感的平衡点吗?显然也是不可得的。“我”对着镜子窥视自己,却被人窥视。在看与被看之间,完成了主被动地位的转换,宣示了“我”的自恋以失败终结。
四、暗恋
就在“我”窥视自己裸体的时候,“我”发现窗外多了一双窥视的眼睛,“这一个月来天天都是相同的人影,远远望似苍白的脸,穿着深蓝色高中生夹克,短短的青发,鼻梁上的眼镜反照着微弱天光,他居高临下一动也不动的注视着“我”的浴室。错不了,绝对错不了,窗外这蓄意的偷窥者,一个月来不曾间断过。”[3]287镜子把“我”的美和瑕疵一并呈现,所以“我”渴求有一道这样陌生而隐蔽的目光来肯定自己。“看自己”由于多了一束目光而变成“自己被看”,自恋也随之终止。而“我”由于每天准时进浴室洗澡,偷窥者每天准时偷窥,“我”和偷窥者之间竟像是在进行一场“无言的秘密约会”。“我”明知有偷窥者,却故意赤裸相对,很显然“我”在暗地里是喜欢这位高中生进行偷窥的,以至于“我”竟然开始反抗丈夫对“我”肉体的侵犯,“因为觉得自己背叛了水塔顶上的高中生”。于是第二天“我”在浴室准时见到高中生时,终于冲出家门飞奔向对面公寓大楼,在楼顶“我”见到了偷窥者,使“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就是丈夫。“我”在浴室对自己窥视的这一行为使“我”自己着迷,以至于“我”忘记了丈夫五点下班,以及“他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剪短了”,“我”对这些细节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判断的错误。
在肉体上反抗着丈夫,在精神上与偷窥者“约会”,而郝誉翔笔锋一转,丈夫即是偷窥者,使“我”对“无言的约会”的暗恋之情转为莫大的悲情。文章结尾写道:“我低下头,看见对面公寓里我的浴室还亮着灯,莲蓬头的水尚且哗啦啦的流着,但是地上却躺着一尾巨大的鱼,它搁浅在瓷砖上面,奋力拍打着尾巴,鲜红的鳃大开,薄薄的鳞片掉落了一地。而水正哗啦啦地打在它光滑的身躯上面。”[3]文章最后出现的“巨大的鱼”,与前文写自己给公公买鱼做饭时杀鱼相对应,“五年下来杀了一千条以上活生生的鱼,就只为了填塞住两张在嚼动的嘴,一千条以上的鱼在我的面前哗哗拍打鱼尾以示抗议。”[3]286
王德威在给郝誉翔的短篇小说集《洗》写的序中说过:“鱼与水的象征不言而喻,她却能推陈出新,连锁到自恋、恋人与恋物的层次上。同性还是异性、偷窥还是暴露,欲望如流水,总是渗透身体与生活的肌理间。”[5]5-9郝誉翔在自序中也提到:“我喜欢洗,譬如说,我自己......每当我打开莲蓬头清洗自己的时候,我身上覆盖着的鳞片就会被一一刮下来,剥露出里面跳动的血肉。”[6]10-13这样结尾,自有作者的用意。“鱼”暗指“我”,也可以说是郝誉翔自己,“水”则表示欲望。巨大的鱼搁浅在地板上,即使有莲蓬水哗哗地流着,也不免悲剧的结局。
郝誉翔在《洗》中使“我”经历了常态的异性恋、变态的同性恋、病态的自恋和暗恋,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意味着郝誉翔对女性角色的认识过程。女性角色的定位首先表现在男女地位的比较中,女性主义作家们一反传统,在作品中突出表现女性的主体地位以及角色体验,将男性置于附属地位,从而打破了维持几千年的男权主义;接着,女性主义作家们听到了男性反抗的声音,于是将男性的地位再次放低,甚至到了不需要男性的地步,同性恋和自恋作品便出现在这一时期;但是将女性角色的定位问题交给一个隐秘的窥视者似乎也是不妥当的,窥视者给予女性一束偷窥的目光,并不代表“他”就能定位女性角色。郝誉翔意识到,女性之所以为女性,就是与男性相区别而为之,所以凸显女性主义并不能完全去男性化,女性角色是无法脱离两性关系来下定论的。
郝誉翔通过自身的女性体验来塑造出女性角色的演变过程,充分展示了女性主义者应该有的理性色彩。她在小说《洗》中,通过对几种畸形的“恋”情的大胆体验,细致地刻画出女性在这几种状态下的角色扮演以及内心的微妙感受。对于女性主义者在女性解放话题上的激进,郝誉翔则表现出了无比的理性,她在对异性恋、同性恋、自恋和暗恋的剖析中升华出女性角色的合理定位,女性的解放并不是将男性关进大牢中,而是要在两性关系中营造出一种和谐平等的氛围来。
参考文献:
[1]樊洛平.社会人生的拆解与颠覆:台湾新世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态势[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8(3).
[2]巫汉祥.自恋主义文化的写真:评郝誉翔的短篇小说《洗》[J].台湾研究集刊,1999(3).
[3]郝誉翔.洗[M]//杨际岚,宋瑜.台港澳小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M].陈红雯,吕明,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
[5]王德威.一扇自己的窗子:读郝誉翔的《洗》[M]//郝誉翔. 洗.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序.
[6]郝誉翔.关于记忆与欲望的几种洗法[M]//郝誉翔.洗.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自序.
(责任编辑:陈丽娟)
作者简介:王佳欢(1991-),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湾文学。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研究生核心学位课程项目”台湾文学研究“,立项编号:YJSXWKC201557。
收稿日期:2015-12-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16)01-0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