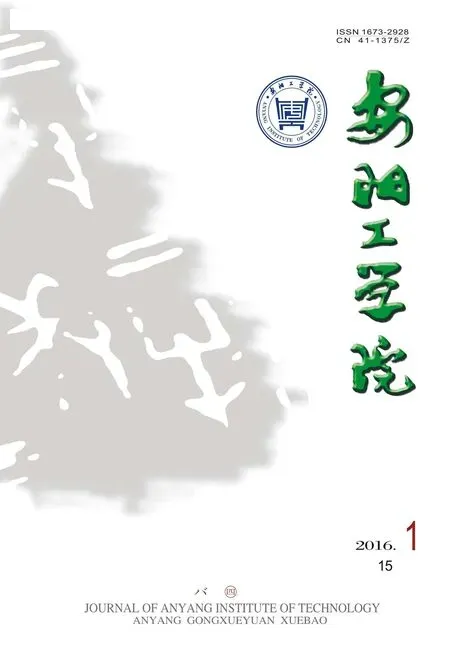泅渡于现代与传统间的闺秀——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与计文君《剔红》等的比较
黄鋆鋆(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泅渡于现代与传统间的闺秀
——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与计文君《剔红》等的比较
黄鋆鋆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摘要:台湾女作家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大陆女作家计文君的《天河》《剔红》等,都在社会变迁之际对传统和古典做出了回望,并从女性视角切入社会与历史、人性与心灵的变迁。她们的创作着重表现了女性在“无父”时代借由男性恋人和“她者”镜像的双重参照建构自我的跋涉之旅。但不同的是,二人笔下的闺秀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一个在受伤后回到传统的怀抱,一个在挣扎中向着现代泊岸。女性是否真正建构了自我,也留给读者辨析与思索的空间。
关键词:萧丽红;计文君;传统文化;女性成长;“她者”镜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与新世纪初的大陆,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时代风云变幻的负重往往更多由社会的弱势群体所承担。在男权主流文化中,女性往往以社会边缘地带的存在,成为衡量时代变革与社会解放程度的标杆。“50后”的台湾女作家萧丽红、“70后”的大陆女作家计文君,在相似的时代背景和女性题材中寄寓了各自对现代和传统的不同价值选取,并在《红楼梦》般的古典笔调与张爱玲式的闺秀情感中呈现了女性破茧成蝶的成长经验。但在风格和题材的相似中,作家借泅渡于现代与传统间的闺秀女性贞观与秋染等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传统与现代的取向也成为她们内在的分野。以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和计文君的《天河》《开片》《剔红》《帅旦》为例,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之于女性的双重意义,同时探明女性成长与长成的自我建构历程。
一、传统文化的救赎与束缚
古典韵味与闺秀气质是萧丽红与计文君创作风格中最相似的地方,这与二人都成长于传统气息颇为浓厚的古镇有关。萧丽红的故乡位于台湾省嘉义县布袋镇,有着初期大陆移民古老的中原文化传统,而计文君的故乡则是钧瓷产地河南许昌。同宗同源的中原传统文化在二人的创作中都显示出重要的意义:宽厚仁义的民间道德、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祖孙情深的大家族,给了贞观一个美好的栖梦之所,也成为她受伤后的疗救之地;而钧瓷的美丽精湛、古老阁楼的诗情画意,除了给秋染们一个立足之地外,更给予了她们“开片”的坚韧和独自出征的勇气。
传统文化是《千江有水千江月》最大的着力点,主人公贞观和大信的名字中就暗含了“女有贞,男有信”的传统文化要义。在欧风美雨不断侵袭台湾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萧丽红通过文化寻根的努力,想要用来自故乡和传统的民间道德,以及贞观与大信纯洁守礼的爱情方式,为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城市和现代吹去清风,通过回望传统来找寻人类在追赶中所遗失的“许多高贵品质”,“找回精神的源头与出处”[1],同时又在台湾乡土的回溯中串联了祖国大陆的中原传统文化。对于读者来说,“这震撼了他们的,又非寻常所谓乡情、乡村怀念,而是一种更浩茫的文化感动与文化怀念。”[2]赵园更认为其与《京华烟云》有着同等的文化境界。
爱情与时代总脱不了干系,黛玉与宝玉在封建家庭的爱情悲剧,娜拉们在现代启蒙之际走出旧家,夏丹琪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失身与出轨,皆不是偶然。贞观同样是在走进时代风云中去经历爱与痛后,才回到故乡寻找“情归”与“救赎”。贞观与大信的爱情悲剧,“究其根源,依旧是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作祟”[3],同样也有二人各自所热爱的乡土与城市的不兼容性。贞观对城市的最大感受是“隔”,与大信情感破裂时感受亦是“隔”。传统与现代的鸿沟,成为横亘在贞观与大信之间最遥远的距离。
计文君的创作里,有着大家闺秀式的优雅、从容与自信,她擅长以女性细腻的情感、绵密的笔触,去描摹这个“说不清”的时代中人物内心繁杂幽微的畸变。她笔下的闺秀既能出世,又能入世。从传统和乡土中“脱域”而出的秋染将自己抛诸现代的潮流中摸爬滚打,在都市体验了迷惘和伤痛后回到故乡,流连于小娴的庭院并在中药调理中获得疗救。这里,以小娴为代表的古典女性就成为一种精神救赎的象征,她们身上的传统文化特质成为现代都市病症的一剂良药,进而给予女性人物独立出征的勇气。
在传统文化的救赎之外,我们必须看到它对女性的束缚与压抑,这是女性自我成长的一层厚茧。两位女作家的文中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但都有意无意做了回避和美化。萧丽红着意从闺阁与婚姻生活中迈出脚步去构建自我,同时也并未封闭于闺阁之内,置时代风云于不顾。从新娘子不再亲手做香包,到台北人的“巧取、豪夺”,透过闺阁,她看到了世事的变化;从大妗、二姨、母亲在深宅大院的幽暗角落里独自流下的泪水,到妗子、嫂子被丈夫无端呵责的尴尬,作者也并未忽视传统中女性的受难。萧丽红的传统充满了“月”的温情,但温情从来都有温暖与温凉之分。她在刻意渲染传统之美的同时,也浸淫了传统的幽怨和哀思,进而传达出一种“梨花一枝春带雨”式的美,这也正是她对传统的认知。但由于作家文化立场偏于传统,她只能让人物对此做出理解和消化,把女孩的迷蒙和质疑咽回肚里,达到所谓的“彻悟”。
计文君最善于表现人物的淑女气质。不管是《开片》里被大学教授苏戈玩弄的殷彤,还是《天河》中撞见丈夫与赤裸“小三”的秋小兰,她们都能以自己沉静、端庄的方式处理问题,或干净利落地摆脱,或隐忍小心地求全。这种中原女性传统的端庄隐忍,正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最大压抑,失语即是埋葬。作者对此有意回避,不作道德评价与情感鼓动,只将其作为女性成长的“开片”或“剔红”,意在经历失败感情后达成自我的彻悟与蜕变。这或许与计文君所理解的红楼的精髓——“不确定性”有关,她给予每个人物自在发展的空间,不对男性作“负心汉”的评判,也不呈现女性被背叛后的歇斯底里与病态。正如有学者所说,“她的作品里没有怨怼,没有刻薄,没有虚荣,只是理解,理解自我和这个世界。”[4]
二、女性成长的蜕变之痛
必须承认,“女性写作者则会时常陷入两种话语类型的窘境中:一种是支持性别统治的话语倾向,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表达;另一种是坚持女性真实体验的反性别统治话语倾向,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反抗和消解。这种语言窘境直接会产生出一种认同与质疑、抵抗与服从杂糅的创作心理。”[5]15这也是女性常常面临的现代与传统的挣扎。女性的成长从来不像男性,作为主体的他们早已有自己的成长范式和价值判定,而女性,总在长长的暗巷里摸索,并没有一个“现代”或“自我”的参照系,她们从自我身体的认知,从对母亲的反叛,从私语空间等各个角度试图突破那无形的茧。而这其中,必然面临着左右摇摆和暧昧不明。
贞观与秋染们同处于一个“无父”时代,正是“无父”,给予了女性自由选择和自我发展的可能,也让她们的成长更加飘摇。在大妗面对有了日本新人的大舅时,贞观的态度由迷蒙到折服,包括母亲教导的对弟弟们的尊卑之别,“不准贞观将衣服与弟弟们作一盆洗”,贞观是最后才彻悟的,也就是成长过程中的她其实有不解和迷蒙,只是这力量过于微小,很快被传统的洪流所遮蔽。一方面,她在这种被男权内化的母系家族中浸淫、成长,自身也被逐渐内化;另一方面,标志着启蒙和自我的现代对贞观一直是冷漠的,穿西服、西裤的父亲的冷漠,对盐场莫名的恐惧,虽然进入台北像现代女性一样工作,却并未获得身心的收容,她与大信分手所生的病痛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城市给予她的身心创痛。来自现代的启蒙就这样把贞观拒之门外,同时也被贞观所拒斥。城市加之于女性的创伤性体验,导致女性生出回乡的逆旅之心,这在女作家笔下并不少见。
从客体到主体的女性成长,总会面临爱情的梦想:女孩希望男性通过爱情像主人一样把为奴的她们拯救,但这种希望却常常破灭。男性就成为女性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道关卡,成为她们磨砺自我的一个“推手”。对于爱情,贞观把所有的错误归于自身的不够贤德。她在此间经历了大信为了前途对她的忽略与放弃,却没有怨怼,只是将此作为成长必经的破茧成蝶。且其身心自始至终都是“女孩”,并未经历女性成长小说中所常见的性的启蒙与背叛,也没有完成主体的建构,因而只能是“成长”,而非“长成”。
计文君虽然在文化方面笔力不及萧丽红的明净辽阔,却对女性成长进行了具有深广度的开掘。她将女性身心的受难与磨练生动地命名为“开片”与“剔红”,这种命名也为她的女性书写加了一个注解。典型如《天河》中的秋小兰,在姑妈镜像笼罩下成长的她,童年充满了姑父打骂姑妈时躲在床下咬嘴唇、咬鞋帮的恐惧,以及姑妈背上的红花油味。男权的阴影与传统的性不洁意识,让她一直活在恐惧与压抑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成长中的女性总希冀有一只男性的小船(萧舸、苏戈)带她脱离苦海,然而,浸淫商业气息和主体霸权的男性实际上恰恰是这种白日梦的打破者。经历这种身心的破碎之后,女性才明确了男性的不可靠与依靠自身反抗的唯一性。这种破坏一定程度上又促使了女性的觉醒,成为其成长的推手。经由男性在女性成长过程中由主体到客体的降落,男权神话的破除,女性主体才能真正开始建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女性才构成真正的成长与长成,计文君的小说遂成为女性成长的典型文本。
作为闺秀文学,人物能不能摆脱这种被定义的“闺秀”或“淑女”,成为衡量其是否真正破茧的标准。因为“所谓‘淑女’,就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将女性的被动性、依附性、软弱性被视为最高典范并给予的命名,其实就是要求女性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视为一个没有欲求的、任由其他主体摆布的客体。”[5]34而女性成长即是对自我的寻找,“多少年来文化的禁忌与圈套早已内化为女性的自我束缚,把它们一层层地剥离下来才有可能让那被压抑扭曲了的自我还原复活,女性那生命与创作的活力才会像花一样开放!”[6]同样在淑女的外壳里深受其累,贞观将其作为自欺欺人的保护套,秋小兰却在三次衣服的变换中层层蜕下了“淑女”之壳。从沉稳的白衣绿裤到肆意开放的缠枝玫瑰,再到沉淀明净的茶色长裙,她在外表的死静里内含了疯狂的反抗,经由对自我价值的争取、对姑妈的“母性批判”、对男性神话的破除而终于达成了蜕变。对于贞观,她的“彻悟”仅仅是明白了大信在其成长中的过客角色,却并未从从一而终的贞节观里跳脱,淑女外壳仍然是套在其身上的一重枷锁,因而她的成长并未完成。
三、“她者”镜像下的女性自我建构
在女性成长类小说中,我们总能发现有一位“母亲”或隐或显地指引着女孩的成长,如陈染《私人生活》里的乔、迟子建《东窗》中的李曼云、《晚安玫瑰》中的吉莲娜。这类母亲或是妖魔化的恶母,或是温良恭俭的女性亲友,或是具有神秘魅力的女性偶像。而女性成长又必须发生在脱离父权统治的“无父”时代,只有父权缺席的情况下,女性才能获得“自己的天空”。但“无父”又意味着一种价值的失范,“女性意识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性符码系统时,在无法借用原有的男性的理性符码系统表述时,在最初的生命感性经验无法上升为理性语言时,感性的形象的文学语言,就成为她们最好的写作方式与表达方式。”[7]如果“感性”体现为对家庭日常生活、婚姻情感困境的关注,那么“形象”就表现为她必须寻找的一位老师,作为自己的镜像和参照系,在模仿和对比中确立自我呈现的方式。
在贞观的成长中,众多女性人物如大妗、二姨、母亲、祖母、嫂子、姐妹都可以作为参照。同属于一个父权话语系统中,女性“第二性”色彩浓重的大妗,成为她成长过程中的直接镜像。面对男性的抛弃、不忠,她们选择认命、顺从;对于爱情,她们从一而终,在“贞”的牢笼里暗自落泪,把青春和一生都埋葬在陈腐的宅院里。萧家大宅,既是庇护孤儿寡母的娘家,更是囚禁她们的封建堡垒。大妗对于贞观的最终成长为淑女,找到“自己”,起了最大作用。虽然作者认为“当事者心甘情愿,这样做才是自己”,但这种主动纳入父权统治下的驯化和依附,正是女性家族世世代代走不出悲剧怪圈的直接原因。
计文君的小说中,二元的镜像参照更为明显,似乎成为女性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定式。其中,有母女、姐妹、姑侄等,如《帅旦》中的母亲与赵菊书、《剔红》中的秋染与小娴、《天河》中的秋依兰与秋小兰。作者刻意将镜像与主体塑造为性格完全相反的两极,一方古典、恬静、隐忍,另一方就必得现代、泼辣、反叛。作者坦言喜欢“一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互为镜子,一个人物的自我认知和周围世界对他的判断互为对照”。[8]古典的女性固然可以为她们带来精神救赎,但拥有“现代”和“自我”内核的女性,往往在镜像的参照下修正、调节自己,进而向着现代都市作更勇敢的出征。
反叛的闺秀是计文君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最精彩的一笔。她们似乎是作者所钟爱的《红楼梦》中的探春,或静或辣地保守自己的领地。而反叛的闺秀这一主题又可以与《喧哗与骚动》中的凯特·康普生相提并论,这类人物从女性的自我建构出发,直抵社会与时代的核心,成为女性书写深广度的一种标杆。“帅旦”赵菊书以豫剧中的穆桂英作为互文性的对象,她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房子泼辣反抗,不惧身体的裸露和邻里的眼光。在解放前后的历史变迁中,赵菊书由一个柔弱的闺秀主动又不乏被动地迅速成长为“帅旦”,以主体的姿态英勇地捍卫自己的“房间”。这个“帅旦”虽然把战场从国境缩小到了家界,但却收复了女性失去的许多领地,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帅旦”显然被赋予了超越原型穆桂英的力量,她对于现代女性的生存来说意义更大。
镜像的意义,或意在模仿,或意在打破。在对镜像的不同处理中,女性的屈从与建构,作茧与破茧的不同姿态已十分了然。“母亲作为高度社会化的男性文化的产物,她的悲剧正是女性将外在的男性文化压抑转为内化的恶果。她作为社会存在的价值就是充当将女儿带入这种内化循环的引路者。”[6]因而,母亲镜像的打破就成为女性自我建构的必由之路。贞观或许打破了大信的爱情之茧,却不曾打破女性自己构筑的、封闭自己为客体的厚重之茧;她对大妗镜像的依从,则是又走入了女性自缚的茧。而计文君的小说中,不管是“帅旦”赵菊书对隐忍母亲的反叛,还是弱态的秋小兰对强势的姑妈秋依兰的反抗,都经由了镜像的打破。从而,一个新的“我”,作为主体的、自我的“我”,才从影像中破茧而出,化蛹成蝶。正像秋小兰所表现的,女性只有找到自己,成为自己,才能获得快乐,获得方向。
参考文献:
[1]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00-301.
[2]赵园.萧丽红的小说世界:读《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J].当代作家评论,1990(6).
[3]樊洛平,王萌.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66.
[4]刘海燕.河南青年女作家论[J].小说评论,2012(3).
[5]高小弘.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潘延.对“成长”的倾注:近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种描述[J].江苏社会科学,1997(5).
[7]傅书华.新的话题新的言说[M]//高小弘.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代序言.
[8]计文君,张元珂.面向内心的写作[J].创作与评论:下半月刊,2014(5).
(责任编辑:陈丽娟)
The Lady Struggling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The Comparison of Xiao Lihong's 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and Ji Wenjun's Ti Hong etc
HUANG Yuny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written by Taiwanese female author Xiao Lihong, and Tian He, Ti Hong etc written by the female author Ji Wenjun who comes from Chinese mainland, which look back to the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in social changing, and the works also cut into the chang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hu⁃manity and soul from the female perspective. Their works focus on the hard trip of female who construct herself via the double reference of the male lover and female image in the era without father. W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choices made by the two ladies written by them: one returns to the hug of traditional, the other one struggles towards the modern shore. Whether female truly construct herself or not leaves a space for readers to analysis and ponder.
Key words:Xiao Lihong; Ji Wenjun; traditional culture;female grow-up;female image
作者简介:黄鋆鋆(1992-),女,河南省平顶山市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湾文学。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研究生核心学位课程项目“台湾文学研究”,立项编号:YJSXWKC201557。
收稿日期:2015-11-28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16)01-0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