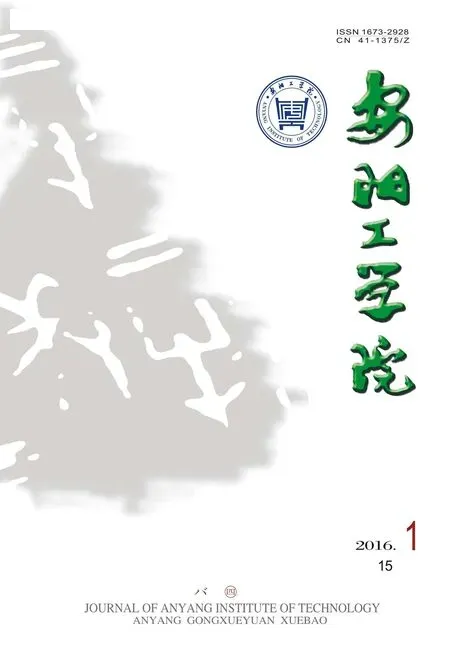婚恋中的女性困境——《心锁》与《晓云》人物形象对比分析
江梦洋(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婚恋中的女性困境
——《心锁》与《晓云》人物形象对比分析
江梦洋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台湾长篇小说领域,女作家林海音的《晓云》和郭良蕙的《心锁》,透过以女性为中心的不伦之恋故事,大胆碰撞了婚外恋描写的题材禁忌,由此探讨了女性婚姻与爱情的复杂命题,且敏锐地触及了台湾经济起飞时代社会价值观的最初变异。通过两部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本文意在揭示两位女作家企图表达的真相: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弥漫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价值观冲击下,传统的情爱观念和婚姻生活原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女性所追求的爱情婚姻理想往往会在现实中破灭。
关键词:《晓云》;《心锁》;痴情女子;母女关系;婚恋困境
郭良蕙与林海音同为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两人都著有大量关于女性婚姻与恋爱的小说,对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和推动作用。郭良蕙的《心锁》与林海音的《晓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化的时代背景下,描写了以女性为中心的不伦之恋,是具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两部小说均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年轻女性在婚姻与爱情中的迷茫与沉沦,以细微的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内心,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在社会风气刚刚解放的环境下大胆涉及了婚外恋、第三者等有悖传统伦理道德的话题,展现了婚姻与爱情的错位,以及女性在婚恋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
一、深陷迷途的痴爱女子
《心锁》是郭良蕙小说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争议性的一部,作品讲述了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女主角丹琪在几个男人之间周旋的故事;林海音的长篇小说《晓云》中同样有一个热烈追求爱情的女子晓云,她所陷入的是一桩婚外恋情。两位女作家深入女性心理的隐秘领域,塑造了两个深信爱情、深陷欲望、不知不觉走上不归之路的痴情女子形象。小说中男女爱情理念的不同以及女性自身的脆弱与彷徨注定了女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通过这种故事构架,两位女作家旨在揭示社会变迁背景下女性的爱情理念和生存困境,更深层次地透露出人性的变异和冲突,以及人生命运的变化无常。
《心锁》中的美丽女大学生丹琪,是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女性形象。丹琪原本与大学生恋人范林痴情相爱,但范林出于对金钱和地位的渴望,后来和富家小姐江梦萍订了婚。万分愤懑的丹琪怀着报复心理接受了梦萍的大哥江梦辉的追求,不料梦辉却是个性格憨直、毫无生活情趣、更不懂得浪漫的男人,以至于丹琪在婚后难以拒绝范林的诱惑,终于旧情复燃。深陷于道德谴责的丹琪,给梦辉以暗示希望能拯救她,梦辉却并未觉察。他的弟弟梦石则是个情场高手,此时趁虚而入,又将丹琪拉向了更加罪恶的深渊。小说以对女主角丹琪内心大胆的性心理描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相较于传统男权话语社会中贤良淑德、内敛矜持的女性形象,作家对丹琪内心的性渴望描写可谓极富突破性。透过丹琪的心灵,作家想要描摹的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那些被金钱的腐朽和贪婪的欲望所侵蚀的人性。“罪恶往往是富于刺激性的,因此披着诱惑的外衣,只是从罪恶里寻找到的欢乐是暂短的,剩下的漫长时间将被悔恨所占据。像丹琪那样年纪的少女,多半是富于幻想的,尤其对于两性关系充满了奥秘感和新奇。少女的感情又太脆弱,经不住诱惑,失足,经不起打击,报复,结果都是自造痛苦,难以解脱。”[1]340在丹琪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女性的脆弱、敏感、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以及人性内心深处的欲望。欲望对丹琪的操控,超出了她所能控制的程度,她于是失控地一次又一次犯错,一次又一次沉沦。她也有强烈的占有欲,一开始正是因为害怕失去范林,才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后来她又害怕失去所拥有的一切,于是不断地补救,却无奈陷入罪恶的深渊。欲望是造成丹琪悲剧的根本缘由,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人所普遍面临的心灵考验。
在林海音的《晓云》中,夏晓云则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单纯女孩,她原本对爱情抱有纯真的幻想,虽然有一个亲友极力撮合的对象俞文渊,但晓云却认为他不是真爱。她在做家庭教师时爱上了学生家的男主人梁思敬,由此从内敛自卑的性格逐渐转向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一次又一次欺瞒家人和朋友做出疯狂的举动,沉沦在婚外恋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在晓云身上显示出爱情对于女性内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会让人迷失自我和方向。竭力追寻真爱的晓云排除一切阻挠,忘却一切道德的约束,只愿和心爱的人奔向幸福的前途,却最终被现实打回了原型。晓云的悲剧是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她对爱情的强烈渴望使得梁思敬这位成熟的已婚男子趁虚而入,占据了她内心的全部,并为之疯狂;她的家庭环境又造就了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性格,家庭不健全,父亲的缺失,母亲同样陷于不伦之恋,使她常常感到孤独、自卑、敏感而脆弱,外表的柔弱和内心的孤寂、执拗,促使她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晓云是怀着对爱情的纯真渴望和对梁思敬相同命运的认同感而陷入了不伦之恋,造成晓云悲剧的是爱情本身,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不被人接受的爱情终究只能是惨淡收场。
两位女主角同样追求纯真的爱情,对爱情抱有天真的幻想和渴望。与此同时,她们的内心却都有压抑和克制:一方面来自家庭的教育,一方面来自道德的约束。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她们的爱恋对象都深陷于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于是她们共同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爱情与婚姻的错位。她们所追求的灵与肉、婚姻与伦理道德的统一总是难以实现。通过这样的形象塑造,两位女作家都想要表现出女性在这样的时代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自我内心的挣扎,以及理想的最终落空。不同的是,郭良蕙注重通过女主人公的性心理描写,表现其内心的脆弱性与在欲望中的沉沦,迷失在道德与欲望的双重矛盾中。而林海音作为一个具有母性关怀和人间大爱的女作家,在她的作品中更多表现出的是同情与宽容,作品中透露出爱情是命运使然,深陷痴爱中的人是无罪的观点。
二、相依为命的母女关系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家庭关系非常相似。父亲形象的缺失,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成长,以及上一代同样陷于非道德恋爱的背景,对于女儿的心理影响和剧情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心锁》中的丹琪与母亲多年相依为命,父亲与母亲长期分居,并和丹琪的表妹在一起又构成另一段不伦之恋。母亲对于父亲充满了恨意,出于报复,坚决不跟丈夫离婚,使父亲始终生活在道德和伦理之外。上一代的恩怨,以及母亲自幼对丹琪的保守教育,对丹琪的心理产生了一定影响。小说中多次写到丹琪在陷入欲望的深渊之时,脑中总会响起母亲的话语。例如在范林对丹琪第一次进攻时,丹琪就因为想起母亲的话而拒绝了他。在丹琪每次做出有违道德伦理之事时,也总会想起母亲对她的训示。母亲总是对她说:“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这是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也是一种偏见和执妄。而实际上丹琪对她的表姐并无芥蒂,在多年后见到她时很快就原谅了她,并且深深地同情她,因为她们具有相同的命运。母亲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教育女儿,真切地希望她们不要重蹈覆辙,这是全天下母亲共同的心愿,但大多时候,带来的却是女儿表面的顺从和内心的叛逆。
晓云与母亲则在成年后才相聚。由于母亲的离经叛道,爱上了自己已婚的老师,所以只得逃离故乡,将孩子托由晓云的外祖母照顾。直到抗战胜利后外祖母去世,全家来到台湾,晓云才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深受母亲的影响,形成了执拗的性格。不久后父亲又去世,母女变成了真正的相依为命。母亲的长期独居又给晓云带来了压力。她曾偷看到母亲写给林教授的信,明白了是因为她才使母亲不敢接受林教授的追求,同时母亲和父亲的经历也使得晓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认为只要是真心相爱,婚外恋也不无不可。这种错误的导向致使晓云的爱情最终走向了偏离道德的轨道。台湾作家高阳曾对晓云和母亲的关系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晓云母女在爱情上的惊艳,前一半是‘历史的重演’,后一半所以有差异,是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她的亲属关系由母系上推,两代寡妇,两代孤女;……作者是写一个故事的两种发展,也可以说是把一个主角化身为二:女儿现在的经验,是母亲二十年前的经验重现;母亲现在的境况,是女儿将来的境况的预告——如果女儿重蹈母亲的覆辙。”[2]101-102由此可见林海音在安排母女两代同样命运的深意,便是揭示女性在婚姻与爱情之间不可化解的矛盾与彷徨。
母女关系是女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男权话语统治的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往往通过女性命运的发展来表现。母亲和女儿是女性与生俱来所拥有的角色,二者之间又是血肉相连、充满着冲突与对立的。母女之间血脉相连的命运对女性恋爱观念的影响,注定了主人公最终走向的命运之途。两位母亲都深爱着自己的女儿。丹琪的妈妈对丹琪的管教严之又严,全都是出于浓烈的爱,生怕女儿走上自己的老路。晓云的妈妈则是为了女儿放弃了自己的幸福。林海音透过晓云说出:“母亲对我的爱,正像蛛丝缠住了我俩的脚。”[3]14然而两位女儿却无可逆转地都走上了畸恋的道路,这是无奈却又必然的。女儿对于母亲始终是爱恨交织。母亲是束缚她们行为的约束者,但无形中也会成为一个导向者。她们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沉浸在欲望的深渊时,总是会想起母亲的谆谆教导;当她们欺骗母亲时,内心又会充满愧疚;但当她们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时,母亲又会成为为支撑她们继续下去的依据。与此同时,对于犯了错误的女儿,母亲即使再痛心,也不会过多责备她们。丹琪的母亲在遇到丹琪和范林私会后,只得拉着丹琪向上帝忏悔;丹琪在范林和梦石两败俱损、事情眼见要败露之时,第一想到了去妈妈那里寻求庇佑,因为妈妈一定会宽恕她。对于晓云来说,妈妈在得知她和梁思敬的私情后,因为自己的过去,难以责备她,连劝解的话都说不出口,自己却急病了。对于的女儿的关切,体现着最博大的母爱,也包含着母女之间难以消解的矛盾。
三、金钱至上的男子形象
两部作品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台湾社会经历了工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展开。金钱至上的理念摧毁了许多人原有的价值观念,贪婪的欲望侵蚀了人们的心灵。在这种背景下,两位女作家同时刻画了为名利放弃感情的男性形象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不约而同将男性置于对爱情不忠的地位,与女性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形成强烈对比。
在《心锁》中,郭良蕙塑造了三位性格迥异的男子。范林和梦石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产物。工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急遽变化,社会财富的集中使得阶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由此造成了人们心理的失衡。范林对于金钱和地位的渴求,梦石对于刺激和快感的追求,都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在社会中失却理想的典型心理。大哥梦辉虽沉稳,却有些过于木然和呆板。《晓云》中的梁思敬,面对自己的初恋情人和一份好的前程,毅然选择抛弃了前者。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人性内心深处的欲望似乎永远无法被填满。
对于郭良蕙《心锁》中的男性形象,她的兄长曾做出评价:“女作家写女性,自然是当行出色。女作家写男性,写的那样真实、深刻,应当说是非同一般。”[4]2男性与女性价值观的截然不同,形成了男女主人公心灵之间的隔膜,也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不同的是,郭良蕙对于范林这样的男子无疑是批判和不齿的态度。但林海音对于梁思敬,却透过晓云的目光和心理,表达出同情与理解。在别人都说梁思敬的不轨行径时,晓云却相信他是迫于无奈的。林海音更多地表现了二人对爱情的追求,希望突破世俗的界限而获得爱情的圆满。总之两位作家通过对男性形象的刻画,折射出他们与女性对于爱情的不同追求,对于婚姻的不同理解,最终还是表现出身为女性的悲哀。
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与比较,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两位女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林海音以温婉细腻的笔触表现了女性追求的理想爱情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的境况,表达了她深切的同情和对爱情的赞歌,以及对女性不能实现爱情理想的悲叹。郭良蕙则通过描摹像丹琪这样沉沦在欲望与道德深渊中而无法自拔的心理,剖析了人性阴暗面和罪恶面,表现出当时社会的拜金主义倾向,以及女性的生存悲剧。两位作家都透过对个人情感境遇的书写,反映出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最终都指向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以及人生在世命运的无常和无奈,表达了她们对爱情和婚姻、人生和命运的深层思考。
参考文献:
[1]郭良蕙.我写《心锁》[M]//郭良蕙.心锁.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初版后记.
[2]高阳.云霞出海曙[C]//李瑞腾,夏祖丽.一座文学的桥:林海音先生纪念文集.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2.
[3]林海音.晓云[M]//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裥裙.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4]郭良夫.小妹的小说[M]//郭良蕙.心锁.北京:台声出版社,1989:郭良蕙小说系列序.
(责任编辑:陈丽娟)
作者简介:江梦洋(1991—),女,郑州市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湾文学。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研究生核心学位课程项目“台湾文学研究”,立项编号:YJSXWKC201557。
收稿日期:2015-12-3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16)01-0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