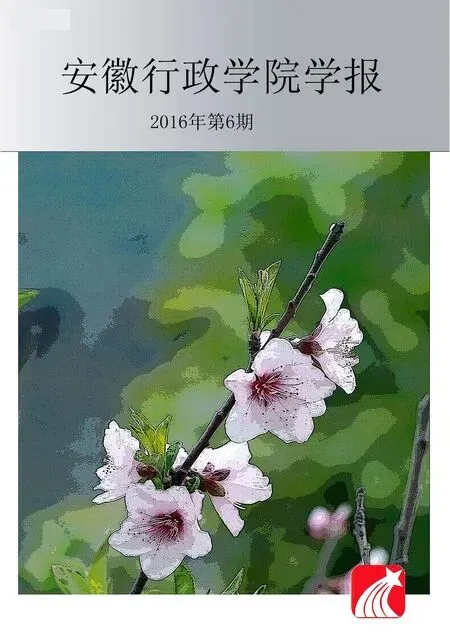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分析起点及其特征
——兼论“利益”作为分析起点的局限性
王志行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理论视点
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分析起点及其特征
——兼论“利益”作为分析起点的局限性
王志行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中国政治学研究自恢复以来一直努力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构建更加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对于政治学的理论基石也经历了从以前的“阶级说”到如今的“利益说”,从而使政治学摆脱了革命烙印,但以利益为逻辑分析起点也有自身内在难以避免的困境和局限性,文章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逻辑分析起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需具备的特征。
中国政治学;分析起点;利益
政治学理论自诞生以来在探索人类政治社会基本分析单位的道路上从未中断,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原则试图建立起政治学的逻辑起点,以期达成政治学理论的逻辑自洽,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不断拓展,而且在发展中政治学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愈加紧密,使得理论的解释性与宏观性之间在你消我长中向前推进。近代以来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后,政治理论的发展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天然的现实关怀导向,其每发展一步都带有深深的现实烙印,反映出政治学理论自身的理论使命与走向相关。同时,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分野变得相对模糊,使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难以摆脱价值因素的影响,而规范性研究也有借鉴行为主义研究途径的倾向。并且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国家、政体、统治者、公民等静态的制度、主体等,而是随着政治现象的复杂程度而变得越来越多元,从静态的制度、法规、规则等到动态的行为,从具体的政治现象到抽象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这并不是说在中世纪及以前政治哲学的“纯粹性”更高,或是与现实的联系不密切,而是说在现实的复杂程度较低时政治学理论的单一度相应呈现出更高的面貌,因而在近代以来政治现实的多元性要求越来越丰富的政治理论。中国在19世纪与国际“接轨”后固有的政治学说也被打破而卷入世界上占主流话语的国家中的政治理论中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学话语紧跟世界潮流,一时出现了“有世界无中国”的宏大视野与微小解释力的矛盾状态。然而在政治理论与现实的不可分割性的规律下,中国的政治学尤其是在近几年越来越将理论目光转回国内,寻求建构与我国的政治历史与现实相契合的政治理论,在此基础之上探求政治理论的更准确的解释性与更普遍的宏观性之间的平衡。
建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分析的逻辑起点,新中国的政治学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将利益作为政治现象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起点。当前由于我国的政治语境和政治现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作为理论分析起点的利益也出现相应的转向。
一、以“利益”作为分析起点的转向
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历史唯物主义由利益作为起点建构起宏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利益是最抽象的最简单的范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本原和根据。从利益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全面论述了利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形成一套逻辑严密的论证体系。反观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是从对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界定开始,进而考察在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中由于利益差别导致的利益冲突,产生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立,这种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并推动阶级斗争的开展和社会的变革。因此,整个社会是利益运作过程的集合体[1]。利益差别一旦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环境下就不可避免地形成阶级差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只有在战胜了资产阶级之后才能真正完全实现自身利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生产力极度发达,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时国家将不复存在,阶级随之消亡。
马克思主义着重从利益的物质属性出发,与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观相联系,抽象与具象结合形成了利益(抽象)—劳动(具象)—阶级(抽象)的螺旋式逻辑关系。利益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在这一基础范畴上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通过劳动获得利益,劳动是利益的物质实现形式。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性使得无产阶级劳动不断异化,利益的抽象意义转换成社会分层意义上的阶级差别。在这一体系中与其说阶级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不如说是其在饱满的利益理论之后有意识地建构其阶级学说的理论前提,从而顺利地将理论重点放在国家的阶级属性方面。尽管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为其阶级学说服务的主要使命,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革命学说、未来社会学说等都是以阶级学说为基础。可以坦诚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利益这一抽象范畴上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为我国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主要表现在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形成与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纲领。在多种尝试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努力失败,中国人民陷入民族民主危机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成功地将阶级意识纳入到广大人民中,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全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向,培养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合的革命土壤。新中国建立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新中国的领导人夸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地位,试图通过单纯改造生产关系来弥补生产力不足带来的问题,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主要矛盾视为生产关系,人为地制造了阶级斗争依然激烈的假象,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规律,给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了重大损失。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弯路,与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只能作为其一部分,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不等于在任何时候都把阶级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而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换句话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是在其利益学说的基础之上的“二次”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利益的研究走向了阶级学说。我国在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实践直接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围绕阶级学说的基本理论,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足且对生产关系的作用夸大导致新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主观意志被过分推崇,人为地将由于物质条件匮乏的弊端强加于生产关系上,进而妄图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来弥补生产力不足的问题,这本身是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化歪曲理解,也是对在客观环境变化下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劳动产生了利益差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主要社会阶级的利益决定政治关系。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所有,生产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而是平等合作,其最高发展阶段是能够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全面发展。因此,在对国家的认识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应摆脱旧有的基础,将目光向前移,从其更高层次的理论建构寻求药方而非将事实建立在理论之上。新中国走的这条过分看重主观意识而忽略客观环境的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道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惨痛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摆正理论姿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利益观立场,将国家大政方针转到生产力发展上来,坚持实事求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行动的最后根据[1]。这是对阶级斗争的彻底抛弃,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学说的重新审视,结果是正确地将“利益”这一基本范畴提取出来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从而摆脱了革命惯性,既维持了革命之后对人民这一群体的阶级存在的肯定,又从更高层次上重新审视国家的群体结构,按照利益而非阶级划分,超越了阶级的狭隘性,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缓和性的政治分析单元,使得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有向一般性理论即适用范围更广、现实解释性更强的理论趋向,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建设。
以“利益”作为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分析起点,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是以利益为基础,利益是需要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以实践成果为基本内容,以主观欲求为基本形式,以自然生理需要为前提,使需要主体与需要客体之间的矛盾得到克服,需要主体对客体进行分配,从而使主体满意[2]。利益是思想的基础,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有主体关系、客体关系、集团关系。利益差别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而导致利益差别的原因有很多,如人的自然需要跟社会需要的差别、社会劳动分工的差别、由旧式分工造成的差别以及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占有的差别等[2]。利益差别、利益冲突等属于围绕利益而生的基本政治学话语,在将利益理论去马克思主义化、构建一套理论性强、解释性强、宏观性强的努力中产生了许多较为有益的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属王浦劬在《政治学基础》中构建的一套以利益为基础的理论分析路径[3]。他以利益的内在矛盾进展到社会利益关系,而社会利益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利益差别分别形成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按照这两条主线在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领域内分别进行了分析,从而形成了包括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政治主体、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在内的政治学基础理论。这种理论的优势在于从政治的根本起点出发建立起完整的逻辑链条,包含了政治生活的全部活动,并且与逻辑起点保持严密的逻辑关系,因而实现了宏观性与微观性、抽象性与实践性、整体性与开放性的结合。同样以利益作为逻辑起点形成的中国化政治学逻辑体系里还有整体利益论、广义政治论等理论,它们相互之间并无矛盾之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相同出发点的基础上由于关注对象的范围、视野等的差异形成的不同理论解释。并且二者都较为抽象,关注的是政治理论的根本性概念,把人类、人类社会作为主导话语。
理论的发展源于现实需求又能指导对现实的理解和解释,因此,真正检验或审视有关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逻辑的努力就需回归到我国的政治现实中去,结合我国的政治历史与发展阶段。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前提下开展的,因此社会现阶段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既有利益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同时改革导致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具体利益的差异性,是利益矛盾容易激化的敏感时期,由于群际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不平衡,必然造成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矛盾冲突。在指出当前我国的利益现状之后,王伟光认为现阶段我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还没有达到能够决定政治关系以至于改变现有政治结构的地步。而主要阶级的利益决定政治关系[4],因此,在对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上要保持清醒客观的头脑,一方面要认识到当前我国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客观存在,承认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会对政治、社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要明晰我国主要的阶级仍然是人民大众这一基本事实,局部的、短期的、小范围的利益冲突无法改变我国的主要利益矛盾性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人民是发展成果的最终享用者。并且,利益冲突的形式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2]。对抗性利益冲突意味着双方的根本利益不相容或对立,非对抗性利益冲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或者由于实现条件和实现时间的制约,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不能同时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从根本上讲,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完全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依然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非对抗性利益群体,而只要政府里面没有被利益集团掌握,政府本身没有成为一种独特的阶级,就不会与公民成为相对立的阶级[4]。
那么,既然社会主义时期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如何化解当前的利益冲突呢?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既然利益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的基本规律[1],这就需要在遵守利益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
首先,充分利用利益的激励机制。利益是人的行为的动力源泉,应从思想动机上将人的情欲冲动转化为需要,并将需要刺激转化为动机,使主体能够树立利益目标,有意识地谋取利益,并克服各种制约因素,从而实现利益[2]。利益激励分为物质利益激励和精神利益激励,激励方式有正面和反面激励。其次,及时跟进利益的协调机制。利益的激励机制解决了利益的获取问题,那么在获取利益之后,由于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会不断发生变化,影响利益获取的因素复杂导致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差异性存在,需要及时利用利益的协调机制对利益进行适当的二次分配,以形成健康的利益关系。具体的协调途径有政治协调、经济协调、法律协调、道德协调等。在当前我国复杂的利益格局下,出现利益冲突与经济与政治的利益协调机制不足有关,“被剥削阶级之所以是被压迫的,是因为他不掌握能够像剥削者那样充分有效的实现自己利益和意志的足够手段。”[4]公民参与渠道扩大化、有形化、高效化,形成良好的对话机制。经济上加大创新力度,向持续、健康、整体发展迈进。
因此,从当代学者企图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努力来看,不仅是在理论上试图淡化多年来的阶级学说色彩,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和关怀,试图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相连接以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无缝对接。这种做法非常值得肯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需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站出来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为现实提供解释性理论和指导性理论,这也正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最高表现。
二、以“利益”为分析起点的局限性
不难看出,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学者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论作为政治学分析基石时普遍是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强调利益的物质基础,在论述由利益引发的社会基本关系及解决出路时注重利益的物质性根本特征。但是以“利益”代替“阶级”来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基石指导政治实践也由于其自身在哲学层面上的模糊性和逻辑结构上的开放性以及实践层面上的宏观性等方面的弱点而存在许多局限性。
首先,在哲学层面上,由于利益是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概念,不同于政治学分析的其他起点,如社会分层、社会关系、社会规则、社会具体要素等为具象意义上的逻辑起点,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这种分析视角可从实践中得出调查结果或者有形观察,并非人为杜撰也非严密的假设想象,这种理论基石在政治现实中比较容易把握,现实导向性强,对政治现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解释力。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隐藏在具象背后的抽象概念的考察和搭建容易导致对动力性因素的忽略。这种不足的弱点恰恰在从抽象意义上的人性假设来把握人的社会活动作出的解释中得到弥补。从人性假设出发能够推导出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权力关系、权力结构,这种抽象的假设能够形成自洽的逻辑结构,将政治还原到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人”,分别从人的不同特质如道德性、理性、社会性等特征出发来说明人的行为,进而论证政治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进而解释制度、体制、机制的选择与建构,从而使得任何客观的政治现象都能回归到人的层面得到解释。但这种理论逻辑本身的基础是一种主观假设,个人道德性品质是否存在单一性规律存在许多质疑,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难以单纯从个人品质层面上进行定论的情况比比皆是。且这种假设根本上看是一种二次假设,因为在假设人性的前提之前是先对人性的各种特质进行区分,这就说明了人性本身的客观存在性。而对其特质的假设其实是埋没或忽略了人性中的其他成分,并且会带上时代烙印而更加飘忽不定。因此既无法保证二次假设本身的客观科学性,也无法保证对人性特质的全面理解,结果是将政治行为建立在本身就难以确定的基础之上的理论逻辑很难形成说服力极强的严密结构。
因此,从具象意义和抽象的假设意义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漏洞,那么,将利益作为理论基石能否避免这些弱点呢?很难下定论,这是由于利益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特征。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利益与社会生产相联系,因而着重强调利益的客观性。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并以物质利益的形态表现出来,利益与特定的社会关系相结合形成不同的阶级属性,并且从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利益的差别。因此,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利益是客观存在,人类并不能主观想象更不可能人为创造,人类只是通过劳动发现了它,进而发现由利益产生社会关系。而许多西方其他理论则是从利益的主观性出发,认为利益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判断的,利益多少、需要何种利益、利益的紧迫程度等都由人主观确定。如功利主义将利益纳入一种抽象的主观享受范畴。因此,对于利益的主客观性质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到利益的界定、评估、实现利益的手段等一系列问题,甚至会走向相反的理论路径,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分离一样。利益本身是否为人们像假想出自然状态一样的假设概念。如果不是,那么利益从何而来,利益在根本上是否是具有主观性或客观性的单一性质的概念,抑或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物。不同的理论学说都是建立在对利益特性的一定界定基础之上的,我们本无需追究利益本身到底是呈现出什么特性,就像无需去探底自然状态是否真正存在过。但需要明确的是在对以利益为逻辑基石的政治学理论进行阐释时需要超越从前的学说,建立更具包容性、延展性的理论。而当前尽管中国政治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超越或者创新体现在将利益而非阶级视作政治理论起点,但对利益的论述其实并没有做出完全超越马克思主义对利益的分析。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的本质内容是否仍然是经济利益值得怀疑。利益的主客观性并未得到明确答复的同时,再深入思考现有理论对利益本身的思考和论述并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论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利益是由个人的主观需求为基本形式,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以实践成果为基本内容[2],因此,利益的物质属性是其本质特征,而这种物质属性的外在表现为经济利益。并且在一国社会发展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更加外向且易测量,往往成为掌权者优先考虑和安排的事务。但利益的内在内容是否只有经济利益值得怀疑。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自我发展属于最高层次的需求,生存与安全即物质方面的条件只是最低层次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在理想的未来的社会中生产力大发展带来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种发展想必不只是物质需求得到无限满足而已。在现实的经验层面上来讲,主体的利益也表现具有许多层次,经济利益占据重要地位,但主体的所有利益绝非仅以经济利益就可以搪塞过去。
如果承认了利益的多样化内容,那么如何来区分不同内容的利益相互之间的关系,占据决定地位和次要地位的分别是什么利益,各种利益的满足机制是什么以及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机制如何开展等都是需要更深一步分析的问题。
再次,将利益作为分析起点是政治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向一般性做出的努力,但是一般性越强,抽象程度越高,其显示解释的效用性越低。因此,果断抛弃阶级作为分析起点而启用利益的分析路径固然可以避免由社会发展带来的理论局限性问题,但其同时也会产生其他问题,抽象程度太高即是学界不得不面临的难题,理论的最终目的和使命仍是要回到具体事务中,若对现实政治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有效的解释力那么其存在的指导性意义难免就会大打折扣。再者,过于抽象还有可能使理论的拓展性太强而导致衍生或细化了的次理论与次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不紧密,无法形成内在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再次导致对现实的分析和解释无力。
通过对利益作为分析起点的局限性的分析使我们不得不正视两组关系。首先是中国政治学与国外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笔者坚信知识与思想的形成与流动并无国界,但同时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密不可分性这一已经公认的共识也毫不质疑,尽管既有的理论难以定性为某国或某地区的理论,不过相比于认为某一理论更加适用于某国或者说是某国的理论,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论断更加令人难以接受。本土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依托和保障,只有如此才能拥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安身立命之地。因此,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在不断捕获、学习西方政治学理论、套用其学术话语来解释中国政治现实建构中国政治学的时代似乎正在或应该发生转向,在政治学本身中划分出一定意义上的所谓“中国”的成分,在当前我国的政治发展中有着迫切的必要性和理论的可行性。其次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关系。我国的政治学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阶级、国家、革命、斗争等学说作为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术语,将利益作为分析起点,沿着一条由利益的差别性和共同性衍生出的阶级、阶层进而斗争、革命的分析路径形成我国政治学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指导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并已上升为宪法成为全民意志。但在利益的分析途径上既然出现了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政治学理论就应该寻求理论上的更高程度上的自洽性,或者抛弃现有理论,或者弥合现有理论的不足。而摆在当前我国政治学者面前的历史使命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从前存在的约等关系或主理论与关键子理论的关系转变为继承与创新、源理论与衍生体之间的关系。
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基石的特征瞻望
经历了革命—改革之后,我国已经平稳迈入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结构、利益结构、社会结构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明显化。各个利益群体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2]。为避免走入国家被某些占有社会主要资源的利益集团所控制而走入改革怪圈,必须提出先进的具有高度解释力和效用性的理论来指导改革。沿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对我国当前构建起以政治实践为基础的一般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的学者自政治学恢复以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为指导,积极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尽管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等学术思潮传入中国以来对本土政治学带来了许多启示和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学界对政治科学的态度不一,但普遍认为中国需要构建起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以适应本国的政治实践。当前我国的政治学在理论体系、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方面进行了新的论述和大胆创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5],在如何构建起政治学的一般理论方面,朱明雄的《整体利益论》、王伟光的《利益论》、王浦劬的《政治学基础》,都将利益作为逻辑起点,清华大学的吕嘉也认为政治学的基本范畴是政治需要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利益范畴,在建构完整理论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对如何建立我国本土政治学的分析起点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尽管如此,我国政治学在基础理论建构和国外政治学本土化的努力方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论的建构尤其是政治学的理论建构要与国家的现实相契合,我国的政治学在吸收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同时也应反思未来的发展,正确处理中西方政治现实的差异性以明确理论产生的土壤因素。综合国际与国内、历史与当前,西方的资本主义自17、18世纪以来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与磨合,而进入资本主义的完善阶段。而我国的社会主义仅经历了不到70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家发展道路曲折,综合实力水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因此,不论是从国家性质还是国家发展进程来看,中国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学必然会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如果中国的政治学一味地追求与西方理论靠拢,企图建立在已有的话语体系下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宏观理论,结果有两种可能,要么彻底西方化,成为西方政治学理论下的子体系,解释性强而宏观性不足,沦为削足适履的工具,要么宏观性有余但适用性差,无法理性认识、正确解释中国的现实,因此,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构建起与我国的历史与当前、社会性质与发展程度相关的理论体系。
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尽管国家间的性质差别不断在淡化,国与国之间的区别更多体现在中间的具体环节上,如在对民主的共同认识上,对于在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等问题上有所差异。作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必然会是现实的一定程度反映,政治学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它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政治生活新现象、新态势的关注和研究,其落脚点和出发点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具体或抽象地、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具体的政治现象上。因此,我国的政治学理论范式必然会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从理论上讲越为宏观、严密的理论其历史继承性越强,西方的政治学尽管分支众多,能够对世界许多其他国家政治学产生很大启示,但其源远流长,有较多深厚的理论根基,从根本上讲与西方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相匹配。而我国与西方国家经历了完全相异的发展进程,漫长的封建社会伦理政治观占据主导,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我国的政治学理论冲击的责任首先在于吸收伦理政治观的合理成分,构建起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历史相匹配,并且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政治学理论框架。
由于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经历了漫长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而如今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当前我国主导的政治话语为改革、国家治理等,基础性的理论分析一般以利益为起点,对于我国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有指导意义。许多政治学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有益探索,理论成果颇为丰富,与我国当前的政治实践较为契合,理论解释性很强。那么随着改革的攻坚阶段结束,国家日益迈入小康社会,作为理论先导的政治学需要思考能够指导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更为宏观的理论框架。因此,新的政治学逻辑起点应同时协调三种因素:一是观念上破除封建社会等级制,强调地位与机会的人人平等,即正确科学地扬弃传统政治文化;二是与社会主义性质息息相关,将人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三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能指导未来国家发展的大方向。
要清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既要防止全盘否定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又要警惕有些人过度推崇传统政治文化而忽视传统中不利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因素。窃以为要真正清楚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之所在,将其与现代政治文明结合起来,当然要明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政治文明的相互排斥的因素和可以相互融合的因素,或者换一种思维,就是从现代政治文明入手,认为现代政治存在哪些矛盾,从传统文化而不是西方理论中寻求答案而是“试错”的过程。
强调政治理论基石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相适应并非否定政治理论的宏观性、规范性和逻辑自洽性,而是关心这样的理论逻辑能否对中国的政治建立理论和实际之间的联系,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政治与西方政治或者全球政治是否有区别,有何区别,为何有区别。中西方在政治历史发展路径和现实呈现结果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中国的政治转型而引起并且在动荡中继承着一定的传统政治文化,并且在与世界的政治融合中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中西混杂型政治文化。其内在机理运行高效,但并不符合西方主导的现代政治基本价值,这种内外矛盾越来越成为饱受世界诟病并为国人认识而反思的不可回避的现象。现有的政治哲学并不能解释为何出现这种矛盾,提出的措施构想也难免因植入而无法适应,因此,政治学理论基石的构建还应从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入手,将传统政治文化纳入现代政治理论的视野中才能真正建立适合于我国当前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理论。
[1]谭培文.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锡克·O(Sik,Ota).经济—利益—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杨海蛟.新世纪新拓展:政治学理论研究概观[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The Analysis Starting Poi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On the Limitations of“Interest”as the Starting Point
WANG Zhi-hang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Since the resumption,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has been trying to build a more advancing theoretical system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political science,while the cornerstone of political theory experienced from the previous“class theory”to today'“sinterest”,thus politics got rid of the imprint of revolution.However,taking interest as the logic analysis starting point has its own inherent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There’s a larg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to establish the logical analysis starting point of politic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he features are also considered.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analysis starting point;interest
D0
A
1674-8638(2016)06-0005-07
[责任编辑:张 兵]
2016-09-11
王志行(1989-),女,河北邢台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现当代中国政治。
10.13454/j.issn.1674-8638.2016.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