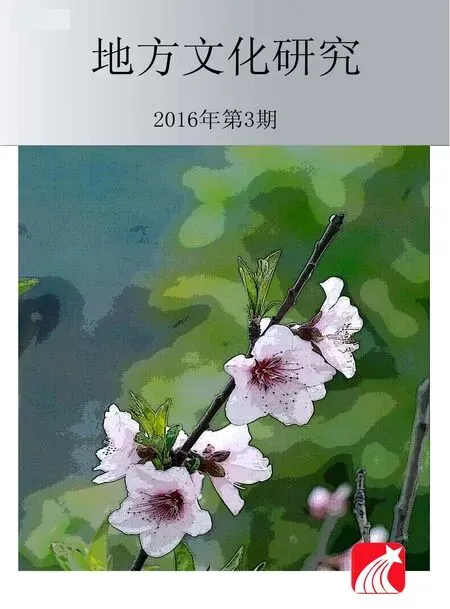花山女神信仰的复苏与变迁——湖南江永县花山庙的人类学考察报告
伦玉敏
(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116600)
花山女神信仰的复苏与变迁——湖南江永县花山庙的人类学考察报告
伦玉敏
(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116600)
花山庙重建与民众的社会记忆和信仰需求有关,然而作为地方性民间信仰,女神信仰的宗教资源相对匮乏单一,文化资源也未能得到充分地利用和发展,导致其处于被民众选择性淘汰的危机之中。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女书”活动的中心地区——湖南江永县社下村花山庙的重建经过,分析了当下花山女神信仰的功能和现状,指出只有通过“女书”文化和女神信仰的互构,才能实现两者的可持续发展。
民间信仰;复苏与变迁;“女书”;互构
庙宇重建和信仰“复苏”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民俗文化的肯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开展,使得蛰伏已久的民间信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庙宇、宗教师、仪式、信众重新活跃在大地上。然而有些民间信仰在香火缭绕不久复又沉寂,甚至消失,有些则香火日益旺盛。任何信仰都是民众选择的结果,在当下,一种可持续的民间信仰既要符合民众生活需求,也必须有“传统文化资源”为支撑,如果具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格,它的发展会更迅速。但是,仅凭这些条件,处于法律边界的民间信仰也并不能获得长足性的发展动力。
2012年,笔者曾在湖南江永县专就与目前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女书”①“女书”,系在我国湖南江永、道县一带妇女中流传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女性文字。一般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女性专用的语言文字,又称“女字”,当地妇女把男性使用的汉字称为“男字”,自己所使用的文字称为“女字”或“女书”;二是指用“女字”书写的作品;三指书写“女书”的载体,如扇面、巾帕、女红、纸帛等物件。现实中,“女书”的这三层含义是并存的,只是在有些场合会突出其某一方面属性。在学术研究中,往往倾向于“女书”作为“女字”的属性,其作品和物件往往标以“女书作品”、“女书物件”等予以区分。参见宫哲兵:《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谢明尧、贺夏蓉等编著:《女书习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伦玉敏:《花山庙女神与女书文化》,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相关的花山庙女神信仰进行过田野调查。“女书”因其特殊的文字价值和女性文化,在湖南众多的传统民俗文化中脱颖而出,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花山庙位于江永县允山镇的社下村,又称姑婆庙,里面供奉着“坐化成仙”的谭氏姐妹,②文献资料上关于花山和姑婆的记载,始见于清代蒋云宽(公元1765-1822年,字锦桥,又字牧叔,嘉庆四年进士,本地人)的《近游杂缀》一书,书中言“层岭之麓又有花山,山开如花,故名。唐时谭氏二女入山采药蜕化,土人即山为祠,山多菪石,石隙透一小径,天然梯级,竹树翳蔽,云雾蓊蔚。每岁五月间士女多赛祠矣。”当地人也称其为姑婆女神。该庙是学术界认定的解放前“女书”最重要的教学、使用和传承的中心地区之一,③宫哲兵:《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页。“文革”期间被毁,2006年复建。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花山庙重建与民众的社会记忆和信仰需求有关。作为地方性的民间信仰,花山庙的宗教资源匮乏单一,也未能承担起“女书”文化活态传承发展之平台的功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堪忧。
一、社会记忆与信仰重生
据史料记载,①1933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将女神与“女书”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其文载:“花山,……谭姓姊妹,学佛修真,入山采药,相与坐化于此。……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掉之。其歌扇所书头蝇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头蝇细字”即“女书”。解放前每逢花山庙庙会,周围县乡的妇女便会带着用“女书”写成的祷文,成群结队来庙里祭拜姑婆女神,把祷文唱给姑婆后放在香案上或直接烧掉,祭祀完毕后还要聚到一起唱“女歌”。不会识写“女书”的女性于此过程中向精通者学习,实现了“女书”的自然教育和传承。花山庙、姑婆神、“女书”都在“破四旧”运动中成为了被破除的对象,庙宇倒塌、神像被砸,很多珍贵的“女书”传本被烧毁殆尽。2006年,社下村村民谭全苟和“女书”传承人何静华号召大家筹资建庙,部分“女书”研究学者给予了相关指导和建议。在“女书”传人、民众和学者共同努力下,当地民众根据史料和民间传说于花山庙原址上重立新庙,重塑了姑婆神像,恢复了花山庙会。
新建的花山庙以一座屏风为隔,分为内外两间,外间为正门,前面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地,逢有庙会演出即为天然的观众席,也是民众上香时放鞭炮的地方。庙门上面写着“花山庙”三个大字,两旁挂一幅隶书体木质门联,上书:“花山仙境吸引天下游客,女书奇文凝聚寰宇宾朋”。外间左面墙上是何静华手书的“女书”祭祀歌,右面墙上是八仙画像;屏风上画的是姑婆姊妹坐化图,一幅楹联写着“有求必应,心诚则灵”。内间屏风墙上画福禄寿三星,对面是一块高台,上面坐落着头戴金冠、身着绿披风的姑婆神像;神像的脚下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鞋。神像左侧是一尊矮其20公分左右的土地公塑像,没有土地母(村民解释说因为姑婆是女性,就不再给土地公另配土地母)。神像前面为供桌,供桌前面是香炉、竹签筒和蒲垫,左墙根下堆放着几大袋复印好的“观音灵签”纸。重建后的花山庙除了供奉姑婆神外,也将当地较为流行的神灵信仰纳入进来,形成了“众神”共存共享的宗教场域。
采访中得知,花山庙重建被提上日程乃是“姑婆托梦”所致。谭全苟,重建牵头人之一,曾说姑婆二人两次托梦给自己,梦里面两姐妹在大雨中无处安身,只能躲在树叶下面避雨,向他哭诉着无家的痛苦。谭将此事告诉了当地著名的“女书”传人何静华,二人商量后开始号召大家为姑婆修庙捐钱。捐资者很少有人质疑“姑婆托梦”的真实性而是纷纷解囊,有些老人甚至为姑婆不幸的遭遇痛心不已,后悔没有早点捐钱建庙。由此能否推断,女神信仰一直在民众记忆中延续?这从田野调查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社下村街道上几位老人说,花山庙塌了以后也一直有人去拜姑婆,庙和神像没有了,就在遗址那里烧香磕头,但是这种行为必须避人耳目。笔者在花山庙里采访的几位来上香的老人也说,庙毁了以后他们也经常来,在废墟上放一块石头代表姑婆神像,对着石头磕头烧纸、诉苦祈愿,所来之人男女皆有,也有带着孩子来的。就这样,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被禁止的女神信仰由民众以不公开的、象征性的方式延续着。随着国家对传统民俗文化态度的转变,人们不再有太多顾虑,重建花山庙的愿望愈发强烈,在“姑婆托梦”的号召下愿望遂成。其缘由正如王铭铭所说:“尽管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影响了当地社区生活的自在性,不过,这些影响没有彻底推翻传统。地方传统可以在某些强制性的改造中暂时在社会地平线上消失,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其在当地的社会记忆中,历来都存在。”②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9-150页。
作为延续性的文化,当地关于姑婆传说、花山庙的记忆、祭祀活动一直在民间按照它的内在逻辑脉络传承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过去的生活经验正是今天的生活背景,其核心元素是始终延续而未曾断裂的。外人眼里看似荒诞的“姑婆托梦”唤醒了当地人“沉默”的记忆,未曾断过香火的花山庙原址也是证明传说和托梦真实性的依据。花山庙原址是当地民间传说中谭氏姊妹坐化成仙的地方,对信众而言那是连接尘世和仙界的神圣空间。伊利亚德认为,这是一种宗教徒才能体会到的“空间的中断”,并且能够走进这中断之中,“在一个宗教徒看来,这种空间的非均质性(no homogeneity)是在神圣空间与无状苍弯中所有其他的非神圣空间的对立的体验中体现的。这种神圣的空间是指真实的空间和确实存在的空间。”⑥花山庙遗址具有这种“真实的”和“确实存在”的空间特征和神圣的象征意义,并凭借民众的感知、记忆来传承和延续,这也是花山庙能够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花山庙庙会纪实
花山庙修好后,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附近和周边的村民们便会来这里祭拜姑婆,当地人称之为庙会。谭全苟夫妇有偿提供鞭炮、黄纸、香等祭祀用品,何静华负责给前来上香的人写“女书”祷文。这里还有专人负责给人解签,以前是当地的文化人周汶龙,后来他跟儿子去广东打工,何静华便代替了周汶龙成为了一名“兼职”解签人。农历五月十五是传说中姑婆升天的日子,这一天也要举行花山庙一年中最为隆重的庙会,附近很多村庄的村民都会过来赶会,还有业余戏班的义务演出。与其他地方“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不同,花山庙从重建到日常运行,都是民间自发行为,江永政府并未介入。
重新获得生机的花山庙女神在新的环境中承担了什么样的宗教功能呢?带着疑问,笔者来到江永花山庙进行田野调查。第一次来的时候并非庙会的日子,庙里空荡荡的没有人,没有任何点燃的香火,守庙的谭全苟也不在庙里。农历五月十五庙会那天,笔者很早就来到了花山庙,虽然刚下过雨,泥泞的土路并没有阻挡人们来花山庙祭拜姑婆,袅袅的香火和高燃的红烛几乎可以将庙外的院子包围起来,不断有进香的人放鞭炮,还有人带活鸡为贡品,中午也成为聚餐的菜肴。表演戏剧的业余戏班和锣鼓队多是上了岁数的老人,平时忙着农活或照顾儿孙,一到庙会的日子就会聚齐演出,自己做衣服、化妆、选曲。很多老人和孩子早早地坐在场地上只等着好戏开演。花山庙右侧小厨房也热闹非凡,几个妇女在里面烧水做饭,异常忙碌。后有一小块平地,不看戏的人就坐在这里聊天。午饭时刻,人们从厨房里拿出很多“桌布”(农村晒粮食时铺在地上的粗帆布)铺在庙外面的地上,所有人围在一起,席地而食,如同过节聚会一般。饭毕后大家都帮着收拾打扫,谭全苟则拿着账本向人们核对这次庙会收到的捐助和花销。
农历六月初一那天,谭全苟夫妇依旧在一张长条凳几上摆满了待售的祭祀用品,几个人坐在庙厅堂里聊天,三位妇女正在庙外点烛烧纸。两位40岁左右的妇女刚刚从庙内堂走出来,笔者便去采访她们,得知这两人是亲姐妹,社下村人,后来出嫁外村,大姐嫁到了县城里“女书”传人何静华的隔壁:
(姐姐说)小时候我们也跟着老人来这里烧过香,上学以后觉得这种事情太荒谬了,就不再来了。何静华问我们要不要捐资建庙,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女神嘛,总是保佑过我们的,所以就捐了。建好了庙,我年年来。(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求姑婆保佑平安哪,还有就是日子困难了,(或者)要投资生意的时候,总是要来姑婆这里上上香,抽签算个卦。(这里的签灵不灵?)抽的签还是蛮灵蛮准的,好几回都说中了。(知道“女书”吗?用它给姑婆写过愿望吗?)“女书”嘛,江永人哪个不晓得呢。何阿姨在的话,我们也会买份“女书”烧给姑婆,老人家讲以前许愿就是用“女书”的。这样做更正式些。不过不用“女书”写祭文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是经常买,也不认得那些字。
妹妹不善言辞,很多事情都是跟着姐姐一起做,她相信姑婆是灵验的。姐妹两人知道解签人何静华不在庙里,所以今天并没有抽签。
花山庙抽签卜卦的活动并不见于史志资料和“女书”传世文本中,应该是重建后新增加的。盛着“观音灵签”竹筒就放在姑婆神像供桌的下面,竹签上面刻着数字,代表签文的序号。抽签是免费的,不过要花1元钱从谭全苟那里买对应序号的签文。签文是印在16开白纸上的“观音灵签”,签纸右侧抬头是“(女书)发源地花山庙「观世音灵签」「洞庭湖居士」周汶龙总监”,然后是七言签文和解签文,左侧是中国民间常见的观音画像,和民间流行的解签书类似。如果看不明白,就要花2元钱请何静华解签。
一位50多岁的老汉刚刚抽了一支签,竹子上刻着“第七下签”,脸上带着几许失落,交了一元钱后他拿到了签文,上写“第七下卦丑宫”。该签文字面意思比较直白易懂,解签人何静华不在,笔者便和他一起研究签文。他文化不高,识字不多,笔者就照着签文的字面意思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讲给他听。签文的意思是老汉有些事情久而未决,还想去别的地方谋事,但诸事不顺,保持现状是比较理想的。老汉听了之后憨厚地笑了笑,告诉笔者这里的签是十分灵验的。据老汉讲,他家里很穷,一直没有娶到媳妇,去年经人介绍谈了一个对象准备结婚,给了四千元彩礼,后来媒人说女方反悔不嫁了,也找不到人了,给出的彩礼也没有办法要回来,和媒人讨要说法未果,一直拖延到现在。现在又想出去打几年工,所以来姑婆这里抽签看看。去年谈对象前也来求过签,签上说结不了婚,不顺利。笔者劝慰他签文的意思都模棱两可,很多事情还是要靠自己把握自己定夺。看笔者也能“解签”,刚才姐妹俩中的姐姐也进去抽了一支,买出签文纸后拿给笔者看,“二十九中签”,字面意思是有“贵人相助”,对她们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预兆。
不久,一位左臂打着石膏的老人家,在一中年妇女的搀扶下来到姑婆像前上香跪拜,打石膏的妇女嘴里还念念有词。等她们起身后我便上去采访。两人为婆媳关系,社下村邻村人。前些日子老人去女儿家探亲,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老人家前臂骨折,皮肤擦伤。后来老人的孙子搭别人的摩托车回家路上也发生了车祸,所幸没有受伤。老人心里非常惶恐不安,让孙子开着电动三轮车带着她和儿媳妇到姑婆这里祈求家人平安。问及有关“女书”的问题,老人说以前也听过江永有种女人的文字叫“女书”,至于“女书”和花山庙的关系就不甚了解,只是何静华在的时候偶尔会买本“女书”祭文,平时只是带些水果供品过来上香磕头而已。老人的孙子今年17岁,来到花山庙后就一直坐在庙外堂的条凳上,没有跟随老人到里面祭拜姑婆,交谈后得知他根本不相信有神灵存在,迫于奶奶和母亲的要求才过来。
姑婆神像下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手工儿童鞋,非常漂亮,我问谭全苟的爱人这些小鞋放在这的缘故,她说这些小鞋都是来求子的人有了孩子以后,回来向姑婆还愿时放在这里的,再有人过来求子的时候挑一双自己喜欢的鞋拿回去,有了孩子后还愿时再放一双新做的。如此往复,好运气便不断地传递下去,而且非常灵验。求神送子一直是重视子嗣传承的中国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民间信仰,也是目前大多数民间神灵都要承担的“义务”。来求子的人无法怀孕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是一边寻医问药,一边求神拜佛,一旦怀孕生产,功劳则归功于神灵。求子未果的人,或会继续多方求医、多方拜神。在信仰神灵的人那里,愿望达成总是归因于自己的虔诚感动了神灵,愿望未果则归因于虔诚度不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如现代医学等手段,则成为“被忽略的变量”。
三、女神角色变迁及信仰危机
通过史志文献以及部分“女书”文本①参见(清)周鹤修、王缵修:《永明县志》,康熙四十八年版(1709);(清)盛赓、李镜蓉修:《道州志》,光绪四年版(1878);曾继梧:《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卷1《花山条》,和济印刷公司,1931版,湖南省图书馆藏书;赵丽明主编、周硕沂注译:《中国女书集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可知,解放前花山女神主要是妇女们聚会交流“女书”、结交好友的见证人,偶尔也承担着为女性分忧解难的职能,宗教功能相对单一。花山庙庙址在离村落几公里远的半山腰上,周围树木丛生,与通常立在村落中心或村边等相对开放的祠堂、庙宇相比地理位置较为隐蔽,便于人们私下祭祀。这期间,花山庙周边诸多信仰实体(如佛道信仰、盘王信仰)业已消失,原有的民间信仰秩序也随之不再,民众则将占卜预测、祛灾消难、安抚慰藉等诸多原始、朴素的信仰需求寄托在极为隐蔽的花山庙遗址上。
改革开放以后,花山庙因缘际会重新建立起来,成为了当地民众可以崇拜的为数不多的信仰实体,也不断有新的功能被赋予女神。比如,求神送子一直是重视子嗣传承的中国社会较为普遍的民间信仰,亦是大多数民间神灵都要承担的“义务”,花山女神也被人们赋予了送子功能,女神像下的儿童鞋即为最好的例证。花山女神承担的这些新功能,于任何民间信仰中都能找到踪迹,与其说新,不如说是向民间信仰功能的复归。正如前文所言,解放前女神信仰的功能主要与女性活动有关,相对单一,这既缘于宗教信仰场域中的等级秩序,又缘于其存在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宗教神灵的等级地位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姑婆信仰的场域中有很多高阶位的神灵,如佛教神灵、道教神灵、盘王、祖先等神灵,他们的“本领”更加专业、强大,在神灵等级秩序中均高于姑婆;更何况当地民众遇到较大困难时多求助于“融合三教”的“师公”,请他们做道场法事而非求助于姑婆。女神信仰的空间场域被压缩的很小,很难发挥出更多的作用来。
从庙会情况看,复建后的花山庙更像是一个居民社区的文化站,或者说老人剧院。来参加活动的大多是上了岁数的老人和小孩子,尤以六七十岁的老人居多,他们来这里除了祭拜姑婆,更热衷于同他人聊天;姑婆更像居委会委员,负责倾听、排解民众的忧愁,给他们鼓励和希望。现实中种种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解决的需求,都被寄托在姑婆身上。社下村所在的江永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收入基本与邻县国家级贫困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持平。①2012年,江永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63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254元。邻县国家级贫困县江华县,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62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169元。数据来源:永州2013年鉴,http://www.hnyzszw.com/msg.php?id=1422,http://www.hnyzszw.com/msg.php?id=1425。江华县很多农村都建成了功能相对齐全的文化站,多是两层楼房,楼前面还有一块比较宽敞的水泥面场地。与之相比,江永县农村社区文化站建设这一块相对落后。或因如此,姑婆和花山庙除了宗教功能以外,也被民众赋予了社区文化站的功能,成为为大家提供心理慰藉、人际交往、文化娱乐的重要平台。
另外,花山女神信仰承载的“女书”文化非常具有特色,是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可以使花山庙突破低层次民间信仰的角色,向“女书”文化保护与传承博物馆方向转型。按此,花山庙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实际情况却是,花山庙复建后,仅有每个月庙会两天才会有些民众过来,它依旧处于一种原始的、极低层次的民间信仰阶段,背后所蕴藏的文化资源几乎未能发挥作用。虽然花山女神承担着满足民众基本信仰需求的功能,但是它的“宗教社会网络”特别不发达,每个网络点的力量都十分有限,地缘、人际关系等宗教传播因素的作用似乎已发挥到极限。据谭全苟保存的历年花山庙信众捐资账目记录统计前来上香的民众地域分布,可知,近8年来花山庙女神信仰始终没有突破允山镇范围,偶有其他地方(如江永县的上江圩镇、黄甲岭镇,以及江西、香港等地,也多是回家探亲顺道而为)的人过来参加活动,自2010年开始这些地方也很少有人过来祭拜姑婆了。
总体来说,花山庙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来看,一旦当地经济稍有起色,社区功能相对完善,它为民众提供的宗教职能和其他服务就有可能被取而代之。作为一种低层次的地方民间信仰,自由生灭是再正常不过的历史规律,大可不必为它的命运过多担忧。然而花山庙历史上是“女书”这种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中心,是“女书”使用、教育和传承的重要平台,诸多女性文化和女性习俗,都是以“女书”为载体展开的。就现实而言,当地民众也希望能够借助“女书”文化吸引外地人来参观花山庙,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花山庙的门楹已充分表达了村民的这种期盼。但是,目前显然它不具有这样的吸引力,尚无法承担起民众的迫切愿望。
四、“女书”文化与女神信仰的互构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相关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旨趣大致在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民间信仰的合法性与现代化等方面,近年来尤为重视从现实层面关注民间信仰复苏的内在动力、信仰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这种趋向与民间信仰正在经历“一场或许是历史上最大的地方宗教仪式传统的大规模复苏和重塑”①范丽珠:《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宗教的复兴及其策略》,《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6期,第63页。的趋势相关。就民间信仰复苏的动力而言,学界一般除了从“需求—满足”的视角进行功能性和心理学的分析外,更加着力凸显民间信仰作为“当下”传统文化重要来源的文化正统性,强调民间信仰对民众日常生活、地域文化、社会秩序的塑造和维系功能,继而呼吁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②参见覃琮:《人类学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第58页。。特别是民间信仰在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领域往往因其文化的同源性而备受重视,如海峡两岸民众共同崇拜的妈祖信仰、关公信仰,在加深两岸文化认同和民族向心力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正是民间信仰体系中本就蕴含着的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才使得过去一度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各种“封建迷信”“脱胎换骨”,成为支撑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花山女神信仰亦如此。
就花山女神信仰这种宗教功能单一、发展水平低但又具有重要的文化资源的民间信仰来说,如何发展是一个难题。在社下村及其附近,过去几十年里也有大大小小的庙宇和神灵信仰出现,但大都如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重建后的花山庙却生存了下来。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花山庙重建是他们将心中延续的宗教信仰变成现实的重要努力。对支持花山庙重建的学者来说,花山庙本身是“女书”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了“女书”作为文字继续存在的土壤,只有花山庙还有可能重新建构“女书”的宗教神圣性吸引人们再次使用,从而将这种宝贵的民间文化传承下去。换言之,在当代社会,花山女神信仰生存发展的最大保障就在于其深厚的“女书”文化资源。
“女书”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国家将“女书”习俗收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突显了其重要的文化价值,但政府又不宜介入民间信仰的发展。江永县政府努力打造“女书”文化品牌、发展“女书”文化产业,却任花山庙自然发展的作法也表明了这种态度。当代“女书”作为文字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再,新中国男女地位在法律上的平等,很多女性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方便和普及的汉语很快就取代了“女书”成为她们交流的工具。江永独特的女性世界也发生了改变,随着“城市化、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原来依靠乡土、家庭、自愿结拜的姐妹们的交往空间、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为工业化所取代,女红市场逐渐消失,信息化代替同伴之间的相互倾诉,手机信息满天飞,再不用在歌堂互诉离愁别绪。现代社会的发展使长期传承的女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③王风华:《女书文化资源开发的女性主义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25页。脱离了民众生活的“女书”,尽管有政府的倾力支持,但其前景堪忧,它需要重新扎根在民众生活中。
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后,各地的文化传承主体开始积极地回应并向“非物质文化遗产”靠拢。花山庙曾是“女书”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姑婆女神也是民众用“女书”倾诉情感、祈求福报的对象。如果花山庙能够成为“女书”在现代社会中民众使用的自然场所,成为展示和传承“女书”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台,那么不仅“女书”能够获得重新走进民众生活的机会,花山庙也能因“女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部分,从而获得多方面的支持。对政府来说,未来有可能通过开发花山庙在“女书”文化方面的特殊价值而将其纳入政府的“女书”文化发展规划之中;通过与学者的合作,将花山庙打造成为活态的“女书”文化博物馆和“女书”学校,为“女书”的传承发展提供内在的源动力。在此过程中,政府、学术界、地方精英和民众之间如何有机的配合,是需要思考和反复实践的。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本身宗教资源极为有限的花山女神信仰之所以能够复苏且延续至今,仅靠地方信众之维系是难以实现的,它最重要的持续性推力是与之关系密切的“女书”。自20世纪80年代“女书”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女书”研究蔚然成风,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学者,涉及到文字学、宗教学、女性学等十多个领域,在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中一时独领风骚,其研究之盛乃至有学者提出了“女书学”之说。“女书”及其研究之所以受到关注,与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正值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再度发展,进而影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妇女也开始作为与男性相对立的性别群体而“存在”,女性群体内部也急剧分化,中国的社会性别问题变得分外复杂。①参见何萍:《中国女性主义问题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702页。另外,改革开放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回应现代化且彰显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显得尤为重要。而“女书”及其蕴含的文化资源正契合了这些思潮和社会需要,作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主义资源,“女书”自然很容易受到国内外的关注。②恰恰是这种心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女性乃至诸多国家的女性其社会地位、角色等方面处于一种低于男性、被歧视的状况,大家迫切需要一种资源来力证女性的聪明才智和社会贡献。从此角度看,“女书”的出场可谓恰逢其时。
这种时代环境,使得濒危的“女书”从偏远闭塞的山区走向了国际,也使得在中国万神殿中几乎毫无地位和知名度的花山女神受到了学者的重视,从而走进了公众视野。地方民众和学者在参与花山女神信仰复苏的过程中,均有意识的将“女书”的文化资源融入到这个地方民间信仰中去,且力图通过“双名制”③可理解为,花山庙对民众而言名为“花山庙”,对国家社会而言名为“女书文化教育传承中心”或“女书文化活态传承博物馆”等,即一物两名。高丙中认为“双名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并被人们作为政治艺术运用到处理诸如国家和地方的紧张关系等问题中,这种做法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民间信仰复苏中获得广泛运用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参见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4-168页。实现女神信仰的现代化转型。这也是中国大多数民间信仰复苏所采用的方式。问题在于,花山女神首先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而存在,“女书”亦不过是其信仰要素中的一部分,它自诞生起至今日,其生命力乃是基于它的宗教资源而非文化资源。如果我们仅着力于开发和打造花山女神信仰的“女书”文化资源,明智之举是在城区而非交通不便的社下村规划一座现代化博物馆即可,处于村落山脚的花山庙是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这种功能和角色的。如此甚或加速信众的流失,也加速它的衰败。我们在理解一些学者希望传承发展“女书”文化的迫切心情之际,也要遵循民间宗教信仰本身的发展规律,重新审视花山女神信仰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刘丽)
The Resurgence and Changes of the Goddess Faith-an Anthropological Report based on the Fieldwork from the Huashan Temple in Jiangyong Countryside
Lun Yum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Northeastern Minorities of Dalian Minzu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116605)
Based on the fieldwork from the Huashan Temple in Shexia village,Jiangyong country of Hunan province,we find out the rebuilding process of the temple and known what the role is the goddess played on.In this progress,the present situation for the goddess is clearly.One of its rebuilding is in the religion areas that the goddess faith lives in the memory of people’s and also they have the need that the goddess can provide.But both the limits religion resources and the underutilized culture cannot make the goddess faith to develop well,leading the faith also in the crisis of people selection.Only through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Nü-shu culture and the faith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folk belief;Resurgence and changes;Nü-shu;Mutual construction
K892.29
A
1008-7354(2016)03-0067-07
伦玉敏(1985-),男,山东茌平人,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
本文是大连民族大学人才引进启动项目(项目批准编号:0710-120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女书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