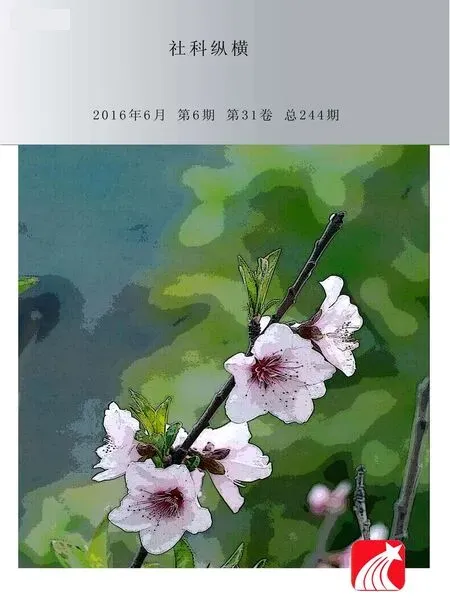论林志纯的封建社会观
靳艳(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论林志纯的封建社会观
靳艳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内容摘要】林志纯在对奴隶社会的阐释中,解读了他对封建的社会认识。租佃制和人身依附不能作为判断封建社会的标准是林氏封建社会观的重要内容,用依次演进五段论的标准判断社会形态,是林氏封建社会观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林志纯封建租佃制人身依附
林志纯是中国世界古典史学科的开拓者,长期致力于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著述颇丰。林志纯并没有系统地解释过何谓封建社会①,但在其对奴隶社会的阐释中,我们可以了解他所认识的封建社会。林志纯认为“古代东方各国,由于奴隶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就始终在数量上占据绝大优势”[1](P274)的论断是准确的。本文拟就林志纯对封建社会的认识进行评述。
一
租佃制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是林氏封建社会观之一。
林志纯肯定了奴隶社会自由农的主导地位,指出这些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主要地分化为奴隶制中的奴隶以及租佃制中的佃农。这样,林志纯就给出了他对封建社会的第一个认识,即租佃制并非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租佃制原来也是奴隶社会的正常现象”,甚至还可以非常地流行,“租佃制流行的程度……要看时间、地点条件的具体情形”[2](P193-194)。林志纯认为,租佃制下的佃农并不等同于封建制里的农奴,他以雅典梭伦改革前的“六一汉”为例,说道:“他们是佃农,他们在雅典农民中占据极大多数……从古典作家的记载和恩格斯的描述来看,当时雅典或亚蒂加的租佃制显然已经十分流行,而六一汉和佃农在农业生产者中已居绝大多数”;此外还提出“罗马的被保护人,其实同时也就是佃农”。[2](P193-196)
结合当时众多历史学家将租佃制的流行作为封建社会特色的学术背景,林志纯关于租佃制同样可以在封建社会以外的某段时期内流行的论断无疑是有很大意义的。林志纯这一学说突破了当时史学界关于某一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必然由某种所有制(如奴隶制、租佃制)所主导的僵化思维模式,给后世以很大的启迪。以农奴制为例,21世纪之前的我国史学界曾一致认为西欧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者是农奴,但是晚近的研究却越来越多地表明半自由农和自由农并不少于农奴的数量;反而是农奴制,不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而且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在农奴制较为发达的英国,农奴制形成于12世纪,到15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便已瓦解,而且即使是在其全盛的13世纪,农奴也只是占农村人口户数的3/5,全国人口户数的1/3。[3](P200)由此例可见,林志纯这种多种所有制可以同时流行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林志纯将雅典的佃农(六一汉)与农奴相区别,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前者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后者不是。[4](P182-183)不过,林志纯的论证也并非是全无瑕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在论证雅典的佃农(六一汉)并非农奴时所采用的方法十分牵强,林志纯是从雅典佃农(六一汉)的发展方向来考虑这一问题的:他认为在农村公社成员被排除出父权制大家庭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变为奴隶,而另一部分变为佃农,但这部分佃农的地位是不稳定的——随着地主压迫强度的不断增高,这部分佃农迟早也会变成奴隶。[2](P192)在这种思路下,他说道:“如果像资产阶级学者那样的做法,把六一汉也说成‘农奴’,或可能成为‘农奴’的人……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由‘农奴制’发展为奴隶制,由‘封建社会’进入奴隶社会!”[2](P195)像这样不用事实性证据而采用先入为主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作论证,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由此可见,林志纯关于奴隶社会可以流行租佃制的见解也是构筑在对佃农的这种认识之上的——毕竟这种佃农终究还是会成为奴隶。至于罗马的被保护人,林志纯将其与雅典六一汉并列相提的做法则更显不妥,因为罗马被保护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反而是不自由的。那是不是就可以认为罗马被保护人就是林志纯所说的作为奴隶前身的佃农呢?答案并非如此。尽管被保护人的地位确实不太稳定,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主宾关系或主奴关系不同,并非严格的法律关系;投靠人仍然不是自由人,只是信义和习惯使他们的不自由得以减轻”[5](P57),但仔细来看,被保护人“起初是由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力量软弱的人们组成”[6](P70),他们“有些是离开故土的逃亡者,在他乡寻求收容和保护;有些是奴隶,主人对他们暂时放弃权力的行使,给他们以实际上的自由”。保护人授予他们土地、牲畜和保护,作为交换,他们则要在军事、法律和政治活动上支持保护人并在保护人之女出嫁之时捐赠嫁妆。这样看来,被保护人的发展方向便似乎并不是奴隶;反之,他们所要履行的义务倒是极似于中世纪农奴所要承担之职责[7](P6)。如此一来,罗马的被保护人也就同样不能成为林志纯的论据了。
二
人身依附关系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是林氏封建社会观的重要内容。
既然奴隶社会中可以流行非自由雇佣型的租佃制,那么林志纯对封建社会的第二个认识——人身依附关系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也便产生了。他先是批评道:“我们史学界有些先生们几乎一看到‘依附’或‘隶属’的身份就联想到‘封建社会’……很奇怪,为什么不想一想,奴隶社会也有贵族地主,也有‘依附’或‘隶属’身份的农民呢?”随后,他同样以雅典和罗马的情况举例,试图说明自己的论断。他指出,在雅典,不仅梭伦改革前的贫人会沦为富人的依附者,而且在雅典的外邦人也必须以某一公民为自己的保护人。至于罗马,依附关系则更是充斥于各式各样的场合之中——解放奴隶与其主人、诉讼人与其代言人、蛮族与征服其的罗马将领间均是被保护人和保护人的关系,甚至连帝国时代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手工业协会也往往请罗马显贵作为自己的保护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依附关系呢?林志纯认为,“这一切不同的保护制或依附制方式,皆溯源于家长制依附制”。[2](P191-193)
毫无疑问,林志纯有关依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封建社会的论断澄清了一个长期被学术界误解的问题,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即我们是否可以在林志纯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不可将依附关系作为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之特色”的结论呢?显然不可行,其原因就在于古典时代的依附关系和后来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中的依附关系至少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中的依附关系是有所特指的。
在雅典主要存在两种依附关系。一是部分出生低微者对贵族的依附。这些出生低微者多来源于被释奴的后代而非林志纯所认为的失地的农村公社成员,他们由于无法独立地维持生计,因此选择依附于某一家族或家庭,通过“参与家内祭祀而与家长发生联系”[8](P282)。他们的地位介于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其具体处境则取决于与主人的关系。通常来说,他们或是通过在家内充当劳役以为主人服务,或是以分成制交租的形式从主人处取得一块土地而变为佃农。二是作为个体的个人对于作为整体城邦的依附。“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那些出于本性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9](P6)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雅典社会中,雅典公民的的权利只有在作为共同体的公民集体中才能得以实现;但当视角转向个体时,我们却会发现,他们几乎只是附属于共同体的一个个奴隶,毫无权利可言。具体来看,当一个雅典公民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而出现时,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乃至处以死;但当他脱离了共同体而作为个人出现时,他的所有行为都受到了限制、监视和压迫,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剥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至于奴隶,虽然他们是其主人的私有财产,但是比起对主人的依附,他们同样更依附于城邦共同体。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事实中明显地看出来,即作为城邦共同体意志体现的国家公法可以解除奴隶与其主人之间的私人依附关系,从而使奴隶获得解放。[10](P36)
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罗马社会中主要存在过四种依附关系。首先是“被保护人”对“贵族”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主要流行于共和国时期。早在王政时期,罗马人通常会将外来居民以及被释奴通过拟制血缘的方法纳入罗马氏族,这样,前者就成为了贵族而后者成为了被保护人;两者共同组成了“罗马人民”。但是随着外来人口和被释奴的数量越来越大,罗马氏族无法再将他们吸收进来,于是这些被排除在罗马氏族之外的人口只能以共同体的形式依附于城邦,并逐渐形成了“平民”。至于贵族与被保护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前文已有说明,兹不赘述。其次是贵族对贵族的依附,这种主要流行于帝国时期的依附形式并不常见,依附的目的主要在于取得某样经济或政治利益。再次是某一共同体对贵族的依附,如林志纯所说的城市或城市中的手工业协会对某一贵族的依附,这同样是流行于帝国时期。最后,同希腊一样,罗马社会中的个人也依附于作为整体的国家(共和时期的城邦和帝国时期的皇帝),而这一点亦同样集中地表现在国家公法可以凌驾于其他各种私人依附关系之上。
在中世纪的欧洲流行封建主义,那里主要存在着三种依附形式: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封臣对封君的依附,以及自由人(非贵族)对国家的依附。在法律上,农奴与领主、自由人(非贵族)与国家的隶属关系世代相传,某一农奴及其后代永远都依附于其领主,而自由人及其后代则一直依附于国家;封臣对封君的隶属关系自由缔结,每一代的封君与封臣都要举行重新结成依附关系的受封仪式。在这里我们主要来看一看可以体现出欧洲中世纪与古典时代差别的有关的农奴与领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在三个层面上依附于领主:人身依附;土地上的依附;司法上的依附。由此,我们发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对领主的依附是要强于其对国家的依附的。
可见,在雅典和罗马无论是贵族、平民还是奴隶,他们所要依附第一个对象一定是国家,其他一切依附关系的地位都是低于这一组关系的。而在流行封建主义的欧洲中世纪,情况则大不相同了:在那里,农奴对贵族的依附是高于其对国家的依附的。因此,当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不将依附关系作为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之特色时,答案便是很明显的了——既然依附关系在古典时期和欧洲封建社会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那么我们当然也就不能拿前者抹杀后者的独特性了,即使是提醒人们不要将封建制和领主制混为一谈[11](P124-125)的马克·布洛赫也还是将“依附农民”和“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两者一起纳入他对欧洲封建主义基本特征的描述之中[12](P70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林志纯有关“人身依附关系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的论断正确却不精确——它正确在从广义上肯定前资本主义时代依附关系盛行的基本特征,可却又失之于未从狭义上认识欧洲封建主义依附关系的独特之处。
三
用依次演进五段论的标准判断社会形态,是林氏封建社会观的鲜明特色。
林志纯在“自由农在奴隶社会中长期存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得出了租佃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不是判断封建社会标准的结论,否定了当时多数史学家以“租佃制是否盛行”、“人身依附关系是否盛行”作为判断封建社会的标准。那么林志纯又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封建社会的呢?他认为这取决于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但与其他史学家不同,他认为不能从量上判断何者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因为“从量法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从这个社会的发生、发展来看,从这个社会的本质来看”。他举例道,当埃及和两河流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阶级社会和国家时,“原始公社制在全世界就好像一片汪洋大海,而尼罗河和两河流域的一些阶级社会和国家只是大海中的几点孤岛而已。但是,人类的‘文明’阶段已从此开始,而这些‘孤岛’在当时世界上就是‘主导’的和‘进步’的地区。再就这些刚刚发生奴隶社会的地区而言,公社残迹、氏族残余在其中还占极大优势,而奴隶制关系不过就是广大沙漠中的几点绿洲而已,然而就是这一些为数无多的奴隶制关系,在这些阶级社会中起了‘主导’作用,因而是‘主导’的、进步的”。[2](P196-198)
从林志纯解释和举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林志纯的全部判断标准其实都是构建在“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与“某一生产形式是否在发展”这两点思想基础之上。他认为,当奴隶制出现时,虽然“在人口比例上,奴隶未必便能多过自由民”,也可能“会出现较普遍的租佃制”,但相比奴隶制而言,农村公社和租佃制都是“落后的”,都“无损于奴隶社会的实质”[2](P193-197),因为根据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紧接着原始社会的应该是奴隶社会,而奴隶制又恰恰是在发展,这样一来,奴隶制虽然不盛行,却也应该是“主导”的、“进步”的。根据这种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林志纯还提出了带有其自身特色的“魏晋封建说”——在魏晋以前,虽然“奴隶在农业生产上的数量比重仍不及农民”,但是由于殷周以后、魏晋以前的奴隶数量是不断在加多,因此这一时段便是紧接着夏代原始社会之后的奴隶社会;到了魏晋之后,由于奴隶数量开始减少,因此这就代表着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社会的到来;至于其他的,如奴隶制是否最为盛行、奴隶人口是否从事当时最为主要的农业、奴隶人数是否超过佃农等等问题则都是不重要的。[1]毫无疑问,林志纯本末倒置地用理论去证明史实,更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量”向“质”转化的论断。“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为数不多的奴隶,如果它的生产不是建筑在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把它叫做奴隶社会?难道不管奴隶的数量如何,也不管奴隶劳动是否已构成所在社会的支配的劳动形式,只要有奴隶存在,一个社会就可以叫做奴隶社会吗?”[13],同理,对封建社会的判断亦是如此。
综上所述,林志纯在促进我国史学界对封建社会研究方面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有关租佃制并非封建社会独有、人身依附关系并非封建社会独有的论断无疑纠正和澄清了当时被学术界误解的问题,给后人的研究以很大的启迪。但是林志纯的封建社会论没有看到战俘构成早期奴隶的主要来源;将雅典的六一汉与罗马的被保护人不加分别地加以并列,认为他们来自于被农村公社排除出来的失地农民,是奴隶的前身;没有看到依附关系在古典世界和欧洲封建主义下的区别而将其笼统的涵盖在一起。亦步亦趋地将苏联历史学研究的僵化模式应用到历史事实上来。
注释:
①林志纯其实并不同意将“Feudalism”与“封建主义”对译。他认为中国史书中的“封建”一词,其内涵更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殖民建邦”。不过,他最后也表示“仍可继续使用‘封建’之类的习惯用语,因为我们误用此译语已有百年”。参见林志纯.“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的百年误译[M].载日知文集·卷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95- 312.
参考文献:
[1]林志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A].日知文集·(卷一)[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林志纯.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A].日知文集·(卷一)[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厉以宁.希腊古代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蒙森,李稼年译.罗马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6]科瓦略夫,王以铸译.古代罗马史[M].上海:三联书店,1957.
[7]腾尼·弗兰克.王桂玲,杨金龙译.罗马经济史[M].上海:三联书店,2013.
[8]古朗士.吴晓群译.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82.
[9]亚里士多德.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A].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0]威廉·威斯特曼.邢颖译.古希腊罗马奴隶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11]马克·布洛赫.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2]马克·布洛赫.李增洪,侯树栋,张绪山译.张绪山校,封建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3]张广志、李学功.中国古史分期三家说平议[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63.
*作者简介:靳艳(1963—),女,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中图分类号:K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106(2016)06- 0088-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