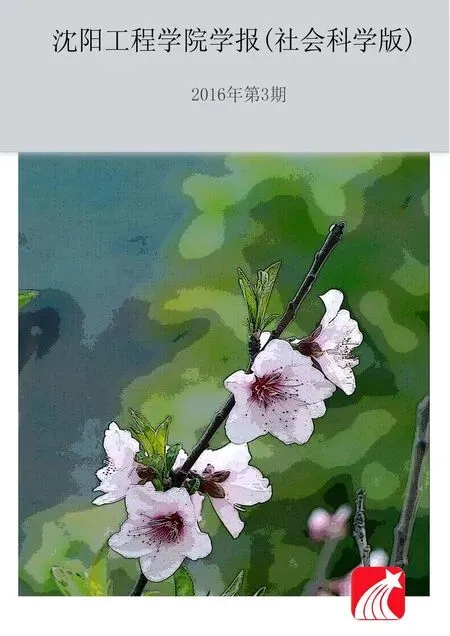论两种对话中的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
陈士部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论两种对话中的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
陈士部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是中国文论现代化进程中凝聚出来的思想方法。“历史还原”的唯物辩证原则与“意义还原”的现代性视阈相联结应成为还给两种对话的“本体论承诺”。在全球化思潮与反思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中,西方美学的“主体间性转向”是经由两种对话谋求中国文论现代性的新契机。
古今对话;中西对话;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诉求是一种跨世纪的隐忧,百年来无数学人对之魂绕梦牵。从晚清的“中体西用”到五四时期的“中西会通”,从域外新儒家的“中西互为体用”到国内当下学人的“现代转换”,表征着中国文化现代性祈求的痴迷心态与艰难征程。其中,在传统性与现代性、承续性与断裂性以及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精神张力结构中,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建构与价值取向更显出复杂纠缠的学术生态,更展现出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焦虑之深与企盼之切,并由此在长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学术论争中形成了古今中西多方比较对照的思想方法。
一、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对话格局及其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严谨的全方位的古代文论研究是从新时期开始的。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论研究打破了已有的视阈窄浅的学术瓶颈和因主流意识形态辖制而形成的僵滞局面,呈现出多元化探索的学术格局。尤其是经由新世纪以来的学科史反思,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的思想方法已成为学界研究古代文论的思想利器,“‘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问题,‘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对话’问题,都是具有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真正的重要学术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1]自古代文论学科建制始,就是纠缠在一起的:在学理逻辑上,中西关系问题意味着在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文论的对峙与互补、独白与融通,这是空间意义上异类聚首的现代机遇;古今关系问题意味着在现代化语境中古今文论的互反互通、互逆互融,这是时间意义上“古典的复活”的现实机缘。因为古今维度中的“今”是在中西维面中被界定的,而中西维面中的“中”是在古今维度中界定的,所以,古今中西四者具有超时空的措置、交叉或叠合等复杂情形。
因此,当前如何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问题仍是我们面临的学术难题。表面看来,学界至今仍因袭过往的学术路径,古今对接、中西比较几成习得的“口头禅”。不过,新时期三十余年来古代文论研究中所形成的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绝不能简单等同于以往的比较方法,这里的两种对话有自己的学理背景与价值追求,从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对话格局:首先,古今对话机制与中西对话机制衍生于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全球化思潮中,两种文论对话立足于本土性与全球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关系的自觉反思基础上。如果说,“一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学术史,本身就是在从古典形态到现代范式转型的历史语境中行进的,其间蕴涵了丰富的古今对接的经验和教训”[2],那么,在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后殖民理论与反思现代性危机的策动,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意识更为强劲,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愈发成为一种强烈而焦灼的理论自觉,中国文论“西方化”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迷恋的“中国梦”。
其次,新时期以来的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同先前的“古为今用”与“西为中用”有别,前者改变了后者的“以今释古”“以西释中”之偏失。这里的两种对话化用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思想精神并借鉴了西方现象学与阐释学等思想资源,不论古今对话抑或中西对话都是主体间性的即交互主体性的,都是两方或多方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一方并不遮蔽或抑制另一方。这就是说,古今对话、中西对话就是古今互证、中西互释,彼此是生成性的双向互释互审,“‘你’呈现在对话中,‘我’生存在与‘你’的关系里”[3]。这正是新世纪以来乐黛云、钱中文、童庆炳和曹顺庆等学者推重中西文化、中西文论对话的理论旨趣之所在。再者,前后比较与对话的思想资源不同。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往往按照西方某种单一的文学观念、话语资源或学术框架进行研究,局限于单向度的比附性阐释中,缺乏开放的、宏阔的学术眼光;而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多借鉴诸如现象学、阐释学、存在论和身体美学、文化学等西方现当代话语资源,有意识地走向文化诗学,注重在多元性的互为主体的对话中挖掘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建设中华现代文学理论的资源有四个方面: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华古代文学理论,西方文论中合理的成分。在四种资源上的创造性改造与融合,是建设现代文论新形态的必由之路。”[4]344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已消解了原有的学术焦虑,探求到一劳永逸的良性学术路径。就当前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生态而言,它仍置身于特定的困境中,这种困境的形成既缘于因袭的重负又源于突破旧有思维模式之繁难,同时也归咎于理论研究主体的“众神之争”:一者,在20世纪上半叶古代文论学科的建制中,由于西学抽象思辨的理论话语和一元论的学理体系的强大感召,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被连根拔起并经“奥卡姆剃刀”的削剪而嫁接于新的人文学科,缘此造成了“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批评史与更宽泛意义上的批评观念的割裂”以及“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5]。按照西学理念,从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文论话语,进而沉迷于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思辨演绎。这种旧有的治学路径依凭惯性力而得以延展,并布下循环往复的“魔圈”,从而遮蔽了甚或丢弃了面向传统的理论还原与历史还原。这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后遗症”所造成的理论困境,一时难以彻底扭转。再者,当代学人两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思想方法加重了这种理论困境。学界面对西学话语资源与中国传统话语资源,往往预设前者重自然哲理,后者重人伦政治;前者重“天人相分”,后者重“天人合一”;前者重审美客体,后者重审美主体;前者重再现,后者重表现;前者重理性思辨,后者重直觉体验等。这种无反思地超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理论预构很容易陷入削足适履的武断。如果不能超越两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并把价值诉求的根须植于深远的历史情境中,如果不能恪守交互往返的多层级对话原则并把“自我确证”的权力交付于“他者”,要想冲破现有的理论困境仍然是乏力的。此外,晚近围绕“失语症”与“转换论”以及中国文论有无体系等问题的“众神之争”,昭示着当前理论研究主体内部存有多种学术路径,各有心仪的学术目标。这本是学术活力的表征,但如果学术论争掺杂个人身份的情绪化固守与个体利益的狭隘考量,而不能将其视为磨练理论个性的良机,无力将其引向更深层的学理境地,则无谓的论争只能是“自毁长城”。
前述所言的“跨世纪的焦虑”与理论困境其实并非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的过错,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祈求只能在两种对话中达成。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场域以撩开遮蔽“真理”的雾霾让对话拥有坚实而阔大的平台,并依托对话形成的“视界融合”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提供知识学与价值论的双重保障。而要彻底清理对话的场域,就必须依靠理论还原与历史还原把对话的平台前移于本体性的人文场景与终极性的价值担当之中。
二、两种对话的价值指向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
在百年谋求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进程中,学术史从西方文论的“独白”走向了中西文论的“对话”,其间暗含着由“西化”到“化西”的学理冲动。鉴于此,无论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还是中国文论的西方化,都不是现有文论话语资源的简单切换,更不是中西双方互通有无的语言补缀,而是牵涉审美理想、审美价值基于中西对话的文论话语重建。此处隐含着两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反思中西文论对话应有的双重前提,即:中西文论对话的基点或“问题域”在哪里,这种学理对话应有怎样的动态机制。
中西双方各有深广的文论话语资源,走上对话平台的言说对象应该是特定的“问题域”映带出来的前沿话题,同时对话要遵循的话语规则也便提到议程上。如若舍弃这些反思环节,中西文论对话不是表浅的皮相比照就是单方的环视自雄。曹顺庆认为要清理出中国文论话语所呈现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并指出中西文论对话的基本规则,即:“话语独立”“平等对话”“双向阐释”和“求同存异,异质互补”等四个原则[6]。要害是,即便如此,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中国文论的西方化所引发的中西文论对话还能否、有无必要在“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层面上进一步作历史境遇中的“理论还原”呢?在深层牵动、规约中西文论对话不断推进的学术价值究竟是什么?后文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这里先澄清一个比较诗学中常见的学术观念。这种学术观念认为,中西文论相似之处表明双方有沟通的可能性,中西文论相异之处则表明双方有彼此不可取代的独立价值。其实,“求同存异”存有学术隐患:“同”带来的对话的通畅极可能使其流于“闲谈”,而湮灭了对“同”之背后隐藏的审美旨趣歧异的深度拷问;“异”导致的对话之抵牾极可能使其被打入“存而不论”的冷宫,从而丧失了“辨异”有望带来的学术思想生长的潜能。只要经过冷静的文化反思,我们就不会轻易质疑如下的断言:“同”不能充当取消“第三者”的充足理由,“异”也不能表明“多元化”可以享受“免检特权”。
所以说,有历史厚重感的文论对话不会以“求同存异”为目标导向,它必然是由特定的“问题意识”开启的,并要把对话的价值目标锁定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重建上。否则,文论对话很容易在追“新”逐“后”的忙乱中滞留于一波又一波的“求同存异”。有一个学案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况,这个学案就是文艺的审美感性与审美理性的理论吊诡问题。总的说来,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雄霸思想界,尼采、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等都通过反叛黑格尔的纯粹理性展开了现代哲学反思。而在西方当代美学中,韦尔施、伊格尔顿和舒斯特曼等又开展对鲍姆嘉通美学初建中理性主义残留物的清理,要么说他“首先要处理的并非是艺术,而是认识论的一个分支”[7]12,要么说“鲍姆加通从希腊语aesthesis(感性认识)得出它的名字,打算用他的新哲学科学去构成感性认识的一般理论。这种感性认识被当作逻辑的补充,二者一起被构想为提供全面的知识理论,他称之为Gnoseology(知识论)”[8]。为此,伊格尔顿断言审美是“肉体的话语”[9],韦尔施更把“重构美学”定位于“‘享乐主义的’意义”“表达感觉的快感积累”[7]15,西方美学由此表现出从“理性”向“感性”单向反弹的态势。审美感性与审美理性之间的悖谬在中国当代美学界、文艺学界也有所体现。晚近以来,有关“文艺理论边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围绕“实践美学”或“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论争等热点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这些热点问题往往最终聚焦在审美与文艺中的感性与理性之关系上,并显示出热捧“新感性”的情势。
当带着诸多问题谋求同西方对话时,是不是要一味追“新”逐“后”,效颦学步,滑向“肉体”或“感性”呢?钱中文和童庆炳等学者为中西文论对话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钱中文提出了文学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10];童庆炳提出了审美的“溶解性特征”:“文学艺术所撷取的审美因素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凝聚政治、道德、认识等各种因素”[11];王元骧则提出:“审美尽管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审美情感的形成过程中却始终离不开认识因素的参与和作用。”[12]这种注重感性与理性交融关系的文艺观念承续了“物我冥合”“文质彬彬”“神与物游”“身道合一”和“天人合一”等传统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并切合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特殊语境。这样,我们在中西文论对话中既可以有效展开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反思,也可以针对其或“新”或“后”的诸种文化观念表达出中国立场、中国经验。为何要在追“新”逐“后”的无根性精神漂浮中迷失自我呢?
不管“失语症”及其相关的“转换论”有怎样的争论都不能否定经由中西文论与古今文论的对话来谋求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学术路径。忌患“失语症”而排斥中西文论对话,疑虑“转换论”而否认古今文论对话,均是因噎废食的鲁莽做法,当前古代文论研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优化两种对话内部的张力结构并展示其价值重构功能。如果说,古今对话重在“今”意在“用”,中西对话重在“中”意在“实”,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中,“今”之“用”必然要有西学话语资源的理论镜鉴,“中”之“实”必然要有传统话语资源的历史倚重。正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正如当我们在理解活动中取得进展时令人惊奇的东西便失去其陌生性一样,对传统的每一次成功的运用都化为一种新的显然的熟悉性,使得传统属于我们而我们也属于传统。新奇的东西和传统一起汇入一个共同占有和分享的世界,它包容了过去和现在并在人与人的对话中获得其语言表达。”[13]“古”之“实”与“今”之“用”,“西”之“用”与“中”之“实”及其互为“实”“用”,都是在同场共时的对话中彼此的“陌生性”化为彼此的“熟悉性”。为此,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认为古今对话的障碍在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分”,中西对话的艰涩在于直觉体悟性话语与分析思辨性话语之“隔”。实际上,古今对话的真正难题在于如何切实处理同西方异质文论话语的共在关系,中西对话的真正困惑在于如何有效释放传统文论的超越性价值与意义。因此,“失语症”及其应对的“转换论”是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共谋的学术命题,也是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重建的宏阔语境,过激而实则薄浅的论争根本不能推进实际的重建工作。
三、两种对话的学术原则与理论前景
考察新时期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中的古代文论研究之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意义与价值,不仅要搞清导引两种对话的理论主体的时代境遇,还要捋顺言说对象的衍化脉象,更要考究对话的根基与立场等前提性的“元理论”。倘若“视界融合”果真能作为分析传统文论现代遭际的“收结点”[14],这种“收结点”也不表明“一体化”思维的绝对胜利,它仍包孕着“道之文”的内在裂变的因子,这既是由两种对话的自主性立场决定的,也是由文论自身的学术性征决定的。
其一,针对特定话题展开的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应沉潜在“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的层面上,揭示该话题指涉的对话双方深层次上的异同关联。要强调的是,这种异同关联即“殊相”与“共相”的关系,仍可向前作历史纵深境遇中的“理论还原”,而这种“理论还原”将抵达“异同关联”的源初性场景。正是这种“源初性场景”滋生出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成为诸种文化的本根,卢卡奇在审美人类学的意义上触及这个问题,认为文艺的起源、审美反映的生成机理只能以历史回溯的方法才能得到真正的阐释,并依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找到了文艺与审美问题的“本体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不是由理念的内在发展推演出历史发展各个阶段,而是相反地从以下观点出发,即由纷繁复杂的历史体系的规定中去把握实际进程。理论(在此即为审美)与历史规定的统一,最终是以极其矛盾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不论是在原理上还是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只有通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间断的合作才能确立。”[15]因此,探究中西文论观念和范畴的深刻区别不能滞留在纯粹理性话语的抽象演绎上,“必须以中西经济不同形态的发展入手,才能得到正确而深刻的解释”[4]62。所以说,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各有自己的根基与立场,对话主体拒绝未经反思的比较诗学成见;两种对话不是一次性公认出凝固的结论,而是在“倒行逆施”与“顺藤摸瓜”、“左顾右盼”与“瞻前顾后”的多向度、多层级的言说机制中趋近共识。惟其如此,中西古今的异同之辨才能见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理论图景;惟其如此,富有学术张力的两种对话才能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构提供新鲜而深刻的思想启示。
其二,真正在深层牵动、制约两种对话的“元问题”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又衍化为中国文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全球性、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以及多元化与一体化辩证关系等“次级问题”。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总要在这些“次级问题”的境域中给予回答,或者说,这些“次级问题”的研讨最终要回落到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上。而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就是一个如何应对一元论与多元论关系的问题,新加坡学者严寿澂认为,包括传统文论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研究要想自立于世,“历史文化的自觉实不可或缺”,而“历史文化自觉的最大障碍,则在于一元论的世界观”[16]。哈贝马斯提出“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的著名论断,且西方文化更没有权利与能力为整个世界提供现代性的“金字招牌”。多元化现代性不能否认现代性自有其共享的文化特征;同样,现代性的共有特征也不能否认须经特定的民族文化才能得以对象化。而“多元化”与“共有化”、“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的张力关系应在“交往”与“对话”中互动生成:“现代性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17]“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科学分析”与“人文祈求”两相交织、渗透是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之活力的保证,“历史还原”的唯物辩证原则与“意义还原”的现代性视阈相联结应是还给两种对话的“本体论承诺”(奎恩语)。
其三,在反思现代性危机与全球化思潮的双重语境中,中国文艺美学已日益引起域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后期海德格尔特别推崇老庄的“诗性的思想”,“在‘亚洲’或‘东亚’的范围内,海德格尔主要是与中国的道家进行了完全主动的并很有深意的哲学对话”[18];顾彬则在为卜松山的汉学研究成果写的《中文版序》中不无遗憾道出:“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却不了解这一点。”[19]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思想”内蕴深厚,且具有活态性、共生性和流变性等特征,特别是阴阳、有无、虚实、身心、形神、浓淡、笔墨、文质和情景等交互性观念,依照某种哲性或诗性的层递逻辑而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隐性思想体系,并在不同的文艺时空中显示出古典审美主体间性特征的诸种样态。而20世纪以来,随着“现象学运动”的风起云涌,伴随西方美学的“主体间性转向”,生存论美学、阐释学美学、现象学美学和接受美学等西方现当代美学展现出反叛传统形而上学美学的积极姿态,超越了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视审美关系为交融互答的“我-你关系”,它们与注重物我冥合、心物交融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相遇是必然的,中西古今文论有了更为广阔、更为坚实的对话平台。在这个对话平台上,“天人合一”观与“四方游戏”说、“身心一如”与“身体间性”以及“言意之辨”与“语言学转向”等中西美学基本命题可以在“互视”与“交谈”中进入“澄明之境”。中国古代文论蕴含的生存智慧与诗性精神在新一轮的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中会有更深广的开掘。
总之,途径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是我们谋求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重建不可抛却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在全球化思潮持续涌动与现代性方案不断优化的当代境遇中,应合两种对话的新契机,以主体间性思想观念为精神基点,既重视纵向梳理中国审美精神的生成与流变,也关注横向上中西主体间性美学的趋同与殊异之处,力求在经纬交织的学术坐标中厘定中国古代文论的主体间性特质,以期对重构中国文论话语有所助益。新时期以来,古今对话与中西对话中的古代文论研究将何去何从,不仅牵涉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基点与价值诉求,也承载着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思想厚度与审美效能,值得我们执着关注与理论深究。参考文献
[1]李春青.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34.
[2]蒋述卓,刘绍瑾.古今对话中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1.
[3]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86.
[4]童庆炳.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党圣元.学科范围、体系建制与书写体例[J].甘肃社会科学,2007(4):15-20.
[6]曹顺庆.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23-129.
[7]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49.
[9]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
[10]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J].文艺研究,2007(2):4-16.
[11]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12]王元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56.
[13]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25.
[14]党圣元,章辉.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7(2):63-68.
[15]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一卷[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
[16]严寿澂.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历史文化的自觉[M]//徐中玉,郭豫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二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
[17]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6.
[18]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事实、评估和可能[J].哲学研究,2009(8):65-76.
[19]卜松山.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M].向开,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责任编辑伯灵校对伊人凤)
Research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in Ancient and Modern Dialogue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in New Period
CHEN Shi-b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235000,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dialogue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are the the condensed thinking way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zation.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reduction principl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meaningful reduction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should be 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 to two kinds of dialogue.In the double contexts of globalization trend and reflecting on modernity,the divis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of Western Aesthetics has been the new opportunity of seeking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zation through two kinds of dialogue.
aancient and modern dialogue;dialogue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a;new period;ancient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2015-12-2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01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11YJA751005)
陈士部(1968-),男,江苏东海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
10.13888/j.cnki.jsie(ss).2016.03.001
B83-0
A
1672-9617(2016)03-02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