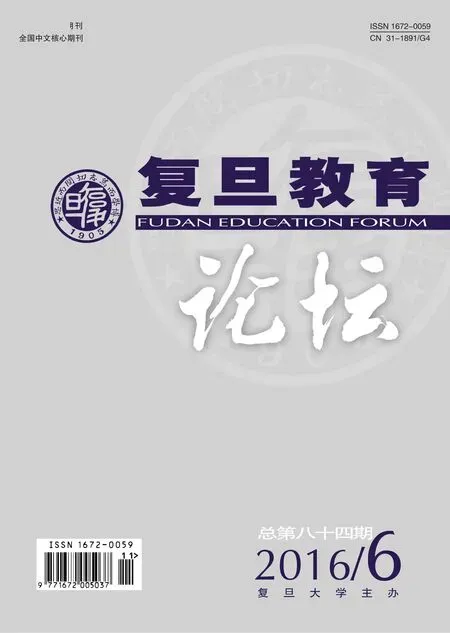对香港大学舍堂育人模式的反思
杜晓馨,邓卓
对香港大学舍堂育人模式的反思
杜晓馨1,邓卓2
(1.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香港999077;2.香港大学理学院,香港999077)
香港的舍堂教育一直在高等教育中彰显出全面育人的特色,在高校课堂之外发挥着重要的公民教育作用。作者对香港大学的舍堂教育进行了参与式的实证研究,通过反思港大住宿申请模式、管理模式和舍堂的日常运营及其公民教育功能,对这一育人模式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评议;从学生学习习惯培养、公民意识培养和国际视野拓展等角度探讨舍堂教育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
香港;舍堂教育;公民教育
住宿制度是高校课堂之外重要的育人场域。香港大学的舍堂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对于住宿制度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都能提供有意义的素材。在大陆各地高校都推行通识教育和住宿型书院之时——如北京大学的元培项目、复旦大学的书院制等等,对华人地区高等教育机构里较为成熟的住宿育人制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尽管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本文提供了以香港大学住宿舍堂为基础的案例,作为一种具有比较视角的资源,为中国大陆的各高校提供参考。
一、目前舍堂教育研究的不足及对其研究的意义
在研究香港高校的相关文献中,以香港大学作为案例的较少,研究深度也不够。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以舍堂教育作为香港高校全人教育的一个部分来阐述,大多讨论了香港大学学生多地域性的混合住宿模式是一种良好的国际化尝试,学生自治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丰富的舍堂活动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1-3]。然而,这些研究或多为通过二手资料整理而成,或由于相关数据比较陈旧,而不能反映舍堂教
育的全貌。除了学术性研究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料,包括留学杂志、网络文章或者网络博客,提到了不同人对舍堂教育的相关体会和观点,其中有对舍堂教育促进学生融合和认同感进行讨论的[4-5],也有对舍堂教育提出批评的[6-7]。这些虽然都是第一手资料,但都比较偏重于主观感受和个人经验分享,而在学术性分析上略显不足。显然,对这一案例的深入了解需要通过客观学术性和主观感受性两方面结合的研究以呈现其全貌,才能更好地为相关的大陆和海外高校住宿制度比较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因此,本项研究致力于填补这样的空缺。
本文主要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以香港大学的舍堂教育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数据收集方式为文献资料搜索、观察和访谈。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可以带领研究者进入对问题更深层次的解读,与访谈者共同进行研究[8]。案例研究是对现实某一具体问题、现象或者事务的考察、描绘和探索,能够为理论检验、发展及修改提供重要的研究途径。案例研究具有特殊性、描述性和启发性的特点[9],是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根据研究中使用案例的数量,可以分为单一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10]。本文通过单一案例为读者提供更加深入的视角。文献资料一般通过文字、数字等形式出现,文献研究的目的就是将这些资料收集,通过分析、归纳、总结来探讨需要探索的行为、现象等[11],是一种非接触性的研究方法。观察法有助于得到在访谈中对象不愿表达的一手资料;而访谈是对现象及其背后观点的解释和补充[9]。本研究所采用的非结构性访谈即非正式访谈,相较于结构性和半结构性访谈而言,更能够获得访谈对象比较真实的观点和感受。三种数据收集方法最后整合在一起呈现研究发现。
本文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包括了香港大学官方各下属网站的基本政策和规定的信息、舍堂录取资料、与舍堂教育和文化相关的网络文章等等。本文的两位研究者在舍堂有2-7年的住宿或工作经历,期间采用非结构性方式访谈了15位不同类型的宿生及住宿导师①。所访谈的宿生生源包括大陆生源、香港生源和国际生源(台湾地区、德国、美国、斯里兰卡、印尼等),学生类型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及交换生。
通过对以上收集资料的研究,发现香港大学的舍堂制度尽管有设施良好、活动丰富、高度自治等特点,但也有一些内在规则制度及其产生的影响值得反思,包括在学生学习、活动意义和育人目标方面存在的几点不足。
二、舍堂育人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舍堂这一育人模式有其正面积极的影响,比如舍堂的第二课堂作用、学生的自主管理和国际化的社群等,这些都为培养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世界公民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但其中却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一)丰富的第二课堂:舍堂活动繁重造成对学业的忽视
舍堂中的学生活动组织主要依靠各类学生社团。社团主要分成三个类型:运动类,包括各种球类、田径、水上运动等;文化类,包括音乐、舞蹈、合唱、戏剧、辩论、桥牌等;社会服务类,包括编撰舍堂所办的刊物,组织公益活动等,内容多涉及社会热点问题,如香港法制制度、大陆高考移民、香港外籍劳工福利等等,同时也会定期组织学生到香港各社区进行探访和慰问。运动类和文化类社团日常训练的频率比较高,以准备舍堂间的各类竞赛。
除了学生社团之外,还有正式宴会、新生迎新营和期末聚餐等舍堂和楼层的活动,以增进学生之间的了解,学习一定的社交礼仪,熟悉学校。这些活动让年轻人打开视野,关注课堂之外的社会,丰富精神生活,为学生提供了积极健康的住宿环境。
然而,一位曾在香港大学就读的学生在《上海观察》上有这样一篇文章,表达了非本地生②的心声:“港大,想说适应不容易”[12]。舍堂活动一直被港大学生认为是大学事务里最耗费精力的一项,并且这种精力的牵扯已经影响到了学习,以至于很多同学在课堂上不愿意和住在舍堂的同学同组做课程作业,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会因为宿舍活动太忙而无暇顾忌学业。事实上,舍堂本身对学生学习习惯的鼓励和帮助一直以来都比较少。
因为繁重的舍堂间竞赛和舍堂、楼层内部的活动以及集体生活,本地学生很少有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首先是活动过多引起的普遍精力不足。有教授表示上课的时候看到下面学生睡倒一片的一定是住舍堂的学生[13]。在新生迎新营期间,学生可能会开会到晚上两三点,五六点的时候就相约去喝早茶,甚至一天只有一小时的睡眠。这虽然也是非常有趣的学生生活经历,但在新生迎新营过去之后的新学期伊始,学生还在排练各种口号和访问高年级的堂友③,舍堂的各种活动仍旧占据了学生大量的时间,留给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的时间却非常少。在非本地生的受访对象中,多数都表达出不愿意在课堂上与住在舍堂的本地生分在同一个课题小组,因为会有被搭便车(逃避责
任)或者小组作业做不好的风险。受访的一位某舍堂楼主表示,第一年学生的综合绩点(GPA)都没有超过2分(总分为4.3分),因为实在没时间读书,只好答应父母第三年退出舍堂住在家里以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尽管舍堂在录取学生时候要求学生的GPA不能低于某一个值,但这个值普遍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并没有对学生的学习起到激励的作用。
其次,舍堂目前为学生们提供和学术有关的活动还略显不足。香港大学对舍堂功能的定位有别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度(College)和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学术导师制度(Academic Tutor),宿舍既是活动的地方,也是学习的地方。观察和访谈中发现,舍堂一般会组织成绩较优异的高年级学生组成一个“住宿学术顾问”(Residential Academic Advisor)团队来为宿生提供学习辅导的相关活动,然而这种顾问团队的执行大多都是被动性的,往往需要宿生自己去主动联系。总的来说,舍堂里很少为学生提供学术性的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舍堂内的大部分活动基本与学术和课业无关。尽管在舍堂功能的定位上可以以学生课外活动为主,但如对学生学习造成了影响,这种定位模式还是值得深思的。
(二)自主的舍堂管理:人为设定的竞争机制扭曲活动本意
舍堂中学生的主要事务管理基本上都遵循自主性的原则。尽管在一些基础的管理层面上会有学校的教授、教工等提供援助,但在舍堂中的大小事务主要都由学生自主决定。
宿生会(Student Association)是舍堂中最核心的学生自主管理机构,由包含了内务、外务、财政、文化、运动等职能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组成。这些成员通过自主报名成为候选人,通过舍堂内的民主选举成为执委,为学生们发声和服务。同时,舍堂也在各个楼层设定了负责人,即楼主④。他们作为学生领袖会负责本楼层的各项事务,策划楼层的各项活动并配合舍堂的各项要求。这些学生干部在学生事务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增强了整个舍堂的凝聚力,增进了学生之间的感情,学生的社会参与积极性也因此被调动起来,自主管理的热情很高。
然而,正是因为学生事务由学生自主决定的原因,学生建立出来的整个管理体系都建立在舍堂入住的这个前提之上,即学生均以成功入住舍堂为一个目标,而资源稀缺和由学生制定的标准形成一个牵制的机制,自主管理的体系使得学生拥有了较大的决定他人去留的权力,因此一部分人的自主建立在一部分人自由限制的基础之上。
如之前一个部分的内容所述,香港大学的舍堂活动丰富多彩,包含了社区服务、体育文艺及社会关怀的方方面面,然而很多学生都表示,他们参与舍堂活动的动机就是获得来年的住宿机会。与大陆高校的宿舍相比,香港大学的宿位显得尤其紧张。首先是在校园中的入住比例较低,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入住宿舍;第二是住宿环境相对较好,因此是比较优质的资源。这两点造成了宿位的稀缺,从而使竞争的机制得以形成。
港大虽有十三处住宿舍堂,然而本科学生入住的满足率却不足三分之一。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香港大学在籍本科生为15411人[14],而同年开放给学生的所有舍堂的宿位只有5914个(其中已经包括了不同于舍堂的学生书院的1800个宿位)[15],因而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住在学校的宿舍中,远远低于国内大学全员住宿模式的在校住宿比例。未能入住校园宿舍的本地生只能住在家里,每日的通勤也需要占据一定的时间;而未能入住的非本地生可以在外租房。然而学校附近类似条件的公寓的租金可能在舍堂宿费的两倍甚至以上。在香港大学,大部分的宿舍设施也都比较齐备,管理井然有序。一般都有宿舍大堂和办公室、洗衣房,并有相应的楼层作为宿生活动室和阅览室,卫生设施也都整洁,学校配有专人进行日常维护。可以说,在硬件方面,香港大学的住宿环境普遍比较整洁和完备。
在舍堂对学生的录取方面,对本地生与非本地生采用不同的标准,学生有不小的压力。本地生需要更加投入地参加舍堂的各类活动才能获得下一年的住宿资格,为本科生住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香港大学的住宿申请比较系统化和规范化。学生在获得学校的录取通知后可以在香港大学学生发展与资源中心(Centre of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for Students,简称CEDARS)网站上看到各个宿舍的概况,可以通过点击链接直接到舍堂的网站上了解更多的信息,最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喜好进行宿舍的申请。学校会根据学生对宿舍的需求情况酌情进行审批,同时舍堂宿生会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本地生必须经过面试才能入住舍堂。原本住在宿舍的旧生⑤在新生开放申请的前一段时间就开始了内部申请的程序,主要由宿生会决定学生去留,由CEDARS进行申请审核和备案。宿生会根据学生在舍堂过去一年的表现来为学生进行量化评估,例如学生参与活动的总体情况、成绩不能低于某一个标准、学生与其他同学相处的情况、是否有违纪等等,而其中最大的比重在学生对舍堂活
动的参与度上。
由宿生会制定的入住标准中,活动参与度的评定对于本地生和非本地生是双重标准的。非本地生在舍堂的参与度可以低于本地生,而对于本地生的要求是希望大家都尽量参与到每一项活动中去。对于非本地的本科生,包括大陆学生和国际学生,学校提供不超过两年的在外租房补贴;特别针对中国大陆学生,提供了在到港第一年内能确保住进舍堂的优待制度。有了这些保障,非本地生便能以相对自由、有选择地参与到舍堂活动中去,而不必过分担心住宿的问题。然而,非本地生需要通过“对舍堂做贡献”来确保自己的宿位,参加的活动越多,甚至如果能帮助舍堂在一些竞赛中获奖,那在来年留下宿位的几率就越大。对非本地生来说参与活动是加分项,而对于本地生来说都是必须完成的事项。
例如,新生迎新营的活动,原本应该主要是帮助新生了解舍堂和学校历史、增进相互之间了解的过程,而现在则更多是本地生将舍堂传统进行强制性传承的过程。高年级学长学姐对于新生极其严厉,在宿舍中排练口号和歌曲可以持续进行到第二天凌晨,其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强度绝对不亚于中国大陆学生的军训,且时间更长,压力更大。在新生迎新营结束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本地生还被要求走访本舍堂大部分的高年级宿生的寝室[5],和他们进行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沟通以相互了解。如果有学生因为之前申请失败没有参加新生迎新营,而是之后进入舍堂住宿的,这些工作就要从头补齐。虽然迎新营及之后的活动培养了新生比较强的认同感,但其形式很有值得商榷之处。
另外,作为香港大学舍堂中传统的高桌晚宴,也渐渐失去原有的旨意。原本的高桌晚宴主旨是想让学生结识更多优秀校友、社会人士,并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提升大学学习的品质,同时帮助学生学习社交礼仪。然而,近两年来高桌晚宴的嘉宾演讲和社交内容都不能持续吸引学生,宿生会便使用强制手段来要求宿生参加。所有学生在进入晚宴举办地和离开时都要刷学生卡,若缺席或早退而没有提前请假,就会收到舍堂办公室发出的警告信,甚至影响学生下一学年的住宿。一些原本有意义的活动现在成为了评估学生表现的手段,约束了学生自主参与活动的意愿。
这些活动、规则、传统,大部分是由学生自主提出、宿生会民主通过的,便形成了一套入住的标准和规矩。这尽管在管理形式上是民主的、自治的,但是其内核却很值得反思。
(三)国际化的舍堂居民:本地生与非本地生的文化隔阂阻碍世界公民的培养
香港大学舍堂里的学生通常来自世界各地,这与大陆的高校将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分开在不同的宿舍区域差异较大。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国际化社区,舍堂里不同背景的学生可能住宿在同一房间,或者通过舍堂活动增进彼此的了解。舍堂的宿生会或者楼层里也设有专门联络非本地同学的学生代表,以了解不同地区学生的诉求并且与他们保持沟通。舍堂主要的交流语言是英语,这也是香港大学的官方教学语言。让世界各地的学生居住在一起有利于学生认识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可以相互了解文化,打开视野,消除偏见,让学生的心态保持开放。
然而,在促进本地生和非本地生交流的层面上,舍堂本身的制度或机制还稍显不足,或者说舍堂的一些现存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会增强对这种交流的壁垒。在港大的舍堂中虽然保证了对国际学生和大陆学生一定的录取名额,舍堂中也确实住着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然而交流却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本地生和非本地生的融合不足,相互了解也非常有限。
首先,语言是一个很大的沟通障碍。虽然生活在同一区域,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无论是内地生还是国际学生都很难和本地学生融合。虽然学生之间的英语水平用于交流都毫无问题,但是本地学生多习惯说粤语,有不少受访者就认为作为一个华人社区实在没有必要时刻用英语交流[6]。即使不使用英语,大部分的国际学生还是希望学习运用范围更广泛和更加书面化的普通话而非粤语。同时英语又是学校的教学语言,教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不匹配造成了学生之间交流的隔阂。对于中国大陆的学生来说,他们不够熟练的粤语和香港本地学生不够熟练的普通话也造成了一定的沟通障碍。在舍堂中,大部分时间里同为中国人的大陆宿生和香港本地宿生主要还是用英语进行沟通。当舍堂社团进行训练时,为了提高效率,大部分的沟通都是用粤语进行的。尽管非本地生可以报名参与到社团中去,但是能真正完全融入到团队中是很困难的事。以合唱队为例,尽管歌曲大多是英文歌曲,但在排练中不时以粤语进行沟通和队友之间使用粤语聊天,使得一些受访的印尼或者中国大陆学生表示无法真正感觉到是团队的一份子。
在楼层的活动中,尽管部分本地生是有兴趣去了解非本地学生的,但有些学生则完全沉浸在本地生的生活中,并没有与其他非本地学生沟通和相互了解的
意愿。本地生总是集体活动,即使是晚上的课余时间,也都是坐在公共空间里看电视、聊天、做运动,过半强制的集体生活。非本地生很少和本地生一起在公共空间活动,基本是都是回到自己的房间自行活动。尽管非本地生在参与活动上的要求低于本地生,但非本地生与楼层里本地生的关系亲密与否却有可能直接影响下一学年的住宿。这是因为楼主会给每一个楼友⑥进行年度综合评价,评价内容包括了楼层/舍堂活动参与频率,与楼友的人际关系,以及一些主观印象等,这些评价会在宿生下一学年的住宿资格上有较大的决定权。因此,可以说非本地生的去留极大程度上是被本地生所掌握的,而这种制度导致了很多楼友之间的互动带有一定的目的性。而在个人权益上,在某些舍堂里非本地生并不享有楼主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使得大部分的楼层事务也都由本地生决定。本地生和非本地生之间友谊的建立,完全靠个体之间的积极互动和一些偶然的契机。
三、研究结论及对舍堂教育的反思
在港大这种各地学生混合住宿的整体环境中,舍堂中的重要事务都由学生自主决定,学生参与度非常高,但是却并没有给本地学生和非本地学生提供足够自由地学习、生活和交流的机会,同时一些规则的运行也违背了舍堂原有的育人目标。这些与条件、资源的限制不无关系,但在制定学生录取规则等方面,还是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首先,针对自主管理却缺乏民主的问题,各舍堂看似具有一套完备的规则体系,且舍监⑦的权力确实相当有限,学生自主程度很高[16],然而使得规则并没有成为真的制度的却是学生自己。所有学生入住之后都会得到一本舍堂的规则手册,但是对于如何在舍堂中生活,如何获得下一学年的宿位,施行的却是一套并非完全透明的规则。尽管讨论舍堂内部事务可以进行民主商议,投票决定,但学生下一学年住宿去留成为了让学生加入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最重要的砝码。本地生一旦进入舍堂住宿,就要做好最大程度地、毫无私人时间地投入到舍堂活动中去的心理准备。对于非本地生而言,自己的下一学年住宿非常可能全部倚赖于和本地生的关系。所有活动的参与并不是完全量化的,依靠一定的个人印象,本地生的互动参与度评价全部基于并依靠高年级生给低年级生的朋辈压力,所谓沿袭传统;非本地生则依靠熟悉度,例如男生宿舍的同学是否有共同打游戏的经历等等,来评估一个非本地生和本地生的熟悉程度和楼层活动参与度。学年末楼主会向导师提交报告,内容关于对楼层中楼友的活动参与情况及对舍堂的贡献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总结。住宿导师会进而向舍监提交报告,舍监、导师和舍堂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共同讨论决定宿舍下一年的录取情况。这一制度赋予楼主一定的评估权力,这样的主观成分也使得舍堂内学生活动参与的动机呈现出部分非自愿的扭曲状态。
民主制度具备“法治”与“问责”的重要功能和特点[17],但在舍堂内,有法制却没有法治,也根本没有问责的系统,其起源是资源的紧缺和分配的完全不平等。在个人-社会这一公民教育的层次中,舍堂教育首先失去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通过舍堂教育得到了一种固化:为了争夺资源,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合群的人,以融入共同生活中。通过访谈和观察,研究者看到了不同的学生心态:学生也并非人人都出于不自愿,有些学生乐在其中;有些能感觉到制度有不合理的地方,想要略作微调,但程度有限;有些为了得到一个宿位忍气吞声;有些经历了一段舍堂生活后发现实在无法认同和适应,愤然退出舍堂,宁愿每日在学校和家之间来回奔波两个小时以上。舍堂虽有自由和规则,却谈不上有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制度。资源的紧缺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人为的规则制定却也成就了一部分的不公平。这一点值得舍堂的规则制定者,包括学生事务部门、舍监和学生共同来思考:存在问题的舍堂教育是否是一种有益的、能帮助学生学习政治知识、习得政治参与的公民教育模式?
第二,香港大学希望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并希望通过舍堂活动来锻炼学生全方位的能力,尤其在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上,但很遗憾,这一点并未能在舍堂中有所促进。学校的具体育人目标为“培育优秀的毕业生,既好学不倦,又具个人操守和专业精神,而且触觉敏锐,能在所属行业担任领袖和联系人”。同时学校提出将香港大学打造成为香港、中国和亚洲的学术中心,加强与世界的交流[18]。从学校相关网站还可以看出,大学希望推进学生在社区中的公民参与,同时,CEDARS和相应的学院都有推出有关“世界公民”的教育项目或学术项目,以及一系列到内地考察的项目来促进学生与中国大陆和全世界的交流。而舍堂自身也会对学生提出国际化和全面发展的要求,例如太古堂作为香港大学传统舍堂中的一个,也是旨在贯彻舍堂教育的目标:“为在课室环境以外向学生提供各种学习机会,进而协助他们达至全面个人发展”,并将鼓
励学生多元发展、民主议事、参与社区、不仅仅关注本地等作为自身的教育特色[19]。在这其中不难看出公民教育的几个层次——世界的、国家的、本土的——在港大的育人目标和内部的舍堂教育目标中都有所体现:参与社区事务关注本地、在多元学生活动中关注自身、在交流活动中关注中国大陆和世界。然而这一些学校和舍堂都提倡的价值却恰恰没有体现在舍堂教育中,空设有良好的国际化混合住宿的框架,却没有让学生真正相互沟通、了解中国、放眼世界。在这一点上香港大学的舍堂教育确实存在一定的缺憾。打破本地生与非本地生之间的壁垒应该可以通过更多有意识的促进来完成。如果要在公民教育的层次上增添世界公民的认知[20],那么本地学生和非本地学生在舍堂中的融合问题将会是很需要重新定位和策划的。
综上,香港大学应当在保障学生自主管理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评估舍堂育人目标和实际达成之间的成效关系,在舍堂录取制度、学生活动的策划和促进学生交流的制度上能有所改进。大陆的高校在推行通识教育、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其中的一些制度设计的弊端,并且从中规避,以还原通识教育和住宿教育的本质和意义。
注释
①住宿导师主要负责舍堂宿生日常纪律、操行和福利事宜,包括:舍堂办公室制定的每月夜间值班工作;了解堂友、开展不定期非正式的聚会和讨论,给予他们由舍监制定的针对个人或者集体的总体性指导和建议;在舍监和高级导师无法履职期间承担执行舍监的职责;其余由舍监制定的特定职责,同时检查学生是否违反舍堂相关规定,如留宿舍堂之外的学生、身体伤害等。
②非本地生指所持护照为香港以外的国家/地区的学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国外学生。
③堂友指住在同一舍堂的宿生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称呼。
④楼主指某一舍堂的楼层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楼层代表,负责统筹楼层的一般学生事务及活动发起。
⑤旧生指原本住在这一舍堂的宿生。
⑥楼友指住在同一楼层的宿生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称呼。
⑦舍监指由学校任命的舍堂最高管理者,一般由学校教师担任。
[1]徐蕾. 香港高校学生工作主体性教育的特点分析及其启示[J]. 北京教育(德育),2013(2):79-80.
[2]杜久楠. 全人教育视角下香港大学舍堂教育研究[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105-108.
[3]林正范. 香港高校的“舍堂教育”[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89 (4):43-46.
[4]叶诗安. 港校迎新,逗比青年的癲狂聚会[J]. 留学,1989(17):84-87.
[5]马金馨. 安睡之外——记香港大学的“舍堂文化”[J]. 中学生天地(B版),2007(3):39-41.
[6]GENIUSCHAN. 港大舍堂文化[EB/OL]. (2006-11-22) [2015-11-24]. http://geniuschan.mocasting.com/p/91902.
[7]河西. 谈大学教育,又谈舍堂教育[EB/OL]. (2013-05-06) [2015-11-24].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3/05/06/ 37742.
[8]陈昺麟. 社会科学质化研究之扎根理论实施程序及实例之介绍[J]. 勤益学报,2001(19):327-342.
[9]MERRIAM S B.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M].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ossey-Bass Publishers,1998.
[10]YIN R K. Applications of Case Study Resear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3.
[11]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2]晓波. 香港内地生:理解状元不选港大[EB/OL]. 上海观察(2014-09-24)[2015-11-24]. http://www.shobserver.com/news/ detail?id=1273.
[13]翡翠台. 一宿难求[EB/OL]. (2012-09-29) [2015-11-24]. http://programme.tvb.com/news/newsmagazine/episode/ 20120929/.
[14]香港大学. 数据一览[EB/OL]. [2015-10-06]. http://www. cpao.hku.hk/qstats/student-profiles.
[15]CEDARS. A Profile of New Full-tim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2012/2013 (2012-2013学年全日制本科生新生概况) [EB/OL].(2014)[2015-11-24]. http://www.cedars.hku. hk/publication/UGprofile/UG1314_Full_Report.pdf.
[16]程介明. 我与大学宿舍[J]. 上海教育,2006(5):35.
[17]刘瑜. 重新带回国家——重读福山(下)[EB/OL]. (2014-07-12) [2015-11-24].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 /read/article_20140713109320.html.
[18]HKU. 抱负与使命[EB/OL]. (2014)[2015-11-24]. http: //www.hku.hk/about/c_vision.html.
[19]明德·知·格. 团结真诚多元发展——太古堂专访[EB/OL]. (2013-09-12)[2015-11-24]. http://blog.hkuaa.org.hk/node/139. [20]LAW Wing-Wah. Citizenship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Politic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M].New York: Peter Lang,2011.
The Critiques on Hall Education Model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U Xiao-xin1,DENG Zhuo2
(1.Faculty of Education,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SAR 999077; 2.Faculty of Science,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SAR 999077)
Hall education in the major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SAR has been carrying out its function of whole-person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 beyond conventional highereducation.This paper reports an empiricalstudy on hall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ased on participatory data collection in the field.By analyzing the collected data,the paper presents thorough critique and evalu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management mechanism,daily operation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function ofresidentialhalls.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halleducation have been addre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learning habit,cultivation of civic awareness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vision.Origin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ofthese problems are also discussed.
Hong Kong;Hall Education;Citizenship Education
2015-11-24
杜晓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及政治社会化研究;邓卓,香港大学理学院博士,上海科技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从事半导体光电子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