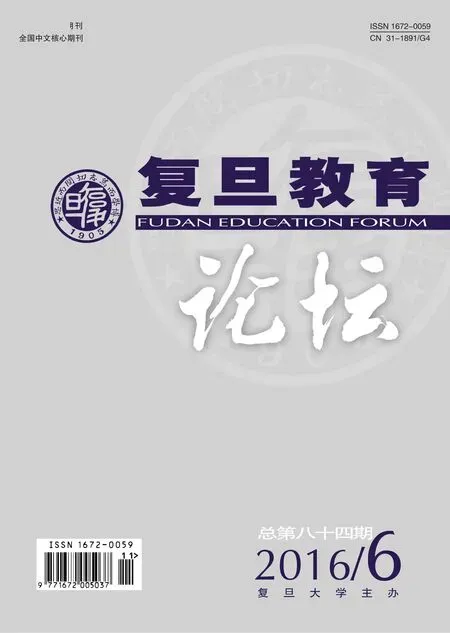恢复高考以来替考治理的制度变迁及现实启示
段斌斌
恢复高考以来替考治理的制度变迁及现实启示
段斌斌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100872)
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替考治理制度的变迁提供了极佳视角。恢复高考以来,替考治理经历了从“道德治理”到“行政治理”、再从“行政治理”走向“刑罚治理”的制度变迁,最终形成了处罚与刑罚并行的双轨治理制。替考治理制度的变迁,是主政者在关键节点破除路径依赖而选择断裂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唯有建构动态平衡、多元治理、过当其罚、比例适当的治理制度,方能使替考治理从低效乏力走向高效有力,最大限度地惩治替考行为。
替考治理;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
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通过,这意味着“替考入刑”时代的来临,也意味着替考治理制度阶段变迁的完成。自恢复高考以来,替考治理经历了近40年的制度变迁,最终形成了处罚与刑罚并行的双轨治理制。作为对过往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敏锐洞察,替考治理制度渊源于过去,塑造着现在,并影响着未来。因此,从学理层面系统梳理替考治理制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依法治考”的背景下不可谓无意义。“历史制度主义从历史长时段展开过程的事件序列,来分析制度变迁所受到的动力影响以及制度变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特性”[1]3,则为研究替考治理制度的变迁提供了极佳分析框架。运用该理论不难发现,恢复高考以来,替考治理经历了从道德治理到行政治理,再从行政治理走向刑罚治理的制度变迁。而治理制度的变迁则是在社会诚信水平、整体替考形势以及法治进步程度等环境的约束下,主政者在关键节
点破除路径依赖而选择断裂性制度变迁的产物。但囿于篇幅,本文着重选取从“行政治理”走向“刑罚治理”的阶段,进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分析。
一、制度变迁:恢复高考以来替考治理制度的演进
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并不是一个绝对稳定的因素,而同样有其生成和变迁的历史。制度变迁是把制度当作因变量,分析制度在什么客观条件和情境下将会发生再生、转型、替换和终止的过程。[1]123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一旦制度被正式确定,它就将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并陷于路径依赖的制度惰性之中,从而显现为制度的静态平衡期。但伴随着外部环境的重大变迁,现有制度的种种缺陷会被历史进程无限放大,并显现为制度难以应付各种新问题。而当制度的“阀值效应”出现之时,就会引发制度危机。制度危机往往要求主政者抓住“关键节点”和“历史否决点”,舍弃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由此也就导致了突发性的制度变迁,出现了制度的断续平衡。自此之后,制度又重新恢复稳定,再次进入静态平衡期,直至下一个“关键节点”的出现,如此形成制度的周期波动。不难发现,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是从制度生成、路径依赖、外部危机、关键节点、制度断裂等关键概念出发,来分析制度变迁的。有鉴于此,下文拟从替考行政治理的形成时段(即形成时段分析)、行政治理的自我复制机制(即路径依赖分析)、行政治理的重大危机(即关键节点分析)以及自我强化过程的中断(即制度断裂分析)出发,对替考治理制度的变迁进行解读。
(一)形成时段:替考泛滥而道德治理乏力导致行政治理制度的确立
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任何制度都起源于一个已经充满制度的环境之中,新制度的产生往往渊源于新环境带给旧制度的危机,且其产生过程无不受到旧制度的作用。而替考治理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遵循着同样的制度变迁逻辑。众所周知,1977年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考试取代推荐成为大学入学的新方式。在恢复高考的鼓舞下,华夏大地掀起了一股全民学习的浪潮,发自内心的知识渴望促使人们真心实意地勤奋求知,而对替考等作弊行为则极其不屑、避而远之。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替考作弊确实少见,而且替考作弊也仅被学校视为个人道德缺陷,社会舆论对此也不无宽容。梳理史料不难发现,面对较少的替考作弊行为,学校形成了一个以道德约束为主的软性治理机制:一方面,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考前纪律教育,重在预防;另一方面,对于胆敢(被)替考者则实行道德教育为主、纪律惩罚为辅,旨在挽救。譬如,某校规定学生考试作弊“除宣布该科成绩不及格外,应注明是‘考试作弊不及格’,存入档案”[2]。除此之外,再无它罚。应当说,在那个讲道德、重诚信的年代,道德治理机制对于预防和惩治替考行为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考试地位的提升以及诚信水平的下滑,替考作弊也开始在各类考试中“初露锋芒”、“崭露头角”,甚至在举国关注的高考中都曝出过替考作弊丑闻。一项针对某校大学生的实证研究表明,到1987年大学生考试作弊已不是个别现象,该校有过作弊经历者高达82.74%。[3]显然,道德约束机制对于治理替考作弊行为已然失效,由此替考治理制度也亟待变革。
面对日益严峻的替考作弊歪风,教育部陆续颁布了治理替考的规范性文件。1988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指出:“应考者在考试中有夹带、传递、抄袭、换卷、代考等舞弊行为以及其他违反考试规则的行为,省考委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取消考试成绩、停考一至三年的处罚。”该规定实际上是中央政策层面治理替考的制度开端。同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处罚暂行规定》指出:“在考试中,夹带、接传答案、交换答卷、代考、找人代考、抄袭他人答案或者将自己答案让他人抄袭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取消报名资格、考试资格、被录取资格,或者取消入学资格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并给予一至三年不准报考的处罚。”不难发现,此时替考治理在思路上并未严格区分“代考”与其他作弊行为。尽管如此,上述规定事实上开启了替考治理的“2.0时代”,即行政治理制度正式确立。正如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所说:“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是因为相关利益主体为避免两害而达至两利所形成的契约规则,这种规则能够为相关个体带来较之于其他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4]220因此,替考治理从“道德治理”走向“行政治理”,在当时背景下无疑是“避免两害而达至两利”的最优选择。
(二)路径依赖:行政治理制度的自我强化与制度惰性
如果说行政治理制度的产生是整体作弊形势与社会治理水平的共同产物,那么行政治理制度的长期存续则是因为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特性。所谓路径依赖就是指制度自身的自我强化机制,即一旦某种制度被选择之后,制度自身将会产生自我捍卫的内在强化机制,从而使得扭转和退出这种制度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高昂。不难发现,行政治理制度自确立
以来就深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但路径依赖绝不意味着行政治理制度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事实上,治理制度无时不在根据替考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针对猖獗的替考行为及其危害,1992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处罚暂行规定》就开启了重罚替考行为的历史先河:“考生由他人代考,取消当年考试资格,并从下一年起三年内不准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而其他作弊行为则仅被处以扣除该科所得分的30%-50%、取消当年考试资格、禁考1-2年等处罚。2004年《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指出:“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应当认定为作弊;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其他人员,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则将“由他人代替考试或替他人参加考试者”正式列为学校可以开除学籍的法定情形之一。2012年修订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则进一步延续了重点惩治替考作弊的治理思路。总之,行政治理制度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最终确立了取消考试成绩、禁考1-3年或开除学籍等行政处罚措施。
但在行政治理制度中,替考的潜在收益明显高于替考的违法成本。对替考者而言,一旦替考就意味着不菲的收入,即使失败行政处罚措施也在能承受范围之内;而对被替考者而言,一旦得逞就意味着获取了稀缺的入学(职)机会,即使失败也顶多失去未来1-3年的考试机会。[5]显然,违法成本过低的行政治理制度无疑纵容了私心私欲的膨胀和替考行为的发生。其实,早在2008年甘肃天水替考案之后,就有一批专家学者呼吁通过刑法强力惩治替考行为。但“替考入刑”的呼声仅长期停留于民间和学界的“摇旗呐喊”,而难以真正成为主政者心头的制度诉求。为此,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是,路径依赖是制约制度变迁的首要原因。任何一种制度一旦因具有比较优势而被选定之后,该制度存续下去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虽然另一种选择也存在,但特定制度安排所筑起的壁垒将阻碍初始选择中非常容易的转换。因此,虽然行政治理制度在惩治替考作弊方面软弱无力,但是路径依赖所产生的自我捍卫机制,却使得行政治理制度历经30年而难以实现断续性的制度变迁。
(三)关键节点:大规模高考替考案暴露了行政治理的严重危机
在系统论证行政治理制度的形成时段和路径依赖之后,必然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回答替考治理制度是如何破除路径依赖、实现断续性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并不认为路径依赖会一直存在下去,当客观环境不断发展,制度总是在某个特殊关键节点出现根本性变革。所谓关键节点是指“历史发展中的某一重要转折点,在这一节点上,政治冲突中的主导一方或制度设计者们的某一重要决策,直接决定了下一阶段政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4]236。也就是说,行政治理制度在被选择和设计出来之后,随即进入了路径依赖时期。在此期间,冲突各方之间、制度和环境之间以及各项制度之间都会保持静态平衡。但行政治理制度在经历了长时间稳定之后,也必然会被某一外部危机所打断,从而产生突发性的制度断裂。这一外部危机正是“关键节点”所在之处,而导致行政治理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正是频繁发生的大规模高考替考案。2014年河南杞县高考替考案震惊全国,仅查实的替考考生就多达127人。作为一个有着浓郁“高考情结”的考试大国,高考发生大规模替考无疑触碰了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并影响了替考治理制度的最终走向。杞县替考案曝光之后,社会在严厉要求惩治替考行为的同时,却发现在猖獗的替考面前,行政治理制度(取消成绩、禁考1-3年或开除学籍)极其苍白无力。经历了这一持续发酵的热点事件以后,立法者终于痛下决心,要根本改变乏力的替考治理制度,因为替考作弊已经严重到非得动用刑法制止的程度。2014年10月27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其中替考作弊与组织作弊等行为一同被规定为犯罪,纳入刑法打击范围。
然而,制度的路径依赖特性和自我强化机制却仍在捍卫行政治理制度。“对于替考者和被替考者是否应入刑,实际上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是有争议的。有意见认为,对替考者可以通过取消考试成绩、限考、终身禁考甚至是开除、解聘等措施,足以达到惩戒效果。根据刑法谦抑原则,不宜作为犯罪。”[6]全国人大常委会杨卫委员也表示:“很多学校的规章制度都规定,代考或者让人代考将会被开除,这种行政处理手段还是恰如其分的。……现在规定更严了,不但要开除,而且要入刑。组织代考行为入刑是应该的,但对年轻学生来说,有时候他们是为了帮帮同学,有的是想挣点外快,因为这个错误一下就被判了刑,会不会处罚过重?”[7]而正当“替考入刑”因存在争议而难以决断之时,2015年江西高考替考案再次将行政治理制度的治理危机暴露无遗。如果说2014年
河南杞县替考案将“替考入刑”正式提上制度议程,那么2015年江西替考案则加速了替考治理从“行政治理”走向“刑罚治理”的制度变迁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几年发生的有组织、大规模高考替考案,实际上成了治理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事实上,它不仅成了行政治理制度断裂的历史否决点,而且也成了刑罚治理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四)制度断裂:“替考入刑”标志着行政治理制度自我强化的中断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当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失去调适功能而不可能容纳新冲突时,原有制度就会出现断裂。而在制度断裂期内,制度自身就成为一个因变量,它的形成将受到环境和政治行为的塑造。因此,大规模高考替考案所引发的诚信危机和治理危机,正是行政治理制度的断裂根源。正如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中所言:“针对当前社会诚信缺失,欺诈等背信行为多发,社会危害严重的实际情况,为发挥刑法对公民行为取向的引领作用,维护社会诚信,惩治失信、背信行为,特将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8]事实上,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的表决通过,不仅意味着特定考试中的替考行为将会是犯罪行为,更意味着替考行政治理制度在经历了近30年的静态平衡之后,最终出现了断裂式的制度变迁。在刑罚治理制度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不难发现,替考治理从“行政治理”走向“刑罚治理”的制度变迁,不仅表现在处罚量刑的加重,更体现为国家对替考危害性认识的升格。在行政治理制度中,替考行为仅被视作违反考试秩序的行为,一般科处行政处罚;而在刑罚治理制度中,替考则被视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一旦定罪量刑,(被)替考者将终身背负“罪犯”标签,严重影响今后的学业、求职和升迁。
“由于任何新制度都是在旧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即使在进行新制度设计时引入了大量新观念和新制度的成分,但新铸就的制度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旧制度的影子。”[9]事实上,替考治理制度的变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不难发现,刑罚治理虽然确立了刑法惩治的基本原则,但“替考入刑”的有限适用范围则决定了行政治理机制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即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司法考试、会计师考试、公务员考试等)替考才适用刑罚治理,而在其他考试中替考则不适用“替考入刑”,但这并不意味着替考行为就能逃脱处罚、“逍遥法外”。实际上,在非“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替考的,仍然将按照原有的行政治理制度处罚,即受到取消考试成绩、禁考1-3年或开除学籍等行政处罚。另一方面,即使“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替考被科处刑罚,仍不能免除取消考试成绩、禁考或开除学籍等行政处罚。显然,刑罚治理制度渊源于行政治理制度,并保留了旧制度的诸多治理内容。自此,我国“双轨制”的替考治理制度也正式形成。
二、多元开放:历史制度主义对替考治理的现实启示
历史制度主义告诉我们,刑罚治理绝不是替考治理制度的演进终点,而只是其在未来演进道路上的全新起点。因此,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不仅为深入理解替考治理制度的过去提供了历史蓝本,而且其对制度变迁规律的揭示也为准确把握替考治理制度的未来演进提供了有益启示。
第一,替考治理制度应根据替考形势和治理效果而适时做出调整。根据克拉斯勒的“断续平衡理论”,“替考入刑”只是意味着替考治理制度暂时进入了静态平衡期,在新的外部危机来临之前,替考治理制度会被长期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路径之中;直至新关节点的出现,替考治理制度才会重新出现突发性制度变迁。有鉴于此,一方面,为避免陷入路径依赖之后的低效率,替考治理制度应保持一种开放态势,并根据替考形势和治理效果而适时对制度做出调整和修正。为此,加强刑罚治理的后期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抽象的法律规范能否转化为具体的事实规范,不仅关系到刑罚治理的最终实施效果,也影响着替考治理制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替考入刑的“成本-效益”分析是替考治理制度演进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替考治理制度的危机再次显现,则要求主政者果断抓住历史契机、打破原有路径依赖,从而实现替考治理制度的断裂变迁。否则,替考治理制度就只能长期迟滞于替考形势和治理效果之后,而难以有效惩治替考行为。
第二,替考治理在注重刑罚治理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行政治理和道德治理的应有作用。作为治理替考的两种重要方式,道德治理和行政治理都曾在替考治理的不同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作为替考治理的最
后一道防线,刑罚治理不可不用,又不可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替考治理的实效将最终取决于三种治理方式形成的有机合力。一方面,刑法的严厉性与杀伤性决定了刑罚治理的谦抑性与治理对象的有限性。正如卢梭所言:“刑罚的频繁总是政府衰弱或无能的一种标志,绝不会有任何一个恶人,是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使其为善的。”[10]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替考行为都适合诉诸刑法打击,刑罚治理的止步之处正是行政治理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11],因而替考邪恶的铲除必定离不开道德治理方式的参与。道德治理贵在增强刑罚治理和行政治理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从这个意义上说,替考治理不仅需要依法治理,也需要以德治理。为此,在以处罚和刑罚促进替考治理有序化的同时,又必须以德治促进替考治理的实效性。进而言之,道德治理需要浸润法治精神,强化法律对考生诚信的规范作用;而行政治理和刑罚治理则需涵养道德理念,强化道德对违法行为的教化作用。一言以蔽之,替考治理既要重视发挥刑罚治理的惩罚作用,又要重视发挥行政治理的约束作用,同时又不能忽视道德治理的教化作用。
第三,无论是道德治理还是行政治理,抑或刑罚治理,都离不开依法治理。在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的大背景下,依法治理替考行为已成为社会共识。依法治理通过建章立制既为治理替考行为提供了明确依据,同时也为行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明确指引,使其能够趋利避害、择善而从,从而达到积极预防并有效惩治替考行为的治理目标。而作为治理替考的重要方式,不管是道德治理、行政治理抑或刑罚治理都必须以依法治理作为依托和载体。毋庸赘言,行政治理和刑罚治理需以有法可依为前提,需以法治精神为支撑。即便是道德治理也不能完全摆脱依法治理的踪影:依法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而道德治理又不得与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相抵触。因此,对于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替考的,不能仅以道德说教而赦免其责;同样,对于在非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替考的,也不能仅仅一罚了之而舍弃道德教化。当前《国家教育考试条例》①正在起草拟制,如何将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真正浸润到各种治理方式之中,使其既有法治的刚性又有德治的韧性,对立法者而言显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四,平衡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比例关系是完善替考治理制度的关键。美国法哲学家富勒曾说:“与其告诉人们要做好人,不如设定条件迫使他们变成好人。”[12]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和理性算计的能力,当替考的违法成本明显低于潜在的灰色收益之时,替考或找人替考的冲动无时不在侵蚀人的道德良知和对法律的敬畏。更何况在行政治理制度中,替考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而只是违反考试秩序的行政违法行为。显然,替考行为之所以难以根治,重要原因便在于过低的违法成本极大纵容了私心私欲的膨胀,从而导致替考行为有恃无恐。经验表明,一项符合理性且设计精良的替考治理制度,将有效遏制替考行为的频率和范围;反之,无疑会纵容替考行为的滋生和扩散。与此同时,当替考成本明显高于违法收益之时,对替考行为的遏制极有可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治理保持必要之谦抑也必不可少。因此,治理制度能否恰当平衡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比例关系,将直接决定替考治理的成效以及权益保障的目标。
此外,从重从快取缔替考组织也是替考治理的必然选择。从目前曝光的多起替考案件来看,替考作弊大多涉及专业替考组织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正是有了替考组织的造假技术支持和幕后人情疏通,被替考者才敢“光明正大”地花钱雇“枪手”考试,替考者也才胆敢“堂而皇之”地走进考场应试。显然,专业替考组织的策划和运作,才是替考行为屡禁不止、禁而不绝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刑法才对替考行为的组织者和帮助者科处3-7年的有期徒刑,而对替考行为本身则仅科以拘役或管制,甚至情节轻微,可由财产罚取代自由罚。就此而言,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并取缔替考作弊组织,那么替考治理的实效就势必大打折扣。因此,不管替考治理制度未来会走向何方,从重从快取缔替考组织的治理思路,都应当一以贯之、不能动摇。
总之,替考治理制度的变迁,是主政者在关键节点破除路径依赖而选择断裂性制度变迁的产物。而充分把握历史制度主义的现实启示,有利于适时调整替考治理制度,也有利于形成多元治理的有机合力。如此,方能使替考治理制度从低效乏力走向高效有力,最大限度地惩治替考行为。
致谢
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申素平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以及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
注释
①由于立法体制的掣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原来提出的“六修五立”(《考试法》就在其中)的立法计划,在《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中被迫做了重大调整。其中,拟由全国人大拟制的法律《考试法》最终降格为教育法规,即《国家教育考试条例》。
[1]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朱从矩.搞好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2):118-122.
[3]史志英.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心理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1987(4):77-85.
[4]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段斌斌.替考入刑:政策演进、制度逻辑与现实局限[J].高校教育管理,2016(5):29-33.
[6]翁小平.端正考风,仅仅作弊入刑还不够[J].教育家,2015(12):48-51.
[7]王涵.刑九之后,哪些改变影响我们生活[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5-09-13(008).
[8]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草案)》的说明[EB/OL].(2014-11-03)[2016-02-23].http://www. npc.gov.cn/npc/lfzt/rlys/2014-11/03/.
[9][美]凯瑟琳·西伦,斯温·斯坦默.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G] //何俊志,等,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60.
[1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7.
[1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162.
[12][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1.
The Governance of Surrogate Exam-Taking since the Resumption of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DUAN Bin-bin
(Schoolof Educ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rovides an excellent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governance of surrogate exam-taking.Since the resumption of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the governance of surrogate exam-taking has gone through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moral restraint,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to punishment,and eventually formed a dual-track system.The breaking of path-dependence and the choice of fractured institutional change contribute to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governance of surrogate examtaking.Only by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system featured with dynamic balance,multigovernance and appropriate proportion ofpenalty,can the governance ofsurrogate exam-taking realize high efficiency.
Governance of Surrogate Exam-Taking;Institutional Change;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2016-09-18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高等教育法制的国际比较与最新发展”(10XNJ068)
段斌斌,男,1989年生,湖南冷水江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