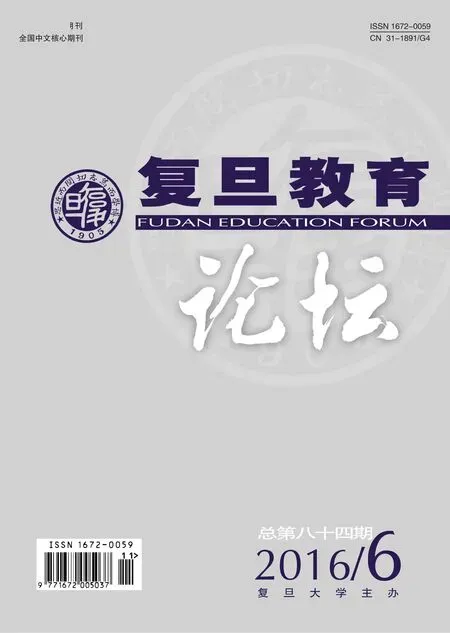洪堡的“大学之道”
俞可,弗里德里希·W·克罗恩
·域外·
洪堡的“大学之道”
俞可1,弗里德里希·W·克罗恩2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基地,上海200234;2.美因茨大学教育科学系,德国美因茨55131)
威廉·冯·洪堡诞辰250周年纪念在即,盘点其教育遗产,首推其“修身”理想,而非广为全球追捧并复制的柏林大学。作者追溯洪堡的“修身”理想之道统,进而展现洪堡为落实其“修身”理想而擘画的教育改革蓝图,并分析理想从蓝图中剥离之后所遭遇的窘境,最后以德国当今大学开设通识教育为例,剖析洪堡的“修身”理想重获新生的尝试。作者发现,洪堡的“修身”即为中国士阶层所遵循的“大学之道”,其使命在于,由“以文化人”而“止于至善”。“至善”实为愿景,故而,洪堡的“修身”及“大学之道”永远在路上,洪堡的“修身”理想之生命力就潜隐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性之中。
洪堡;“修身”;“修身”理想;大学之道;德国教育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教育遗产,必然首推其“修身”(Bildung)①理论甚或“修身”哲学,立足点为人,旨在创设自成一体的教育世界。统整这个世界的是“修身”[1]。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传统、元理论以及研究范式,对“修身”的概念释义千差万别,对“修身”的理论阐释莫衷一是,
对“修身”的现实批判波云诡谲。可达成共识的是,“修身”构建一种关联,即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反思性关联。就此,洪堡擘画的“修身”理论甚或“修身”哲学厥功至伟,最终以洪堡的“修身”理想(Bildungsideal)载入史册。作为教育遗产,其历史地位远甚于广为全球追捧并复制的柏林大学及洪堡的大学理念。
洪堡的道统
贵族出身的洪堡天资聪颖,自幼浸淫于精英教育,从而得以全面发展,语言禀赋尤甚,13岁便能在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中游刃有余。洪堡成长的那个年代,神圣罗马帝国如强弩之末,解体在即,诸侯割据,群雄争霸,却为思想繁荣营造一片沃土。而柏林,洪堡的故乡,当年在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s Groβen,1712-1786)治下迎来柏林启蒙时代[2]。洪堡尽情遨游,并主动介入百家争鸣,涉及的学界名家有克洛普斯多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海德尔(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Christian Wilhelm Wolf,1759-1824)、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舍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以及洪堡的挚友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其胞弟亚历山大(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及其自然科学界同仁。就思想史而言,这一学人群体所点燃的时代被教育史学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称作新人文主义(Neuhumanismus)时期[3]。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以古希腊文明为渊源,经由文艺复兴运动的继承与光大,新人文主义宣扬的实为欧罗巴道统。其在洪堡身上留有鲜明烙印,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目的论洪堡以终极取向为出发点来思索人的发展,目标是走进“全面完美的境界”(allgemeine vollkommenheit)[4]。人的发展应该指向一类理想化的典范型人才。于洪堡而言,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所诞生的博学多才者(uomo universale)或古代的贤人(polyhistor)。在文艺复兴时代,人走出黑暗的中世纪,首度被确认为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的个体(individual),受内心驱使,自主性地、批判性地、创造性地与自然、与社会乃至与自身构建意义,由此实现人的解放。以古代圣贤为榜样,可追溯至洪堡早年对古代史尤其是对古希腊文明的痴迷,以及对古代语与古代史专家沃尔夫著作的崇拜。探究历史,“根本在于以哲学来观照人”。对博学多才者的膜拜,洪堡则受希勒格尔的影响。作为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希勒格尔提出“进步的博学诗歌”(progressive universalpoesie),主张诗歌应该由博学的天才自由创作[5]。
精神性人不仅需要衣食住行,即物质生活,还要与思想共存,即精神生活。在其1793年创作的论著《关于古代尤其古希腊的研究》(U··ber das Studium des Altertums und des Griechischen insbesondere)中,洪堡不仅对古希腊文化崇拜(Philhellenismus)毫不讳言,而且强调个体的精神生活,并以三个群体为例: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这三个群体的创造力分别源自人类精神生活的三大旨归:真、善、美。洪堡认为,人一旦精神生活丰盈,其个性必然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即现在所说的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只有开启自我同一性构建进程,投身于与文化与社会的交互,世界才能完整地投射于个体;同时,个体亦可通过知与行为世界代言与担责,个体精神力量得以激活并迸发。这便是“修身”。力量(Kraft)则为核心概念。在1803年10月22日致友人布林克曼(Karl Gustav Brinckmann,1764-1847)的信函中,洪堡指出,力量具有“真正先验性”(wahre a priori)[4]。个体精神力量并非由外力注入,而是个体本源性力量即洪堡所说的“本源的自我”或“原始力量”,潜隐于个体肉体,蓄势待发。人的自由恰恰建立在此基础上[4]。强调力量源自内心深处,从中可以窥探克洛普斯多克的印迹。与启蒙时代人物不同,克洛普斯多克并没有高举理智的大旗,而是推崇伤感主义(Empfindsamkeit)。1779年,他把内心世界(Innerlichkeit)列为诗歌创作的九大要素之一[6]。洪堡认为,唯有“修身”才能使内心深处涌动的力量激活并迸发。
个性化在语言和文学中存有个体与世界之间互动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个体实现自我陶冶。洪堡的另一重身份是语言学家,被誉为比较语言学之父。如今,德国语言科学学会每年颁发“威廉·冯·洪堡奖”。在其1806年发表的论文《论作为特定精神形态之表述的语言》(U··ber die Sprache als Ausdruck eigentümlicher Geistesform)中,洪堡把语言置于人的精神生活进而人的完成之中心。其语言哲学的要义是,作为介质,语言既介于自我与世界,也介于自我与他人[4]。语言的多样性折射世界的多样性[7]。语言与思想之间存有密切关联,只有在语言与思想交互之下,个体才能“以理想化
的方式领悟”世界,精神力量由此得以生成,且描述世界尽显个性化[8]。唯有“修身”方能使个性(individuality)在个体身上闪耀。在1797年发表的文章《论人性本质》(U··ber den Geist der Menschheit)中,洪堡指出,个体通过“修身”让“更真更善更美的人性在自己身上滋养”,由此,个性充盈着人性与德性。在1791年8月16日致友人福斯特(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的信函中,洪堡把“修身”视作“真正道德的首要原则”[9]。
和谐度个体的精神力量生成与人的完成呈同构关系。“修身”就是个体所有精神力量的和谐绽放,由此助力实现人的完成。个体精神力量,用当今学术话语来表述,就是思想、兴趣、情感、内驱型动机、好奇心、想象力、胜任力等等,借助语言,在与环境产生符号性互动中得以生成。和谐绽放意味着,精神力量的舒展显现为全面性与共时性。任何一种精神力量的精细化发展,倘若以牺牲其他精神力量的发展为代价,均不可持续。由洪堡推崇备至的个性应该被视作不同维度的精神力量齐鸣而演绎的一曲交响乐。在洪堡的论述发表之后若干年,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也抛出相似观点[10]。精神力量的绽放并非自发行为,而是自觉行为,需要与外界即大千世界产生自由、积极、全面的互动。在洪堡眼中,这只有通过与文化产品交互。这种交互须远离功利性,仅为纯粹的“精神交会”。既然“精神交会”必须纯粹,文化产品就要尽可能经历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近乎经典。奉古希腊文明为圭臬的洪堡尤为推崇研读古籍(studia humaniora)。洪堡发现,这才是成为圣贤的捷径。
洪堡的蓝图
洪堡的“修身”理想自萌发伊始便着手落实到教育制度中,让所有人都有获取“修身”的权利与机会。教育体系无疑是“修身”理想付诸现实的最佳载体。而1809年2月出任普鲁士内务部文化与公共教学司司长,则为天赐良机。洪堡遂架构三级教育体系,即三年制小学、十年制中学、大学[11]。这幅教育改革蓝图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契合洪堡的目的论,即国家需要圣贤辅佐,以图强盛。培育圣贤,大学最佳,即学术渊薮(universitas litterarum),囊括学术各大门类,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大学师生以研究者的身份“为学术而共处”[4]。大学堪为教育改革蓝图的皇冠。其生源须由十年制的人文中学(Humanistisches Gymnasium)来培育,实为大学预科。为此,洪堡推出三大规范:规范大学招生制度,1812年统一并强制实施人文中学毕业考试(Abitur),以该考试成绩作为大学准入的参考;规范人文中学课程设置,1816推出《课程设置计划》;规范人文中学教师入职制度,1810年设立师范生毕业考试(examen pro facultate docendi),重点测试师范生的古希腊语、拉丁语、历史和数学素养[12]。
国家主义1806年普鲁士惨败在拿破仑铁蹄下以及柏林沦陷,民族屈辱的切肤之痛激发全民对国家复兴的满腔热血。国家复兴,何人担纲?于洪堡而言,以古代圣贤为表率的知识精英为不二之选。洪堡的精神导师克洛普斯多克被视作德国民族国家思想之父。在1789年的诗作《认识你们自己》(Kennet euch selbst)中,这位法国大革命的拥趸把法国大革命奉为“百年来最大壮举”,并号召德国民众以法为师,揭竿而起。1792年,法国国民议会接纳他为荣誉国民。克洛普斯多克早在1774年创作的《德意志学人共和国》(Die deutsche Gelehrtenrepublik)描绘的就是一幅启蒙时代的乌托邦图景:以知识精英统治来取代权贵统治。这个共和国应该由乡贤、公会与大众来统治,但最大的统治权限应赋予知识精英。克洛普斯多克对人民专制持否定态度,认为那仅为一群“乌合之众”,在议会只会“惹是生非”[13]。
平民情怀洪堡设计的蓝图,每一学段终结毕业生均拥有就业能力。1809年,他推出两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校改革方案:《柯尼斯堡学校规划》(Ko··nigsberger Schulplan)和《立陶宛学校规划》(Litauischer Schulplan)。设计两份学校规划的意义在于,以基础教育(Allgemeinbildung)来抵制沿袭下来的等级制教育如贵族学校、军官学校和市民实科学校。洪堡认为,社会走向文明与德性,基础教育不可或缺。这里的基础,洪堡使用Allgemein,指的是全面,分为三大向度:首先是学习主体的全面性,即全民性,教育体系不应针对农民、市民和学人三个阶层而分成三六九等,设计三年制小学所借鉴的模板则为瑞士的平民教育之父裴斯泰洛奇(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其次是学习内容的全面性,如洪堡所言,木匠学习古希腊语并非毫无价值;再次是学习目标的全面性,即核心素养的综合发展,以实现洪堡所殷殷期盼的精神力量和谐绽放[14]。洪堡之所以被誉为德国自由主义之父,缘由尽在Allgemein之中。
精神革命如同克洛普斯多克,洪堡及其新人文
主义战队对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创设的共和制亦心潮澎湃。洪堡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自由、平等、博爱”不可以暴力如战争与杀戮来实现,而是以和平方式。这种和平方式只可能是“修身”,从而内可促进个体的个性发展,外可推动国家的制度建设。遵循克洛普斯多克的观点,“修身”为“德意志学人共和国”至高无上的财富。由“修身”而成人的公民(Citoyen)理应肩负统治国家的使命[13]。在洪堡的教育改革蓝图上,人文中学堪为中流砥柱。既然洪堡式的大学定位于学术共同体,那么,人文教育实施的最佳场所无疑是人文中学。既考虑到中学年限漫长,又顾及中学生年龄适当,故而,洪堡强调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在人文中学的主导地位,认为这是精神修炼。完成人文中学学业,人的完成已告终结,大学仅为学术修炼的殿堂。由此断言,“修身”理念,在制度上引发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在精神上则点燃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洪堡的教育史地位,大抵由这份蓝图决定。德国当今教育制度留有洪堡蓝图鲜明印迹:人文中学门庭若市的壮观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文中学毕业考试(Abitur)仍为跨入象牙塔最坚挺的通行证;人文中学教师照旧必须经由大学而非师范院校培养;大学依然信奉“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
洪堡的窘境
蓝图化作现实,却以失败告终。洪堡的厄运在于,理想虽为蓝图之魂,却从中剥离,神形割裂。“修身”理想在制度性转化中陷入无立锥之地的窘境。洪堡试图在其任上付诸现实,却到任仅16月便黯然消隐。离职其实另有隐情,在此不必赘述。上述窘境,洪堡在任期终结之际才有所感知,却已无力回天。
在理念层面,资本主义逻辑惯性无以复加洪堡希望所开办的学校能助力所有人实现“修身”,并让这个设想在教育政策与组织上得以实施。在这点上,洪堡的“修身”理想迸发出辩证的魔力。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知识在专科化或学科化过程中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提供极佳批判视角。“修身”日趋实利化,即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所言的“半吊子修身”(Halbbildung)。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社会再生产所制造的只有赢家与输家。阿多诺把“半吊子修身”在当今社会的蔓延视作“精神异化的无孔不入”[15]。由此可见,“修身”在理念层面是辩证的,在现实层面是两难的。
在学校层面,臣仆教育思维定势梗顽不化18世纪形成的精英教育体系旨在为国家输送臣仆[16]。制度化的教与学在精耕细作中走向工具化,并最终使制度中的人即教师与学生机械化。而洪堡认为,精神力量的生成与绽放只有通过与文化产品发生纯粹的“精神交会”。显然,这在教育体系中无以实现。学生强烈抵制洪堡改革,给人文中学扣上“应试”罪名。其实,学生只是惧怕文化产品的深奥以及精神交会的艰辛。譬如,人文中学强制要求用拉丁文完成作文,令学生不寒而栗。而推行拉丁文,只是因为学生逃避古希腊语而实施的妥协[17]。在洪堡一手打造的柏林大学,早在1818年,时任柏林大学校长马莱讷克(Philipp Konrad Marheineke,1780-1846)在一次动员报告中就对学习的“功利取向”予以抨击,认为学生为“未来实践生涯所必备的技能”而徒劳[18]。一味追求与文化产品发生的纯粹的“精神交会”,则把社会撕裂为能够享受人文教育的知识精神阶层和未能接受人文教育的劳苦大众阶层。原因在于,自幼接受精英式家塾教育的洪堡虽因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而心怀平等意识,却在其教育人生中,无论幼年作为读书郎还是壮年作为教育家,与平民教育体系无任何交集。
在社会层面,工业革命时代浪潮汹涌澎湃在1809年设计的两份学校规划中,洪堡坚决反对教育体系的分层化与工具化,尤其尖锐批判以培养技术与实用人才为使命的实科中学(Realschule)。工业革命浪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尽管德意志大地直到19世纪中叶才迎来工业革命,但周邦英国的现实,拥有全球视野的洪堡绝不可能闻所未闻。洪堡依然把整个教育理念与政策建立在故纸堆上,重塑古希腊的知识权贵(enkyklios paideia),而完全无视社会驶入工业时代的现实,实用型学科(Realien)如当年欣欣向荣的自然科学在学校教育遭遇无情压制。两份学校规划以束之高阁而告终,尽在意料之中。把“修身”物化为原料即教材,在“教教材”和“学教材”中把“修身”工具化为产品即文凭。这才是当时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现实需求。学校教育由拟古式走向求实式。这一现实,洪堡不愿接受,却不得不隐忍。
在政治层面,官僚势力保守习性积重难返洪堡的母亲伊丽莎白(Marie-Elisabeth von Humboldt,1741-1796)望子成龙心切,志在把洪堡兄弟俩培养成为国家领袖人物。故而,洪堡深知,只有进入内阁,方可有恃无恐地推行其理念。结果,受聘的职位仅为普鲁士内务部文化与公共教学司司长,受部长的掣肘,难以施展宏图。他写信给夫人说,委任使他沮丧万分。
1809年1月,长达两周,他对委任状置之不理,之后拒绝,并请求国王重新把他派往罗马教廷出任使节,但遭到国王严拒[19]。洪堡力图把德意志社会打造成为一个知识精英市民社会(Bildungsbürgertum),却在普鲁士国家机器中遭遇保守成性的官僚市民阶层(Beamtenbürgertum)的阻遏。他甫离任,1810年3月31日的内阁指令便彻底“摧毁了(洪堡)作为部门主管的作用”[20]。1819年的政治复辟之后,洪堡追随者推行的自由主义改良运动屡遭重创。政府高官贝克多尔夫(Ludolph von Beckedorff,1778-1858)指责洪堡“蓄意营造一幅大众教育平等景象”,其理念“与君主制度不相符”[21]。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改良主义教育学派(Reformpa··dagogik)进入巅峰时期,虽未给新人文主义敲响丧钟,却形成一种替代性选择,势如破竹。洪堡的“修身”理想付诸现实,必须寻求一个制度化的载体,否则便会折戟于残酷的现实。唯一载体就是洪堡以及克洛普斯多克理想中的“德意志学人共和国”,但这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洪堡的新生
洪堡的“修身”理想为教育史留下一座海市蜃楼,尽管其擘画的教育改革蓝图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洪堡身后不乏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作出种种尝试,由此在教育版图上铺展一条独特风景线。德国大学开设通识教育(Studium Generale,Studium Universale,Studium Fundamentale),此举即为尝试。
毋庸置疑,“修身”基于学习。遵循洪堡的“修身”理想,学习务必脱离工具理性的羁绊,而驶向价值理性。这就是为何在以学校为代表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中“修身”无处安放。但只要万事俱备,“修身”照样可以安身。在1809年12月向国王呈交的一份报告中,洪堡写道:“某些通识性知识绝对存在,当然,某些思想与性格的孕育就更不可缺失。就个体本身,无关乎其所从事的职业,要是一个人是优秀的、本分的、在所处阶层属于开明的人士和市民,那么,每个人看来均可成为一名出色的技工、商人、军人和企业家。提供给他必要的学校教育,他今后习得职业技能就相当容易,并拥有换一种活法的自由,如人生道路上所习以为常的选择自由。”[4]然而,随着以研读古代典籍为重点的人文中学日渐式微,而以学习自然科学为重点的新式文理中学异军突起,实现“修身”的使命便从中学阶段推延至大学阶段,其载体便是德国大学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在二战后进入德国高校。最初,通识教育作为必修课程,还需考试。但20世纪80年代,随着德国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跨入大众化阶段,通识教育普遍流于形式。大学生对通识教育产生强烈逆反心理,认为接受通识教育简直在浪费时间。冠冕堂皇的理由则是,通识教育违背学术自由原则。显然,这是工具理性在作祟。
尽管如此,德国目前仍有不少高校坚持实施通识教育,且不乏通过制度化与实体化予以强化。譬如,作为德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维腾-赫尔德克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Herdecke)1983年建校伊始便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最初设立通识教育中心,1993年改设为通识教育学院。通识教育课程为该校所有学生必修。每周一天,全校各专业的课程一概停课,为学生选修通识教育课让道,以培育学生的反思素养、交往素养、艺术素养[22]。该校甚而视通识教育为办学特色中的特色。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开设通识教育的历史悠久,为最早开设通识教育的德国高校之一,以“广开视野,深究知识”为宗旨。该校在1948-1949学年开启通识教育,最初承担引领大一新生学术入门的功能,一年后旋即转而面向全校学生。1953-1954学年,州政府拨款用于开设面向社会的系列讲座。该校早先就把通识教育中心设为校级机构,现设置专职岗位共10个:主任1名,副主任1名,秘书1名,学术人员7名。
通识教育所提供的不仅是跨学科知识,以破除专业学习的窠臼,更旨在培育与生活世界紧密关联的,学人在由知识爆炸所导致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时所应保持的学术定力——洞察力、辨析力、反思力、创造力。譬如,美因茨大学通识教育的主干课程是跨学科课程系列,由两大模块组成:面向本科生的“跨学科素养”和面向硕士生的“学术原理与基本素养”。每个模块由一门讲座课和一门练习课组成,既可供全校学生任选,也可由各相关专业纳入其培养方案,设定为专业必修课。后者,在需求量激增的情况下,可以与相关专业合作,单独开设[23]。
然而,德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实施方式更多显现为知识积累,把由学科化而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知识以大杂烩的形式灌输给学生。何以大快朵颐并消化吸收,进而融于个体的认知体系,则无从过问,任凭学生独自煎熬。就此,缺位的是引导,引导学生精神力量绽放,引导学生唤醒良知,引导学生激发兴趣,引导学生深刻反思,引导学生积极追问。这便呼唤学习进入更
高境界,即基于项目的探究性学习,是行动、研究与认知的完美结合。最佳为团队合作,因为项目所要解决的问题,其复杂性需要多学科戮力合作,个体显然难以胜任。项目遴选与团队组建,则需要教师的专业引领。通过这种学习,学生学会把自己的认知进展放置在项目中检验、与他人交流观点、欣赏他人的观点,与维腾-赫尔德克大学的通识教育所孜孜以求的反思素养、交往素养、艺术素养对应得严丝合缝。这既是洪堡的“修身”理想之意蕴,亦契合杜威及其弟子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所倡导的“项目教学法”(Project Method)[24],即唤醒并增强个体的精神力量,进而在团队、社区乃至全球合作中认识并改造世界。由此,洪堡的“修身”理想之两大维度,即知与德,在当下得以激活,重获新生。
洪堡的未来
行文至此,须重返始终未能释义的“修身”概念。“修身”是目的还是手段,是状态还是过程,学界至今各执一词。从目的论出发,洪堡主张状态,即有修养(gebildet sein),但更倾向于目的,即有修养者(Gebildeter)或知识精英市民。承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之衣钵的洪堡把“修身”概念建立在康德“成人”(Mündigkeit)理念基石之上,视“修身”为成人即人的完成的必要前提[25]。自由、自主、自觉地与世界互动,在找回自我同一性之际铸就个性,走向完人。完人乃成人进程的终极目标。在1792年撰写的论文《关于尝试确定国家权力边界的几点思考》(Ideen zu einem Versuch,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中,洪堡写道:“人的真正目的就是……在坚如磐石的理性的感召下,精神力量最崇高与最和谐的绽放,由此成为一个全人。这种绽放的首要并必要的前提是自由。”这里的“绽放”,洪堡使用的就是“修身”。绽放,既是过程,也是状态,但肯定不是目的。绽放,由含苞吐萼的花蕾而姹紫嫣红的花朵。显然,全人方为目的,“修身”仅为手段。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视修身为“君子之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路径,被朱熹尊为“入德之门”的《礼记·大学》开篇即言,此乃“大学之道”,终极指向乃“至善”。大学,大人之学、君子之学、圣贤之学。“至善”之境界即庄子所言“内圣外王”。洪堡的“修身”即为中国历代士阶层所遵循的“大学之道”,其使命在于,由“以文化人”而“止于至善”。“至善”实为愿景,如洪堡“修身”理想中的有修养者或知识精英市民所奉为最高表率的古代圣贤。故而,洪堡的“修身”及“大学之道”永远在路上。由此断定,当今大学开设的通识教育,无论未遂洪堡之愿,由中学推延至大学,抑或试图以此为支点来革新大学课程体系抑或颠覆大学育人理念,均无法“止于至善”。洪堡擘画的“修身”理论甚或“修身”哲学之所以作为“修身”理想彪炳史册,正因为其生命力潜隐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性之中。
谨以此文追思今年3月6日去世的恩师、本文第二作者、德国教育学家弗里德里希·W·克罗恩(F riedrich W. Kron)。
注释
①Bildung是德语特有的词汇,在其他任何语言并无对应。国内译界通常把Bildung译为“教育”。当Bildung走进现实,与事业、制度、体系、机构、财政等组合成新词汇,译为“教育”,无可厚非,且绝对精准。然而,德语中另一词汇Erziehung确确实实是教育,且只能作此翻译。在本文的讨论中,Bildung含有教育、教化、陶冶、自我塑造之意,难以用一个准确的中文词汇表达,在此权且译为“修身”。
[1]BENNER D. Wilhelm von Humboldts Bildungstheorie: Eine problemgeschichtliche Studie zum Begründungszusammenhang neuzeitlicher Bildungsreform [M]. Weinheim/München: Juventa, 2003.
[2]FROMM E. Die Herren der Mittwochsgesellschaft: Zur Geschichte der Berliner Aufkl a··rung [M]. Berlin: Luisenst a··dtischer Bildungsverein, 2005.
[3]KELLMANN K. Friedrich Paulsen und das Kaiserreich [M]. Neumünster: Wachholtz, 2010.
[4]FLITNER A, GIEL K.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fünf B a··nden [G].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0.
[5]FRANK M. Einführung in die frühromantische A··sthetik [M].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9.
[6]HILLIARD K, KOHL K. Wort und Schrift - Das Werk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s [G]. Tübingen: Verlag der Franckeschen Stiftungen zu Halle, 2008.
[7]TRABANT J. Weltansichten. Wilhelm von Humboldts Sprachprojekt [M]. München: Beck, 2012.
[8]SCHILLER H-E. Die Sprache der realen Freiheit: Sprache und Sozialphilosophie bei Wilhelm von Humboldt [M]. Würzburg: K o··nigshausen & Neumann, 1998.
[9]ENZENSBERGER U. Georg Forster. Ein Leben in Scherben [M]. München: dtv, 2004.
[10]BENNER D. Die P a··dagogik Herbarts: Eine problemgeschichtlicheEinführung in die Systematik neuzeitlicher P a··dagogik [M]. Weinheim/München: Juventa, 1993.
[11]MENZE C. Die Bildungsreform Wilhelm von Humboldts [M]. Hannover: Schroedel, 1975.
[12]GEIER M. Die Brüder Humboldt [M]. Reinbek: Rowohlt, 2009.
[13]KOHL K.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M]. Stuttgart: Metzler, 2000.
[14]KLAFKI W. Neue Studien zur Bildungstheorie und Didaktik [M]. Weinheim: Beltz, 1991.
[15]ADORNO T W. Gesammelte Schriften 8: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1 [M]. Frankfurt/M.: Suhrkamp, 1972.
[16]ELLWEIN T. Die deutsche Universit a··t.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M]. Wiesbaden: Marix, 1997.
[17]BLANKERTZ H. Die Geschichte der P a··dagogik: Von der Aufkl a··rung bis zur Gegenwart [M]. Wetzlar: Büchse der Pandora, 1982.
[18]SCHLOEMANN J. Von wegen Humboldt! [N]. SZ, 2007-07-11.
[19]GALL L. Wilhelm von Humboldt: Ein Preuβe in der Welt [M]. Berlin: Propyl a··en, 2011.
[20]GEIER M. Die Brüder Humboldt [M]. Hamburg: Rowohlt, 2009
[21]HERRLITZ H G, et al. Deutsche Schulgeschichte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M]. Weinheim/München: Juventa, 2009.
[22]Universit a··t Witten/Herdecke. Studium fundamentale [EB/OL]. [2016-11-20]. http://www.uni-wh.de/studium/studium-fundamentale/.
[23]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 a··t Mainz. Studium Generale [EB/OL]. [2016-11-20]. http://www.studgen-iful.uni-mainz.de/96.php.
[24]KNOLL M. Dewey, Kilpatrick und “progressive”Erziehung: Kritische Studien zur Projektp a··dagogik [M]. Bad Heilbrunn: Klinkhardt, 2011.
[25]KRON F W. Grundwissen P a··dagogik [M]. München/Basel: UTB, 2009.
On the Ideal of Bildung by Wilhelm von Humboldt
YU Ke1,Friedrich W.Kron2
(1.National Bas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2.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University of Mainz,Mainz 55131,Germany)
In commemoration ofthe 250thanniversary ofhis birth,the educationalinheritances of Wilhelm von Humboldt a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among which the Ideal of Bildung rather than the highly-regarded conception of University of Berlin is the mostprecious one.The paper argues thatthe Idealof Bildung,which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Greek Orthodoxy,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blueprintfor educationalreform by Wilhelm von Humboldt.When the Ideal was split from the educational reform blueprint,Humboldt was faced with a dilemma.Taking the Liberal Education in current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for instance,the paper analyzes an attempt to revitalize the Ideal of Bildung.Besides,the paper reveals high similarity between the Ideal of Bildung and the Way of Self-Cultivation proposed by Saints and Sages in Ancient China,whose mission lies in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throughout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by humanistic study.Striving for Perfection is de facto the vision, hence,the Ideal of Bildung and the Way of Self-Cultivation proposed by Saints and Sages in Ancient China are ever-lasting process.Therefore,the vitality of the Ideal of Bildung has being precisely hidden behi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dividual as well.
Wilhelm von Humboldt;Bildung;Ideal of Bildung;Way of Self-Cultivation Proposed by Saints and Sages in Ancient China;Education in Germany
2016-11-21
2014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4YS035);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领导研究创新团队”项目。
俞可,1970年生,男,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基地研究员,教育领导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留德哲学博士,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会荣誉会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从事比较研究;弗里德里希·W·克罗恩(Friedrich W. Kron),1933年生,男,德国美因茨大学教育科学系前系主任,哲学学院前院长,终身教授,德国教育学系列指定教材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顾问兼荣誉教授,从事教育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