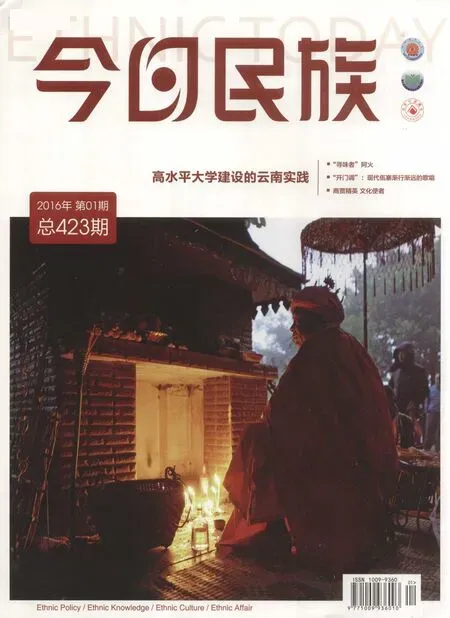探索“非遗”保护的各种途径——以云南经验为中心的学术对话
文·图 / 龙成鹏
探索“非遗”保护的各种途径——以云南经验为中心的学术对话
文·图 / 龙成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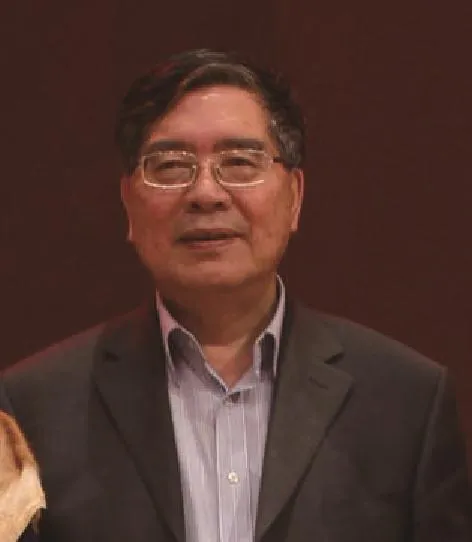
樊祖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谢嘉幸中国传统音乐节艺术总监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郭净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对当代问题有洞察力的民族学者

于坚著名诗人、作家对云南民族文化有独到见解
2015年12月21日至25日,由源生坊主办的首届“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在昆明举行,其间,还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论坛,近三百位民族民间音乐“非遗”传承人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云南“非遗”保护的经验和云南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本刊一直关注“非遗”传承问题,作为此次活动的媒体支持方,我们把活动中几位“非遗”专家和民族学者的核心观点整理发布,以飨读者。
樊祖荫“非遗”保护“在路上”
1993年中央交响乐团作曲家田丰在昆明的安宁市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这是中国第一个保护民族民间音乐的学校。该馆2000年倒闭,次年田丰病逝。由于田丰的开创性工作,此后昆明有了《云南映象》的成功,有了“源生坊”(全称“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这样的民族民间音乐保护组织。
12月24日,“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论坛开始时,播放了云南电视台原纪录片导演、源生坊负责人刘晓津拍摄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纪录片——《传习馆春秋》。下面内容是樊祖荫教授在看完纪录片后的发言:
田丰先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曲家,是我们国家“非遗”保护的开拓者、开创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这个片子中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理想非常清楚,指向非常明白,但作为一个作曲家,他缺乏很好的管理,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果。
这个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今后工作很多的启示。源生坊与传习馆不同,传习馆把传承人请到城市来集中教学,而源生坊则把传承班办在乡村,办在传承人的家里。这样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既继承了田丰的优点,又避免了田丰可能出现的困境。其中的观念就是在本土做“非遗”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是很大的进步。
国家对“非遗”保护的投入不断增加,但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远的如意大利、法国,近的如韩国、日本,对“非遗”的投入都比我们高得多。在现在的条件下,由私人、民间资本投入到这样的事业,我认为这是对“非遗”保护非常好的补充,做了一些政府一下子办不到的事情。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源生坊也有很多很好的创造。比如说,我们对传承人比较重视,但对被传承人还缺乏思考。因此源生坊在这个问题上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我跟着他们去考察过一次,到石屏巴窝村。他们的做法是给传承人和被传承人都发补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它既重视了传承人,又重视了被传承人。被传承人是农民,他不靠这个钱生活,但学了之后,有了这个津贴,可以补助他们误工带来的经济损失,就使他们安心留在农村。既丰富文化,又促进生产,能够使我们的非遗文化活态地传承下去。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当年盛况
我之所以推荐这样的好做法,就是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和了解。因为这对国家有利,我也希望政府、地方、民间加强交流,三位一体做好“非遗”保护工作。
说到全国范围“非遗”保护的情况,据我了解,目前国家正在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城市化背景下进行“非遗”保护的探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提倡城市化,但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我们“非遗”保护可以说还没有跟上。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山上到平地,从游牧改作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到了新的环境,他们原来“非遗”的生活基础没有了,传承就失去了土壤。新疆的哈萨克族牧民,原来是在迁徙当中传承文化,现在集中居住,如何传承成了问题;东北的鄂伦春人从山上下来以后,打猎这样的生产方式没有了。这些问题都是被关注的。我希望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有好的顶层的文化上的设计。这个文化,包括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承。
另外一个,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保护区、保护园区,国家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整顿。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好,有的地方只有一个名,没有实际的工作。有关“非遗”的项目,各地都在申报,国家的投入还在继续增加,相关做法政府也在继续探索。
我们还做一个大的工作,就是申报世界级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又成功申报了几个“非遗”。
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录之后,对具体的保护实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正面的影响较大,列入“非遗”名录,从国家的管理上来说,对“非遗”项目给予更多关注,在资金上会有相应的投入。
但是在地方政府做保护的时候,也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一些项目,比如“花儿”,青海有,甘肃有,新疆也有。现在“花儿”作为国家的项目,保护的名录就叫“花儿”。国家最重点的保护在哪儿呢?没说。那具体的保护就有问题了,各地都在保护,都在做相关的工作,但较难真正落实到保护具体措施上来。另一方面,“非遗”保护落实之后。有些“非遗”,很多地方都有,但国家把这个地方列入重点保护,那个地方没有列入,那没被列入的地方可能关注和资金较少,保护也就落空了。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丽江国家级“非遗”项目白沙细乐收徒授艺
谢嘉幸“非遗”保护的四种生态和三个阶段
考察“非遗”现在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简单说有四种生态环境。
第一种是社区文化。第四届全国高校区域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2015年在襄阳举行。会上我发现,一个节目一出场,就可以看出它是由哪种文化生态提供支持。在各种生态中,社区文化是相当强大的。我们第七届“中国传统音乐节”2015年举办了传统文化进社区微视频大赛。全国一共有513个创意作品,有80多种“非遗”和传统文化项目参赛。这个活动促使我们思考社区文化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我们想下一届就搞“非遗”项目进社区。
第二种是民俗文化。凡是民俗活动活跃的地方,它的传统文化的生态就很好。换句话说,我们政府多大程度上鼓励我们的民俗活动,我们的“非遗”保护就会显示出多大的活力。
以上这两种文化生态,是相互融合的,在这种生态环境下,“非遗”项目更多的是自娱自乐。
第三种是旅游生态环境。旅游生态环境下,“非遗”项目原来的语境和文化功能就会发生改变,“非遗”自身也发生改变,它变成了取悦他人的表演。但这种生态环境,对当下的影响很大。
第四种生态是校园文化。我们从1999年就提出让每个学生唱一支自己家乡的歌,这个项目2010年获得国际音乐教育大奖。校园是“非遗”保护特别重要的场所,我这里介绍下挪威的经验。在挪威,所有的民间音乐都到每一所学校去表演,每年每个学校至少要有两场,这是他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国策,我们也争取要有这样的活动,我希望“非遗”能够进入学校文化传承的主渠道。
我们国家“非遗”保护起步较晚,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初步收集整理阶段。我们就把民歌收集起来,整理成谱子,弄点录音就完了。
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意识到了要传承,要活态传承。“传习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它的问题是它已经离开了它的文化环境。
第三个阶段是传统文化的整体复兴阶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以后,我们文化研究的尺度放宽。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做这个“非遗”保护?在我看来就是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当代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所有力量结合起来。
在第三阶段,核心的问题是要恢复我们的民间信仰,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恢复原来由乡绅阶层来支撑的民间和社区的功能。这个任务在各位身上。这个阶段的任务要复杂得多。
现在民间话语和官方传统的话语正在拉近距离,这是对传统文化保护有利的现象。2014年11月份,首届“华夏乐府”论坛,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乐府,中宣部的王世明副部长参加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我们现在所做的音乐遗产的保护,在传统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板块。我们的音乐歌舞保护好了,我们传统文化的整体复兴才能有望。反过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又为音乐歌舞的保护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个人,一遇到我们这些传承人,50步就要敬礼,那我们的“非遗”保护就不再是一个难题。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1993-2000)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的“非遗”传承学校,它在城市办学的模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郭净探索“非遗”保护的各种可能性
各个民族,你教我,我教你
源生坊举办的这个艺术节像一个学校,把这么多的老师请到这里,大家互相交流,这样很好。各个民族,你教我,我教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教育形式。
这次的艺术节跟很多艺术节非常不一样。我们看到的很多艺术节,包括电视上的选秀,是演给别人看的。而我们这次的艺术节,是演给我们自己看的。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聚在这里。来看表演的,在场的没有一个是游客,为什么大家还兴致勃勃呢?因为我们探讨的是我们文化怎么传下去的问题。因此各位传承人回去以后,你们的任务还很重。

卡瓦博格文化社在探索藏族社区文化保护时做了多种尝试,图为他们做的村民摄影师项目
歌舞艺术的背后,是整个民族的生活
现在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受到了各种外来冲击。 如何让孩子懂得自己的文化,这是大家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巫师”,你们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你们以前是怎么做你们的教育的?你们用宗教的形式,用家庭教育的形式,去传承给后代。这个大家要重新来考虑,因为我们看到的歌舞艺术的背后,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如果没有祭祀活动,你们祭祀的歌就不在了;如果没有节日,你们只表演给游客看,你们的那些乐器、音乐也就变样了。
我们“非遗”保护有各种可能性
应该说有很多地方的传承工作做得非常好。比如像卡瓦格博文化社,源生坊下面这些艺人在各个村寨做的普及班、提高班,还有各地的文化局、文化馆、文化站所做的各种艺术培训,这些方式将来都可以互相交流。甚至,像今天这样的艺术节,除了在昆明办,可不可以在丽江办、在红河办、在佤族地区办呢?我想经过这样的交流,会给大家一些启发。
我们“非遗”保护有各种可能性,大家回去之后,在村子里,在县城都可以做自己的尝试,将来我们再交流的时候,会看到新的成果。
于坚来自云南高原诸神的盛会
“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这4天以来的活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大事,不仅仅是云南的,也是整个世界的。我去过世界的很多地方,而且不是去一次,是去好多次,所以,我说这个话一点也不夸张。
这个是为什么?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伟大的艺人,都是大师。都是云南高原上,几千年几百年民族文化培养出来的大师。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对云南民族文化的认识,停留在一个非常粗浅的,简单的,粗糙的层面。很多年来,人们总是把云南高山中的各民族的文化认为是落后的,愚昧的,迷信的,在改革开放以前,这种文化是被压制的。只有到了今天才开始有少数人真正意识到云南民族文化重要的价值,这种文化全世界都非常罕见了。
一个民族不能只是吃饭穿衣就完了,它必须有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什么?就是要好玩嘛。要不然你的生命怎么度过呢?你的漫长的生命,总不能只是吃饭睡觉。你必须要有这些音乐家、艺术家,这些部落中的精神领袖来指引。我认为在座的诸位,水平远远地高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是你们民族的精神领袖。
在一百两百年前,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巫师,在今天,汽车、收音机、电视机、现代化把这种文化慢慢消灭掉了。特别是在欧洲,我90年代去欧洲,我跟很多的诗人艺术家在一起,他们非常悲伤地告诉我,他们那个地方没有少数民族,因为少数民族在过去几百年,一神教、理性化的过程中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
为什么我要说这是世界文化的大事?因为要把这么多的精神领袖、巫师、大师,聚聚在一起,搞那么一个节日,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是不可能的。这是那么多年,我看到的唯一一次,让我非常激动。
我觉得在座的都是伟大的鲍勃·迪伦,你们就是蓝调,布鲁斯。如果要讲什么是蓝调,什么是布鲁斯,我觉得课堂上讲不清楚,但在这里,我完全能够听明白。云南高原上天生的蓝调,天生的布鲁斯。我刚才跟岩兵大师说,你们的音乐使我内心充满了幸福、爱和喜悦。这是在招魂啊!他们的音乐和舞蹈唤醒了我,我有被复活的感觉,就像从教堂出来一样。
我的意思不是说,高山中的每个民族不能够有现代化的生活,那也是必须的。公路是要有的,电视机是要有的,但是,仅仅只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人不能够活着就为了看电视,人必须有精神生活,生命要好玩。玩不是玩物丧志,玩是守住本真,开始意识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玩这个字,就是由玉字和元字组成。大师们唱的史诗,讲的就是这个嘛。不要忘记人的开端。
在座的大师,来到昆明,昆明虽然很丰富,但也很乏味呵。有一位大师,要吹他的树叶笛,但那种树叶在昆明很难找。如果现代化的结果是我们再也不能唱歌,再也不能跳舞,失去了灵魂,只有日复一日地挣钱购物看电视,那这样的生活太乏味,是活着的死亡。
云南高山中的各个民族还保留着那些伟大的祭典,这个艺术节很了不起,刘晓津(活动主办者)积了大德。这个活动让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什么东西不能丢掉,永远也不能丢掉。在这方面已经很危险,中国越来越不好玩了,特别是内地,同质化,千篇一律很普遍,越来越乏味了,拜物教席卷诸多领域,我们丢掉的东西已经非常多了。而云南高山中的各个民族,还依然保存着那种伟大的精神力量,非常了不起,一个奇迹。横断山脉进行了伟大的抵抗,固守,就像古代一样。
我不知道将来你们会怎样做,我担心的是,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要举行这样的大会是不可能了。在座的大部分是老人,中国舞台现在是青春崇拜,他们还要老人吗?大师都是老的啊!我们也许将完全最终沦入物质主义,人性异化的社会,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每个人的价值,就以货币的占有量来衡量。而我认为在座诸位最了不起的是不在乎钱,而是声音,舞蹈,乐器,歌喉,招魂的魅力,是它们显示出人的尊严,人性的魅力,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最高价值。
这个艺术节最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怎么样才能让高山中的每个民族,既过上他们自己希望的温饱的生活,但是又保持了纯粹,独立,古典的民族民间艺术,保持那种招魂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在座的刘晓津、郭净要思考的,也是在座的各位大师要思考的,也是你们要给年轻一代交代的。生活的意义何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责任编辑 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