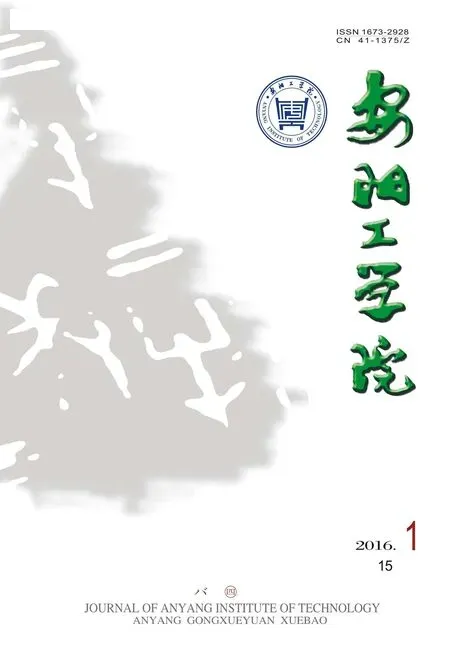“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象征关系研究
王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象征关系研究
王鑫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在认知语法的理论框架下研究“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的象征关系发现,“给”字结构“NP1+V+ 给+NP2+NP3”和其语义结构“施事+动作+与事+受事”之间的象征关系是通过“自主/依存联结”实现的。运用“新自主/依存联结”分析模型分析了“NP1+V+给+NP2+NP3”的语义合成过程,以期对其语义建构机制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NP1+V+给+NP2+NP3;象征关系;语义建构
“给”字句是汉语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句式,它有多种变体,充分体现了汉语句式的灵活性,NP1+ V+给+NP2+NP3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给”字句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以往对“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的研究散见于“给”字句的研究之中,主要包括:朱德熙(1979)认为大部分出现在NP1+V+给+NP2+NP3结构中的动词的词汇意义中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语义成分——给予。他将“给予”描述为:1)存在着“与者”(A)和“受者”(B)双方;2)存在着“与者”所与亦即“受者”所受的事物(C);3)A主动地使C由A转移至B。袁明军(1997)把进入“V给”的动词按照语义特征分成三类,分别是[传递]、[给予]和[位移],并各自细化为四个语义因子(房晓蓓,2010)。沈家煊(1999)从句式的整体意义出发对“给”字句进行了阐释,指出,一个句式是一个完形,即是一个整体结构。他将“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的句式意义解释为“惠予事物转移并达到某终点,转移和达到是一个统一过程”。周长银(2000)以Larson(1988)中的Larson壳为句法推导基础,从句式转换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的“给”字句进行了研究,认为“给”字结构NP1+给+NP2+NP3的生成需要根据Larson中的重新分析规则,将Larson壳中的内层V’重新分为V后再作动词提升才可完成。刘丹青(2001)以语言类型学的理论为依托考察了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认为“V给”句因“给+与事”直接插在动词和直接宾语之间而背离了观念距离象似性原则,这点又由“给”的介词性弱化而得到补偿;延俊荣(2003)证明了“V给”的语义属性,然后讨论了“V给”的引申途径;房晓蓓(2010)把“V给”句的动词分为六类,归纳出了主语NP1、NP3和NP2的分类及语义特征并考察了“V给”句的句式特征。
纵观以前的研究,我们发现,对“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从传统的句法-语义描写的角度开展得较多,从认知角度开展的研究尚不多见。诚然,先前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的句法、语义结构的认识,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启发意义。然而,传统的句法-语义描写法给动词分小类的做法忽略了构式的整体意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只重视该结构的整体意义固然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却又对结构中各组成成分的贡献重视不足。此外,生成语法认为,该结构式是从某种原始的底层结构转换而来的观点,未能认识到该结构独立存在的价值。关于结构NP1+V+给+NP2+NP3的研究,有些方面还是悬而未决或者鲜有论及。比如该结构中的各个要素NP1、V、给、NP2和NP3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或者说,该结构中的各个成分是如何联接成一个语义完型的?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NP1+V给+NP2+NP3的句法结构特征
从句法上看,1)主语“NP1”一般由代词或者名词充当,“V给”是谓语部分,V由及物动词充当,多为单音节词,如“卖”“送”“寄”等,也有少数双音节词,如“贡献”“赠送”等,间接宾语“NP2”一般由名词或者代词充当,直接宾语NP3常常采用“数+量+名词”的形式。2)“NP1”和后面的成分偶尔可以用逗号隔开,如①;也可以加一些修饰性成分,如②中的“从费城”和③中的“还珍重地”。3)“V给”后可以加体助词“了”。外在的体助词“了”是对事件“有界性”的加强(延俊荣,2003),如④。4)当“V”是本身含有“给予”义的动词时,“给”可以省略,例如⑤。(文中语料均来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①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读者唯恐本书夭折,寄给我两千元钱。
②美国朋友从费城[寄给]郑小瑛一张当地载有纪念这位老人文章的报纸。
③布托夫人还珍重地送给我一本她的专著。
④朱棣看罢图、表很高兴,下令赐酒赏钱,还送给了廖均卿50斤鱼、50斤猪肉。
⑤老金说:“我送你们一副对联:上联是‘梁上君子’,下联是‘林下美人’。”
二、NP1+V+给+NP2+NP3语义特征
NP1+V+给+NP2+NP3的语义结构可以大致描写为“施事+动作+与事+受事”。
1)施事“NP1”一般指人,有时也可以指转喻的人,如机构等,如⑥。与事“NP2”只能是人,或转喻的人,如⑦。受事“NP3”一般指物,可以是具体的物,如⑧;也可以是抽象的物,如⑨。
⑥一汽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这部车。
⑦国家加快退还给企业应退的增值税。
⑧送给我们一包关于周公的书。
⑨或是他的家庭遗传给他当时战争所造成的某种心理缺陷。
2)谓语部分“V给”。出现在“V给”中的V的原型是给予类动词“卖”类。此外,非给予类动词:“寄”类“写”类和“炒”类也可以出现在该结构中。事实上,从典型的给予动词到典型的非给予动词这两端之间是一个连续统(沈家煊,1999:96)。“V给”的“给予”义主要来自动词“给”,“V”只是“给予”的方式或途径(严俊荣,2003)。例如在“他送给我一本书/小王卖给他一辆车”中,“送”和“卖”都只是“给”的方式(邵敬敏,2009:2)。
延俊荣(2003)将NP1、NP2、NP3和“V给”的语义特征分别描述为[+有生性][+自主性][+使因性]、[+有生性][+终点性]、[+受动性][+位移性][+自立的] 和[+方向性][+终点性][+途径性]。
3)NP1+V+给+NP2+NP3的构式义。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子。一个构式的构式义是一个完型,不是构式各成分意义的简单加合。(Goldberg, 1995:2)需要指出的是,说一个构式的构式义不是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并不意味着构式的构式义与其组成成分的意义毫不相干。相反,一个语言表达式的语义就是通过动词的语义和构式的语义相互作用生成的(牛保义,2015: 17)。构式与动词存在着互动。按照构式语法的思想,本文认为,“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的语义是构式和动词“V给”的语义相互作用的产物。
构式NP1+V+给+NP2+NP3的意义离不开“V给”等各组成部分的贡献,但该构式的意义又不是这些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该构式是双宾语句的一个次类,根据构式语法中动词和构式的互动观,结构NP1+V+给+NP2+NP3的构式义为“NP1通过动作V的方式或途径致使NP2收到NP3”。
三、NP1+V+给+NP2+NP3的象征关系分析
认知语法认为,语法是象征性的(symbolic),语法是语义内容的象征化(Langacker,1987:12;牛保义,2008:3)。一个象征单位是音位结构和语义结构组成的,音位结构同语义结构是象征关系。基于这一理论指导,我们可以将NP1+V+给+NP2+NP3看作是一个象征单位,其象征关系如图1所示。

图1构式NP1+V+给+NP2+NP3的象征关系
图1读作,“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中,句法成分NP1、V给、NP2和NP3分别象征语义成分施事、给予、与事和受事,同时,句法合成结构NP1+V+给+NP2+NP3象征着语义合成结构“施事+给予+与事+受事”。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给”字结构NP1+V+给+ NP2+NP3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是怎样建立起象征关系的呢?根据认知语法的理论,概念化是一个认知过程,是认知过程所表现出的某个(些)规律或特征。一个语言表达式的句法结构形式正是这样的认知规律和特征在语言中的投射(牛保义,2008:4)。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尝试运用“新自主/依存联结(autonomous /dependency alignment)分析模型”来探讨“给”字结构NP1+V+ 给+NP2+NP3的认知规律和特征,以期对“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的句法结构语义功能之间的象征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新自主/依存联接分析模型
根据Langacker(1987)认知语法的配价思想,牛保义(2010)对自主/依存联接分析模型(2008)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建立了新自主/依存联接分析模型(图2)。

图2新自主/依存联接分析模型
该分析模型将一个合成结构表达式的生成过程表述为:在一个合成结构中,各成分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自主成分,有的是依存成分。在一个自主成分与一个依存成分联结的过程中,依存成分D的语义凸显一个次结构,提供一个阐释位e;自主成分A的语义凸显对依存成分提供的阐释位进行阐释,即二者建立对应关系。可以说,正是由于自主成分的凸显和依存成分的凸显在概念上的重合或对应,才使得一个合成结构成为一个完型。
(二)NP1+V+给+NP2+NP3的语义概念化
1. NP1+V+给+NP2+NP3的语义建构模型
按照新自主/依存联接分析模型,笔者认为“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的语义建构依赖其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结。在该结构中,NP1、NP2和NP3是概念自主成分,动词“V给”是概念依存成分。“V给”凸显一个图式性射体和图式性界标,提供两个阐释位。NP1语义凸显对“V给”凸显的图式性射体进行阐释,NP2对“V给”凸显的图式性界标进行阐释。NP1和NP2的语义凸显分别对应于“V给”的射体和界标,即NP1和NP2的语义凸显分别同“V给”的射体和界标在概念上重合,三者整合成一个合成结构“NP1+ V+给+ NP2”。概念依存成分“NP1+ V+给+ NP2”凸显一个图式性的界标,NP3的语义凸显对“NP1+ V+给+ NP2”的图式性界标进行阐释并在概念上重合,二者联结成合成结构“NP1 +V+给+NP2 +NP3”。“NP1 +V+给+ NP2 +NP3”继承“V+给”的语义凸显,将NP1、NP2 和NP3分别识解为““施事”“与事”和“受事”论元。这一分析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NP1+V+给+NP2+NP3的语义联结模型
(二)NP1+V+给+NP2+NP3的语义建构实例分析
⑩宋教仁回乡探母时,袁(袁世凯)送给宋教仁一张50万元支票,也被宋退还。
按照上面的分析模型,依存成分“送给”凸显一个次结构射体和一个次结构界标,提供两个阐释位。自主成分“袁世凯”凸显一个次结构“有能力实施‘送’行为的实体”,将“送给”凸显的射体阐释为“一个称为‘袁世凯’的,有能力实施‘送’行为的实体”。同时,自主成分“宋教仁”语义凸显的一个次结构“有能力接受‘送给’行为的实体”将“送给”凸显的一个次结构界标阐释为“一个称为‘宋教仁’的,有能力接受‘送’行为的实体”。自主成分“袁世凯”的语义凸显对应于依存成分“送给”凸显的次结构射体,或者说自主成分“袁世凯”的语义凸显与依存成分“送给”凸显的次结构射体在概念上重合,“宋教仁”的语义凸显与依存成分“送给”凸显的次结构界标在概念上重合,三者整合为合成结构“袁世凯送给宋教仁”。“袁世凯送(给)宋教仁”作为依存成分,凸显一个次结构界标,即送给的是什么。自主成分“书”的语义凸显“有封面、封底和内容、可以被购买、赠送、阅读等的实体”将“袁世凯送给宋教仁”凸显的次结构界标阐释为“有封面、封底和内容、可以被购买、赠送、阅读等的实体”。自主成分“书”的语义凸显对应于“袁世凯送(给)宋教仁”的次结构界标,二者整合成合成结构“袁世凯送给宋教仁一本书”。这一合成结构继承“送给”的语义凸显,将“袁世凯”“宋教仁”和“书”分别识解为“施事”“与事”和“受事”论元。上面的分析如图4所示。

图4“袁世凯送(给)宋教仁”的语义联结
又如,
在该结构中,“舒婷”“你”和“信”是概念自主成分,“写给”是概念依存成分。按照自主/依存联接分析模型,“写给”凸显一个过程,提供了两个阐释位:射体和界标,即写的人和写的东西。自主成分“舒婷”凸显的次结构“有能力写的实体”和“信”的凸显“可以被写的实体”分别对“写给”提供的射体和界标进行阐释,即“舒婷”凸显的次结构“有能力写的实体”和“信”的凸显“可以被写的实体”分别对应于“写给”提供的射体和界标,从而构成下层合成结构“舒婷写给一封信”;“舒婷写给一封信”作为依存性成分,凸显一个次结构界标:接收所写信件的人。“你”的凸显的次结构“一个能够接受信件的人”对这一界标进行阐释,从而构成合成结构“舒婷写给你一封信”。这一合成结构继承“写给”的语义凸显,将“舒婷”“你”和“信”分别识解为“施事”“与事”和“受事”论元,表示“施事+动作+与事+受事”的动作关系。上面的分析如图5所示。

图5“舒婷写给你”的语义联结
四、结语
本文在认知语法配价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新自主/依存联结”分析模型对“给”字结构NP1+V+ 给+NP2+NP3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象征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给”字结构NP1+V+给+NP2+ NP3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象征关系是通过自主/依存联结实现的。结构NP1+V+给+NP2+ NP3的语义概念化是通过依存成分“V给”的语义凸显的次结构和自主成分NP1、NP2和NP3的语义凸显之间的对应或者概念重合实现的。这一发现表明,一个句法结构的语义和其组成部分的语义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牛保义,2008:6)。因此,我们要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起来,既要重视一个表达式的整体构式义,又要重视构式各组成部分对整体构式义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对句子的合格性作出充分的解释(沈家煊,2000:293)。
参考文献:
[1]房晓蓓.“V给”句复合生成机制探索[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2]刘丹青.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J].中国语文,2001(5):387-398.
[3]牛保义.“知道的……不知道的……”是隐喻吗? [J]外国语,2015(3):12-23.
[4]牛保义.英汉语工具主语句的象征关系研究[J].外语教学,2008(1):1-7.
[5]牛保义.新自主/依存联结分析模型的建构与应用[J].现代外语,2011(3):230-236.
[6]邵敬敏.从“V给”句式的类化看语义的决定性原则[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6)1-8.
[7]沈家煊.“在”字句和“给”字句[J].中国语文,1999(2):94-102.
[8]沈家煊.句式和配价[J].中国语文,2000(4):291-297.
[9]延俊荣.给予句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3.
[10]周长银.现代汉语给字句的生成句法研究[J].当代语言学,2000(3):155-167.
[11]朱德熙.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173-182.
[12] GOLDBERG A E.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13] LANGACKER R 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I [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责任编辑:陈丽娟)
作者简介:王鑫(1981-),女,商丘宁陵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认知语法的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研究项目“‘给’字结构NP1+V+给+NP2+Np3的认知语法研究”(项目编号:2015-QN-508);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基于‘实践共同体’的河南省农村初中英语教师队伍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5-JSJYLX-005);河南大学第十五批教学改革项目“语料库辅助的英语语法课教学模式改革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0-26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16)01-00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