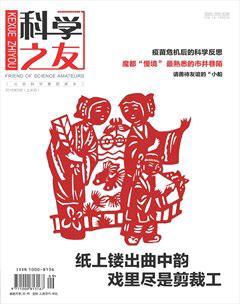绛州绝艺:方寸薄纸上舞出的“凝固之戏”
行走在山西省新绛县这片文化沃土上,在龙香村聆听“龙见于绛郊”的神话,到龙兴镇寻访《弟子规》诞生地,登龙兴寺瞻仰闻名于世的“碧落碑”,欣赏誉满华夏的绛州鼓乐……文化根脉流淌出鲜活的乳汁,滋润着这方充满勃勃生机的土地。
新绛在历史上享有“七十二行城”的美誉,各类民间工艺品繁花似锦,刻瓷绘画、刺绣剪纸、皮影、木雕、石雕、云雕、漆器等异彩纷呈。以新绛剪纸艺术馆为例,馆内由当地民间艺人创作的《弟子规》《庄嫁姐妹》等作品,可谓巧夺天工。
戏曲跟风 也来剪一剪
新绛县地处汾河与黄河交汇处,当年曾经是晋南一个繁华的水旱码头。轻纺工业和民间手工艺品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出口商品。工商业的发达,促使集市贸易活跃,逢集、赶会、迎神、唱戏等频繁的文化活动,使新绛成为远近闻名的“戏曲之乡”。新绛剪纸就产生在这个“戏曲之乡”的土壤之中。各种精湛的剪纸作品也随之充分体现了以戏曲见长的特点。由于剪纸艺人看的戏多,懂戏、识戏,摸透了戏曲艺术的表演形式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剪纸作品,自然会更生动而别具地方风味。新绛剪纸讲究以意造型,作品充分体现了剪刀的工具性。由于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同一出戏,不同的艺人会剪出不同的造型,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度概括和夸张。他们用这种形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这就形成了新绛剪纸粗犷中见典雅、简练而不简单、简洁而又明快的风格。作品多以单色为主,黑白相间,具有版画黑白之美和厚重稳健之感。
作为植根于民俗活动的传统装饰艺术,新绛剪纸分布广泛。清代流传下来的剪纸艺术的实物和文献很多,像剪纸薰样、刺绣花样稿本、佛前挂钱、礼品花、嫁妆花、走马灯人等。剪纸艺术不仅用以婚嫁喜庆、传统节令美化居室,又可用作服饰、鞋、帽、枕头等刺绣的底样,还可用作独立的欣赏品。因此,剪纸已成为极受民众喜爱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成了一种极为普及的民俗现象,历经数代更加多姿多彩,妙趣横生。
纸上万象 巧妇轻松“裁”

民间剪纸和织绣品一般出于农家妇女之手。中国古代的女子,根据传统文化的要求,在闺中待字时要从事女红,亦即进行描画、针线、纺织一类的手工作业,从而培养自己的性格与爱好,同时也锻炼自己手和心的灵巧程度,为成人以后挑起生活担子做准备。剪纸和织绣品,就是女红的一部分。这种风气在民间长期保存下来,因此,多数农家妇女通常都会从事这类手工艺术创作。由于明清时期戏曲娱乐几乎可以说是农村女子唯一的娱乐样式,因此她们对于生活的理解,进而对于生活的描绘,自然就有很多是出之于戏曲,并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民间戏曲工艺品。
每到新年前后,在新绛农村就可以看到,不分老少的村妇在床头、院落围坐在一起,小巧的剪刀在她们手中转动飞舞,一会儿工夫,手中的一叠纸张便绘制成一幅幅精美的画图,鲜艳的花朵、开屏的孔雀、十二生肖的动物、孩子活动的场景……刻画得活灵活现,让人目不暇接。当人们为这些技艺叫绝时,她们自己则显得十分平淡:“这没有什么?从小就会。”
大不盈尺 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新绛剪纸之所以能够跻身于全国民间美术之林,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主要是以它的戏曲人物作品而自立于世的,不但数量可观,关键是自成体系,高手云集,名作荟萃。她们不只熟练地掌握传统民俗剪纸技法,对表现民间传说、戏曲故事也很得心应手,而且更喜欢取材现实生活中的人与情。
民间艺术家的文化素质不同于文人知书识理的修养。中国老百姓过去不识字的多,不知戏的少。他们从戏里了解民族历史、民族精神,那就是精忠爱国、憎恶奸佞、清廉正直、果敢为仁、打抱不平、为民请命等,当然也包括那些神话传说、爱情故事。新绛剪纸以戏曲人物为母本、戏曲为父本,是集二者之大成的“优生儿”,既不同于历代文人画,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画;既非对自我的表现,也非对自然的模拟,而是千百年来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集体创造和艺术积累。剪纸艺人们的作品如同中国戏曲和中国画,是以形象来传神达意的,总是得其意、忘其形,她们选取画龙点睛之处和最能引人入画的瞬间场面,使之动静相融、虚实相生,这时整个布局已不再是“肖像”画了。艺人们通常会选用最少的舞台场面,以最少的线条,取得最好的艺术效果。舞台可以“三五步行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剪纸则大不盈尺,不需要像舞台表演那样还要假定的虚中见实、静中见动,而是把多视点浓缩到一瞬间。因此,作者若没有一定的观察力和凝聚力,很难高人一筹。艺人们“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运用剪纸的朦胧美,以大写意手法,使特定情境的剧中人物维妙维肖,达到“有即无、无即有,一等于无限,无限凝聚于一”的艺术效果。
其实,这种美学理论不用远溯上古,新绛戏曲剪纸里的《包公》《劈山救母》《状元拜塔》等,就是这样的好作品,它们变形夸张,不失其真、不失其美,无论怎样抽象、荒诞,也不管怎样千变万化,都能使人一目了然,能把作者、人物和观众的感情凝聚在一起,进而引起共鸣。
联手破冰 众人拾柴火焰高

20世纪80年代,段吉庆曾带领新绛已故老艺人苏兰花、辛百巧、赵喜梅等参加山西省首届民间剪纸大会剪,获一等奖。并先后在中国美术馆、重庆、成都、西安、太原等地巡回展出,被誉为“民间美术的一朵奇葩”。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美术丛书》2《新绛剪纸》选编了新绛108位作者的308幅作品。令人担忧的是,老一辈剪纸守望者陆续谢世,所剩寥寥,剪纸艺术后继乏人,特别是一些剪纸发源地,产销流程中依然固守传统观念,只在春节前后投放市场,用于渲染“年味儿”,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剪纸无奈处于“被冷落状态”,正像文物专家所说,如果不更新观念,不关注保护古文化的传承,这些古文化将渐渐消失,前景堪忧。如今,在有识的文化界人士大力呼吁,多方奔走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种古老的手工制作艺术得以延续,逐渐受到人们关注。目前,新绛剪纸经过挖掘、整理、培训剪纸爱好者,开展剪纸进校园等活动,剪纸队伍得以发展壮大,正一步步走向繁荣。